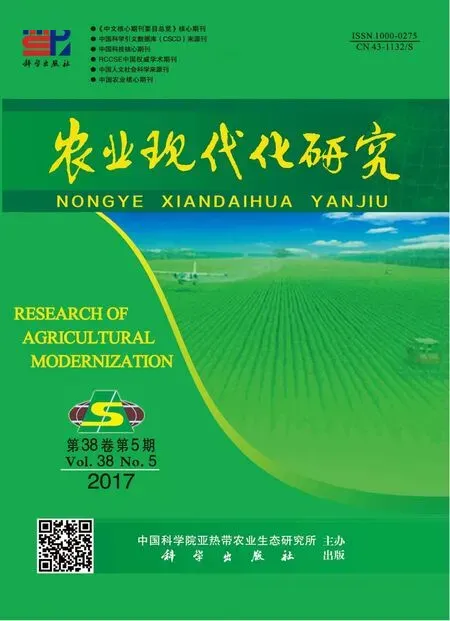公平與安全對農民工社會融入的影響研究
——基于生活滿意和經濟收入的作用
楊春江,田鵬妹,陳亞碩
(1. 燕山大學經濟管理學院/現代旅游產業與組織發展研究所,河北 秦皇島 066004;2. 煙臺南山學院,山東 煙臺 265713)
公平與安全對農民工社會融入的影響研究
——基于生活滿意和經濟收入的作用
楊春江1,2,田鵬妹1,陳亞碩1
(1. 燕山大學經濟管理學院/現代旅游產業與組織發展研究所,河北 秦皇島 066004;2. 煙臺南山學院,山東 煙臺 265713)
作為城市的新移民,農民工的社會融入問題日益受到社會各界的關注。基于社會比較理論、需求層次理論和社會階層理論,以河北省秦皇島、唐山、保定和石家莊4個城市的農民工為研究對象,應用結構方程模型,分析了公平感和安全感對農民工社會融入的影響,及其間生活滿意的中介效應和經濟收入的調節效應,探討其整個過程的心理作用機制和邊界條件。結果表明,生活滿意在公平感對社會融入的影響過程中起著部分中介作用;生活滿意在安全感對社會融入的影響過程中起到了完全中介的作用;經濟收入負向調節公平感和安全感與生活滿意的關系,即經濟收入越高,上述關系越弱。可見,公平感和安全感會影響農民工的社會融入程度,其影響多是通過心理評價活動來間接產生的。因此,政府應著重關注社會公平和安全體系的建設,維護農民工合法權益,關注其心理健康,使之以一個積極的心態融入城市生活。
農民工;公平感;安全感;社會融入;經濟收入;生活滿意
Abstract:As city’s new migrants, the social inclusion issues of migrant workers have become a big concern by different interest groups of the whole society. Based on a survey data of 310 migrant workers of Qinhuangdao, Tangshan,Baoding and Shijiazhuang in Hebei Province, and applying the social comparison theory, the demand hierarchy theory,and the social stratification theory, this paper constructed a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to analyze the influences of the perception of fairness and security of migrant workers on their social inclusion in cities, and specifically, the mediating effects of life satisfaction and the moderating effects of economic income. Results show that: 1) life satisfaction partially mediat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erception of fairness and social inclusion; 2) life satisfaction fully mediat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erception of security and social inclusion; and 3) economic income negatively moderat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independent variables and social inclusion. In summary, the perception of fairness and security would affect the social inclusion of migrant workers, and the influence was indirectly generated through the psychological evaluation activities. Therefore, to guide migrant workers to integrate into city life with a positive attitude,the Government should focus on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 fairness and security system, safeguard the legitimat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migrant workers, and pay attention to their mental health.
Key words:migrant workers; perception of social fairness; perception of social security; social inclusion; economic income; life satisfaction
改革開放以來,城—鄉關系從之前的相互隔離、排斥和對立的封閉狀態,逐漸演變為當今的相互流動、兼容與合作的開放狀態[1]。但這種關系并非對等,更多地表現為城鄉要素向城市的單向流動,最典型的是勞動力向城市聚集[2]。城市生活富裕,資源充足,經濟收入相對較高,加之工業與服務業對勞動力的巨大需求,促使越來越多的農村剩余勞動力向城市轉移,形成了浩浩蕩蕩的“民工潮”。農村勞動力進城務工,既能夠提高剩余勞動力的就業率,增加經濟收入,也能夠彌補城市勞動力缺口,推動城鎮化建設,促進其城市經濟的增長。然而,受限于我國的二元社會體制,農民工普遍存在勞動環境較差、工作時間較長、收入偏低和勞動強度大等問題。他們雖生活在城市社會中,但往往游離于城市邊緣,難以充分享受城市福利并且真正地融入城市生活[3]。他們與城市的矛盾、摩擦和隔閡成為有礙社會和諧穩定的重要因素,不利于和諧社會建設。近年來,農民工的社會融入問題也越發受到國家的重視,為此民政部專門出臺了《關于促進農民工融入城市社區的意見》。由此可見,研究農民工這一龐大群體的社會融入問題對維持社會穩定與構建和諧社會具有重要意義。
鑒于農民工社會融入的重要性,近年來圍繞該主題的研究迅速增加,學者從不同視角對社會融入的影響因素進行辨析和解讀。如朱力[4]、胡杰成[5]、錢文忠和張忠明[6]從社會層面探討了戶籍制度對農民工社會融入的影響。梅亦和龍立榮[7]分析了學歷、普通話水平、身體健康狀況等個體層面因素對農民工社會融入的影響。楊春江等[8]從工作要素視角分析了工作時間和收入對社會融入的影響。社會融入不僅涉及物質生活條件的改善,更涉及社會和精神層面的接納與認同。因此,學界號召從社會心理視角探究農民工的社會融入問題[9-10]。其中社會公平感和安全感的作用尤其受到重視。社會公平感是個體對社會公平程度的整體感知和判斷,即人們以“社會應有的狀況”為基準來評價社會是否符合這一標準,從而做出公平與否的主觀判斷[11]。安全感是個體對危險或風險的預期和可控性感知,通常可區分為確定感和可控制感[12]。個體心理對社會行為有重要的指導作用[13]。在城市化進程中,農民工對周圍環境的認知勢必引發其社會行為和動機,其中便包括他們參與社會活動,進行人際交往的動機與行為。劉電芝等[10]研究發現,城市農民工低層次的安全需要基本得到滿足,萌生更高程度的“融入效能感”和“發展意愿”。王甫勤[14]也指出社會公平感是影響農民工城市融合的重要因素。
綜上所述,以往關于農民工社會融入的研究主要從社會、人口統計特征和工作要素等因素進行分析,相對忽視了農民工心理因素對社會融入的影響。即使少數文獻探討了心理因素的作用,也是淺嘗輒止,缺乏對內在機制和邊界條件的深入分析。為此,本研究基于社會比較、需求層次和社會階層理論,建構生活滿意和經濟收入在安全感與公平感影響社會融入過程中的中介和調節作用模型,在河北省秦皇島、唐山、保定和石家莊4個城市收集了310位農民工的調查數據,運用信度分析、效度分析和結構方程模型方法,分析農民工安全感和公平感對社會融入的影響,生活滿意在兩條路徑中的中介作用,并考慮經濟收入在其間的調節效應。研究結論可以為政府相關部門制定更有效的管理政策提供理論支撐和實施指導。
1 研究模型及研究假設
1.1 社會公平感與社會融入
社會融入是指不同個體、群體或文化之間相互配合與適應的過程[15]。國外主要關注發展中國家移民到發達國家的城市融入狀況[16-17],我國則主要關注農村外出務工人員的城市融入問題。公平理論強調,人們的公平感知會影響對工作和社會的主觀評價,并繼續影響其自身行為。在城市生活的農民工不可避免地會與城市居民發展出雇傭、買賣、親朋等各種社會關系。基于這些關系的互動會形成公平感知,并進而影響上述關系的發展趨勢和強弱程度,同時影響農民工的群體意識和歸屬感。公平感知高的農民工對城市環境有著更高的認同和滿意度[18],看待市民和社會的態度也更為積極和正向,同時也會以一個更加平等和開放的心態參與城市生活,融入現實社會。
作為個體對自身生活質量的總體評價,生活滿意是內在標準與現實感知對比后獲得的主觀感受[19],具體可以通過自身的經濟收入、工作環境、生活條件等途徑來評價。國內關于公平感的研究大多存在于組織層面。史耀疆和崔瑜[20]研究顯示,機會公平對生活滿意具有顯著的作用。劉靜[21]的研究顯示,上班族的社會公平感與主觀幸福感顯著正相關。依據社會比較理論的觀點,農民工群體會自然地將自己的付出和回報與其有接觸的城市居民進行對比。受城鄉二元身份的限制,他們很可能將比較結果歸因于社會體系,形成對社會整體的公平感知,產生對社會生活的評價,并影響接下來的社會互動。倘若比較之后,他們認為付出與回報是相對公平的,便會對現有生活產生積極的評價,對未來也會有更好的預期,以更樂觀的心態投身于社會生活中,從而產生更高的社會融入感。研究表明,積極的主觀認知可以幫助個體緩解精神壓力,調節情緒,增強適應社會的能力[22]。反之,則在消極的生活評價中,逃避社會生活,減少人際交往。張洪霞[23]研究發現,擁有較高心理資本的農民工具有更強的城市融入動機。
1.2 社會安全感與社會融入
依據社會認同理論的觀點,人們會對交往過程中所接觸的社會群體進行分類,從而產生群體歸屬感和認同感,對群體內形成偏好,對群體外呈現偏見。人們普遍具有規避風險的傾向。在感知安全的情況下,人們會以開放的心態嘗試接受新鮮事物,與外界群體進行交流;在感知風險和不安全的情況下,人們則會選擇在群體內部進行社會交往,規避與其他群體交往的不確定性。農民工群體從農村遷徙到城市,生活存在較多的不確定性。不安全感會讓他們將社交圈局限在農民工群體內部,只有在體驗到安全后才會積極地與城市居民互動。
需求層次理論認為,社會需要的滿足是人們追求幸福的重要組成,須以保障安全為前提。可見,社會安全感是人們生活滿意的基礎,并進而影響著人們的社會互動。生活滿意者會以更加樂觀的心境預期未來的生活,以更加包容的態度處理困難和矛盾,以更加積極的行動開展工作和社會交往。閔婕[22]發現,農民工的安全感與生活滿意正相關。馮冬冬等[24]發現,工作不安全感對企業員工的生活滿意有顯著的消極影響。為獲得更多的經濟收入和發展,農民工離開熟悉的農村環境,踏入陌生的城市社會。在這期間居住空間的轉移比較容易,而社會身份的認同和轉變卻是較為困難的[25]。大多數的農民工在經濟收入、社會角色和生存環境等多方面仍處于弱勢地位,其心理安全感較低,更依賴社會體系的保障。安全的社會環境會減少農民工的不確定性,降低生活壓力,促進對生活的積極評價,增加社會交流和提升社會認同。相反,缺乏安全感和較高不確定性的情況下,他們會感受到生活壓力,降低生活滿意水平,進而減少和規避與外界社會的互動,阻礙其融入城市社會。正如李丹和李玉鳳[26]發現,生活滿意是農民工市民化的內在驅動力。
1.3 經濟收入的調節作用
經濟收入很大程度上決定著個體的社會階層,上述作用關系可能受到經濟收入的權變影響。梁波和王海英[27]指出,農民工所擁有的社會資本數量和社會關系網絡質量與規模對其融入城市社會起到關鍵作用。社會階層理論認為,由于在社會資源上的差異,各階層會形成相對穩定的社會認知傾向[28]。對于階層較低者而言,由于占有和可支配的社會資源較少,他們相對會更多地考慮物質成本的問題,因此更需要社會公共資源的支持。與之不同,階層較高者擁有較多社會資源,更容易從社會網絡中獲得支持,對社會公共資源的依賴性相對較低,從而弱化了社會情境因素對個體認知和評價的影響。換言之,社會地位低者有一種情境主義的社會認知傾向,社會地位較高者有一種唯我主義的社會認知傾向[29]。就農民工群體而言,高收入者可以通過購買的方式獲得與城市居民相當的物質生活(如住房、汽車等)和商業服務(如醫療、社會保險等)。較高的經濟收入,能夠降低他們對社會保障和公共服務系統的依賴性,使得他們可以通過自己的力量決定生活質量。因此,社會公平對其影響較弱。低收入者一方面依賴于公共體系來保障生活,另一方面則因戶籍制度和城鄉差異的限制,難以獲得與城市居民相當的社會福利。公共資源需求的迫切,加之需求的難以滿足,使得他們對社會公平性更為敏感,生活評價也更容易受到公平感的影響。
需求層次理論強調人的需求由生理需求向安全、社會、尊重等需求逐級發展,效價也隨之變化。低收入農民工對生理和安全需求較高,使得安全感對他們生活的影響較大;而高收入農民工則更多地關注社會和尊重等需求,使得社會交往和認同對他們生活的影響較大。此外,作為較低層次需要,安全感的滿足更依賴于外部條件。缺乏技術和資源的低收入農民工,生活更依賴社會體系的幫助;具有較好經濟基礎和社會資源的高收入農民工,則更依賴自身的力量改變生活。也就是說,不同收入的農民工對社會安全的敏感性存在不同。低收入者更為敏感,他們對生活的評價更易受到安全感的影響。
綜上所述,社會安全感和公平感會影響農民工的生活滿意,并進而影響社會融入。因此,本文運用結構方程模型,以安全感和公平感為前因變量,以生活滿意為中介變量,以經濟收入為調節變量,構建了農民工社會融入的研究模型(圖1)。

圖1 研究模型Fig.1 Research model
2 研究設計
2.1 問卷與量表
調查問卷包括兩個部分:第一部分是樣本的人口統計變量,包括性別、年齡、婚姻狀況、受教育程度、工作狀況和健康狀況等指標;第二部分是社會公平感、安全感、生活滿意和社會融入的測度項,運用的方法是李克特5級量表。
本研究借鑒以往研究中成熟量表的題項,所有變量均由多題項測量。其中,社會公平感的測度項參考了胡榮和陳斯詩[1]的研究;安全感的測度項參考了李培林和李煒[30]的研究;生活滿意參考了Diener等[31]的研究;社會融入主要參考了胡榮和陳斯詩[1]的研究。最終形成了包括16個測度項的量表,運用SPSS17.0統計軟件進行公平感、安全感、生活滿意和社會融入變量的描述性分析(表1)。

表1 測度項、均值及標準差Table 1 Variables, means, and standard deviations
2.2 數據收集和樣本特征
本研究中的農民工樣本是指狹義的農民工,即生活在城鎮,具有農業戶籍身份,從事第二、三產業勞動,以工資為主要收入來源的從業者。如此限定樣本范圍,主要是考慮到雇主、個體經營者和自我雇傭者在勞動形式、經濟地位等方面與狹義農民工存在顯著差異。
調研區域選擇河北省,主要考慮到這里是我國勞動力輸出和輸入大省,農民工群體集中且較為龐大。具體調研城市包括秦皇島、唐山、保定和石家莊,調研時間在2016年6-8月,選擇農民工集中的餐飲業、建筑業和服務業,以問卷的形式進行實地調查,調查對象涵蓋不同性別、年齡、婚姻狀況和受教育程度的農民工。此次調查共發放問卷358份,剔除掉不合格問卷后,最終得到有效問卷310份,有效率為86.59%。樣本的基本特征見表2。
3 結果與分析
3.1 變量的共同方法偏差檢驗

表2 調查樣本的基本特征統計表Table 2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the sample
本研究采用兩種方法檢驗數據的共同方法偏差。首先,應用Harman單因子檢驗,即將社會公平感、安全感、生活滿意和社會融入4個潛變量合并為一個潛變量,檢驗其擬合程度(模型Ma)[32]。接著,采用不可測量潛在方法因子檢驗,即允許各個題項同時歸屬理論因子和共同方法偏差因子(模型Mb)。模型Ma的擬合指數較差,不可接受;模型Mb與理論模型M0均達到可接受的水平,且Mb各指數未明顯優于M0(表3)。由此可以認為問卷中各個變量間不存在嚴重的共同方法偏差問題。

表3 共同方法偏差檢驗Table 3 Common method bias test
3.2 量表的信效度檢驗分析
應用SPSS17.0計算整體問卷和各分量表的一致性信度,其中整體調查問卷的Cronbach’s α值為0.827,公平感量表的Cronbach’sα值為0.701,安全感量表的Cronbach’sα值為0.787,生活滿意量表的Cronbach’sα值為0.872,社會融入量表的Cronbach’sα值為0.796(表1),均大于0.7,說明問卷的內部穩定性較高,具有較好的可信度。
為了檢驗本研究中所有變量的結構效度,使用MPLUS7.0統計軟件對指標數據進行驗證性因子分析。按照Hair等[33]的研究,x2/df值應在1-3之間,越小越好,RMSEA應小于0.08,CFI和TLI指標應該大于0.8以上,越接近1越好。軟件運行結 果 為:x2/df=1.715,RMSEA=0.048,CFI=0.972,TLI=0.960。所有指數都達到了較好的擬合水平。
為進一步檢驗潛變量間的區別效度,我們在理論模型的基礎上,構建了12個替代模型(M1-M12),分別計算了各個模型數據的擬合指數。由表4數據可知,理論模型M0的擬合水平明顯優于其它替代模型,且達到較優的擬合水平,說明各潛變量測量具有較好的區分效度。

表4 競爭模型適配度比較Table 4 Comparison of measurement models
3.3 各變量的相關分析
相關分析結果(表5)顯示,社會公平感與生活滿意正相關(r=0.197,P<0.01);社會安全感與生活滿意正相關(r=0.494,P<0.01),與社會融入正相關(r=0.171,P<0.01);生活滿意與社會融入正相關(r=0.160,P<0.01)。相關分析初步支持了本研究模型中的變量關系。此外,各潛變量間的相關系數呈中低相關(0.030-0.494),表明本研究的多重共線性問題并不明顯。我們計算了各潛變量的平均抽取方差(AVE)值(表5中對角線數據)均大于0.5,表明判別效度較佳。
3.4 生活滿意的中介作用分析
應用MPLUS7.0軟件對調節—中介假設模型進行檢驗。結果顯示各項擬合指數良好(x2/df=2.314,RMSEA=0.065,CFI=0.949,GFI=0.931),說明理論模型可以接受。
在中介效應檢驗方面,本研究按照方杰等[34]的建議,借助MPLUS7.0統計軟件,使用Bootstrap方法來檢驗生活滿意的中介效應的顯著性(本方法不要求數據符合正態分布,如果路徑系數95%的置信區間沒有包括0,表明中介效應顯著)。由表6的Bootstrap法檢驗結果可見,公平感通過生活滿意來影響社會融入的間接效應為0.136(P=0.009),95%的置信區間為[0.049,0.223]。安全感通過生活滿意對社會融入的間接效應為0.167(P=0.001),95%的置信區間為[0.079,0.254]。以上兩個間接效應的置信區間均不包含0,說明兩條路徑中的中介效應都是顯著的。

表5 各主要變量的均值、標準差和變量間的相關系數Table 5 Means, standard deviations of the main variables and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between variables
由圖2數據可知,在控制中介變量生活滿意的影響之后,公平感對社會融入的直接效應仍然顯著(r=0.093,P<0.05),表明生活滿意在社會公平感對社會融入的影響中起部分中介作用;安全感對社會融入的直接效應不再顯著(r=0.020,P>0.05),表明生活滿意在安全感對社會融入的作用過程中起完全中介作用。

圖2 結構方程模型結果驗證簡圖Fig.2 Result diagram of the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3.5 經濟收入的調節作用分析
為檢驗調節效應,我們構建了自變量(公平感和安全感)、調節項(收入)、交互項(收入×公平感、收入×安全感)通過中介項(生活滿意)對因變量(社會融入)施以影響的路徑模型(圖2)。
圖2的各路徑上標注了標準化后的路徑系數和顯著水平。其中,公平感對生活滿意的標準化路徑系數為0.568(P<0.01),說明公平感對生活滿意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而公平感與收入的交互項對生活滿意的標準化路徑系數是-0.537(P<0.05),說明收入負向調節了公平感對生活滿意的影響,即個體的收入水平越高,公平感對生活滿意的正向關系就越弱。樣本數據支持了經濟收入在公平感對生活滿意影響中的負向調節作用。按照收入的均值加減1倍的標準差區分了高、低收入組,兩組中公平感對生活滿意度影響效果如圖3(左)所示。安全感對生活滿意的標準化路徑系數是0.697(P<0.01),說明安全感對生活滿意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安全感與收入的交互項對生活滿意產生負向影響,其標準化路徑系數是-0.321(P<0.01),說明收入水平越高,安全感對生活滿意的正向關系就越弱,調節效果如圖3(右)所示。
4 結論與啟示
4.1 結論
研究表明,社會公平感和安全感均會影響農民工的社會融入程度。其中,在公平感影響農民工社會融入的過程中,生活滿意起到部分中介作用。一方面,隨著公平感的提高,農民工個體對自身生活感到滿意,從而以更樂觀的心態,積極地投身于社會生活中,產生更高的社會融入感;另一方面,公平也體現在社會參與機會的公允上,直接影響著他們的社會融入。在安全感影響農民工的社會融入過程中,生活滿意起到完全中介作用。安全的社會環境會減少農民工的不確定性,降低其生活壓力,促進他們對生活的積極評價,增加社會交流和提升社會認同。經濟收入負向調節公平感和安全感對生活滿意的作用,即低收入農民工對公平和安全更為敏感,其生活滿意更易受到二者的影響。

圖3 收入調節作用示意圖Fig.3 Schematic diagram of moderation of income
4.2 啟示
改革開放三十年來,農民工背井離鄉,進城務工,辛勤勞動,對社會發展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他們不僅是我國經濟建設的主力軍,更是社會轉型時期的標志,推動了改革開放與現代化建設的進程。現階段如果我們只關注經濟發展而忽視經濟發展過程中的社會問題,忽略整個社會中公民的真實感受,必然造成發展的片面性,無助于社會的和諧穩定[21]。“和諧社會”歸根到底體現為公民對現實社會公平現狀的心理認可[35]。此外,中央一號文件從2003年開始回歸農業。黨和政府連續十幾年聚焦三農問題,在政治會議上多次探討農村、農業、農民的發展,并制定一系列的相關政策來服務三農,保障基層群眾的利益。基于以上思考,本研究立足國家的宏觀方針政策,從改善農民工的社會認知和縮小收入差距兩個層面出發,提出以下建議與對策:
第一,加強對進城務工農民的專業技能培訓,積極引導農民工再學習。農民工從小生活在生產力落后、經濟較為貧困的農村地區,自身文化素養和技能水平相對城市工人較低。經濟適應是農民工立足城市的基礎。通過繼續教育,農民工可以學習到與職業密切相關的技能知識,提高意識,開拓眼界,不再局限于那些高強度、低收入的苦力工作,轉而投向技術層面的工作崗位,縮小與城市居民的收入差距。伴隨科技進步與經濟發展,未來的職業發展必將與更為專業的技能緊密聯系。為了緊跟時代腳步,提高生活滿意,解決現實問題,農民工接受繼續教育是大勢所趨。
第二,改善農民工在城市中的生活和工作環境。個體內心狀態與其周圍環境緊密相關。就農民工而言,生存和工作環境將直接和客觀地影響其在城市生活的主觀感受(包括社會公平感、安全感、生活滿意等)。作為政府有關部門,應不斷完善和大力扶持農民工廉租房制度,為農民工解決居住和社區安全問題,保證從根本上消除他們融入城市的后顧之憂。作為企業,也有責任和義務為農民工提供足夠的薪酬補償和安全穩定的工作環境,保證他們既能夠安心生產,又能夠享受城市生活。
第三,充分重視農民工的心理健康。從熟悉的家鄉環境遷移到陌生的城市生活,農民工面對未知的環境會產生較大的不適應感,從而引發一系列的心理困擾。受自身教育水平較低的限制,農民工缺乏正確處理心理問題的專業知識,不能良好解決自身困惑,甚至會引發負面群體性事件。社會相關部門和機構有義務開辟緩解農民工生活壓力、疏通其心理困擾的渠道,定期為他們進行心理問題的援助和輔導,既要從源頭減少負面事件的發生,又要幫助農民工正確解讀社會事件,順利完成社會融入。
[1]胡榮, 陳斯詩. 農民工的城市融入與公平感[J]. 廈門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2010(4): 97-105.Hu R, Chen S S. Migrant workers’ intergration into city life and their sense of fairness[J]. Journal of Xiamen University (Arts & Social Sciences), 2010(4):97-105.
[2]任鑫, 薛寶貴. 生產要素單向流動對城鄉收入差距的效應研究[J]. 人文雜志, 2016(7): 49-54.Ren X, Xue B G. Study on the effect of one-way flow of production factors on the income gap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J]. The Journal of Humanities,2016(7): 49-54.
[3]張斐. 新生代農民工市民化現狀及影響因素分析[J]. 人口研究, 2011, 35(6): 100-109.Zhang F. The statu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citizenization of new generation rural migrant workers[J]. Population Research, 2011, 35(6): 100-109.
[4]朱力. 論農民工階層的城市適應[J]. 江海學刊, 2002(6):82-88.Zhu L. On the urban adaptability of the peasantworker strata[J]. Jianghai Academic Journal, 2002(6):82-88.
[5]胡杰成. 社會排斥與農民工的城市融入問題[J]. 蘭州學刊,2007(7): 87-90.Hu J C. Social exclusion and the problem of urban inclusion of the peasant-workers[J]. Lanzhou Academic Journal, 2007(7): 87-90.
[6]錢文榮, 張忠明. 農民工在城市社會的融合度問題[J]. 浙江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 2006, 36(4): 115-121.Qian W R, Zhang Z M. The incorpo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in the urban society[J]. Journal of Zhejiang University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2006,36(4): 115-121.
[7]梅亦, 龍立榮. 中國農民工城市融入的問題研究[J]. 江西財經大學學報, 2013(5): 101-106.Mei Y, Long L R. A study of the issue of China’s migrant workers merging into urban society[J].Journal of Jiangx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2013(5): 101-106.
[8]楊春江, 李雯, 逯野. 農民工收入與工作時間對生活滿意度的影響——城市融入與社會安全感的作用[J]. 農業技術經濟, 2014(2): 36-46.Yang C J, Li W, Lu Y. The influence of migrant workers’ income and working hours on life satisfaction—Based on the role of urban integration and social security[J]. Journal of Agrotechnical Economics, 2014(2): 36-46.
[9]周秀平, 南方. 心理期待與進城務工青年的城市融入[J].當代青年研究, 2014(5): 41-46.Zhou X P, Nan F. Expectation and urban acculturation of young rural worker[J]. Contemporary Youth Research, 2014(5): 41-46.
[10]劉電芝, 魯遲, 彭杜宏. 進城農民工城市融入分析——以蘇州地區為例[J]. 蘇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2008,29(1): 29-33.Liu D Z, Lu C, Peng D H. A survey report of the condition of rural migrant worker’s merging into urban society—A case of the Suzhou region[J]. Journal of Soochow University (Philosophy & Social Science Edition), 2008, 29(1): 29-33.
[11]Jost J T, Kay A C. Social justice: History, theory,and research[M]//Handbook of Social Psychology. 2010:1122-1165.
[12]叢中, 安莉娟. 安全感量表的初步編制及信度、效度檢驗[J]. 中國心理衛生雜志, 2004, 18(2): 97-99.Cong Z, An L J. Developing of security questionnaire and its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J]. Chinese Mental Health Journal, 2004, 18(2): 97-99.
[13]李景春, 李玉杰, 劉志峰. 心理和諧與和諧社會辯證互動機制及其發展趨勢[J]. 燕山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9, 10(1): 104-107.Li J C, Li Y J, Liu Z F. The dialectical interaction mechanism and development trend of psychological harmony and harmonious society[J]. Journal of Yanshan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Edition),2009, 10(1): 104-107.
[14]王甫勤. 公平感影響農民工城市融合[N]. 中國社會科學報,2013-04-26(A08).Wang F Q. The influence of fairness on migrant workers’ urban integration[N]. Chinese Social Science Today, 2013-04-26(A08).
[15]任遠, 鄔民樂. 城市流動人口的社會融合:文獻述評[J].人口研究, 2006, 30(3): 87-94.Ren Y, Wu J L. Social integration of floating population in urban China: A literature review[J].Population Research, 2006, 30(3): 87-94.
[16]Dávila A, Mora M T. The marital status of recent Mexican immigrants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1980 and 1990[J].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2001, 35(2):506-524.
[17]Rijt A V D. Selection and influence in the assimilation process of immigrants[J]. Advances in Group Processes, 2013, 30: 1-35.
[18]錢文榮, 李寶值. 初衷達成度、公平感知度對農民工留城意愿的影響及其代際差異——基于長江三角洲16城市的調研數據[J]. 管理世界, 2013(9): 89-101.Qian W R, Li B Z. The impact of the original degree of achievement and the perception of fairness on migrant workers’ willingness to stay in cities and their intergenerational differences—Based on the survey data of 16 cities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J]. Management World, 2013(9): 89-101.
[19]Shin D C, Johnson D M. Avowed happiness as an overall assessment of the quality of life[J].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1978, 5(1): 475-492.
[20]史耀疆, 崔瑜. 公民公平觀及其對社會公平評價和生活滿意度影響分析[J]. 管理世界, 2006(10): 39-49.Shi Y J, Cui Y. An analysis of the concept of citizen fairness and its impact on social justice and life satisfaction[J]. Management World, 2006(10): 39-49.
[21]劉靜. 蟻族群體社會公平感與主觀幸福感的關系研究——基于心理彈性和壓力知覺的視角[D]. 河南大學, 2013.Liu J. Research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n tribe” social justice and subject well-being- on the resilience and stress perception perspective[D].Henan University, 2013.
[22]閔婕. 農民工安全感、生活滿意度及應對方式的相關研究[D]. 河北師范大學, 2012.Min J. Study on the relationship of security,life satisfaction and coping style among migrant workers[D]. Hebei Normal University, 2012.
[23]張洪霞. 新生代農民工社會融合的內生機制創新研究——人力資本、社會資本、心理資本的協同作用[J]. 農業現代化研究, 2013, 34(4): 412-416.Zhang H X. New research on endogenesis mechanism of social integration for new generation of farmworks—synergistic effect among human capital, social capital and psychological capital[J]. Research of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2013, 34(4): 412-416.
[24]馮冬冬, 陸昌勤, 蕭愛鈴. 工作不安全感與幸福感、績效的關系:自我效能感的作用[J]. 心理學報, 2008, 40(4):448-455.Feng D D, Lu C Q, Xiao A L. Job insecurity, wellbeing, and job performance: The role of general selfefficacy[J]. Acta Psychologica Sinica, 2008, 40(4):448-455.
[25]崔巖. 流動人口心理層面的社會融入和身份認同問題研究[J]. 社會學研究, 2012(5): 141-160.Cui Y. A study on migrants’ psychological integration and self-identity[J]. Sociological Studies, 2012(5):141-160.
[26]李丹, 李玉鳳. 新生代農民工市民化問題探析——基于生活滿意度視角[J]. 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 2012, 22(7):151-155.Li D, Li Y F. Exploring the urbanizition of newgeneration migrant workers in China: From the prospective of life satisfaction[J]. China Population,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2012, 22(7):151-155.
[27]梁波, 王海英. 城市融入:外來農民工的市民化——對已有研究的綜述[J]. 人口與發展, 2010, 16(4): 73-85.Liang B, Wang H Y. Urban integration: The citizenization of migrant workers—A review of existing studies[J].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2010, 16(4): 73-85.
[28]Kraus M W, Piff P K, Mendozadenton R. Social class,solipsism, and contextualism: How the rich are different from the poor[J]. Psychological Review,2012, 119(3): 546-572.
[29]胡小勇, 郭永玉, 李靜, 等. 社會公平感對不同階層目標達成的影響及其過程[J]. 心理學報, 2016, 48(3): 271-289.Hu X Y, Guo Y Y, Li J, et al. Perceived societal fairness and goal attainment: The different effects
The influences of the perceptions of fairness and security of migrant workers on their social inclusion in cities: Based on the role of economic income and life satisfaction
YANG Chun-jiang1,2, TIAN Peng-mei1, CHEN Ya-shuo1
(1. School of Economics & Management and Institute of Modern Tourism Industry & Organization Development, Yanshan University, Qinhuangdao, Hebei 066004, China; 2.Yantai Nanshan University, Yantai, Shandong 265713, China)
F323.6
A
1000-0275(2017)05-0843-09
河北省社會科學基金項目(HB16SH049)。
楊春江(1978-),男,遼寧丹東人,博士,教授,主要從事農民工社會心理和三農問題研究,E-mail: ycj@ysu.edu.cn。
2017-02-17,接受日期:2017-05-15
Foundation item:Hebei Provincial Social Science Foundation(HB16SH049).
Corresponding author:YANG Chun-jiang, E-mail: ycj@ysu.edu.cn.
Received17 February, 2017;Accepted15 May, 2017
10.13872/j.1000-0275.2017.0047
楊春江, 田鵬妹, 陳亞碩. 公平與安全對農民工社會融入的影響研究——基于生活滿意和經濟收入的作用[J]. 農業現代化研究, 2017, 38(5): 843-851.
Yang C J, Tian P M, Chen Y S. The influences of the perceptions of fairness and security of migrant workers on their social inclusion in cities: Based on the role of economic income and life satisfaction[J]. Research of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2017, 38(5): 843-8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