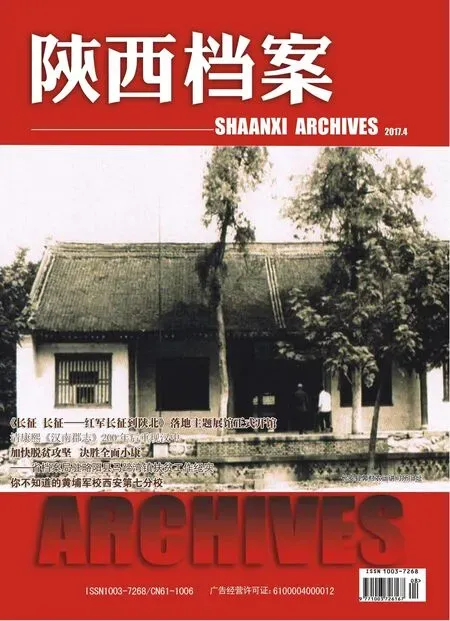詩說潼關
文/董燕翔
詩說潼關
文/董燕翔
“(曹)操在亂軍中,只聽得西涼軍大叫:‘穿紅袍的是曹操!’操就馬上急脫下紅袍。又聽得大叫:‘長髯者是曹操!’操驚慌,掣所佩刀斷其髯。軍中有人將曹操割髯之事,告知馬超。超遂令人叫拿:‘短髯者是曹操!’操聞知,即扯旗角包頸而逃”。這一段繪聲繪色的描述,是《三國演義》講述曹操統一北方、與西涼馬超集團初期對決時大敗而逃的情景。一位調和陰陽、紫綬金章的丞相掛帥出征,竟被敵軍追殺的連自己的穿著和胡須都成了累贅,只顧逃命而無暇顧及身份和形象,這可真是主動攻擊敵方時少有的事情。按理說,此時的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文武干才濟濟一堂,勇夫悍卒眾喣飄山,揚蕩滌河北之威、攜平定荊州之勢,正值春風得意之際。所到之處,自然應該是云屯席卷,奮武揚威,雖不至馬踏泥丸,一戰定乾坤,也不至于栽面到如此狼狽境地啊。對此,曹操本人亦為不解。對于馬超這個對手,他自信還算了解。此人占據西涼,經營有年。雖然勇猛,卻是一介武夫。既缺良謀,也無輔佐,所帶士卒雖號稱20萬,卻分由家族統領,各懷心事,各行其是,不足為訓。對手不過如此,敗績必有他因。一向喜歡尋源的曹操,決定一探究竟。于是,聚攏殘卒,重整旗鼓,再次舉兵西進。迎頭看去,只見一座寫著“潼關”二字的關隘橫亙眼前,擋住了去路。初看上去,字跡油漆尚未風干,可見是一座年輕關隘。曹操征戰多年,破關無數,這等無名關隘開始并未放在眼里。等到湊到近前仔細端詳,方才驚出一身冷汗。只見潼關位于秦、晉、豫三地之要沖,南依秦嶺——崇山峻嶺,層巒疊嶂,高壁低壑,溝谷淵深。綿綿亙亙,無窮無絕,白云在城頭繚繞,飛燕在城腰穿行。北臨黃河——九曲回腸,彎急灘險,濁浪滾滾,咆哮奔騰,聲如雷鳴,巨浪拍天,船舶隨浪花沉浮,艄公因顛簸瑟瑟。正所謂“重崗如抱岳如蹲,屈曲秦川勢自尊。天地并功開帝宅,山河相湊束龍門”。看到這里,曹操方知“天地并功”如此,絕非人力可為,失利亦實屬不免。絕望之下,只好轉身悻悻而去,另尋他途。
曹操鎩羽自然可惜,但潼關卻經過這場金鼓連天、飛箭如蝗的洗禮,一戰成名!從此,后世眾多文人每每經過此地,都會情不自禁地揮毫落紙,暢敘胸懷。或嗟嘆城固,或唏噓山河,或追念往昔,或感慨人生。由此,“潼關”之意也已遠非“軍事要地”四字所能包容,而成為社會萬象的代名詞了。我以為,借助潼關,歷代詩詞章句所達之意或可歸之為三絕五喻。
一曰阨絕。但凡關隘,總以遏制交通為關節。“誠曰咽喉,吞八荒而則大”方顯其基本功能。潼關之作為“咽喉”,是因其完全能夠隔絕豫、晉兩地西進關中的交通,阻遏住中原一帶軍事行動對秦地的影響。這一點,以兵少將寡的馬超憤然阻止曹操兵馬西進并獲得成功就足以為證。如果把潼關與它的“師兄”函谷關做一番比較,其“阨”的意義則會更加彰顯。大名鼎鼎的函谷關,曾經也是拱衛秦地的重要關隘。
賈誼曾有“秦孝公據崤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窺周室,有席卷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說的就是函谷關曾經的輝煌。公元前318年,秦國兵馬曾在函谷關城下大敗東方五國合縱聯軍,從此,東方六國就以函谷關為夢魘,雖有含恨之心,再無西顧之膽了。但函谷雖有“囊括四海之意”,卻無“包舉宇內”之姿。函谷關以西,只有一條峽谷可以溝通豫、陜兩地,所以能夠“關函守峣,山東道窮”。但在函谷的北面,尚有一條潼水河谷,雖然曲折,卻能溝通秦晉兩地。秦晉交通既然不需經過函谷,則作為關隘,函谷關的功能自然減半。這正是函谷黯然失色,逐漸淡出歷史風云的主因,而同時,據函谷以西七十余公里的潼關既可以“塵土長安古道深,潼關依舊接桃林”,成為豫陜的必經之地,又可以“殘云歸太華,疏雨過中條”,成為陜晉的交通要沖。從而一舉取代函谷關,成為名副其實的“山勢雄三輔,關門扼九州”的戰略要地了。

潼關古城
二曰險絕。既然要扼守,當然就要選擇置攻方于無奈的要沖。所謂“洞壑雙扇入到初,似從深井睹高墟”,“槐柏蟬聲柳市風,驛樓高倚夕陽東”,居高臨下,俯瞰敵方,方可使敵軍雖蟻附關下,卻只能進退維谷。只是唐人看待潼關,已經不再單純看其“山形朝闕去,河勢抱關來”的地勢,而更多地是從軍事戰略的角度解讀潼關了。如“天開白日臨軍國,山夾黃河護帝居”,“唯皇王之建國,分中外于上京”。把潼關與長安城緊密聯系起來,用以謳歌潼關拒敵于國門之外的戰略險境。而作為軍事家的李世民,則更是從全局的角度看待潼關的攻守作用:“崤函稱地險,襟帶壯兩京”。不僅考慮守護長安城,還可隨時環伺處于百戰之地的洛陽。這或許只有他當年反守為攻,兵出潼關,剿殺身處洛陽、自立為王的王世充、以及援軍竇建德后才能別出的心得吧。
三曰固絕。潼關之固,不僅在于自身的巍峨,還在于周邊環境的襯托。在它東面,有一隘口,名曰黃巷坂。南依高原,北鄰深澗,中間只容單車通行。關南有一深谷,名曰禁溝,“谷勢壁立,望者禁足”。“曠覽古今,鑒觀成敗,其于建連城以控禁溝,控禁溝以固關”。有了這兩處要隘,加之秦嶺、黃河的捍蔽,潼關之固可說是鬼斧神工,渾然天成。對此,杜甫曾不無感慨地說:“士卒何草草,筑城潼關道。大城鐵不如,小城萬丈馀”,“連云列戰格,飛鳥不能逾。胡來但自守,豈復憂西都?”這樣的城池,也真正做到了“蓋神明之奧區,帝宅之戶牖,百二之固,信非虛言也”。
潼關在地勢上的三絕,使它迅速躋身古代著名關隘之列,也成為“秦皇曾虎視,漢祖昔龍顏”的又一亮點。不過,古代文人贊嘆潼關三絕之余,更愿意借題發揮,翻空出奇。把地勢的絕,化作人事的絕。據此浮想聯翩,隱喻萬象。
一曰尚武之喻。以出關為題,比喻尚武之情,這在漢唐詩句中多有表現。究其起因,則大概都與終軍有關。終軍,漢武帝時期人。雖然年輕,卻多有報國之志。當時南越國時叛時降,心懷二意。身為諫大夫的終軍自請長纓,然后單人單騎,義無反顧,直出函谷,勸降南越王。終軍請纓出關的壯舉令漢武帝感動,同時也感召著無數后世文人趨之若騖。既然終軍所出的函谷已廢,后人便正好將潼關作為隱喻。唐代魏征就曾用“中原初逐鹿,投筆事戎軒。縱然計不就,慷慨志猶存。杖策謁天子,驅馬出關門。請纓系南粵,憑軾下東藩”的詩句,表達自己獨出潼關,招降李密叛軍的壯志。當然,如果一旦壯志難酬,同樣可以借助這段悲情的歷史,一展情懷。如唐代詩人曹鄴途經潼關時就曾有“山上黃犢走避人,山下女郎歌滿野。我獨南征恨此身,更有無成出關者”的哀嘆。可見,本以雄壯著稱的潼關,帶給人間無盡雄武之風的同時,也會帶來些許悲愴的氣息。
二曰及第之喻。唐代開始,科舉取士已蔚然成風。每年,來自全國各地的才子都會齊聚長安,競相爭取拔得頭籌。但科舉科目雖多,錄取幾率卻很低。“三十老明經,五十少進士”已是當時的常態。于是,各地舉子便將科舉比喻成闖潼關,以示求職的艱難。著名詩人岑參19歲時參加科舉。落第后來到潼關,用一首《戲題關門》自謔,引以解嘲:“來亦一布衣,去亦一布衣。羞見關城吏,還從舊路歸”。岑參自認為考試名落孫山,已屬倒霉。沒曾想其后有個名叫呂溫的詩人路經潼關,被早已熟悉的守關人問及應試結果時,只能緋紅著臉回答道:“本欲云雨化,卻隨波浪翻。一沾太常第,十過潼關門”。闖關十年方才修得正果,比起岑參,確實更應感到慚愧。但這還不是最慘的。唐末有位詩人名叫吳融,連續應試二十五年。他在《出潼關》這首詩中說道:“飛軒何滿路,丹陛正求才。獨我疏慵質,飄然又此回”。已經記不住出入潼關多少次,只能用“飄然又此回”自我解嘲了。
三曰斥貪之喻。說到潼關,人們總會聯想到楊震其人,也總會因此而企盼政治的清明。這一點,也確為潼關增色不少。楊震,東漢潼關人,以廉政著稱。在他擔任東萊太守時,一天晚上,有一人到楊府行賄,并認為“暮夜無知者”。但楊震卻說:“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謂無知?”予以拒絕。從此,“四知”便成為拒腐蝕、永不沾的代名詞而蜚聲天下。后人只要來到潼關城下,便會不由自主地追念楊震本人,也會大加頌揚他的四知。比如唐代詩人周曇寫有:“為國推賢匪惠私,十金為報遽相危。 無言暗室何人見,咫尺斯須已四知。”胡曾則有:“楊震幽魂下北邙,關西蹤跡遂荒涼。四知美譽留人世,應與乾坤共久長”。但“四知美譽留人世”不假,而“應與乾坤共久長”則只能成為一個夢想。在“官老爺”統治時代,既然權力缺少必要的監督,以權謀私之風就永遠無法得到有效遏制。楊震作為那個時代的特例,僅僅只能作為那個時代的標本予以展示,而如洪水猛獸般的貪腐行徑,則在不斷地朝代更迭過程中得以傳襲,成為那個制度下永遠揮之不去的幽靈。你看,“河上關門日日開,古今名利旋堪哀。終軍壯節埋黃土,楊震豐碑翳綠苔”,漢代豎起的千古楷模,到了唐代,就早已湮沒在綠野青苔之上了。

潼關黃河風景區
四曰仁德之喻。唐玄宗時代,君臣之間有一次專門以潼關為題進行的唱和。主題當然由玄宗而生:“河曲回千里,關門限二京。所嗟非恃德,設險到天平”。針對潼關拱衛京畿的功能,玄宗拋出了德與險的關系問題。在座的三位丞相低頭沉思后,首先由張九齡接招:“嶙嶙故城壘,荒涼空戌樓。在德不在險,方知王道休”。蘇颋隨之奉上“在德何夷險,觀風復往還。自能同善閉,中路可無關”。張說壓軸唱和道“天德平無外,關門東復西。不將千里隔,何用一丸泥”。君臣之間雖角度不同,但落點同一。都看到了險不可恃、仁德為上的至理。而“超千載而垂績”的開元盛世似乎也證明了這個道理。可見,此時的唐玄宗,自以為德政超前,四方來投,又有四近之臣列坐,虎體鹓班廣布,就可以“春宵苦短日高起,從此君王不早朝”了。卻不想一個安史之亂,“漁陽鼙鼓動地來,驚破霓裳羽衣曲,”直接消弭了玄宗君臣沾沾自喜的唱和情調,也徹底阻止了指山賣嶺式的“在德不在險,方知王道休”的空談。當安祿山的虎狼之眾涌向潼關城頭時,曾經被君臣信奉的“德”早已不見蹤跡,就連潼關的“險”也未能產生應有的效應,頃刻之間便城堞傾墜,瓦解冰泮。整個王朝也因失去潼關隘口而高岸為谷,地坼天崩。由此,這場以潼關為題材、搜腸刮肚積成的德與險的唱和,隨即變成了千年之中百姓茶余飯后的笑柄。
五曰怨民之喻。安史之亂,讓人們對“昔帝御中原,守國用三策。上策以仁義,天下無能敵。其次樹屏翰,相維如盤石。最下恃險固,棄德任智力”的治國理念產生了懷疑。基于對本朝曾經輝煌的眷戀,唐人最早開始總結這段歷史。比如杜甫就曾說:“請囑防關將,慎勿學哥舒”。把潼關失守歸因于守將哥舒翰。杜牧也曾說:“廣德者強朝萬國,用賢無敵是長城。君王若悟治安論,安史何人敢弄兵?”把唐朝失利歸因于痛失德政和所用非人。柳宗元甚至直接提出“失在于政,不在于制”,干脆拒絕承認制度存在問題。唐人雖痛心疾首,卻囿于窠臼,無法更深層次地揭示內中究竟,倒是元人張養浩一語道出了真諦。他在《潼關懷古》中說道:“峰巒如聚,波濤如怒,山河表里潼關路。望西都,意躊躇,傷心秦漢經行處,宮闕萬間都做了土。興,百姓苦;亡,百姓苦。”潼關失守,王朝沒落,根本原因都在于一個“百姓苦”。“中路可無關”,百姓苦,“嶙嶙故城壘”,百姓亦苦,潼關的建與不建,固與不固,他的根基都為怨民。如此,還會有什么真正的固若金湯的城池呢?
作為一個符號,潼關走過了它的輝煌,也見證了怨民的哀嘆。正所謂“虎踞龍盤此要津,迢遙懸處不生塵。行人若問金湯固,半屬山河半屬人”。它所留給后人的,永遠都是“險”、“德”、“賢”、“怨”的遐思,“雄”、“渾”、“悲”、“愴”的嘆惋。而這或許才是你登上潼關城頭、極目遠眺時萌生的心緒吧。
當今有人對中國古代名關排列座次,潼關屈居第二。我以為非常不妥。位列第一的山海關雖然顯赫,但其城破之日僅僅是完成了一個朝代更迭,潼關則不然。它的傾頹,直接宣告了一種社會制度的衰微。僅就這一點來看,潼關,也只有潼關,才真正配稱千年歷史第一關!
(作者單位:陜西省檔案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