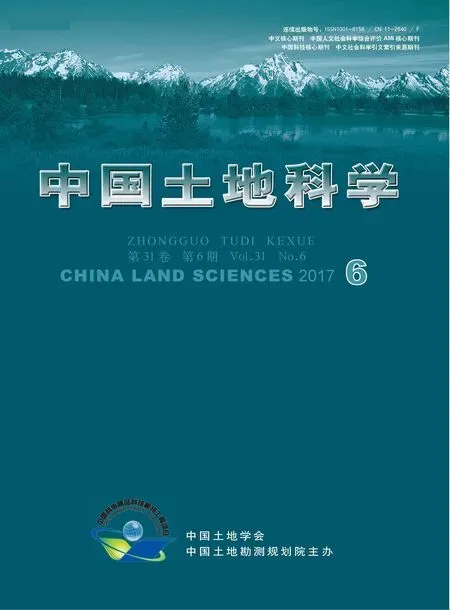社會資本如何影響征地拆遷農(nóng)戶的生活?
——基于有序Logistic模型的實(shí)證分析
盧圣華,姚妤婷,汪 暉
(浙江大學(xué)公共管理學(xué)院,浙江 杭州 310030)
社會資本如何影響征地拆遷農(nóng)戶的生活?
——基于有序Logistic模型的實(shí)證分析
盧圣華,姚妤婷,汪 暉
(浙江大學(xué)公共管理學(xué)院,浙江 杭州 310030)
研究目的:從社會資本的視角解釋被征地拆遷農(nóng)戶的生活變化差異,為進(jìn)一步完善征地制度改革提供參考思路。研究方法:研究基于2015年浙江省杭州市的抽樣調(diào)查數(shù)據(jù),從村域制度信任、村域民主、村民個(gè)體網(wǎng)絡(luò)關(guān)系與村域合作4維度衡量社會資本,綜合運(yùn)用主成分分析與有序Logistic模型就社會資本對征地拆遷后農(nóng)戶生活狀況的影響進(jìn)行計(jì)量分析。研究結(jié)果:村域制度信任、民主程度與農(nóng)戶自身的社會網(wǎng)絡(luò)均對提高拆遷后農(nóng)戶的生活水平有正向效應(yīng),而村域合作卻不利于拆遷后農(nóng)戶生活水平的提升。研究結(jié)論:在征地制度改革的過程中,充分發(fā)揮村域社會資本的作用,比如在土地問題上號召更廣泛的公眾參與,對征地拆遷農(nóng)戶的生活狀況是有利的。
土地管理;征地拆遷;社會資本;生活水平;有序Logistic模型;主成分分析
Abstract: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interpret the differences of rural households’ life change after land acquisition from the social capital perspective and to provide suggestions for improving the land acquisition institution. The research method is based on a sample survey conducted in Hangzhou, Zhejiang Province in 2015, the social capital is measured from four dimensions, including level of trust, degree of democracy, social network, and collective cooperation. The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and ordered logistic model are used to study the influence of social capital on rural households’ life change after land acquisit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level of trust, degree of democracy, and social network have positive effects on improving rural households’ life after land acquisition, whereas collective cooperation has a negative effect. The conclusion is that social capital, such as extensive public participation on land-related issues, can serve to enhance rural households’ life conditions after land acquisition.
Key words:land administration; land acquisition; social capital; living condition; ordered logistic model;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1 引言
隨著中國經(jīng)濟(jì)的快速發(fā)展與城市化的推進(jìn),征地規(guī)模不斷擴(kuò)大,如何有效保障農(nóng)民的土地財(cái)產(chǎn)權(quán)益成為了學(xué)界探討的焦點(diǎn)。自2004年中央提出“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要采取切實(shí)措施,使被征地農(nóng)民生活水平不因征地而降低”以來①資料來源于《國務(wù)院關(guān)于深化改革嚴(yán)格土地管理決定》(國發(fā)[2004]28號)。,各地都在努力探尋一條保障被征地農(nóng)戶生活水平之路。目前,一部分研究表明征地會造成農(nóng)戶的收入水平下降、發(fā)展空間縮小[1];另一方面也有調(diào)查顯示被征地農(nóng)戶的收入水平上升、生活水平得到了改善[2],如此截然不同的結(jié)論當(dāng)然可以用地域差異加以解釋。但顧娟對蘇州市婁葑鎮(zhèn)的調(diào)研發(fā)現(xiàn),即使是同一個(gè)鎮(zhèn),也有部分農(nóng)戶的生活水平因征地而上升,另外部分則下降[3]。相同地域內(nèi)個(gè)體的分化顯然無法由地域差異解釋,是什么造成了這種差異?
筆者認(rèn)為,在研究征地問題時(shí),必須加以關(guān)注的是農(nóng)村這一特殊地域。中國農(nóng)村的經(jīng)濟(jì)發(fā)展、社會管理模式都深受傳統(tǒng)文化的影響,以親緣和地緣關(guān)系為紐帶形成了獨(dú)特的文化經(jīng)濟(jì)體系。最新的文獻(xiàn)研究表明,社會資本在農(nóng)村治理過程中起著重要的作用[4-5]。首先是社會資本與農(nóng)村糾紛,大量的農(nóng)村基層司法研究表明在農(nóng)村這個(gè)特定的社會結(jié)構(gòu)中,社會資本影響了糾紛的解決方式[6-7];其二是社會資本與農(nóng)民生活,實(shí)證研究證明社會資本會對農(nóng)民的生活質(zhì)量與滿意度產(chǎn)生影響[8-9]。由此看來,面對征地造成的農(nóng)戶生活水平差異,對社會資本的研究可能有助于筆者解釋這個(gè)現(xiàn)象。
以往研究存在以下幾點(diǎn)缺陷:一是研究對象存在盲區(qū)。關(guān)于征地拆遷農(nóng)戶的社會保障、經(jīng)濟(jì)補(bǔ)償、就業(yè)和安置模式等方面已有涉及[10-16],但只有少量研究著眼于其生活水平的變化情況[1,17-19];二是指標(biāo)選取值得推敲。在少量研究被征地農(nóng)戶生活的文獻(xiàn)中,多以“滿意、不滿意”等方式來評價(jià)農(nóng)戶對征地后生活水平的態(tài)度[17-19]。但人們對于生活的滿意程度不僅取決于自身的生活水平,還依賴于與他人生活的比較[20]。因此,以滿意程度衡量農(nóng)戶征地后的生活水平有失客觀;三是影響因素的選取過于宏觀。關(guān)于農(nóng)戶征地拆遷后的生活狀況,現(xiàn)有文獻(xiàn)通常更關(guān)注征地區(qū)位、政策執(zhí)行等宏觀因素的影響,卻鮮有研究關(guān)注社會資本這種重要的非市場力量。但如前文所述,這種力量可能正是解釋同一宏觀環(huán)境下不同個(gè)體分化的有效證據(jù)。
針對以上問題,本文基于2015年在浙江杭州調(diào)查的結(jié)果,以主成分分析方法獲取衡量被征地拆遷農(nóng)戶生活水平變化的指標(biāo),并采用有序Logistic模型來探究社會資本是否對其產(chǎn)生影響。
2 文獻(xiàn)綜述與理論假說
學(xué)界通常將社會資本定義為“社會組織的特征,諸如信任、規(guī)范以及網(wǎng)絡(luò),他們能夠通過促進(jìn)合作行為來提高社會效率”[21]。從系統(tǒng)主義的角度出發(fā),可將社會資本劃分為宏觀、中觀和微觀三個(gè)層次[22],對農(nóng)民生活產(chǎn)生影響的主要是中觀和微觀方面。而具體到征地拆遷中,村組織為補(bǔ)償安置、社區(qū)建設(shè)的具體實(shí)施者,因此農(nóng)民生活狀況變化不僅受個(gè)人社會資本影響,還受到村域社會資本的影響,后者在此指村民與其他村民及村組織的互動及關(guān)系特征。
社會資本之信任、規(guī)范、網(wǎng)絡(luò)三大核心要素為學(xué)界共識,而在實(shí)際解釋應(yīng)用中得到具化延伸。其中較為權(quán)威的是世界銀行設(shè)計(jì)的指標(biāo)體系,即將社會資本劃分為群體與網(wǎng)絡(luò)、信任與團(tuán)結(jié)、集體合作、民主與政治行動、信息交流、社會凝聚力6大類。雖然這一體系便于應(yīng)用,但指標(biāo)間存在包含及重疊關(guān)系,例如信息交流內(nèi)含于網(wǎng)絡(luò)、社會凝聚力產(chǎn)生于信任與合作。為保持指標(biāo)獨(dú)立性,結(jié)合中國農(nóng)村形態(tài)及征地拆遷特征,本文以村民個(gè)體關(guān)系網(wǎng)絡(luò)、村域制度信任、村域合作、村域民主4個(gè)維度研究社會資本如何影響被征地拆遷農(nóng)戶的生活水平。
個(gè)體網(wǎng)絡(luò)通過提供各種資源與機(jī)會,幫助實(shí)現(xiàn)個(gè)人的發(fā)展與生活水平的提高[23-25];國內(nèi)的許多研究也表明,網(wǎng)絡(luò)規(guī)模、網(wǎng)絡(luò)差異對降低農(nóng)戶的貧困發(fā)生率有顯著正效應(yīng)[26-28],對提升家庭福利水平也有顯著作用[28-30]。唐為等進(jìn)一步指出網(wǎng)絡(luò)使個(gè)體得以利用另一方所擁有的某種資源為自己帶來收益[31]。各地征地拆遷雖有統(tǒng)一的補(bǔ)償安置標(biāo)準(zhǔn),但在具體實(shí)施環(huán)節(jié)中仍存在資源傾斜、分配先后。此時(shí)村民的關(guān)系網(wǎng)絡(luò)便至關(guān)重要,尤其是聯(lián)系緊密的親緣、業(yè)緣關(guān)系中可用的政治資源。據(jù)此形成假說1。
假說1:個(gè)體網(wǎng)絡(luò)水平越高,征地拆遷農(nóng)戶生活改善的可能性越大。
村域環(huán)境中,集體合作有兩方面的效應(yīng)。其一是就村民間關(guān)系而言,合作有助于信息交流、提升互惠關(guān)系,從而對生活水平有提升作用[32];其二是就村民與村組織關(guān)系而言,當(dāng)個(gè)體間零散互動無法滿足合作需求時(shí),便需要村民讓渡權(quán)力給其代理人(往往是村組織),由此可能形成強(qiáng)勢的集體并導(dǎo)致權(quán)力的不均衡分配,從而導(dǎo)致公共事務(wù)決策偏離公共利益[33]。根據(jù)國家與地方的相關(guān)規(guī)定,土地補(bǔ)償費(fèi)集體有權(quán)提留一定比例,具體比例由村集體組織商議決定①資料來源于《中華人民共和國村民委員會組織法》與各個(gè)地方頒布的征地補(bǔ)償辦法。。近些年不少研究表明,過于強(qiáng)勢的村集體常常在征地補(bǔ)償款的分配上損害農(nóng)戶利益[34-36]。征地拆遷中,比之村民間的互動,村民與村組織的關(guān)系對其生活狀況影響更大。因此可以預(yù)期第二種效用更明顯。據(jù)此得到假說2。
假說2:村域合作水平越高,征地拆遷農(nóng)戶生活改善的可能性越小。
信任可分為人際與制度信任。在征地拆遷事務(wù)中,村組織作為具體實(shí)施者,村民對其的制度信任較大。一方面,制度信任促進(jìn)農(nóng)民積極參與到征地拆遷事務(wù)中,使其有更多機(jī)會爭取利益。另一方面,已有的研究證明了信任顯著地提升了個(gè)體幸福感[37],甚至有學(xué)者通過工具變量分析證明了信任與個(gè)體幸福感之間存在因果關(guān)系[38]。不難想象,在征地拆遷事務(wù)中,村民基于制度信任而易產(chǎn)生滿足感。據(jù)此得到假說3。
假說3:村域制度信任水平越高,征地拆遷農(nóng)戶生活改善的可能性越大。
村域民主為村民提供了協(xié)商的可能性。已有文獻(xiàn)指出,協(xié)商機(jī)制有利于提升補(bǔ)償標(biāo)準(zhǔn)、減少征地沖突[14,39];基于大樣本的實(shí)證研究也證明,談判作為一種強(qiáng)勢的協(xié)商方式,對提高征地補(bǔ)償有顯著的正效應(yīng)[40]。事實(shí)上,除了協(xié)商這一種體現(xiàn)民主的方式之外,大量的國外研究證明民主對人們生活質(zhì)量的提升有顯著的積極作用[41-44]。據(jù)此得到假說4。
假說4:村域制度民主水平越高,征地拆遷農(nóng)戶生活改善的可能性越大。
3 數(shù)據(jù)來源與變量描述
3.1 數(shù)據(jù)來源
本文數(shù)據(jù)來源于2015年7—8月在浙江杭州市桐廬縣與余杭區(qū)開展的實(shí)地調(diào)查。余杭區(qū)的經(jīng)濟(jì)水平高于桐廬縣,2015年前者的人均GDP為15996美元,后者為12777美元。在兩個(gè)區(qū)(縣)中各隨機(jī)抽取了10個(gè)村,每個(gè)村再隨機(jī)抽取16戶進(jìn)行問卷訪談,調(diào)查內(nèi)容包括農(nóng)戶家庭及成員特征、村征地拆遷事務(wù)、村民主狀況等。共收回有效問卷307份,其中桐廬縣152份,余杭區(qū)155份。樣本中未被征地或拆遷的不符合本文研究目的,予以剔除,最后獲得129個(gè)樣本。
3.2 變量描述
3.2.1 因變量 本文將征地拆遷后農(nóng)戶的生活水平變化作為因變量。在調(diào)研過程中,為避免單一指標(biāo)描述的片面性,筆者將生活水平的變化劃分為6個(gè)維度,分別是“家庭經(jīng)濟(jì)狀況變化情況”、“家庭住房狀況變化情況”、“生活便利狀況變化情況”、“居住地周圍道路交通狀況的變化情況”、“居住地周圍環(huán)境狀況的變化情況”以及“娛樂休閑方便狀況的變化情況”,這些問題的答案均為“差很多”、“差一點(diǎn)”、“沒有變化”、“有一點(diǎn)改善”和“有很大改善”5級,分別記為1—5分。
在統(tǒng)計(jì)檢驗(yàn)中,為簡化描述指標(biāo),并為了模型的正確設(shè)定與估計(jì),筆者對以上6個(gè)項(xiàng)目進(jìn)行了主成分分析。在主成分分析之前,對變量進(jìn)行KMO檢驗(yàn)和Bartlett球形檢驗(yàn),結(jié)果顯示KMO值為0.814,適合做主成分分析,Bartlett檢驗(yàn)的結(jié)果也支持了這一點(diǎn)。于是筆者對上述描述農(nóng)戶生活水平變化的6個(gè)維度進(jìn)行主成分分析,并按照所有因子的方差貢獻(xiàn)率進(jìn)行加權(quán),得到農(nóng)戶生活水平變化指數(shù)(SHSP*i),計(jì)算公式如下:

式(1)中,n為保留的因子個(gè)數(shù),σi為第個(gè)因子的方差貢獻(xiàn)率,mi為第i個(gè)因子的因子得分即是各個(gè)成分的權(quán)重。本文保留了所有6個(gè)成分,并得到如下加權(quán)結(jié)果:

式(2)中,m1—m6分別表示家庭經(jīng)濟(jì)、住房、生活便利、道路交通、環(huán)境與娛樂休閑方便狀況的變化情況。本文對落入的三個(gè)連續(xù)區(qū)段(0,3]、(3,4]、(4,5]進(jìn)行分析①之所以不對(0,3)區(qū)間進(jìn)行細(xì)分是因?yàn)樾∮?的樣本數(shù)只有1個(gè),繼續(xù)細(xì)分意義不大。,參照前文6個(gè)維度的衡量標(biāo)準(zhǔn),三個(gè)區(qū)段具有現(xiàn)實(shí)意義,分別表示征地拆遷后農(nóng)戶生活“變差或沒有變化”、“有一點(diǎn)改善”、“有明顯改善”。具體的分布情況如圖1所示。可以看出,在129個(gè)農(nóng)戶當(dāng)中,生活狀況發(fā)生改善的占大部分,其中有59位農(nóng)戶被征地后生活水平發(fā)生很大改善,48位農(nóng)戶有一點(diǎn)改善,僅有22位農(nóng)戶的生活水平未得到提高。

圖1 被征地拆遷農(nóng)戶生活變化狀況Fig.1 Life change of rural households after land acquisition
3.2.2 自變量 社會資本是本文中的自變量,如前文所述,本文通過4個(gè)層面對其進(jìn)行測度。具體問題的設(shè)置與含義、變量的名稱與賦值如表1所示。

表1 自變量說明Tab.1 Independent variables explanation
3.2.3 控制變量 根據(jù)已有文獻(xiàn)的經(jīng)驗(yàn),農(nóng)民的個(gè)體特征與家庭狀況會對征地后生活水平的變化產(chǎn)生重要影響。因此,本文選擇受訪農(nóng)民的性別、年齡、受教育年數(shù)、家庭收入、家庭人口數(shù)、婚姻狀況、戶口類型與補(bǔ)償標(biāo)準(zhǔn)作為控制變量。其中,性別、婚姻狀況、戶口類型采用虛擬變量的方法進(jìn)行構(gòu)造,具體來說,性別變量1為男性、0為女性,婚姻狀況變量1為有配偶、0為離婚、喪偶、未婚等無配偶情形,戶口類型變量1為農(nóng)村戶口、0為非農(nóng)村戶口;家庭年收入分為9個(gè)等級,分別為0—4999元、5000—9999元、10000—19999元、20000—29999元、30000—39999元、40000—49999元、50000—99999元、100000—299999元、300000元以上;年齡、受教育年數(shù)、家庭人口數(shù)為定距變量。需要特別指出的是,由于征地補(bǔ)償政策的原因,余杭區(qū)的補(bǔ)償標(biāo)準(zhǔn)要高于桐廬縣。因此加入了地區(qū)的虛擬變量來控制補(bǔ)償標(biāo)準(zhǔn)的系統(tǒng)性差異,1表示余杭區(qū),0為桐廬縣。本文所有變量的描述統(tǒng)計(jì)如表2所示。

表2 變量統(tǒng)計(jì)情況Tab.2 Statistics of variables
4 模型設(shè)定與結(jié)果分析
4.1 模型設(shè)定
本文根據(jù)主成分分析的結(jié)果把生活水平的變化情況劃分為3個(gè)層次,分別賦值1、2、3以表示生活水平逐步提升。顯然,被征地農(nóng)戶的生活水平的變化情況是有序分類變量。鑒于此,線性模型會存在很大缺陷,因此,本研究采用有序Logistic模型進(jìn)行分析:


一般而言,假設(shè)μi的分布函數(shù)為F(x),yi取各個(gè)值的j概率分別為:

有序Logistic模型的系數(shù)估計(jì)采用的是極大似然估計(jì)法MLE,但需要注意的是,估計(jì)得到的系數(shù)α1并不等于Xi對因變量各個(gè)取值概率的邊際效應(yīng)。邊際效應(yīng)的表達(dá)如下所示,其中φ(·)為密度函數(shù):

4.2 估計(jì)結(jié)果與解釋
本文采用Stata 13.0進(jìn)行估計(jì),模型的估計(jì)結(jié)果如表3所示。
首先關(guān)注全樣本的回歸結(jié)果,可以看出,3個(gè)維度的社會資本均通過了顯著性檢驗(yàn),且與假說預(yù)期的符號一致,假說基本上得到了驗(yàn)證。第一,在信任程度方面,雖然筆者測度的是村民對村干部的信任,但應(yīng)該注意到,在農(nóng)村社會這種以血緣、親緣為基礎(chǔ)的信任體系下,對非親友的信任恰恰能比較好地衡量整個(gè)村的信任氛圍。因此,信任程度正的系數(shù)驗(yàn)證了假說3,良好的村莊信任氛圍有助于提升征地拆遷農(nóng)戶的生活水平。第二,有親友在政府機(jī)關(guān)部門擔(dān)任干部會對征地拆遷農(nóng)戶的生活產(chǎn)生正面效應(yīng)。此結(jié)果符合常識,在中國農(nóng)村這樣一個(gè)人情社會,政治與經(jīng)濟(jì)資源常常向“干部家庭”、“關(guān)系戶”傾斜。在征地過程中,干部家庭可能會被安置到更舒適的居住環(huán)境中,或者較之其他農(nóng)戶能更早地拿到征地補(bǔ)償款,從而造成征地拆遷農(nóng)戶對生活水平感知的差異性。第三,村民會議的系數(shù)顯著為正。因村務(wù)而召開村民會議在村莊中形成了民主的環(huán)境,使得農(nóng)民更有機(jī)會就征地表達(dá)自己的利益訴求。同時(shí),村民會議提供了一個(gè)聚集民意的平臺,增強(qiáng)了與基層政府談判的力量,有利于征地拆遷后生活水平的提高。最后,集體合作是4個(gè)維度中唯一系數(shù)為負(fù)的變量,這意味著,筆者在假說中提到的“削弱效應(yīng)”要強(qiáng)于“提升效應(yīng)”。村里擁有集體經(jīng)營管理的合作社或公司,這樣的村集體往往會比較強(qiáng)勢,在集體事務(wù)中也有更大的自主裁量權(quán)。加之法律賦予村集體提留征地補(bǔ)償款的權(quán)力,導(dǎo)致了集體行動反而不利于農(nóng)戶生活的改善。

表3 分組估計(jì)結(jié)果Tab.3 The results of grouped regression
在全樣本的回歸結(jié)果中,關(guān)注到控制變量中婚姻狀態(tài)的系數(shù)顯著為負(fù),說明已婚農(nóng)戶征地后的生活水平得到提升的可能性要低于未婚農(nóng)戶。鑒于因變量“生活水平”是農(nóng)戶的主觀感受,筆者認(rèn)為負(fù)的回歸系數(shù)是由兩方面的原因造成的。一方面,征地給已婚農(nóng)戶帶來的主觀上損失感會更大。由于一個(gè)完整家庭的存在,已婚者對土地的依戀程度更大,征地給其帶來的不僅是物質(zhì)上損失,還有情感上的損失;另一方面,已婚農(nóng)戶對拆遷后生活水平的衡量標(biāo)準(zhǔn)更加嚴(yán)苛,不僅包括受訪者個(gè)人的要求,還受到子女的教育醫(yī)療保障、配偶的工作安置情況等多種因素影響。在兩方面的共同作用下,已婚農(nóng)戶感受到生活發(fā)生改善的可能性自然發(fā)生下降。
最后分析分組回歸的結(jié)果。在兩個(gè)調(diào)研區(qū)域中,無論是組間比較還是與全樣本比較,社會資本的作用都具有明顯差異。余杭區(qū)經(jīng)濟(jì)更發(fā)達(dá)可能是造成這種差異的原因。余杭區(qū)集體行動依然顯著為負(fù),但信任程度變?yōu)椴伙@著,而桐廬縣恰好相反。這可能是因?yàn)椋诮?jīng)濟(jì)發(fā)達(dá)的地區(qū),面對更高的補(bǔ)償金額,村集體會有更強(qiáng)的激勵(lì)提留補(bǔ)償款;同時(shí),由于信任的正向作用是通過農(nóng)民間的互惠行動與信息交互實(shí)現(xiàn)的,而在接近市中心的余杭區(qū),農(nóng)民被征地拆遷后有更多的就業(yè)選擇,個(gè)體能動性更強(qiáng),因此村域信任的作用不夠明顯。值得注意的是,在全樣本中顯著為正的親友任職變量在分組回歸中均不顯著。對此,筆者在模型中添加了親友任職與地區(qū)的交互項(xiàng)之后發(fā)現(xiàn),親友任職的作用對地區(qū)有很強(qiáng)的依賴性,全樣本中的顯著性來自于桐廬縣且親友中無干部的樣本;同時(shí),桐廬縣親友有無干部的樣本之間的差異不夠大,不足以在桐廬縣子樣本的回歸結(jié)果中表現(xiàn)顯著,因此分組回歸中這一變量不再顯著。盡管個(gè)體網(wǎng)絡(luò)的影響機(jī)制更為復(fù)雜,但不可否認(rèn)的是,這一社會資本確實(shí)在改善農(nóng)戶的生活水平中發(fā)揮著作用。
4.3 邊際效應(yīng)分析
雖然表3中的估計(jì)系數(shù)反映了不同因素對被征地農(nóng)戶生活水平變化的影響,但難以準(zhǔn)確反映出這些因素的影響程度。因此,本研究利用臨界點(diǎn)估計(jì)值與相關(guān)估計(jì)系數(shù)計(jì)算各個(gè)因素的邊際效應(yīng)。依據(jù)式(6), Xi對yi的邊際效應(yīng)的計(jì)算結(jié)果見表4。

表4 邊際效應(yīng)Tab.4 Marginal effects
從表4可以看出,集體行動在因變量取值“明顯改善”(y = 3)時(shí)邊際效應(yīng)顯著且為負(fù)數(shù),這與表3中的回歸結(jié)果一致,表明村域合作使被征地農(nóng)戶生活水平發(fā)生明顯改善的可能性下降。進(jìn)一步分析,當(dāng)y<3時(shí),上述變量的邊際效應(yīng)大小的排序是“有點(diǎn)改善(y = 2)”、“有所降低(y = 1)”,說明隨著變量取值的增加,被征地農(nóng)戶的生活水平更傾向于“有所改善”。信任程度、親友任職與村民會議三者的邊際效應(yīng)皆與前者相反,表明隨著這些變量取值的增加,被征地農(nóng)戶生活水平發(fā)生明顯改善的可能性上升。表(4)還表明,婚姻狀態(tài)對被征地農(nóng)戶生活水平的邊際影響最大,家庭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對農(nóng)戶生活水平的變化產(chǎn)生影響。
5 結(jié)論與討論
從已有的文獻(xiàn)看,被征地拆遷農(nóng)戶的生活狀況差異主要來源于地域差異,然而,這并不能解釋同一地域內(nèi)不同農(nóng)戶間的分化。本文從社會資本的視角出發(fā),提供了一個(gè)解釋此種差異的不同視角,并基于2015年杭州市桐廬縣與余杭區(qū)的抽樣調(diào)查數(shù)據(jù),就社會資本對被征地拆遷農(nóng)戶生活狀況變化的影響進(jìn)行實(shí)證分析。研究結(jié)論主要有以下幾點(diǎn):
第一,村民個(gè)體關(guān)系網(wǎng)絡(luò)、村域制度信任與村域民主水平均對征地拆遷后農(nóng)戶的生活變化產(chǎn)生顯著的正向影響。高水平的社會網(wǎng)絡(luò)關(guān)系,如有親友在政府機(jī)關(guān)部門任職有助于政治與經(jīng)濟(jì)資源向其傾斜;村域制度信任促進(jìn)農(nóng)戶積極參與到村級事務(wù)中去;民主意味著更廣泛的公眾參與,為農(nóng)戶提供了表達(dá)利益訴求的途徑,從而有助于農(nóng)戶被征地拆遷后生活水平提升的可能性。后兩者還從主觀感知層面提高了農(nóng)戶對生活狀況改善的評價(jià)。
第二,村域合作對拆遷后農(nóng)戶的生活水平具有顯著的負(fù)效應(yīng)。集體合作可能有助于農(nóng)戶相互支持,但是集體合作強(qiáng)化了村集體的權(quán)力。在村集體掌握征地補(bǔ)償款提留與分配的情況下,過于強(qiáng)勢的村集體并不利于農(nóng)戶生活的提升。
第三,婚姻狀況負(fù)向影響拆遷后農(nóng)戶的生活水平。這與筆者選取的主觀評價(jià)指標(biāo)有關(guān),已婚的農(nóng)戶不僅要考慮個(gè)體的感知,還要考慮配偶、子女等因素,所以對生活水平的評價(jià)更加嚴(yán)苛。另一方面,有完整家庭的農(nóng)戶往往對土地更加依戀,拆遷對其造成的不僅是經(jīng)濟(jì)上、更是情感上的損失。邊際效應(yīng)分析表明,婚姻狀況對被拆遷農(nóng)戶生活水平變化的邊際影響最大。
基于以上結(jié)論,可以得出如下政策啟示:一是在征地制度改革的過程中,除了關(guān)注就業(yè)安置、經(jīng)濟(jì)補(bǔ)償?shù)群暧^因素外,還應(yīng)考慮基層自治組織的情況,應(yīng)當(dāng)吸引更廣泛的公眾參與,避免村集體權(quán)力過于集中;二是對不同的被拆遷農(nóng)戶區(qū)分對待,以“公平”代替“平均”,例如對子女教育、老人醫(yī)療受拆遷影響的家庭,應(yīng)當(dāng)給以充分的政策配套。
(References):
[1] 劉勁龍,周寶同. 征地對農(nóng)民生活水平的影響評價(jià)——基于重慶市永川區(qū)的調(diào)研[J] . 中國農(nóng)學(xué)通報(bào),2012,28(26):168 - 172.
[2] 樓培敏. 中國城市化過程中被征地農(nóng)民生活狀況實(shí)證研究——以上海浦東、浙江溫州和四川廣元為例[J] . 中國農(nóng)村經(jīng)濟(jì),2005,21(12):35 - 45.
[3] 顧娟. 征地前后農(nóng)民生活水平對比研究[D] . 蘇州:蘇州大學(xué),2013:61.
[4] Baylis Kathy, Gong Yazhen, Wang Shun. Bridging vs. Bonding Social Capital and the Management of Common Pool Resources[J] . Nber Working Papers(No. w19195),2013.
[5] Gerard Padr ó I. Miquel, Qian Nancy, Xu Yiqing, et al. Making Democracy Work: Culture, Social Capital and Elections in China[J] . Nber Working Papers(No. w21058),2015.
[6] 高其才. 鄉(xiāng)土司法[M] . 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364 - 368.
[7] 蘇力. 送法下鄉(xiāng)[M] . 北京:中國政法大學(xué)出版社,2000:6 - 9.
[8] 趙雪雁,毛笑文. 社會資本對農(nóng)戶生活滿意度的影響——基于甘肅省的調(diào)查數(shù)據(jù)[J] . 干旱區(qū)地理,2015,38(5):1040 - 1048.
[9] 韋璞. 村落社會資本及其對老年人生活質(zhì)量的影響[J] . 南方人口,2008,23(2):30 - 36.
[10] 張學(xué)英. 可持續(xù)生計(jì)視域下的被征地農(nóng)民就業(yè)問題研究[J] . 貴州社會科學(xué),2010,31(4):86 - 91.
[11] 陳晨,陸銘,周國良,等. 關(guān)注城市化進(jìn)程中的弱勢群體——對被征地農(nóng)民經(jīng)濟(jì)補(bǔ)償、社會保障與就業(yè)情況的考察[J] . 經(jīng)濟(jì)體制改革,2004,22(1):15 - 20.
[12] 劉海云,劉吉云. 失地農(nóng)民安置模式選擇研究[J] . 商業(yè)研究,2009,52(10):11 - 15.
[13] 楊翠迎. 被征地農(nóng)民養(yǎng)老保障制度的分析與評價(jià)——以浙江省10個(gè)市為例[J] . 中國農(nóng)村經(jīng)濟(jì),2004,20(5):61 - 68.
[14] 胡大偉. 水庫移民征地補(bǔ)償協(xié)商機(jī)制構(gòu)建研究——基于合意治理的思考[J] . 中國土地科學(xué),2013,27(4):15 - 21.
[15] 胡健敏,曾令秋. 我國征地行為中農(nóng)民權(quán)益保障的思考[J] . 農(nóng)村經(jīng)濟(jì),2011,29(8):27 - 31.
[16] 王麗. 征地補(bǔ)償制度問題及失地農(nóng)民的權(quán)益保障[J] . 農(nóng)業(yè)經(jīng)濟(jì),2007,27(6):31 - 33.
[17] 王鋒,趙凌云. 我國被征地拆遷居民滿意度調(diào)查——以浙江省湖州市為例[J] . 安徽農(nóng)業(yè)科學(xué),2010,50(2):584 - 587.
[18] 龍騰飛,徐榮國,施國慶. 城市拆遷的滿意度研究[J] . 安徽農(nóng)業(yè)科學(xué),2007,47(7):2195 - 2196.
[19] 鐘水映,李魁. 工程性移民征地滿意度的影響因子分析——以某公路征地拆遷為例[J] . 華中農(nóng)業(yè)大學(xué)學(xué)報(bào)(社會科學(xué)版),2008,28(1):43 - 47.
[20] Ariely, Dan. Predictably Irrational[M] . Betascript Publishing,2010:526 - 528.
[21] Putnam R D, Leonardi R, Nonetti R Y. Making Democracy Work: Civic Traditions in Modern Italy[M] .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4.
[22] 托馬斯·福特·布朗,木子西. 社會資本理論綜述[J] . 馬克思主義與現(xiàn)實(shí),2000,11(2):41 - 46.
[23] Coleman James S. Social Capital in the Creation of Human Capital. The American[J] .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1988,94(Suppl 1):95 - 120.
[24] Bourdieu P. The Forms of Capital[M] .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s Ltd,1986:280 - 291.
[25] Lin, Nan. Social Capital: A Theory of Social Structure and Action[M]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1:167 - 186.
[26] 張爽,陸銘,章元. 社會資本的作用隨市場化進(jìn)程減弱還是加強(qiáng)?——來自中國農(nóng)村貧困的實(shí)證研究[J] . 經(jīng)濟(jì)學(xué)(季刊),2007,7(2):539 - 560.
[27] 趙劍治,陸銘. 關(guān)系對農(nóng)村收入差距的貢獻(xiàn)及其地區(qū)差異——一項(xiàng)基于回歸的分解分析[J] . 經(jīng)濟(jì)學(xué)(季刊),2010,10(1):363 - 390.
[28] 王朝明. 社會資本與城市貧困問題研究[M] . 成都:西南財(cái)經(jīng)大學(xué)出版社,2009.
[29] 林燕. 社會資本投資對我國居民福利改進(jìn)的理論與實(shí)證研究[D] . 成都:西南財(cái)經(jīng)大學(xué),2010:172.
[30] 邵興全,林艷. 社會資本的累積效應(yīng)及其家庭福利改善[J] . 改革,2011,24(9):131 - 136.
[31] 唐為,陸云航. 社會資本影響農(nóng)民收入水平嗎——基于關(guān)系網(wǎng)絡(luò)、信任與和諧視角的實(shí)證分析[J] . 經(jīng)濟(jì)學(xué)家,2011,23(9):77 - 85.
[32] Coleman James S. Social Capital in the Creation of Human Capital. The American[J] .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1988,94(Suppl 1):95 - 120.
[33] 盧維良. 整合農(nóng)村社會資本的內(nèi)在張力,促進(jìn)農(nóng)村社區(qū)治理[J] . 理論與改革,2012,25(2):100 - 103.
[34] 楊群. 農(nóng)村征地補(bǔ)償款分配管理制度的法律完善[D] . 重慶:西南政法大學(xué),2006:42.
[35] 王海鴻,王丹,杜莖深. 征地補(bǔ)償款村級分配問題研究[J] . 開發(fā)研究,2009,25(2):74 - 79.
[36] 高海. 征地補(bǔ)償款分配糾紛之民事責(zé)任探究[J] . 西北農(nóng)林科技大學(xué)學(xué)報(bào)(社會科學(xué)版),2014,14(4):8 - 15.
[37] John Hudson. Institutional Trust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across the EU[J] . Kyklos,2006,59(1):43 - 62.
[38] KUROKI, MASANORI. Does Social Trust Increase Individual Happiness in Japan?[J] . Japanese Economic Review,2011,62(4):444,459.
[39] 鄭鴻,鄭慶昌. 征地補(bǔ)償安置協(xié)商:一個(gè)不完全信息討價(jià)還價(jià)動態(tài)博弈模型[J] . 福建農(nóng)林大學(xué)學(xué)報(bào)(哲學(xué)社會科學(xué)版),2012,15(3):47 - 51.
[40] 汪暉,陳簫. 土地征收中的農(nóng)民抗?fàn)帯⒄勁泻脱a(bǔ)償——基于大樣本調(diào)查的實(shí)證分析[J] . 農(nóng)業(yè)經(jīng)濟(jì)問題,2015,26(8):63 - 73.
[41] Moon Bruce E., Dixon William J. Politics, the State, and Basic Human Needs: A Cross-National Study[J] .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1985,29(4):661 - 694.
[42] London Bruce, Williams Bruce A. National Politics, International Dependency, and Basic Needs Provision: A Cross-National Analysis[J] . Social Forces,1990,69(2):565 - 584.
[43] Young Frank W. Do some authoritarian governments foster physical quality of life?[J] .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1990,22(4):351 -366.
[44] Wickrama K. A. S., Mulford Charles L. Political democracy, economic development, disarticulation, and social well-being in developing countries[J] . Sociological Quarterly,1996,37(3):375 - 390.
(本文責(zé)編:陳美景)
How do Social Capital Influence Rural Households’ Life after Land Acquisition: An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Ordered Logistic Model
LU Sheng-hua, YAO Yu-ting, WANG Hui (College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30, China)
F301.2
A
1001-8158(2017)06-0003-10
10.11994/zgtdkx.20170519.135807
2017-01-06;
2017-03-20
國家社科重大課題“城鄉(xiāng)統(tǒng)一建設(shè)用地市場構(gòu)建及利益分配機(jī)制研究”(15ZDA024);2016年度浙江省哲學(xué)社會科學(xué)規(guī)劃課題“完善我省征地補(bǔ)償機(jī)制的研究”(16NDJC267YB)。
盧圣華(1995-),男,浙江麗水人,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yàn)檗r(nóng)村土地制度。E-mail: Answer_Lu@126.com
汪暉(1968-),男,浙江湖州人,教授,博士生導(dǎo)師。主要研究方向?yàn)橹袊鞯刂贫取⒔?jīng)濟(jì)增長與土地政策。E-mail: wanghuidn@zju.edu.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