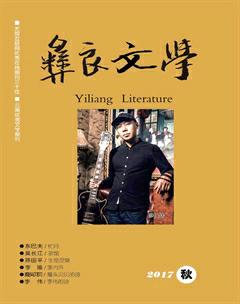生命涅槃
陳田平
我曾經問過自己,如果我不去啟蒙讀書,如智慧未啟,我在老家的那一畝三分地上,成長、耕地、娶妻、生子、放牛,進行周而復始的本質輪回。
那也許是另外一種幸福,命運的輪子主導著宿命的因子,我的母親還是堅持讓我去上學,于是,我走過了我家門口的小河,翻過門口的大山,過童園、下寨、九里十三灣、墳場、馬杠在新場中學上完初中,之后到縣城上高中,在到昆明讀大學,我離開了故鄉, 拋棄了我的土地,羊群和牛。踏上了另外一條求學的路。
大學畢業,參加了工作后,鄉下人面臨著大城市人的復雜和貪婪,目睹了社會底層的辛酸苦辣,我收起我寫詩的夢想,我努力地奮斗著,在丟了祖先給我本質之魂后。我總惦記在故鄉行走的那些日子,苦難而單一,簡單而幸福。有時覺得我的衣袍之地,我就像一個過客,記得一兄弟說的一樣,他回老家過春節的時候,背起背籮走進地里劈菜的那一瞬間,覺得人生是多么的幸福,有時,人在瞬間的幸福是可以終極的。
這些年,很少回故鄉,她就只能是一個心中的一種特殊符號了,可我的父母還在哪里,我一直以為我裝了我父親的身體,竊取了我母親的思想,我可以帶著他們離開,其實,我是幼稚的,他們根本走不了,我卻走了,我不知道離開故鄉是我的身體還是我的靈魂。但我已經離開了,生活讓我魂都沒有了,整天混跡于一群丟了魂的形尸走肉中。
我一直努力找回我丟掉的魂。
其實,人生在世,如草木一秋,轉眼間,半生已過,想想過去那些事情,雖歷經苦難和磨難,生命重生過多次,有時想想,覺得挺不容易的,向死而生,我要找回我丟掉的魂,我知道,他就在我苦難的故鄉,我的故鄉在昭通彝良的山上,那里是一個貧窮的村子,生長苦難和幸福,記得小時候,家里窮,生活異常艱辛,姊妹多,還記得我們兄妹幾個想吃肉得提前給爸爸媽媽申請,一個月能吃一次,可每次的肉及其少,我們兄妹幾個吃完就沒有了,我母親就把碗底的油給我父親拌飯吃,畢竟父親是家里唯一的支柱,我不懂事的妹妹問我媽媽,媽媽,你怎么不吃肉,我母親說道,媽媽不喜歡吃肉,妹妹信以為真,我看見媽媽把菜湯倒進裝肉的碗里筭了喝了下去,我的父親眼里布滿血絲。
那是一段苦難的歲月,他成長我的童年,像那些草木一樣的簡單,記得有一次,我過生日,我媽媽給我煮了一個雞蛋,家里不管有多窮在兒女過生日的時候都得煮一個雞蛋讓過生日的兒女吃,我六歲的生日,我媽媽給我煮了雞蛋,我最小的一個弟弟看見煮了雞蛋一直在火爐邊守著,像是自己過生日一樣,可他只能看看,任其嘴里的清口水流淌,我和媽媽說多煮一個分弟弟吃一個,我媽媽說不行,煮一個分三弟,那另外的幾個怎么辦,家里就這兩只母雞在下蛋,好不容易積滿10個那是要到集市上去賣了給家里買鹽巴和燈油錢的,絕不能浪費。雞蛋煮好了,我媽媽給剝皮的時候,想吃雞蛋想吃瘋了的三弟起來開始搶奪母親手里的雞蛋,我媽媽怕他搶走雞蛋就把雞蛋給我,我剛拿著媽媽給我的雞蛋的時候,我的三弟伸手過來就抓,三弟才兩歲,他什么都不知道,我媽媽看著三弟要搶給我過生日的雞蛋,過生日的雞蛋是不能分別人吃的,必須一個的吃下去,她狠狠地給了她三兒子兩個耳光,三弟被我媽媽打得嚎啕大哭,我在旁邊吃雞蛋,媽媽看著我吃完雞蛋,她走過去抱著三弟,我看見媽媽眼里的淚水,我把最后一口咽完,我看見我的別的弟妹在撿地上的雞蛋殼在嘴里舔著,添得很香,那是我人生中吃得最難忘的雞蛋,參加工作后,我曾經有30天,幾乎天天在吃雞蛋,失去了以前的滋味。
生命像野草一樣瘋長著,那個時候的日子每天都是一樣的,七歲開始上學,每天早上干完農活,跑步到學校聽課,下午放學后繼續干農活,生命就像是在跑圈圈,周而復始,在故鄉,辛苦的故鄉人,重復著簡單而復雜的輪回,千百年不變。最苦的就是晚上要推磨,現在人估計連磨是什么樣的都沒有見過,我和弟弟那個時候的工作就是要負責每天晚上推磨,磨玉米面第二天煮飯吃,我和我弟弟像兩頭小驢一樣在黑夜中推磨,直到自己精疲力盡,呼呼大睡,多數時間我60多歲的奶奶也參加,奶奶主要負責添磨。
1992年,我考上了初中,家里弟弟妹妹全部開始上學,家里負擔越來越重,我們一年只能買一次衣服,平時我們都不準穿鞋,除非是冬天,我們的腳上長了厚厚的繭子,一般的木刺都難以刺進去,褲子永遠都打著補丁,除了過年那天,記憶猶新的是我們那個時候基本不興穿內褲,就穿一條寡褲子,任風霜穿透,記得有一次我被學校評了一個三好學生,我穿著一條沒有橡皮筋的褲子,我在家找一根草繩系著去學校,我上臺領獎的時候給大家敬禮的時候褲子離開草繩掉了下去,里面什么都沒有,光著,臺下面人聲顫動,笑聲不斷,我在臺上還以為是下面的同學在鼓掌,我正得意著給大家轉動哈身體的時候我們校長趕緊把我的褲子提起來把我抱下演講臺,并告訴了我的父親,當晚我父親狠狠的揍我一頓,原因是我把褲子里面的橡皮筋拿出來做了彈弓。我睡覺后我媽媽連夜幫我補好了褲子,差不多有半年的時間我們學校的女生見我都在笑話我。
上初中后,我每周會回一次家,我每周回來都可以吃一頓肉,我在學校吃的就是現在豬吃的,我家離學校有半天的路程,記得,我們每個星期交兩塊錢的菜錢,家里背五斤半包谷面交在學校里,每天兩頓飯,菜里沒有半點油,偶爾有一頓油基本是漂湯油,里面的油珠珠都可以數清楚。我一般為了節約五毛錢吃早點,兩毛錢一個的包子,我星期六放學后不吃飯直接回家,30里的路程,走不動了就開始數數,數我走過的九里十三灣有多少步,實在餓的不行了就用樹枝刨地里的紅薯充饑,到家里我的奶奶總是給我煮了好吃的,最好吃的就是豬腳桿坨坨了,我工作后得出的結論:那基本是我吃的終極價值,
艱難的初中生活,差點要了我的命,三年中我被折磨得皮包骨頭,我拖著幾乎散架的軀體念完了初中,中考我考了200分的總分。
初中畢業后,我回家務農一年,這一年,我趕著牛放牧于故鄉的山水間,我的身體開始恢復,開始從我軍醫外公家(我媽媽的姑媽)的廁所里偷他家用來擦屁股的水滸傳和三國演義來看,看了很多遍,我媽媽賣了家里的一頭過年豬給我去縣城報名讓我復讀,村里幾乎所有人都勸我媽媽說:送他去讀書還不如給他討個媳婦,我的母親還是堅持讓我去復讀,復讀時我喜歡我們班一個叫紅的女孩,我以為我努力讀書考上中專就能娶她,可是中考她去了昭通讀衛校,而我又因為年齡大了不能上中專,我又回家放牛,看故鄉的藍天,讀不懂那些變換的云彩和那些巋然不動的大山,我又開始讀三國演義和水滸傳,在故鄉的天地間學會了手淫,我著迷一樣的讓那種怪異的液體射到那些遠去的河水里,一種莫名的快感讓我精神錯亂,我像是丟了魂的人,我母親看著日漸消瘦的身體,她送了一只我家的大公雞給我的老師,讓我去讀了普通高中,這是我人生中的轉折點。
讀高中后,我的弟妹因為沒有錢交學費無法在繼續上學,他們輟學在家,我二弟獨自一人來昆明打工,記得我收到他寫給我的信的時候,我讀得放聲大哭,我的妹妹開始在縣城打工掙錢給我讀書,她每個月掙80元錢,她一分未用全部給我做我上高中的學費和生活費,苦了我的妹妹。同時三弟也輟學在家,他還小,他想上學,他甚至求過我媽媽,可是家里實在拿不出錢給他上學了,我看見我三弟抹著眼淚說媽媽我不上了給大哥上,我看見我媽媽哭了,高中三年我的學習一直很好,我帶著全家人的希望在讀書,也許命運就是這樣的不公平,他總是要這樣的折磨我,我高三開始生病,病得很嚴重,吐了很多血,我當時以為我肯定活不成了,家里幾乎值錢的東西都賣了給我看病,我堅持上學,病魔折磨我的身體和心靈,我來來回回走在地獄里,活著只是一種存在,一種虛無飄渺的存在,我的媽媽為了照顧我累起一身的病,我看著自己這樣,我放棄了讀書的念頭,那年高考,我未考上。
為了逃避,我離開了家參加修內昆鐵路,在陰暗潮濕的隧道里我看懂了生死,我用瘦弱的身軀掙每一分錢,直到我的路費夠了后我離開了工地,我到昆明打工,我沒有告訴我的母親及其家人,我難以從我高考的失敗的陰影中走出,我相信了命運。
昆明打工期間,我走在社會最底層,看慣了人世間的酸甜苦辣,我開始拼命地看書,期間我讀完了很多世界名著,當時最艱難的時候我和二弟餓得受不了就喝自來水充饑,昆明的自來水是最難喝的,氯氣太重,連續兩天喝自來水,走路都沒有了力氣,第三天老板給了我兩百元生活費才買米煮飯。饑餓讓人的意識處于一種饑荒狀態,兩年時間我讀了太多的書,卻一事無成,我依然決定回家參加高考,那年是2001年,我都23歲了,我悄悄回到老家,用打工掙的錢交了報考費,我晝伏夜出,怕別人看見我,通過兩個月的復習我參加了高考,成績出來那天我告訴我媽說我考上大學了,我媽媽眼淚都出來了。考上大學,又開始為我的大學學費發愁了,那么多的錢那里來,我媽媽每天天不亮就從家里背菜走十幾里山路來縣城賣,幫我贊學費,我們全村的鄰居和親戚不管多少都幫忙,在我離開家鄉的時候把學費籌齊,我數錢才發現那些全是零票,我數著眼睛都濕了。
非常不幸的是三弟就在我準備上學的時候他在砍豬草喂豬時手被機器扎了,兩個拇指沒有了,媽媽哭得最傷心,除了我的學費,家里沒有一分錢了,我的學費已經打入學校賬戶沒有辦法取出來,車費又不能用,那時,我遇見了這個世界上的好人彝良縣三角醫院的宋醫生,她出錢給我三弟做完手術,一直不要還錢,真是好人啊。
啃著故鄉和親人的骨頭,我上了大學。
大學是我人生中最幸福的時間了,我像著魔一樣地博覽群書,努力的學習著,古的、中的、外的,黃的,情的、愛的,我如饑似渴地讀著我能找到的書,并完成了小說《原色》,以對故鄉的眷念,這是2005年的事情,之后我就為了生計一直行走于云南各地,流浪他鄉,即將完成的下一部書里寫著對另外社會現象的痛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