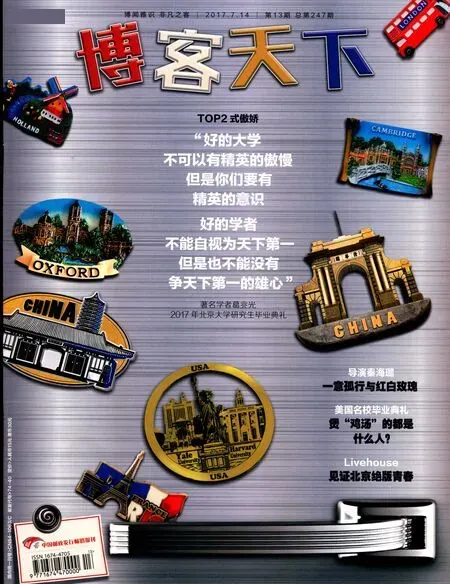Livehouse見證北京絕版青春
文 崔一凡 編輯 卜昌炯
長報道
Livehouse見證北京絕版青春
文 崔一凡 編輯 卜昌炯

很難說年輕人和Livehouse誰塑造了誰,但至少兩者達成了某種契合
下下午6點,北京鼓樓東大街逐漸熱鬧起來,絡繹而來的人開始重新定義這條古老街道。他們衣著時髦,發型新潮,文身和耳洞并不鮮見。香煙是這里的名片,遞上一支煙,就能加入一場志趣相投的談話。也有人不理會周遭的一切,一位長發披肩、頂著黑色瓜皮帽的年輕人背著吉他,徑直從人群中穿過。
暮色緩緩降臨,他們開始向一扇銹跡斑駁的大鐵門聚攏。晦暗的鐵門上布滿鉚釘和劃痕,像是廢棄已久的防空洞,焊接痕跡毫不掩飾地裸露在外,用指節輕叩,會發出剛硬的回響。
不出意外的話,它只在夜晚打開,透出暖黃色的燈光,和劇烈的聲壓。
十年間,已有數以十萬記的年輕人穿過這扇標志性的大鐵門。在鼓樓東大街躁動的夜色里,他們將進入另一個世界。
平行世界里的自己
這里是MAO,北京乃至中國最知名的Livehouse,搖滾圣地,過去十年里,它成為北京的文化地標之一,是“去鼓樓就一定要走到的地方”。
Livehouse源于日本,特指具有頂級音樂器材、完善的音響設備和舞臺燈光以及具有一定專業水準的小型展演場館,適合近距離欣賞現場音樂。誕生之初,它就成為各種樂隊以及獨立音樂的重要輸出地。很多時候,衡量一個城市是否有音樂土壤,得看那里是否有Livehouse。
北京的Livehouse大約有10家。雖然同是北京夜生活的代表,但Livehouse不同于三里屯光鮮亮麗的夜店,也不像后海那些被稱為約會圣地的酒吧,這里無關金錢、性和酒精。
“酒吧、夜店是社交場所,去Livehouse就是為了欣賞音樂。”搖滾愛好者不知周對《博客天下》說。
大約400平方米的展演廳里沒有座位,人們擁擠其中,伴隨音樂不自覺地扭動身體,揮舞著Pogo手勢,T恤黏在肩膀上,一個背著書包的姑娘擠到前排,大聲喊著樂手的名字。十幾臺擴音音響同時制造出的強大聲場湮沒了她的聲音,也將現場幾百名觀眾完全包裹起來。
演出漸入佳境,臺上的樂手們越發投入,仰起上身把吉他掃得翻江倒海。
Moon享受這種與眾不同的演出現場。她站在后排,手握啤酒,隨著音樂晃動腦袋,一副碩大的耳環來回搖曳。她喜歡看樂手們有力地甩動長發,充滿力量感的音樂制造了一個令人亢奮的場域。
展演廳外,有一個幾十平方米的前廳,墻壁上布滿奇形怪狀的涂鴉,還有觀眾們信手涂抹的痕跡。

很多時候,衡量一個城市是否有音樂土壤,得看那里是否有Livehouse
從初中第一次走進L ivehouse,Moon就決定成為特立獨行的人。事實上,那時的她靦腆羞澀,是老師眼里的乖孩子,但她厭倦了這種標簽,迫切地想撕碎它。那時她熱衷于吹噓自己在Livehouse的經歷,對方刮目相看的眼神給她帶來極大的滿足感。
如今她大三,仍覺得在Livehouse里暫時“偏離軌道”,依然能帶來某種安慰。她的主業是服裝設計,平時除了上課、實習,她還會參加各種活動,每個月從圖書館借7本書。她想過上想要的生活,想快點長大,為了鍛煉自己的交際能力,她會去各種活動做志愿者,專門找“大人多的地方”,她會參加校內的創業比賽,也會接私活賺些錢。
在大多數人的刻板印象中,文身、香煙和怪異發型是Livehouse的標配。干凈清爽的李偉給人一種違和感。他穿著淺色休閑襯衫,搭配西褲、皮鞋,一副職場精英的打扮。李偉有時會幻想平行世界里的另一個自己,是樂手或Livehouse老板,過不一樣的生活。
現實中,他是公司白領,從事管理咨詢方面的工作。這培養了他富有邏輯感的思維方式和生活方式。他早早規劃好了職業生涯,每年達到什么目標,之后再把目標分解至每月每周和每天。對他來說,生活的每個部分都是一個問題,他要用一個個樹狀圖來解決。但當生活的枝枝杈杈被砍掉,內心總覺得有些荒蕪。
心情不好時,他會把尊奉的邏輯統統打破,把本應存在的不確定感重新注入生活。他會脫下西服和皮鞋,換上運動裝走進MAO的那扇鐵門,在吧臺前和陌生人搭話,認識新朋友,在燥熱的觀眾區蹦跳,享受不同類型的音樂,在激烈的鼓點和失真的吉他聲中釋放情緒。
Livehouse像一個巨大的容器,收納了無數年輕人的快樂和悲傷。他們大多剛剛進入社會,尚未被磨平棱角,與外部世界的關系總是碰撞多過屈服。在Livehouse里,他們這一刻,不屬于任何家庭,不屬于任何單位,只屬于自己。
音樂的重要性不能退居次席
MAO做舊的大鐵門是創始人李赤的設計,他喜歡這種破敗的金屬質感,有搖滾范兒,接地氣卻又不流俗。
Livehouse最初因搖滾樂而生,在它狹小黑暗的空間里,誕生了上世紀60年代的反戰歌曲;70年代的英國朋克青年;80年代末,臺灣獨立音樂人以livehouse為據點,以嘶吼的方式迎接戒嚴解除的新時代。這里孵化了諸多世界著名的搖滾樂隊,披頭士、地下絲絨都在 Livehouse舉辦了人生的第一場演出,而汪峰剛出道時,也一度混跡于北京早期的Livehouse。
Livehouse和搖滾樂對李赤的影響尤為明顯。上世紀90年代初,李赤在中關村賣電腦,每月能賺到1.7萬元。那時他是標準的商務人士,每日西裝革履,戴著金絲眼鏡。朋友帶他去看了地下搖滾演出,一進去他就被鎮住了,“那音樂一響,太牛了”。兩個小時后,他的人生發生了改變。一萬七的工資不要了,公司折價賣給了朋友。
“大家都想(賺錢),我就是放棄掙錢,覺得更應該做一些有意義的事。”李赤對《博客天下》說。當時國內還沒有Livehouse的概念,他糾集一竿子朋友開了一家“人民迪廳”,其他迪廳放迪曲,人民迪廳只放搖滾。直到2007年,他終于夢想成真,MAO開門迎客。
李赤準備了300萬元,“就算一直不賺錢,也能撐3年”。第一場演出,他花了4000塊做宣傳,最終來了4個觀眾。后來觀眾越來越多,但MAO一直都是勉力維持。
不只M A O,目前北京的Livehouse大部分都生存艱難,2015年,麻雀瓦舍因房租問題倒閉,之后在位于工體的美高美酒吧“復活”,但為了和酒吧氣質相襯,新麻雀瓦舍吊了頂,裝上水晶燈,置辦了十幾組皮沙發卡座和大理石吧臺,吧臺上擺起了馬爹利。
讓Livehouse賺錢在李赤看來并不難,只要把經營重心放在酒水和小吃上即可。之前曾有銀行找到他,希望在MAO的前廳放置兩臺ATM機,報酬能抵大半房租。李赤拒絕了,他不希望Livehouse的性質因此改變,其后果就是音樂的重要性退居次席。
“音樂是Livehouse賴以生存的根基。”李赤說。他不希望年輕人對音樂的理解局限在“小鮮肉”和“大嗓門”,“年輕人正在思想的波動期和成長期,對整個世界都在思考和探索中”。而搖滾樂給予年輕人的,是獨立思考的能力和勇氣。
沒人能準確說出音樂對人的影響是如何產生的,但當音符流入腦海,感情便開始發酵。李赤曾在陪同“逃跑計劃”樂隊巡演過程中遇到一個年輕人,演出結束后非要請樂隊和工作人員吃飯。飯桌上,年輕人端起一杯酒一口喝完,說:“你們讓我重 新相信愛情了。”
Moon曾在演出現場看到有觀眾跪在地上甩頭,那首點燃全場的歌叫《世界是塊憂傷的石頭》。
“感覺很宏大,跟生命有關,就覺得人生這么短暫,想做的事一定要去做。”Moon告訴《博客天下》。
當時她一邊聽一邊默默流淚,喜歡的女孩站在身后,她不敢回頭看。演出結束后,她向喜歡的女孩表白。這段同性之間的戀情沒有持續多久,但Moon并不覺得遺憾。
一定要用你的熱血去做最喜歡的事
Moon確信Livehouse和搖滾樂一直在塑造著她,影響了她與周遭世界的相處方式。幸運的是,她從中獲得了成長,盡管這種成長會伴隨陣痛。她一度跟父親屢屢沖突,這反倒成了她成長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她一點點挪動父女間的楚河漢界,讓父親相信她已經長大了,有權利選擇自己的生活。
現在她和父母的關系緩和了許多,她開始嘗試照顧他們,幫他們作決定。她知道父親喜歡民樂,帶著父親去Livehouse聽了一場民樂主題的演出。父親喝啤酒,她喝飲料。演出結束后她開車載父親回家,兩個人聊了最近的生活和工作,還有平時羞于表達的愛。往日里一扇橫亙在他們之間的鐵門被緩緩推開,那一刻她意識到自己真的長大了。
但她一直沒敢向父母透露自己的性取向,只是旁敲側擊講過學校里有很多同性戀人。
特立獨行在不知周身上體現得并不明顯,她認為貼標簽是“一個簡化思考的過程,一種反智的行為”。
她曾在父親的壓力下申請加入學生會。但僅僅是面試已經無法忍受,她不明白那些只比她大一個年級的學生為什么一身官僚氣。后來學生會通知她面試通過,她果斷拒絕加入,然后騙父親說自己面試沒有通過。

Livehouse源于日本,特指具有頂級音樂器材、完善的音響設備和舞臺燈光以及具有一定專業水準的小型展演場館

北京MAO Livehouse標志性的大鐵門
不知周考上大學后,本來想選自己喜歡的社會學,但父母告訴她“學這種專業要熬成老太婆才能找到工作”,于是她選擇了語言專業,“至少可以養活自己”。她已經開始擔憂北京高企的房價。
“如果要在這里生活,這是不得不考慮的。”不知周說。焦慮和迷茫一直纏繞著她,她不知道未來是怎樣的,不確定自己能不能過上想要的生活,她害怕自己的無能為力,害怕因生存的壓力而被迫去做不喜歡的事。她準備下學期去挪威交換留學。“有些人逆來順受習慣了,但我不想這樣。”
在葛優癱流行的時代,Moon想的是如何站直了。她討厭庸常的生活,母親是她的反面教材。自她出生之后,母親就辭去工作當家庭主婦,沒有自己的朋友,每天的生活都被家務和微信朋友圈填滿。
“現在大家都有點喪,每個人都避免不了,但要找到解決方式。Livehouse對我來說就意味著一種生命力,是一個加油站,讓我更有動力去面對生活。”Moon說。
她曾看過一場法國樂隊的演出,主唱是位白發蒼蒼的老先生,穿著牛仔馬甲,上面全是徽章。他的眼睛很亮,流露出熱情,“不像那些菜市場砍價的老爺爺老奶奶,他有自己的生活,有希望,如果我老了之后是這種狀態,我還挺向往的”。
以后的事還很遙遠,充滿不確定感,她唯一篤定的,就是把握好現在。這也是Livehouse里大多數年輕人當下的狀態。那扇沉默的鐵門見證著他們東來西往,留下故事,又四散而去,繼續各自普通的、開心的抑或煩惱的生活。
李赤從來沒想過清理大鐵門上的污跡,至于未來如何,他不去多想。“未來總會超出你的想象,所以就放任自流地去生活,這才是最有意義的。”
他50歲了,還是喜歡和年輕人待在一起。“面對青春,一定要用你的熱血去做最喜歡的事。”
作為年長者,他有時會犯好為人師的毛病,但轉過頭又會告訴那些年輕人,“別聽我的,我說的都是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