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德昌電影中的現代性呈現:一種反叛的凝視
林孟潔
臺灣新電影范疇中的許多部電影,有很大篇幅是此時期的導演所處理的,筆者認為都是在某種程度上,試圖為臺灣在經濟高速發展中所經歷的時代下一些具有個人色彩的注腳、批判或者反思,站在影片拍攝的時點上,由兩個方向去走。一是面向過去而生,透過對于歷史題材、事件的處理,用電影這樣具有藝術作品創造性的媒介,且并非如紀錄片般非虛構影片類型所必須遵守的一些限制,以同時可表達作者(導演)個人觀點和鋪展出文本上意義的方式,去為站在該時(如1989年侯孝賢的《悲情城市》、楊德昌的《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的片頭文字)的人們、時代、社會,去進行向更久遠之前具有獨特意義的事件,進行意義的賦予、闡釋和反思。
第二層意義則是用作品本身去面向未來而生,透過對于現狀,或者對于急遽改變的社會歷程、脈絡進行的爬梳,去預測、推斷未來社會發展的方向性和可能的脈絡。也與此同時進行全面的回顧和深刻的批判反思,但也依導演各自的鮮明獨特性格、關心傾向的差異而呈現有所不同的批判方式,后文將對楊德昌多部作品進行論述。以現代性為命題,都市與現代化已經是現代人無法脫離的宿命空間與時間。而都市的物質條件的吸引力,和科技、工業、經濟等面向的發展,也改變了臺灣社會中人們不同于以往的生活型態,現代主義的意識形態無所不在地滲透在臺灣現代化歷程中城市人們的生活里。進而連帶產生了各種形式的問題:傳統與現代的沖突,人際關系的疏離和偽善化,以往信仰的意義與理想的消失等。楊德昌個人的選擇傾向和價值信仰可以從他影片里的一些角色看出端倪。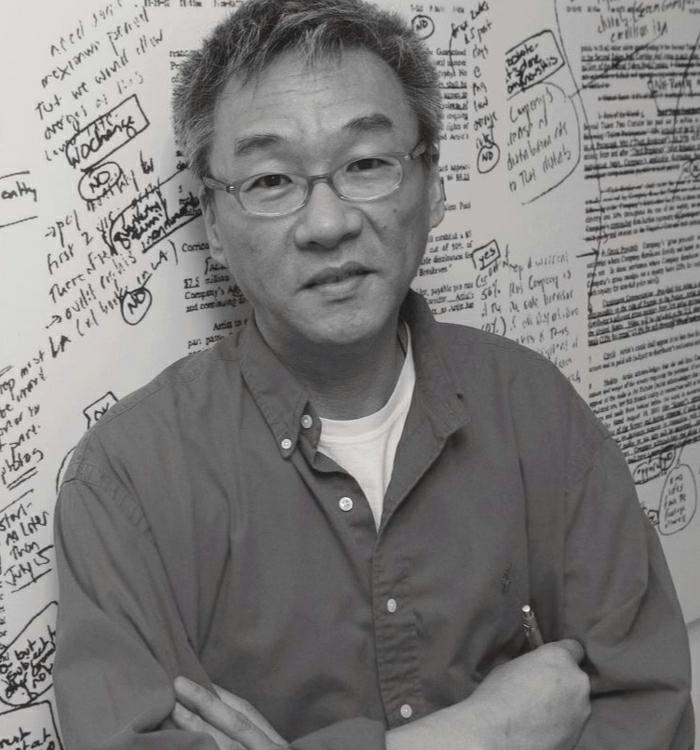
像是楊德昌關于臺北都會的系列影片,從《海灘的一天》、《青梅竹馬》、《恐怖分子》到《獨立時代》、《麻將》,記錄了臺灣從上世紀50、60年代質樸農業、鄉村社會轉型到工商業社會歷程中,都市尚未徹底、完全轉型卻又回不到過去的單純的那種困頓、荒謬與掙扎。對于臺灣都市發展典型代表的臺北的荒謬,進行一針見血的嘲弄和社會問題的探掘及批判,如《海灘的一天》中,從日本殖民史過渡、移轉的父權沙文結構和追求物質欲望的中產階級思維,以殘酷且直接的方式讓那一代的人們在虛偽的人際互動關系中漸漸長大,認清青年理想主義的不可行和隳壞崩解的理想性,在人際關系冷漠的悲劇之中進而半自愿、半被迫地可悲地順從社會的游戲規則。而《青梅竹馬》里則延續經濟擴張而割裂了臺灣社會和傳統親情關系的命題,指出城市在都會化過程中和過去傳統價值的斷裂性。楊德昌的電影里不斷探討著表面性、虛浮的現代化中城市里人們生活的片段,相互傷害以及被傷害,最終導向一個共犯結構的循環:服從、順從體制者得以留存。如《海灘的一天》里的張艾嘉愿意被社會化因此沒有死;而不愿遵守社會賦予的游戲規則者例如《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中張震飾演的小四,在封閉的早期臺灣社會中曾經純真的、具理想性的自由心靈被壓抑、傷害而選擇自我放逐,至終導向以殺戮做為反社會手段,這樣的一種微弱抗爭的極端結局,其毀滅的執行實也歸因于小明做為小四認定讓他落至此下場的一種報復,也是對社會本身的一種無聲控訴。
楊德昌此時期電影中反復對臺灣經濟發展后的新興社會問題進行質疑和批判,并且他慣用電影片頭的文字去給觀者一些訊息的暗示,需要自我判讀,例如《獨立時代》中電影開頭的引文其實就指出了楊德昌所欲探究的,中華文化傳統儒家倫理結構在面臨時代轉換時所產生的巨大困惑(即論語內文:子適衛,冉有仆……子路篇等句。以及“臺北在短短的20年間,變成世界上最有錢的城市”等),也可從英文片名《A Confucian Confusion》中看出其內在想要探討的意旨。而在這部片子里一反過去的低調壓抑,想要追求新方向的改變和突破,但卻又稱不上成功的處理,一如黃建業所言:因為第一次在電影里處理戲劇的緣故,在人物塑造與喜感建立方面,都出現了過去鮮見的明顯失控現象。卻也因而成為契機,在后面的《麻將》中體現更純熟的嘲謔、嬉戲怒罵、近Woody Allen式神經質快節奏的劇情展演。
在另一例子中,他卻又不見得在影片末了真的提供意義的解釋,這也讓讀者擁有更大的解釋權和想象的空間。以《麻將》開頭的“臺北市陳姓富豪失蹤了據說負債高達百億”等文字為例,這樣的敘事引起了觀者的好奇心,進而開展了影片尋找他兒子的一個歷程,但到影片中后段其實幾乎已經放棄了這樣的命題追尋,加入了更多組人物錯綜復雜的關系,最后導向楊德昌式的憐憫和救贖企圖:結尾的擁抱,看似已經沒有與片頭的直接關聯性,但卻又實則迂回地呼應和產生某種連結。楊德昌的電影允許觀者自行解讀并豐富它的可能性,他從不希望任何一家一派的論述去局限住他電影的可能性,也不希望存在著所謂的標準答案。而在語言使用上,《麻將》也和《青梅竹馬》一樣玩弄到極致的語言特性,除了國語外,還有英語、法語、閩南語等,大量使用的英語對白其實是楊德昌的一種策略。用外語來批判西方對臺灣的殖民式的心態,在臺北一味地追求現代化、國際化而放任西方商人、投機者一同將這個都市視為俎上肉一起合力宰割時,楊德昌在用盡力道嘲諷、批判的同時,其實還是有一些不忍心隱隱然的流露,似乎和前述的《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一樣其實他的關懷里還是帶著一點溫暖的溫度,以小四、和四人幫為主的當代臺灣青少年問題探討總是會讓楊德昌心軟,而稍微磨平他尖銳的批判刀鋒力道,為整個城市的荒謬和沉淪提供一種救贖的可能性,像《麻將》中的綸綸所代表的良心和與馬特拉間真愛(而非其他三人的放棄相信感情的玩弄性作為)的力量,才是唯一的救贖力量和迷航的出口。這樣臺灣男、法國女的組合也展現出對于西方帝國、殖民心態侵略者的一種反制,長長的深吻結尾也代表了楊德昌的某種對于臺灣在現代化迷失自我的困境中,尋得出路的一種期望和失望但并不絕望的關懷。
再論及楊德昌的《一一》,如果說在《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中他展現了少有的放任與自由,在《一一》中則看到他少有的圓融與和諧感。《一一》從一場近似喪禮氣味的婚禮中開展故事,又在一場近似婚里的喪禮中結束。昏迷的婆婆在這段日子里好像發生了些什么,又好像什么也沒發生。
在《一一》的以“家庭”為主的敘事軸線當中,所有的年齡都有一個代表角色,所有的人又都存在著一定程度上的關聯,彼此的生命相互投射到各自身上,隨著情節的推展及演進,原初看似有些混亂的諸多小事件、人物等慢慢地回歸到一種秩序的平衡感上面,把那些意外和偶然的至終導向安定和圓融的統整結尾。《獨立時代》、《麻將》反映的是臺灣社會轉型時期的混亂,如同前述前者反映的是新時代下人倫秩序的關系意義的再定義,而后者則是面對商品化、物質化的城市蓬勃發展同時要如何去尋找城市中人與人的關系和出路的一種意義,《一一》之所以成為楊德昌最為世人所道的極大原因,大概是他在保持對于都市的高度觀察力的同時,也保留了《獨立時代》和《麻將》的“喜”,拋棄了它們的“鬧”。這也是他的最后一部電影,《一一》整個故事一如闡述著老莊哲學“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的精神,這部以家庭為主軸漸次從成員身上發展出各自生命故事的片子,把日常的瑣碎提煉出深刻的意義,講的是再平凡也不過的日常生活,但往往越簡單的東西里蘊含著的,是越復雜的道理。從“一”的簡單,到“一一”的次簡單,他多一點,但并不多太多,因而這部影片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簡約和極致復雜的深刻意義。
楊德昌電影中承載著高度的社會使命感和歷史感及憂患意識,且是少數在臺灣電影中具備可以去處理宏大架構、復雜情節交錯但結構卻完整、清晰的導演,也具備自己獨特的一套影像敘事語言,例如他總是傾向冷靜且理性地再現和記錄生活里的某些真實樣態,以刻意限制攝影機移動的方式大量使用固定機位和長鏡頭的拍攝手法,讓攝影機仿佛一種真實的記錄器,例如《恐怖分子》的前20分鐘的定鏡拍攝,但又由楊德昌再次進行事件序列的重組、安排而產生楊德昌式的意義。他也善于透過對演員的調度和空間、框、結構的不同使用方式,如《一一》中全片用得淋漓盡致,去讓限制里生出一種無限的感受性。他的理性也表現在少用特寫而多用中景、全景、遠景的較疏離的拍攝方式,使平視的距離感呈現在觀者和作品之間。為了達到他自己對于影片的某些品質和藝術性的追求,1989年成立的楊德昌電影公司也使他的理想實踐成為可能。就僅僅生老病死喜怒哀樂,看似庶民、日常、不足為奇,但是楊德昌利用了通俗的元素,包括愛情、家庭以及各種形式的別離、尋找救贖等待被拯救諸般故事,去為他自己所相信和質疑的事情說出一個又一個好聽、好看的故事,不僅可以顧及藝術性、哲學思考,也可以兼顧讀者的想聽好聽故事的欲望,為臺灣的現代化歷程寫下獨樹一格的注腳,也用電影去記錄下了大時代下小人物生命故事里最深刻的意義和獨特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