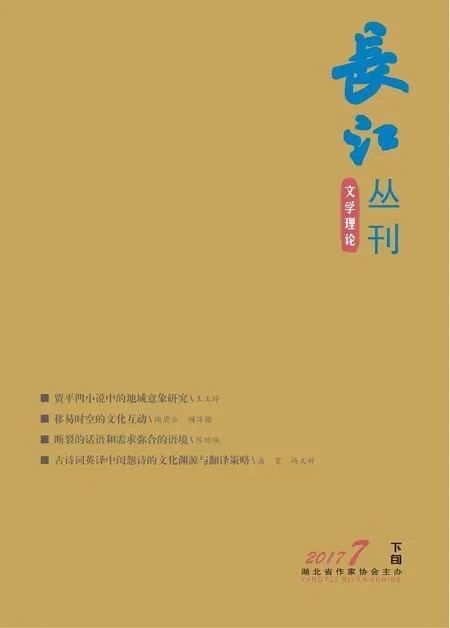現(xiàn)代奧狄浦斯的悲劇
——讀福斯特的《離開科洛諾斯之路》
凌瑞寧 朱 瑩
現(xiàn)代奧狄浦斯的悲劇
——讀福斯特的《離開科洛諾斯之路》
凌瑞寧 朱 瑩
人們不能選擇自己生命的開始,卻可以選擇自己生活的方式、生活的追求和生活的價值觀念。可以真實(shí)地生活在以綠水、青山和古樹為象征的希臘古典的鄉(xiāng)村,也可以茍活在位于工業(yè)化的大都市倫敦的公寓,整日忍受象征工業(yè)發(fā)展的自來水的咕嚕噪聲。《離開克洛諾斯的路》利用像征和暗喻的手法向人們揭示了傳統(tǒng)價值觀念與現(xiàn)代工業(yè)發(fā)展之間的矛盾與沖突,也進(jìn)一步向讀者展現(xiàn)了面對資本主義工業(yè)發(fā)展而產(chǎn)生的思考以及人們?nèi)绾螌ι顑r值觀念進(jìn)行選擇這一嚴(yán)肅問題。
暗喻 象征 離開科洛諾斯之路
英國著名小說家E. M. 福斯特(E.M. Forster, 1879-1970)的短篇小說《離開科洛諾斯的路》(“The Road from Colonus”)被公認(rèn)為福斯特最優(yōu)秀的短篇小說之一。①通過小說中主人公盧卡斯先生,福斯特象征性地向生活在現(xiàn)代社會的人們揭示了西方人文主義的傳統(tǒng)和價值觀念與西方現(xiàn)代工業(yè)發(fā)展之間的矛盾與沖突。這篇充滿希臘神話暗喻和象征的小說,充分揭露了20世紀(jì)初期英國的中產(chǎn)階級在面對生活選擇時的蒼白和迷惘,深刻反映了福斯特的人文主義思想和面對現(xiàn)代資本主義工業(yè)發(fā)展產(chǎn)生的思考。盧卡斯先生由于沒能抓住在希臘旅游時發(fā)現(xiàn)的生活真諦而回到倫敦,在公寓中遭受自來水管發(fā)出的咕嚕噪音、隔壁鄰居孩子們玩耍時的吵鬧聲以及貓和狗的叫聲,整日苦不堪言,抱怨?jié)M腹。他已喪失了生活的激情和興趣;他所能做的只是不斷地向房東寫信訴說對房子的不滿,卻永遠(yuǎn)得不到回復(fù),伴隨他的也只會是水管發(fā)出的稀里嘩啦的噪聲以及蒼白的老年生活和終結(jié)生命的死亡。這種生活種沉悶枯燥,毫無生命的活力和生命的意義。這種狀況與他在希臘旅游時發(fā)現(xiàn)的簡單、純樸但卻真實(shí)的生活恰成鮮明對照。這種對照反映了福斯特對現(xiàn)代工業(yè)的發(fā)展和這種發(fā)展與人的生活之間關(guān)系所作的認(rèn)真和深刻的思考。
一、水:樸實(shí)自然的生活
盧卡斯先生來到希臘想實(shí)現(xiàn)他的一個已經(jīng)40年之久的夢想。“40年前他染上希臘文化熱,覺得一生中只要能去一趟那片土地也不算枉活。”②但是來到希臘后他卻發(fā)現(xiàn)雅典塵土皚皚,德爾斐陰雨連綿,而德爾摩比利也是平庸乏味。其他游人不斷發(fā)出陣陣驚嘆,但他覺得雅典和倫敦不分軒輊,“希臘和英格蘭一樣,是一位落入暮年的老人”。他最后想與生活和命運(yùn)抗?fàn)幰幌拢墒桥c他同行的那些虛偽的英國人使他最后的希望走向失敗。
盧卡斯先生在希臘鄉(xiāng)間小客棧的經(jīng)歷——準(zhǔn)確地說,他在那兒親眼看到的古樹,親口喝的泉水,親眼目睹的藍(lán)天——充滿了豐富的象征意義和深刻的暗示;這是作者崇尚的一種價值觀念。來到那個鄉(xiāng)間客棧,來到那棵大樹旁,盧卡斯先生的內(nèi)心起了變化。“希臘是年輕人的土地,”他自言自語地說,“但是我要成為其中一分子,我要擁有它。樹葉一定要再次變綠,水一定要是甜的,天空一定要是藍(lán)的。40年前就是那樣,現(xiàn)在我一定要把它們搞回來。我不愿意變老,我不再裝模作樣了。”
福斯特用非常浪漫和不乏象征的手法向盧卡斯先生和讀者展現(xiàn)了一條獲得拯救和重生的道路。那棵大樹傾靠著客棧生長著,樹心已被人們用來燒炭了。一股湍急的泉水從活著的樹干向外流淌著,使樹干長滿了綠蕨和青苔。當(dāng)?shù)厝巳匀槐3种爬系纳罘绞剑瑢γ篮蜕衩氐氖挛锶猿钟惺愕墓Ь础K麄冊跇渖峡塘松颀悾颀惿戏胖槐K燈和一幅圣母瑪利亞的像,使她既有水仙女的優(yōu)美,又有樹仙女的妖嬈。盧卡斯先生面對這個神龕猶豫了,他想知道泉水的出處,想“成為其中一分子”。這種欲望驅(qū)使他鉆進(jìn)了大樹。樹洞內(nèi),泉水源源不斷又悄然無聲地從樹根和大地那看不見的縫隙中向外涌著。樹內(nèi)掛著許多諸如腿、胳膊、大腦和心模樣的還愿物,這些還愿物“都象征著某種重新獲得的力量、智慧和愛”。福斯特寫到:“這里的自然沒有絲毫的孤獨(dú),因?yàn)槿祟惖陌С詈蜌g樂都涌進(jìn)了大樹的內(nèi)心”。在這里,盧卡斯先生發(fā)現(xiàn)并找到了他所夢寐以求的:“盧卡斯先生嘗了一下泉水,泉水是甜的,他舉目從黑黑的樹洞向上看去,發(fā)現(xiàn)天空是藍(lán)的,樹葉是綠的”。那是生活的本來面目,那是自然的真實(shí)顏色。顯然,從象征意義上講,盧卡斯先生在這里找到了傳統(tǒng)和真實(shí)的生活,實(shí)現(xiàn)了40年前的希望。這一時刻也就是喬伊斯所說的對生活真諦的“領(lǐng)悟”(epiphany)。用福斯特自己的話說,就是“永恒的時刻”③這棵大樹的樹干外集有簡樸的傳統(tǒng)和古老的神話,樹干內(nèi)的樹洞又有充滿生命的活力和永不枯竭的生命之源:“泉水源源不斷又悄然無聲地從樹根和看不見的大地的縫隙中涌現(xiàn)著”。在這種充滿自然的真實(shí)和簡樸的傳統(tǒng)相結(jié)合的氛圍中,盧卡斯先生背靠著樹干閉上了眼睛。此時,“他產(chǎn)生了一種奇妙的感覺,覺得自己在移動,但卻很平靜,一種一個游泳的人在與海浪搏擊后發(fā)現(xiàn)海浪會把他帶到目的地的感覺”。
水乃生命之源,因此是生命的象征。盧卡斯先生此時面對和品嘗的水,是自然中的泉水,是從古老大樹的樹根下和大地的縫隙中無聲無息地、不斷地涌出的。作者的意圖顯而易見:這種出自大地的水象征著古樸簡單、真實(shí)自然的生活。由于出自大地,所以永不枯竭。毋容置疑,這種生活,正是盧卡斯先生要尋找的。這種自然的泉水,與盧卡斯先生在倫敦公寓中所遭受的那種不斷發(fā)出咕嚕噪聲的自來水形成截然不同的對照。自來水是城市化的體現(xiàn),是工業(yè)化的標(biāo)志,雖然包含著工業(yè)文明的發(fā)展,但也含有對工業(yè)文明的發(fā)展所付的代價。福斯特已經(jīng)在小說中指出了工業(yè)化的后果:盧卡斯先生在希臘看到的是“雅典的塵埃、德爾斐的陰雨…”作為歐洲文明的發(fā)源地,希臘遭受了工業(yè)文明發(fā)展帶來的嚴(yán)重后果。福斯特對此發(fā)出了他的聲音:“某種更大的東西出了差錯”。福斯特一語而過,卻留給讀者更多的理性思考。
二、科洛諾斯:拯救
科洛諾斯是希臘神話中奧狄浦斯王在女兒安提戈涅的伴陪下在希臘流亡的終點(diǎn),是他解脫痛苦、拯救靈魂和獲得新生的地方。但是盧卡斯先生這位現(xiàn)代的奧狄浦斯在來到科洛諾斯時,即沒有解脫生活的痛苦,也沒有獲得心靈的重生。
在小說中,科洛諾斯小客棧的女人主人以及她的家人,象征著古老的生活和文化傳統(tǒng);艾絲爾、雷厄姆和福爾曼夫人則象征著英格蘭膚淺、勢利、頭腦愚鈍的中產(chǎn)階級。盧卡斯先生在古樹中對生活升華的感覺,被象征著勢利和淺薄的艾絲爾、雷厄姆和福爾曼夫人等人所打斷。他們把盧卡斯先生從樹洞中拉出來的舉動,表面上是出于對盧卡斯先生安全的擔(dān)心因而可以冠以“拯救”,但實(shí)際上是對他生活的強(qiáng)差人意。他們把他帶離希臘的鄉(xiāng)間回到倫敦公寓,實(shí)際是把他帶回到一種毫無生氣和活力的生活。可以說,他被帶回到一種死亡。
鄉(xiāng)間小客棧的生活方式古老真實(shí),充滿了純樸和傳統(tǒng)的氣息,顯然象征著一種生活方式和價值觀念。彎腰紡線的老婦人,不停活動的小豬仔,老婦人面前不斷變小的毛線球——這些都對到訪的盧卡斯先生都充滿了含意。那位騎著騾子回家的年輕人,沿著小河一邊走一邊唱歌,盧卡斯先生覺得“他的狀態(tài)很美,他的問候充滿了真誠”,他還在不斷搖擺的長春花和小河的潺潺流水中發(fā)現(xiàn)了新的意義。此地、此時和此刻的盧卡斯先生覺得自己“不但發(fā)現(xiàn)了希臘,而且還發(fā)現(xiàn)了英格蘭和整個世界,發(fā)現(xiàn)了生活的全部”。他產(chǎn)生了一種欲望,一個一點(diǎn)也不荒唐的欲望:“在那棵大樹內(nèi)再掛一個還愿物:一個完整的人的模型”。
福斯特這些象征性極濃的描寫包含著深刻的含義。為報答找到的新生命和新的生活方式,盧卡斯先生的還愿物不就是“一個完整的人的小模型”嗎?小客棧的一家人就是這種新生命和新的生活方式的代表,科洛諾斯就是盧卡斯先生的真正歸宿。
兩種不同的生活方式和價值觀念的矛盾和沖突,最后發(fā)展成了兩軍對壘,甚至使用了原始的方式進(jìn)行搏斗——石頭和拳頭。盧卡斯先生留在客棧下榻還是跟隨艾絲爾等人一起繼續(xù)旅游,成了雙方爭奪的焦點(diǎn)。英國游客們認(rèn)為客棧有跳蚤,還有比跳蚤更可怕的可能:希臘人可能用刀子捅死他們。福爾曼婦人和艾絲爾的這些恐嚇沒有攔住盧卡斯先生。他執(zhí)意在紡線老婦人開的客棧下榻。那位老婦人及家人好像有一種天生的本能(本能在福斯特的小說里非常重要),他們心里明白英國人為什么爭執(zhí)。老婦人停下紡線的活,用期待的目光注視著盧卡斯先生;老婦人的兒子和他兩個孩子站在路卡斯先生身后,“宛如支持他一般”。在艾絲爾的指揮下,格雷厄姆強(qiáng)行將盧卡斯先生抱到騾子上繼續(xù)前行,結(jié)果沒走幾步就被孩子們投擲的石塊擊中后背。老婦人的兒子試圖奪過盧卡斯先生坐騎的韁繩,卻被格雷厄姆發(fā)揮出拳擊手的本領(lǐng)(“格雷厄姆是一位優(yōu)秀的拳擊手”)而幾下將他擊倒在地。石頭和拳頭這種原始的爭戰(zhàn)方式,將雙方的沖突推向了高潮。“拯救”盧卡斯先生的英國隊(duì)伍“在混亂中撤退了”,他們強(qiáng)行帶著可憐的盧卡斯先生離開了“泉水是甜的…天空是藍(lán)的,樹葉是綠的” 的科洛諾斯。如果說奧狄浦斯王最終來到并歸宿在科洛諾斯從而得到靈魂的拯救,那么盧卡斯先生則最終離開了科洛諾斯而沒有在那里留下——在象征層面講,他離開了本應(yīng)得到的拯救。
三、盧卡斯先生:現(xiàn)代奧狄浦斯
盧卡斯先生可憐悲哀的活著,與科洛諾斯的老婦人和她的家人死亡,是小說產(chǎn)生的另一個對比。回到倫敦,艾絲爾收到福爾曼夫人從希臘寄來讓他們種養(yǎng)的花草,名叫長春花。福斯特通過包裹長春花草用的報紙,向艾絲爾流露了發(fā)生在科洛諾斯可怕的消息:大風(fēng)刮倒大樹,砸死了經(jīng)營客棧的老婦人和她的家人。發(fā)生悲劇的那一天,正是盧卡斯先生一行經(jīng)過科洛諾斯那天的夜晚。就在艾絲爾為自己沒有聽從盧卡斯先生的意思在客棧過夜,而是強(qiáng)行把他解“救”走的舉動而感到慶幸時,小說的反諷也展現(xiàn)得淋漓盡致。盡管大風(fēng)刮倒大樹砸死老婦人和她家人,但他們的死亡與自然的真實(shí)渾然一體。死亡是生命的一部分,它是痛苦的,但卻是真實(shí)的。雖然盧卡斯先生還活著,但是那種可憐和虛偽的生活毫無意義。福斯特向人們轉(zhuǎn)達(dá)的信息是:與其在倫敦遭受自來水的噪音之苦和折磨,倒不如剝?nèi)ヌ搨蔚耐獗恚鎸φ鎸?shí)的生活,勇敢地接受真實(shí)自然和有意義的生活,哪怕那種真實(shí)是死亡。
長春花的象征意義也充分揭示出作者的含義。根據(jù)荷馬的《奧德賽》,長春花是生長在理想樂土(Elysium)上的植物,而理想樂土是只有英雄死后才能去的地方。長春花的象征意義顯然是讓人們這樣理解科洛諾斯的老婦人和她家人的死亡:他們的生活是真實(shí)的;他們有勇氣面對真實(shí)但有痛苦的生活;他們是不乏勇氣的英雄。與他們形成明顯對照的是那些典型的英國中產(chǎn)階級,他們的生活虛偽、自私、膚淺,毫無真實(shí)可言。
在希臘旅游時,福斯特充滿反諷意味地安排福爾曼夫人把盧卡斯先生和女兒艾絲爾比作奧狄浦斯王和女兒安提戈涅。如果將奧狄浦斯王和盧卡斯先生比較,會有許多有意義的發(fā)現(xiàn)。
根據(jù)希臘神話,眾神知道奧狄浦斯不是自愿違反自然法律和人類最神圣的道德原則,所以神諭告訴奧狄浦斯經(jīng)過一個長時期的流浪抵達(dá)命運(yùn)女神指定的地方,他將在那里得到復(fù)仇女神的解脫。那個地方就是科洛諾斯。奧狄浦斯篤信神諭,在希臘流浪,最后來到科洛諾斯。在一個雷聲轟鳴的夜晚,他精神抖擻,神清氣爽地步入復(fù)仇女神圣林中大地裂開的地縫,從得到了解脫和靈魂的拯救。盧卡斯先生在希臘旅游也來到科洛諾斯,他也想尋找生活的意義和發(fā)現(xiàn)生活的真諦以得到解脫。最終以失敗告終。
在科洛諾斯,奧狄浦斯王在得到解脫前也停在一個空心大樹下喝了泉水。他用自然的泉水洗去流亡的塵埃,換上女兒為他準(zhǔn)備的節(jié)日華服迎接死亡。盧卡斯先生在科洛諾斯也停留在一棵空心大樹下喝了泉水。但是女兒來為他換掉在空心大樹內(nèi)沾上來自大地的泥土的衣服,他穿著這身與大地沒有聯(lián)系的衣服離開了本應(yīng)得到拯救的地方。
《科洛諾斯之路》充滿了象征和暗喻。福斯特這種有意識又充滿詩意的象征性描寫,將他本人對現(xiàn)代工業(yè)發(fā)展對人的生活帶來的玷污,對人的心靈造成的傷害,對生活真諦的向往和追求,以及對個人生活和個人生活價值的實(shí)現(xiàn)等這些復(fù)雜深刻的重大問題,既自然又深刻地躍然紙上,令人讀來浮想連翩,回味無窮。

1927年福斯特在劍橋大學(xué)“三一學(xué)院”關(guān)于小說作過一系列講座。在講座中他提出了小說情節(jié)中“圖形”(“pattern”)這一概念④。如果把他提出的關(guān)于小說情節(jié)中“圖形”的概念應(yīng)用于他的《離開科洛諾斯之路》就會發(fā)現(xiàn),這部短篇小說的情節(jié)與希臘神話中奧狄浦斯王在科洛諾斯的故事構(gòu)成了一個獨(dú)特的圖形,一種如同照片的正負(fù)片關(guān)系的圖形。換句話說,如果把其中之一比作上衣的左一半,那么另一個就形成了上衣的右一半(如上圖)。無疑,這種情節(jié)的圖形增加了小說的藝術(shù)美,使它的藝術(shù)性進(jìn)一步凝聚,從而增加了小說的藝術(shù)價值。
在文明和工業(yè)發(fā)展如此之快的現(xiàn)代社會,福斯特的力量不再為現(xiàn)代人指出一條通往拯救的路;他的力量在于喚醒人們通過理性能力產(chǎn)生認(rèn)真的思考。如果他在《霍華茲別業(yè)》(Howards End)探討的文化與工商業(yè)的結(jié)合頗有悲觀意味,在《印度之行》(A Passage to India)中描繪的不同的個人、階級、階層、種族、文化、宗教、國家和民族等之間的和睦和諧難以實(shí)現(xiàn)——騎著馬的菲爾丁和阿奇茲各自表達(dá)了要做“朋友”的心愿,但是他們各自的馬卻突然轉(zhuǎn)向,分道揚(yáng)鑣,那里的蒼天、大地……神廟、監(jiān)獄、宮殿、鳥兒、動物、客棧……所有這一切都異口同聲的說:“不,不在這里”,“不,不在此時”——那么,《離開科洛諾斯之路》中豐富的象征和隱喻,卻使人們對生活的價值和如何選擇生活這一嚴(yán)肅問題產(chǎn)生認(rèn)真和深刻的思索。這也許就是福斯特創(chuàng)作《離開科洛諾斯之路》的動機(jī)之一吧。
注釋:
① Norman Kelvin.E.M. Forster: the Man and His Works[Z].Forum House,1969.
② E. M. Forster.“The Road from Colonus”,CollectedShort Stories,Middlesex: Penguin Books[Z].1954.
③福斯特另一本著名的短篇小說就叫《永恒的時刻》(“Eternal Moments”).
④ E.M.Forster.Aspects of the Novel[Z].Harcourt,Brace & World,1955,ChapterVand Chapter VIII.
(作者單位:中國海洋大學(xué))
凌瑞寧(1990-),女,漢族,山東臨沂人,碩士研究生,中國海洋大學(xué)外國語學(xué)院,研究方向:英語語言文學(xué);朱瑩(1992-),女,漢族,河北邯鄲人,碩士在讀,中國海洋大學(xué),研究方向:英美文學(xu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