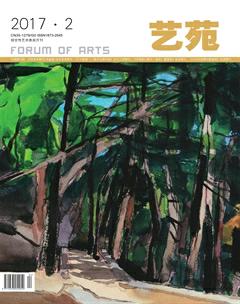紀錄片的故事化敘事探析
林余穎+++閻立峰
【摘要】 故事化敘事作為紀錄片創作的一種敘事策略,強調情節因素,突出戲劇沖突和矛盾,以此塑造鮮活的人物形象,增強故事的感染力,使觀眾產生情感上的共鳴。文章以系列紀錄片《我們的留學生活——在日本的日子》為研究對象,從敘事題材、敘事視點、敘事方法和敘事技巧四個方面,探討其故事化敘事策略的運用。
【關鍵詞】 故事化敘事;紀錄片;《我們的留學生活》
[中圖分類號]J90 [文獻標識碼]A
故事是對一個事件發展過程的描述,強調情節的連貫性和生動性。故事對人有著天然的誘惑性:人生來喜歡聽故事,而不喜歡聽枯燥的道理和刻板的描述。一個故事是否吸引人,除了故事內容本身是否精彩外,還取決于講故事的方式是否得當。平常的故事也能通過豐富的敘述手段而變得扣人心弦。
故事化敘事強調了“化”這一動態詞語,即運用故事的特點和元素來敘述事件,使之具有故事的特征。格里爾遜認為紀錄片是“對現實生活的創造性處理”,故事化敘事則可視為紀錄片“創造性處理現實”的一種方式,即在真實記錄的前提下,借鑒戲劇創作中講故事的方法,運用故事化的元素來組織某一事件,并結合影像剪輯和聲音配樂等,使紀錄片的呈現具有故事的特征,以此提高紀錄片的觀賞性和趣味性。
20世紀90年代,中國出現了一波赴日留學潮。紀錄片《我們的留學生活——在日本的日子》(以下簡稱《我們的留學生活》)便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創作產生的。該片以在日本留學、生活的中國留學生為聚焦對象,講述了中國人在異鄉拼搏的故事。《我們的留學生活》曾先后在中日兩國播出,不僅在國內引起強烈反響,也在日本創下年度最高收視紀錄;其中的兩部作品——《小留學生》和《含淚活著》先后獲得被譽為日本奧斯卡的“日本放送文化基金獎”,得到了國內與國外、業界和市場的雙重肯定。時至今日,《我們的留學生活》中的每個故事、每個人物仍能給觀眾帶來諸多感動。本文將以《我們的留學生活》為研究對象,結合紀錄片創作的特點,分析其故事化敘事的策略。
在戲劇創作中,一個完整的故事應該包含人物、環境和情節,具有開端、過程、高潮和結局。套用到紀錄片創作的領域,筆者認為,紀錄片的故事化敘事策略主要體現在敘事題材、敘事視點、敘事方法和敘事技巧等四個方面。
一、敘事題材:選擇有故事的人物
人物是故事化敘事的核心線索。紀錄片大師尤·伊文思認為:“紀錄片最合乎邏輯的發展就是人物化,即通過個人的見聞或遭遇來展現紀錄片的內容。”[1]261-276選擇一個有故事的人物,借由人物的故事來展開紀錄片的內容,以此傳達創作者的創作意圖,是紀錄片故事化敘事的一個重要策略。
好的人物題材不僅能讓紀錄片敘事“故事化”更為容易,也能吸引觀眾的注意力。《我們的留學生活》選擇在日中國留學生為拍攝對象,本身就具有極強的故事性。一方面,留學生群體對于觀眾有獨特的吸引力:國內觀眾對身處異國他鄉的同胞們總是抱有一種天然的關切心理;國外觀眾也好奇于這些“外來客”在本國土地上的生活狀況。另一方面,本片選擇的一些留學生,其經歷似乎不同于人們所想象的那般具有光鮮亮麗的外表:有人丟了簽證淪為“黑戶”,以非法手段艱難謀生;有人為了掙錢留在日本,8年未和親人相聚;有人執著于一紙博士文憑,12年來和家人矛盾重重。這些經歷不僅有悖于觀眾對于留學生活的期待,也成為創作者為滿足人們好奇心而展示的素材,能最大程度地調動觀眾的觀賞興趣。
另外,紀錄片的創作者善于通過人物故事來還原人性。人性是人類最普遍的、也是最容易打動人的東西。《我們的留學生活》之所以能在中、日兩國同時引發強烈的社會反響,并在專業和市場領域獲得雙重肯定,作為共同精神基礎的“人性”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創作者并非簡單地通過紀錄片展現生活流的場景,而是通過有表現力的畫面進行人性的挖掘,喚起觀眾在情感上的共鳴,從而引發觀眾對于自身的觀照和“人”的思考。不同于其他致力于表現人性復雜的作品,《我們的留學生活》重在挖掘人物身上正面、積極和善良的一面。蘇格拉底認為:“善是人的內在靈魂,世界上沒有人自愿作惡。”片中人物的身份背景、性格特點不盡相同,但還原到人性層面,卻有著相似的情感:會因生活環境的落差而產生失望的情緒,因語言環境的陌生而面露無助,因思念家鄉和親人而留下淚水。但最終,他們都會選擇在逆境中保持樂觀、向上的生活態度。紀錄片通過展現個體身上的人性閃光點和人性中共通的因素,強烈地震撼和感染了熒幕前的觀眾,也讓紀錄片的教化功能在故事化敘事中得到了充分實現。
二、敘事角度:第三人稱結合全知視點
敘事人稱有人稱敘事與非人稱敘事之分。人稱敘事包括第一人稱、第二人稱和第三人稱敘事。第一人稱敘事以“我”或“我們”為敘事中心,雖帶有強烈的個人主觀色彩,但也因為有了人的參與而顯得更加真實;第二人稱的敘述者直接稱呼被敘述人物,以旁觀者的姿態講述他人的故事,但不涉及人物的內心;而第三人稱敘事的敘述者較為自由,既能詳盡地敘述故事的全貌,也能描繪人物的內心活動。紀錄片運用的敘事人稱以第一和第三人稱居多。
敘事人稱常與敘事視點緊密聯系在一起。如果說敘事人稱解決的是“誰說”的問題,那么敘事視點解決的就是“誰看”的問題,即創作者站在何種角度給觀眾講故事。不同的敘事視點賦予敘事內容多樣的表現力。美國學者華萊士·馬丁認為:“敘事視點不是作為一種傳達情節給讀者的附屬物后加上去的,相反,在絕大多數現代敘事作品中,正是敘事視點創造了興趣、懸念乃至情節本身。”[2]131可以說,敘事視點是故事化敘事中富于創造力和表現力的因素。一般意義上,敘事視點可分為全知視點和限知視點。相較于限知視點的限制性,全知視點下的敘述者比任何人知道得都多,表現為如同上帝一般全知全能地掌握故事的走向和人物的內心活動。
《我們的留學生活》主要采用第三人稱結合全知視點的敘事模式。敘述者擁有一種“無所不知”的特權,敘述者雖未出現在畫面中,卻可以不受時空所限,從各個角度、各個方面為觀眾講述一個完整的故事。具體表現為:在時間上,該片極力遵循時間順序,按照人物“初來日本—適應日本—融入日本—離開日本”的順序展開敘述,對人物的拍攝時長往往持續到2年以上;在空間上,該片盡可能多地涵蓋人物出沒的地點,包括居住場所、工作(打工)場所、學習場所等,甚至跨地域拍攝人物在國內、國外分別的生活場所。此外,第三人稱結合全知視點的敘事模式還能模擬劇中人的目光,使觀眾產生一種真實的在場感。這種模擬是通過鏡頭之間的銜接來實現的:先用一個鏡頭表現主人公“在看”,接著出現“被看”的場面和對象,由此產生了一種模擬劇中人目光的效果。如分集《初來乍到》里出現了主人公王爾敏坐在電車里,望向窗外的一幕,下一個畫面則是車外的風景和車內交談的日本人;隨即,鏡頭又給向王爾敏——她正低著頭,不一會兒又望向窗外。此時,畫面變成了東京夜幕降臨的場景。幾個鏡頭下來,觀眾的視線似乎也在跟隨者劇中人的目光,對異國他鄉的一切感到既新鮮又陌生。
情感化的畫外音解說,也是第三人稱結合全知視角在《我們的留學生活》中的重要體現。解說除了掌握事物的發展走向,還能生動描述人物的內心活動、感情變化等。解說雖能使紀錄片的故事呈現更完整、具體,便于觀眾清晰地理解創作者想要傳達的意圖。但從另一個角度來說,解說也限制了觀眾對于畫面的想象。一千個讀者尚有一千個哈姆雷特,何況現實本身即是多義的,不同的觀眾對于紀錄片所拍攝的畫面亦有不同的解讀。《我們的留學生活》熱衷于使用描述性的解說文字,配以解說員張麗玲富有情感的聲音語調來解讀人物的行為,全知地描述人物的內心活動,雖有助于觀眾的理解,但也將畫面限制在某一意義之內,扼殺了現實的多義性,限制了觀眾的自我思考。
三、敘事方法:制造沖突和矛盾
生活本身就是一個充滿沖突的矛盾體。按照黑格爾的觀點,沖突一般需要解決,所以,“充滿沖突的情境特別適宜于用作劇藝的對象”[3]260。沖突是戲劇創作的主要旋律。生活本身就是由無數沖突構成的,沖突就是生活的本質。在紀錄片創作中,敘述者將這些沖突、矛盾加以選擇和概括,形成跌宕起伏的故事情節,成為故事化敘事的主要方法。《我們的留學生活》也運用了許多沖突制造的策略:
一是通過細節來展現沖突。“細節是事物的存在方式,對細節的感知,是人體驗世界、理解世界并獲得感染的基本途徑。”[4]101《我們的留學生活》有意通過描摹人物和環境的細節,凸顯人物內心的掙扎,以及人物與周圍環境之間的沖突。片中用大量的鏡頭展現留學生的生活環境:居住條件差——“隔音效果差”、“沒有洗澡間”,甚至“連家具都是撿來的”;生活壓力大——為了支付生活費和學費,不得不“打多份零工”;“每天晚上兩三點才能到家”。以此種種來展現人物與外在環境之間的沖突。同時,《我們的留學生活》也注意捕捉人物面部表情和動作變化,如生硬的笑容、自嘲的神情和不自覺的小動作等,用特寫鏡頭打造人物的內心世界,揭示人物在特定環境中內心沖突。
二是注重呈現多重矛盾沖突。片中的矛盾不是單一的,一個人的身上往往交織呈現著多種矛盾。如分集《我的太陽》中呈現的多重矛盾就包括:主人公與妻子因金錢而產生的沖突(人與人之間的矛盾)、主人公的學業壓力與打工賺錢的沖突(人與環境之間的矛盾)、主人公內心對家庭的內疚和追求學業的信念的沖突(人物內心的沖突)等。一個矛盾還未解決,又出現了新的矛盾。《我們的留學生活》通過不斷制造矛盾沖突,反復交織在個人或家庭的身上,營造出主人公“命途多舛”的氛圍,在吸引觀眾持續關注的同時,也推動故事朝著新的方向發展。
四、敘事技巧:設置突轉和懸念
亞里士多德將“突轉”視為戲劇創作中安排情節的一種敘事技巧,指情勢“按照可然律或必然律”突然向相反的方向轉變。[5]41從紀錄片的角度來看,突轉一方面使事物的發展偏離觀眾的預期,增強了故事的曲折性和可看性。另一方面,突轉也有助于揭示人物的性格特征。因為突轉往往是矛盾沖突的高潮,而高潮又能使人物的性格得到最為充分的展示。[6]116-124《我們的留學生活》中亦有不少分集采用了突轉的敘事技巧,推動了全片的故事發展。如分集《我的太陽》有意使用突轉的敘事技巧來展現人物故事:主人公李仲生在日苦讀11年終于考上博士。正當全家人對未來充滿期待時,李仲生意外受騙,將全部財產投入詐騙組織,結果血本無歸,妻子一氣之下帶著女兒離開了李仲生。此為第一次突轉。除夕之夜,分居多日的夫妻二人終于和好,李仲生的論文也接近完成,一家人正其樂融融地籌劃未來的生活,一切似乎朝著觀眾期待的大團圓結局發展。然而,接下來劇情的走向再次偏離觀眾的預期:李仲生的論文答辯未獲通過,沒能拿到博士學位;夫妻二人又因經濟不景氣而先后丟了工作。雙重變故讓這一家人的生活雪上加霜,也讓熒屏前的觀眾頻頻受到沖擊,對片中人物的命運發展更為關切。這些轉折看似出乎意料,但又在情理之中:既有當時日本社會經濟條件的客觀因素,也是主人公自身固執、矛盾的性格因素使然。觀眾的關注欲望也在曲折的故事敘述中被極大地調動起來。
突轉之余總會留下懸念。紀錄片在處理情節、安排沖突時,采用的“懸而未決”的處理方式,即為懸念。其目的是利用觀眾對人物命運的關切心理,調動觀眾的情感因素,引發觀眾對未知情節的期待。《我們的留學生活》構建懸念的方式有多種,較為常見的是利用分集呈現的形式來設置懸念:許多敘述同一個故事或同一主題的片子被劃分為“上”“下”集播出。這其中既有播放平臺時長限制的考慮,也是為了避免觀眾長時間收視而產生疲勞。于是,上集結束的地方往往被用來設置懸念,以維持觀眾對人物故事的關注熱度。如上下分集《小留學生》將主人公張素一家人的命運劃分為兩個階段:來日定居和離開日本。在上集即將結束時,片子敘述了日本經濟下滑、失業率上升的背景,引出張素父親所在的公司經營狀況不容樂觀,從而設置了一處懸念:張素的父親是否會下崗?隨后,解說又暗示了接下來的轉折:“然而,接下去的路卻突然發生了變化。張素一家不得不面對新的挑戰。”從而調動了觀眾的好奇心:張素一家人究竟發生了什么?他們能否應對新的挑戰?
紀錄片還通過扣押關鍵信息來設置懸念。美國劇作家麥基認為:“你不是靠給予信息來保持觀眾的興趣,而是靠扣押信息,除了那些為了便于觀眾理解而絕對必要的信息。”[7]134阿拉伯民間故事《一千零一夜》中,宰相之女山魯佐德每天晚上給暴君講故事,只講開頭和中間,不講結尾。暴君為了聽故事的結局,不得不把殺山魯佐德的日期延遲了一天又一天。從某種程度上來說,山魯佐德講故事正是通過扣押關鍵信息的方法以設置懸念。紀錄片的創作者早在剪輯播出前就先于觀眾知曉人物命運的發展,但為了引起觀眾注意,選擇在敘述的過程中扣押部分關鍵信息,以設置懸念、刺激觀眾好奇心。如分集《角落里的人》敘述了這樣一段故事:主人公馮明和史國強是沒有簽證的“黑戶”。為維持生計,二人相約去老虎機房“打假卡”。解說告訴觀眾:“假卡風潮興起后,老虎機房紛紛加強了警備力量,配備了最新的防范設備。”隨即出現了二人正在游戲廳“打假卡”的畫面,身后則是走動巡邏的安保人員,觀眾的緊張感一下子被調動了起來:馮明和史國強會不會被抓?之后,馮、史二人帶著前來投奔他們的小李去“打假卡”。畫面停留在三人走進老虎機房的那一刻,解說告訴觀眾:“小李被捕了。”因其沒有簽證,又在日本犯了法,小李的命運走向格外引人關注。然而,片子接下來并沒有把小李最終安全回國的結果直接告訴觀眾,而是將這一重要信息延后,先講述馮明如何輾轉收到小李的求救信,自己又因身份問題無法出面“營救”、內心愧疚等曲折,并因此感嘆“黑戶”在日本生活的艱難,使觀眾在緊張之余產生了疑問:小李的命運將會如何?馮明和史國強會怎樣選擇自己的命運?
五、小結
紀錄片的創作者曾長期推崇“墻上的蒼蠅”式的處理手法,認為拍攝者應該像墻上的蒼蠅一樣默默觀察和記錄事態的發展,而不能直接干預其中。然而,多數情況下,紀錄片畢竟是依照人的主觀意圖來創作的,“紀錄片的影像是已經被中介了的現實”[8]67-69。按照格里爾遜的觀點,紀錄片是“對現實生活的創造性處理”;筆者認為,“故事化敘事”理應被視為紀錄片“創造性處理”生活的一種方式。
一般意義下,紀錄片同故事片最大的區別在于它的“非虛構性”。由于無法事先虛構,紀錄片的視覺語言和表達方式也許遠不如故事片豐富,但這并不意味著它失去趣味性和可看性。創作者通過長時間的等待來發現生活中的戲劇性,從生活流的場景中發掘細節,以此構建富有沖突的故事情節和飽滿的人物形象。《我們的留學生活》聚焦中國留學生在日本的生活學習狀況,通過長時間的跟拍積累了大量的素材,從中選取富有矛盾沖突的關鍵情節,以故事化的敘事手段加以描摹,以此塑造鮮活的人物形象,增強故事的感染力,使觀眾產生了情感上的共鳴。
此外,紀錄片采用故事化敘事也有商業方面的考量。《我們的留學生活》是由日本富士電視臺制作的一系列紀錄片,并先后在中日兩國電視臺播出,收視率好壞所帶來的收益必然是商業電視臺考慮的重點。紀錄片的創作者適當運用故事化敘事的手法,發現和強調生活中的沖突與矛盾,充分調動人性的積極作用,以此吸引觀眾的注意,引發持續關注的行為,從而獲得商業方面的利益。
參考文獻:
[1](荷蘭)尤·伊文思.對紀錄片的幾點看法[J].沈善,譯.世界電影,1979(4).
[2](美)華萊士·馬丁.當代敘事學[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
[3](德)黑格爾.美學. 第一卷[M].朱光潛,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
[4]閻立峰.思考中國電視——文本、機構、受眾[M].西安:陜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9.
[5]亞里士多德,賀拉斯.詩學·詩藝[M].郝久新,譯.北京:九州出版社,2007.
[6]古漸.“發現”與“突轉”——對《詩學》戲劇理論的現代闡釋[J].外國文學評論,1999(3).
[7] (美)羅伯特·麥基.故事——材質、結構、風格和銀幕劇作的原理[M].周鐵東,譯.北京:中國電影出版社,2001.
[8]趙伯平.對紀錄片真實性與主觀表現的思考[J].電視研究,2008(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