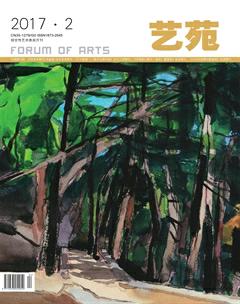《骷髏幻戲圖》研究
黃月婷
【摘要】 本文以李嵩《骷髏幻戲圖》為研究對象,關注畫面上較為特殊的形象,探討志怪故事中的“骷髏幻戲”和抱嬰兒乳之婦女形象的寓意;分析三組人物關系,即大骷髏與小骷髏的關系、嬰孩與懸絲“小骷髏”的關系、大骷髏與其身后抱嬰兒乳之婦女的關系,對此圖進行情景分析;借以解讀其中的寓意。
【關鍵詞】 《骷髏幻戲圖》;抱嬰婦人;嬰孩;乞子求福
[中圖分類號]J22 [文獻標識碼]A
李嵩,史料中最早記載:“錢唐人。少為木工。頗遠繩墨。后為嵩訓養子。光、寧、理三朝畫院祗候。得嵩訓遺意。雖通諸科。不備六法。特于界畫人物。粗可觀玩。他無足取。”[1]9《骷髏幻戲圖》是李嵩的一幅畫作,歷代記錄中傳為《李嵩骷髏圖》,有作于團扇絹面、方絹、澄心堂紙等。可見,元明清時期可能流傳多本材質不一、名為“李嵩骷髏圖”的作品,但我們不能肯定這些作品皆為李嵩所作。現存此類“李嵩骷髏圖”只有一幅,為北京故宮博物院收藏,今定名為《骷髏幻戲圖》(圖1)。
明人陳繼儒在《太平清話》中記錄了他所收藏的團扇絹面的《李嵩骷髏圖》:“予有李嵩骷髏圖。團扇絹面。大骷髏提小骷髏戲一婦人。婦人抱小兒乳之。下有貨郎擔。皆零星百物。可愛。”[2]28清人吳其貞在《書畫記》中記載了畫于澄心堂紙的《李嵩骷髏圖》:“李嵩骷髏圖紙畫一幅。畫于澄心堂紙上,氣色尚新。畫一墩子,上題三字曰:‘五里墩。墩下坐一骷髏,手提小骷髏,旁有婦乳嬰兒于懷,又一嬰兒指著手中小骷髏,不知是何義意。識二字曰:‘李嵩。”[3]31由記載可知,這些材質、題跋等不同、傳為《李嵩骷髏圖》的作品的畫面基本信息與今本北京故宮博物院藏的《骷髏幻戲圖》沒有多大出入。明代顧炳輯錄的《顧氏畫譜》云:“觀其骷髏圖。必有所悟。能發本來面目意耳。”[4]但他究竟能悟到什么,未加說明。又有清人陳撰《玉幾山房畫外錄》云:“骷髏弄嬰圖。骷髏而衣冠者眾見。粉黛而哺乳者已見。與兒弄摩候羅亦骷髏者。日暮途遠。頓息五里墩下者。道見也。與君披圖復阿誰。見一切罔眼作如是觀。”[5]76他也未能講明其中的寓意。
關于李嵩和《骷髏幻戲圖》的資料較少,著錄中的“不知是何義意”卻引發了不少人的思考。人們所認為的圖中的寓意也并沒有所謂的正確與否。諸多學者的闡釋也只是其中的多種可能性。或許李嵩本人創作此圖時并無特別之意,只是后人附會而上的想法。筆者最初關注此圖,也是因當中的特殊性引起了多個疑問。而筆者的研究意義則在于解決疑問的前提下,對《骷髏幻戲圖》有一個重新的認識。所以本文希望從畫面內容出發,通過建立宋代社會生活與之相關關系,借以探討其中的寓意。
一、《骷髏幻戲圖》的畫面內容
(一)志怪故事中的骷髏幻戲
我們假設畫家李嵩可能根據流傳至宋代的志怪故事情節而作《骷髏幻戲圖》。宋代李昉的《太平廣記》記載一則出自《乾月巽子》的發生在唐代元和時與骷髏有關的志怪故事:“只在崇仁北街。居無何。僖伯自省門東出。及景風門。見廣衢中。人鬧已萬萬。如東西隅之戲場大。圍之。其間無數小兒環坐。短女人往。(往原作準,據明鈔本改)前。布冪其首。言詞轉無次第。群小兒大共嗤笑。有人欲近之。則來拏攫。小兒又退。如是日中。看者轉眾。短女人方坐。有一小兒突前。牽其冪首布。遂落。見三尺小青竹。掛一觸髑髐然。”[6]2722學者莊申研究的最大貢獻就是將《骷髏幻戲圖》與志怪故事相聯系,他認為“骷髏戲弄傀儡圖”可能是對于中唐開始流傳的一個荒誕故事的記錄,李嵩可能據此故事將崇仁里改為五里堠,把短女人改為開懷乳嬰的婦人,在地上匍匐而行的男嬰則是“乾月巽子”所記述的故事里的原有的成分。[7]426但是從志怪故事出發,筆者認為“布冪其首的短女人”被畫家改成“頭戴幞頭穿紗衣的大骷髏”可能更為合理。
《太平廣記》還記載一則出自唐代前期的漢族志怪傳奇小說集《廣異記》的、與骷髏有關的故事:“止有幞頭布。掩然至地。其下得一髑髏骨焉。”[6]2671從《太平廣記》記載而言,我們知道宋人也是通過前人記錄熟知此類故事。宋人洪邁的《夷堅志》是宋朝著名的志怪小說集,當中亦有記載一則這樣類似與骷髏相關的故事:“白書有緋衣婦人蒙首入門,云有疾求治。劉不在家,家人以實告。婦人徑入及中堂端坐以待。或發其首幕,乃一髑髏,驚呼間遂不見。”[8]127
上述幾則與骷髏有關的志怪故事和《骷髏幻戲圖》的“大骷髏”有一個共同之處,即短女人“布冪其首”、亡娣“身衣白服戴布幞巾”、婦人“緋衣蒙首”與畫中“頭戴幞頭身穿紗衣”的大骷髏的穿著效果是一樣,旁人沒掀落衣服之前都未能發現遮掩下的骷髏。由此可知,這類與骷髏有關的志怪故事從唐代流傳至宋代仍十分流行,而李嵩所畫的“頭戴幞頭身穿紗衣的大骷髏”形象很有可能是這類故事的一種圖像轉變。
(二)抱嬰乳之的婦女形象
筆者有意將《骷髏幻戲圖》中抱嬰婦人的形象與宋代“鬼子母”形象聯系,則是因為發現抱嬰婦人的形象與西藏西部東嘎石窟出土的壁畫(圖2)極為相似。筆者認為這并非偶然性,《骷髏幻戲圖》中婦人形象可能與宋代“鬼子母”崇拜文化及其藝術形象存在某種關系。
宋代的“鬼子母”究竟是以什么樣的藝術形象出現?唐代義凈在《南海寄歸內法傳》記載了鬼子母神原始供養方式是在諸寺門屋處、食廚旁塑畫母形像,有“抱一小兒于其膝下”[9]50之態。鬼子母神形象出現在繪畫中,是否蘊含著其他寓意?在《太平廣記》中記載了古人供養鬼子母求子的現象:“越中士女求男女者。必報驗焉。”[6]261此書也記載了一則張應因祭拜鬼子母神而使得妻子病全愈的故事,張應“秉火作高座及鬼子母座”“妻病有間。尋即全愈”[6]782。這兩則材料表明在宋代信仰鬼子母神多與求子求福的心愿有關。可見,由于宋人崇拜鬼子母神現象十分常見,鬼子母神的形象才會如此頻繁地出現在繪畫上。這一時期的鬼子母神的崇拜文化可能也因此影響了李嵩的作畫。
顯然,我們也會把“抱嬰婦人”形象與宋代的乳母形象聯系一起。研究宋代乳母形象的學者程郁認為,宋代的繪畫和雕塑有不少流傳至今,下層婦女往往當眾敞懷喂乳,即使不乳時,其襦裙的衣領也較上層婦女為低。對于這個階層的婦女來說,露出豐乳或胸部微露并不是驚世駭俗的。她們未必典雅端莊,但卻是極具女性特征的。[10]那么,從《骷髏幻戲圖》中婦女的穿戴來看,其應該屬于下層婦女。所以,李嵩在這樣的情境下安排“旁有婦乳嬰兒于懷”也不足為怪。
二、畫中三組人物關系
(一)大骷髏與小骷髏的關系
學界普遍認為,《骷髏幻戲圖》中大骷髏手中的懸絲“小骷髏”是宋代懸絲傀儡戲表演。筆者認同此種說法,在此不贅述。宋人孟元老《東京夢華錄》、周密《武林舊事》、吳自牧《夢梁錄》、灌圃耐得翁《都城紀勝》和《繁盛錄》中有大量的文獻資料可以展示出宋代傀儡戲的盛行情況。這些文獻記載了傀儡戲的分類、羅列了一些專業的表演者以及傀儡戲所扮演的故事類型。在宋代的文獻中,傀儡戲計有五種,即懸絲、杖頭、藥發、肉傀儡、水傀儡。在宋朝時期的一些重要節日都可以見到傀儡戲演出,如周密《武林舊事》中記載了圣節、元夕等節日的傀儡戲演出。我們還可以從文獻中得知一些技巧精湛的傀儡戲專業表演者,有傀儡舞鮑老、弄傀儡盧逢春、金線盧大夫、陳中喜等,還有專門的傀儡社[11]1,如福建鮑老社、川鮑老社。
研究此畫的學者康寶成認為:“這種利用《骷髏圖》或用木制骷髏(傀儡)說法的形式,來自佛教密宗儀式。”[12]在有關傀儡戲的研究中,學者許地山、常任俠認為印度的提線木偶對我國的傀儡戲產生過一定的影響,康寶成進一步指出,這種影響可能是通過密宗儀式影響全真教,從而以畫《骷髏圖》和懸絲傀儡的形式得以實現。所以從這個角度出發,宋代懸絲傀儡戲如果受到密宗儀式的影響,那么李嵩《骷髏幻戲圖》可以說是有利的圖像證據。
傀儡戲為何如此盛行?紹熙三年(1192年)二月,時任漳州太守的朱熹曾頒發《勸農文》,想要勸告農民不得因為雜聚觀戲而輕于農事,內云:“約束城市鄉村,不得以禳災祈福為名,斂掠錢財,裝弄傀儡。”[13]這則公文較為真實地記錄宋代漳州農村演戲情況。其中還指出了傀儡戲的一大社會功能:禳災祈福。誠如《西湖老人繁盛錄》所言:“或作傀儡神鬼,驅邪鼎佛。”[11]18又如宋人范成大以懸絲傀儡戲作喻,記錄了傀儡戲還被用作祭祀求雨,“刻木牽絲罷戲場,祭余雨后兩相忘”(《請息齋書事三首·之一》)[14]。再如北宋朱彧《萍州可談》記載江南地區用傀儡戲祭祠神明的情形:“張樂弄傀儡。初用楮錢。熱香祈禱。猶如祠神。”[15]因此,除了玩耍所用,傀儡戲更為重要的是承載禳災祈福的社會功能,是祭祀神明,驅除邪崇的手段之一。現在福建許多地區仍然還有將傀儡戲用于驅除邪崇、佑庇嬰兒等禮儀中。據學者葉明生考察,傀儡戲參與的禮儀有新婚探房、斬煞求子、拜斗求壽等等。所以,我們完全有理由認為《骷髏幻戲圖》中“大骷髏”手提“小骷髏”不只是宋朝時期懸絲傀儡戲的記錄表現,而在畫中還蘊含消災祈福之寓意。
(二)嬰戲與懸絲傀儡戲
兩宋時期的傀儡戲高度發展,不僅在宮廷里備受歡迎,更是在民間十分流行。一種類似傀儡戲的民間游戲,尤其受到嬰孩的喜愛,即文獻記載中的“傀儡兒”[16]111。在宋代出土的實物中就有反映這一時期兒童戲耍傀儡的圖像,如河南濟源出土的宋代嬰戲三彩瓷枕(圖3),繪畫作品有如《百子嬉春圖》(圖4)、《侲童傀儡圖》(圖5)等,都繪有兒童表演傀儡戲的場景。
在文獻中也有記載嬰童戲耍傀儡玩具之說,如宋代陳普《石堂先生遺集》曰:“三二百年天地里,十棚木偶弄嬰兒。”在宋代,嬰孩耍玩傀儡,或是木偶戲弄嬰孩都是常見之事。那么,在《骷髏幻戲圖》中,大骷髏以懸絲“小骷髏”吸引嬰孩的注意,也是合情合理的。
(三)大骷髏與“旁有婦乳嬰兒于懷”的關系
前面已通過幾則與骷髏有關的志怪故事來說明“頭戴幞頭身穿紗衣的大骷髏”在圖中所設定故事情節的合理性。宋代以來,都市生活進一步發展,城鎮各大小巷都可發現貨郎身影,《貨郎圖》就是此類題材的真實寫照。因李嵩存世多幅的《貨郎圖》,研究此畫的學者多將“頭戴幞頭身穿紗衣的大骷髏”與貨郎形象聯系在一起。如陳繼儒就這樣形容:“旁有貨郎擔”。而實際上,《骷髏幻戲圖》擔上多是有如睡席、傘等生活用具,很難稱得上“零星百物”。所謂“貨郎”,就是一種流動出售小雜貨的小商販。在宋代,文獻記載中有賣客弟子通過有戲耍傀儡招徠顧客,“撮弄泥丸,咸酸蜜煎,旋造羹湯,唱耍令,學像生,弄傀儡,般雜半,瓶啜酒,點江茶蔬菜,關撲船”[11]8,還有戴傀儡面兒的貨郎賣糖,“內魚龜頂傀儡面兒舞賣糖”[16]109,以吸引顧客。假使“大骷髏”為貨郎,擔上貨品鮮少,有一疑問是貨郎如何借以傀儡售賣何物?《骷髏幻戲圖》中所示為宋代懸絲傀儡戲的表現形式,這點并無疑問。據此筆者進一步猜想,圖中大骷髏可能借用懸絲傀儡完成一種“貨郎兒”的說唱形式。作為演唱形式的“貨郎兒”,一般認為最初源于宋代現實生活中賣貨郎的吆喝,后來發展成演說各類故事的說唱藝術。[17]宋人筆記《武林舊事》記載的“舞隊”條下有“大小全棚傀儡:貨郎”[18]。根據王國維的研究,“舞隊”應該是一種以人來表演故事的戲劇。[19]31換言之,從周密記載此條信息來看,傀儡戲也是一種表演故事的戲劇,而貨郎則有可能是傀儡戲題材其中一種表現形式。之后稍晚一些的陶宗儀也記錄一種元代院本雜劇《貨郎孤》[20],鄭振鐸認為,所謂的“孤”可能是男角色的總稱,因此“貨郎孤”應該就是以男角為主的滑稽雜耍戲。以此出發,“頭戴幞頭身穿紗衣的大骷髏”有可能扮演的是貨郎孤。再者,我們細觀圖中所示的“貨郎擔”,當中傘上系綁疑似響鈴樂器之物,具體何物尚不明確,可能是扮演“貨郎兒”用以配樂之需。
在宋人筆記中不乏見有藝人的身影,如:“有村落百戲之人,拖兒帶女,就街坊橋巷呈百戲使藝,求覓鋪席宅舍錢酒之貲。”[16]79宋代,民間藝人社會低下。為了衣食,拖家帶口,走街串巷,在各種街巷、空地、茶肆、寺廟等地出售技藝。而此畫戲耍傀儡表演貨郎的說唱形式可能就是這類民間藝人的生活寫照。
通過分析三組人物關系,筆者認為《骷髏幻戲圖》可能是描述這樣的一個情景:在宋代流行與骷髏有關的志怪故事中,旁人很難發現紗衣隱藏之下的骷髏。在標有“五里”城墻旁的空隙地段是民間藝人的演出場所,他們攜家帶口在此演出。我們可以看到幞頭與紗衣之下的大骷髏借以懸絲“小骷髏”表演“貨郎兒”說唱藝術招徠顧客,以及其顯要標志“貨郎擔”。大骷髏身后是其妻抱襁褓嬰兒就地盤足而坐。在宋代,懸絲木偶玩具深受嬰孩群體的喜愛,所以“大骷髏”成功地利用懸絲“小骷髏”吸引到嬰孩的注意。
三、小結
《骷髏幻戲圖》有一個重要的圖像元素是我們不可忽略的,即關于骷髏的圖像描繪。探討此圖的學者多數以骷髏為《骷髏幻戲圖》的主題,他們從《莊子·至樂》中“莊子嘆骷髏”的故事出發,以及其引申演繹而來的張衡的《骷髏賦》、曹植的《髑髏說》、呂安的《骷髏賦》、蘇軾《骷髏贊》等文本探討骷髏的寓意。骷髏不僅出現在文學作品意象中,更是與宗教關系密切。如有藏傳佛教中手執骷髏杖或頭頂骷髏冠的神祇、骷髏成就法、白骨觀,還有金元全真教的骷髏觀修習法以及王重陽《骷髏圖》、譚處端《骷髏歌》。當然無論是文學中的骷髏意象或是宗教中的骷髏形象都有助于我們理解骷髏的含義。史料記載的南宋李嵩“工畫人物道釋”[21]、“佛像尤絕”[4]、“精工人物佛像”[22]。另外,《骷髏幻戲圖》對幅題跋是元代王玄真書黃公望散曲題詠,吳其貞《書畫記》著述的《李嵩骷髏圖》的臨摹本上也有張伯雨等人題跋,黃公望和張伯雨等人都是道士身份,所以他們也是從宗教角度觀讀此圖。今人研究受到前代著述的影響,部分學者認為圖中的“骷髏”意象具有一定的宗教意味。而這些看法恰是圍繞著骷髏作單一的探討。究竟骷髏與嬰孩為何同時出現李嵩此畫中,至今仍是個迷。
總結全文,筆者更傾向認為圖中抱嬰兒乳之的婦女形象與宋代鬼子母崇拜文化的關聯性,李嵩在圖中安排該形象也蘊含著求子求福之愿。目前沒有找到相關文獻資料來證明懸絲傀儡造型有骷髏狀,康寶成對此研究頗為詳細,筆者援引其觀點“印度木偶戲通過密宗儀式影響全真教進而影響傀儡戲”,而李嵩此圖則是有利的圖像證據。在宋代,傀儡戲之所以如此盛行,不僅是其娛樂作用,更為重要的是禳災祈福之愿。所以,《骷髏幻戲圖》中的懸絲小骷髏也應有此意。此外,從圖中嬰孩的數量來看,共有三個,有一男一女外加一襁褓嬰孩,這可能寓含著宋人的“多子多福”傳統生育觀念。因此整體來看,本圖當是乞子求福之圖。
參考文獻:
[1]莊肅.畫繼補遺[M].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1963.
[2]陳繼儒.太平清話[M].寶顏堂秘籍本排印,1985.
[3]吳其貞.書畫記[M].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2006.
[4]顧炳.顧氏畫譜[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3.
[5]衣若芬.骷髏幻戲——中國文學與圖象中的生命意識[J].中國文哲研究集刊,2005(2).
[6]李昉.太平廣記[M].北京:中華書局,1981.
[7]莊申.羅聘與其鬼趣圖——兼論中國鬼畫之源流[J].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1972(44).
[8]洪邁.夷堅志.北京:中華書局,1981.
[9]義凈.南海寄歸內法傳校注[M].北京:中華書局,1995.
[10]程郁.進入宋代皇室的乳母與宮廷政治門爭[J].歷史教學月刊,2016(3).
[11]佚名.西湖老人繁勝錄[M].北京:中國商業出版社,1982.
[12]康寶成.補說《骷髏幻戲圖》——兼說“骷髏”、“傀儡”及其與佛教的關系[J].學術研究,2003(11).
[13]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M].四部叢刊初編集部.
[14]吳之振.宋詩鈔[M].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15]朱彧.萍州可談[M].北京:中華書局,2007.
[16]吳自牧.夢梁錄[M].北京:中國商業出版社,1982.
[17]黃小峰.樂事還同萬眾心——《貨郎圖》解讀[J].故宮博物院院刊,2007(2).
[18]周密.武林舊事[M].北京:中國商業出版社,1982.
[19]王國維.宋元戲曲史[M].北京:東方出版社,1996.
[20]陶宗儀.南村綴耕錄[M].四部叢刊三編景元本.
[21]夏文彥.圖繪寶鑒[M].上虞羅氏宸翰樓據元至正本影刻本,1914.
[22]厲鶚.南宋院畫錄[M].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