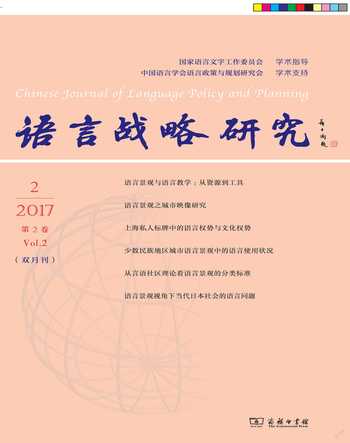《語言政策與規劃·理論與歷史基礎》述評
編者按:盧德里奇出版社(Routledge)于1998年開始編撰出版“語言學中的關鍵概念”(Critical Concepts in Linguistics)系列叢書,旨在通過重印經典的方式介紹語言學各個分支學科最優秀與最具影響力的學術成果。2016年,該系列推出了四卷由知名學者托馬斯·李圣托(Thomas Ricento)主編的《語言政策與規劃》(Language Policy and Planning)文選。文選標題分別為“理論與歷史基礎”(Theoretical and Historical Foundations)、“語言政策與語言權利(Language Policy and Language Rights)”、“教育中的語言政策(Language Policy in Education)”和“語言政策與全球化”(Language Policy and Globalization),收錄了近60年來對語言規劃與語言政策學科的產生與發展巨大影響的68篇文章,總計達1600多頁。從本期開始,我們將陸續刊出關于這套文集的四篇評論。每篇書評先對相應文選的內容進行介紹,然后做簡要評論,最后分析對中國語言政策與規劃研究的啟示。我們希望,本系列書評有助于推動中國語言政策與規劃研究的進一步發展。
一、內容介紹
“理論與歷史基礎”是這套書的第一卷。此卷的正文部分包括Thomas Ricento的一篇“概述”以及精心挑選的22篇經典文獻。
“概述”部分,主要包括以下內容:(1)四卷本編寫的理念、原則及篩選程序;(2)LPP早期的重要會議與著作;(3)LPP的主要雜志和年度會議;(4)其他重要著述;(5)1—4卷內容簡介;(6)LPP的未來。為了保證叢書的質量,Ricento為這套四卷本聘請了五位顧問:David C. Johnson,Kendall King,Selma K. Sonntag,James Tollefson,Terrence Wiley。
第一篇,論雙言/雙語體①(Charles A. Ferguson 1959)②。“谷歌學術”上,此文以4587次的引用率高居榜首。其影響深遠的另外兩個例證是:這篇文章發表后,John De Francis依據“雙言(Diglossia)”提出了“雙文(Digraphia)”的概念,指同一種語言使用兩種或兩種以上的文字系統;之后Peter Auer在“雙言”的基礎上,提出了“雙方言(Diaglossia)”的概念,指的是地方方言和標準語之間存在中間變體的狀態③。
第二篇,現代挪威標準語的規劃(Einar Haugen 1959)。此文被公認為當代語言規劃研究的開端,正是通過此文“語言規劃”才開始進入研究者的視野。這一研究的重要意義在于它提出了“語言規劃”這一術語,但是其文中的界定比較狹窄,基本上相當于后來所說的“本體規劃”。十年之后,Heinz Kloss才區分了“地位規劃”和“本體規劃”;二十年后,Robert Cooper又提出了“習得規劃”。
第三篇,語言保持和語言轉用:作為一個研究領域(Joshua A. Fishman 1964)。正如文章的副標題(“領域界定及其未來發展的建議”)所示,此文開啟了社會語言學、LPP領域的一個核心研究領域:語言保護—語言保持—語言轉用。28年之后④,一個與此相關的重要領域才開始引起學者們的關注,即瀕危語言研究。正如Fishman在小注3中所說:“(比起之前的許多術語)‘語言保持和語言轉用的說法有個優勢,即更清楚地展示了一個過程和結果連續統的存在。”(第74頁)
第四篇,距離型語言與培育型語言(Heinz Kloss 1967)。此文是Kloss(1952)這一德文著作的英文版釋讀。可能是找不到合適的英文對應詞,Kloss直接使用了德文原詞abstand和ausbau。這一理論模型對于語言標準化研究很有價值,也常被用來與Stewart(1968)(該卷第七篇文章)等提出的“自主型語言和他主型語言”的框架相對應(Trudgill 2004)。《國際語言社會學期刊》2008年第3期還專門針對此論題刊發了一期專輯。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區分了保守的語言規劃和創新的語言規劃,并指出“培育型語言”就屬于創新的語言規劃之列。
第五篇,語言與社會場景的互動模型(Dell Hymes 1967)。此文發表于“社會語言學”作為一個學科方興未艾之時,其主要貢獻在于對“社會語言學系統”進行了一次類似對語言/方言進行參考語法描寫那般的描寫,列述了言語社會化分析的框架、語言使用理論的分析單位、言語的構成成分,以及理論描寫的形式化規則。這些描寫為之后社會語言學,特別是專注于社區—交際民族志方向的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基點。
第六篇,雙語現象的社會心理⑤(Wallace E. Lambert 1967)。1960年,Labert與其同事一起發表了《口語的評價反應》一文,首次提出了“變語配對測試”(matched-guise test),用以測定個體或社區群體對某特定語言、方言或口音的真實態度。此文就是對這一測試的應用,也是雙語與二語習得的心理視角研究的經典文獻。
第七篇,一個描寫國家多語現象的社會語言學類型模型(William A. Stewart 1968)。盡管類型學的視角由來已久,但是類型學視角的社會語言學研究一直是一個難點⑥(Owens 2005等),Stewart這篇文章是早期的嘗試之一,也為多語現象的研究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第八篇,一個面向語言規劃的理論(Bj?rn H. Jernudd & Jyotirindra Das Gupta 1971)。在LPP的研究史上,Rubin & Jernudd(1971)是一部重要著作,不僅是因為其中許多文章都成為LPP研究領域的經典,而且在于其核心論題“語言能被規劃嗎?”給LPP的研究提供了進一步闡釋的動力。對這一問題,此文給出的答案是肯定的。他們對語言問題的類型學區分、對國家層面語言規劃的理論構建、將語言規劃放在公共規劃視域下的審視等,都給后來的研究提供了很多啟示。此外,學者們往往將“作為一種資源的語言”這一理念回溯到Ruiz(1984)一文,但這之前,Jernudd和 Das Gupta就專門用一小節討論此話題。
第九篇,作為參與國家系統的輔助和障礙的語言(Herbert C. Kelman 1971)。Kelman主要從情感和工具兩個維度,分析了個體及團體參與到國家系統的一些模式、語言作為統一/分化的力量、以及上述分析對語言政策的啟示。
第十篇,評估與語言規劃(Joan Rubin 1971)。盡管已經有了一些嘗試性探究(比如Fran?ois Grin的一些研究),但是在Rubin⑦發表這篇文章45年后的今天,其文章首段的論斷卻還依然適用:“在語言規劃的過程中,評估一直是最不常用的術語。”(第191頁)而LPP評估所受到的限制也顯然沒有超出Rubin在文中所提到的那些因素。除了對“評估”的聚焦,Rubin一文還提出了一個LPP的工作框架:發現事實——規劃(目的、策略、成果)——實施——反饋。Lo Bianco(2010,2015)據此提出了一個五步工作框架:問題識別(收集數據)——目標詳述(政策撰寫)——成本—收益 分析(理性演示可選擇方案,投資回報率)——政策執行(政策付諸實施)——評估(將預期與實際結果進行比較)。
第十一篇,作為一種社會控制手段的語言:美國經驗(Arnold H. Leibowitz 1974)。此文以及其之前和之后的一系列著述都有一個核心理念,即理解語言教育政策的最佳方式是將其置于宏觀社會政策、主流觀念和集團間權力關系的相互聯系中進行考察。而其將語言看作是一種社會控制的手段的觀點,是建立在對20世紀50年代到70年代現代民權運動時代斗爭的法律淵源分析和歷史分析及反思上的。其中一個核心概念就是“限制型語言政策”,這一概念對于理解多數族群的語言和少數族群語言的關系、語言政策與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等領域的密切聯系提供了有用的視角,也給后來James Crawford和Terrence G. Wiley的一系列研究提供了基礎。
第十二篇,領地性原則和個體性原則在多語國家的應用(Kenneth D. McRae 1975)。McRae將政治學、生物學領域的領地性和個體性這兩個概念應用到了語言政策的分析中。此文是對Kloss(1952,1969)的進一步闡釋和發展,也為后來的“語言體制”(language regimes)研究提供了借鑒。
第十三篇,地位規劃中的種族問題(Juan
Cobarrubias 1983)。此文及Ruiz(1984)是最早對語言規劃的意識形態取向進行探討的文章,他們開始讓人們意識到語言規劃并非之前人們所認為的那樣持中立的意識形態,而是帶有很大的意識形態傾向。這是學者們對語言政策與規劃在認知上從技術性轉向政治性的前奏(托爾夫森2014[2013]:32),也給后來James W. Tollefson的許多研究帶來了啟示。
第十四篇,什么是逆轉語言轉用以及如何才能成功(Joshua A. Fishman 1990)。此文提出了“逆轉語言轉用”這一概念,并構建了其理論和實踐模型,成為了繼其“語言保持”和“語言轉用”等研究⑧之后在少數民族語言、語言瀕危等研究領域中的又一個突破。一年之后,《逆轉語言轉用》則以專著形式對這一觀念進行了詳細闡述。
第十五篇,語言政策的政治目標(Brian Weinstein 1990)。此文提出了語言政策的三個宏觀目標:維持國家或社會現狀;改革國家或社會現狀;改造國家和/或社會。此文篇幅不長、關注度也不高,但是其分析卻鞭辟入里。
第十六篇,語言規劃理論的意識形態性(James W. Tollefson 1991)。此文摘自Tollefson(1991)的第2章內容,其核心內容是將LPP的研究路徑分為“新古典主義”和“歷史—結構”兩大類,并對之進行深入對比。Tollefson(1991)在LPP研究史上有著重要意義,Tollefson受哈貝馬斯、吉登斯、福柯等學者的影響,著眼于語言的權力機制,將批判研究范式進一步引入到了LPP的研究中并確立了其核心地位。此外,盡管上面的第十三篇文章以及Ruiz(1984)都提到了意識形態取向,但是真正對之前學界認為的“LPP是意識形態中立”這一觀念提出系統批判的是Tollefson(1991)。
第十七篇,語言復興與語言復活中的純潔觀與折衷觀(Nancy C. Dorian 1994)。此文區分了“語言復興”與“語言復活”,并表達了對“純潔觀”在這兩類活動中的悲觀以及與之相對的對“折衷觀”的樂觀。正如作者文末所說:“不管對小語言還是大語言來說,純潔觀不一定就是持久之必需,而折衷觀也未必就是消亡之喪鐘。”(第398頁)
第十八篇,作為語言與社會的一種話語的語言規劃:一個學術傳統的語言學意識形態(Jan Blommaert 1996)。此文將以往的“語言規劃”研究分析看作一個話語分析元場地,聚焦語言規劃是否有理論背景、語言規劃的直觀局限性、語言與社會的有機性觀點等,進一步強化了語言規劃的政治路向,并提倡歷史與民族志相結合的方法論研究路徑。
第十九篇,語言規劃與語言生態(Peter Mühlh?usler 2000)。盡管將生態學視角應用于語言學是上世紀60、70年代的事情,但是Mühlh?usler的這篇長文卻首次把生態學與語言規劃連接起來,將生態學理念應用到了語言規劃領域,并闡明了生態視角語言規劃的理念、宗旨以及操作路徑。
第二十篇,語言政策與規劃的歷史和理論視角(Thomas Ricento 2000)。無疑,這篇文章已經成為LPP歷時研究的經典文獻。Ricento從宏觀社會政治、認識論和戰略/策略性三個因素分析LPP研究的興起,并將過往的LPP研究分為三個時期,最后對LPP當時的現狀和未來方向做了一些展望。
第二十一篇,語言規劃與經濟學(Fran?ois Grin 2003)。此文可以看作對之前他所研究的語言與經濟關系的一個集大成之作,不僅對語言研究的經濟學視角的利弊、研究歷史、主要研究領域做了梳理和呈現,更對語言政策的經濟學視角以及在語言教育規劃領域的應用做了系統、深入的闡釋。
第二十二篇,語言政策的民族志視角(David Cassels Johnson 2009)。LPP民族志的研究方法顯然源于人類學,Hornberger(1988)則被公認為是民族志方法在LPP的首次使用。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特別是新世紀以來,“批評家指出歷史—結構方法過分強調自上而下的規劃和決策,而他們認為應當更多地關注于語言使用者個體、教師、家長、管理者和社區的局部性決策”(托爾夫森2014[2013]:33),于是利用民族志和話語分析來考察“接地氣”(on the ground)的LPP過程的研究開始快速增長,Johnson這篇文章堪稱其中典范之作。
二、幾點評論
正如Ricento所言,“從浩如煙海的LPP文獻中選出1600頁的四卷本匯編,實屬不易”(第1頁)。盡管篇幅有限,但是Ricento也還是盡可能向讀者展示了LPP研究的跨學科性:語言學、社會學、經濟學、心理學、歷史學、人類學、民族志、政治學、倫理學、美學、法學、教育學,以及與這些學科相關聯的其他許多跨學科的領域。
顯然,Ricento在匯編時似乎并未將引用率看作是篩選的主要標準之一⑨,而是更關注其內容。即這些文章或者在研究領域的開拓上、或者在研究方法論上、或者在研究范式的構建上、或者在學科歷時的梳理上,都顯示出了它們的開拓性和巨大影響力。這一點在上文第一部分對每篇文章的介紹中就可以清晰地看到。但該書也有一些缺憾。
(一)英語/西方體系傾向。正如Ricento本人在“概述”一章中所指出的,因為四卷本所選取的所有論文都是用英語寫成的,所以就不可避免的帶有“明顯的講英語人/英語圈偏向”(第2頁),而其呈現的所謂的“研究社區”也主要就是“六個核心英語圈國家”,即美國、英國、加拿大、澳大利亞、愛爾蘭和新西蘭。這種傾向,顯然是LPP(以及其他許多學科)研究的“歐洲中心主義”(威利 2016[2006])的又一體現。第一卷許多文獻的理念是反對英語霸權、提倡多樣性和多元化,但是僅從文獻的選取來看,離這一目標還是有很大距離。可是,在英語已經成為國際學術通用語以及單極多元的世界語言格局模式下(王春輝 2016),不如此操作,又能怎么辦呢?
(二)政治視角/歷史—結構路徑傾向。LPP研究不像數學、物理、生物等學科那般有著一些中立的原理、定理,它不是中性的(Gorter 2012:100;Edwards 2012:431),而是與研究者及研究對象群體的想法和信念密切相關。這一點也體現在了Ricento的匯編當中。Ricento本人本科時專業是政治學,盡管后來碩士和博士都是應用語言學,但是其研究卻保持了一貫的政治視角傾向。第一卷中大多數的文獻即是對LPP政治/歷史—結構視角研究的聚焦。由此也就可能過濾了許多其他方向的努力,比如Bernard Spolsky的系列研究。應該說,政治視角對于語言的地位規劃以及涉及宏觀層面的習得規劃研究最有價值,但是對本體規劃而言則較少有具體的操作性意見可言。此外,作為對政治/歷史—結構路徑的批判,對LPP實踐方/代理方的研究也呈現出了新趨勢,即從最初主要集中于“自上而下”路徑時對國家、政策制定機構的關注,到擴展到“自下而上”路徑中其他機構、團體、家庭及個人的關注⑩。
第一卷關注的是LPP的歷史和理論,李圣托(2016[2006])以及Hult & Johnson(2015)也是近幾年來在這方面的重要總結性成果。但是“盡管語言規劃領域有豐富的理論,但是對語言政策的創制、解讀、實施、實例化等經驗數據的收集工作卻無法與理論和概念的繁榮相匹配。在某種程度上,這是這一領域方興未艾的本質的自然結果。”(Johnson 2013:95)Ricento早在十年前就已提醒人們注意LPP研究的兩大困境:(1)有關語言規劃的實踐問題還沒有深入的探討,即具體語言政策的制定、實施和評估;(2)研究者們對語言規劃的機制缺乏興趣?(李圣托2016[2006]:17)。時至今日,這些困境依然存在。
三、幾點啟示
LPP研究在中國的發展大致是:新世紀之前的研究基本上是介紹性的,新世紀之后探究性研究越來越多。有些學者認為,中國的語言戰略與語言政策研究已漸成體系(趙蓉暉 2014),語言規劃學作為一門學科也已呼之欲出(李宇明 2015)。LPP儼然已經成為了中國社會語言學研究最火熱的領域以及中國本土社會語言學研究走向國際的領域重鎮?。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Ricento的四卷本,特別是本文評述的第一卷可以給中國的相關研究一些啟示。
(一)需要加強民族志、經濟、批評話語特別是政治視角的LPP研究,增強LPP研究的跨學科視域。中國的LPP研究有一個“語言生活研究/語言生活學術共同體”(郭熙、祝曉宏 2016)的大背景,研究者往往有語言學背景,他們立足于中國實際國情,非常注重問題驅動以及對問題解決之道的探求(趙蓉暉 2016)。Spolsky(2015)在為《中國語言生活狀況》英文版寫的序言開頭,摘錄了李宇明的一句話表明了他對這一研究取向的認同之意:“政府應當管理的是語言生活,而不是語言本身。”
在這一研究范式的基礎上,近幾年也出現了對LPP政治性話題的討論(如郭熙 2007;周慶生 2016)或政治視角研究的呼吁(如杜宜陽、趙蓉暉 2016),也出現了一些對民族志方法的介紹性研究(如李英姿2016)。徐大明主編的“語言資源與語言規劃叢書”“語言規劃經典譯叢”和劉海濤主編的“應用語言學譯叢”相繼翻譯出版了一系列LPP研究界的經典著作,而這些著作中的大部分都展示了對政治性、民族志、方法論等視角的強調與分析。
此外,值得一提的一點是,埃杰(2012[2001]:175—176)用一個表格展示了英國的政治家與語言學家對標準英語的態度差異,這一差異是學院派學者與最終決定政策制定的當權者之間經常會出現的一種狀態。也就是說,不僅在研究中需要政治視角的切入,在實踐中更是無法回避的事實。
該卷恰恰強調了LPP的政治、經濟、民族志等理論和歷時視角,這對于中國的LPP研究來說無疑是具有促動作用的。期待在已有的介紹的基礎上,中國的LPP研究能在這幾個維度上有更具經驗性、更細致、更系統的研究。
(二)加強學科理論和方法體系的研究和構建。本卷的每篇文章都體現出了很強的理論和方法論價值,而這可能恰恰是未來中國LPP研究的另一個需要加強的方面。Hult & Johnson(2015)列述了十幾種LPP研究的方法論路徑,坦白地說,中國的LPP研究在書中提到的大部分方法路徑上的探索都尚顯乏力(趙蓉暉 2016;張天偉 2016)。
注 釋
① 漢語譯文可參見祝畹瑾(1985:218—238)。
② 括號內注明論文的作者及首次發表的時間以便讀者查找。由于這些論文已入選該論文集,參考文獻列表中不再出現。
③ 比如我們經常提到的“地方普通話”就可以看作是較為典型的例證。
④1992年,Ken Hale在Language雜志第68卷第1期組編了幾篇瀕危語言的文章,從此這一議題開始引起學界的極大關注。
⑤ 漢語譯文可參見祝畹瑾(1985:264—287)。
⑥Peter Trudgill在這一路徑上做了許多探索,最近的比如Trudgill(2011)等。
⑦ 至此,Hornberger(2015:11)提到的“LPP的早期四巨頭”就都集齊了,他們是:Joshua A. Fishman、
Jyotirindra Das Gupta、Joan Rubin和Bj?rn Jernudd。
⑧ 見本論文集的第三篇文章。
⑨ 根據“谷歌學術”的檢索數據,22篇文獻的被引用率依次為:4587、210、607、481、921、1136、436、164、195、150、31、126、260、188、2、1223、165、161、168、393、207、122。數據截止到2016年12月25日。其中,第十六篇的數據“1223”是Tollefson(1991)整本書的被引用率。
⑩ 也就是周慶生(2010)、張天偉(2016)所說的“微觀語言規劃”的內容。
?Ricento提到缺乏興趣的一個原因:大多數的社會語言學家和應用語言學家缺乏政策科學方面的科研訓練。
? 代表性事件就是李嵬和李宇明主編的Language Policies and Practices in China系列叢書在德古意特出版社的陸續出版。
參考文獻
丹尼斯·埃杰 2012[2001] 《語言規劃與語言政策的驅動過程》,吳志杰譯,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
杜宜陽、趙蓉暉 2016 《構建融合政治學與語言學的語言政策理論——評〈語言政策與政治理論〉》,《外語研究》第5期。
郭 熙 2007 《以“國、 中、 漢、 華、 唐” 為上字的詞與社會認同建構》,《語言教學與研究》第4期。
郭 熙、祝曉宏 2016 《語言生活研究十年》,《語言戰略研究》第3期。
李英姿 2016 《語言政策研究中的民族志方法及啟示》,《民族教育研究》第5期。
李宇明 2015 《語言規劃學的學科構想》,《世界華文教育》第1期。
托馬斯·李圣托 2016[2006] 《語言政策導論:理論與方法》,何蓮珍、朱曄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
王春輝 2016 《當代世界的語言格局》,《語言戰略研究》第4期。
威 利 2016[2006] 《歷史研究的經驗:對語言政策和語言規劃的啟示》,《語言政策導論:理論與方法》,托馬斯·李圣托編,何蓮珍、朱曄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
詹姆斯·托爾夫森 2014[2013] 《危機與變革時代下的語言政策》,《語言教育政策:關鍵問題》(第二版),詹姆斯·托爾夫森主編,俞瑋奇譯,北京:外語教學出版社。
張天偉 2016 《語言政策與規劃研究:路徑與方法》,《外語電化教學》第2期。
趙蓉暉 2014 《語言戰略與語言政策研究漸成體系》,《中國社會科學報》,12月30日。
趙蓉暉 2016 《論語言規劃研究的中國學派——評〈語言規劃概論〉》,《語言戰略研究》第1期。
周慶生 2010 《語言規劃發展及微觀語言規劃》,《北華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6期。
周慶生 2016 《語言與認同國內研究綜述》,《語言戰略研究》第1期。
祝畹瑾 1985 《社會語言學譯文集》,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Edwards, John. 2012. Language Management Agencies. In Bernard Spolsky (ed.), The Cambridge Handbook of Language Policy. Cambridge: CUP.
Gorter, Durk. 2012. Minority Language Researchers and Their Role in Policy Development. Language, Culture and Curriculum 25 (1), 89–102.
Hornberger, Nancy H. 1988. Bilingual Education and Language Maintenance: A Southern Peruvian Quechua Case. Dordrecht: Foris.
Hornberger, Nancy H. 2015. Selecting Appropriate Research Methods in LPP Research: Methodological Rich Points. In Francis M. Hult and David Cassels Johnson (eds.), Research Methods in Language Policy and Planning: A Practical Guide. Oxford: Wiley-Blackwell.
Hult, Francis M. and David Cassels Johnson (eds.). 2015. Research Methods in Language Policy and Planning: A Practical Guide. Oxford: Wiley-Blackwell.
Johnson, David Cassels. 2013. Language Policy.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Kloss, Heinz. 1952. Die Entwicklung neuer germanischer Kultursprachen von 1800 bis 1950. Munich: Pohl.
Kloss, Heinz. 1969. Research Possibilities on Group Bilingua?lism: A Report. Quebec: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Research on Bilingualism.
Lo Bianco, Joseph. 2010. Language Policy and Planning. In Nancy H. Hornberger and Sandra L. McKay (eds.), Sociolinguistics and Language Education. Bristol: Multilingual Matters.
Lo Bianco, Joseph. 2015. Exploring Language Problems Through Q-Sorting. In Francis M. Hult and David Cassels Johnson (eds.), Research Methods in Language Policy and Planning: A Practical Guide. Oxford: Wiley-Blackwell.
Owens, Jonathon. 2005. Introduction. Linguistics 43 (5), 871–881.
Rubin, Joan and Bj?rn H. Jernudd. 1971. Can Language Be Planned? Sociolinguistic Theory and Practice for Deve?loping Nations. Hawaii: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Ruiz, Richard. 1984. Orientations in Language Planning. NABE Journal 8 (2), 15–34.
Spolsky, Bernard. 2015. Foreword. In Li Yuming, Language Planning in China. Berlin/Boston/Beijing: De Gruyter.
Tollefson, James W. 1991. Planning Language, Planning
Inequality: Language Policy in the Community. London: Longman.
Trudgill, Peter. 2004. Glocalisation and the Ausbau Sociolinguistics of Modern Europe. In Anna Duszak and Ursrula Okulska (eds.), Speaking from the Margin: Global English from a European Perspective. Frankfurt: Peter Lang.
Trudgill, Peter. 2011. Sociolinguistic Typology: Social Determinants of Linguistic Complexit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責任編輯:戴 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