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住民的語言復興與心理健康
諸葛漫 陳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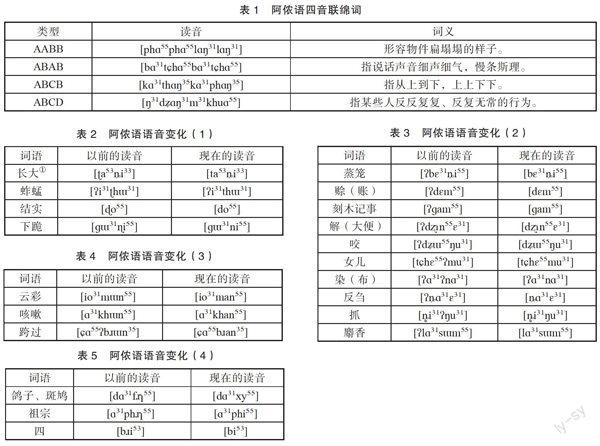
提 要 主要通過文獻法和個案研究探討母語復興對澳大利亞原住民的心理健康的影響。在分析語言、認同感與心理健康之間關系的基礎上,以澳大利亞邦格拉語的復興實踐為中心,結合澳大利亞相關機構的報告和美國、加拿大等地的調查結果,說明母語的復興有助于原住民群體提高自信,養成心理韌性,增強認同感,樹立更明確的生活目標,提升幸福感,從而促進心理健康。為了系統評估語言復興對心理健康的益處,語言復興研究者還必須與具備心理健康專業知識的研究人員緊密合作,確定、檢驗、必要時改造現行的量化分析方法和工具。在對復興成效的評估中,復興的過程與復興的目標同樣重要。
關鍵詞 語言滅絕;語言復興;心理健康;評估
Abstract This study is an attempt to explore the impacts of language revival on the mental health of Indigenous Australians through lit?erature review and case study. On the basis of a delineation of how language, a sense of identity and mental health are interrelated, the study, with a focus on Barngarla reclamation, integrates the data from various reports of Australian institutions and the findings about minority groups in the U. S. and Canada, and demonstrates that language revival may enhance the mental health of minority groups like the Barngarla people through improving their self-confidence, helping them develop resilience, and improving their sense of identity, sense of purpose and wellbeing. However, for a systematic assessment of the benefits of language reclamation to mental health, revivalists need to cooperate with mental health research professionals so as to identify, review, and (when required) adapt existing quantitative methods and tools. In addition, we contend that, in the evaluation of language reclamation activities, the revival process is as important as the revival goals.
Key words linguicide; language revival; mental health; assessment
一、導 言
語言、文化乃至健康是相互依存的關系(Aboriginal and Torres Strait Islander Social Justice Commissioner 2009)。在人類生活中,語言具有核心作用,關乎一個群體的幸福和心理健康,這是語言研究中的一個公設。從語言系統的變化中,我們很容易觀察到群體的邊緣化現象(Heinrich 2004)。此外,根據 Phinney(1990)的族群認同發展理論,語言是族群認同的關鍵因素之一。傳統語言作為群體身份和個人身份的構件之一,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對于語言與心理健康之間的關系,學界已做過一些研究,比如 Hallett等(2007)對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省的研究顯示:青少年的自殺與母語口語能力的缺失之間有著明顯的相關性。他們發現,在為數較少、至少一半成員自陳具備母語口語能力的群體中,青少年的自殺率明顯下降,甚至為零。在某些群體里,比如澳大利亞西北部的金伯利地區,青少年的自殺率是平均自殺率的7倍(Australian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 2012;Tighe & McKay 2012)。在一些澳大利亞原住民區域中心,從那些母語正在消亡的孩子們的表現來看,他們承受著異文化的巨大壓力(The Western Australia Aboriginal Child Health Survey 2005)。心理健康的一個必要條件是強烈的認同感(King et al. 2009),然而對大多數澳大利亞原住民而言,心理健康是一種奢望,他們的健康數據尤其清楚地說明這是一種社會現實。過去200年來,由于系統性的種族歧視、虐待和文化失落,澳大利亞原住民和托雷斯海峽島民遭受了巨大的痛苦,他們生活貧困,受人歧視,人均壽命短,健康狀況惡劣,心理疾病高發(Australian Bureau of Statistics 2010a;Purdie et al. 2010)。由于語言、文化、群體、家庭和認同感等因素相互聯系、相互影響、相互強化,因此,關注原住民健康的人士已經形成一種共識:若要全面了解原住民群體的健康狀況,就不能不考慮這些因素(National Aboriginal Health Strategy Working Party 1989)。
然而遺憾的是,迄今為止,對于語言復興與心理健康之間的關系尚無系統的研究,原因之一是語言復興活動還處于起步階段,尚未在澳大利亞廣泛開展起來,學界很少關注語言復興究竟會帶來哪些心理效益。一些原住民群體雖然急切盼望恢復自己的原住民權益,卻缺乏捍衛權益所必需的母語和母語知識,在這種背景下,語言復興研究的焦點之一是復興母語對于增進這些群體的心理健康有何作用。我們認為,通過語言復興實踐,可以系統評估語言復興與心理健康的關系,包括語言復興是否因增權益能(empowerment)而促使原住民群體減少自殺、增強認同感、樹立更明確的生活目標。因此,在下文中,我們將以澳大利亞邦格拉語的復興實踐為中心,結合全球范圍內的相關研究成果,探討語言復興與心理健康之間的關系。我們的假設是:語言復興具有一些可評估的益處,比如增權益能,提高自信心、自豪感、認同感和幸福感,因而有助于彌合原住民群體與非原住民群體之間健康上的差距。
二、語言、認同感與心理健康之間的關系
(一)語言對認同感和心理健康的影響
原住民若想獲得成功,哪些心理健康因素會起到關鍵性作用?影響心理健康的積極因素雖然不多,但是已有一些綜合性研究揭示了心理健康的關鍵因素(Human Rights and Equal Opportunities Commission 1997;Purdie et al. 2010;Trewin 2006;Zubrick et al. 2005),其中包括對傳統語言的了解和使用、與土地的聯系、家人間的聯絡、文化實力和精神境界。
Hunter 和 Harvey(2002)曾經對原住民自殺現象做過廣泛的調查,其研究對象包括澳大利亞原住民、加拿大原住民、因紐特人和美國原住民青少年。他們發現,就缺乏文化參與與自殺之間的關系而言,這些群體中存在著相似的模式。在對邊緣化青少年的信心所做的研究中,Wexler等(2009)發現,那些自我報告具有較強幸福感的人與那些積極從事傳統文化活動的人之間有著某種關聯。當前,文化遷移的兩個主要問題是日益加劇的全球化進程和殖民造成的遺留問題,而文化知識的遷移也稱為文化傳承(de Souza & Rymarz 2007)。每當面對不同文化、建立的認同感不穩定時,一代代新人由于未能成功地進行文化傳承或遷移而倍感失落(Wexler 2006)。
據 King等(2009)研究,強烈的認同感是心理健康的一個必要條件。語言據說是影響青少年和年輕成年人的民族認同感的第三大因素,其影響力僅次于自我認同和家庭認同(Kickett-Tucker 2009)。然而,在澳大利亞,由于語言滅絕(linguicide)現象極端嚴重,僅有19%的原住民會講流利的母語(Australian Bureau of Statistics 2010a)。語言滅絕使得許多原住民不了解自己的文化,比如,雖有60%的原住民認為自己屬于某一語言社團,但其中35%的人并不清楚自己的祖先屬于哪一個原住民部落,而這正是由“被偷走的一代”和文化斷層等不幸現象所導致(Australian Institute of Aboriginal and Torres Strait Islanders Studies & Federation of Aboriginal and Torres Strait Islanders Languages 2005)。
(二)失去母語對心理健康的危害
母語是原住民文化的核心組成部分,關乎原住民的文化表達、文化保護和自主權,關乎其集體認同和個人認同,還關乎其精神主權和知識主權,因而對原住民的健康至關重要(Marmion et al. 2014)。然而,隨著殖民化的不斷發展,原住民的母語普遍衰微,許多原住民群體最后失去了自己的母語。據預測,世界上至少一半語言將會在21世紀消失(Marmion et al. 2014;Global Language Hotspots Living Tongues Institute for Endangered Languages 2007)。
就澳大利亞而言,在英國人定居澳大利亞之前,澳大利亞約有330種原住民語言,而現在僅剩13種還處于健康狀態(即作為口語被各年齡段的大部分人廣泛使用),亦即僅有4%的原住民語言被作為母語使用(Australian Institute of Aboriginal and Torres Strait Islander Studies & Federation of Aboriginal and Torres Strait Islander Languages 2005;Indigenous Remote Communications Association 2013)。由于侵略、殖民化、全球化和同質化等因素的影響,越來越多的原住民群體正在失去自己的文化。舉例來說,在澳大利亞南澳州的艾爾半島,邦格拉語(Barngarla)曾經是一群原住民的母語,但是這個群體正在蒙受語言滅絕所帶來的不良后果,而與邦格拉群體同命運的還有其他原住民和托雷斯海峽島民群體。總體而言,由于殖民統治,在澳大利亞沿岸地區(比如南澳州、維多利亞州和新南威爾士州)生活的原住民比中部曠野地區的原住民遭受了更為嚴重的語言滅絕。母語喪失、隨之而來的文化自主權喪失、知識主權喪失、對殖民者語言的依賴等加重了原住民的無力感和自卑情緒,自殺現象也更為常見。
失去母語的現象遍及全世界,對原住民的健康與幸福產生了極大的負面影響。澳大利亞原住民被公認為心理疾病高發群體(Swan & Raphael 1995),與非原住民相比,他們心理痛苦、抑郁、自殘和自殺的比率更高(Social Health Reference Group 2003),死于心理障礙和行為障礙的概率更高(Australian Bureau of Statistics 2005)。種族歧視、邊緣化、家人分離、社區功能萎縮、社會地位低下等諸多因素給原住民造成巨大壓力,并對個人心理健康和幸福產生持續的影響(Swan & Raphael 1995)。不過,失去母語的惡果遠不止此。就“被偷走的一代”而言,孩子被從家人身邊強行帶離,不得再講祖先的語言,被主流社會強行同化,這樣造成的影響巨大而持久。這些孩子成年以后,因不會講母語而無法與家人交流,也無法參加各項傳統活動。“母語消失、文化遭破壞以及隨之而來的親屬結構斷裂等因素與成癮性疾病、社區暴力、家庭破裂、自殺等現象之間存在著聯系,這些損失的代價難以估量,不僅涉及原住民個人,而且波及幾代人”(Memmott et al. 2001)。在原住民看來,他們產生健康問題的根本原因是失去土地、失去自己的文化、失去認同感(National Aboriginal Health Strategy Working Party 1989)。對原住民而言,保護、維護、贊美自己的文化不僅是一條核心原則,而且是自己主權的一種重要體現(United Nations 2009)。
如上所述,自被殖民以來,澳大利亞原住民遭受了巨大的痛苦和折磨(參見Sutton 2009),在這些群體中,抑郁、藥物濫用、自殺等心理疾病頻發,比如2007年的一份調查顯示,自殺是原住民的第六大殺手,原住民的自殺率幾乎是非原住民的3倍(Purdie et al. 2010)。原住民和托雷斯海峽島民的心理問題十分嚴重,亟待社會各方加以關注和解決,他們的心理健康成為澳大利亞健康專業人員、健康機構和政府機構所關注的一個重要問題。若要從根本上改變原住民與非原住民在健康上的不平等狀況,我們就必須找到一些創新性的方法,樹立可持續發展的長期目標,提供更好的服務,讓原住民群體增權益能并融入主流社會。原住民的健康理念是整體性的,涉及“個人和群體的身體健康、社會幸福感、情感健康、文化健康”的方方面面,是推動原住民群體掌握主動權、更好地為自己服務的基本前提(National Aboriginal Health Strategy Working Party 1989)。只有接受這種整體性健康理念,才能更好地認清有哪些因素能夠保證和促進原住民的健康。
殖民化和壓制性的法律法規致使原住民蒙受損失、悲慟和創傷(Purdie et al. 2010),但是在面對一種強加的、一向于自己不利的文化時,原住民文化和群體有一些獨特的保護性因素成為原住民力量和自愈力的源泉。有鑒于此,我們提出一個主張:語言始終是一個基礎性的保護因素,能為我們支持群體的生存、發展與繁榮提供一些讓人耳目一新的解決方案。
三、澳大利亞原住民和托雷斯海峽島民心理健康現狀
曾被診斷為患有心理疾病的澳大利亞人中,3成以上的人在24歲之前表現出相關癥狀并得到確診(Australian Bureau of Statistics 2010b;Headspace:National Youth Mental Health Foundation 2011)。在澳大利亞原住民群體中,年齡在25歲以下的人口占比高達57%(Australian Institute of Health and Welfare 2011)。這樣的人口分布加上各種不利的生活條件,使原住民和托雷斯海峽島民中的青少年比澳大利亞其他群體更容易患上心理疾病;他們可能飽受各種社會問題和情感問題的折磨,因而無力保持積極的心態,無法應對生活中的逆境,比如摯愛之死、摯愛之人被強迫離開、歧視、貧困、暴力、虐待、賭博、監禁、教育競爭、創傷等(Purdie et al. 2010)。舉例來說,三分之一的原住民青少年的祖父母或看護人屬于“被偷走的一代”(the Stolen Generations),那些長輩被政府強行帶離自己的家人,使得長輩和后輩們的痛苦水平居高不下,負面的心理沖擊至今顯而易見(Australian Health Ministers Advisory Council 2012;Australian Institute of Health and Welfare 2011;Dodson et al. 2010)。這種文化斷層、創傷和失落可能延續至后代并日益嚴重,這些群體的行為往往表現為不合群、怨恨、易怒、暴力、濫用藥物等,而這一切的根源在于強烈的絕望、抑郁、焦慮以及各種錯綜復雜的精神苦悶(Dodson et al. 2010;Social Health Reference Group 2004)。
因失去身份、失去生活目標、失去自豪感、失去自尊而形成的集體危機感可能導致集體絕望和集體自殺(Hunter & Harvey 2002)。2001年至2011年,年齡在10歲至24歲的北領地青少年自殺者中,75%是原住民(Hanssens 2008、2012)。以Mowanjum群體為例,他們的人口總數為300,幾個月之內就有5人自殺身亡(Australia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 2012)。群發性自殺(即因一人自殺而引發多人效仿)現象在原住民群體中發生的可能性大大高于非原住民群體,而且原住民往往沒有辦法擺脫悲傷(Hanssens 2008、2012)。
原住民的自殺率幾乎是非原住民自殺率的3倍,而自殺率最高的群體是年輕人(Australian Institute of Health and Welfare 2011)。2010年,據澳大利亞統計局(Australian Bureau of Statistics 2010c)統計,與非原住民同齡人相比,年齡14歲至19歲、20歲至24歲的原住民男性發生自殺的概率分別是非原住民同齡人的4.4倍和3.9倍,而與此同時,這兩個年齡段的原住民女性發生自殺的概率甚至更高,分別是非原住民的5.9倍和5.4倍。每5個原住民青少年中,就有2個曾經想過要自殺。這些數據無疑是觸目驚心的。作為語言研究者,我們可以從語言的角度去分析哪些關鍵性的積極因素有助于改善這種嚴峻的形勢。
四、邦格拉語語言復興個案研究
(一)邦格拉語語言復興概述
澳大利亞原住民是澳大利亞最早的居民,于40 000多年前定居澳大利亞大陸。他們與世界上的其他地方完全隔絕,以打獵和采摘為生。在歐洲人占領澳大利亞之前,原住民部落共有 500 多個,人數達75萬之多。18世紀時,歐洲人到達澳大利亞,強迫原住民離開他們的家園。19世紀早期,一些捕鯨人和海豹捕獵者到達邦格拉部落活動的區域,邦格拉人從此開始與殖民者接觸。在南澳州的林肯港殖民地周圍地區,邦格拉原住民與殖民者爆發過激烈沖突(Brock & Kartinyeri 1989)。林肯港和周邊地區在1840年路德教會傳教士Clamor Wilhelm Schürmann到達之前,仍是暴力頻發地區(Schurmann 1987)。林肯港附近的Poonindie 傳道所從1860年一直運行到19世紀90年代。現在的邦格拉人群體中,老一代的人屬于“被偷走的一代”,他們小時候被政府機構帶走,去接受文化教化,而這種教化過程意味著與家人、故土、文化和母語分離開來,給他們留下了深深的創傷,不僅讓他們本人刻骨難忘,也成為其他未被偷走的家庭成員的心靈創傷。隨著對土地、母語、文化等權益的認識的提高,邦格拉人希望重新找回自己的文化之根,重新建立起與祖先的聯系。邦格拉群體自2011年決定復興自己如“睡美人”一般沉睡的母語以來,一直與諸葛漫教授緊密合作,希望能拯救、重新學習、記錄邦格拉語并將它傳給后代。
實際上,在復興活動開始之前,已經沒有任何人講邦格拉語。澳大利亞的記錄語言學家Luise Hercus 在20世紀60年代記錄下來的零星資料非常有限,而這些記錄正是邦格拉語復興活動必不可少的文字資料。目前,邦格拉人主要居住在艾爾半島的三大區域:林肯港、懷阿拉和奧古斯塔港。這里的邦格拉人現在使用的語言是一種原住民英語(有時稱為West Coast Talk,即西岸話),詞匯中混合了其他原住民語言中的一些詞和短語,但是似乎沒有源于邦格拉語的詞匯,這說明邦格拉語早已消亡。
2011年9月,邦格拉人代表和諸葛漫等人召開第一次會議,探討復興邦格拉語的有關問題,此后又在阿德萊德、林肯港、懷阿拉和奧古斯塔港多次召開會議。2012年5月,第一屆邦格拉語言復興講習班在林肯港開辦,兩天內共有25人參加,主要討論了邦格拉語詞匯的發音和現有詞典(Schürmann 1844)的問題。從那以后,參與復興活動的各方開始密切合作,而當前的工作重點包括核對現有的邦格拉語詞匯、核對文獻資料、設計與文化相契合的地名和建筑物名、擬定“歡迎來到故土”禮儀、解決邦格拉語教師及講習班學生和大眾有關邦格拉語詞匯的問題。此外,還有一些更為細致的工作,包括建立一套更為用戶友好的拼寫體系以方便教學、傳播和會話,修改1844年的邦格拉語原版詞典等。這些初步工作促成了10個講習班在艾爾半島開辦。
到目前為止,邦格拉語的復興試驗一直運行良好。諸葛漫積累的一些資料可以作為定性數據,供我們分析語言復興與原住民的心理健康之間的關系。比如,在對參與復興活動的邦格拉原住民的訪談中,已有數位原住民表示,學習邦格拉語讓他們找到了認同感、獲得了自由、認清了生活的目的,因而對他們具有增權益能的作用(諸葛漫、姚春林 2014)。從邦格拉人民的表述中,我們得到一個非常重要的認識:在對語言復興的益處進行評估時,僅對被復興的語言作為口語使用的狀況做出評估是不夠的;從原住民的權益和幸福來看,復興語言的過程與結果同等重要,也就是說,最后能否完成對被復興語言的記錄、分類和頻繁使用雖然很重要,但是復興該語言的過程本身是同樣重要的。總之,復興過程與復興目標一樣重要。
正是在2011年,諸葛漫(Zuckermann & Walsh 2011)提出了復興語言研究(Revivalistics)這一概念。復興語言研究是一個新興的跨學科研究領域,它包括復興語言學(Revival Linguistics)和復興組學(Revivalomics,即語言復興的大數據分析),旨在通過對全球不同社會背景下的語言復興實踐進行系統研究和比較,探索語言復興的普遍制約條件和全球機制(Zuckermann 2009)以及與文化相關的特異性(Zuckermann & Walsh 2011)。復興語言研究的范圍大大超過復興語言學,其研究角度多種多樣,涉及法律(Zuckermann et al. 2014)、心理健康、社會學、人類學、政治、教育、殖民地開發、傳教研究、音樂、建筑等。邦格拉語復興活動自2011年開展至今,急需完成的一項工作是:通過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全面系統地評價語言復興對澳大利亞原住民心理健康的影響。我們的假設是:在語言復興過程中,原住民的心理健康將得到顯著改善,自殺意念降低,自我傷害減少,自殺率下降。到目前為止,我們已經收集了一些一手材料,但是還缺乏相關的具體數據作為定量分析的根據。所幸的是,2016年年底,諸葛漫率領的研究團隊獲得了澳大利亞國立健康與醫學研究理事會(National Health and Medical Research Council,簡稱NHMRC)101萬澳元的資助,將在未來5年內逐步完成邦格拉語語言復興對邦格拉人心理健康之影響的量化研究。據我們對公開信息的研究,這種類別和力度的研究資助在全球范圍內尚屬首次。
(二)語言復興的目標
語言復興的目標必須切合實際。如果將語言復興視為一個連續體,那么根據待復興的語言的特點和對語言復興的需要,我們可以將復興活動分為收復(reclamation,像Kaurna語)、更新(renewal,像Ngarrindjeri語)和復興(revitalization,像Walmajarri語)三大類別。2014年,澳大利亞第二次原住民語言調查報告出爐,其中列出了語言復興活動的目標及排序,該調查數據得到了參與邦格拉語復興實踐的原住民的認同,詳情如下所示:
澳大利亞第二次原住民語言調查報告說明,澳大利亞當下開展的大部分語言復興活動的目標不僅僅是增加語言使用者數量,而且要幫助原住民與自己的文化建立聯系、構建認同感并提升幸福感(Marmion et al. 2014)。這些目標能否實現?復興活動是否會帶來預期的效益?邦格拉語的復興實踐為探討這些問題提供了一個獨特的機會,我們可以從中驗證語言復興與心理健康之間的關系,還可以摸索出一些技巧和方法去幫助有心理疾患的原住民,并為其他原住民群體的母語復興提供一種可資借鑒的模式。
(三)邦格拉語復興實踐對語言復興研究的啟示
通過學習祖先的語言,原住民能夠找回自己的文化之根,增強自己的認同感,因而他們愿意付出努力,去復興自己“沉睡的”母語(Zuckermann & Monaghan 2012)。為了支持原住民的語言活動,幫助他們重拾認同感,我們急需開發一些語言工具,從跨學科角度(包括從進化的角度)去深入研究語言復興。邦格拉語的復興實踐有助于確立語言復興研究這一新的跨學科研究領域。與復興語言學相比,記錄語言學旨在在瀕危語言陷入沉睡之前對其進行記錄和描寫,而語言復興研究可以有效彌補記錄語言學之不足。此外,語言復興研究一反以西方語言學家為中心的做法,將那些文化處于瀕危狀態的群體置于研究的中心,對語法的編寫和詞典編纂都提出了新的要求:語法和詞典都必須滿足語言復興的需求,以用戶友好的方式呈現給相關語言群體,而不僅僅是給語言學家使用。舉例來說,我們必須避免使用那些華而不實、基于拉丁語的語法術語,提供便于使用的拼寫形式。以表示“恢復”之義的詞為例,路德教會傳教士Clamor Wilhelm Schürmann 給邦格拉人提供的拼寫形式為nunyara,這種拼寫會被念為nanyara(重音在倒數第二個音節且第一個元音的發音類似于cup中的發音),而正確的發音為Noonyara,因此他的拼寫不符合用戶友好原則。熟悉德語和國際音標的語言學家會覺得nunyara更合適,但是從語言復興研究的角度來看,邦格拉人現行的母語是一種英語,因此Noonyara這種拼寫更可取。
語言復興可能涉及原住民、少數民族或文化瀕危群體,在語言復興的初期階段,語言學家必須進行長期觀察、傾聽和學習,了解這些群體的需求、愿望和潛能,才能激勵并幫助他們。即便如此,一切語言復興活動都存在語言學上的制約條件,比如希伯來語、邦格拉語、毛利語、夏威夷語、Kaurna語、Ngarrindjeri語、Wampanoag語、Manx語和Cornish語。掌握這些待復興的語言有助于復興者和第一民族(First Nations,現今加拿大境內的北美洲原住民及其子孫,但不包括因紐特人和梅提斯人)領導人有效開展工作,比如更多地關注基礎詞匯和動詞變位而不是發音和詞序。
從語言復興研究的角度看,邦格拉語的復興活動可視為一個運行良好的試驗項目(Zuckermann & Monaghan 2012)。該項目的開展可能會給歷史語言學帶來顯著的變化,比如會削弱“譜系樹模型”,對其“一種語言只有一個祖先”的論點提出質疑。我們相信,沉睡的語言一旦成功復興,必將呈現混合的特性,它不僅將包含該語言本身的成分,而且會吸收語言復興者和記錄者的母語成分(諸葛漫 2008;諸葛漫、姚春林 2012;諸葛漫、徐佳 2013;諸葛漫等 2015)。
五、語言復興效益的初步觀察
如前所述,語言是社區認同和個人身份認同的重要構件之一,因而母語對于澳大利亞原住民而言具有重要意義。澳大利亞原住民語言的復興實踐既稀少又獨特,雖然現在還處于起步階段,但是在原住民爭取恢復文化自治、獲得精神主權和知識主權、提升幸福感的過程中,母語的復興變得越來越重要。澳大利亞統計局(Australian Bureau of Statistics 2012)的報告顯示,與不會講母語的人相比,會講母語的年輕原住民和托雷斯海峽島民過度飲酒和濫用藥物的概率更低,成為暴力受害者或受暴力威脅的概率更低。
2007年,Hallett等(2007)曾對文化傳承與心理健康之間的關系做過一項基礎性研究,他們從自主自理、土地權、教育、健康護理、文化設施、警察/消防服務、語言等7個文化傳承影響因素入手,分析評估了150個因紐特原住民群體約14 000人中曾有過記錄的自殺現象。他們抽樣調查的結果表明,調查所涉及的所有群體中,母語熟悉度較高(50%以上的成員熟悉)的群體自殺率低于母語熟悉度較低的群體;在母語語言技能較高的16個群體中,每10萬人中有13人自殺身亡,而母語語言技能較差的群體中,每10萬人中有97人自殺身亡。除了母語技能之外,若有其他文化保護因素(即上述7種因素)同時存在,那么就可以更有效地預防自殺。這種研究結果表明,語言是文化保護因素之一,母語有助于提高文化認同感,降低原住民群體的自殺率。澳大利亞的情形或許與此類似,因為已有一些證據支持這種說法。比如,一項研究顯示,童年時母語較為流利的人較少出現情感問題和社會問題(Zubrick et al. 2005),這可能意味著早期干預有助于青少年和成年時期的心理健康。據此我們可以推斷:那些母語講得流利或者至少具備足夠的母語知識的人,其文化認同感更為穩定。
澳大利亞原住民既難以融入白人社會,又失去了自己的傳統文化,可謂生活在文化裂縫之中,而語言復興能夠幫助他們提高對自己的文化傳統的認識,提升幸福感和自豪感,因而具有增權益能的作用。美國語言復興領域的杰出人物Fishman(1990)曾經指出:
現代生活真正的問題,同時也是逆向語言轉換必須解決的一個問題,是如何才能建立一個我們仍然可以號稱屬于自己的“家”,又如何通過建設這個家而構建社區認同、得到安慰、找到陪伴、發現生活的意義?這些本是生活的基本條件,而主流社會卻越來越無力提供。
諸葛漫注意到,一些投入Kaurna語和邦格拉語語言復興實踐活動的原住民不僅自信心得到增強,而且更有可能繼續學習下去。有的人因受自殺事件的刺激而開始投身于語言復興。比如,Jack Buckskin的姐姐自殺,促使他投身于Kaurna語的復興;Geoff Anderson先前患有嚴重的焦慮癥和抑郁癥,后來開始聽課學習母語Wiradjuri語,他說,學習母語救了他的命。這兩位原住民現在都擔任母語教師,在語言復興活動中發揮著主導作用。可見,教育的成功可以提高就業能力,消除差距,減少違法犯罪行為的發生。
正因為語言復興具有一些可感知的或潛在的益處,一些原住民群體把復興母語當作群體要務,越來越多的群體希望恢復文化自主權,獲得精神主權和智力主權,提升幸福感。已有一些零星證據表明,少數群體與傳統語言和文化之間的緊密聯系會給社會、情感、就業、認知、健康等方面帶來好處。例如,與不會講傳統語言的原住民青少年相比,會講母語的青少年有害使用酒精、濫用藥物、接觸暴力的概率更低(Aboriginal and Torres Strait Islander Social Justice Commissioner 2009)。一項針對美國少數群體的研究發現了一些證據,說明流利掌握傳統語言、熟悉傳統文化與后來養成心理韌性之間存在緊密聯系,對高危城市群體而言,“傳統因素和文化因素都是心理韌性的預測指標”(即生活品質的正面指標)(Utsey et al. 2007)。這些研究結果得到了原住民群體的高度認可。人們感到,語言復興的益處可能會通過三個方面表現出來:第一,增強認同感和對“傳統、文化、家庭、土地、群體”的歸屬感;第二,因提升自尊和自豪感而使原住民增權益能;第三,增進群體、家庭和代際之間的交流。
遺憾的是,在澳大利亞的語言復興研究中,迄今無人通過實證研究對這些潛在益處進行系統評估。不過,已有支撐性數據顯示,語言復興可以為新的健康干預活動提供機會。例如,一些研究者對澳大利亞中部群體做了一項為期10年、由國際注冊內部審計師(Certified Internal Auditor,簡稱CIA)監督的縱向研究,結果發現,原住民群體與其語言、土地和文化的緊密聯系可以帶來顯著的健康效益,這一點從心臟病和糖尿病的發病率上得到證明。非常重要的是,這些健康效益是在社會經濟狀況極為惡劣的情況下取得的。對原住民而言,語言、文化和相互關聯的感覺是不可分割且至關重要的心理韌性因素,可以抵御身處弱勢、難享健康服務、缺少就業機會、基礎設施不足等各種不利因素的負面影響(Rowley et al. 2008)。Biddle 和 Swee(2012)研究發現,參與語言復興的原住民提升了自信,更容易繼續學習其他知識,這可以作為一種初步證據,說明語言與原住民健康之間存在聯系。此外,還有證據表明,一些促進教育成功的干預活動可能會提高原住民的教育水平,增加其就業機會,減少違法違紀行為的發生(Aboriginal and Torres Strait Islander Social Justice Commissioner 2009)。
六、語言復興成效的評估問題
為了評估語言復興的成效,我們在持續進行語言復興干預的同時,還需要進行縱向的隊列研究,對復興之前、之中和之后的心理健康狀況進行比較。在對語言復興的成敗進行評估時,我們參照的標準既要包含語言標準,比如日常會話、拼寫、翻譯、口語等方面是否流利,也要從原住民群體的增權益能和幸福感等方面加以評判。語言復興過程結束時,即使被復興語言的群體中并非所有成員都以該語言為母語,并非在所有場合使用該母語進行會話,我們也不能就此認定該復興項目已經失敗,因為復興的過程與復興的目標同等重要。
邦格拉語復興活動開展至今,我們除了需要繼續設計并實施行之有效的復興活動之外,還需要著手研究如何進行復興成效評估。從事復興工作的人員需要掌握各種溝通策略和手段,編寫語法和詞典,開辦語言講習班,與學校和社區聯手推進母語教學,培訓母語教師。除此以外,他們需要應對隨時出現的各種狀況。從提高原住民的權益和幸福感這一角度來看,是否會出現全體成員在各種場合使用被復興的母語進行會話這種現象,在許多時候都屬于次要的事情。從根本上說,正如前文反復強調的那樣,復興的過程與目標同樣重要。因此,我們不僅要根據一些語言標準去評估個人和群體在語言使用和語言水平上的變化,而且要評估復興過程對參與者心理健康和幸福感的影響。為此,我們需要了解并記錄語言復興活動的積極影響,摸索出一些方法,用于檢測語言復興在個人和群體層面所產生的效益。研究者必須系統記錄語言干預對個人和群體所產生的潛在影響以及可感知的影響,深入分析調查結果,以便確定、檢驗或在必要時改造現行的評估工具。這就需要語言工作者與具備心理健康專業知識的研究人員緊密合作,仔細研究那些聚焦于原住民或少數群體流行病學研究或臨床研究的相關文獻,確定或必要時改造各種潛在的分析工具,或者設計出切實可行的分析工具。所有這些工具都必須根據一些預先確定的標準進行考察,其中的關鍵標準包括表面效度、所設問題的文化契合性、可以理解的反應分類、簡潔性、受試的完成(或經協助完成)能力、先前在跨文化語境中的使用情況、心理測量學特性(如果已知的話)等。確定分析工具之后,再根據一些方法(如Vogt et al. 2004;Brislin 1980;Van de Vijver & Hambleton 1996)加以使用,以增強心理學工具的內容效度,確保實驗工具、項目、反應分類等的文化契合性,促進對各種構件的整體性理解(Manson et al. 1985;Kirmayer et al. 1997)。
七、結 語
我們先前的假設是:語言復興與一些可評估的益處(如增權益能、提高認同感、增進心理健康)之間存在相互依存的關系,因而有助于彌合原住民群體與非原住民群體之間健康上的差距。這一假設還需要經過充分、獨立的評估才能驗證。只有準確評估語言復興過程對參與者以及更廣大群體的心理健康所產生的影響,我們才能從語言之外的標準去判斷語言復興是否成功。我們相信,語言復興會對心理健康、社會幸福和情感健康的各項指標產生積極影響。
參考文獻
諸葛漫 2008 《混合還是復蘇:以色列語的起源——多來源,形式和模式》,王曉梅譯,曾曉渝校編, 《南開語言學刊》第2期。
諸葛漫 宋學東 韓 力 2015 《希伯來〈圣經〉中詞匯的語義世俗化》,《猶太研究》第13期。
諸葛漫 徐 佳 2013 《復興語言學:一個新的語言學分支》,《語言教學與研究》第4期。
諸葛漫 姚春林 2012 《一門新的語言學分支:復興語言學——兼談瀕危語言和瀕危方言復興的普遍制約條件和機制》,徐佳譯,《世界民族》第6期。
諸葛漫 姚春林 2014 《試論澳大利亞原住民的母語權及語言賠償》,《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1期。
Aboriginal and Torres Strait Islander Social Justice Commissioner. 2009. Social Justice Report 2009. Canberra: Australian Human Rights Commission.
Australian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 2012. 7:30 Report: Spate of Suicides Grips Aboriginal Community. Perth: ABC.
Australian Bureau of Statistics. 2005. Deaths Australia 2004. Canberra: ABS.
Australian Bureau of Statistics. 2010a. The Health and Welfare of Australias Aboriginal and Torres Strait Islander Peoples. Canberra: ABS.
Australian Bureau of Statistics. 2010b. Measures of Australias Progress 2010. Canberra: ABS.
Australian Bureau of Statistics. 2010c. Suicides, Australia, 2010. Canberra: ABS.
Australian Bureau of Statistics. 2012. Publication. Canberra: ABS.
Australian Health Ministers Advisory Council. 2012. Aboriginal and Torres Strait Islander Health Performance Framework: 2012 Report. Canberra: Office for Aboriginal and Torres Strait Islander Health.
Australian Institute of Aboriginal and Torres Strait Islander Studies & Federation of Aboriginal and Torres Straight Islander Languages. 2005. National Indigenous Languages Survey Report 2005. Canberra: Department of Communications,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the Arts.
Australian Institute of Health and Welfare. 2011. The Health and Welfare of Australias Aboriginal and Torres Stait Islander People: An Overview. Canberra: AIHW.
Biddle, Nicholas & Hannah Swee. 2012.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Wellbeing and Indigenous Land, Language and Culture in Australia. Australian Geographer, 43, 215-232.
Brislin, Richard W. 1980. Translation and Content Analysis of Oral and Written Material. In Triandis, Harry C. & John W. Berry (eds.), Handbook of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 (Vol.1). Boston: Allyn and Bacon.
Brock, Peggy & Doreen Kartinyeri. 1989. Poonindie: The Rise and Destruction of an Aboriginal Agricultural Community. Adelaide: Government Printer & Aboriginal Heritage Branch, Dept. of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e Souza, Marian & Richard Rymarz. 2007. The Role of Cultural and Spiritual Expressions in Affirming a Sense of Self, Place, and Purpose among Young Urban, Indigenous Australian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hildrens Spirituality, 12 (3), 277-288.
Dodson, Michael, Adele H. Cox, Paul Stewart, Maggie Walter & Margaret Weir. 2010. Trauma, Loss and Grief for Aboriginal Children. Canberra: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Fishman, Joshua A. 1990. What Is Reversing Language Shift (RSL) and How Can It Succeed? In Durk Gorter, Jarich F. Hoekstra, Lammert G. Jansma and Jehannes Ytsma (eds.), Four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Minority Languages, (Vol. I). Clevedon and Bristol: Multilingual Matters.
Global Language Hotspots Living Tongues Institute for Endangered Languages. 2007. (http://www.swarthmore.edu/SocSci/langhotspots/index.html, accessed 16/02/ 2016)
Hallett, Darcy, Michael J. Chandler & Christopher E. Lalonde. 2007. Aboriginal Language Knowledge and Youth Suicide. Cognitive Development, 22 (3), 392-399.
Hanssens, Leonore. 2008. Clusters of Suicide. Aboriginal & Islander Health Worker Journal, 32 (2), 25.
Hanssens, Leonore. 2012. The Impact of Suicide Contagion and Intergenerational Segregation on Youth and Young Adults in Remote Indigenous Communities in Northern Territory, Australia. Paper presented at 3rd Australian Postvention Conference, Sydney.
Headspace: National Youth Mental Health Foundation. 2011. Mental Health and Mental Illness. In headspace (http://www.headspace.org.au/parents-and-carers/ find-information/mental-health-and-illness, accessed 03/05/2013)
Heinrich, Patrick. 2004. Language Planning and Language Ideol?ogy in the Ryūkyū Islands. Language Policy, 3 (2), 153-379.
Human Rights and Equal Opportunity Commission. 1997. Bringing Them Home: Report of the National Inquiry into the Separation of Aboriginal and Torres Strait Islander Children from Their Families. Canberra: Commonwealth of Australia.
Hunter, Ernest & Desley Harvey. 2002. Indigenous Suicide in Australia, New Zealand, Canada and the United States. Emergency Medicine, 14 (1), 14-23.
Indigenous Remote Communications Association. 2013. Language and Culture. (http://www.irca.net.au/about-irca/friends/sector/language-and-culture, accessed 01/11/2014).
Kickett-Tucker, Cheryl. 2009. Moorn (Black)? Djardak (White)? How come I dont fit in Mum?: Exploring the Racial Identity of Australian Aboriginal Children and Youth. Health Sociology Review, 18 (1), 119-136.
King, Malcolm, Alexandra Smith and Micheal Gracey. 2009. Indigenous Health Part 2: The Underlying Causes of the Health Gap. The Lancet, 374 (9683), 76-85.
Kirmayer, Lawrence J., Christopher Fletcher, Ellen Corin and Lucy Boothroyd. 1997. Inuit Concepts of Mental Health and Illness: An Ethnographic Study. Montreal, Canada: Culture and Mental Health Research Unit, Institute of Community and Family Psychiatry, Sir Mortimer B. Davis-Jewish General Hospital and the Division of Social and Transcultural Psychiatry, McGill University.
Manson, Spero M., James H. Shore and Joseph D. Bloom. 1985. The Depressive Experience in American Indian Communities: A Challenge for Psychiatric Theory and Diagnosis. In Arther Kleinman & Byron Good (eds.), Culture and Depression Studies in the Anthropology and Cross-Cultural Psychiatry of Affect and Disorder.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Marmion, Doug, Kazuko Obata and Jakelin Troy. 2014. Community, Identity, Wellbeing: The Report of the Second National Indigenous Languages Survey. Canberra: Australian Institute of Aboriginal and Torres Strait Islander Studies (AIATSIS).
Memmott, Paul, Rachael Stacy, Catherine Chambers and Catherine Keys. 2001. Violence in Indigenous Communities,
Report to Crime Prevention Branch of the Attorney-Generals
Department. Brisbane: University of Queensland.
National Aboriginal Health Strategy Working Party. 1989. The National Aboriginal Health Strategy [NAHS]. Canberra: National Aboriginal Health Strategy Working Party.
Phinney, Jean S. 1990. Ethnic Identity in Adolescents and Adults: Review of Research.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08 (3), 499-514.
Purdie, Nola, Pat Dudgeon and Roz E. Walker. 2010. Working Together: Aboriginal and Torres Strait Islander Mental Health and Wellbeing Principles and Practice. Canberra: Office of Aboriginal and Torres Strait Islander Health.
Rowley, Kevin G., Kevin ODea, Ian Anderson, Robyn McDermot and Karmananda Saraswati. 2008. Lower than Expected Morbidity and Mortality for an Australian Aboriginal Population: 10-year Follow-up in a Decentralised Community. The Medical Journal of Australia, 188: 283-287.
Schürmann, Clamor Wilhelm. 1844. A Vocabulary of the Parnkalla Language. Spoken by the Natives Inhabiting the Shores of Spencers Gulf. Adelaide: Government Printer.
Schurmann, Edwin A. 1987. Id Rather Dig Potatoes: Clamor Schurmann and the Aborigines of South Australia, 1838-1853. Adelaide: Lutheran Publishing House.
Social Health Reference Group. 2003. Consultation Paper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Aboriginal and Torres Strait Islander National Strategic Framework for Mental Health and Social and Emotional Well Being 2004-2009. Canberra: Commonwealth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Ageing.
Social Health Reference Group. 2004. National Strategic Framework for Aboriginal and Torres Strait Islander Peoples Mental Health and Social and Emotional Well Being 2004-2009. Canberra: Australian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Ageing.
Sutton, Peter. 2009. The Politics of Suffering: Indigenous Australia and the End of the Liberal Consensus. Melbourne: Melbourne University Press.
Swan, Pat & Benerley Raphael. 1995. Ways Forward: National Consultancy Report on Aboriginal and Torres Strait Islander Mental Health. Canberra: AGPS.
The Western Australia Aboriginal Child Health Survey. 2005. The Social and Emotional Wellbeing of Aboriginal Children and Young People 2005. Perth: Telethon Institute for Child Health Research.
Tighe, Joe & Kathy McKay. 2012. Alive and Kicking Goals!: Preliminary Findings from a Kimberley Suicide Prevention Program. Advances in Mental Health, 10 (3), 240-245.
Trewin, Dennis. 2006. National Aboriginal and Torres Strait Islander Health Survey, Australia, 2004-05. Canberra: ABS.
United Nations. 2009. State of the Worlds Indigenous Peoples.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Utsey, SO, MA Bolden, Y Lanier and OI Williams. 2007. Examining the Role of Culture-Specific Coping as a Predictor of Resilient Outcomes in African Americans from High-Risk Urban Communities. Journal of Black Psychology, 33: 75-93.
Van de Vijver, Fons & Ronald K. Hambleton. 1996. Translating Tests: Some Practical Guidelines. European Psychologist, 1: 89-99.
Vogt, DS, DW King and LA King. 2004. Focus Groups in Psychological Assessment: Enhancing Content Validity by Consulting Members of the Target Population. Psychological Assessment, 16: 231-243.
Wexler, Lisa Marin. 2006. Inupiat Youth Suicide and Culture Loss: Changing Community Conversations for Prevention. Social Science & Medicine, 63 (11), 2938-2948.
Wexler, Lisa Marin, Gloria DiFluvio & Tracey K. Burke. 2009. Resilience and Marginalized Youth: Making a Case for Personal and Collective Meaning-making as Part of Resilience Research in Public Health. Social Science & Medicine, 69 (4), 565-570.
Zubrick, Stephen R., S. Silburn, David Lawrence, Francis G. Mitrou, R. B. Dalby, Eve M. Blair et al. 2005. The Western Australian Aboriginal Child Health Survey: The Social and Emotional Wellbeing of Aboriginal Children and Young People. Perth: Curti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and Telethon Institute for Child Health Research.
Zuckermann, Ghil‘ad. 2009. Hybridity versus Revivability: Multiple Causation, Forms and Patterns. Journal of Language Contact, Varia, 2, 40-67.
Zuckermann, Ghil‘ad & Michael Walsh. 2011. Stop, Revive, Survive!: Lessons from the Hebrew Revival Applicable to the Reclamation, Maintenance and Empowerment of Aboriginal Languages and Cultures. Australian Journal of Linguistics, 31 (1), 111-127.
Zuckermann, Ghil‘ad & Paul Monaghan. 2012. Revival Linguistics and the New Media: Talknology in the Service of the Barngarla Language Reclamation. Paper presented at Foundation for Endangered Languages XVI Conference: Language Endangerment in the 21st Century: Globalisation, Technology & New Media, Auckland.
Zuckermann, Ghil‘ad, Shiori Shakuto-Neoh and Giovanni Matteo Quer. 2014. Native Tongue Title: Compensation for the Loss of Aboriginal Languages, Australian Aboriginal Studies, 1: 55-71.
責任編輯:姜 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