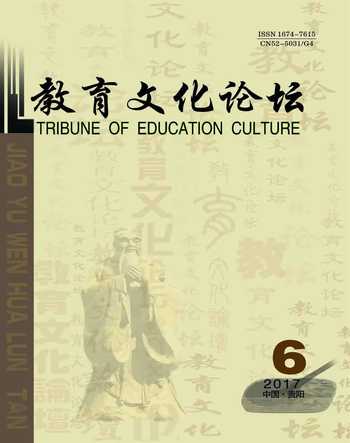從《苾園詩存》看李端棻追求的人格構建
曹正勇
摘要:李端棻是清末重臣,其思想對當時和后世都產生了重要影響。今天能見到的表現其思想的材料并不多,《苾園詩存》便是其中之一。文章以弗洛伊德的三重人格分析理論為指導,以《苾園詩存》中的詩歌為研究對象,看看李端棻所追求的“本我”、“自我”和“超我”統一于一身的人格。
關鍵詞:李端棻;本我;自我;超我
中圖分類號:G40-09;G529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4-7615(2017)06-0130-04
DOI:10.15958/j.cnki.jywhlt.2017.06.027
精神分析學說的創始人弗洛伊德在他的理論里,提出了“本我”、“自我”和“超我”的三重人格分析法。他認為,“本我”是原始的,天賦的無意識結構,處于意識的底部,是人的本能的體現,因而是人格中最耐人尋味而又神秘莫測的部分,“快樂”是其遵循的原則。“自我”來源于“本我”,是意識與潛意識之間的橋梁,同時也是“我”與外部聯系的橋梁,因而遵循著“現實”原則。而“超我”又來源于“自我”,是理想化了的“自我”,因此處于人格的最頂層,遵循著“理想或道德”原則。弗洛伊德同時強調,三者之間沒有明晰的界限,而是相互聯系,彼此共存。人,都是此三重人格的統一。之所以表現出差異,原因不是違背了三重人格理論,而是在不同的場合,為了不同的需要,就會選擇性地表現出三重人格中的某一種。
本文即用弗洛伊德的人格分析理論,從《苾園詩存》看看李端棻的人格建構。
李端棻所著《苾園詩存》 140余首,大部分寫于1898年被流放新疆之后。其中作品,有書寫流放的抑郁之情,有揭露黑暗現實,表達對封建王朝殺害維新志士的憤怒與不滿,有總結維新變法運動的得失,展現了變法改革的決心;有與親人的直抒胸臆;有對還鄉生活的描寫等等。
按照弗洛伊德的理論,李端棻免不了三重人格共附一身。但不同的是,面對世事滄桑,他雖有憤怒與不滿,但不是怨天尤人,而是用詩歌給我們展現了“本我”、“自我”和“超我”三重人格的交織與沖突,從而不僅造就了其詩歌魅力,更提升了其人格魅力。
一、本我:聽從內心的聲音
李端棻做人處事,不僅遵從外在的道德和理想,更聽從自己內心的聲音。面對戊戌維新變法,朝廷命官中,言新政者二品以上大臣一人而已。因此,他被擢升為禮部尚書。李端棻的言行,絕不是為了升官,而是出于一個中國人尤其是朝廷重臣的責任與擔當。他原本也可以趨炎附勢,力求自保,但他無法欺騙自己的心性和良心,于是,他不計后果地挺身而出,結果是被流放新疆,差點病死于甘州(今張掖)。
這種憂國憂民的心性,在《戊戌十二月朔日寄九弟秦州》一開端便表現了出來:“我本傷心人,迭遭傷心事。垂老遭愈奇,一遭成往事”。由此可以看出,他傷心的,絕非兒女私情,家庭瑣事,而是維新變法失敗后對國家和民族命運的擔憂。正如李端棻自己所言:“吾一生為人之道,得之吾叔;為學之道,得之吾舅”。從小在叔父李朝儀的身邊長大,耳濡目染叔父的為官和為人之道,深受影響,繼承了叔父心系百姓,為國為民的良好品德。在《在甘州病余自遣》中,因為身體有恙,寫出了“希望輪臺萬里長,休將白首戍遐荒”的詩句,但轉念便能自我安慰,“此日轉覺逍遙甚,自問何曾險阻嘗。老夫心情無冷暖,閑中歲月是羲皇。近來漸少還家夢,識破迷途即故鄉”。字里行間,體現的是作者心曠不羈的闊達。然而,這種胸襟,真正的源動力還在于他為天下蒼生請命的使命感和責任感。因此,既然都是愛國愛民,便能不分遠近,“識破迷途即故鄉”。
李端棻為官,盡管曾經位高權重,卻始終沒有丟失作為人的心性,一生堅守著人的本真。這一點,在《答甘郡諸茂才》中也有體現,“羅雀門多佳客至,集膳堂近圣人君。眷言芹采皆同類,何幸樗材不棄予……”。他不但沒有把自己曾經的輝煌作為炫耀的資本,反倒是對“諸茂才”心懷感恩之心。遠赴流放地的路上,他還能欣賞沿途風光。“始識雷霆皆雨露,要乘風雪看天山……”(《寓甘州示諸弟》),“數載飽看蔥嶺雪,一鞭歸踏隴頭云……”(《和文信國乩詩》),“思量往事真優孟,坐看浮云幻太虛”(《靜中偶成》)。除此之外,作者還寫了不少有關花的詩句,比如詩歌《白梅》、《紅梅》、《水仙花》、《瓶花》、《臬署觀荷》等。借寫花傳達對自然的傾心,聽從內心,綻放心性,不背意。
李端棻在官場能堅守做人的理想和道德,聽從內心,為國家民族之命運大膽進言,被流放新疆。但他又未能被現實所打到,能在詩歌里尋找到屬于自己的快樂。他的心性,對國對民的大愛,無法遮掩,真正是內化于心,外化于行,展現了心靈深處的“本我”。然而,作為接受儒家精神洗禮的人,他無法完全徹底地放下“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理想。所以,他又總是在無意識中展現“本我”的同時,又極力追求實現“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宋·張載 語)的“立功、立德、立言”的理想,擺脫“本我”的束縛而追求“自我”的實現。
二、自我:仕和隱的交織與沖突
弗洛伊德認為,“自我”來源于“本我”,是對“本我”的非潛意識沖動的控制與壓抑。雖如此,“本我”對“自我”有一種根源上的決定性,但同時“自我”又有一種向“本我”施加外界影響的傾向性,即促使現實原則取代快樂原則的傾向性。換句話說,人作為生命主體,所受影響不完全來自于“本我”,還有來自于“自我”,在“自我”中展現現實的影響,而現實又往往是與快樂相違背。因此,“本我”與“自我”常常處于矛盾與對立中。按照這一理論,《苾園詩存》里的詩歌就充分展現了仕(自我)與隱(本我)的糾結與沖突。
李端棻的進仕之路已經證明,在他的內心深處,不僅有對光宗耀祖的仕途追求,更有對天下蒼生的關切。他提倡教育,請推廣學校;向光緒帝舉薦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等維新志士,使新政得以推行;屢上封事,比如開懋勤殿,裁減冗員等,都是為建設一個強大的封建王朝,讓國家和百姓免遭外敵欺辱。盡管后來由于多種原因維新未能成功,但他的功績卻不容淡漠。可見李端棻的“仕”,不是為了求權,而是為服務天上蒼生尋找更好更高的平臺。
這種情懷,在遠赴新疆期間,依然時有流露。“幸予被遣為遷客,匹馬秋風出帝城”(《和文信國乩詩》)。字面上是遠離了皇帝,但文字背后,是對“帝城”的不舍。他不舍的,當是還沒成功的改革,而非手中的權力。在《杞憂》里,他寫道:“……但以苞苴權子母,那知恩澤被人民……時代至今成黑暗,昏昏點漆更粘膠”。那種因人民生活在水生火熱的黑暗現實中而又無能為力的痛苦,躍然于紙上,讀來不能不使人動容。在《有感》里,他寫道:“……四方多猛士,定可挽天河”。雖然已經遠離皇城,已是戴罪之人,但他堅信,有識之士仍然能夠同心協力,奮力推進維新改革,挽救封建王朝之大廈于將傾之際。在《國家思想》里,他寫道:“……奴隸心腸成習慣,國家責任互相推……”。身在高位,看到了國家人民需要之時,官僚們的無作為,置百姓國家于不顧后的憂心忡忡,同時也透露出一絲的無奈。他對無所作為的“恨”,在《黨禍》里表現得更直接,“幾見清流誤國家,權奸顛倒是非差。狹心但解酬恩怨,盲眼何曾識正邪……”。甚至在《傷老》里,他一方面感嘆虛度光陰,另一方面又鞭策自己奮力前行,實現人生理想。“……謹防歲月閑中過,磨煉精神病后多。縱使前途無影響,莫因垂老便蹉跎……”。
然而,李端棻的這種“仕”之心,卻深深地被流放所傷。離開帝都,戴罪流放,就如雄鷹關進鳥籠,無法展翅翱翔。他失去了他可以一展抱負的平臺。盡管在客觀上,李端棻從帝都前往荒涼的新疆,有些“小隱”的嫌疑,但他的詩歌又時常提醒我們,無論何處,他都極力安撫自己躁動的內心,讓它寧靜下來,把不幸當作難得的放松之旅,實現真正的“大隱”。于是,沿途的風光,眼中的各色花朵,都成為了他筆下描摹和贊美的對象。
但我們應該明白,作者總是借景抒情,托物言志,寫景是假,抒情是真。往往在字里行間,都蘊藏了作者的理想與抱負。他始終無法面對“仕”與“隱”的選擇,他總想盡力分清二者的界限。然而,越是掙扎,越是渾濁,始終處于“仕”與“隱”的糾結與沖突中。于是,他不得不轉向“超我”的自構。
三、超我:儒和道的統一
李端棻生于官宦之家,長輩的教育,家風的嚴謹,加上圣人之學的影響,促使他形成了心納萬物,為天下憂的胸襟。《苾園詩存》里,大量而深刻地反映了他骨子里儒家“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價值觀。《有感用書車魚韻》中寫道:“薦引昔年空抗疏,進賢深愧直哉魚”。雖然已近古稀之年,但他仍然惦記著為國家引薦人才賢士的重任,聯系到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等因其推薦得以重用而最終因為變法失敗或血灑菜市口或背井離鄉的下場,不免陷入深深的自責之中。這種自責,既是因被舉薦之人的悲劇結局,更是因光緒皇帝的宏圖大業的夭折。
1901年,年近古稀的李端棻赦歸鄉里。由于長時間患病,李端棻早已年邁體微。但他并未因年老多病和殘酷的政治打擊而消沉。相反,他為家鄉風氣的開通盡心盡力,成為當時貴州維新人士公認的一面變法旗幟。1902年,李端棻受聘主講貴州經世學堂,所講內容,開了貴州學子之眼界。同年。與于德楷、樂嘉澡等人創辦了貴州第一所公立師范學堂(后來的貴陽市師范學校),開貴州師范教育的先河。1905年,與人共同創辦了貴州通省公立中學堂(后來的貴陽一中)。1906年,發起成立了貴州教育總會籌備會,對推動近代貴州教育的發展具有積極的作用。
從以上歸鄉后的所作所為可見,李端棻為官與否,對他心系天下的心性和品德沒有任何影響。因為在他已經沒有政治地位和平臺的條件下,依然在為家鄉的發展,國家的富強盡心盡職。
正因為他有這樣的理想和抱負,便能始終初心不改,不甘墮落,在不順之境中磨練和強大自己的內心。《讀陶淵明集》中寫道:“布帛文章清且真,先生寧是一詩人。庶乎屢空自耕讀,藐焉寡儔無喜瞋。暫現宰官終處士,深防異代作遺民。山民素裕經綸志,惜不逢時但隱淪”。寫出了作者內心對陶淵明歸隱山林的道家生活方式的追求與向往。但事實上,所謂的歸隱,只是為自己量身定制的自我麻痹的藥方而已,他的心,始終追隨著天下蒼生。
道家人格強調生命的個性體驗,反對生命在現實中的異化,追求與天地共往來的自由生活。李端棻一定懂得這一精髓,便寄情于花草,覓得心靈的平靜。“好山多被雉垣遮,欲去尋花路轉暇”(《菊山》),“只惜籬邊新種菊,連朝冒雨損芳華”(《瓶花》),“休道玉顏蕭索甚,愿經霜雪更增輝”(《詠梅》)等等。然而,李端棻終歸未能在儒道的斗爭里堅定地選擇某一家。換句話說,他的身上,既有儒家的責任擔當,又有道家的自我安慰,二者和諧統一,成為李端棻“超我”的最好表達。
從“本我”到“自我”,再到“超我”,既有各自的獨白,又有三者的合音。但李端棻作為儒家知識分子的典型代表,在國家、民族和人民風雨飄搖時代環境里,他無法真正做到三選一而終老,總是在不斷地斗爭和努力,但永遠不變的是,為天下蒼生的心始終如一。但有一點我們必須清楚,由于時代的局限性,他所倡導的維新變法,在本質上還是為了維護和鞏固即將結束的封建統治。當然,從他后來閱讀梁啟超寄給他的《清議報》后所作的詩歌來看,他不僅對維新變法的失敗進行了反思,還逐漸接受了資產階級民主思想。比如《政治思想》寫道:“天地區分五大洲,一人豈得制地球。國家公產非私產,政策群謀勝獨謀。君為安民方有事,臣因佐治始宣流。同胞若識平權義,高枕無憂樂自由”,《國家思想》里寫道:“君不堪尊民不卑,千年壓制少人知。奴隸心腸成習慣,國家責任互相推。峽經力士終能剖,山有愚公定可移。緬昔宣尼垂至教,當仁原不讓于師”。由此可見,不管他愿不愿意,他所追求的人格建構,就是“本我”、“自我”和“超我”統一。
其實,李端棻研究的現有成果,幾乎都局限于教育思想研究和他在維新變法中的作用這兩大方面。筆者認為,他的教育思想固然很重要,也可以說是他貢獻最大的領域。但無論怎樣,他都必須首先有儒家文化構建的儒家人格作為基礎和前提,同時還必須有與時俱進的改革精神作為補充。這兩種精神,是推動他走上歷史舞臺的兩大動力,這便是李端棻思想的“變”與“不變”。
如前所述,盡管《苾園詩存》中的詩歌大都為流放新疆之后所作,但我們透過它,依然能夠窺見一個血肉與靈魂無比豐滿的李端棻。因為這些詩歌,我們看到了一個始終走在斗爭路上的李端棻,一個真實的李端棻。
參考文獻:
[1]貴陽市志辦.貴陽五家詩鈔[M].貴陽:貴州教育出版社,1995.
[2]秋陽.李端棻傳[M].貴陽:貴州民族出版社,2000.
[3]鐘家鼎.李端棻評傳[M].海口:海南出版社,2004.
[4]黃江玲.“詩界革命”的宿將——評李端棻《苾園詩存》[J].貴州文史叢刊,2010,(2).
[5]張建新.從《苾園詩存》看李端棻思想的轉變[J].福建論壇(社科教育版),2008,(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