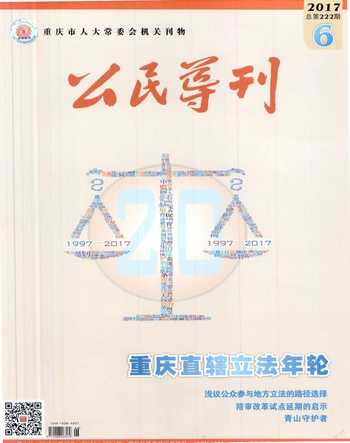青山守護者
方娟

傍晚,迎著夕陽,孫清維駕車載著記者奔馳在云陽縣濱江公路上。車窗外的長江猶如玉帶,纏繞著兩岸青山,仿佛一幀幀絕美的水墨畫從眼前掠過。
“你相信嗎?1958年前,長江云陽段兩岸全是禿山,這片長68公里,面積超過12萬畝的長江防護林是靠人一棵棵種出來的。”孫清維告訴記者。
命運
孫清維,云陽縣長江林場副場長。上世紀90年代轉業回鄉后就一直與林業打交道,如今算來已20多個年頭。
1992年轉業后,孫清維被分配到了當時的云陽縣江南林場當伐木工。
“有關系的戰友都分到供銷社、糧站、養路隊,林場是最差的去處。”那時,孫清維的抵觸情緒很大,天天和家人吵架,不愿去。
孫清維的父親是老林場工人,1958年進場,一干就是37年,直到退休。希望兒子繼承自己“衣缽”的老父親悄悄對他說,自己曾找算命先生測過,他只有和樹打交道,才能保一世平安。
最終,孫清維選擇了服從命運。
護林工作既艱苦又單調。工人每次進山,一待就是30、40天。
“我們3、4個人負責一片山頭,砍小留大、砍密留稀,為樹木更好生長騰出空間。”孫清維回憶,每次上山都要背幾大包,包里裝著大米、鍋碗、咸菜和塑膠布,并且吃睡都在野地。
“幾塊石頭支口鍋,林下撿柴來生火,大米就著咸菜吞,下雨扯起棚布睡”,是當時護林工人生活的真實寫照。
與外面的世界相比,林場里的工作和生活簡單而純粹。“每天要砍200—500斤撫育的樹林并負責下山集中堆放,流一身大汗,晚上倒頭就睡,沉靜安寧。進山時,我還會帶幾本專業書,坐在林間讀書的感覺也無比美妙。”
在國有林場工作,不但辛苦,待遇也差。孫清維回憶,當時林場工人的人頭經費,40%靠財政撥款,60%需要自籌。“我當時的工資標準是每月137元,其中82塊錢要靠砍樹、賣樹來彌補,按當時一毛錢一斤的價格計算,我每月最少要砍800斤樹。”
越是艱苦的環境,越磨練心性毅力。從護林員到辦公室文書到工會主席再到副場長,孫清維從基層做起,不但走上了領導崗位,還考取了副高職稱,成為當地的林木專家。
多年以后,孫清維的父親才說出實情,當年他根本沒替兒子算命,說那番話,只是為了讓兒子能安心留在林場工作。
“我父親進場時,林場的林木覆蓋面積為0;我進場時,林場的林木覆蓋面積6萬畝,而今這個數字已經翻了倍。”望著兩岸青山,孫清維自豪溢滿心頭。他不禁要感謝父親二十多年前那個善意的謊言,感謝命運讓他們成為這片青山的締造者和守護神。
戰斗
三峽大壩開工建設后,為防止水土流失,重慶通過石漠化治理、退耕還林,使長江兩岸的森林覆蓋面積大幅增長。到2012年,庫區大規模造林基本完成,林場的主要工作也轉向了管護。
在孫清維的帶領下,記者來到位于長江邊半山腰的三壩管護站。出來迎接記者的是管護站站長盧海軍。48歲的他,工齡比孫清維還多一年。
說一口純正普通話的盧海軍成長在河北,轉業后選擇回老家云陽。“與北方空曠遼闊的壯美相比,我更喜歡這兩岸青山一江碧水的秀美。”
護林比造林難。這一點,盧海軍最懂。
從上世紀80年代中期起,云陽縣長江防護林開始發生局部柏木葉蜂危害。2004年以來,12萬畝長江防護林連年暴發蟲災,到2010年,蟲害面積已達到8萬畝,涉及長江林場5個管護站林區。
三壩管護站的轄區屬于重災區。當時,盧海軍等護林員幾乎天天守在山上,查病樹、作統計、找對策、想辦法。“看著病害蔓延,我們卻束手無策,真是剜心的痛。后來,在專家的建議下,我們通過輕型直升機施藥,最終才控制住了蟲害。”
繼柏木葉蜂后,近年來,長江防護林又受到松材線蟲侵蝕。“松材線蟲對于松樹就像癌癥對于人類,是不治之癥,被感染后最快40多天就會枯死,只能發現一棵砍一棵。”
那段時間,盧海軍帶領管護站工人每天6點上山,逐一排查、尋找病樹,并挨棵砍伐、剝皮、灌藥、套袋、掩埋,一天連續工作13、14個小時。“累得腰都直不起來。”管護站的小龍告訴記者,為防治松材線蟲,他們站長曾2個月不出山,吃住在農民家。
又到了該出發的時間,盧海軍手握伐木刀帶領站里的護林員,準備向山里進發。他棱角分明的臉上寫滿對勝利的渴望。
其實,病蟲害防治對于護林人來說就是一場沒有硝煙的戰斗。他們像一群戰士一直守衛著自己的陣地,守衛著這一江碧水、兩岸青山。
傳承
龍洋,1986年出生,西南交大本科畢業,三壩管護站最年輕的護林員。他是2015年通過公招考入長江林場的,現在已經快兩年了。
國有林場是財政全額拔款的事業單位,與二十年前相比,護林工人的待遇已經有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小龍告訴記者,他每月能拿到近3000元的工資。
由于工作的特殊性,下班后,管護站的7名護林員只能集體住在站上,輪休時才能回家。因為沒有配炊事員,他們必須輪流買菜、做飯,每人每頓的伙食標準是10元。
“晚上時間有點難打發,年輕人都喜歡夜生活,看個電影、K個歌什么的,而在這里,只能看電視或玩撲克牌。”小龍說。
“今年站里通了網絡,吃完晚飯就看不到人,一直躲在寢室玩手機。”盧海軍在旁笑著接話。
小龍每天的工作很單調,在山路上來回巡視,查看火災隱患,制止盜伐行為。問他苦不苦,他搓手靦腆地回答:“還好,就是路走得多點,而且節假日回不了家。”記步器顯示他每天在山里行走步數都在30000步以上,折算下來約有十多公里路程。
“龍洋報考那年,林場只招1人,而報考人數是43人。”孫清維嘆了口氣,別看考的人多,但真正愿意長期干的卻寥寥無幾,前幾個年輕人一、兩年就走了,“林場只是個跳板而已。”
看龍洋一直低頭玩手機,孫清維用手指戳了戳他的背,“有時間多看點專業書,趕快把中級職稱拿到,今后,站長、場長還等著你接班咧。”
對于孫清維的期冀,小龍默不作聲,整個房間一片靜默。
臨走前,孫清維還告訴記者,龍洋的妹妹今年也考入了林場。
對于孫清維、盧海軍等老一輩護林人遞過來的“接力棒”,或許這對兄妹已經給出了答案。
編后語: 直轄20周年來,重慶經濟社會事業、生態環境保護都有著長足的發展,魔幻的輕軌、青山綠水的庫區都是其中典型的代表,與過去記憶的境況早已不可同日而語。
從當初到江對岸還需要坐船,到現在上天入地的輕軌;從當初長江云陽段兩岸全是禿山,到目前長68公里、面積超過12萬畝的長江防護林,這座城市的每一個人都在為她的美而努力著。
無論是人大代表,還是普通人,即便是最微小的付出,都值得書寫和記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