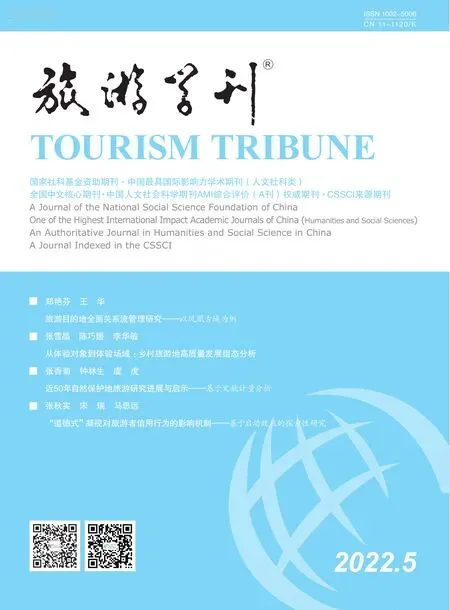跨境購物中的“馬太效應”:制度信任對產品外部屬性的調節作用研究
雷超++衛海英
[摘 要]喜歡購買信任產品是中國內地游客跨境購物的一大特點,其根源主要在于國內信任產品行業危機,這場危機的重要原因就是制度信任的缺失。研究認為,在跨境購買信任產品的情景下,制度信任會通過調節產品外部屬性對購物意愿的作用,從而在境內外的老字號與初創品牌之間形成一種強者愈強,弱者愈弱的“馬太效應”。通過兩個情景實驗,探討境內外不同的制度信任對品牌歷史、用戶規模和參考群體這3個產品外部屬性的調節作用。結果表明:(1)制度信任會調節品牌歷史和用戶規模對購買意愿的影響,也會調節品牌歷史和參考群體對購買意愿的影響。(2)對于老字號而言,制度信任會增強消費者的從眾效應和外群體從眾效應,從而對老字號產生“錦上添花”的作用。(3)對于初創品牌而言,制度信任會弱化消費者的從眾效應和外群體從眾效應,從而對初創品牌產生“雪上加霜”的作用。
[關鍵詞]跨境購物;品牌歷史;參考群體;從眾;信任商品
[中圖分類號]F5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5006(2017)05-0036-10
Doi: 10.3969/j.issn.1002-5006.2017.05.009
引言
自2012年中國開始成為世界最大出境旅游國,我國游客在日本、美國、韓國和中國香港等國家(地區)均已成為人均消費最高的境外消費者。購物開支大是中國內地游客跨境消費的一大特點。以中國香港為例,2015年來自中國內地的過夜旅客購物占總消費的比例高達68.8%1。喜歡購買信任商品(credence goods)是另一大特點。2014—2015年,在香港,中國內地不過夜旅客購買率前三類商品均為:小食/糖果、美容及護膚品、個人護理用品2。2015年中國游客在日本購買率前三位為:化妝品/香水、糖果點心、藥品/營養保健品3。其中,食品、化妝品、護膚品、藥品、保健品和營養品等均為消費者即使在消費中和消費后都難以感知和評價質量高低,通常只能給予信任的信任產品4。研究表明,購買地這一因素對于消費者購買搜索產品(search goods)和體驗產品(experience goods)的決策影響十分有限,消費者并沒有對粵港兩地市場產生明顯偏好[1]。為何內地中國人喜歡跨境購買信任產品呢?這與中國信任產品行業的危機有重要關系。這場危機是消費者對政府監管和信任產品行業不信任而產生的“傳染效應”和“競爭效應”所導致。信任產品的質量保證高度依賴于政府的監管,一旦公眾對政府監管的效力沒有信心,一家企業的丑聞會被放大成整個行業的普遍性問題從而對整個行業產生不信任,造成傳染效應;傳染效應結果可能會導致國內市場需求轉向采用外國原料和在外國完成全部生產工序的原裝進口商品,甚至是消費者直接到海外購買商品,即需求從本土市場轉向海外市場的“競爭效應”[4] 。這就導致該類商品的需求和消費在國內被壓抑了,而在境外卻得以“井噴”。
這種對政府監管和行業的不信任是通過一種什么機制影響消費者的跨境購買決策呢?有學者認為,信任產品行業的傳染效應乃至中國市場轉型期的信任危機,本質上都是制度信任的缺失[4-5]。梳理文獻發現,制度信任的研究主要聚焦政治、社會、行業和企業層面的問題,較少關注消費者層面的問題。筆者認為,這種對國內市場的制度信任缺失加劇了對本地信任產品外部屬性的不信任,從而抑制了購買意愿;同時,對境外市場的制度信任加深了對境外信任產品外部屬性的信任,從而放大了購買意愿。基于此觀點,本研究結合線索利用理論(cue utility theory)旨在探討跨境購物情境下,“制度信任”對產品外部屬性的調節作用,以探尋中國消費者境外“爆買”信任產品的催化劑。時下,中國政府正設法將經濟增長模式由以往的投資拉動型轉變為消費拉動型,也在各地推出了自貿區來鼓勵人們境內消費以促使消費回流。所以,本研究不但擴充了產品外部屬性的理論外延,而且豐富了制度信任的相關文獻,推進了旅游消費這一領域的研究深度,還為政府和企業的實踐和決策提供了重要的指導依據。
1 理論背景與研究假設
消費者會利用產品本身的內部和外部屬性來判斷產品的質量[6]。但當商品內部屬性缺失的情況下,人們會通過產品的外部屬性(品牌、價格和原產地等)來判斷質量[7]。現實是,包裝已隔絕了大部分商品的內部屬性,同時競爭已使商品的外部屬性日益同質化,一些獨特的外部屬性正越來越被商家和消費者所重視,如品牌成立的時間、用戶規模和參考群體。而這三個外部屬性往往是跨境消費者處于陌生環境時最容易獲取的線索,因為許多企業喜歡在其包裝、宣傳資料和大門上注明“成立于某年”以標明其為歷史悠久的老字號,而店鋪內外眾多等候和消費的人潮同樣具有很強的吸引力,如果這些消費群體是本地顧客居多,則其參考意義就更為顯著。所以本研究將探討境內外不同的制度信任對品牌歷史、用戶規模和參考群體這三個產品外部屬性的調節作用。
1.1 品牌歷史與購買意愿
中國企業在初創期死亡率偏高,是一個不爭的事實[8]。如何“基業長青”成為“長壽企業”一直以來是管理學界戰略領域饒有興趣的話題,吸引了很多管理大師,如彼得·德魯克和吉姆·柯林斯等從組織內部尋找企業長壽的秘密。然而在組織外部,“品牌歷史對消費者行為的影響”這一主題仍存在大量的研究機會。悠久的歷史不但可以為品牌帶來正統性和社會影響力,還可以增加消費者的偏好[9-10]。作為一個經驗線索,企業壽命可以確保企業能夠提供可靠的和高效的服務[11]。因為歷史悠久的組織有足夠長的歷史記錄供消費者去預測其未來的質量表現,所以企業成立的時間可以有效降低消費者的感知風險[12],如人們通常認為,品牌歷史對于評價一個葡萄酒品牌的優劣是非常重要的[13]。王靜一實證發現,品牌的長壽性對形成消費者的老品牌購買意向有顯著的正向影響,且這一正向關系主要是通過品牌信任的感知能力而不是感知誠實友善發揮作用[14]。不僅如此,悠久的品牌歷史還可以提升家庭中代際吸引力(intergenerational appeal),進而提升品牌形象和消費者購買意愿[15]。綜上,品牌歷史對消費者購買意愿的主效應是清楚的,但多線索情況下的交互效應研究則仍有待完善,如初創品牌在何種情境下方可獲得消費者青睞呢?后者也更接近現實。
1.2 用戶規模與購買意愿
這兩者之間的關系往往可以用從眾效應去描述。從眾效應是一種人類社會所普遍存在的現象,其本質是模仿多數人的行為或決策。當商品的質量難以判斷時,人際的和非市場的因素往往在決策和信息獲取中發揮關鍵作用[16]。對于質量難料的信任商品(如金融服務和大學教育),消費者往往憑借“用戶規模”和“組織歷史”來選擇,用戶規模和數量不但表明了其受歡迎的程度,而且還約束了企業不忠行為,因為“從眾行為”的反作用將會是災難性的;同樣,組織在市場上的歷史越悠久,用戶使用其商品后的價值越容易被體現,如各大高校的那些明星校友[17]。一般而言,風險性和模糊性越強,市場環境透明度越低,群體內部一致性越高,出現從眾行為的可能性則越大[18]。劉世雄和陳孟燃都認為,“從眾消費”是集體主義文化的我國所普遍存在的一種典型消費行為[19-20]。從2011年3月的“食鹽搶購風波”到2013年3月香港的“奶粉限制出境令風波”也可見一斑,其程度似乎明顯高于歐美等成熟市場上的消費者。根據社會學和心理學的觀點可以推測,商品信息越少、感知風險越大,市場環境越不透明,以及集體主義的傳統文化三者疊加就更容易在我國信任商品的消費中出現從眾行為。現實中的跨境購買信任商品的浪潮正印證了這一推測。而且,老字號本身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和號召力,加之“用戶規模”的從眾效應,便會產生一種影響更為顯著的“老字號從眾效應”。如彭惠和宋倩倩就發現,消費者的從眾購買行為導致C2C市場上歷史銷量高的店鋪能獲得更多的交易機會,即對于經營時間長久的店鋪而言,歷史銷量對消費者選擇店鋪的決策有顯著正向影響[21]。
1.3 參考群體與購買意愿
自我分類理論(self-categorization theory)指出,人都有把其他的人分成不同級別的傾向,在這個分組過程中,我們會自動地把一些人視為“圈內人”和“圈外人”。同時,認同理論(identification theory)認為,我們不單會把身邊的人分成圈內人和圈外人,也同時對圈內的“自己人”產生很強的認同。如消費者常常基于品牌的群體關聯(group association),即“參考群體”做出購買決策。有學者研究了群體類型對自我-品牌聯結的影響,其研究結果表明,當品牌形象與內群體匹配(關聯)時,或者當品牌形象與外群體不匹配(不關聯)時,消費者的自我-品牌聯結較強[22]。周學春和張曉娟則細化了參考群體,探索了群體地位和群體獨特性的影響[23]。從既有中外文獻看來,雖然結論稍有不同,有一點是相同的,即消費者會遵循與己有關聯的人的行為和建議,從而產生一種“內群體從眾(in-group conformity)”效應[24]。
然而在跨境購物情境下,相對中國內地消費者而言,境外發達地區消費者被認為掌握更多的信息,成為一種判斷商品質量的外部線索,跟隨他們的選擇可以降低感知風險,所以這是一種“外群體從眾(out-group conformity)”效應。當下頻頻曝光的大陸游客不文明行為和挨宰事件就使得中國人在境外消費存在刻意避開“內地中國人”的心態,這種消費心理正好與“外群體從眾效應”不謀而合。根據“攀附”心理理論,當特定對象或群體獲得成功或表現卓越時,個體會樂意去建立、維持和宣傳他們與該對象或群體的關系,以強化或提升他們的社會形象,這種行為表現,被稱為“分享榮譽” [25]。而當特定對象或群體不幸失敗或表現不理想時,個體則會傾向于減少或盡量避免與該對象或群體發生關系,以保護他們的社會形象,這種行為表現,被稱為“防止抹黑”[26]。據此,假設如下:
H1:參考群體會影響消費者的購買意愿,即參考群體為外群體(境外發達地區消費者)時,中國消費者的購買意愿大于參考群體為內群體(內地消費者)時的購買意愿。
1.4 制度信任的調節作用
社會學領域人們大多沿襲盧曼的社會系統理論將信任區別為人際信任(interpersonal trust)與系統信任(system trust)兩大模式[5]。脫出國家-社會領域,一些學者在廣義上將在一切發生在社會層面而非個體層面的信任統稱為社會信任,并在系統信任的內涵里另辟了制度信任,表示人對政策、制度等規范體系所持有的信任[27]。張維迎和柯榮住指出,中國大陸普遍和嚴重的低信任已經不僅僅是效率的高低問題,而是從根本上威脅市場和交易的存在[28]。接連曝光的食品丑聞極大地增加了中國人對食品安全的擔憂,也減少了人們對食品質量的信心 [29],這又導致某些食品的需求銳減,如嬰幼兒奶粉 [30]。王永欽等認為,中國信任品行業的“傳染效應”在本質上是對監管制度缺乏信心的表現,因而可以稱作制度效應[4]。其實,中國市場轉型期的信任危機實質是普遍主義取向的社會本位-制度信任模式的缺失[5]。
那么,在跨境購物情境下,境外制度信任對購買意愿的影響到底有多大呢?2008 年的毒奶粉事件發生后,從內地父母們跨境搶購奶粉的現象可以看出,在一個市場內,當價格、品牌和質量保證這些判斷產品質量的外部屬性均失效時,購買地市場就成為影響消費者購買決策的重要因素 [1]。根據線索利用理論,任何一點額外的信息都可以用來降低風險,故制度信任度高的境外發達地區已被中國內地消費者視為一個非常關鍵的外部線索影響著商品的購買決策。有學者研究了跨境購買荷蘭金融服務的德國人發現,國貨意識(consumer ethnocentrism)會負面影響消費者對外國產品和服務的評價;同時,對外國行業正面的信心會增加消費者的滿意度、信任度、忠誠度和感知價值;更重要的是,其正面的影響超過了國貨意識對滿意度和感知價值所產生的負面影響[31]。這就表明對境外行業的信任不但會正面影響購買意愿,還會抵消甚至超越國貨意識對購買意愿的負作用。所以,在跨境購物的情境下,目的地的市場環境越規范、越成熟、負面事件越少,消費者的感知風險就越小,制度信任就越高。
文獻表明,用戶規模大的老字號可以產生“從眾效應”[21]。筆者認為,高制度信任不僅會強化這一效應,而且還會強化“外群體從眾效應”,理由如下:消費者處于不同的制度信任環境中容易受到暈輪效應(halo effect)和傳染效應的作用,他們會將這種制度信任/不信任擴散并傳染到日常幾乎所有的消費和決策之中,他們不擔心/擔心會購買到假冒偽劣的商品,相信/不相信大部分商家是誠信經營的。由此,對于老字號而言,制度信任度高的境外目的地會賦予它們更強的正宗性和真實性,內地消費者會認為用戶規模和參考群體為外群體的可信度也更大,所以更容易出現“從眾效應”和“外群體從眾效應”。反之,在制度信任度低的中國內地,對于老字號而言,并不太可能出現“從眾效應”和“外群體從眾效應”。因為,我國大量的老字號陸續老化甚至消逝[32],它們漸漸被消費者所遺忘,加之低市場信任對老字號正宗性和真實性的負面影響,所以內地消費者的購買意愿并不會由于用戶規模大和參考群體為外群體而增強。
對于初創品牌而言,筆者認為低制度信任不僅會強化消費者的“從眾行為”,還會強化消費者的“外群體從眾行為”,理由如下:文獻表明,對于質量難料的信任商品,消費者往往憑借“用戶規模”和“組織歷史”來選擇[15]。而初創品牌缺少“組織歷史”這一線索,所以消費者只好憑借“用戶規模”和(或)“參考群體”決策。加之在缺少制度信任的中國內地,產品的外部線索(如價格和知名度)模糊,線索失真和信息缺乏正是從眾行為產生的沃土,所以“用戶規模”和(或)“外群體”(境外消費者被認為掌握更新和更真實的信息)會導致更強的購買意愿,如小米手機的供不應求(用戶規模大的表現)和大疆無人機植入美劇成功闖入好萊塢和迅速占領全國市場(外群體喜歡);反之,制度信任度高的境外目的地,對于初創品牌而言,出現“從眾效應”和“外群體從眾效應”的可能性低。因為,雖然初創品牌缺少“組織歷史”這一線索,但高制度信任讓消費者不擔心會購買到假冒偽劣的商品,產品的外部線索和質量也值得信任,所以從眾行為缺少土壤,消費者的購買意愿也并不會由于用戶規模大和參考群體為外群體而增強。
因此,本文認為在跨境購買信任產品情景下,制度信任、品牌歷史、用戶規模(或參考群體)之間存在三者交互作用。并且高低兩種制度信任的調節作用大小和方向存在較大差別。對此,我們將分兩個研究展開驗證(圖1)。具體而言,對于老字號而言,高制度信任會強化用戶規模(或外群體)對購買意愿的正向影響,低制度信任則會弱化用戶規模(或外群體)對購買意愿的正向影響;對于初創品牌而言,低制度信任也會強化用戶規模(或外群體)對購買意愿的正向影響,高制度信任則會弱化用戶規模(或外群體)對購買意愿的正向影響。假設如下:
H2:制度信任會調節品牌歷史和用戶規模對購買意愿的影響,即目的地、用戶規模和品牌歷史三者會對購買意愿產生交互作用。
H2a:對于老字號而言,制度信任會增強消費者的從眾效應。具體而言,在高制度信任目的地時,消費者對用戶規模大的品牌購買意愿明顯高于用戶規模小的品牌;但在低制度信任的內地時,用戶規模與消費者的購買意愿之間沒有顯著關系。
H2b:對于初創品牌而言,制度信任會弱化消費者的從眾效應。具體而言,在低制度信任的內地時,消費者對用戶規模大的品牌購買意愿明顯高于用戶規模小的品牌;但在高制度信任目的地時,用戶規模與消費者的購買意愿之間沒有顯著關系。
H3:制度信任會調節品牌歷史和參考群體對購買意愿的影響,即目的地、品牌歷史和參考群體三者會對購買意愿發生交互作用。
H3a:對于老字號而言,制度信任會增強外參考群體從眾效應。具體而言,在高制度信任目的地時,消費者對外群體喜歡的品牌購買意愿明顯高于內群體喜歡的品牌;但在低制度信任的內地時,參考群體與消費者的購買意愿之間沒有顯著關系。
H3b:對于初創品牌而言,制度信任會弱化外參考群體從眾效應。具體而言,在低制度信任的內地時,消費者對外群體喜歡的品牌購買意愿明顯高于內群體喜歡的品牌;但在高制度信任目的地時,參考群體與消費者的購買意愿之間沒有顯著關系。
2 研究一:制度信任對品牌歷史和用戶規模的調節作用
2.1 方法
為了實現本研究一的目的,我們選用信任產品——嬰幼兒配方奶粉作為刺激物,中國香港作為境外目的地代表,構建了一個2×2×2組間情境實驗,即目的地(中國內地VS.中國香港)×品牌歷史(歷史悠久VS.初創)×用戶規模(很大VS.很小)來檢驗假設。根據這3個自變量設計成8種各不相同的調查問卷。為了剔除產品品牌和購物商店品牌名稱對購買意愿的影響,設計成如下情景:“您打算購買一罐嬰幼兒奶粉,假如是在香港/廣東省內一家您經常光顧的商店里有一罐品牌歷史悠久/品牌剛創立不久且用戶規模很大/很小的嬰幼兒奶粉。請選擇您對下面這些表述的認同程度”。因變量購買意愿的測量量表參考了Baker 等的量表[33],進行了小幅修改后問項定為:“我會考慮購買這個產品”“我愿意購買這個產品”“我愿意推薦我的家人或親戚購買這個產品”。信度分析表明該量表具有較高信度,Cronbachs α值為0.96。所有的問項均采用Likert 7級量表,1~7 表示從“完全不同意”到“完全同意”。
采用滾雪球抽樣法,在廣州一所開辦MBA課程的高校內進行,3個年級隨機選取3個在職MBA班級,在課堂上每人派發1個問卷袋(每袋含8份各不相同的問卷),共發放95個問卷袋760份問卷。聲明讓其自己隨機填寫一份,然后回工作單位尋找與其收入、職位和/或學歷相仿的同事隨機填寫另外7份問卷。兩周之后收回472份問卷,剔除90份有重要項目缺失的問卷,實得有效問卷382份,8組分布較為平均(最多為50份,最少的為45份)。其中女性占52.9%,26~40歲占83%,這也基本符合2015年訪港不過夜內地旅客的基本特征:女性占58%,平均年齡35.8歲1。
2.2 操縱檢驗
鑒于制度信任對于普通消費者較為晦澀,筆者將從“社會信任”和“市場信任”兩個方面來測量“制度信任”。目前中國社會的信任危機是制度信任模式的缺失,而不是其他[5]。同樣,監管制度的不力和公眾對監管制度的不信任是中國信任產品行業危機的重要原因[4]。所以,在當下市場轉型期的中國社會,社會和市場的信任危機都是一種制度信任危機。本研究借鑒了王俊秀和楊宜音的社會信任量表[35],測量了中國內地和中國香港兩地的社會信任和市場上的品牌信任:“我對中國內地社會非常信任”“ 我對香港社會非常信任”“我對中國內地市場上的品牌非常信任”“我對香港市場上的品牌非常信任”。操縱檢驗表明,人們對香港的社會信任顯著高于對中國內地的社會信任(M香港=4.51, M內地=3.28, M香港-M內地=1.23, df=379, t =12.77, p<0.001);對香港市場上的品牌信任也顯著高于對內地市場上的品牌信任(M香港=4.73, M內地=3.34, M香港-M內地=1.39, df=377,t =17.09, p<0.001),操縱理想。這也與王俊秀和楊宜音的結果相呼應——我國社會信任總體狀況不理想,社會信任總體為“不信任”水平[34]。
2.3 分析和結果
采用SPSS軟件進行方差分析,數據結果表明,目的地(F(1, 373)=22.25, p<0.001)、用戶規模(F(1, 373)=24.99, p<0.001)和品牌歷史(F(1, 373)=111.13, p<0.001) 均對購買意愿產生顯著的主效應,即對于信任商品,中國消費者更愿意購買用戶規模大的商品,也更愿意購買品牌歷史悠久的商品;相比在內地,他們更愿意在制度信任度更高的香港購買此類商品。
目的地、用戶規模和品牌歷史三者之間的交互作用顯著(F(1, 373)=6.73, p<0.05),H2成立,交互作用如圖2所示。經分析發現,對于老字號而言,在高制度信任的香港,用戶規模對購買意愿影響顯著(M用戶規模大=5.41, M用戶規模小=4.49; F(1,96)=10.62, p<0.01),但在低制度信任的內地,用戶規模對購買意愿的影響不顯著(M用戶規模大=4.37, M用戶規模小=4.14; F(1,92)=0.47,p=0.49),H2a得證。但對于初創品牌而言,在制度信任高的香港,用戶規模對購買意愿影響不顯著(M用戶規模大=3.61, M用戶規模小=3.05; F(1,93)=2.75, p=0.101 );但在制度信任低的內地,用戶規模對購買意愿的影響顯著(M用戶規模大=3.27, M用戶規模小=1.77; F(1,96)=26.68, p<0.001),H2b得證。
2.4 附加分析
研究一的分析仍存在不足之處:高信任目的地——香港可能啟動被試的旅游心境(travelling mindset),一般情況下,旅游心境會提升個體購買意愿。因此,為了排除這種可能性,我們在研究一結果基礎上進行了補充分析。
本分析僅局限于中國消費者在內地購買的情境,將被試對中國內地市場的信任題項作為連續變量得分,并推測:制度信任能調節品牌歷史和用戶規模對購買意愿的影響。筆者進行了線性回歸分析,其中購買意愿為因變量,品牌歷史、用戶規模、標準化的市場信任及其三者交互項為自變量。首先,用戶規模(β=-0.86, t=-3.83, p<0.001)、品牌歷史(β=-1.82, t=-8.14, p<0.001)和市場信任(β=0.29, t=2.48, p<0.05)分別對購買意愿的簡單效應顯著,這表明:在中國內地消費情境下,(1)消費者通常會表現出從眾購買的行為;(2)相比初創品牌,消費者對老字號的購買意愿更強烈;(3)消費者對中國市場的信任可以提升其購買意愿。其次,與假設H2一致,三者的三重交互作用邊緣顯著(β=-0.38, t=-1.85, p=0.066<0.1)。
進一步地,分別檢驗了在不同品牌歷史情況下,用戶規模和市場信任的交互作用。其中,在老字號品牌背景下,用戶規模和市場信任交互顯著(β=0.27, t=2.38, p=0.02<0.05)。換言之,市場信任正向調節用戶規模對購買意愿的影響,假設H2a得到支持。另外,在初創品牌背景下,兩者交互不顯著(β=0.01, t=0.05, p=0.96)。用戶規模原主效應顯著,與市場信任交互后不顯著,這說明對于初創品牌,市場信任可能降低用戶規模的主效應,假設H2b得到支持(不同組別的對比見上文分析)。從以上分析可見,制度信任是影響品牌歷史與從眾購買關系的關鍵因素,研究一的原分析結果不僅洞察了不同目的地的制度信任的調節作用,附加分析還進一步證實,即使在同一國家背景下,消費者本身對制度的信任具有相同作用。
3 研究二:制度信任對品牌歷史和參考群體的調節作用
3.1 方法
研究二與研究一的方法類似,同樣采取2×2×2組間情境實驗,但為了提高研究的外部效度我們在組內設計了兩種信任產品(深海魚油和兒童多元維生素片)和兩個境外目的地(中國香港與日本),即目的地(中國內地VS. 中國香港和日本)×品牌歷史(百年歷史VS.初創)×參考群體(外參考群體:中國香港/日本用戶VS.內參考群體:中國內地用戶)來檢驗假設。同樣根據3個自變量設計成8種各不相同的調查問卷,但每份問卷各有兩個產品的購物情景。情景1為:您打算購買一瓶深海魚油膠囊(180粒裝),假如是在香港/廣東省內一家您經常光顧的藥店里有一種品牌歷史悠久(成立于1901年)/剛創立不久(成立于2014年),且香港居民/內地居民最愛購買的深海魚油膠囊(180粒裝),請選擇您對下面這些表述的認同程度。情景2為:您打算購買一瓶兒童多元維生素片(120片裝),假如是在日本/廣東省內一家您經常光顧的商店里有一種品牌歷史悠久(成立于1906年)/剛創立不久(成立于2014年),且日本居民/中國內地居民最愛購買的兒童多元維生素片(120片裝),請選擇您對下面這些表述的認同程度。購買意愿的信度分析表明該量表具有較高信度,兩個情境下的Cronbachs α值分別為0.82和0.84。
問卷調查在廣州某高校的繼續教育學院內進行,對象為教師和成人教育學生。在課間休息時,共發放560份問卷,回收421份問卷,篩選后實得情境1有效問卷301份,情景2有效問卷259份,8組分布均較為平均。其中,在粵港兩地購物情境下的被調查者中女性占69.1%,25歲及以下占47.2%,26~40歲占37.9%;在中日兩地購物情境下的被調查者中女性占66.4%,25歲及以下占50.6%,26~40歲占35.2%。雖然這比2015年訪港和訪日的內地旅客的基本特征要偏年青,女性比例稍高(2015年訪日內地旅客中男女各占44.8%和55.2%,20~39歲占61.7%①),但也一定程度上可以代表女性占多數的中青年出境人群。
3.2 操縱檢驗
與研究一類似,將從社會信任和市場信任兩個方面來檢驗被調查者對中日兩國的制度信任。操縱檢驗表明,就保健品而言,人們對日本市場的信任度顯著高于對中國內地市場的信任度(M日本=4.00, M中國內地=3.08, M日本-M中國內地=0.92, df=250, t =7.96, p<0.001);人們對日本的社會信任也顯著高于對中國內地的社會信任(M日本=3.90, M中國內地=3.56, M日本-M中國內地=0.34, df=248, t =2.58, p<0.05),操縱理想。
3.3 分析和結果
(1)粵港兩地購買深海魚油產品的情景下,數據結果表明,目的地(F(1, 292)=4.83, p<0.05)、參考群體(F(1, 292)=5.83, p<0.001)和品牌歷史(F(1, 292)=13.72, p<0.05)均對購買意愿產生顯著的主效應。故H1成立,消費者更愿意購買外群體喜歡的商品。
目的地、參考群體和品牌歷史三者之間的交互作用顯著(F(1, 292)=6.37, p<0.05),H3成立,交互作用如圖3所示。經分析發現,對于老字號而言,在制度信任高的香港,參考群體對購買意愿影響顯著(M外參考群體=5.19, M內參考群體=4.30; F(1,72)=7.42, p<0.01),但在制度信任低的內地,參考群體對購買意愿的影響不顯著(M外參考群體=4.26, M內參考群體=4.51; F(1,72)=0.57, p=0.46),H3a得證。但對于初創品牌而言,在制度信任高的香港,參考群體對購買意愿影響不顯著(M外參考群體=4.25, M內參考群體=4.04; F(1,73)=0.065, p=0.80 );但在制度信任低的內地,參考群體對購買意愿的影響顯著(M外參考群體=4.14, M內參考群體=3.47; F(1,96)=26.68, p<0.001),H3b得證。
(2)中日兩地購買兒童多維片產品的情景下,數據結果表明,目的地(F(1, 250)=5.84, p<0.05)、參考群體(F(1, 250)=12.00, p<0.01)和品牌歷史(F(1, 250)=12.15, p<0.01)的主效應存在,H1也成立。
目的地、參考群體和品牌歷史三者之間的交互作用顯著(F(1, 250)=4.01, p<0.05),如圖4所示。經分析發現,對于老字號而言,在制度信任高的日本,參考群體對購買意愿影響顯著(M外參考群體=5.22, M內參考群體=4.34; F(1,64)=6.10, p<0.05),但在制度信任低的中國內地,參考群體對購買意愿的影響不顯著(M外參考群體=4.20, M內參考群體=4.01; F(1,58)=0.32, p=0.57),H3a得證。但對于初創品牌而言,在制度信任高的日本,參考群體對購買意愿影響不顯著(M外參考群體=4.10, M內參考群體=3.72; F(1,64)=0.29, p=0.59);但在制度信任低的中國內地,參考群體對購買意愿的影響顯著(M外參考群體=4.26, M內參考群體=3.28; F(1,61)=7.12, p<0.05)。所以粵港和中日兩種情境下,H1,H3,H3a和H3b都成立。
4 結論及啟示
本研究以信任商品為對象,采用情景實驗的方法,調查分析表明:(1)在跨境購買信任產品情境下,品牌歷史、目的地、用戶規模和參考群體均對購買意愿存在主效應。(2)制度信任會調節品牌歷史和用戶規模對購買意愿的影響。在制度信任度高的境外發達地區,老字號的從眾效應明顯,人們更愿意購買用戶規模大的老字號商品,而對于初創品牌,消費者從眾效應不明顯,這就為初創品牌提供了良好的經營環境;相反,在制度信任度低的中國內地,老字號從眾效應并不明顯,但對于初創品牌,消費者從眾效應十分明顯,初創品牌的用戶規模越小,消費者的購買意愿就越小,這對于初創品牌是非常不利的。(3)制度信任亦會調節品牌歷史和參考群體對購買意愿的影響。在制度信任度高的境外發達地區,對于老字號而言,外群體從眾效應明顯,內地消費者更愿意購買外群體喜歡的產品,而對于初創品牌,消費者參考群體效應不明顯;在制度信任度低的內地,老字號的參考群體效應不顯著,即老字號的參考群體為境外發達地區消費者還是內地消費者都不會對消費者的購買意愿產生顯著差異;但在制度信任度低的內地,參考群體卻能在初創品牌上發揮顯著的作用,即初創品牌的參考群體為境外發達地區的消費者時,更容易被消費者所接受。
綜上所述,制度信任不但會直接影響消費者對信任產品購買地點的選擇,還會對重要的產品的外部屬性(如品牌歷史、用戶規模和參考群體)產生“錦上添花”的作用,即強化老字號的從眾效應和外群體從眾效應,而不在初創品牌中產生這兩種效應,這無論是對用戶規模大和(或)外群體喜歡的老字號還是用戶規模小和(或)內群體喜歡初創品牌都提供了一個非常好的生存和發展環境;反之,制度信任低則會對重要的產品的外部屬性產生 “雪上加霜”的作用,即加強初創品牌的從眾效應和外群體從眾效應,而不在老字號中產生這種影響,無疑對用戶規模小和(或)內群體喜歡的初創品牌還是用戶規模大和(或)外群體喜歡的老字號的生存與發展都極為不利。所以,制度信任在信任產品的跨境消費中產生了一種促使“強者愈強,弱者愈弱”的“馬太效應”。如何重塑和提高人們的制度信任,周怡認為并非僅靠頂層設計或單純的草根革命能完成,需要在市場與國家以外,借助全社會力量從中觀的一般信任層面, 探討制度信任模式建構的社會基礎[5]。在既有的制度信任環境下,筆者認為,對于國內的初創型企業,在努力提高自身質量和品牌知名度之外,還有兩點啟示:一是運用營銷策略快速積累用戶規模以實現從眾效應,如小米和360,若不能,用戶規模小的企業則很容易由于馬太效應而被迅速邊緣化,如我國企業初創期死亡率偏高的事實;二是應該積極開拓境外發達地區的市場或挖掘西方外國客戶,因為這些地區的經營環境相對可能更好,且境外發達地區的顧客又可以成為國內消費者的參考群體,從而提升國內消費者的購買熱情,如華為和大疆就是墻內開花墻外香的典型。
參考文獻(References)
[1] Lei Chao. The effect of product extrinsic attributes on willingness to buy across the border[J]. Tourism Tribune, 2013, 28(12): 81-89. [雷超. 產品外部屬性對跨境購物意愿的影響[J]. 旅游學刊, 2013, 28(12): 81-89.]
[2] Darby M R, Karni E. Free competition and the optimal amount of fraud[J].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1973,16(1): 67-88.
[3] Nelson P. Information and consumer behavior[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70, 78(20):311-329.
[4] Wang Yongqin, Liu Siyuan, Du Julan. Contagion effects vs. competitive effects in credence goods markets: Theory and event study on Chinas food markets[J]. Economic Research Journal, 2014, (2): 141-154. [王永欽, 劉思遠, 杜巨瀾. 信任品市場的競爭效應與傳染效應:理論和基于中國食品行業的事件研究[J]. 經濟研究, 2014, (2): 141-154.]
[5] Zhou Yi. Modes of trust and market economy order: Institution-based approach[J].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s, 2013, (6): 58-69. [周怡. 信任模式與市場經濟秩序:制度主義的解釋路徑[J]. 社會科學, 2013, (6): 58-69.]
[6] Miyzaki A D, Grewal D, Goodstein R C. The effect of multiple extrinsic cues on quality perceptions: A matter of consistency[J]. 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 2005, 32 (6) :146-153.
[7] Jacob J, George J S, Jacqueline B. Information acquisition behavior in brand choice situations[J]. 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 1977, 3(4): 209-216.
[8] Wang Shubin, Xu Yingzhi. Trust, entrepreneurial expansion and market exit risk in start-up stage[J]. Finance & Trade Economics, 2016, 37 (4): 58-70. [王書斌, 徐盈之. 信任、初創期企業擴張與市場退出風險[J]財貿經濟, 2016, 37 (4): 58-70.
[9] Crosno J L, Freling, T H, Skinner S J. Does brand social power mean market might? Exploring the influence of brand social power on brand evaluations[J].Psychology & Marketing, 2009,26: 91-121.
[10] Bogart L, Lehman C. What makes a brand name familiar?[J]. Journal of Marketing Research, 1973,10:17-22.
[11] Sukoco B M, Lai M, Weng W. The timing effects of reward, business longevity, and involvement on consumers response to a reward program [J]. Asean Marketing Journal, 2015, 7(1): 40-49.
[12] Desai S P, Kalra, A. and Murthi B P S. When old is Gold: The role of business longevity in risky situations[J]. Journal of Marketing, 2008,72: 95-107.
[13] Zhong Ke, Wang Haizhong. Brand elongation effect: The impact of logo shape on estimation to products' time-related attributes and brand evaluation[J]. Nankai Business Review, 2015, 18(1):64-76.[鐘科, 王海忠. 品牌拉伸效應:標識形狀對產品時間屬性評估和品牌評價的影響[J].南開管理評論, 2015, 18(1):64-76.]
[14] Wang Jingyi. The Longevity, brand trust and purchase intention of old brands[J]. Journal of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Business Studies, 2011, 26 (3): 61-66. [王靜一. 老品牌的長壽性、品牌信任與消費者購買意向關系的實證研究[J].廣東商學院學報,2011, 26 (3): 61-66.].
[15] Chang C, Tung M. Intergenerational appeal in advertising: imp- acts of brand-gender extension and brand history[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dvertising, 2016,35(2):345-361
[16] Griesinger D. The human side of economic organization[J].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1990, 15:478-99.
[17] Choi C J, Kim J B. Reputation, learning and quality uncertainty[J]. Journal of Consumer Marketing, 1996,13: 47-55.
[18] Jiang Duo, Xu Fuming, Chen Xueling, et al. The psychological mechanism and influence factors of herd behavior of investors in the capital market[J]. Advance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2010, 18(5): 810-818.[蔣多,徐富明,陳雪玲,等. 資本市場中投資者羊群行為的心理機制及其影響因素[J]. 心理科學進展, 2010, 18(5): 810-818].
[19] Liu Shixiong. From culture value to analyze modes of consume[J]. Economic Management, 2006, 7:49-52. [劉世雄. 從文化價值的角度看消費形態[J].經濟管理, 2006, 7:49-52].
[20] Chen Mengran. Group psychology analysis of public crisis and government's reaction: Base on case of buying salt[J]. Journal of Donghua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 2015, 15(3): 142-149. [陳孟燃. 公共危機中的群體心理分析及政府應對——以搶鹽事件為例[J]. 東華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2015, 15(3): 142-149].
[21] Peng Hui, Song Qianqian. Consumers conformity in C2C markets based on panal data model[J]. Journal of Chongqing University of Posts and Telecommunications: Social Science Edition, 2015, 27(4): 90-95.[ 彭惠,宋倩倩. C2C市場上消費者從眾決策研究-基于面板數據模型[J].重慶郵電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2015, 27(4): 90-95.].
[22] Escalas J E, Bettman J R. Self-construal, reference groups, and brand meaning[J]. 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 2005, 32, (3): 378-389.
[23] Zhou Xuechun, Zhang Xiaojuan. Research on brand image, reference group and self-brand connection: basing on group status and group distinctiveness[J]. Journal of Marketing Science, 2014, 10(4):29-40. [周學春,張曉娟. 品牌形象、參考群體和自我——品牌聯結研究:基于群體地位和群體獨特性的視角[J].營銷科學學報, 2014,10(4):29-40].
[24] Stallen M, Smidts A, Sanfey G A. Peer influence: Neural mechanisms underlying in-group conformity[J]. Frontiers in Human Neuroscience, 2013,7(3): 1-7.
[25] Liviatan I, Trope Y, Liberman N. Interpersonal similarity as a social distance dimension: Implications for perception of others, actions[J].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2008, 44(5): 1256-1269.
[26] Lemay E, Clark M S. Self-esteem and communal responsiveness toward a flawed partner: The fair-weather care of low-self-esteem individuals[J].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ical Bull, 2009, 35(6): 698-712.
[27] Knack S, Keefer P. Does social capital have an economic payoff?A cross-country investigation[J].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97, 112(4): 1251-1288.
[28] Zhang Weiying, Ke Rongzhu. Trust in China: a cross-regional analysis[J]. Economic Research Journal, 2002, (10): 59-70.[張維迎, 柯榮住. 信任及其解釋:來自中國的跨省調查分析[J].經濟研究, 2002, (10): 59-70].
[29] Liu R D, Pieniak Z, Verbeke W. Consumersattitude and behavior towards safe food in China: A review[J]. Food Control, 2013, 33(1): 93-104.
[30] Liu R D, Pieniak Z, Verbeke W. Food-related hazards in China: Consumers' perceptions of risk and trust in information sources[J]. Food Control,2014, 46: 291-298.
[31] Nijssen E J, Herk V H. Conjoining international marketing and relationship marketing: Exploring consumerscross-border service relationships[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Marketing, 2009, 17: 91-115.
[32] Xu Wei, Wang Ping, Wang Xinxin, et al. Time-honored brand authenticity: Its measurement and influence[J].Chinese Journal of Management, 2015, 12(9):1286-1293.[徐偉,王平,王新新,等. 老字號真實性的測量與影響研究[J].管理學報, 2015, 12(9):1286-1293].
[33] Baker J, Levy M, Grewal D. An experimental approach to making retail store environment decision[J]. Journal of Retailing, 1992, 68(4): 445-460.
[34] Wang Junxiu, Yan Yiyin. Annual Report on Social Mentality of China(2012—2013) [M]. Beijing: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China), 2013: 9-14.[王俊秀,楊宜音. 中國社會心態研究報告(2012—2013)IMI. 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13:9-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