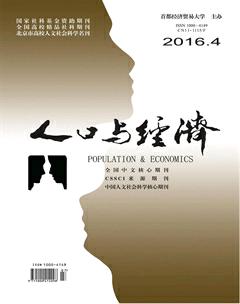“無主體半熟人社會”:新型城鎮化進程中農民集中居住行為研究
田鵬 陳紹軍
摘要:作為現代化的必由之路和必需之策,新型城鎮化已成為解決“三農問題”的重要途徑,對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加快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具有重大現實意義和深遠的歷史意義。隨著新型城鎮化進程的加深,農民集中居住行為及農民集中居住區已逐漸成為學術研究的焦點。文章以江蘇省鎮江市平昌新城為個案,將其置于“城鄉連續統一體”理論框架內,考察作為一種“整體性社會事實”的農民集中居住行為之行動邏輯及農民集中居住區之運行機制。首先,由于農民一國家關系延續使得實踐中的農民集中居住過程表現為“脫身不脫根”;其次,“脫身不脫根”導致農民集中居住區居民委員會“缺位”、業主委員會“缺場”及社區社會資本缺失,使得農民與社區關系呈現“半嵌入”狀態:最后,基于“無主體熟人社會”及“半熟人社會”概念,文章將農民集中居住過程“脫身不脫根”與“半嵌入”辯證作用的社區運作邏輯稱之為“無主體半熟人社會”。
關鍵詞:新型城鎮化;“城鄉連續統一體”;農民集中居住;“無主體半熟人社會”
中圖分類號:F292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0-4149(2016)04-0053-09
DoI:10.3969/j.issn.1000-4149.2016.04.006
一、問題的提出
《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2014-2020年)》指出,城鎮化的快速推進,吸納了大量農村勞動力轉移就業,提高了城鄉生產要素配置效率,推動了國民經濟持續快速發展,帶來了社會結構深刻變革,促進了城鄉居民生活水平全面提升。2015年政府工作報告指出,城鎮化是解決城鄉差距的根本途徑,也是最大的內需所在,要堅持以人為核心,以解決“三個1億人”為著力點,發揮好城鎮化對現代化的支撐作用。作為中國現代化的必由之路,新型城鎮化是以政府主導、產業投資驅動、低成本、外延式擴展的“物的城鎮化”向以農村人口市民化為核心要務的“人的城鎮化”轉變為特征,因此,有序推進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并使其共享改革發展成果就成為新型城鎮化的內在要求。政界和學界關于新型城鎮化推進模式已基本達成共識:鑒于中國城鎮化任務艱巨、區域發展不平衡、轉移人口總量龐大等基本國情,積極推進“就近城鎮化”,充分發揮中小城市在轉移人口、推動就業中的作用,才能解決大城市“城市病”、人口分布嚴重不平衡等突出問題。當前,各地關于“就近城鎮化”的實現路徑仍處于探索階段。正是基于“就近城鎮化”在各地存在不同推進模式,尤其自城鄉建設用地增減掛鉤政策全面實施以來,各地頻頻出現土地集中整治現象,引起了相關學者的關注,他們基于不同學科視角取得了豐富的研究成果,主要包括“撤村并居”社會管理創新問題研究,“撤村并居”進程中農村社會發展問題研究,“撤并村莊”過程中“行政社會”實踐邏輯,“村改居”社區組織建設與運營,農民集中居住區文化適應研究,城鎮化進程中“過渡型社區”生成,轉型與治理。上述研究主要集中探討了下述問題:“撤村并居”社區基本特征,“撤村并居”導致的社會問題及其成因,“撤村并居”社區運行機制及社區治理。雖然關于“撤村并居”現象及“村改居”社區研究已取得相對豐富的學術成果,但筆者認為,上述研究仍然存在局限性:第一,就理論框架而言,由于實踐中新型城鎮化推進模式具有多樣化特征,雖然各學者基于不同學科背景,從不同視角展開了新型城鎮化實現路徑的研究,但缺乏一種“整體性社會事實”的理論框架。第二,就研究范式而言,目前關于“撤村并居”現象研究都是將“村改居”社區視作一個獨立的“孤島”,一個帶有濃濃“鄉愁”、“亦城亦鄉”的特殊聚落空間,具有很強的過渡性、復雜性、可塑性等特征,但這種“孤島”分析范式切斷了“村改居”社區與其所處社會環境的聯系,既未能很好地詮釋其內部治理結構轉型的動力機制,也無法闡釋“撤村并居”的運行機制及其實踐邏輯。第三,就研究內容而言,既有研究缺乏對“人”的研究,作為社區生活主體,“人”往往成為“鄉村一都市”二分框架的“傀儡”,這種二分框架無法展示作為主體的“人”如何發揮主觀能動性,實現其與社會結構的良性互動。鑒于上述局限性,筆者以江蘇省鎮江市平昌新城為個案,將其置于“城鄉連續統一體”(Urban Rural Continuum)理論框架內,以社區主體——“人”及其社會行動為切入點,將農民集中居住區視作一個“被實踐的空間”,即將其社會秩序視作實踐主體行為的制度性后果,考察作為一種“整體性社會事實”的農民集中居住行為之行動邏輯,以及農民集中居住區之運行機制。
二、“脫身不脫根”:農民一國家關系延續
作為就近城鎮化的推進模式及城鄉一體化的實現路徑,農民集中居住過程表現為地理空間上的人口聚集,即人口從村落向社區逐步聚集的過程。對村落而言,該過程導致作為生活空間的村落地域首先解體,農民集中異地居住后導致其“脫身”于原村落空間。平昌新城XR社區居民LAX原來是DG鎮LB村村民,2012年6月搬遷到XR社區至今已有3年多時間,當問及搬遷后是否經常與LB村集體聯系時,他對筆者說:“2012年LB村是最早一批搬進來的,到現在有3年多時間了,但是我們村委會保留著,一直沒有解散,因為關系到集體利益的事情還是會通知村民開會討論。”(20150508PCXRLAX)理論上而言,農民集中居住新社區后將會降低其與原村集體互動頻率及預期,逐漸導致“脫身”后的農民“脫嵌” (dis-embedment)于原村落,包括與原村集體形成組織“脫嵌”,但實踐中則不然,農民集中居住新社區后不但沒有與原村集體發生“脫嵌”,相反,兩者間互動更加緊密,正如LB村村長LCS所言,“村民不但不是斷了線的風箏,反而比以前更加依賴村集體”。(20150508PCXRLCS)顯然,農民集中居住過程中的“脫身”并不能使其與原村落發生“脫根”,作為一種二元悖論式關系,“村落終結”與“村落情結”并存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集體資產是農民集中居住后聯接村民和村集體的重要紐帶。平昌新城XY社區主要由DL鎮QZ村、HZ村、wQ村、zL村、zz村、GST村村民組成,筆者在XY社區調研發現,作為連接紐帶的村集體資產主要來自土地補償費和拆遷補償款。以DL鎮HZ村征地補償款分配方案為例,征地補償費由土地補償費、安置補助費和青苗補償費三部分組成,產權歸屬HZ村集體所有的土地,征地補償款全部由HZ村集體所得,產權歸屬HZ村村組集體所有的土地,征地補償款中,土地補償費由HZ村集體所有,安置補助費和青苗補償費則由組集體所有,組集體再根據小組會議討論決定其所得補償款具體分配方案。因此,作為人民公社運動的重要制度遺產,土地集體所有制使得HZ村集體在“萬頃良田”工程中得到了一筆豐厚的土地補償費,而這也成為HZ村村民集中居住XY社區后仍然高度“關注”村集體及其代理者——村干部的重要原因。“我們現在不在村里住了,村干部就更不約束自己了,還以為我們不關心村里事務了呢!村里的集體土地補償款,村集體的魚塘、道路和其他邊角的土地,七七八八加起來不會低于100畝,這些錢又去哪里了?魚塘是我們村民當年一鍬一鍬挖出來的,現在補償款卻不分給我們,簡直沒有道理!這個事情我們也向DL鎮相關領導反映了,但是到現在都得不到解決。”(20150515PCXYHMS)村民HMS首先對HZ村村集體資產分配方案表示極大不滿,而村民HDS則對村集體拆遷款管理和使用表示擔憂,“村里那么多養豬場的房屋拆遷款應該分給村民,當時養豬場的房子都是村民集資蓋起來的,現在拆遷結束都快5年了,補償款到哪里去了?另外,去年村里已經組織過一次遷墳,村民也拿到了補償款,但是今年村干部又以村民的名義進行一次遷墳,錢也沒有發給我們,到現在也沒有公示出來。村民為這些事情已經多次到新區管委會上訪,但都是不了了之”。(20150515PCXYHDS)正如三農學者于建嶸指出的那樣,因征地拆遷補償款引起的集體上訪和群體性事件已經成為影響中國農村社會穩定的重要因素,成為21世紀以來農村社會又一重要風險源。筆者認為,集體資產分配問題的本質是產權認定過程中利益相關者間的博弈,即村民與村集體(村干部作為村集體資產代理者往往被村民視作整個征地拆遷過程中最大的獲利者,無論是安置房分配還是補償款使用以及辦公用房建造)就如何分配征地拆遷中村集體資產未達成一致的問題是由于對村集體系列產權關系未達成共識。但集體產權認定過程不是經濟學二分關系,即產權與非產權,而是一個復雜的社會問題,尤其在產權人與代理人、代理人與二級代理人之間形成的產權結構,需要一個相應的治理結構進行約束。目前村民雖然搬遷至新社區但仍關心村集體資產分配,是因為集體產權在某種程度上是一種公共物品,具有一定的公共屬性,因此,許多村民都認為村莊雖然不存在,但是村民仍有享受村集體資產的收益權;同時,作為村集體資產的委托人,村民對代理人(村干部)缺乏必要的約束機制,因此,在不能形成集體行動的村組,村民唯有抱怨。
第二,農民集中居住并未使得農民一國家關系徹底轉型為市民一國家關系,村民委員會仍然是基層治理主體,因此,基層公共事務是農民集中居住后聯接村民和村集體的另一重要紐帶。以DJ鎮HL村為例,截止到2013年7月,全村355戶村民“萬頃良田”工程全部集中搬遷至平昌新城XR社區。為方便本村村民辦理村級公共事務,如新型農村合作醫療費、農村養老保險費、高齡老人補貼、低保金、救濟金等,2013年10月,HL村租用XR社區25幢2單元402室作為村委會臨時辦公地點,每周二、周四受理本村村民公共事務。正如居民YT所言,“以前住在村里時,去一趟村委會辦事真不容易,還要走一段爛泥路,現在搬過來方便多了,村委會就在社區里,離村民更近了,辦起事來也容易多了”。(20150512PCXRYT)從農民一國家關系視角看,農民集中居住改變的不僅僅是居住格局和村莊空間形態,本質上體現的是農民一國家關系變遷,即從傳統農民一國家關系向現代市民一國家關系變遷,但實踐中的村委會在農民集中居住后仍然扮演著國家、農民雙重代理人角色,承擔著基層社區治理主體的職責;同時,由于土地集體所有制及村莊集體資產運營的需要,村民委員會及村民自治的社會基礎仍然存在,并未發生實質性改變。一方面,村委會繼續發揮國家、農民代理人作用,保證國家一農民關系延續,因為農民居住空間的轉換并未實現市民一國家關系的現代性轉型,比如農村計劃生育、農村養老保險、新型農村合作醫療、惠農資金等基層公共行政事務仍然帶有濃厚的“鄉土氣息”,文本制度的“村改居”并未真正實現農民市民化的徹底轉型,正如DJ鎮HL村村長HWY所言,“村民的利益仍然留在村集體里,村民與村集體的關系沒有發生變化,有事還得回村委”。(20150512PCXRHWY)另一方面,農民集中居住行為本身不但沒有增強社區關聯度,反而加深了農民原子化程度,因為傳統熟人社會的認同單位是自然村落,而農民集中居住區是由若干不同行政村村民組成的“半熟人社會”,缺乏現代治理規則和社區公共精神,“有事還得回村委”就成為農民集中居住后的理性選擇。
第三,職業轉換多元化是農民一國家關系延續的又一重要維度。職業轉換多元化主要表現為兼業化特征,即非農就業和農業就業兼業化同時成為家庭收入的主要來源。一方面,雖然農村宅基地騰退后鼓勵農民以“返租倒包”的形式進行土地集中流轉,但原則上保留農戶承包地的自主經營權;另一方面,平昌新城居民的職業轉換呈現出“半工半耕”的家庭代際內部分工,即老年人主要從事農業生產,保障家庭口糧供應,而年輕人則選擇進廠務工,通過非農就業最大化家庭經濟收益。XR社區居民LXX告訴筆者:“搬遷前我們GST村還有380多畝的承包地,很多村民都不選擇流轉,因為搬遷到新社區如果不種地就會丟掉家庭的口糧,而且種了一輩子地,徹底放棄一下子還不適應,總感覺如果不種地就無所事事了。所以,我和兒子商量后決定我和他母親仍然耕種3畝左右的責任田,現在兒子兒媳在廠里上班,我們幫他們帶小孩的同時還能靠種地補貼家用。”(20150518PCXRLXX)顯然,LXX認為保留家庭承包地不僅僅是需要通過種地補貼家用,更重要的原因是種地仍然是農民實現自我價值的重要途徑。因此,農民的種地行為已超越職業屬性成為農民一國家關系延續的重要載體,正如LXX所言,“種了一輩子地,徹底放棄一下子還不適應,感覺如果不種地就無所事事了”。
最后,二元戶籍制度的運作慣性使得農民集中居住后無法實現戶籍身份的徹底轉型,戶籍的農業屬性就成為農民一國家關系延續的實踐形態。實踐中平昌新城雖然也實施了“經營權換保障”的安置政策,即擁有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的家庭承包戶,在第二輪土地承包期內,自愿將承包地全部交由村集體經濟組織、村民委員會或村民小組等發包方進行流轉,置換家庭人員一定生活保障待遇的一項制度。但作為一種新型安置模式,“經營權換保障”并未改變農民的戶籍屬性。平昌新城管理委員會副主任LXP告訴筆者:“土地經營權換保障主要是考慮老年人的生活問題,但這種安置模式并沒有徹底改變我國現行城鄉二元分割的戶籍制度,一方面,戶籍制度改革需要一系列配套改革方案,并非一蹴而就;另一方面,作為基層管理部門,更多的時候是執行上級部門的相關政策和國家基本制度,改革還是應該由頂層設計去決定。因此,當初設計土地經營權換保障安置模式時并未觸及戶籍制度改革。所以,平昌新城的居民從戶籍統計口徑而言仍然是農業戶籍,而不是城市戶籍。”(20150614PCGWHLXP)從LXP副主任的敘述中可以發現,“經營權換保障”的初衷是解決老年人生活問題,并非普通居民所理解的“農民進社區就變成城市人了”,這種新型安置模式并不觸及戶籍制度改革,從戶籍統計口徑而言,集中居住后的居民仍然是農業戶籍屬性。城鄉二元戶籍制度的長期運行導致農民集中居住后戶籍屬性無法改變,一方面,已經不再居住在農業生產場所——農村社區,但另一方面仍然從事農業生產活動并且保留農業戶籍。因此,平昌新城農民集中居住區打破了傳統農村作為生產場所一生活空間有機結合的狀態,演繹出一種新型“脫身不脫根”的實踐樣態。
三、“社區里的農民”:一種“半嵌入”狀態
社會網絡是指社會個體成員之間因互動而形成的相對穩定的關系體系,它關注的是人們之間的互動和聯系以及作為互動結果而累積的社會資本。從社會網絡視角看,農民集中居住行為本質上是一種從“脫嵌”到“再嵌入”的過程:一方面,農民異地集中居住導致其與作為生活空間的村落地域發生“脫嵌”;另一方面,入住新社區后村民將憑借獨特的生平情境和“手頭知識”,在一個陌生社會情境中重構“生活世界”。筆者認為,農民集中居住后的“脫身不脫根”現狀直接導致其無法徹底完成新社區“生活世界”的重建,從而形成一種“半嵌入”狀態。
首先,居民委員會“缺位”直接導致以“街居制”為核心的“基層治理網絡”無法形成。作為城市“基層治理網絡”的重要組成部分,居民委員會在后“單位制社會”中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_20]。實踐中,為配合“農民上樓”而通過行政手段強制進行的“村改居”往往流于形式,農民集中居住區中居民委員會處于“空殼”狀態,并未真正承擔其應有之責。以平昌新城XL社區為例,該社區主要由DG鎮DL村、DS村、DM村、DZ村村民組成,2012年11月掛牌成立鎮江新區平昌新城XL社區居民委員會,并按照現代社區治理規則制定了《XL社區居民委員會工作職責》和《XL社區居民委員會規章制度》,其中《工作職責》第四條規定:保障集體經濟組織和居民合法財產權和其他合法權益;第七條規定:依法調解民間糾紛,協助維護本社區社會治安,向中心社區反映居民的意見、要求和建議。但“村改居”文本制度與實踐規則相分離使得農民集中后村民委員會代行居民委員會之責成為治理模式轉型的新常態。正如XL社區居民DLG所說,“我知道成立了XL社區居委會,但是搬過來兩年多了,連居委會干部都不認識,也沒去居委會辦過事,有事情還是回原來的村委會找村干部,居委會實際上就是個空架子,不起任何作用”。(20150509PCXLDLG)DLG認為,人住新社區后雖然掛牌成立了居民委員會,但村委會在其日常生活中仍然扮演著不可替代的作用,而前者則成了不起任何作用的空架子。一方面,傳統村莊認同的基本單位和行動邏輯使得新任居委會主任缺乏必要的日常權威,很難獲得村民認同,并且由上級指派本身不符合基層民主選舉的原則,也導致居民對居委會干部的制度性不認同;另一方面,居委會主任的公共事務處理仍然需要借助村委會實現,大部分日常事務處理均由本村村委會主任負責,因此,這種片區式的責任制治理模式使得日常生活中居民互動的主要對象是社區副主任(即原來村莊的村委會主任),而非其他社區人員。因此,LX社區居委會處于制度與實踐的二元分離狀態,其治理實踐中的“缺位”就成為“社區里的農民”“半嵌入”狀態的首要表現。
其次,業主委員會“缺場”使得農民集中居住區無法實現傳統村落治理模式向現代社區治理模式的轉型。作為中國公民社會的先聲,業主委員會是城市基層社區治理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同時,由于缺乏現代社區物業理念及業主意識,農民集中居住區并不能形成學術界所謂的“有房階級”,即單位制解體后,因權利意識覺醒、“家園意識”增強而形成的一種新型城市社會階層。筆者在平昌新城調研發現,5個社區均成立業主委員會,但發揮的作用有限,當問及原因時,XR社區居民LDS告訴筆者,“你說的那個什么委員會我沒聽過,我們老百姓又沒有文化,怎么成立什么委員會”?(20150520PCXRLDS)而居民LWY則表示,“業主委員會我知道,我兒子住在鎮江,他就是他們小區里的業主委員會成員,業主委員會要定期召開會議,討論社區里的事情,并會要求物業公司公開賬目。但是我們這里住的又不是城市人,都是鄉下的農民,先不說他們不懂什么是業主委員會,就是懂了,又怎么成立?大家的文化水平都不高,年輕人又忙于上班,沒時間參與社區的事物,所以,在平昌新城成立業主委員會是不可能的”。(20150520PCXRLWY)從上述居民的回答中可以發現,“農民上樓”這一空間層面的轉換并不能直接實現農民市民化轉型:一方面,城鄉二元體制的長期運行使得傳統農民缺乏現代物業理念和業主意識;另一方面,作為社區治理的重要主體,年輕勞動力常年外流也使得社區公共事務參與程度不高,導致業主委員會無法運作。因此,農民集中居住區業主委員會“缺場”是農民“半嵌入”狀態的又一實踐形態。
最后,“大雜居、小聚居”居住模式使得農民集中安置過程中未能超越地緣關系形成社區認同感與歸屬感,從而使得社群社會資本無法通過社區參與、鄰里互動轉換為社區社會資本。不同于社群社會資本,社區社會資本是基于社區參與、鄰里互動產生社會網絡,前者是基于地緣、血緣等個體化特征較強的關系而形成的社會網絡,具有封閉性、高同質性、高連帶性、高密度性等特征,而后者則是基于較大范圍內制度化社會互動而形成的普遍性認同,具有邊界開放性、高異質性、低連帶性、低密度性等特征。筆者在平昌新城調研發現,發生社會性“脫臼”的村民入住新社區后,既面臨地緣關系網絡部分斷裂,又由于缺乏制度化社會互動而導致社區社會資本無法重建。平昌新城XY社區居民ZDS告訴筆者:“大家都分散安置到各個社區,現在很難見到原來的老鄰居了,我到現在都不認識我家對門的人。原來在村里有事還能找找鄰居幫忙,遠親不如近鄰,鄰居好,賽金寶,但是現在就不同了,我搬過來都快兩年了,難得碰到以前村里的人。”(20150524PCXYZDS)同時,筆者在座談中多次聽到很多居民抱怨“生活狀態和以前不一樣了”、“鄰里關系不如以前融洽了”、“不認識對門的鄰居”、“躲在家里各自忙各自的事情”、“連個可以說話的人都沒有”、“遇到事情不知道找誰幫忙”,等等,孤獨感、失落感增強是農民集中居住后的普遍感受。正如有學者研究指出,農民集中居住并不能直接使得移民社會網絡擴展,而需社會互助體系和社區支持系統實現社會資本積累。一方面,“大雜居、小聚居”的居住模式改變了傳統村落聚居模式,直接導致原有社群社會資本流失,即基于地緣、血緣關系形成的社會網絡部分斷裂;另一方面,農民集中居住區內居民委員會的“缺位”及業主委員會的“缺場”直接導致被拋入陌生情境的農民無法開展有效社區參與,無法通過制度化社會互動積累社區資本。因此,社區社會資本無法重建也是農民“半嵌入”的實踐形態。
學者吳重慶用“無主體熟人社會”(Baseless Society of Acquaintance)概念形容中國農村年輕勞動力流失后空心化社會的運作邏輯,并指出其與傳統鄉土“熟人社會”的不同之處,即輿論失靈、面子貶值、社會資本流散以及熟人社會特征的周期性呈現。筆者將就近城鎮化進程中農民集中居住區運作邏輯稱之為“無主體半熟人社會”(Unconscious Society of Semi-Acquaintance)。具體而言,一方面,以建制鎮為單位的“大雜居”和以行政村為單位的“小聚居”相結合之居住格局,使得農民集中居住區仍然具有明顯的“半熟人社會”特征:另一方面,筆者所謂的“無主體”(Unconscious)并非吳重慶的研究中意義上的年輕勞動力周期性流失導致農村社區“空心化”、“無根基”(Baseless),而是指居住空間變遷后農民缺乏主體意識,即缺乏社區公共精神和現代業主意識,從而使得居住空間社區化與行動邏輯農民化并存,形成“社區里的農民”。因此,“無主體半熟人社會”就成為就近城鎮化實現路徑——農民集中居住區的運作邏輯。
四、結論與討論
文章以江蘇省鎮江市平昌新城為個案,將其置于“城鄉連續統一體”的理論框架內,以社區主體——“人”及其社會行動為切入點,將農民集中居住區視作一個“被實踐的空間”,即將其社會秩序視作實踐主體行為的制度性后果,考察作為一種“整體性社會事實”的農民集中居住行為之行動邏輯及農民集中居住區之運行機制。筆者將農民集中居住過程中農民一國家關系延續導致的“脫身不脫根”及居民委員會“缺位”、業主委員會“缺場”、社區社會資本缺失導致的“半嵌入”狀態稱之為“社區里的農民”,并將農民集中居住區運行邏輯稱之為“無主體半熟人社會”。
首先,實踐中的農民集中居住過程表現為“脫身不脫根”,即居住格局變遷及生活空間轉型并未使得農民一國家關系徹底轉型為市民一國家關系,作為農民、國家雙重代理人,村民委員會(村干部)仍然是集體資產管理者和農民一國家關系維系者。一方面,土地補償費、拆遷補償款等集體收入使得農民異地居住后不但沒有降低公共事務參與預期,反而對村級資產、財務支出、村干部廉政等切身利益問題更加關注,“脫身”后的農民主觀上并不愿意“脫根”;另一方面,由于中國城鄉二元制度的運作慣性,城鄉一體化進程中戶籍制度、土地制度、財政轉移支付制度、投融資制度等一攬子制度改革并未完全滿足新型城鎮化進程中與人口聚集相關制度改革的需求,使得農民一國家關系在村落生活空間解體后成為農民市民化轉型的桎梏,從而導致農民集中居住過程中的“脫身不脫根”。
其次,農民集中居住過程中的“脫身不脫根”使得農民集中居住區居民委員會“缺位”、業主委員會“缺場”及社區社會資本缺失,從而導致農民的“半嵌入”。一方面,由于農民一國家關系的延續,村民委員會取代居民委員會成為農民集中居住后國家與農民日常互動的載體,既無法實現居委會作為“基層治理網絡”的核心作用,也不利于農民社區公共意識的建立,同時,缺乏現代物業理念的農民也無法通過業主委員會這一“自治理機制”實現農民集中居住區治理模式轉型:另一方面,由于社區主體意識及現代業主意識缺乏,集中居住后的農民無法超越地緣、血緣等先賦性因素,通過制度化社會互動實現現代社區居民關系轉型,使得社群社會資本部分流失后無法重建社區社會資本。因此,以社會網絡視角審視農民集中居住行為則會發現,社群社會資本部分流失及社區社會資本無法重建是實踐中農民集中居住過程中與原村集體“脫身不脫根”及與新社區“半嵌入”困境的核心所在,如何通過集體產權制度改革、農村土地制度改革、新型社區治理體系創新等一攬子改革措施實現農民集中居住過程中社群社會資本與社區社會資本轉換,則成為推進以“人的城鎮化”為核心要義的新型城鎮化之關鍵。
最后,“無主體半熟人社會”是農民集中居住區運作邏輯的核心特征。一方面,“大雜居、小聚居”居民格局使得農民集中居住區“半熟人社會”特征明顯:另一方面,農民的“半嵌入”及其“無主體性”使得農民集中居住區呈現社會空間社區化與行為模式農民化二元并存的特征。因此,以“半熟人性”和“無主體性”為基礎特征的農民集中居住區,其運作邏輯呈現“無主體半熟人社會”特征。當然,中國區域發展的不平衡性要求新型城鎮化推進模式和實現路徑勢必具有多元化特征。目前,“農民上樓”和“資本下鄉”已成為中國新型城鎮化推進模式的新常態,其背后則是由土地、財政、金融三位一體循環機制作為其動力系統。而作為土地整治工程的配套項目,江蘇省鎮江市平昌新城(江蘇省內單體規模最大的農民集中居住區)是新型城鎮化進程推進模式的有益探索。由于社區建設和發展還有待實踐進一步檢驗,因此,筆者嘗試性提出“無主體半熟人社會”概念就不可避免帶有局限性,今后既需進一步探索如何“走出個案”,即通過個案抽象出的概念如何超越個案進行通則式解釋,又需要將此概念不斷與實踐中的農民集中居住區進行對話并檢驗其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