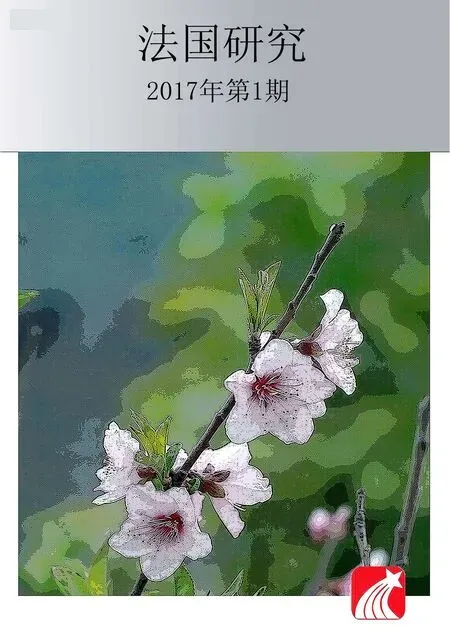“作家減去作品”:《羅蘭?巴特自述》中主體性的拉鋸戰
王漢琦
?
“作家減去作品”:《羅蘭?巴特自述》中主體性的拉鋸戰
王漢琦
北京大學外語學院 法國國立東方語言文化學院
當代法國自傳文學跳脫了自傳寫作的傳統框架,使得自傳的主體性問題備受爭議,其中以羅蘭·巴特的《羅蘭·巴特自述》為先河之作,對其后的新小說派作家影響甚鉅。在巴特縱橫交錯的文風中,“情感性”與“想象物”可作為二條線索,來探究此書所表現的主體性。
主體性 情感性 想象物
《羅蘭巴特自述》()一書, 題名本意為“羅蘭巴特論羅蘭巴特”;看似普通的自傳,實為一部反自傳的作品。在法國發表之后引起兩極化的回響。70年代末,新小說流派的作家們相繼出版了似是而非的自傳小說[1]娜塔麗·薩洛特-加龍省-加龍省-加龍省-加龍省(Nathalie Sarraute) 的《童年》(Enfance, 1983), 杜拉斯(Marguerite Duras) 的《情人》(L’amant, 1984),克洛德·西蒙 (Claude Simon)的《農事詩》( Les Géorgiques, 1981), 阿蘭·羅布-格里耶(Alain Robbe-Grillet)的《重現的鏡子》(Le Miroir qui revient , 1984)等。,被認為直接或間接受到巴特影響,最顯著的例子就是阿蘭·羅布-格里耶(Alain Robbe-Grillet),他不諱言地贊揚此書,并表明他的“新自傳(nouvelle autobiographie)”《重現的鏡子》創作的靈感方針,就是《羅蘭·巴特自述》[2]張雅婷: ? Le Miroir qui revient d’Alain Robbe-Grillet : quel miroir au niveau intertextuel ? ?(阿蘭·羅布-格里耶(Alain Robbe-Grillet)的《重現的鏡子》:互文性層面的哪面鏡子?)。臺灣中央大學,2007年出版: < http://thesis.lib.ncu.edu.tw/ETD-db/ETD-search-c/view_etd?URN=93123003>。
1975年,此書出版的同一年,菲利普·勒熱納(Philippe Lejeune)為法國自傳理論擬下了代表性的定義,大幅縮小自傳文體的范圍,強調以“我”為中心的“自傳契約”,象征著自傳道統的延續和緊縮。迥異于此二路線的自傳理論學者,是法國與歐洲自傳研究的先驅:喬治·古斯多夫(Georges Gusdorf),其自1948年以來,就針對自傳文學加以著墨,他強調自傳的目的是了解自己,臻善人格,為求彰顯人生價值觀,是攫取人類意識的第二文本(seconde lecture)。因此人類學意義大于文學意義。他的理論有著強烈的存在主義跟現象學色彩,環繞著人文主義及個人主義光芒,并具有倫理性。在巴特和勒熱納發表作品之后,古斯多夫立刻大力抨擊兩人,表示他們對人類主體的忽略:勒熱納拘泥于文學形式及修辭,羅蘭·巴特則根本是“驅散”人類現實[3]Jesus, Camerero. ? La théorie de l’autobiographie de G. Gusdorf ?(古斯多夫的自傳理論).Basque espagnole : Universidad del Pais Vasco, 2003, p.5-6: ? < http://webpages.ull.es/users/cedille/cuatro/camarero.pdf >。究竟《羅蘭·巴特自述》,這看似光怪陸離的“自傳”(小說)中,人類的主體性是否無以復存?正乃本文所欲抽絲剝繭一探究竟之處。
1980年,巴特生前出版的最后一本書《明室》(又名《轉繪儀》)問世。書中借著攝影的心得表達對母親的悼念和依戀,充滿了人性關懷與“情感性”(l’affectivité),與前作大相逕庭,雖然仍以散文寫作,但片段的鑿痕已經減弱,又因受現象學影響,亦放松了對主體性的抗拒,對于其母,言明不能釋懷的是“一個存在(的人)、一種品質、一份靈魂”[4]"Car ce que j’ai perdu, ce n’est pas une Figure (la Mère), mais un être; et pas un être mais une qualité (une ame)."Barthes, Roland, La Chambre Claire. Paris : Seuil, 1980, p.163.。因此,也許我們同樣能藉由“情感性”這個“破綻”,尋找他早些年在《羅蘭·巴特自述》中主體性的軌跡。
首先,主體性在此書必定是隱性的,是巴特刻意要抹滅的“玩意”。他運用了各種技巧去掩蓋它:形式上采用支言片語(les fragments)式的散文寫作,為了防止長篇大論會定型出的所謂的意義(sens)及意識形態;修辭層面上人稱混亂,交錯使用,為了防止我(Je)的個人神話,和他/它(il)的歷史權威性,卻又要創造虛擬的故事性效果[5]Il法語中的第三人稱單性,可表中性及公信力,慣用在歷史及正式書寫(它),同時也是小說、故事的常用人稱(他)。。全書號稱“一個小說人物的談話”卻不斷穿插巴特自己的批評理論: 以沒有邏輯的方式,一下子用“我”表述,一下又用“他/它”。而這種不隸屬任何文類的新文類,巴特稱之為類小說(Le romaneque)。
當代文壇的無文類趨勢一如米歇爾·比托爾(Michel Butor)所說:“批評和創作正如同一體兩面,融合而成的新形式泯滅了兩者的對立關系”[6]譯自"[c]ritique et invention se révélant comme deux aspects d’une même activité, leur opposition en deux genres différents dispara?t au profit de l’organisation de formes nouvelles " Butor, Michel, ? La Critique et l’invention ?, OEuvres complètes de Michel Butor II : répertoire 1, sous la direction de Mireille Calle-Gruber, Paris : Edition de la différence,2006, p.727.,正是巴特和后來的格里耶等所欲為者。
透過創作與批評的結合,巴特為了加強破除各種意識型態的迷思,制造書中片段之間以及與各個前作之間的理論文本關連性[7]即互文性。此為黃唏云的譯法。詳見:黃唏云:〈羅蘭巴特思想的轉捩點〉。《世界哲學》,2004年出版:
巴特告訴我們,此書的主要目的,是描繪他和他的“想象物”(imaginaire)的關系[8]原本小說在法文里分為寫實小說跟虛構小說,后者就是稱為 : Roman de l'imaginaire.Imaginaire 是動詞imaginer (想象、虛構)衍生的形容詞與名詞 : 字面上的意思為想象中的事物。,可見《羅蘭·巴特論羅蘭·巴特》指的就是作家巴特論“想象物”巴特,也就是主體性陳述的關鍵詞。到底想象物是什么?想象物不是巴特自創的概念,他也不是首次在本書中啟用,根據此書中的文本關聯性,巴特也自我解釋了他用的理論術語和寫作進程[9](譯自本書原文)Barthes, Roland, Roland Barthes par Roland Barthes. Paris: Seuil, 1975, p.148.:
一、《寫作的零度》(1953)、《神話集》(1957)屬于社會神話階段;其言明這段期間有受到薩特(Sartre)的影響。薩特在1940年曾發表了《想象物》()一書,薩特定義的想象物,是受胡塞爾影響的存在主義現象學,想象(imagination),是與本能的知覺 (perception)相對的概念,是人歸類、理解事物的意識,一種意義的創造。
二、《符號學原理》(1965)、《時裝系統》(1967)屬于符號學階段;此階段引用的理論以索緒爾(Saussure)的結構語言學為主,著名的文章《作者之死》,也是在此時發表。當時伴隨著1968年法國的學運思潮,反對傳統、權威的聲浪高漲;啟蒙運動以后,伴隨著實證主義、經驗主義的發展,作品的權威發言人即是作者,圍繞著作者的傳記、生平、歷史背景的文獻研究限制了文本批評的多元性。因此巴特采用語言符號學的方法去分析文本,以文本中的修辭、言語為依歸,創造新的批評方法,這也是伴隨著當時俄國形式主義、美國新批評派等的潮流。
三、《S/Z》(1970)、《符號帝國》(1970)、《薩德、傅立葉、羅耀拉》(1970)屬于文本性階段;此階段提到了心理分析家拉康(Lacan),拉康在其鏡像階段的理論中亦有用到想象物的概念,是指人在嬰兒時期即自我認同的形成初期,對自己和他人的錯誤認知。
在香港現代(深圳)牙科材料有限公司實習的我校一名學生曾創下該企業實習生最高績效,被稱為“績效之王”;另有一名學生以8個月實習期6次獲評優秀實習生而得到提前轉正的機會,并且一次通過考核享受該公司四級工的待遇。
四、《文本的歡愉》(1973)以及此書(1975),位于第四階段:其啟發來自尼采(Nietzsche)思想中的道德觀(moralité),與傳統的“道德”相佐,尼采的思想主要為抨擊西方的基督教與形而上哲學的傳統,巴特特別指出靈感來自其理論中古希臘人崇尚肉體的道德觀,強調人身的美好、生命的自然狀態、肉體的美,反對基督教中重視靈魂、貶抑肉體的思想。
盡管巴特為自己和讀者做了階段性的整理,他仍不忘加以批注著:這些引用的作者,他的思想跟創作理念“未必受其影響”,所以這些術語也不是照本宣科的學術參照,而是“修辭上”的、“符號”上的運用與創作。此外,各個階段之間也“不是壁壘分明”的,文本間或有關連、或有閃回、或有橫越。另外,在各個理論的評點中,巴特不斷強調一種“不確定”的關聯性: 像是與心理分析的關系是“未決定的”[10]Barthes, Roland. Oeuvres complètes. Paris : Seuil, 2002, p. 724,而對于尼采的道德觀他無法確切的“概念化”,只能說是賦予了他一片“磨筆的天地”。(Barthes, 2002 : 643)
總而言之,我們難以將巴特文中的想象物與薩特或拉康定義的想象物畫上等號:巴特的想象物是是用以批評社會中的宗教、政治、從眾心理的各種教條(doxa),因此社會學的意義大于本體論、認識論的。
在之后的作品中,我們仍看到巴特運用類似的寫作技巧和想象物的概念,以一種令人費解的形式表達他的理念;1977年的《戀人絮語》如同是《自述》的續集[11]懷宇譯:《羅蘭巴特隨筆選》。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2009, 243- 272頁.。如前所述,直到在《明室》中,巴特才對情感性和主體性較為松綁,當中提到了想象物,也似乎沒有像前作中如此這般的鑿刻與掙扎,又或許《明室》是以影像的角度描述,更加形象化些 : “面對鏡頭,我同時是: 我自以為的我,我希望別人以為的我,攝影師眼中的我,還有他藉以展現技藝的我”[12]Barthes, Roland. La Chambre Claire. Paris: Seuil. 1980. 譯文選自許綺玲譯:《明室》。臺灣攝影工作室,1997,23頁。。
反觀《自述》中以文字的角度對想象物的描述,如同在〈我看見了言語〉 (Barthes, 2002 : 735) 中表示,他有三種視野:1.想象物是簡單的:是我看到的來自他人的話語。2.想象物是我對自己的透視,我看見我被他人看見的那些言語。3.視野是無限多級的言語,開放后的括號:烏托邦的視野,試想有一個流動的復數的讀者,迅捷地提放(我的)引號:開始與我一同寫作。
可見一個作者的“想象物”,是他人的言語構成的,是他人的眼中的“我”,是我從他人的眼光中重構的“我”,而巴特的理想,則是實現第三種寫作與閱讀的視野:“想象物”的消失,開放各種詮釋可能性的閱讀。巴特想讓我們理解,他想達到的寫作的烏托邦,是撇除意識型態、神話元素、重視言語本身的、寫作的歡愉(jouissance),是作者死亡(l’auteur est mort)作家(l’écrivain)誕生,重文輕人的寫作。矛盾的是,寫作這一事件本身,無論是“作家”也好“作者”也罷,都無法完全脫離“人我主體”的影子,尤其是自傳寫作,巴特自己也非常掙扎。
他知道一旦寫作涉及了七情六欲、喜惡、個性與外表就十分容易墮入想象物的陷阱——情感性。“事實上當我在泄漏我的私生活,是我自我暴露最多的時候:不是有丑聞的風險,而是我在我的想象物最堅定的狀態中展現它……”(Barthes, 1975 : 85) 因此他對于這些話題特別敏感,總是在其中“畫蛇添足”。在關于身體的文章中,他說:“我的身體不是英雄。” (Barthes, 1975 : 65) 關于朋友的片段中:“必需努力將友誼說成一處純粹的老話題:這樣可以使我脫離情感性的場域——人們可以毫不窘迫地談論情感性,因為它涵蓋在想象物之中(……)”(Barthes, 1975 : 69)或者是在涉及回憶的文本后面“補充說明”:“我將回想稱為動作(l’action)——結合歡愉與努力——主體為了尋回一種微致的回憶所領導的動作,不夸大也不炒作:就像是俳句。傳記素(biographème)不是別的,只是一種造作的回想:我借給我喜歡的作者。” (Barthes, 1975 : 113-114)
但言語的烏托邦總歸是理想,在這場拉鋸戰中,不代表情感性沒有占過上風。在極少數的童年敘事里,我們就可以感受到。〈黑板上〉講述了他在學校的時候,有位老師要求同學們將戰亡的親友寫在黑板上,大家寫的都是親戚,只有小巴特寫了父親。“我很難堪,好像有一個過份的標記。” (Barthes, 1975 : 49)
在〈錢〉中,巴特充分表述了身為貧窮的中產階級的窘迫,并表示可能是成年后為享樂主義者的原因。“…在金錢的危機中,人們體會到的,不是悲苦,而是窘迫;這表示:措辭的恐慌,假期的問題,鞋子,教科書,甚至是三餐。”“也許一種自由的補償來自這種可以接受的剝奪(窘迫)…”(Barthes, 1975 : 50)
但是這些情感常常被之后的言論抹殺去,或述或論,或轉移話題,所以情感性在全書中實為吉光片羽。全書中只有一篇短短的記述是完完整整的童年敘事,沒有任何混淆視聽的評述:
“我小的時候,我們住在瑪哈區;這個區有很多在建房子的工地,孩子們都會在工地里玩;為了蓋房子,黏土地上挖了很多很大的坑,有一天我們在個坑里玩,而所有的小孩又爬了上去,除了我,我就是爬不上;在地上,坑上面,他們笑我:你輸了!一個人!看唷!被排擠!(被排擠,不是被排在外,是孤單地待在坑里,被困在廣闊的天空下:逾期喪權的犯人);然后我看到母親跑了過來;她把我拉出來,把我帶離那群孩子,背著那群孩子。”(〈一個童年的記憶〉)(Barthes, 2002 : 697)
一個人在文中的主體性,在童年敘事和親愛的人身上最難以掩藏。這段可以說是碩果僅存的“活生生”的人的形象,也有明顯的自傳特質。我們不僅可以由此推斷巴特為何終其一生害怕公眾活動,也可以看作后來在《明室》中其深表喪母之痛的預示:一條從未間斷過的感情線。
最后,羅蘭巴特在自述中的主體性到底何以形名?也許我們可以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在〈作家作為幻想〉(Barthes,1975 : 81-82)中,巴特寫的似乎是自己年輕時的夢想:要成為作家:要臨摹的不是作品,而是作為,是姿態,是行遍天下的方式,在口袋里放著筆記本,腦中縈繞著句子。
“幻想”(fantasme)一詞,始自佛洛伊德(Freud)的精神分析,拉康也有加以著墨。原意是生理需要所幻想出的場景,引申為各種欲望的延伸。在巴特的作品中,出現的頻率不下于想象物,但是卻是正面的、積極的; 紀德是啟蒙巴特,憧憬寫作的第一位作家。巴特曾專文評論過紀德的日記,但日記中的作家難道不就是作者? “作家”的形象難道就不算是想象物?喜歡巴特的讀者難道不也是期望看到他的作家姿態? 一旦成為了知名作家又怎能避免不被放在鎂光燈下檢視?活動在寫作領域的作家形象,如何能不被社會框架中作者身份重迭或干擾?
也許對于巴特來說,他眼中的紀德的日記的文學性超越了傳記元素: 他看到的是紀德身為作家的美好。幻想跟想象物的區別在于一種原始欲望般的驅動力,呼應了他所贊同的身體哲學,也代表了一個純粹的寫作烏托邦,是超越世俗阻礙的;而“想象物”只能活在各種人為的成見中,所以巴特抗拒他自己的想象物,卻擁抱成為紀德般的幻想。
這正是此書中巴特意圖流露的主體性,浴血鏖兵后所遺留下的形象:既非淪為其所畏懼的“作者”的想象物,亦非不屬于想象物,乃是“作家減去作品”的“巴特”。
(責任編輯:張亙)
[Résumé] L'autobiographie, en tant que genre littéraire, a toutefois évolué à l'époque contemporaine en termes de diversité.Parmi ces courants, la question sur le ? sujet ?, qui joue constamment le r?le primordial dans l'autobiographie, est effectivement la cible du "sujet" à controverse. Il est considéré que l'ouvrage intituléeffectué par Roland Barthes en est l'instigateur, en conduisant à la vague ultérieure de ? Nouveaux romans ?. Dans cet article, nous allons décrypter le mystère de la subjectivité dans cette "autobiographie", malgré son caractère incompréhensible sur le plan littéral, à partir de deux indices : ? affectivité et imaginair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