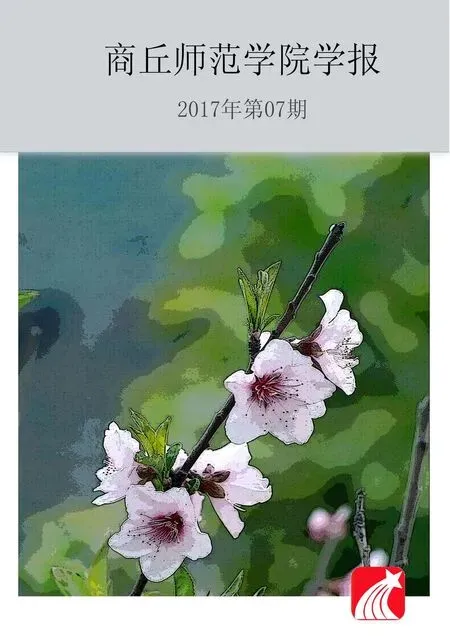《應(yīng)帝王》的體用善惡思想推闡
袁 永 飛
(武漢大學(xué) 哲學(xué)學(xué)院,湖北 武漢430072)
《應(yīng)帝王》的體用善惡思想推闡
袁 永 飛
(武漢大學(xué) 哲學(xué)學(xué)院,湖北 武漢430072)
在解讀《應(yīng)帝王》篇奧義、新意與治道的基礎(chǔ)上,按原論、推論和結(jié)論對(duì)其意蘊(yùn)進(jìn)行探討。它蘊(yùn)涵深刻的體用善惡思想,以至人為主體,對(duì)其體用與善惡作辯證分析,體無善惡之別卻有真?zhèn)沃茫梅稚茞褐麉s見得失之舉。總的論證是以無為體、以虛為用、以天為善、以人為惡,推展其理論訴求為生命道體的本真存在,引領(lǐng)生活器物的實(shí)用發(fā)揮,并由文化圣人傳教與政治王者范導(dǎo)來實(shí)現(xiàn)這種引領(lǐng)。
《莊子》;《應(yīng)帝王》;至人;體用;善惡
目前直接以《莊子·應(yīng)帝王》為題名,進(jìn)行要點(diǎn)闡發(fā)與義理分析的論文主要有三篇,相對(duì)完整地對(duì)此作了細(xì)致連貫的推闡,即:(1)張遠(yuǎn)山的《〈應(yīng)帝王〉的奧義——天人合一的莊學(xué)“至人”論》,主要揭示其“奧義”。文章包括“弁言”“結(jié)語”加七個(gè)分論,共九部分。開頭說“《應(yīng)帝王》是莊學(xué)‘至人’論”,它是《莊子》內(nèi)篇前六篇義理的實(shí)踐“終極目標(biāo)”;“通篇結(jié)構(gòu)”是“前五章言‘王’,第六章點(diǎn)破‘至人’即‘王’,末章言‘帝’”,“‘帝’之本義”是“自然神”、“‘王’之本義”是“貫通天地人‘三籟’的至高理想人格”(如至人、真人、王德之人、素王);六章“寓言”、一章“卮言”,“奧義”藏在“嚙缺、藏仁、日中始、式義、渺茫之鳥、順物自然、無何有之鄉(xiāng)、明王、神巫季咸、至人之用心若鏡、帝”等中,得出“萬物之靈的人類”自始至終面臨“造化真道與文化偽道”的生死較量[1]5-19。(2)梁樞的《〈莊子·應(yīng)帝王〉新論》,文章主要展示其新意。認(rèn)為“《莊子》內(nèi)七篇體現(xiàn)為華夏民族在道家意義上的生命與心靈七步實(shí)踐工夫與義理環(huán)節(jié)”,《應(yīng)帝王》篇“超越了前六步”,“給人類以切時(shí)、切世、切心、切宇宙自然超越性本源立命歸心、價(jià)值上行的新啟示”;它具體分“人的生命和心靈與‘帝王’雙行一體”、人的身心“只有在‘四破’(即破道德障礙,破死的規(guī)章、原則、法度,破天根的‘為天下’的對(duì)政治的執(zhí)著,破對(duì)積極有為的世俗技藝和心術(shù)智巧的執(zhí)著)的超越中才能應(yīng)帝王”、渾沌“被鑿”和“犧牲”的“密義”(即“一體多元”,“和諧與‘破缺’不一不二”)四方面論證;“它的奇特義理”“要求人類的個(gè)體生命能夠領(lǐng)悟內(nèi)外兼修的雙冥雙行”[2]91-95。(3)陳赟的《〈莊子·應(yīng)帝王〉與儒家帝王政治之批判》,文章主要批示其治道。指出,“《應(yīng)帝王》討論外王問題”與《大宗師》“內(nèi)圣問題構(gòu)成對(duì)應(yīng)”,“三個(gè)寓言人物(即嚙缺、王倪、蒲衣子)”推出“兩種政治典范(即王道、帝道)”,“意在思考政治生活的最高可能性”;分“‘有虞氏’與儒家傳統(tǒng)的最高政治理想”、“兩種圣人形象:莊子對(duì)帝道的批判”、“內(nèi)蘊(yùn)在‘藏仁以要人’中的‘人的機(jī)制’”三個(gè)議題,闡發(fā)“仁”解體成“滋養(yǎng)生命的無名的養(yǎng)料”,恢復(fù)“‘不知’的尊嚴(yán)與終極意義”[3]565-572。在此至人奧義、心靈新意與外王治道的論說基礎(chǔ)上,筆者對(duì)其蘊(yùn)涵的“體用善惡”思想進(jìn)行適度闡發(fā),主要從“原論”“推論”和“結(jié)論”求解。
一、原論:圣人之治,明王之治,神巫之說,無為之意
上述三篇論文,第一篇是一字一句一節(jié)一章(正文分七章)地解析其至人奧旨,第二篇大體依據(jù)原典劃作四部分而解讀其生命與心靈的新意,第三篇基本走出文本而從三方面審視其政治的理論訴求。當(dāng)代多數(shù)學(xué)者①總喜歡把此政治訴求看成《應(yīng)帝王》②篇原旨,加以歷史的意義求解與現(xiàn)實(shí)的價(jià)值說明;僅有少數(shù)闡發(fā)其生命與心靈的主旨,認(rèn)為“心靈在超越外在存在形態(tài)之后對(duì)內(nèi)在生命本性的復(fù)歸”[4]252。暫依習(xí)慣性看法,將政治意旨當(dāng)作該篇“原論”,從以下四個(gè)部分對(duì)此進(jìn)行總體梳理,即:一,“嚙缺”到“天下治矣”為“圣人之治”;二,“陽子居”到“游于無有者也”為“明王之治”;三,“鄭有神巫”到“一以是終”為“神巫之說”;四,“無為名尸”到“渾沌死”為“無為之意”。
(一)圣人之治
這一部分由三段對(duì)話組成,即:
嚙缺問于王倪,四問而四不知。嚙缺因躍而大喜,行以告蒲衣子。蒲衣子曰:“而乃今知之乎?有虞氏不及泰氏。有虞氏其猶藏仁以要人,亦得人矣,而未始出于非人。泰氏其臥徐徐,其覺于于;一以己為馬,一以己為牛;其知情信,其德甚真,而未始入于非人。”
肩吾見狂接輿。狂接輿曰:“日中始何以語女?”肩吾曰:“告我君人者以己出經(jīng)式義度人,孰敢不聽而化諸!”狂接輿曰:“是欺德也。其于治天下也,猶涉海鑿河而使蚊負(fù)山也。夫圣人之治也,治外乎?正而后行,確乎能其事者而已矣。且鳥高飛以避矰弋之害,鼷鼠深穴乎神丘之下,以避熏鑿之患,而曾二蟲之無知!”
天根游于殷陽,至蓼水之上,適遭無名人而問焉,曰:“請(qǐng)問為天下。”無名人曰:“去!汝鄙人也,何問之不豫也!予方將與造物者為人,厭則又乘夫莽眇之鳥,以出六極之外,而游無何有之鄉(xiāng),以處壙埌之野。汝又何帛以治天下感予之心為?”又復(fù)問。無名人曰:“汝游心于淡,合氣于漠,順物自然而無容私焉,而天下治矣。”
第一組是“嚙缺”與“蒲衣子”比對(duì)“有虞氏”與“泰氏”(即伏羲氏)的政治作為,蒲衣子說“有虞氏不及泰氏”的實(shí)知、“德真”。第二組是“肩吾”與“狂接輿”闡述“君人”與“圣人”的政治原則,狂接輿認(rèn)為君人“以己出經(jīng)式義度”是“欺德”,“圣人之治”為“正而后行”。第三組是“天根”與“無名人”討論“治天下”的最后根據(jù),無名人得出“順物自然而無容私”。即,泰氏是圣人之治而順物自然、公正大度、惠及眾生,有虞氏是君人之政而用經(jīng)式義度、謀求私利虛名、欺哄百姓。因此,“莊子希望,當(dāng)政的君主能夠效法‘圣人之治’,首先治內(nèi)而非治外,應(yīng)該先正己,然后推及萬物”[5]84。有人對(duì)此圣治的“無為”原則與“自然”根據(jù),作了類似解證,但卻把“明王之治”與“圣人之治”混為一談,說“‘明王’應(yīng)該是以體道之人為榜樣的君王”而“無功、無名、無為”[6]303。下面會(huì)具體講“明王之治”,此處補(bǔ)充老子“圣人之治”(見其《道德經(jīng)》[7]第三章),他說“虛其心,實(shí)其腹”“弱其志,強(qiáng)其骨”,使民“無知無欲”和智者“不敢為”,“為無為”能“無不治”,即虛化心志、實(shí)惠腹骨、排除民眾知欲與智者妄為,按“無為”原則來作為,可大治天下。《應(yīng)帝王》的圣治主旨與此基本一致,不過從旁觀者角度,增設(shè)了“德”與“知”、“圣”與“君”、“內(nèi)”與“外”、“人”與“己”、“身”與“心”、“無為”與“自然”等數(shù)對(duì)對(duì)立性范疇,細(xì)化與深化了其政治的原則依據(jù)與內(nèi)涵要求。
(二)明王之治
“明王之治”是否等同于“圣人之治”呢?此處有“陽子居”(即楊朱)與“老聃”的問答作證,即:
陽子居見老聃,曰:“有人于此,向疾強(qiáng)梁,物徹疏明,學(xué)道不倦。如是者,可比明王乎?”老聃曰:“是于圣人也,胥易技系,勞形怵心者也。且也虎豹之文來田,猿狙之便、執(zhí)嫠之狗來藉。如是者,可比明王乎?”陽子居蹴然曰:“敢問明王之治。”老聃曰:“明王之治:功蓋天下而似不自己,化貸萬物而民弗恃;有莫舉名,使物自喜;立乎不測(cè),而游于無有者也。”
初看其對(duì)話,也會(huì)像上述學(xué)者,相信它們無區(qū)別,除非陽子居“明王”或“明王之治”之“明”是名詞如明慧,或形容詞如明智的;而老聃的“明王之治”是動(dòng)詞,即明達(dá)王者的治國要領(lǐng)。顯然,無憑無據(jù)地說同一段落不同人物的“明”意指有差異,是沒說服力的。若細(xì)讀,會(huì)發(fā)現(xiàn)二人的第一節(jié)對(duì)話中,“學(xué)道”之人是陽子居眼中的“明王”,決非老聃心中的“圣人”或“明王”。陽子居由此追問老聃的明王之治是什么內(nèi)蘊(yùn),老聃從其不居功自傲、無私化育眾生、不貪慕虛名、應(yīng)當(dāng)逍遙自在,闡述其意旨。可見,陽子居口中說的是現(xiàn)實(shí)社會(huì)的明王表現(xiàn),老聃心中設(shè)想的是理想塑造的明王或圣人形象。即站在陽子居的角度看,明王與圣人有別,一個(gè)是現(xiàn)實(shí)政治的權(quán)威人物,另一個(gè)是文化理想的目標(biāo)訴求;按老聃的講法,二者一體、兩個(gè)化身,一個(gè)顯形于現(xiàn)實(shí)生活而悠然自得,一個(gè)隱身于理想世界而無拘無束。若以《莊子·天下》篇補(bǔ)證,當(dāng)時(shí)“天下大亂,賢圣不明,道德不一”,諸子諸侯要“有所明”與“通”、“有所長(zhǎng)”與“全或備”,才明了其“內(nèi)圣外王之道”。這意味著圣與王代表政治或文化社會(huì)的現(xiàn)實(shí)與理想的分裂,需完備內(nèi)圣外王之道來統(tǒng)合圣與王,才有明王的完美出場(chǎng),否則是一廂情愿的政治愿望。基于這種政治現(xiàn)實(shí)與理想無法跨越的距離考量,明王之治實(shí)際蘊(yùn)涵了王者的理想要求,寄托于圣人之治中。
(三)神巫之說
“神巫之說”是明王構(gòu)想的反證,前述論文講“季咸”為“俗王”(即暗王)、“壺子”為“素王”(即圣人),《墨子·非命》[8]談“暴王”愛把人的富貴貧賤、眾寡治亂、生死壽夭看作命中注定,這常表達(dá)人們對(duì)殘酷的政治現(xiàn)實(shí)有兩種極端想法,一種是相信神巫的命運(yùn)測(cè)定,一種是希望圣人的前景規(guī)劃。相對(duì)說,前者裝神弄鬼,嚇唬信眾;后者是理想規(guī)劃,激勵(lì)大眾。此處以一個(gè)完整、具體、形象、生動(dòng)的寓言故事來解說,即:
鄭有神巫曰季咸,知人之死生存亡、禍福壽夭,期以歲月旬日若神。鄭人見之,皆棄而走。列子見之而心醉,歸,以告壺子,曰:“始吾以夫子之道為至矣,則又有至焉者矣。”壺子曰:“吾與汝既其文,未既其實(shí),而固得道與?眾雌而無雄,而又奚卵焉!而以道與世亢,必信,夫故使人得而相女。嘗試與來,以予示之。”明日,列子與之見壺子……壺子曰:“鄉(xiāng)吾示之以未始出吾宗。吾與之虛而委蛇,不知其誰何,因以為弟靡,因以為波流,故逃也。”然后列子自以為未始學(xué)而歸,三年不出,為其妻爨,食豕如食人。于事無與親,雕琢復(fù)樸,塊然獨(dú)以其形立。紛而封哉,一以是終。
它首先講鄭國神巫季咸,有神乎其神、能嚇倒俗人的鬼把戲,迷住學(xué)道之人列子,讓列子懷疑其師壺子的道行沒他高深。接著,壺子為戳穿其鬼把戲,顯示自己高深的道行,讓列子帶季咸給他本人,預(yù)測(cè)生命表現(xiàn)應(yīng)如何進(jìn)展,結(jié)果是四進(jìn)四出都胡說八道、原形畢露。最后,列子認(rèn)可其師壺子的道術(shù)才是真正神鬼莫測(cè),潛心學(xué)道,終有所成。現(xiàn)實(shí)政治社會(huì)中是否有暗王、暴王故弄玄虛,顯示自身高強(qiáng)的本領(lǐng),主宰大眾生活命運(yùn),被有道圣賢識(shí)破而黔驢技窮、貽笑大方呢?歷史上,這樣的俗王事例太多,如秦二世等,我們能像莊子那樣嘲弄俗王的同時(shí),真正反思?jí)刈铀赝醯氖ッ髦朗鞘裁磫幔窟@是總結(jié)圣人無為而治的自然之道的真諦求知。
(四)無為之意
這種自然之道,應(yīng)當(dāng)通過無為之意來破解。此意并非只能意會(huì),借助神悟和寄望奇跡,也可言傳,交流心得與暢談大道。這一部分有兩個(gè)小段,前段說理以明“無為”旨趣,后段敘事以喻“無為”歸路,即:
無為名尸,無為謀府,無為事任,無為知主。體盡無窮,而游無朕。盡其所受于天而無見得,亦虛而已。至人之用心若鏡,不將不迎,應(yīng)而不藏,故能勝物而不傷。
南海之帝為倏,北海之帝為忽,中央之帝為渾沌。倏與忽時(shí)相與遇于渾沌之地,渾沌待之甚善。倏與忽謀報(bào)渾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竅以視聽食息,此獨(dú)無有,嘗試鑿之。”日鑿一竅,七日而渾沌死。
具體細(xì)節(jié)與論證,將在“推論”部分展開,先不鋪張其看法,僅對(duì)前后相關(guān)意旨作一大致疏解。前述“圣人之治”有“德治”(或圣治),優(yōu)越于“法治”(或王治),因順“自然”;其后“明王之治”,出現(xiàn)圣王的理想與現(xiàn)實(shí)二分,強(qiáng)調(diào)“自化”;再后是“人為”(即俗眾誤以為)的“神”(季咸)與“自然”(即天地展示)的“神”(壺子)的“道行”較量,偏重于自然神勝出。這已清楚表明,要確立圣王之治的自然無為精神的指導(dǎo)原則的根本地位。這兩段接應(yīng)這個(gè)無為精神③,首先從“無為”的理論思辨上高度總結(jié)與深刻分析,確保其生命本根的核心地位;然后用“渾沌”的寓言故事,簡(jiǎn)要指明其生活內(nèi)涵與生命歸宿。結(jié)果是,只有無為,才能保證和保障一切事物正常發(fā)生、正當(dāng)作為與合理訴求,否則好心辦壞事、費(fèi)力不討好、弄得兩敗俱傷。由此看無為的本根是什么、它的主體是誰、作用對(duì)象有哪些、功效如何檢測(cè)、命運(yùn)怎樣把握,這是“推論”解答的問題。
總之,明王之治不必贊,圣人之治要自然,神巫之說不可信,無為之意多體驗(yàn)。怎么去體驗(yàn),讓心靈與生命去悟道、證道、修道和行道。
二、推論:以無為體,以虛為用,以天為善,以人為惡
先以至人作《應(yīng)帝王》思想的終極目標(biāo),隨后“原論”以無為作“圣治”的基本原則來統(tǒng)攝“王道”,此處對(duì)至人與無為的本體依據(jù)作深入考察。這是其生命事業(yè)與政治實(shí)踐所形成的規(guī)范系統(tǒng)得以有效建立的精神基礎(chǔ)。此基礎(chǔ)考察是“推論”的主要任務(wù),重點(diǎn)在該篇最后兩段無為之意的說理與敘事中,通過生命本性表征的體用善惡志趣,闡釋其可能意涵。若從宇宙生命本能看,它有體用之別;由其特性講,它有善惡之分。下面按文義分“至人無體”與“善報(bào)惡果”兩議題,推證如下。
(一)至人無體
至人無體,不是說至人沒有自己的本體,而是講人實(shí)現(xiàn)無限后,總以無為本體;就好比現(xiàn)實(shí)事物都是變化的,唯有變是不變或變來變?nèi)ザ际亲冏约海蜻壿嬇袛嗌稀笆恰辈湃恰⑵渌蝗牵蚶硐胄拍钪小罢嫔泼馈辈湃妗⒅辽啤⒅撩蓝渌蝗妗⒉蝗啤⒉蝗馈R部烧f,至人是“人至(或極)”,無體是“體無”(如王弼言的“圣人體無”),因此,“人”的“至”(極限或無限)以“無”為“體”。無是至人與無為的實(shí)踐本體或理論核心,無為是無的作為,并非什么都不做,而是什么都做了。由此可知,生活過程中一切可能實(shí)現(xiàn),也可能失去,最終圓滿是空無其經(jīng)驗(yàn)認(rèn)知內(nèi)涵的生命本真存在。
1.無
“無”是什么?上述是:“無為名尸,無為謀府,無為事任,無為知主。”一般將“無”,理解為否定性副詞或動(dòng)詞,如“絕棄”“不要”④等。就上下文意思講是不錯(cuò)的,但問其為何要“絕棄”或“不要”時(shí),得探索其根本究竟如何。或按古代常用的“者也”表達(dá)形式,也應(yīng)是“無為”做主語,即“無為者名尸也”(其他三句可如此解),不能簡(jiǎn)單憑借現(xiàn)代觀念的想當(dāng)然的語法邏輯,說明“無”是主語、“為”是謂語和“名尸”是賓語。如果無為是無的作為,可意譯此句為“無是名的實(shí)體”(或許它是死了的實(shí)體即尸體,“有”是活著的實(shí)體;《道德經(jīng)》第二章講“有無相生”,有即無,無即有,在終極意義上可互換;黑格爾在絕對(duì)精神意義說“實(shí)體即主體”⑤,正表明此意含)。也可按“形”區(qū)分“有、無”,在具體事物說“有”是“有為”的實(shí)體,在終極命運(yùn)講“無”是“無為”的本體。詹劍峰解析老子哲學(xué)里的“無”有“三義”即“未形的原始物質(zhì)”“虛廓無限的空間”和指稱“無形無象的規(guī)律”,不是“王弼的玄理”“佛家的真如”與“黑格爾的絕對(duì)精神”[9]167。若以自然之道的“體用”看,“無”是“道體”而“有”是“道用”,則“道統(tǒng)有無”是體用自如、圓融無礙,不存在“有無”的絕對(duì)間隔,自然成一片或一體而共用。如此解釋,“無”是“名”的認(rèn)知主體或存在限度,“謀”的生活領(lǐng)域或思想寶庫,“事”的文化任務(wù)或?qū)W術(shù)使命,“知”的精神主旨或意義訴求。“無”作為至人的本體,為其確立存在限度、生活領(lǐng)域、文化任務(wù)與精神訴求。
2.體
至人以無為體,即“體盡無窮,而游無朕。盡其所受乎天而無見得,亦虛而已”。前面講為何以無為體,因?yàn)椤盁o”是其終極根據(jù)而來自“道”,“‘道’的觀念”有“哲學(xué)本體論范疇的性質(zhì)”[10]131,其“道論”“本體論意義”借助“‘道路’、‘途徑’、‘方法’之類的原初意象”[11]57來揭示。此道體超越日常經(jīng)驗(yàn)的局限,無窮無盡、無邊無際、無所不受、無所不得,成無限本體。成中英說,“《逍遙游》《齊物論》《應(yīng)帝王》,含有強(qiáng)烈的本體思想之辯證”,且《應(yīng)帝王》“呈現(xiàn)了本體存在的四個(gè)層面之境界”(即“地文”“天壤”“太沖莫?jiǎng)佟薄安恢湔l何”),是“天地本體(道的本體)和人的本體最終合二為一、彼此相依”[12]68。可見,《應(yīng)帝王》政治群體的理想典范即圣人(或至人)在現(xiàn)實(shí)社會(huì)中,把《逍遙游》理想狀態(tài)的生命整體與《齊物論》實(shí)際狀態(tài)的生活個(gè)體,統(tǒng)攝為天人一體,因應(yīng)萬事萬物的存在與發(fā)展。此以無為體,是否以有為用呢?據(jù)王志楣《論〈莊子〉之“用”》一文的結(jié)語,她認(rèn)為,“莊子整體用的思想”分四個(gè)面向,即“小用”(有限的功利)“有用”或大用(無限的功利)“無用”(無限的存在)“無用之用的大用”(無限的功德),“有用、無用也泯同自然”、內(nèi)蘊(yùn)于心而向外“展現(xiàn)具體靈活之用”⑥。至人的“用”,有別于一般意義上的生活“實(shí)用”與人文“功用”,叫生命“虛用”,即虛已待物而受用無窮;其體“無”用“虛”,即以虛為用而靈動(dòng)無限。這樣,體用才自如、同在、互融、通變,呈現(xiàn)自然之道(或理)與無為之事。
3.至人
至人是自然之道與無為之事的體用圓融的人物形象設(shè)計(jì),如此才會(huì)“至人之用心若鏡,不將不迎,應(yīng)而不藏,故能勝物而不傷”。至人的道體為“無”、道用為“虛”,上已說明,此不贅述;其“道體”與“事用”,下面在“善報(bào)惡果”中細(xì)說。另有,《逍遙游》說“至人無己,神人無功,圣人無名”,《大宗師》說“真人”“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它們比照日常生活中的俗人、常人、眾人、閑人,推出至人與神人、圣人、真人、天人,不局限自己而向所有的事物開放,不居功自傲而把德能全部貢獻(xiàn),不貪圖名利而讓實(shí)惠共同享用,不夸張人心而始終因循天道。至人相對(duì)于“不至人”來說,他是無限的可能存在主體即非常人,不是有限的現(xiàn)實(shí)生活主體即常人。他有神人的變化而不事功,有圣人的明通而不定名,有真人的純樸而不作偽,有天人的寬大而不徇私,有自身的突破而不守舊。他有至德、善言、真知、公正與創(chuàng)新,能為萬物和人類的存在與發(fā)展,提供生命之源、生活之道、生化之機(jī)、生產(chǎn)之具、生態(tài)之美。至人是天然造就的完人,如“中央之帝”(即渾沌),無須有意雕琢其生命,否則,將戕害其本身的正常存在與正當(dāng)發(fā)展。善報(bào)惡果的寓言故事,就表明這個(gè)生命道理。
(二)善報(bào)惡果
如果老子思想蘊(yùn)涵“無體有用”是“道體德用”(圣人之體用),引領(lǐng)孔子的“德體道用”(君子或王者之體用)與墨子的“德體德用”(圣王之體用)⑦;那么,莊子的該篇思想推闡的“無體虛用”是“道體道用”(道用為不得用,無用之大用,是至人之體用),引渡出后來中國道教的人體神用(入世人之體用)和佛教的性體空用(出世人之體用)。即莊子在自然生命的德能與德用上,修正老子思想的“實(shí)”與“有”,變作“虛”與“無”,以此判識(shí)至人的“善惡”是非與“報(bào)果”得失,有別于孟子與荀子⑧從德性與德行的“本心”(或初心)和“本性”(或天性)來分判“善惡”的論證。可以說,至人的生命本體中沒有善惡的區(qū)分,無所謂孟子的“全善”(“習(xí)染”為“惡”)和荀子的“全惡”(“塑造”為“善”),只有在其生活功用中才出現(xiàn)善惡的情狀,渾沌寓言故事的用意即在此。
1.三個(gè)人物說明
該故事的主要人物是:“南海之帝為儵,北海之帝為忽,中央之帝為渾沌。”這三個(gè)人物,有三個(gè)不同的名字即“儵”“忽”“渾沌”,三個(gè)不同的領(lǐng)地即“南海”“北海”和“中央”,卻有一個(gè)共同稱號(hào)即“帝”。前文已解“帝”為“自然神”,不同原典表述的“圣”與“王”;而后世多以“帝王”指稱秦漢以來的“皇帝”,也有以《史記》為據(jù)標(biāo)識(shí)成“五帝”“三王”。就此意含看,“帝”是“圣”與“王”的完美結(jié)合,或自然無為的神圣和合,如此,方統(tǒng)合前面“圣人之治”與“明王之治”,批判“神巫之說”不可信,明達(dá)其“無為之意”的真實(shí)用心。對(duì)此有三方面解讀:一是“自然之現(xiàn)象”說明,如李頤的“有象”“無形”“自然”、成玄英的“有”“無”“非有非無”、陸長(zhǎng)庚的“火德”“水德”“土德”等;二是“人之現(xiàn)象”說解,如林希逸的“渾沌即元?dú)狻?有知識(shí))、陸樹芝的“渾沌——未漓之天真”(有七情)等;三是“歷史之現(xiàn)象”說法,如宣穎講“一渾沌之天下與古今”等[13]290-291。它以自然現(xiàn)象與人類現(xiàn)象所共同表征的現(xiàn)實(shí)生命體悟?yàn)榛A(chǔ),解釋其生活實(shí)體的大致特征,再以歷史現(xiàn)象具體演繹的文化生活過程為構(gòu)造,說明其社會(huì)應(yīng)用的期望效果。
2.兩個(gè)生活故事
這兩個(gè)生活故事的詳情是:“倏與忽時(shí)相遇于渾沌之地,渾沌待之甚善。倏與忽謀報(bào)渾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竅以視聽食息,此獨(dú)無有,嘗試鑿之。’日鑿一竅,七日而渾沌死。”開始是南海之帝“倏”與北海之帝“忽”,在中央之帝“渾沌”的地盤上“相遇”,受到渾沌的善待,感覺不錯(cuò)也心里舒坦,過后仍念念難忘。這是一個(gè)美好開端與幸福過程,成為彼此和諧相處的生活典范。然而,故事的轉(zhuǎn)折性發(fā)展出現(xiàn)了,或者說是另一個(gè)生活故事的開始。儵與忽回到他們的領(lǐng)地后商量,要好好報(bào)答被渾沌善待的生活恩德。該怎么報(bào)答他才好呢?他們的參照標(biāo)準(zhǔn),主要取決于“人”的生活經(jīng)驗(yàn),覺得人有“七竅”,可“視聽食息”,具備多種多樣的生活功能,值得各路“神仙”特別向往,一定能夠改善渾沌的現(xiàn)有生活品質(zhì)。打定主意后,他們就采取實(shí)際行動(dòng),花費(fèi)了七天工夫,為渾沌鑿七竅。結(jié)果,他們鑿?fù)戤叄瑴嗐缢懒恕_@是一個(gè)悲慘的結(jié)局與一個(gè)意外的結(jié)果。
3.一個(gè)意外結(jié)果的反思
這兩個(gè)故事的發(fā)生、發(fā)展與結(jié)局,到底說明了什么問題呢?發(fā)生很平常,好好招待來客是人之常情;發(fā)展極正常,受人恩澤當(dāng)回報(bào),即使不是涌泉對(duì)滴水的感謝,也屬于禮尚往來而無可厚非;結(jié)局太意外,善待與善報(bào)是惡因與惡果,有心成全竟變作十足破壞。這樣虧待了好心也白費(fèi)了力氣,兩種不同的生活對(duì)待導(dǎo)致災(zāi)難性的生命后果,問題究竟出在哪兒呢?他們以人的能用代替了帝的德用,不知道此能用(或德用)對(duì)于帝不能用,帝自有其道用,違背其道將事(用)與愿違。有學(xué)者通過“南、北、中央、時(shí)”的“時(shí)空字眼”,“倏、忽、渾沌”的“擬人化字眼”與“待之甚善”“謀報(bào)”的“倫理、認(rèn)知字眼”,說“中央”是“關(guān)鍵字眼”,揭示“渾沌”“三特性”,即“‘渾沌即吾’,以隱喻‘去主體性’”,“‘渾沌即土’,以隱喻‘包容性’”,“‘渾沌即風(fēng)(云)’,以隱喻‘不確定性’(或無限可能性)”[14]。也有說“莊子‘性惡’思想”不是荀子“性惡論”,但它“對(duì)人性中內(nèi)在的黑暗傾向有真實(shí)的觀察”且“深度”超過荀子性惡論,《莊子》“內(nèi)篇沒有說到‘(人)性’概念,而外篇有若干涉及”[15]5。這兩個(gè)故事難道沒有暗示人性惡的可能與善的根源?它是以人性善(即社會(huì)功用)來造就“神性惡”(即自然存在)的悲慘結(jié)局!在一定意義上反過來看,它以主體人(或人)的“惡”烘托出自然神(或天)的“善”,因而要去除人的“主體性”自覺以伸張自然物(或客觀物)的生命無限包容與可能。或許,渾沌之死也是一種生命的包容與可能,渾沌對(duì)“惡果”的最后包容及儵、忽對(duì)“善待”的重構(gòu)可能,從而獲得整體的無限與永恒。
三、結(jié)論:生命道體,生活實(shí)用,文化德性,政治功效
結(jié)論是,《應(yīng)帝王》篇的最后兩小段,蘊(yùn)涵莊子深刻的體用善惡思想,它以至人為主體,對(duì)其體用與善惡思想作辯證分析,體(此指生命本體或道體)無善惡之別卻有真?zhèn)沃茫?此指人文功用或道用)分善惡之果卻見得失之舉。總的論證是,以無為體,以虛為用,以天為善,以人為惡。即“無”的自然生命之道體,生發(fā)“有”的社會(huì)生活之實(shí)體,再由“有”的社會(huì)生活之實(shí)體,區(qū)分“虛”與“實(shí)”的人文歷史之功用;以此虛實(shí)相結(jié)合,才能滿足人類社會(huì)生活的各種意義訴求。由此可說,善惡狀況是在社會(huì)生活實(shí)體的“用”上發(fā)生的,在其“體”上本無善惡而可善可惡,由于太執(zhí)著人類的“實(shí)用”而求取知覺限定的生活功利,徹底忘記宇宙的“虛用”以護(hù)衛(wèi)自然無限的生命可能。就此神圣意義的“天”,呈現(xiàn)生命的全體,確立生活的“善”及現(xiàn)實(shí)社會(huì)的公正;相比世俗生活的“人”,看重經(jīng)驗(yàn)知覺與享用,由其“德能”與“德用”,彰顯“惡”的存在與后果,進(jìn)而推出:“人王”效法“天帝”,成至人;“天帝”取法“人王”,成不至人。這是“無為”的自然實(shí)踐與“渾沌”的人為悲劇的緣由所在。此推論可展開為二:一是“至人無體”,對(duì)比《逍遙游》“至人無己”,解為沒有個(gè)體的極端執(zhí)著于長(zhǎng)生,只有整體的無限包容于全生,共推群體的美好事業(yè)于相生。二是講善報(bào)惡果,參照《養(yǎng)生主》《人間世》《德充符》《大宗師》等“善生惡死”觀念,不貪求個(gè)體生命的至善完美,也不厭惡群體生活的特殊現(xiàn)狀,贏得整體共存的祥和安樂。
歸納其要旨,大致可說其論證的總體進(jìn)路:首先確認(rèn)宇宙生命的道體即帝或至人,他是能通達(dá)一切的自然神,內(nèi)體是無,外用是虛,行動(dòng)是無為,結(jié)局是圓滿,無善惡分辨,只有本真呈現(xiàn)。其次,對(duì)比人類生活的道用即民或不至人,他是特定生活條件下的社會(huì)人,內(nèi)體是心,外用是身,行為是有為,結(jié)果是殘缺,進(jìn)行善惡劃分,喪失原初存在。再次,要改造這些社會(huì)人,進(jìn)入善的世界,寄望文化生命的德性培養(yǎng)成就即圣人。他是“人文圣”即人文塑造的生命榜樣,他效法自然神的天道,其內(nèi)體是神,外用是人,方法是文化,目標(biāo)是生命,希望清除惡的干擾,回歸真的人生。最后,“人文圣”的生活理想目標(biāo),要“行政王”(即人間權(quán)威的執(zhí)行者)來帶領(lǐng)大家實(shí)現(xiàn)它,他必須借助制度規(guī)范體系來懲惡揚(yáng)善,取得必要的政治功效。這個(gè)規(guī)范體系的基本依據(jù)在“人文圣”心中,不在社會(huì)人手中。因此,其內(nèi)體是圣,外用是民,手段是制度,目的是范導(dǎo),實(shí)際抑制惡的表現(xiàn),全面宣傳善的理念。這與西方或阿拉伯世界的人格神上帝或真主,統(tǒng)攝眾生向善的目標(biāo)進(jìn)發(fā)略有不同,但在理想信念上對(duì)人的主觀能動(dòng)性的徹底消解應(yīng)當(dāng)一致;在現(xiàn)實(shí)生活中更推崇自然無為的生命理念而非歷史文化塑造的自由無限的精神主體。
總之,在解讀《應(yīng)帝王》篇奧義、新意和治道的基礎(chǔ)上,按原論、推論和結(jié)論對(duì)其意蘊(yùn)進(jìn)行探討。它蘊(yùn)涵深刻的體用善惡思想,以至人為主體,對(duì)其體用與善惡作辯證分析,體無善惡之別卻有真?zhèn)沃茫梅稚茞褐麉s見得失之舉。總的論證是,以無為體、以虛為用、以天為善、以人為惡,推展其理論訴求為生命道體的本真存在,引領(lǐng)生活器物的實(shí)用發(fā)揮,并由文化圣人傳教與政治王者范導(dǎo)來實(shí)現(xiàn)這種引領(lǐng)。
注 釋:
①“本篇是論帝王應(yīng)當(dāng)怎樣從政的問題”,多就“治功”說(陸永品:《莊子通釋》,修訂版,中國社會(huì)科學(xué)出版社2006年版,第103頁);它“著重回答帝王治天下的問題,集中反映了作者的無為政治論”(邵漢明:《名家講解〈莊子〉》,長(zhǎng)春出版社2007年版,第81頁);“本篇主要講帝王如何治理天下”(張松輝:《莊子譯注與解析》,中華書局2011年版,第147頁);它“回答帝王如何治天下的問題”,由“道家哲學(xué)本體論引申而來的政治論”(李乃龍:《莊子分解》,廣西師范大學(xué)出版社2012年第2版,第115頁)。
②《應(yīng)帝王》篇所引原文資料,均來自崔大華:《莊子歧解》,中華書局2012年版。不再單獨(dú)每字每句標(biāo)識(shí),也不分段標(biāo)舉,皆在第268-291頁。另《莊子》其他篇的零星引述,只標(biāo)篇名。
③對(duì)此的看法有:上段“要求君主排除名利、智巧之心,不存在個(gè)人成見,一切順應(yīng)自然”,下段說“人為的各種政治措施破壞了人們的純樸天性和幸福生活,表明了莊子順物自然、無為而治的政治主張”(張松輝:《莊子譯注與解析》,中華書局2011年版,第159-160頁)。前段“對(duì)于什么是道,什么是德,進(jìn)行了精辟凝練的概括……道是自然,是無法感知的抽象的虛無……德是道的外在表現(xiàn),道的外化,是不益不損,完全地自然地反映道的物像”,后段對(duì)“道的根本性質(zhì),虛無的抽象性的絕妙表達(dá)”(左孝彰:《莊子還真》,天津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17頁)。上文用“六個(gè)‘無’字,五個(gè)‘不’字,一個(gè)‘虛’字,準(zhǔn)確地把天道虛無的本質(zhì)、修道者以虛無為旨的意思表達(dá)了出來”,下文“鑿死渾沌,是有為的惡果”(李乃龍:《莊子分解》,廣西師范大學(xué)出版社2012年版,第123-124頁)。都忽視具體生命的本質(zhì)內(nèi)涵的尋覓,較看重抽象思維(或人文)的本質(zhì)形式的規(guī)定,從政治或生活的表征來訴求文化的期望結(jié)果,實(shí)際歪曲生命的本有事業(yè)。
④以“無為名尸”為例,有譯作“絕棄求名的心思”(見陳鼓應(yīng):《莊子今注今譯》,中華書局1999年版,第228頁),有譯成“不要求名譽(yù)”(見安繼民,高秀昌注譯:《莊子》,中州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91頁)。
⑤“黑格爾的‘實(shí)體即主體’的思想是批判吸收德國古典哲學(xué)的先行者康德、費(fèi)希特、謝林的哲學(xué)思想而形成的。”(見陶莉:《論黑格爾“實(shí)體即主體”的思想》,《四川大學(xué)學(xué)報(bào)(哲學(xué)社會(huì)科學(xué)版)》1997年第1期,第43頁。)
⑥該論文取自陳鼓應(yīng)主編:《道家文化研究·第22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2007年版,第523頁。已對(duì)其“繁體”化簡(jiǎn),并作簡(jiǎn)釋。
⑦大體論證,可參閱袁永飛的《中國體用關(guān)系內(nèi)涵的辨析和認(rèn)知》,收錄在何錫蓉等主編:《價(jià)值與文化》,上海社會(huì)科學(xué)院出版社2013年版。
⑧此可參閱朱熹《四書章句集注》(中華書局2012年第2版)的“孟子部分”和王先謙《荀子集解》(沈嘯寰、王星賢點(diǎn)校,中華書局1988年版)的相關(guān)章節(jié)。
[1]張遠(yuǎn)山.《應(yīng)帝王》奧義——天人合一的莊學(xué)“至人”論[J].社會(huì)科學(xué)論壇(學(xué)術(shù)評(píng)論卷),2007(9).
[2]梁樞.《莊子·應(yīng)帝王》新論[J].長(zhǎng)安大學(xué)學(xué)報(bào)(社會(huì)科學(xué)版),2012(3).
[3]陳赟.《莊子·應(yīng)帝王》與儒家帝王政治之批判[J].安徽師范大學(xué)學(xué)報(bào)(人文社會(huì)科學(xué)版),2013( 5).
[4]李振綱.大生命視域下的莊子哲學(xué)[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5]萬勇華.莊子的理想世界[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
[6]韓林合.虛己以游世:《莊子》哲學(xué)研究[M].北京: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2006.
[7](魏)王弼,注.樓宇烈,校釋.老子道德經(jīng)注校釋[M].北京:中華書局,2008.
[8]孫中原.墨子解讀[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xué)出版社,2013.
[9]詹劍峰.老子其人其書及其道論[M].武漢:華中師范大學(xué)出版社,2006.
[10]崔大華.莊學(xué)研究——中國哲學(xué)一個(gè)觀念淵源的歷史考察[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
[11]徐克謙.莊子哲學(xué)新探——道·言·自由與美[M].北京:中華書局,2005.
[12]成中英.《莊子》內(nèi)篇中的本體辯證哲學(xué)[J].華中師范大學(xué)學(xué)報(bào)(人文社會(huì)科學(xué)版),2014(6).
[13]崔大華.莊子歧解[M].北京:中華書局,2012.
[14]劉康德.“渾沌”三性——《莊子》“渾沌”說[J].清華大學(xué)學(xué)報(bào)(哲學(xué)社會(huì)科學(xué)版),2014(2).
[15]顏世安.莊子性惡思想探討[J].中國哲學(xué)史,2009(4).
【責(zé)任編輯:高建立】
2017-03-21
袁永飛(1976—),男,貴州松桃人,武漢大學(xué)博士生,河南省社會(huì)科學(xué)院哲學(xué)與宗教研究所助理研究員,主要從事先秦諸子哲學(xué)與道家思想文化研究。
B233.5
A
1672-3600(2017)07-0011-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