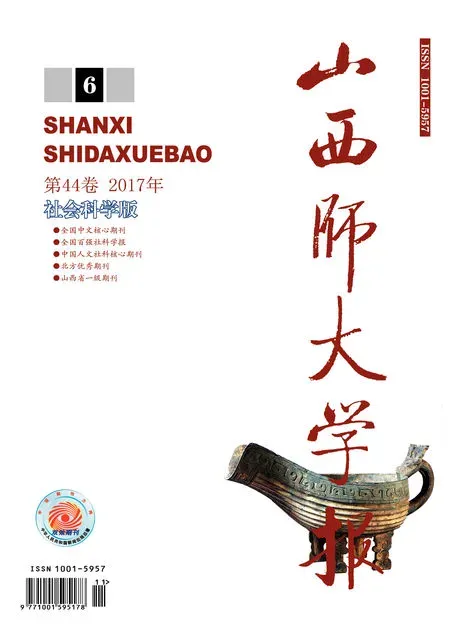政制·宗教·教育
——約翰·亞當斯論政治與道德的關系
李 浩
(清華大學 馬克思主義學院,北京 100084)
以賽亞·伯林認為馬基雅維利將政治學從倫理學中解脫出來并揭示道德與政治乃是彼此沖突的兩個獨立王國。此說流傳甚廣,幾乎為不刊之論。然而,政治與道德果能截然分開么?“在美國國父當中,約翰·亞當斯是唯一真的去閱讀和嚴肅對待馬基雅維利思想的人。”不僅如此,亞當斯“似乎還認識到,存在著兩個馬基雅維利:作為古典共和制度復興者的馬基雅維利,以及作為邪惡教師的馬基雅維利”[1]。那么約翰·亞當斯是如何看待馬基雅維利的教導,他又是怎樣處理政治與道德之間的關系的呢?
一
作為美國的國父之一,約翰·亞當斯為當時所重的原因在于他對美國立國的兩大貢獻:其一是他的《為美國憲法辯護》,該書是他的政治思想的集中體現,系統地闡述了他為馬薩諸塞州起草憲法的政治學原理,曾深刻影響了1787年的制憲會議,并對美國政治制度的形成具有奠基意義;其二是他在美國獨立戰爭期間游說法國、荷蘭為美國爭取戰爭貸款,極大地支持了美國人民的抗英斗爭。約翰·亞當斯的政治思想與亞里士多德、波利比烏斯、西塞羅、馬基雅維利等共和主義思想家一脈相承且有所發展,他明確提出共和政體的目標是維護公民自由與公共福祉,共和政體的本質是法治,而法治的實現依賴于政治體制的平衡,具體而言包括兩項原則,分別是主權在民原則和權力制衡原則。
亞當斯認為國家的權力來自于人民,但受地點、時間的限制,全部人民集體行使國家權力的直接民主制度已經不適用。與馬基雅維利一致,亞當斯亦認為歷史表明人民并非是同一化的整體,他們總是可以區分為精英和大眾、少數和多數。通過消除精英與大眾、少數與多數之區分是不可能的,知識與科學的進步必然同時會帶來新的差異和不平等,唯一可行的方法就是通過科學的制度設計實現社會發展的平衡與穩定。平衡政體的一般原理是立法部門的代表應當既有精英階層的代表,也包括普通大眾的代表。同時,為了避免精英階層影響大眾的判斷以及大眾對精英意志的“綁架”,立法部門應當區分為“元老院”和“平民院”,由“平民院”提出立法意見,“元老院”審議決定通過還是駁回。考慮到兩院之間的爭議可能存在無法決斷而導致沖突的情況,亞當斯認為立法部門應當還包括第三個“分支”,即“執政官”。“執政官”的作用在于調節兩院的矛盾,在關鍵時刻以公共福祉為最高目標做出最后決定,并視兩院之間的力量變化而采取必要措施以維持均勢。
約翰·亞當斯接受并發展了馬基雅維利有關共和政體的基本觀點,而且他對古典共和主義的美德教條也沒有多少信念,他在給阿碧蓋爾的信中寫道:“對現代政治家來說,踐行和主張古代的道德與禮儀,顯得既愚蠢又矯情。美德、愛國和對我們同胞的熱愛是無法為今天的人所關注的。他們的注意力集中在紙牌、賽馬、穿著、歌舞等事物上,集中在對漂亮女人的感情上,集中于對那些有權有勢的人物的阿諛奉承上。”[2]6而且古典共和國的貴族都是一些專制者和高利貸盤剝者,他們性格驕傲、強橫、野蠻,沒有什么美德可言,財富和奢靡成為古典共和國的“噩夢”,卻很少有貴族具有質樸、節儉、虔誠的品德。[3]385他不太相信古典共和國的美德能夠使大多數人在權衡公共利益與自己的私利時會選擇犧牲個人利益,因此只靠愛國主義的宣教根本無法制約商業腐敗和人性貪婪。商業腐敗和財富帶來的奢侈之風亦將腐蝕節制和勤勞等品質,并侵蝕立法權、執行權以至整個國家和人民,導致共和政體衰敗。[4]對此,他舉例指出,“商業、奢侈以及貪婪摧毀了每個共和政體。英格蘭和法蘭西的共和實驗沒有一個超過12年。英格蘭共和國從1640年到1660年實際處在一連串的君主‘保護’之下,皮姆(Pym)、漢普頓(Hampden)、費爾法克斯(Fairfax)、或克倫威爾(Cromwell),而法蘭西共和國一樣是在米拉波(Mirabeau)、布里所(Brissot)、丹東(Danton)、羅伯斯庇爾(Robespierre)等“庇護”之下直到拿破侖皇帝。最近,唯利是圖的精神又成功摧毀了荷蘭、瑞士和威尼斯等共和國。”[5]600
1787年美國聯邦政府建立,經過華盛頓、亞當斯、杰斐遜、麥迪遜等總統之后,聯邦憲法所確立的平衡政體被進一步塑造和完善,并逐漸展現出它的一些優勢,同時亞當斯發現在實際政治運行過程中產生了一些對平衡政體構成破壞的因素。他注意到在美國政制所確立起的平衡機制的背后,權力漸漸集中于一些核心力量的手中,選舉的結果實際上在選舉之前已經被“國會的核心成員、州核心成員、鎮核心成員、城市核心成員、選區核心成員、地方行政區核心成員、宗教核心成員”組成的貴族性的委員會所安排,來自于上述小集團的腐敗往往導致為了少數人利益而犧牲多數人利益,對社會道德和公民自由構成威脅,并破壞政府機構之間以及機構內部的平衡。
基于以上考慮,亞當斯認為國家的偉大、繁榮和幸福不能只靠法治——平衡政體和古典共和主義的美德,還應當充分發揮宗教的作用。在1798年給賓夕法尼亞州迪金森大學學生的信中,他說道:“你們信任我是科學、自由和宗教的守護者使我感動。科學、自由和宗教是上帝對人類最高級的祝福,三者是不可分的。只有她們共同發揮作用,社會才能變得偉大、繁榮和幸福。”[5]205他認為良好的道德風俗的形成需要依靠宗教的力量,宗教對一個共和制國家非常重要。“由宗教信仰神圣化的和鼓舞的道德習慣是維護國家聯合的黏合劑,是人民互相信賴的基礎,也是人民與政府互信的基礎。”[5]206—207事實上,早在法國大革命之前,亞當斯就認為法國不可能建立起“共和國”,革命注定會走向失敗。其理由便是“一個三千萬無神論者的國家的命運令人擔憂”,“激進分子和煽動者會成為主導者,法國人最終將‘沒有平等的法律,沒有個人自由,沒有財產權,沒有生命權’”。[6]255—256而更為深層次的原因在于“沒有政府能夠完全有能力制衡人的過度的情感,特別是與失去宗教與道德約束的情感相抗衡,貪婪、野心、報復、莽撞等情感將會破壞憲法的強有力的束縛,就如同巨鯨沖破羅網一般”[5]229。
他所秉持的自然神啟哲學認為,宗教對道德風俗的積極意義在于宗教能夠調節個人的理性。歐洲在宗教改革之后,人們普遍相信上帝賦予個人理性,使人無需通過教會便可以認識客觀自然界與人類社會的真理。理性是人類能夠決定何為正確的主要工具,因而理性便可成為個人的道德律。但是,亞當斯對此持保守意見。他注意到盡管理性使人民認識到應當過一種更文明的生活,生命的主要事業不是獲得財富、榮譽和地位,而是追求真正的和永久的卓越,但抽象的理性能力也能夠為罪惡作辯護。[7]21他不贊同對理性的無限的信任,并認為正是這種缺少宗教調節的理性在法國革命當中造成對集體意志的崇拜和信仰,最終導致社會動蕩和無序。亞當斯相信,真理和道德源于個人對上帝的信仰,而不是絕對的理性能力,決定公正和良善的是人心與上帝之間的關系。
因此,要建立共和國,維護平衡政體,需要人民信奉并踐行清教的精神,通過培養虔誠、節制的品德來克服人本身在過度的情感方面的弱點,同時還要有堅定信念與氣概反對任何形式、規模的暴政,以及與世俗的腐敗、奢侈現象做斗爭。可以發現,亞當斯接受了馬基雅維利對政制與人性的基本判斷,并在執行權與立法權的關系問題上發展了他的共和政體理論。與馬基雅維利不同的是,亞當斯重視宗教對形成人民之間良好關系、對培養共和國的道德風俗習慣以及對維持平衡政體的穩定的價值。
二
在亞當斯的思想當中,政治與道德面對著共同的“質料”即人性,在政治當中“人類不適宜掌握無限制的權力,更多的是因為其軟弱而不是其邪惡”[8]406。因此對政治制度的設計需要與人性的構成相適宜,通過制度的引導和約束使構成人性的基本的情感可以為公共利益服務。那么亞當斯的人性觀是怎樣的?亞當斯認為人類最初在未開化的狀態中是群居性的,隨著文明的進步這種群居的社會屬性并沒有完全改變。自然條件使人們結成社團,并塑造了人類的情感、欲望和偏好,賦予他們各種各樣的才能以便于他們可以謀求自身之生存,同時也能夠使他們在社會關系中有益于他人。而在構成人性的情感中最為基本的和顯著的是追求榮譽的情感,即渴望得到同伴的注意、尊重、贊美、熱愛和欣賞。“無論男人、女人或孩童,無論年老或者年少,富有或貧窮,高或矮,聰明或愚蠢,無知還是博學,每個人都強烈地受此情感所驅使,渴望被和他有關的人所看到、聽到、談論到,渴望被認可和尊重。”[9]232—233這種追求榮譽的情感使得人們熱衷于和其朋友或敵人相比較,因為他渴望比別人得到更多的關注和尊敬。當其促使個體通過勤奮追求真理,踐行道德來獲得榮譽時,它便可以被稱為是一種良性的競爭或努力超越的行為;當其促使個體只顧通過獲得權力來贏得榮譽時,這種情感就應當被稱作“野心”。亞當斯進而指出,追求榮譽的情感往往使人們羨慕超過自己的人,羨慕之情足夠強烈亦會使它的主人奮起努力,后來居上。但此羨慕之情太強也會變成嫉妒之意,滋長虛榮的情感。事實上,人類歷史乃是構成人性基本的情感的運轉和發揮作用的簡單過程,所有的美德、惡習以及人生中的幸福和痛苦皆源自此情感及其變種。[9]233—234滿足衣食住行并不需要太多的物質,人們之所以追求更多的財富不是為了仁愛或效用的目的,而是源于其對榮耀的渴望。[9]237—240因為財富能夠給人們帶來更多的關注和更多的尊重,滿足其驕傲的虛榮心。
以此為基礎,亞當斯判斷善與惡在人性當中的動因是一樣的,不應對人性本身強分善惡,在現實當中,往往是人性中的軟弱而非邪惡導致了最終的惡果。他說:“沒有人不希望比他人更卓越且被他人所注意,這種情感深植于人的靈魂之中。當這種情感受到良好的指引,它便是個人幸福和公共繁榮的本源,而當其走上歧途則會制造個人不幸和公共災難;故而指引其朝向正確的目標是個人努力、公共教育、國家制定政策的目標和職責。”[9]241因爭奪榮譽而引起的沖突以及種種不良之情況,需要智慧和道德來調節,“策略是控制這種情感但不是完全根除它們。它們對于生活、教育、社會是最為重要的,不僅不應被消滅反而應該滿足它和鼓勵它并引導其朝向道德發展。”[9]246
智慧和道德的養成需要知識的普遍傳播。1765年亞當斯發表了他的第一部政治著作《論教會法與封建法》。在這篇文章中,亞當斯指出封建法與教會法所導致的專制體系使人變得無知和愚昧,而無知和愚昧又反過來助長了專制的暴虐。教會與封建制度兩大體系的聯盟使人民的意識在被壓迫中深刻地烙上了盲目服從統治的印記。只有知識能夠幫助人民意識到沒有光明的塵世和時代的黑暗,知識越在人民當中傳播和增長,教會和封建統治者的力量就越衰弱;人民越不能容忍不正當的統治,他們同封建和教會之間聯盟的斗爭就越劇烈。因為知識的力量最終將匯聚成對自由的熱愛,所以亞當斯主張每個人都要去閱讀、學習、演說和寫作,從而爭取自由,反抗暴政。
在亞當斯看來,知識尤其是有關政治科學的知識如果得到普及,使大多數人都關心國家的權力運行,關心自己的政治權利,那么共和國的腐敗便可獲得一種有動力的抵制。因為隨著知識的增加,人民對國家主權或政治權利的關心也會隨之增長,“知識增加越多對民主的折磨和刺激也越多,除非將民主看作是與西印度的黑種人、蘇格蘭和英格蘭的運煤工人、荷蘭的泥炭工人以及巴黎和倫敦夜色中的站街女有關的事務(因為他們對政治權利的要求最少),否則國家的政治制度必須考慮滿足人民的政治權利。”[9]516基于此,他主張共和國有義務使知識在人民當中傳播,并且激勵人民應當帶著高尚的意識做自由翁;引導他們的榮譽感促進有益的情感、才能、禮儀以及良好的道德的形成。“如果政府能夠通過在人民當中傳播知識,激發社會的高尚情操,使普通大眾變得勇敢和有進取心,那么這類品質將會使他們明智、勤勞、節儉,而且他們將會逐漸變得更加優雅、堅毅、富于事業心。如果將這樣的國家與專制國家相比較,人民將會感覺是生活在天國一般。”[8]199—200
為此,亞當斯認為政府需要將國民教育作為一項長期的計劃*“施特勞斯學派第三代弟子托馬斯·潘格爾在其《現代共和主義的精神——美國建國者的道德觀與洛克的哲學》一書中分析美國建國者對教育問題的看法時指出,“在建國之后,除了華盛頓、麥迪遜、拉什和杰斐遜以外,其他的建國者都避而不談教育的本質,而這個問題卻是古典共和主義政治理論的核心主題。”其實這些名字當中還應加入約翰·亞當斯,亞當斯在1780年馬薩諸塞憲法草案中,專門有一章是對共和國教育機構與文化事業的說明和規定。見霍偉岸:《對美國制憲者的一種政治思想解讀》,高全喜主編:《從古典思想到現代政制:關于哲學、政治與法律的講演》,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年,第405頁。有關亞當斯憲法草案對教育、文化的規定,See Works of John Adams, Vol.4.pp.257—259.,“在所有的政府計劃中有兩條是必不可少的:其一是制定一些為永久保護議員的公平機會的規章法令;其二是國民在知識和道德方面接受教育。”[8]209只有普遍的國民教育能夠使人民學會運用理性控制自身情感的弱點,提高道德水平并增長有關政治的知識。對于當時美國的教育,亞當斯仍有許多不滿之處。他認為早年到美洲建立殖民地的人們,特別是其中的領導者,包括一些教士和普通信徒都富于見識和學識。他們當中很多人對古希臘和古羅馬的歷史學家、演說家、詩人以及哲學家都非常熟悉,而且其中一些人當年留下的個人小型圖書館依舊保留著,這些書卷里儲藏著最為開明時代的和民族的智慧,但是“如今他們的子孫雖然在歐洲的大學接受教育,卻幾乎無法閱讀其中的文字”[10]451,同時他也注意到貴族和精英對教育、知識的壟斷也是造成無知、愚昧的主要原因,因此只有興辦更加普遍的國民教育才能使人民擺脫無知和愚昧。他認為單獨依靠個人的力量只能建立少許學校,在全國也只能建立少數大學,而這些資源對于全民教育是遠遠不夠的,必須依賴國家的力量通過立法來推行教育,國家應當重視對平民的教育,平民的孩子與精英的孩子一樣都需要接受教育才能為公共服務。他說:“有關年輕人的,尤其是有關下層人民文化教育的立法,對幫助他們變得更加仁義和淳厚是非常明智和有效的,為了實現這個目的,再多的花費也是不過分的。而反對奢侈浪費的法律即使不能使人民變得更加明智和有道德,也能極大地促進他們的幸福。”[8]199“教育的普及應當不僅止于富人和貴族的孩子,而是應當遍及每個階層,包括最下層和最貧窮的人。此外,還需要考慮將學校以適當的距離安置,以便每所學校能夠獲得平衡的公共開支。”[9]168
亞當斯還發現在共和政體下,教育不僅是國家政策的重要的一部分,而且由于人民的參與使教育事業得到更加普遍的推行。但是在所有簡單政體下教育從來都不是普遍的,“在君主制下,少數人即那些可能成為統治者的人接受教育,而普通大眾則處于蒙昧無知的狀態;在貴族制下,貴族可以接受教育但是大眾則不然。所以在任何自由政府之下,知識和教育應當是全體人民的事業,應當得到普及。”[9]198托克維爾在《論美國的民主》中說道:“在馬薩諸塞,公共行政的大權掌握在鄉鎮手里。鄉鎮是人們的利益和依戀的集合中心。但越往南方諸州走去,鄉鎮便不再是這樣的中心了。在這些州里,教育還不太普及,所以培養出來的人才不多,勝任行政工作的人較少。”[11]89這段話可以為亞當斯對教育與政制之間關系的判斷提供佐證。即越是在地區狹小、人口越少、教育越普及的地方,民主制就越有可能實行得良好,而越是面積廣大、人口眾多、教育普及程度的差別也就越大,建立平衡政體就越必要。因為在面積較小的地區實行民主制容易實現平衡,而在面積較大和情況復雜的地區也采用簡單民主制,平衡就不容易實現。
因此,亞當斯的教育思想與他對政治制度的思考有關,教育與宗教相似,都是維持平衡政體、構建自由政府的重要條件。“教育理論與政治科學相比較,二者都可以歸納為同一條簡單的原理,即找到如何更加有效地指引、控制和管理人性當中的競爭意識和勃勃野心的途徑”[9]247,“與洛克相似,亞當斯是要在對自然和人性的檢視的基礎上建立起一種指示性的倫理學”。[7]17在1786年給薩斯菲爾德的信中他說:“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嗜好,我的嗜好就是看著美國成長為一個自由的國度,展望在兩百到三百萬自由民當中沒有一個貴族和國王。你說這是不可能的。如果在這點上我是與你一致的話,我仍然要說讓我們盡我們的可能去嘗試保護我們的平等。一個更好的教育體系有可能保護大眾免于由于混淆了正確與錯誤、道德與罪惡之間的自然區別而引起的社會偏見所帶來的人為的不平等。”[5]546
三
綜上,亞當斯承認馬基雅維利對人性的基本判斷,但他并不認為政治與道德無涉(意味著他并沒有放棄政治對道德的追求),他認識到近代政治科學是隨著文藝復興以來的科學的研究方法和各種知識的進步而興起,倫理學也隨著經院哲學的衰落和宗教改革而進步,可以說科學與宗教、道德是并行不悖的。丹皮爾在描寫達芬奇時說道:“他自己的哲學好像是唯心主義的泛神論。從這個觀點出發,他看見了宇宙活生生的精神。但他又抱著思想家的持平態度,看到不相干的惡下面的善,接受了基本的基督教義,作為他內在的精神生活的可見的外在形式。”“當時的一切跡象好像都在說明就要出現一個新的無所不包的天主教,既準許人們虔誠地信仰基本信條,也準許人們保持思想自由。”[12]118因此,時代的發展和科學的進步不僅推動著政治和政治學向前發展,同時也在呼喚新的道德規范與價值體系。在亞當斯那里,新的道德規范和價值體系是清教信仰和自由精神。而能夠確立合理的政治與新的道德規范之間的關系的是平衡政體、宗教和普遍的國民教育。亞當斯確信平衡政體對知識與教育的普及有許多助益,而宗教與文化知識對品德的促進比起頭銜、榮譽、武力更能夠成為政府的支柱。知識與道德的增長會使人民更加獨立且不易再被蒙騙,同時這種增長也是未來社會進步的必然路徑。“只有人民都受到良好的教育,他們才不會輕易相信對共和制的詆毀,他們才會熱愛平衡政體,明了平衡政體制約著人的情感防止其走向過度,而公民自由只有通過他們自己頻繁而自由地參與選舉才能得到最好的保護。”[9]422—424
人類在進入現代社會之前政治與道德常常處于政治的道德化與道德的政治化的狀態,政治與道德皆是維護統治的工具,其自身的價值被異化了。亞當斯實則認為二者合理的關系應當是政治與道德互不相害,就政治而言,平衡政體的設計為宗教信仰和思想文化自由奠定法治基礎,通過立法推進普遍的國民教育,增進人民的政治知識,提高人民的道德文化素質,防止統治者通過宗教與道德進行專制統治和思想鉗制;就道德而言,通過鼓勵宗教信仰和國民教育對人性、政治以及各種科學知識的普及,提高人民的道德水平,為維護平衡政體的穩定與政治的發展提供了文化條件,但是政治權力的運轉主要依賴于制度所架構的法治而非以宗教和教育為基礎的道德,此即是所謂道德與政治互不相害卻互為共和政治的綱要。
[1] (美)布拉德利·湯普森.約翰·亞當斯的馬基雅維利時刻[J].李浩譯,曹欽校.政治思想史,2014,(3).
[2] My Dearest Friend-Letters of Abigail and John Adams, edited by Margaret A. Hogan and C. James Taylor, The Belknap pr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3] John Adams. The Works of John Adams, second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with a life of the author. Notes and illustrations, by his grandson Charles Francis Adams.(Boston: Charles C. Little and James Brown, 1851).Vol.10.
[4] 李浩,郝儒杰.自由精神與均衡政制——約翰·亞當斯的“政治變奏曲”[J].黨政研究,2016,(4).
[5] John Adams. The Works of John Adams, second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with a life of the author. Notes and illustrations, by his grandson Charles Francis Adams.(Boston: Charles C. Little and James Brown, 1851).Vol.9.
[6] (美)約翰·艾茲摩爾.美國憲法的基督教背景:開國先父的信仰和選擇[M].李婉玲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10.
[7] C.Bradley Thompson, John adams and the spirit of liberty, the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 1998.
[8] John Adams. The Works of John Adams, second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with a life of the author. Notes and illustrations, by his grandson Charles Francis Adams.(Boston: Charles C. Little and James Brown, 1851).Vol.4.
[9] John Adams. The Works of John Adams, second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with a life of the author. Notes and illustrations, by his grandson Charles Francis Adams.(Boston: Charles C. Little and James Brown, 1851).Vol. 6.
[10] John Adams. The Works of John Adams, second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with a life of the author. Notes and illustrations, by his grandson Charles Francis Adams.(Boston: Charles C. Little and James Brown, 1851).Vol.3.
[11] (法)托克維爾.論美國的民主(上卷)[M].董果良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
[12] (英)WC.丹皮爾.科學史[M].李珩譯,張今校.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