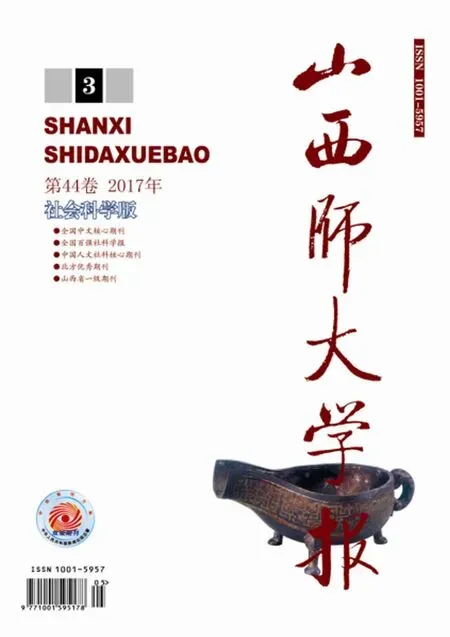施蟄存現代詩歌創作的準現代性特征
彭 秀 坤
(臨沂大學 傳媒學院,山東 臨沂 276000)
施蟄存不僅是30年代現代派詩歌理論的倡導者,還是較早的實踐者。雖然他文學創作的主要成就是新感覺派小說,但其創作是從詩歌開始的。施蟄存說:“在文藝創作的企圖上,我的最初期所致力的是詩。”[1]112他真正從事現代詩歌創作從1932年春開始,在讀了一些英美近現代詩作和評論后,“荒落了好久的詩的興趣重新升華起來”,同時,因看到“戴望舒做詩正做得起勁,于是也高興寫起詩歌來”。[1]施蟄存的現代詩歌作品最早散見于《現代》雜志,較集中收集的有藍棣之主編的《現代派詩選》,內有其現代詩歌作品14首;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的《施蜇存全集》,收錄其新詩26首。雖然施蟄存公開發表的現代詩歌作品數量較少,但其現代詩歌“卻以超越本體的力量姿態”,“為詩派的形成盡了拓荒之力”。[2]
學界對施蟄存的研究,一直重小說而輕詩歌;而對其現代詩歌的研究,一直重視其現代詩歌理論而忽視其創作實踐。新詩研究專家、香港《東方時報》社長葉輝指出:“施先生的新詩是個無窮的寶藏。”[3]他的現代詩歌實踐體現了20世紀30年代現代詩歌發展中存在的某些傾向。
施蟄存在《現代》第四卷第1期提出,現代詩“是現代人在現代生活中感受到的現代情緒,用現代的詞藻排列成的現代的詩形”[4]。這是施蟄存提出的現代詩歌觀念,也是其現代詩歌的創作目標。
一、 “現代情緒”:都市感傷與戀鄉情結
在后期新月派和象征派的基礎上,或者基于對二者的反叛,施蟄存提出現代詩內容“是現代人在現代生活中感受到的現代情緒”。所謂現代生活,是一種新的都市生活,“甚至連自然景物也和前代的不同”[4]。在他的心目中,現代生活是一種與鄉村生活完全不同的都市景觀。所謂現代情緒,也“并不是一種普泛的精神情感,而具有特定的內涵”[5]295。藍棣之把“濁世的哀音,青春的病態”[6]9列為現代派詩歌的特征之一,這也是30年代現代派詩歌的典型情緒。施蟄存現代詩歌大多抒寫都市體驗的痛苦、失望、悲觀,與表達“濁世的哀音,青春的病態”的現代派詩歌情緒具有一致性。但與現代派其他詩人相比,施蟄存詩歌的現代情緒又有其獨特性。具體來說,施蟄存詩歌的現代情緒主要表現在現代都市生活的感傷體驗和戀鄉情結兩個方面。
(一) 現代都市生活的感傷體驗。徐訏說,現代主義作品的主題“很可能只是一種體驗或一種感覺”[7]后記。現代派詩偏重于表現非理性的生命意識和心理體驗,尤其善于表現現代都市人的生活體驗,主張內心的真實是唯一的真實,倡導“把內心的要求作為一切文學上創造的原動力”[8]。施蟄存的現代詩表現了現代都市人的內向性感覺,并往往通過意識流動、自由聯想來展現都市人的無意識或潛意識。
與胡適《嘗試集》的意象及情感體驗不同,施蟄存的現代詩描繪了“一種帶有明顯都市印記的現代生活方式”[9]。如:“橫陳在菜市里的銀魚/土耳其風的女浴場/銀魚,堆成了柔白的床巾/魅人的小眼睛從四面八方投來∥銀魚,初戀的少女/連心都坦露出來了。”(《銀魚》)詩句表達了看到菜市場銀魚時的自由聯想,意象大都是都市化的。如果說胡適詩中的“老鴉”“蝴蝶”等意象所代表的還是一種鄉村體驗,那么施蟄存詩中的“菜市里的銀魚”“煙囪”等意象,表達的應該主要是一種現代都市感受了。
但施蟄存現代詩歌的城市景觀和城市體驗,往往使人感到壓抑和傷感。都市中那“桃色的云”,是“在夕暮的殘霞里,從煙囪林里升上來”的,每當“鵲噪鴉啼的女織工/從逼窄的鐵門中涌出來時/美麗的桃色的云/就變做在夏季的山谷中/釀造狂氣的暴雨的/沉重而可怕的烏云了”(《桃色的云》)。詩句表現了都市的壓抑感。生活在現代都市,詩人的心卻常隨著那“小小的烏篷船”“穿過橋洞”“穿過了秋晨的薄霧”,在“一個新的神秘的橋洞顯現了”時,詩人發現“我們又給憂郁病侵入了”(《橋洞》)。人們面對都市景觀,也面臨都市病的威脅。詩歌字里行間流露出一種迷茫的憂傷。
現代都市感傷體驗的產生既有都市空間的原因,也有社會時代的原因。20世紀30年代,政治的恐怖與現實的黑暗使詩人們感到了悲哀,“可以說是根植于同一個緣由——普遍的幻滅”[10]107。社會黑暗促使詩人從現實社會逃避出來,回到自我的內心世界。施蟄存更是“以一般詩人難以企及的感覺、夢幻、潛意識領域的拓進,而將現代人的心理揭示得精細而有情味”[2]。作為失落的知識分子,施蟄存和其他人一樣,生活在繁華的都市,內心卻似“冷泉亭”,詩人“不問泉自何時冷起/要問的是它冷從何處”(《冷泉亭口占》)。在詩歌《烏賊魚之戀》中,烏賊魚以自己的墨瀋寫下“戀的悲哀”,但海上卷起的風暴,“連他悲哀的記錄/也飄散得不留一點蹤影。”這是在現代都市社會產生的空虛無奈感。施蟄存現代詩中絕望、幻滅、虛無的情調,與戴望舒等現代派其他詩人的作品是相通的。
對于自己詩中的感傷虛無情緒,施蟄存有清晰的認識,他在評論戴望舒詩歌時說:“在精神上,卻竭力想避免他那種感傷的色彩。但這也是不容易的,因為我已寫成的幾十首詩,終于都還免不了這種感傷。”[1]112施蟄存詩歌的感傷情緒其實是一種難以擺脫的時代都市病。
(二)現代戀鄉情緒。施蟄存談到20世紀30年代現代派作家的創作心態時說:“影響創作的因素除了政治,還有就是都會和鄉村。”[11]230年代上半期,正處于鄉村與城市、傳統與現代的轉折點。面對新的都市生活,施蟄存說:“甚至連自然景物也和前代不同了,這種生活所給予我們詩人的感情,難道會和上代詩人從他們的生活中所得到的感情相同嗎?”[4]詩人與現代都市生活間文化心理的反差,在施蟄存的詩歌中表現為對形形色色都市生活的種種異常情緒反應。如《嫌惡》那“永久環行的輪子”的火車“令人嫌棄”,因為它“使我看見了/那個瘦削的媚臉/涌現在輪子的圓渦里”,“對于這神異的瘦削的臉/我負了殺人犯的隱慝”,詩歌展示了現代都市的夢魘。面對黑暗險惡的都市,詩人渴望如“彩燕”一樣,“剪掠寒流,溜出了城闉”,但“有什么東西按抑了我,有什么東西羈絆了我”,這讓我“踟躕不定”。《彩燕》一詩表現了作者渴望逃避都市現實但又猶豫彷徨的心態。詩人從鄉村來到都市,感到自己并未完全被都市所接受,而成了都市邊緣人,內心“感受著古老的農業文明向工業文明轉型期的歷史陣痛,又體驗著波特萊爾筆下的都市文明的沉淪與絕望”[12]363。都市的壓抑使詩人產生了難以排遣的“鄉愁”。
有人說描寫都市,施蟄存有兩個特點:“一是心理分析,二是鄉鎮情結。”[13]對施蟄存來說,他雖然生活在現代都市,卻難以擺脫對故鄉的留戀和向往。在其筆下,鄉愁如“一縷煙”,“在被忘卻的故鄉的山腳下,有我的鉛皮小屋”,在“那頹圮的屋頂上/久已消失了/青色的炊煙”。詩人明白,都市絕不是“恬靜的家居之良伴”,盡管如此,詩人還是希望這如煙的“噓息”,“暫時給我作安居之符號/讓我欺騙別人/又欺騙自己”。這是游子的鄉愁,對于現代都市詩人施蟄存來說,鄉村永遠是可望而不可即的,自己注定是現代都市的游子。可見,在30年代現代派詩人中,施蟄存的戀鄉情緒是較為突出的。
強烈的戀鄉情緒使施蟄存的現代詩表現出某些傳統美學的特點。或者說,施蟄存的現代詩歌作品,表面上是現代都市文化的,但骨子里還殘存著傳統農業文化的印痕。施蟄存是以一個都市里的鄉下人身份來書寫都市的。有人指出,施蟄存詩中“桃色的云”的意象體現了農業時代的美好想象。這也許是人們對他詩歌的現代性評價不高的原因。確實,從其詩歌字里行間的憂郁情思中,我們仍能感受到我國傳統詩歌的某些審美趣味。
有人稱施蟄存“是《現代》都市詩風的開創者與都市風景的吟唱者”[2],這評價肯定了其對現代都市詩的卓越貢獻和獨特價值,但主要還是因為“中國初期的白語新詩很少有現代都市生活的意象詩”[14]。施蟄存的現代詩對現代派其他詩人產生了較大影響,現代派其他詩人也大都表現了這種現代都市體驗,即使寫到鄉村,也多是現代都市意識觀照下的鄉村,只是現代派其他詩人的戀鄉情結沒有施蟄存如此明顯罷了。
二、“現代詩形”:散文化的詩行與古今中西融匯的辭藻
“五四”白話新詩運動是從詩歌形式開始的,形式也是新詩之“新”的根本。但正如朱光潛先生所說:“新詩比舊詩難作,原因就在舊詩有‘七律’、‘五古’、‘浪淘沙’之類固定模型可利用”,而“新詩的固定模型還未成立”,“許多新詩人的失敗都在不能創造形式。”[15]270—271新詩之新在于形式新,新詩難寫也在于形式難寫。也許正因如此,施蟄存的現代詩歌實踐非常重視形式。
施蟄存倡導現代詩歌形式應注重情緒的自由化表達,他認為只要有利于情感表現的形式就是好形式,就是現代詩形。他的詩歌既努力擺脫“五四”自由詩的非詩化傾向,又注意去掉了新月派詩歌極端的形式主義傾向,而努力以自由的形式、自然的音節表達現代人的現代情緒,努力建構一種自由、精致而又新奇的“中國現代詩歌節奏”[16]形式。施蟄存詩形的現代性主要表現為現代詩情節奏和現代詞藻兩個方面,其“現代詩形”也就是用現代詞藻來表達現代詩情節奏的形式。
(一)散文化的詩行。施蟄存的現代詩歌,“從始至終全是‘散文化’”[17]。正如施蟄存對自己現代詩歌的評價,即都是自由體詩,都是對新月派格律詩的革命。他的現代詩歌都不押韻。他認為沒有用韻的詩,只要寫得好,“在形似分行的散文中,同樣可以表現出一種文字或詩情的節奏”[18]。他每一首詩的形式都各不相同,詩無定節、節無定行,顯得新穎活潑。如《祝英臺》:“墻之東/墻之西/何處是永久的侶伴呢/飄蕩的戀女之心/也該悔艾了吧/徒然地炫耀著/彩繪的春服?∥墻之東/墻之西/早知終于要離散的/飄蕩的戀女之心/也該悔艾了吧/徒然地炫耀著/幸福的新生?”全詩兩大段,字句錯落不齊,似乎不講究外在形式美,但又相互對稱,具有均衡和諧的美。再如《橋洞》一詩共有五節,前三節每節三行,后兩節每節五行,每行字數不一,但從第一節到第五節,每一行字數有增多的趨勢,似乎整首詩隨著“小小烏篷船”行進和詩人情緒的發展奔涌向前。《嫌厭》共有五節,每一節的行數不一,沒有規律,但每一節的起首句都是相同的語句:“回旋著,回旋著。”復沓的語句似奔馳的火車,給人以強烈的節奏感,并爭取與詩歌的內容相統一。而《烏賊魚之戀》的形式最自由,全詩共六節,每節從兩行到六行不等,似乎全無規律,但這恰如烏賊魚企圖“顫抖地摸索著戀愛”的十只長短不一的手,內容和形式有機融合,給人以豐富的聯想,是“有意味的”散文體詩歌形式。
施蟄存肯定胡適新詩運動對新詩打破舊體詩歌傳統的貢獻,但他認為從胡適以來的新詩研究者無意中又墮入西洋舊體詩的傳統。“他們以為詩該是有整齊的用韻法的,……這與填詞有什么分別呢?”可見,施蟄存是堅決反對新詩向西洋傳統詩歌方向發展的。不管是胡適用韻的白話體,還是新月派的格律體,施蟄存都強烈反對。另外,他對部分詩人主張用“小放牛”“五更調”之類的民間小曲作新詩的主張,也堅決反對,認為“這乃是民間小曲的革新,并不是詩的進步”。而“《現代》中的詩,大多是沒有韻的,句子也很不整齊,但它們都有相當完美的‘肌理’,它們是現代的詩形,是詩!”[4]施蟄存的詩歌非常注重情感的自由表達,不刻意追求形式,因此帶有散文體的詩形特點。李歐梵先生曾批評施蟄存“沒有能對‘肌理’這概念作深入的探究”[9],而通過施蟄存的詩歌可以發現,所謂的完美“肌理”,主要是指能夠體現現代情緒節奏的散文化詩行形式。
(二)古今中西融匯的詞藻。施蟄存的現代詩歌講究現代詩形的運用,他的現代詩形是與“現代詞藻”聯系在一起的。施蟄存現代詩歌的現代詞藻既涉及到文言詞語入詩,還關系到外來語的運用。可見,所謂的“現代詞藻”,在施蟄存詩歌中既流露出古代與現代詞語融合的傾向,又體現出中西語言合璧的追求。如果說外來語的運用體現了施蟄存對西方現代文化的接納,那么文言詞語入詩就表現了詩人難舍的傳統情懷。“現代詞藻”既是為表現詩人的“現代情緒”服務的,也是詩人“現代情緒”的表現。
關于現代詞藻,施蟄存認為,《現代》中許多詩的作者在他們詩篇中采用一些比較生疏的古字,甚至是文言文的虛字。這些字“并沒有‘古’或‘文言’的概念”,“只是宜于表達一個意義,一種情緒,或甚至是完成一個音節”[4]。施蟄存所說的現代詞藻并不是詞語本身的古今,他并不反對詩歌的文言詞語,而主要看詞語能否恰當地表達現代情緒。施蟄存的現代詩中常出現一些文言詞語。如“難道那落寞的清溪/從迢遞的萬山中流注/到這掩著錦幔的窗外的/綠髹亞鉛管中了嗎?/岑寂的夜坐,燈昏茗冷/遂有那白石上的潺湲/載著比肩之幽嘆/向叢莽間拍浮而逝”(《秋夜之檐溜》)。這節小詩,幾乎每句中都有文言詞語,而且“落寞”“岑寂”“燈昏”“茗冷”“幽嘆”等文言詞語的運用,表現了一個鄉村情結濃厚的現代都市邊緣人內心的孤獨和感傷。這是施蟄存對文言詞語入詩的成功實踐。
如果細讀施蟄存的現代詩歌還會發現,他詩中除了融入一些文言詞匯之外,還嵌入了許多外來語,這些外來語也應算現代詞藻。現代派詩人認為:“現代人的許多思想感情用農業社會的傳統語言來表達,就感到不夠了。”[19]154施蟄存的現代詩,不但借鑒了許多的文言詞匯,也吸收了諸多的外來語。如《衛生》中有這么一節:“已經是豐富的Dessert了/對于我知足的眼的嘴。/如果華爾紗的夜透了曙光∕我是要患急性胃加答兒的。”詩中既有外來語“Dessert”的直接運用,也有“華爾紗”“ 胃加答兒”等音譯外來詞,這既體現了外來文化對中國都市詩的影響,也體現出現代中國都市洋涇浜文化的特點。施蟄存的現代詩歌正是借助一些新奇的現代字眼,表達現代都市人的異樣感受,揭示了復雜的現代都市體驗。
施蟄存的現代詩歌實踐是在西方現代詩歌的影響下產生的,受其影響,但又努力擺脫其影響,是“根植于中國的土壤中,創作出既創新又有民族特點的作品”[20]。施蟄存在追求現代詩形時,很注意節制,他的詩歌形式很少給人炫奇和作怪之感,而是努力追求一種外在詩形與內在情感的統一。施蟄存曾把《現代》中詩的形式和風格的特征歸納為四點:不用韻;句子、段落的形式不整齊;混入一些古字或外語;詩意不能一讀即了解。現在看來,這四點正是施蟄存現代詩歌所體現的形式風格特點。雖然施蟄存的個別詩歌讓人感覺“很難讀懂”,但與20年代晦澀的象征派詩歌相比,已容易把握多了。而且,施蟄存現代詩歌的形式也已基本擺脫了象征派詩歌過分追求省略和跳躍的歐化傾向。他對現代詩歌形式散文化的倡導和實踐,直接影響了30年代詩歌散文化的興起。在其引導下,許多現代派詩人由格律化走向了散文化道路,這非常有利于現代詩歌內容的表達和形式的發展。
總之,施蟄存的現代詩歌實踐與其理論還存在著某些偏離,具有明顯的嘗試痕跡和準現代性特征,但正如他的現代詩歌理論“給今后的現代派詩歌指明了道路”[21],他的創作也給現代派詩歌發展提供了參考。可以說,施蟄存的現代詩歌實踐對30年代現代派詩歌的價值,不啻如“五四”時期胡適的白話詩對新詩“嘗試”的貢獻。
[1] 施蟄存.我的創作生活之歷程[A].應國靖.施蟄存散文選集[C].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2004.
[2] 羅振亞.意象抒情:評施蟄存20世紀30年代的詩[J].云夢學刊,2004,(6).
[3] 劉效禮.一部《施蟄存全集》即為一部“二十世紀文學史”[N].中華讀書報,2012-8-15.
[4] 施蟄存.又關于本刊中的詩[J].現代(第四卷第1期),1933.
[5] 龍泉明.中國新詩流變史:1917—1949[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9.
[6] 藍棣之.現代派詩選·前言[C].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6.
[7] 徐訏.風蕭蕭[M].沈陽:春風文藝出版社,1988.
[8] 成仿吾.新文學之使命[J].創造周報(第2號),1923.
[9] 李歐梵.探索“現代”:施蟄存及《現代》雜志的文學實踐[J].文藝理論研究,1998,(5).
[10] 施蟄存.沙灘上的腳跡[M].沈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5.
[11] 卞之琳.戴望舒詩集·序[C].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
[12] 錢理群,溫儒敏,吳福輝.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
[13] 楊迎平.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施蟄存:為紀念施蟄存誕辰一百周年而作[J].文藝理論研究,2005,(6).
[14] 王澤龍.論中國現代詩歌意象的都市化特征[J].人文雜志,2006,(4).
[15] 朱光潛全集:第三卷[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87.
[16] 王澤龍,王雪松.中國現代詩歌節奏內涵論析[J].文學評論,2011,(2).
[17] 殷鑒,宋立民.20世紀30年代現代派詩歌藝術風格新探[J].洛陽大學學報,2003,(3).
[18] 施蟄存.《現代》雜憶[M].新文學史料,1981,(1).
[19] 杜運燮.穆旦詩選·后記[C].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6.
[20] 施蟄存.關于“現代派”一席談[N].文匯報,1983-10-18.
[21] 楊迎平.施蟄存與三十年代的詩歌革命 —兼談與戴望舒的友誼[J].新文學史料,200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