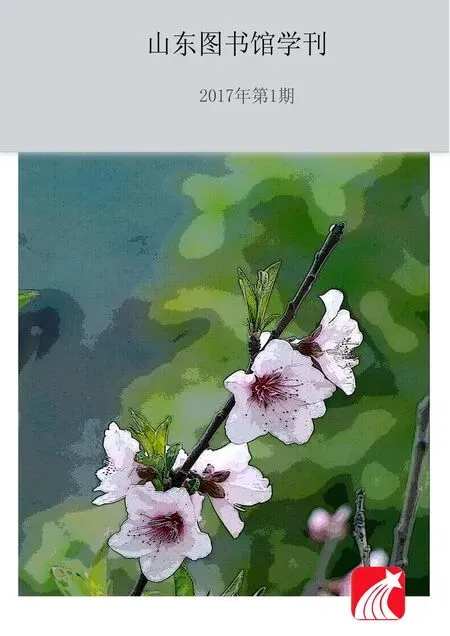知識產權制度應以促進創新為目的
——斯蒂格利茨知識產權思想研究
劉海麗 關思思,2
(1北京大學信息管理系,北京 100871;2天津外國語學院圖書館,天津 300204)
學術論壇
知識產權制度應以促進創新為目的
——斯蒂格利茨知識產權思想研究
劉海麗1關思思1,2
(1北京大學信息管理系,北京 100871;2天津外國語學院圖書館,天津 300204)
斯蒂格利茨認為知識是準公共物品,人們設計知識產權制度的初衷是為了促進創新。但知識產權制度如果設計不當,會對創新不利。目前的知識產權制度是由發達國家設計的,對于發展中國家來說是不利的。他認為獎勵、政府資助、開放資源、自行研發等也可以促進創新。對于發展中國家來說,研究一種以發展為導向的知識產權制度是必要的。
知識產權 知識產權制度 斯蒂格利茨 公共物品 專利
導言
約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E.Stiglitz),1943年生,美國經濟學家,由于他在市場非對稱信息方面的研究成果,2001年獲諾貝爾經濟學獎。斯蒂格利茨1967年獲麻省理工學院博士學位,1970年至今先后在耶魯大學、斯坦福大學、牛津大學、普林斯頓大學、哥倫比亞大學任教。他的政府與社會任職經歷是:1993-1995年任克林頓經濟顧問團成員,1995-1997任克林頓經濟顧問團主席,1997-2000年任世界銀行副總裁,并擔任首席經濟學家。現任哥倫比亞大學教授。
斯蒂格利茨對知識產權方面的貢獻是與他在經濟學方面的研究分不開的。他把知識看作是公共物品,從全球、全人類的角度探討知識產權制度的意義起點及對社會的貢獻與弊端。他認為知識產權制度設計的社會意義是促進創新,而目前的知識產權制度更多是為知識產權所有者保護利益,忽視了社會價值,因此他呼吁設計一種發展型知識產權制度,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使用不同的知識產權制度。他對知識產權制度的質疑主要集中在專利方面,認為著作權范圍適當,沒有限制知識的使用,是一種非壟斷權力,因此著作權不會阻礙創新[1]113。
1 知識產權制度目的是為了促進創新
1.1 知識是準公共物品
斯蒂格利茨認為知識是準公共物品。首先,知識具有公共物品的特點,即知識具有非排他性,如分享知識并不會失去知識。其次,知識的特點使得知識又與物質有所不同,一是知識不是獨立存在的,它與其他知識沒有清晰的邊界,我們可以將物質清楚地區分開來,因而物質的產權的邊界也是很清晰的,知識產權的邊界不清楚。二是知識很難形成獨占性,一個人占有知識,并不能排除別人享有知識。我們很難把知識和人分開,知識是人習得的[2]13。自由傳播知識比限制傳播知識要容易得多。
1.2 知識產權制度設計的初衷是為了促進創新
作為準公共物品,知識的免費傳播會影響人們的創新動力,因此人們設計了知識產權制度。斯蒂格利茨認為知識產權制度是社會創新系統的一部分。知識產權制度創立的初衷是激勵創新,即給予創新者從知識中獲取回報的權力[3]。知識產權制度設計的初衷即確保在創意活動中投入金錢和時間的發明人、作家等獲得回報。不同的知識產權規定不同,專利授權給予發明人在一定時間內從市場獲取收益的權力,其他人未經授權不得在市場上出售涉及專利技術的產品。著作權則給予作者、作曲家著作、歌曲的獨家售賣權。知識產權制度在大部分國家得到了實施[1]507。
2 過度的知識產權保護制度對創新不利
設計不好的知識產權制度會形成對知識產權所有者利益的保護,對創新不利。斯蒂格利茨指出,知識產權限制知識的使用,導致低效率。
2.1 不利于知識獲取
知識產權賦予產權所有人壟斷知識的權利,壟斷一旦形成,就很容易保持,所有人也有動機保持這種壟斷[3]1705。專利的特點是壟斷權,任何使用專利的人都需要向專利所有人交納一定的費用,專利所有人傾向于將收益最大化,會盡量收取多的費用。后繼研究者向專利所有人交納的費用越多,他能投入到后續研究中的經費也就越少,因而影響研究進展,因此專利制度不利于知識獲取[2]10-11。
越多越多的專利導致“專利叢林”。專利越來越多,導致任何發明都難以避免侵犯他人的專利,為此發明人不得不花費時間和精力尋求專利許可,無疑加重了創新的成本。知識產權制度給予人們的壟斷權,使得各種知識使用權掌握在不同人手中,加大了充分使用知識的難度[2]11-12。
授予知識以專利相當于將知識私有化了。斯蒂格利茨認為,獲得專利的人只是比別人先發現了知識,將知識創新的所有收益給予專利所有人顯然是不公平的。他提出,即使他沒有發現非對稱信息,將來也會有人研究出來。將知識私有化實際上將大眾排除在了知識之外,這對于知識的利用是不利的。他認為,知識產權的目的應該是提高知識利用率,而不是降低,目前的知識產權制度顯然降低了知識利用率[3]1708-1709。
2.2 不利于創新[3]1703-1704,1711
知識是創新的最重要源泉,限制了知識的利用,就會阻止創新。專利阻止了知識的傳播和利用,拖慢了創新進展,所有的創新都是建立在以前的創新基礎上的,知識產權拖慢了創新的速度。他舉一案例,上世紀初年就有人獲得了所有自驅動四輪的專利,1903年汽車制造上圍繞這個專利組成了一個壟斷組織,該壟斷組織擁有汽車制造專利,控制了汽車制造商人選,他們只選擇愿意維持汽車高價的人制造汽車。亨利·福特(Henry Ford)的汽車理念是“人人買得起”(people’s car),為此他進行了研究,生產出了物美價廉的汽車,大幅提高了汽車在美國的覆蓋面。沒有福特的堅持,或福特沒有成功的話,汽車技術的發展肯定要緩慢很多。擁有專利的多個組織容易聯合起來形成壟斷組織,而他指出,專利本身就是一種壟斷,壟斷意味著高利潤,專利所有人必然不愿意放棄這種壟斷地位。壟斷提高了知識的價碼,也阻止了創新[1]110-111。
知識產權阻礙創新的另一方面是我們難以確定專利的邊界。專利不像物質那樣,有著清晰的邊界,因此如何定義一項專利的邊界是困難的,如果專利的邊界太寬泛了,就會影響到其他人員的創新意愿,因此專利授權應清晰規定專利的邊界[4]。萊特兄弟(Wright brothers)20世紀初葉獲得了制造飛機的一些專利,格倫·柯蒂斯(Glenn Curtiss)也獲得了部分制造飛機的專利。一戰之前,制造飛機的技術一直沒有發展起來,因為兩方都聲稱擁有專利,如果從兩方獲得授權則成本太高,如果只從一方獲得授權則面臨被另一方起訴的風險。戰爭終于使得美國政府認識到贏得戰爭比知識產權要重要得多,因此規定了兩方在飛機制造中各自應得的費用,之后飛機制造術進展迅速[3]1703-1704,1712。
創新定義本身也為知識產權的確定帶來了難度。例如,制藥公司為了延長專利的有效期,會對藥物進行漸進式改進。所以這里又涉及到如何定義“創新”。而且創新的比較對象應該是世界水平,管理部門很難確定世界上是否有同類發明,例如泰國香米已經有上千年的歷史了,上世紀卻在美國獲得了專利,這都說明了創新定義的難度。
知識產權對研究的導向作用影響創新模式。知識產權容易引起因專利而研究,從而加強壟斷。斯蒂格利茨認為,微軟公司開發Vista系統的目的即弱化系統交互性,強化壟斷地位。相比于公司從新系統中獲得的收益,社會效益比較低[3]1703-1704,1712。
2.3 不利于發展中國家
斯蒂格利茨認為目前的知識產權制度是發達國家強加給發展中國家的。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的差距不僅僅是資源方面的,還有知識方面。嚴厲的知識產權制度讓發展中國家為獲得知識而付出高昂的代價。美國、德國、日本等在工業趕超的過程中,知識產權制度還不健全,他們通過模仿積累本國的科技能力,而現在這些國家通過在全世界推行知識產權制度,嚴格禁止發展中國家使用模仿這種方法,這就阻止了知識從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傳遞[2]34。而發展中國家要想獲得知識,必須向發達國家繳納高昂的費用,這對于發展中國家顯然是不利的。知識產權全球化的推手主要是以美國為主的發達國家,美國認為,其在知識資本上的投入沒有得到相應的回報,損害了美國利益,因此他把知識產權植入到國家間的自由貿易中[4]243。
知識產權制度是由發達國家設計的,更有利于發達國家。美國的知識產權制度將傳統知識如植物的傳統藥用方法授予了專利,而發展中國家認為不應該賦予專利。因為在發展中國家看來,這些知識是民間都知道的,像印度楝樹油、泰國香米、藥用姜黃。美國政府迫于制藥公司的壓力,卻沒有批準慣例優先原則,因為制藥公司擔心一旦實施了慣例優先原則給予發展中國家“過多”保護。斯蒂格利茨認為這種較量反映了公司利益,制藥公司因“發現”被獎勵,發展中國家保護生物多樣性卻不受獎勵,而沒有發展中國家的生物多樣性,可能就沒有制藥公司的發現。這也反映了美國知識產權制度的一貫原則是最大化公司收益,最小化公司應付出代價[2]2。美國認為可以賦予傳統知識專利的另一個原因是:發展中國家從未將傳統知識予以公開發表,如果有公司將這些知識“發現”了,可以賦予專利。斯蒂格利茨認為,將知識發表才能證明其早已存在,這種觀點也是西方做法,發展中國家目前不得不順從這種西方把持的話語體系[1]126。
2.4 不利于大眾
知識產權抬高了專利藥物價格。斯蒂格利茨強烈反對TRIPs,他認為TRIPs限制了非專利藥的生產。非專利藥由于價格低廉,是不發達國家患者的福音。他以艾滋病舉例說,知名制藥公司的藥物,患者每年的藥物花費需要一萬美元,在不發達國家,人們的人均收入只有三百美元到三千美元,那里的艾滋病患者顯然難以承受每年一萬美元的藥物費。非專利藥售價不到二百美元,而TRIPs成員國簽署協議之后就不能再生產非專利藥物了[3]1701。TRIPs的勝利意味著公司(歐美國家)利益的勝利,公司利益高于環境、生命這樣的基本價值觀[1]105。
知識產權的趨利性導致研究資金流向能產生利潤的研究領域。斯蒂格利茨說,為了利益,相比于在研發上投入的資金,制藥公司會在廣告和推廣上投入更多資金;其次制藥公司會在更賺錢的領域投錢,比如提升生活質量的藥物,在那些沒什么錢賺的藥物方面即使是救命藥,也會減少投入[3]1703-1704,1713。
3 知識產權制度不是促進創新的最好方法
知識產權與創新沒有必然的關系,他說沒有知識產權制度的國家也可能是創新力極強的,如瑞士1907年、荷蘭1912年才建立專利制度。他強調,知識產權只是一個國家創新系統的一部分,絕非全部[1]113。
3.1 知識產權適用范圍具有局限性
有一些知識不適用于知識產權制度,例如數學,因為把他們專利化之后,專利所有人所獲甚豐,而社會收益則非常有限。還有基因檢測、化學物質本身、化學反應結果、蛋白質、酶類,這些是生活的基礎物質,這些物質是人們“發現”的,而非發明的。在人類基因工程中,美國Myriad公司申請了一些專利,他們提供的基因檢測費用高達幾千美元,這顯然超過了一般人能承受的范圍。美國也有很多人沒有保險,他們收入也不高,高昂的基因檢測費用,會影響到他們的生活。2010年聯邦法院裁定Myraid所持有的兩項有關基因的專利超出了合理范圍。加拿大政府則認為將基因授予專利超出了合理范圍,因此未授予任何公司在基因方面專利,那里的基因檢測費用就要低得多[3]1708。斯蒂格利茨認為這些都不應納入知識產權范圍。
3.2 獎勵、開放資源等也可以促進創新
作為促進社會創新制度的一部分,斯蒂格利茨認為,我們不應該將所有希望都寄托在專利上面,他指出設置獎勵、政府資助、開放資源、自行研發等也可以促進創新。
3.2.1 獎勵
獎勵是促進創新的有效方式。獎勵是一種比較古老的方法。英國皇家藝術、制造和商業促進會一個多世紀以來設立了多種獎勵來促進技術發展,其中一個例子是煙囪清掃技術。在這種技術沒有發明之前,需要將兒童送到煙囪底部進行清掃,這對兒童的健康是不利的,也比較危險,但如果不清掃煙囪的話又容易起火。因此該學會設立了一筆獎金,用于獎勵發明煙囪清掃技術的人,后來該發明得到了廣泛應用。斯蒂格利茨說,如果使用知識產權這種手段的話,也可以有這樣的發明,但這樣的發明由于收取高昂的許可費用,只有有錢人家才能負擔,窮人家的煙囪還是需要兒童來清掃,這對于整個社會來說,顯然是不利的。而獎勵系統的應用使整個社會收益[2]28。
獎勵與知識產權激勵創新的不同點體現在三個方面。首先知識產權給予所有人的“獎勵”是壟斷權力,壟斷權會限制知識的使用。而知識創新的一個特點是知識的廣泛使用和擴散,這與知識產權的限制南轅北轍。獎勵系統鼓勵知識的擴散,所有參與生產的人參與競爭,必然會降低產品價格、促進知識傳播。其次獎勵系統不需要在廣告上投入,也不會形成壟斷。而藥物公司由于在專利上進行了投入,會盡量提高價格,獲取更多的壟斷利潤。最后,專利扭曲研究機制,例如擁有專利的藥物公司在無利可圖的藥物上沒有研發動力,這些藥物可能嚴重影響窮人的生活。為了攫取更多的利潤,藥物公司會申請類似專利,進而延長專利的有效時間。獎勵的缺點是,研究目標不明確時就起不到應有的作用[2]28-29。
3.2.2 政府資助
政府資助主要是指公辦大學和政府資助的實驗室。斯蒂格利茨認為政府資助是促進創新的最重要手段。
3.2.3 開放資源
開放資源運動已經從IT行業擴展到了其他行業。開放資源這種方式符合學術研究需要合作的特點,開放的資源有利于后續研究。在學術研究中,非物質獎勵發揮著重要作用,或者研發機構有很多其他方式能夠獲得補償。開放資源運動獲得成功的一個例子是Linux,據2007年估計,它占據了12.7%的服務器市場,60%的網絡服務器使用了Linux系統[4]247。
3.2.4 自行研發
斯蒂格利茨認為,生產的特點本身就容易產生專屬權,因為生產設計到研發周期、批量復制、學習時間、特制生產機器的獲得、銷售網絡等,這些導致率先在創新中投入的人能夠獲得回報,即使沒有知識產權的保護。商業秘密及知識的“緘默”特性,強化了機構從知識投資中獲得收益的能力[5]。因此這種策略也能夠補償企業的研發投入。
斯蒂格利茨認為以上促進創新的策略都有利弊。他從選擇強度、資金效率、風險、對創新的促進作用、知識傳播積極性、交易費用等方面對這幾種策略進行了比較。
4 建立發展導向型知識產權制度
知識產權制度是人為制定的,并不是一成不變的,也不是同一個模子里刻出來的。如何理解、規定、執行知識產權制度至關重要。斯蒂格利茨以世界發展的眼光指出,好的知識產權制度能夠促進創新。他指出,在美國,一旦授予了某人專利,其他人無法反駁,而在歐洲,如果有人舉證不應授予,則會取消已經授予的專利。這也說明知識產權制度本身如何設計也是至關重要的。他舉例說,在印度尼姆樹油長期以來用途廣泛,其作用在美國和歐洲都被授予專利,印度提出抗訴后,歐洲取消了專利,而美國則拒絕取消專利[3]1716。他援引美國研究人員的觀點認為,美國應在專利申請程序中加入抗訴機制,即專家或其他人有權在申請過程中提出抗議,而不僅僅由管理人員來決定是否授予專利[4]246。
2004年10月,世界知識產權組織(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zation,WIPO)聯合國大會第一次討論了以發展為導向的知識產權大會,WIPO認識到知識產權并不是終點;重新確立了WIPO的初衷:促進創新和將科技傳遞到發展中國家[2]1。
結語
斯蒂格利茨認為,社會創新系統依賴于基礎研究的進展,大部分基礎研究是在學術界和政府資助的研究中產生的。金錢回報只是激勵研究人員的一小部分動力,因而知識產權制度并不能完全促進人們創新。比起來用金錢激勵研究,我們更應該探索如何資助研究[3]1698。
知識產權制度初衷是為了促進創新,這是他一直強調的,目前美國的知識產權制度顯然受到了太多的利益牽制,他警告說,這樣的制度強行推廣到發展中國家會產生不好的影響,解決的辦法就是重新設計知識產權制度[4]248。
斯蒂格利茨的知識產權思想是以關注生命、關注世界公平的角度來進行闡述的,因此其思想特別有人性關懷。一種制度是否合理,不是看其是否在世界得到了推廣,而是看這種制度是否真的關懷生命和社會發展,這也是斯蒂格利茨知識產權思想給我們的啟示。
〔1〕 Joseph E.Stiglitz.Making the Globlazation Work[M].New York:W.W.Norton &Company Inc,2006
〔2〕 Giovanni Dosi,Josph E.Stiglitz.The Role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in the Development Process,with Some Lessons from Developed Countries:An Introduction: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Legal and Economic Challenges for Development[G].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4
〔3〕 Joseph E.Stiglitz.Economic Foundation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J].Duke Law Journal,2008(57)
〔4〕 Claude Henry & Joseph E.Stiglitz.Intellectual Property,Dissemination of Innovatio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J].Global Policy,2010,3(1)
〔5〕 Joseph E.Stiglitz.The Case Against Gene Patents[EB/OL].[2016-08-20]http://www8.gsb.columbia.edu/faculty/jstiglitz/sites/jstiglitz/files/WSJ_Stiglitz_Sulston.pdf.
Intellectual Property should Take Promoting Innovation as the Aim ——Research on Stiglitz’s Intellectual Property Ideology
Liu Haili Guan Sisi
As Stiglitz points out that knowledge is quasi-public goods. The most important aim of the intellectual property regime is to promote innovation. Whether it works well depends on how it is designed. The current intellectual property regime was designed by the developed countries, so it doesn’t work well in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does not take the livings into consideration. He proposes that reward, government financing, open sources and research could also inspire innovation. It is necessary for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 to design an intellectual property regime with development as the intent.
Intellectual property; Intellectual property regime; Stiglitz; Quasi-public goods; Patent
D923.4
A
劉海麗(1985-),女,北京大學信息管理系2013級博士生。研究方向為:公共文化服務、公共文化法治,已發表學術論文5篇。關思思(1985-),女,天津外國語學院圖書館員,北京大學信息管理系2013級博士生。研究方向為:公共文化社會化,已發表學術論文多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