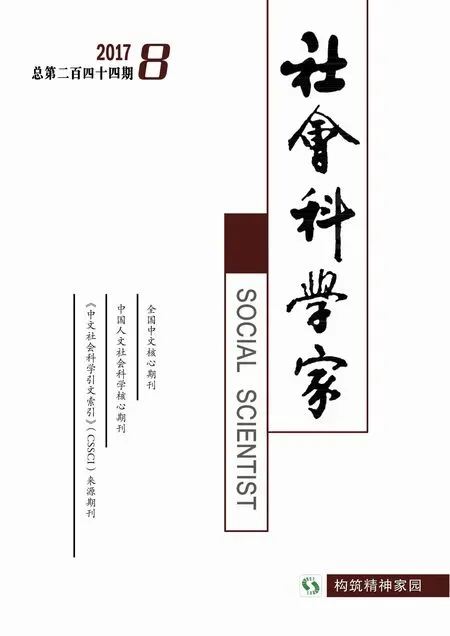“斷”而不“裂”的歷史
——兼論艾蒂安·巴里巴爾的結構主義過渡理論
陳廣思
(中國人民大學 哲學院,北京 435000)
“斷”而不“裂”的歷史
——兼論艾蒂安·巴里巴爾的結構主義過渡理論
陳廣思
(中國人民大學 哲學院,北京 435000)
依據艾蒂安·巴里巴爾的結構主義過渡理論,我們能夠很好地闡釋馬克思關于一種歷史狀態的內在結構及其向另一種狀態過渡的內容,初步展示馬克思視域中的歷史運動圖景。但是出于結構主義的立場,巴里巴爾只講了“故事”的一半,通過他的理論歷史只能被展示為“斷裂”的歷史。因此闡釋馬克思的歷史圖景不能只停留在他的解釋范圍里。我們必須把另一半“故事”講完,闡述人與自然之間具有社會歷史性質的矛盾運動關系,這樣才能夠完整地描繪出歷史唯物主義“斷”而不“裂”的歷史圖景。
結構;過渡理論;歷史圖景;矛盾運動
如何理解歷史,在哲學領域中是頗受關注的一個問題。艾蒂安·巴里巴爾的結構主義過渡理論試圖對此做出自己的回答。到目前為止,他跟隨阿爾都塞的路線用結構主義來闡釋馬克思的歷史理論的觀點仍然值得我們去思考,因為他采用的方法論本身就比較切合馬克思對歷史的理解方式。但是,當我們沿著巴里巴爾指示的路往前走時,才發現路是沒走錯,但卻沒有走完。巴里巴爾的過渡理論并不能完整解釋歷史唯物主義中歷史的運動圖景,他只是講了故事的一半,另一半卻還必須讓我們去完成。
一
馬克思認為,每一個社會形態都有它“特殊的以太”[1],理解一個社會形態必須從它的“特殊的以太”出發,而不能只是從發生學的角度根據范疇在歷史中起決定作用的先后順利來研究這個社會形態[1],這是馬克思理解歷史的特殊方法。在《資本論》的手稿《資本主義生產以前的各種形式》中,馬克思運用這種方法來理解社會歷史的內在結構。在這里我們可看到,一種社會生產的所有制形式,即勞動者對勞動條件的占有關系,構成了這種生產方式“特殊的以太”,同時也就構成了它的內在結構。在這部分內容中,除了勞動者之外,馬克思把勞動的條件概括為四個要素:勞動原料、勞動工具、勞動者的生活資料和勞動本身。①馬克思偶爾也把貨幣也歸入為勞動的客觀條件之一(《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第155頁),但是這只是一種特殊的情況。就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來說,貨幣財富與其說是與這四個要素相并列的另一個要素,還不如說是它們的貨幣表現形式或支付手段,因而不需要將其作為一個單獨的要素出列舉出來。另外,在這四個要素中,“勞動工具”和"勞動原料"為勞動的客觀條件,“生活資料”和“勞動本身”為勞動的主觀條件(《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第98頁),但如果這些主觀條件與勞動者相對立,馬克思稱之為勞動的客觀條件。依據勞動者對這四個要素的占有情況,我們可以總結出四種所有制關系,即馬克思所說的四種“歷史狀態”[1],它們每一種都表示著一種生產方式的內部結構:
第一種狀態:勞動者+勞動工具+勞動原料+生活資料+勞動本身
第二種狀態:(勞動者+勞動工具+勞動本身)→(勞動原料+生活資料)
第三種狀態:(勞動者+生活資料)→(勞動工具+勞動原料+勞動本身)
第四種狀態:勞動者→(勞動工具+勞動原料+生活資料+勞動本身)①在這里需要作一些初步的說明:“+”表示結合的關系,“→”表示分離的關系,因而表示兩邊的相互外在和對立關系。對于“勞動本身”這個要素,馬克思說:“這些形式由于勞動本身被列入生產的客觀條件(農奴制和奴隸制)之內而在本質上發生了變化,于是屬于第一種狀態的一切財產形式的單純肯定性質便喪失了,發生變化了。”(《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第152頁)這句話是針對第三種狀態說的。在第三種狀態中,由于勞動者與勞動本身相分離,所以“勞動本身”作為一個要素被突顯了出來。為了相互對應,在其他三種狀態中我們也表明“勞動本身”的歸屬關系。
首先在這里,我們印證了巴里巴爾的一個重要觀點:一種生產方式與另一種生產方式之間的區別是同一些結構性要素的組合方式的區別。[2]勞動者對勞動條件不同的所有制關系形成不同的歷史狀態。根據馬克思的論述,我們可以基本確定,第一種狀態指的是以公共土地所有制為基礎的歷史狀態,包括亞細亞所有制社會、古典古代所有制社會和日耳曼所有制社會。在這些所有制形式中,勞動者可以在土地上獲得幾乎所有的勞動的條件,土地既是勞動工具,也是勞動原料,還可以以果實的形式直接為勞動者提供生活資料。作為共同體成員的勞動者直接占有勞動的條件,這種“勞動同勞動的物質前提的天然統一”[1]的所有制關系,是這種歷史狀態的生產方式的結構。第二種歷史狀態相對應于手工業的生產方式,勞動者“在他個人的勞動之內”[1]占有勞動工具,“原料和生活資料成為手工業者的財產,只是以他的手工業,以他對勞動工具的所有權為中介。”[1]與第一種狀態一樣,在第二種狀態中由于生產還不直接就是商品生產,勞動力還沒有成為一種商品,因此勞動者與勞動本身是直接結合的。第三種狀態是歐洲奴隸制和農奴制社會,在其生產方式中,勞動者只擁有生活資料,土地、生產工具乃至勞動本身這些條件都不歸他們所有。[1]第四種狀態顯然是資本主義社會,在那里勞動者與勞動的全部客觀條件相分離。當然,我們在這里只是根據馬克思的相關論述來規定這四種歷史狀態,對于這些規定會存在一些例外的情況②例如對于第二種狀態,從行會師傅的角度來看,勞動者(行會師傅)直接擁有生活資料,但如果從學徒的角度來看,勞動者沒有直接擁有生活資料(《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49頁);第三種狀態也可能出現在不是奴隸制和農奴制社會的情況,在以土地財產為基礎的原始共同體中,如果勞動者失去了自己土地財產就會出現第三種形式(《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第152-153頁)。,另外馬克思對這四種歷史狀態的排序顯然不是嚴格根據歷史時間來進行的。但是,這些對于我們討論的主題來說都不構成本質的影響,我們只是試圖通過比較這四種生產所有制的內部結構來說明不同的生產所有制之間的區別是一種結構性的區別,即勞動過程中勞動的各種要素之間不同組合方式的區別。
第二個判斷也是結合巴里巴爾的觀點而形成:一種生產結構向另一種生產結構的過渡是結構之間的更替和位移過程,而不是直線運動的過程。[2]上述四種歷史狀態之間可能的過渡(例如第一種狀態[公共土地所有制社會]-第三種狀態[歐洲奴隸制和農奴制社會]-第二種狀態[手工業社會]-第四種狀態[資本主義社會]的過渡)表現為結構與結構之間的更替或位移。這種過渡雖然歸根到底是由于生產力的發展而引起,但不能歸結為是隨著生產力的量的發展而引起的量的變化,而應歸結為由此引起的質的變化。因而這是兩個具有質的區別的結構之間的過渡。在過渡中,舊的結構消失了,新的結構取而代之。以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形成為例,馬克思說:“資本生成,產生的條件和前提恰好預示著,資本還不存在,而只是在生成;因此,這些條件和前提在現實的資本存在時就消失了,在資本本身從自己的現實性出發而創造出自己的實現條件時就消失了。”[1]資本的生成過程與資本主義的現實存在處于不同的生產結構之中,當前者過渡到后者,前者消失了(雖然這并不意味著在同一個歷史空間中這兩者不可以并存),這是因為它內部的要素改變了組合的方式,形成了新的結構即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并被新結構取代。因而整個過渡過程呈現為新結構“更替”舊結構的過程。
既然過渡是新結構對舊結構的“更替”,而不是舊結構直接產生出新結構,那么這就意味著一種生產方式不是以前一種生產方式作為自己直接的形成原因或歷史前提。這樣一來,一種生產方式的結構是如何形成的?它直接的歷史前提是什么?
這是一個重要問題,對此巴里巴爾借用馬克思的再生產概念來進行回答。他認為,一切社會生產其實都是再生產,它不僅是物質產品的生產和再生產,同時還是使得這種生產得以進行的社會關系的再生產,也即是說,“每一種生產方式都不斷地再生產出作為它的運動前提的生產的社會關系。”[2]因此,一種生產方式的歷史前提實現在它的歷史產物中,它的起點就是終點,前提就是結果。我們可以這樣歸納巴里巴爾的這個觀點:一種生產結構的直接前提不是別的,正是這種結構本身。一個結構體只有借助自身的結構形式才得以成為自身。從上述列舉的四種歷史狀態中,我們可以看到,構成一種生產方式的結構的是使得這種生產方式的內部要素得以以一定的方式結合起來的社會關系,即勞動者對勞動條件的所有制關系。任何一種社會生產作為只有借助一定的所有制形式才能進行的社會活動,都必然以這一定的所有制關系為前提,因而也就是以自身為前提;也正因此,這種生產才必然把這種所有制關系當作結果而生產出來。例如在第一種歷史狀態即公共土地所有制社會中,共同體的生產活動必然以共同體成員共同占有勞動條件為前提,而這種所有制關系本身就是共同體的生產方式的結構,因此,共同體的生產方式以自身為前提,并在生產中把這種前提作為結果而不斷再生產出來。
對于資本主義生產來說這一點尤其明顯。馬克思說:“一旦資本成為資本,它就會創造它自己的前提,即不通過交換而通過它本身的生產過程來占有創造新價值的現實條件。”[1]“資本為了生成,不再從前提出發,它本身就是前提,它從它自身出發,自己創造出保存和增殖自己的前提。”[1]勞動者與勞動的整個客觀條件相互分離;勞動力的規模與生產資料的規模必須具有互相適應的、量的關系[3];貨幣財富必須達到“最低限度價值額”才能轉化為資本[4],等等,這些都是資本主義生產具有的結構性規定,用馬克思的一個說法就是“技術上規定的”[3],它們共同形成了資本主義生產的結構形式。資本主義生產只有在具備這種結構形式的情況下才能形成自身,而資本主義的生產就是對這些前提條件的不斷再生產。例如它不斷地加深著勞動者與作為資本的勞動的客觀條件之間的對立關系;由于勞動力的數量和規模必須與生產資料相互對應,資本的規模和勞動生產率的變化使它既吸收工人的同時也游離出過剩人口;它以一定的資本積累為前提,但同時又不斷地引起資本的加速積累。這些都是資本主義以自身為前提而存在和發展的表現。
但是,以自身為前提而形成自身,這是不是意味著一種生產方式的結構能夠從“無”到有地把自己“生產”出來?顯然不是。雖然一種生產方式不能為它的后來者提供新的結構形式,但畢竟能夠為它提供物質內容。以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關系為例,這就是一個涉及資本的原始積累的問題。巴里巴爾認為,資本原始積累之于資本主義生產的關系是,一方面,兩者處于兩個不同的結構之中,另一方面,資本原始積累的過程是“自由”勞動者與貨幣財富這兩個在后來構成資本主義生產的基本要素的各自獨立發展的過程,等到這兩者獨立發展到“能夠結合起來構成(一種生產方式的)結構并從屬于這個結構、成為結構的作用”的程度,它們就構成了一種新的、與各自的形成過程所處的結構完全不同的另一種結構,即資本主義生產的結構。[2]以這種方式,歷史完成了資本的原始積累,為資本主義的形成提供了物質內容,但它并沒有直接提供資本主義生產的結構形式,這種結構形式只是資本主義根據它的內部本質利用這些物質內容而形成。這個充分體現了巴里巴爾結構主義立場的觀點很好地解釋了馬克思思想中資本的“形成史”和“現代史”的關系,只有通過這個觀點,我們才能夠更好地理解馬克思下面這段話:“當資本第一次出現時,它的前提條件本身表現為從外部由流通中來的,對資本的形成來說表現為外在的前提條件,因而不是由資本的內在本質產生的,也不能用資本的內在本質加以解釋。這些外在的前提條件現在表現為資本本身運動的要素,因此資本本身預先要求這些條件成為它自身的要素——不論這些條件在歷史上是如何形成的。”[1]
二
依據巴里巴爾的“引路”,馬克思上述四種歷史狀態共同描繪了這樣一個歷史圖景:歷史的發展是一個個以一定的生產方式為根據而形成的、呈現為結構體的社會形態的不斷更替和位移的過程。這樣一種歷史圖景顯然不同于馬克思所批判的資產階級思想家的歷史圖景,后者由于忽略了歷史運動的結構形式而認為歷史只是一種抽象的、線性發展的過程,從而把當前的歷史狀態理解為此前的歷史狀態的發展目的,它“所說的歷史發展總是建立在這樣的基礎上的:最后的形式總是把過去的形式看成是向著自己發展的各個階段……所以總是對過去的形式作片面的理解。”[1]資產階級思想家就是用這種對歷史的理解方法為資本主義作合理性辯護。例如他們忽略資本的“形成史”和“現代史”之間的結構性區別,把后者看作是前者直線運動的結果,認為在資本主義中資本最初是由資本家從他的勞動產品中節省而來或通過其他一些非雇傭勞動的方式而獲得,這樣資本家用資本來購買工人的勞動力就是公平合理的行為。但是,如果認為這兩者處于不同的結構,因而認為資本主義以自身為前提而形成自身,那么我們很容易看到,在資本主義生產中資本只是通過無償占有勞動者的剩余價值而獲得自身存在的條件,“所有現實的、現有的資本,它的每一要素,都同樣是對象化的、被資本占有的他人勞動,是不經交換、不付給等價物而被占有的。”[1]這樣就暴露出資本主義生產的不合理性。
顯然,這是理解歷史的一種深刻的方法。在第一部分中,我們以巴里巴爾結構主義過渡理論的幾個核心觀點為“路標”,通過自己歸納和整理材料來論述馬克思歷史理論的相關內容,主要是為了證明巴里巴爾對這些內容的闡釋是基本正確的,而且也不乏深刻。借此我們甚至也證明了,巴里巴爾的方法未嘗不是馬克思理解歷史的一種方法,亞當?沙夫就認為,結構性分析法是馬克思主義的歷史方法的要素之一[5]。因此,我們不應該完全拒斥運用結構主義來理解馬克思。但問題是,巴里巴爾到此結束了。他認為到此故事已經講完了。于是我們身處于此,環顧四周,發現馬克思的歷史圖景在這里都被附上了結構主義的色彩。這未必是件好事。
在20世紀,說結構主義是一種文化思潮乃至文化時尚并不為過,在法國,做一個結構主義者甚至成了一種“文化義務”[5],以阿爾都塞為代表的結構主義的馬克思主義受這種思潮的影響而形成。沙夫對結構主義的馬克思主義做出了著名的批判,他指出,阿爾都塞的結構主義的馬克思主義主要有三個特點:主張并認為在馬克思主義思想中具有反經驗主義、反歷史主義和反人道主義的內容。[5]巴里巴爾作為阿爾都塞的追隨者,他的過渡理論也在不同程度上具有這些特點。例如,巴里巴爾認為,我們不能經驗地確定作為理論認識對象的歷史,而必須根據生產結構的作用來“建立實際的歷史”[2],因此我們研究的不可能是“本來意義”的歷史,而是通過一定的生產結構而呈現出來的對象,這是馬克思思想中所具有的理論的而非經驗的特點。[2]這一點滿足阿爾都塞的反經驗主義概念的某些要求,這個概念批判把認識看作是對現成事實的被動反映的理論[5],而認為“科學產生事實”[5]。在反歷史主義方面,巴里巴爾遵循結構主義慣有的做法:重同時性輕歷時性。他認為,歷史的動態發展是“結構內在的發展運動”,“這種運動完全由結構(積累的運動)決定并按照結構所決定的固有節律和速度進行。”[2]它體現的是暫時性概念或同時性概念;一種生產方式向另一種生產方式的過渡并不是歷時性的運動,而是同時性結構的更替,而且它是“比生產方式本身的同時性更為普遍的同時性問題。”[2]歷時性的概念只能在同時性的總問題中來被思考;同時性表現事物發展的非連續性或斷裂性,而歷時性則表現連續性。因此,巴里巴爾重同時性輕歷時性的做法的結果就是認為歷史“斷裂”的歷史:“社會的歷史可以歸結為生產方式的非連續性的更替。”[2]在反人道主義方面,如沙夫所說,巴里巴爾的立場更為“激進”[5]。沙夫指出阿爾都塞的反人道主義概念包含著對馬克思主義思想體系中人的地位的否定[5],巴里巴爾的確具有這種傾向。他認為人是“社會結構中相互聯系的各種實踐的現實的(具體的)承擔者”[2];馬克思在討論勞動時從來沒有說過“人”或“主體”,因而并不涉及“具體的人”,僅涉及在結構中完成某種特定職能的人,即勞動力的承擔者[2];人的“外在軀體”被“代替”了[2],換作社會的或生產方式的結構。這樣,在社會歷史發展中我們就看不到人,只看到一個又一個結構體的過渡,“這種歷史的主體是找不到的。一切局部歷史的真正主體就是各個要素和它們之間的關系所從屬的結合,即某種不是主體的東西。”[2]
到這里我們可以看到,上述結構主義的三種特點結合起來就使巴里巴爾所描繪的歷史圖景成為一幅只見結構不見人的圖景,而且,由于——如詹姆遜所說——連續運動的結構之連續性不過是一種“虛在”的連續性,其實質是“連續不斷的林林總總的斷裂”[6],因而這種表現為結構的連續運動的歷史不過是一種“斷裂”的歷史。如果說,巴里巴爾是在正確地分析了馬克思的相關內容的基礎上形成了這樣一幅不太符合歷史唯物主義主張的歷史圖景,那么,這與其說是他的觀點有問題,還不如說是他還沒有把“故事”講完。他只講了一半,因而使得歷史圖景呈現出一些“虛假特征”,如關于資本主義生產,如果只是孤立地講生產過程而沒有講再生產的內容就會出現“虛假特征”一樣。巴里巴爾之所以沒能講完這個“故事”,是因為他只看到了馬克思生產概念必然形成生產結構這一方面的內容,而沒看到,這個概念同時還有更為本質的一層內容,那就是人與物之間具有社會歷史性質的物質交換過程。
三
我們所要繼續另一半“故事”,不僅建立在上述幾個結論之上,而且還是對這個問題的繼續思考:一種生產結構如何能以自身為前提而形成自身?這不僅是它作為一種“結構”使然,而更是馬克思生產概念中勞動者與勞動對象通過相互規定而相互生成的關系使然。
從物質生產的角度來看,勞動過程的基本要素是:有目的的活動或勞動本身,勞動對象和勞動資料,其中后兩者又表現為生產資料[4]①馬克思在這里對勞動要素的說法是和前面的“五要素說”(勞動者、勞動工具、勞動原料、生活資料、勞動本身)是一樣的。“有目的的活動或勞動本身”包括“勞動者”和“勞動本身”,“勞動對象”包括“勞動原料”和“生活資料”(因為生活資料作為一種通過勞動而形成的東西,它本身也不過是勞動對象);“勞動資料”就相當于“勞動工具”。另外,勞動對象在這里嚴格指那種通過勞動而發生變化的對象,因而不包括沒有經過勞動而存在的對象(例如水里的魚、地下礦藏里的礦石等天然存在之物)。因為前者才是主要的、具有典型意義的勞動對象。不過,后者雖然不是以它的歷史性來制約著人們的勞動,但卻是以它的自然物質性制約著人們的勞動。勞動對象的存在方式無論是什么,都必然在或大或小程度上規定著人們的勞動,使之只能采取這種存在方式所允許的方式進行。。勞動是人和自然之間的物質變換運動,是人消滅物的舊的物質形式而創造出新的物質形式的過程。新的物質形式首先孕育在勞動者的生產目的之中,然后勞動者通過勞動資料而把自己的力量傳導到勞動對象,使這種新的物質形式得以實現出來。這個過程就是新的勞動對象被生產出來的過程。[4]物的物質形式并非與物本身漠不相關,相反,它深入到物的本質存在之中,使得物得以呈現為具體之物。這種物質形式不是純粹自然的,它具有歷史性的規定。物的任何物質形式都是一定的,因為賦予物以這種物質形式的勞動任何時候都是一定的勞動,是通過被一定的社會歷史條件所規定的一定的勞動對象、勞動資料和生產目的而進行的賦形活動。馬克思曾追問:“構成資本的生活資料、勞動工具和原料,難道不是在一定的社會條件下,不是在一定的社會關系內生產出來和積累起來的嗎?”[7]顯然答案是肯定的。從總體(而非個別之物)的角度來看,在任何情況下勞動對象、勞動資料和生產目的都是一定的社會歷史條件的承載者。勞動對象和同樣作為勞動產品的勞動資料任何時候都只能是一定的社會歷史條件的物質化,它們作為通過勞動而改變的對象,必然具有與為它們“賦形”的勞動一樣的歷史性規定。馬克思說,“勞動資料不僅是人類勞動力發展的測量器,而且是勞動借以進行的社會關系的指示器。”[4]由此也可以看出勞動資料的歷史性規定。勞動者的生產目的作為一種觀念也必然受制于一定的社會歷史條件,它是這一定的條件的觀念化。它的能動范圍同樣被這種條件所限定。只有在這個范圍內,人們才擁有將這個目的實現出來的條件;超出這個范圍,要想實現這個生產目的就必須等待新的生產條件的形成。在同一個勞動過程中,勞動的這幾個因素所具有的歷史性規定是基本一致的,它們共同制約著勞動的進行,但同時也受勞動的制約。
一方面,勞動者在勞動過程中要賦予勞動對象以新的物質形式,即產生新的勞動對象,這就意味著它需要破壞和否定舊的勞動對象已有的物質形式。但既然這已有的物質形式作為一定的社會歷史條件的反映,作為一種“舊勢力”,它必然在一定范圍內先行決定著勞動者所能采取的勞動資料和所能形成的生產目的,馬克思說:“人們用以生產自己的生活資料的方式,首先取決于他們已有的和需要再生產的生活資料本身的特性。”[7]這里所謂的“特性”也就是勞動對象所具有的、反映著一定的歷史性規定的物質形式。只有在被這種物質形式規定的情況下,勞動者才能賦予勞動對象新的物質形式。因此,勞動者就是在被自己所要規定的對象所規定的情況下規定著這個對象。
另一方面,勞動對象也在被勞動者所規定的情況下規定著勞動者。勞動對象被一定的勞動者規定,由此勞動對象也以一定的物質形式呈現出來,它作為一種物或使用價值而成為人們的消費(個人的消費和生產的消費)的對象,從而生成著人。物的這一定的物質形式規定了人們只能以一定的方式對之進行消費,而這種一定的消費方式也就生產出一定的消費者,馬克思說:“生產不僅為主體生產對象,而且也為對象生產主體。”[1]不同的消費方式規定了人們不同的存在方式,“饑餓總是饑餓,但是用刀叉吃熟肉來解除的饑餓不同于用手、指甲和牙齒啃生肉來解除的饑餓。”[1]用刀叉來消費熟肉的方式造就了文明的消費者;用手、指甲和牙齒來消費肉的方式只能造就野蠻的消費者。黑人只有在奴隸制下才是奴隸,因為奴隸制的生產方式(即生產性消費的方式)使他成為奴隸,他在資本主義生產中則是雇傭工人,因為這種生產“就是把工人當作雇傭工人來生產”[4]。消費對象的一定的物質形式總是與一定的社會歷史條件相對應,因此,如果說一定的消費對象生產著一定的個人,那么也就是生產著一定的社會歷史條件的人格化。
在勞動者與勞動對象通過相互規定而相互生在的這種關系中,值得注意的還有這一點:那體現在勞動者與勞動對象身上并對它們進行規定的一定的社會歷史條件,不僅是一定的勞動者與勞動對象交互運動的前提和條件,它同時還由這種運動產生出來。馬克思說:“一切生產都是個人在一定社會形式中并借這種社會形式而進行的對自然的占有。”[1]但要注意,這一定的社會形式只是在這一定的生產中才形成。在第一部分中我們已經很清楚地看到,當歷史的發展使勞動者與勞動條件處于一定的關系時,它們便構成一定的生產方式,但這一定的生產方式只有通過勞動者與勞動條件的交互運動中才能實現出來和發展下去。因此,一定的勞動在這個勞動過程中與它的前提條件同時發展,如馬克思說:“資本主義生產是和它的條件同時發展的。”[3]勞動者與勞動條件的一定的關系使得勞動得以以一定的方式進行,這一定的方式在勞動過程中體現為勞動者與勞動條件的存在方式。勞動的條件在這里顯然是指勞動工具和勞動原料等因素,它們作為勞動的產品都是上面所說的勞動對象。因此在勞動過程中,不僅勞動者和勞動對象在相互規定中作為一定的勞動者與勞動對象而不斷地相互生成,而且使得這種交互運動得以進行的前提條件也從中不斷地生成,從而使得整個運動不斷地發展下去,并最終形成一定的社會形態,由此而產生出來的社會關系和政治關系也就被當作一種法的和文化的范疇而確定下來。
這樣一種運動既生產著自我生成的條件,也生產著自我否定的條件。雙方的矛盾發展到自我否定的時刻,就是新的社會歷史條件從潛在狀態轉化為現實狀態的時刻,借此發展到新的程度的勞動者與勞動對象通過相互規定而相互生成,同時產生并發展著這新的社會歷史條件。這是新一輪的式運動。人類社會歷史的運動規律與宇宙天體的運行規律有一種內在的相似性,在談到社會生產規模跳躍式膨脹和收縮的規律時,馬克思說:“正如天體一經投入一定的運動就會不斷地重復這種運動一樣,社會生產一經進入交替發生膨脹和收縮的運動,也會不斷地重復這種運動。而結果又會成為原因,于是不斷地再生產出自身條件的整個過程的階段變換就采取周期性的形式。”[4]在社會歷史的運動中,兩個矛盾范疇的新運動形式的形成恰如一個天體從舊的橢圓運動軌道中逃逸出來的情況一樣:它一經逃逸出來就立刻進入并形成新的橢圓運動軌道,新一輪的運動與使得這種運動得以可能的新運動軌道同時發展。換而言之,勞動者與勞動對象在新的社會歷史條件下通過相互規定而相互生成的物質交換運動,同時也就是這新的社會歷史條件的形成和發展的運動。每一定的社會歷史條件下勞動者與勞動對象的矛盾運動都是以這種方式形成自身、否定自身,并最終過渡到新一輪的運動。這種以自身為前提而形成和發展的過程不僅是“自然界的和人的通過自身的存在”(Durchsichselbstsein)[7],而且還是整個社會歷史通過自身而存在和發展的過程。
上述的討論始終潛在地針對著巴里巴爾歷史圖景只見結構不見人、只有斷裂性沒有連續性的缺點。從討論的結果來看,歷史從來都是連續性的,因為它從來都是人與自然的具有社會歷史規定的、并不斷地產生著一個又一個階段的社會歷史規定的物質交換運動。在任何歷史運動中,正如在馬克思任何時期的活動中一樣,“人都沒有‘死’”[5],而且還不斷地通過社會以介入到自然的存在的方式呈現在歷史之中;正是由于人與自然之間具有社會歷史性質的“二律”相生關系,歷史運動才表現出連續性的特征,雖然就歷史運動的階段性來看,非連續性也始終是歷史運動的另一個特征。因此,巴里巴爾所說的生產方式的結構,在這里應當被理解為一定的勞動者在勞動過程中與一定的勞動對象之間所發生的通過相互規定而相互生成的關系。這樣,我們去除了巴里巴爾過渡理論的“結構”這個外殼,展示了一個“斷”而“不裂”的歷史圖景:“斷”指的是從生產方式的角度來看每一種歷史狀態都是借自身的結構形式而形成的一定的社會關系總和,“不裂”指的是所有這些結構的運動、因而整個歷史的運動本質不過是人與自然通過不斷地形成特定的、具有社會歷史性規定的“二律”相生運動而形成特定的社會形態的過程。
四
[1]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8 卷)[M].人民出版社,2009.31;32;150-153;122;151;151;152;108;108;109;98;30;157;16;16;11.
[2]阿爾都塞,李其慶.讀《資本論》[M].中央編譯出版社,2008.297;296-297;333;341-351;314;302-307;370;380;247;251;308-309;251;305.
[3]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6 卷)[M].人民出版社,2009.33;91;380.
[4]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5 卷)[M].人民出版社,2009.358;208-211;232-243;210;659;124;730.
[5]亞當·沙夫,袁暉.結構主義與馬克思主義[M].山東大學出版社,2009.115;19;57-116;75;63;97;97;97.
[6]弗雷德里克·詹姆遜,胡志國.重讀《資本論》(增訂本)[M].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5.68.
[7]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M].人民出版社,2009.724;519;195;196.
[8]大衛·哈維,謝富勝.跟大衛·哈維讀《資本論》(第二卷)[M].上海譯文出版社,2016.44.
[9]王慶豐.《資本論》的再現[M].中央編譯出版社,2016.28-34;卡萊爾·科西克,劉玉賢.具體的辯證法——關于人與世界問題的研究[M].黑龍江大學出版社,2015.139-142.
B031
A
1002-3240(2017)08-0047-07
2017-01-02
本文系中國人民大學2015年度拔尖創新人才培育資助計劃成果
陳廣思,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馬克思主義哲學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資本論》和歷史唯物主義。
[責任編校:趙立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