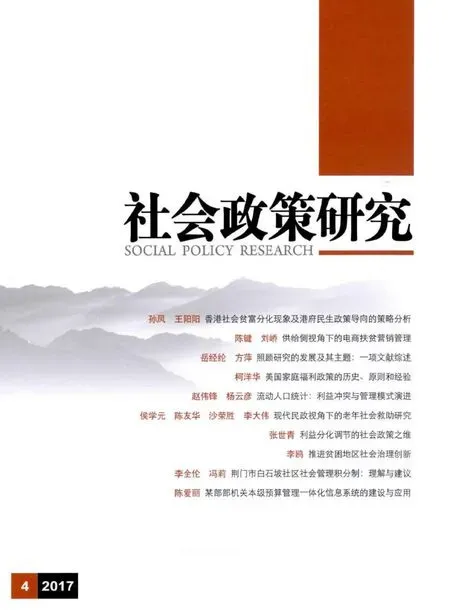利益分化調(diào)節(jié)的社會(huì)政策之維
張世青
一、當(dāng)前中國利益分化的基本表征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全國的利益分化大致經(jīng)歷了這一過程:由計(jì)劃經(jīng)濟(jì)時(shí)期的利益相對(duì)均等化到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時(shí)期的利益嚴(yán)重分化。具體而言,計(jì)劃經(jīng)濟(jì)時(shí)期,由于中國形成了一種總體性的社會(huì)結(jié)構(gòu),國家?guī)缀鯄艛嗔怂械馁Y源,并對(duì)各種資源統(tǒng)一分配(孫立平,1994),在這種社會(huì)結(jié)構(gòu)下,社會(huì)成員間的利益分化程度并不嚴(yán)重。據(jù)世界銀行的測(cè)算,1978年之前,中國的基尼系數(shù)為0.16,處于絕對(duì)公平水平。當(dāng)然,這一時(shí)期帶有普遍貧困的特性。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社會(huì)結(jié)構(gòu)發(fā)生了巨大變遷,地區(qū)之間、城鄉(xiāng)之間、階層之間的社會(huì)異質(zhì)性不斷增加,并致使利益分化的程度在擴(kuò)大,具體有如下體現(xiàn):
一是貧富差距一直處于高位運(yùn)行狀態(tài)。全國性質(zhì)的貧富分化可通過基尼系數(shù)來理解。國家統(tǒng)計(jì)局2013年1月公布的數(shù)據(jù)顯示:2003年的基尼系數(shù)為0.479,2004年為0.473,2005年為0.485,2006年為0.487,2007年為0.484,2008年為0.491,2009年為0.490,2010年為0.481,2011年為0.477,2012年為0.474。盡管基尼系數(shù)有回落現(xiàn)象,但是依然高于國際上通行的0.4的警戒線。這說明,防止貧富分化加劇、實(shí)現(xiàn)共同富裕依然面臨嚴(yán)峻挑戰(zhàn)。
二是城鄉(xiāng)之間的收入差距依然嚴(yán)重。城鄉(xiāng)間的收入差距一直是中國二元社會(huì)最顯著的特征。依據(jù)國家統(tǒng)計(jì)局的數(shù)據(jù),2005~2012年間,城鎮(zhèn)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別為:10493元、11760元、13786元、15781元、17175元、19109元、21810元、24568元;同時(shí)期的農(nóng)村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別是:3255元、3587元、4140元、4761元、5153元、5919元、6977元、7917元。據(jù)此計(jì)算,城鄉(xiāng)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比例均在3倍以上。國際上普遍接受的城鄉(xiāng)居民收入差距之比為1.5倍,發(fā)展中國家的貧富差距也多在1.7倍(湯夢(mèng)玲,2011)。可見,中國的城鄉(xiāng)收入差距分化異常嚴(yán)重。
三是地區(qū)之間的收入水平差距明顯。因地理環(huán)境、經(jīng)濟(jì)基礎(chǔ)、自然資源等方面的差異以及國家對(duì)不同地區(qū)采取異質(zhì)化的發(fā)展戰(zhàn)略,地區(qū)間的收入水平差距較大。據(jù)測(cè)算,1978年中國東北和東部人均GDP為488元/人,中西部人均GDP為271元/人,兩者的差距比例為1.8倍,差距數(shù)為217元/人。2009年,東北和東部人均GDP提高到39024元/人,中西部人均GDP提高到19031元/人,二者的差距比例為2.05倍,差距數(shù)為19993元/人。世界發(fā)達(dá)國家區(qū)域差距一般為1.2倍左右,發(fā)展中國家區(qū)域差距為1.4倍左右(湯夢(mèng)玲,2011)。由是觀之,中國區(qū)域之間收入差距依然很大,且收入差距并沒有得到根本解決。
四是行業(yè)之間存在著顯著的收入分化。行業(yè)間的收入差距主要體現(xiàn)在壟斷性行業(yè)上,而這些行業(yè)多為行政壟斷。根據(jù)經(jīng)濟(jì)學(xué)家王小魯(2007)的測(cè)算,2005年,石油、金融、保險(xiǎn)、電力、電信、煙草、水電氣供應(yīng)等壟斷性行業(yè)共有職工833萬人,不到全國職工總數(shù)的8%,但平均工資和工資外收入總額估算高達(dá)1.07萬億元,相當(dāng)于當(dāng)年全國職工工資總額的55%,多出全國職工平均工資水平的部分約9200億元。根據(jù)國家統(tǒng)計(jì)局2014年公布的數(shù)據(jù),2013年,人均年薪(99659元)最高的行業(yè)仍然是金融業(yè),是人均年薪最低行業(yè)農(nóng)林牧漁業(yè)(25820元)的將近四倍。這一事實(shí)表明,經(jīng)過十余年的收入分配改革,由行政壟斷造成的行業(yè)收入差距問題沒有得到根本控制。
上述利益分化的形成與當(dāng)下我國的初次收入分配制度、市場(chǎng)競(jìng)爭(zhēng)機(jī)制有很大關(guān)聯(lián),也和第二次分配制度不夠完善相關(guān)。實(shí)踐表明,適度的利益分化在一定時(shí)期有助于激發(fā)勞動(dòng)者的創(chuàng)造潛能,也符合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的運(yùn)行規(guī)律。但是,各種排斥性的、歧視性的社會(huì)制度會(huì)造成持續(xù)性的利益分化,而不合理的利益分化須加以調(diào)節(jié)。當(dāng)前我國主要采取規(guī)范壟斷收入、打擊非法收入、提高中低收入者的收入等經(jīng)濟(jì)政策調(diào)節(jié)利益分化。在這種情勢(shì)下,國家可以轉(zhuǎn)變利益分化的治理理念,采取社會(huì)政策這一重要的二次分配手段。
二、利益分化的調(diào)節(jié)需要公正的社會(huì)政策
社會(huì)政策創(chuàng)始人瓦格納認(rèn)為,社會(huì)政策是“運(yùn)用立法和行政手段,以爭(zhēng)取公平為目的,清除分配過程中的各種弊害的國家政策”(曾繁正,2010:165)。從這個(gè)界定看,社會(huì)政策是國家為了解決初始分配導(dǎo)致的利益分化問題,通過對(duì)弱勢(shì)群體、落后地區(qū)的資源或收入的轉(zhuǎn)移支付,從而實(shí)現(xiàn)公平、公正的社會(huì)發(fā)展目標(biāo)而采取的一系列公共政策。西方發(fā)達(dá)國家一直使用社會(huì)政策調(diào)節(jié)因第一次分配所導(dǎo)致的收入差距。研究表明,1980~2000年間,踐行社會(huì)民主主義福利國家模式的瑞典,社會(huì)保障對(duì)基尼系數(shù)調(diào)節(jié)的貢獻(xiàn)率高達(dá)82.5%,稅收政策的貢獻(xiàn)率則為17.5%;同一時(shí)期,即便是實(shí)行自由主義福利國家模式的美國,社會(huì)保障對(duì)基尼系數(shù)調(diào)節(jié)的貢獻(xiàn)率也達(dá)到了55.3%,高于稅收政策的44.7%(陶繼坤,2010)。由此可見,西方國家在調(diào)節(jié)收入分配差距方面,社會(huì)政策比經(jīng)濟(jì)政策的再分配作用更為明顯。
中國政府也通過實(shí)施相關(guān)的社會(huì)政策調(diào)節(jié)收入分配差距,尤其是近些年來更是加大了民生建設(shè)、社會(huì)建設(shè)的投資力度。王延中、龍玉其(2013)指出,我國通過最低收入保障、養(yǎng)老保障、醫(yī)療保障、失業(yè)保障、教育保障等社會(huì)政策加大了對(duì)低收入地區(qū)和貧困人口的轉(zhuǎn)移支付,“在調(diào)節(jié)收入分配中發(fā)揮了一定的作用”。但是,通過社會(huì)政策實(shí)現(xiàn)降低收入差距的預(yù)期目標(biāo)還受到宏觀因素的影響。如鄧大松等(2013)以北京、天津、浙江、江蘇等東部15個(gè)省市為例,發(fā)現(xiàn)“社會(huì)保障轉(zhuǎn)移支付拉大了東部農(nóng)村地區(qū)居民之間的收入差距,對(duì)東部城市居民收入分配調(diào)節(jié)作用不明顯,相對(duì)縮小了東部城鄉(xiāng)居民之間收入分配差距,但是對(duì)整個(gè)東部地區(qū)收入不平等的貢獻(xiàn)率在提高”。究其原因,鄧大松認(rèn)為,區(qū)域間經(jīng)濟(jì)發(fā)展水平的差異以及城鄉(xiāng)社會(huì)保障制度的不完善造成了農(nóng)村居民的社會(huì)保障待遇產(chǎn)生了受損。
由上可見,并不是所有的社會(huì)政策都能有效地縮小地區(qū)之間、城鄉(xiāng)之間的利益分化,有時(shí)反而會(huì)再次拉大收入差距。以養(yǎng)老金雙軌制為例,在養(yǎng)老保險(xiǎn)雙軌制時(shí)期,機(jī)關(guān)事業(yè)單位的養(yǎng)老保險(xiǎn)替代率一般為75%,企業(yè)退休人員自2007年至2014年一直低于50%(鄭秉文,2015)。在初次分配中,企業(yè)與機(jī)關(guān)事業(yè)單位的工資性收入本來就存在差別,通過養(yǎng)老保險(xiǎn)的再分配,不是縮小了收入差距,反而拉大了差距。為解決養(yǎng)老金雙軌制公平性缺失的問題,2015年國家實(shí)施了養(yǎng)老金雙軌制的并軌改革,這是邁向?qū)崿F(xiàn)公平養(yǎng)老保險(xiǎn)制度的重要一步。在并軌過程中,機(jī)關(guān)事業(yè)單位參照企業(yè)年金的做法,增加了職業(yè)年金這一項(xiàng)。與此相照,城鄉(xiāng)居民并沒有職業(yè)年金,且絕大多數(shù)城鎮(zhèn)職工也沒有企業(yè)年金。這就意味著,如果城鄉(xiāng)居民以及企業(yè)退休人員的養(yǎng)老金水平不能大幅提高,那么機(jī)關(guān)事業(yè)單位與城鄉(xiāng)居民及企業(yè)退休職工的養(yǎng)老金待遇仍將難以縮小。
三、公正社會(huì)政策所具備的品格
為治理不合理的利益分化問題,國家需要制定公正的社會(huì)政策。對(duì)何為公正的社會(huì)政策,學(xué)界并沒有統(tǒng)一的認(rèn)識(shí)。關(guān)信平(2013)認(rèn)為,社會(huì)政策的公平性“是從社會(huì)公平的角度對(duì)社會(huì)政策進(jìn)行的評(píng)價(jià),即一個(gè)國家或地區(qū)社會(huì)政策符合主流社會(huì)公平觀的程度,它體現(xiàn)在社會(huì)政策總體水平的合理性和社會(huì)政策行動(dòng)中公共資源分配的合理性兩個(gè)層面”。這一觀點(diǎn)有助于理解何為公正的社會(huì)政策,如遵循公共資源總量和分配的合理性。筆者認(rèn)為,對(duì)公正社會(huì)政策的理解可從其應(yīng)當(dāng)具備的品格來認(rèn)識(shí)。
1. 公正的社會(huì)政策意味著正義
通常而言,正義是與個(gè)人利益、群體利益相對(duì)的。“正義是一種道德命令,它要求我們不應(yīng)該從自己的利益出發(fā)來做出選擇、判斷和決定。正義是一種道德約束,它給我們每個(gè)人的思想和行為施加了公正的道德限制”(姚大志,2001)。當(dāng)涉及到財(cái)富、機(jī)會(huì)和權(quán)力等利益的分配時(shí),如果沒有公開、透明的正義分配規(guī)則,那么人情、關(guān)系、潛規(guī)則等不正當(dāng)手段就會(huì)介入,結(jié)果造成公正的社會(huì)政策無法實(shí)現(xiàn)。
2. 公正的社會(huì)政策意味著平等
公正的社會(huì)政策須保證一國公民擁有同等的權(quán)利和機(jī)會(huì)獲得相應(yīng)的社會(huì)福利資源。考諸西方福利國家的發(fā)展史可以發(fā)現(xiàn),只有社會(huì)政策追求權(quán)利平等和機(jī)會(huì)平等時(shí),才能有效化解階層間的利益分野和沖突。如圈地運(yùn)動(dòng)時(shí)期的英國、工業(yè)革命時(shí)期的德國、經(jīng)濟(jì)大危機(jī)時(shí)期的美國,這些國家無不是借助比較公正的社會(huì)政策來保障社會(huì)成員(尤其是底層社會(huì)群體)享有平等的社會(huì)保障權(quán)和勞動(dòng)就業(yè)權(quán),此舉一并緩和了勞資矛盾、官民矛盾,推動(dòng)了社會(huì)有序轉(zhuǎn)型。反觀社會(huì)保障制度“碎片化”現(xiàn)象嚴(yán)重的法國,由于不同行業(yè)、職業(yè)、族群間的社會(huì)保障制度的公正性缺失,罷工、上街游行等群體性事件時(shí)常上演。以至于有學(xué)者(鄭秉文,2008)認(rèn)為,法國的社會(huì)保障制度不但沒有成為社會(huì)的“安全網(wǎng)”,反而演變成了社會(huì)沖突的“火藥桶”。
3. 公正的社會(huì)政策意味著公共理性
羅爾斯認(rèn)為,公共理性是民主國家的基本特征,它是公民的理性,是那些共享平等公民身份的人的理性。公共理性的目標(biāo)是公共善,這是“政治正義觀念對(duì)社會(huì)之基本制度結(jié)構(gòu)的要求所在,也是這些制度所服務(wù)的目標(biāo)和目的所在”(約翰·羅爾斯,2011)。社會(huì)政策作為國家調(diào)節(jié)收入分配為全體社會(huì)成員謀取福祉的一種重要手段,在社會(huì)政策的諸環(huán)節(jié)也需要公共理性,這是一項(xiàng)社會(huì)政策能否實(shí)現(xiàn)公正的必要條件。而缺乏公共理性,僅憑精英傾向或民粹傾向均會(huì)導(dǎo)致社會(huì)政策的不公。研究表明,當(dāng)前有些階層成員心理存在著某種被剝奪感,這種被剝奪感一是表現(xiàn)為客觀的失去,即已經(jīng)有的東西被剝奪;二是主觀的不滿足,即認(rèn)為自己應(yīng)該有的東西卻沒有得到,在需求和獲得之間出現(xiàn)了差距(王磊、胡鞍鋼,2011)。具有公共理性的社會(huì)政策將有效縮減不合理的利益分化,從而降低公眾心里的被剝奪感。
據(jù)上所析,社會(huì)政策只有體現(xiàn)正義、平等和公共理性,才有可能保證第二次分配不至于再次拉大收入分配差距。因此,為切實(shí)有效的調(diào)節(jié)利益分化,必須制定和實(shí)施公正的社會(huì)政策,并在源頭上做好制度性的預(yù)防。加之當(dāng)前中國正步入“社會(huì)政策時(shí)代”(王思斌,2004),與民生相關(guān)的社會(huì)政策正密集出臺(tái)以及社會(huì)建設(shè)的財(cái)政投入力度逐年加大,在此大背景下,出臺(tái)和實(shí)施公正的社會(huì)政策就更加重要。
四、公正社會(huì)政策的實(shí)現(xiàn)
吳忠民(2004)認(rèn)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社會(huì)政策價(jià)值理念的演化軌跡是從“平均走向公正”,并主張以現(xiàn)代的公正觀作為社會(huì)政策的立足點(diǎn)。結(jié)合公正的社會(huì)政策所需具備的品格,筆者認(rèn)為,公正的社會(huì)政策的實(shí)現(xiàn)可從如下方面著力探索:
1. 社會(huì)政策的受惠對(duì)象應(yīng)以公民身份為標(biāo)準(zhǔn)
英國社會(huì)政策大師馬歇爾首先提出,公民身份主要由公民的民事權(quán)利、政治權(quán)利和社會(huì)權(quán)利所組成。 “公民身份是一種地位,一種共同體的所有成員都享有的地位,所有擁有這種地位的人,在這一地位所賦予的權(quán)利和義務(wù)上都是平等的”(馬歇爾,1949,轉(zhuǎn)引自:郭忠華、劉訓(xùn)練,2007)。可見,公民身份的精髓在于,凡一國之公民,均有平等的資格以充分享受該國所賦予的各項(xiàng)權(quán)利,而不是有選擇性地賦予特定的社會(huì)階層,除非有法律的明文規(guī)定。顯然,一種理想的社會(huì)政策模式是建立全國統(tǒng)一的以公民身份為資格的社會(huì)政策,因?yàn)檫@是實(shí)現(xiàn)權(quán)利主體平等的必要條件。
有學(xué)者認(rèn)為,由于中國地域之間發(fā)展水平不同,社會(huì)政策呈現(xiàn)著地方化的現(xiàn)象,且福利地區(qū)逐漸形成,遂提出可以首先建立以地域公民身份為標(biāo)準(zhǔn)的社會(huì)政策,然后再建立以全國統(tǒng)一的公民身份為資格來制定社會(huì)政策。也就是“在一定地域的范圍內(nèi)建立了統(tǒng)一的社會(huì)福利制度,這種不分戶籍身份、不分職業(yè)群體的社會(huì)福利制度有利于形成‘地域公民身份’”。從長遠(yuǎn)發(fā)展看,“‘地域公民身份’在空間上的不斷擴(kuò)張無疑將有利于全國統(tǒng)一的‘公民身份’ 的形成”(岳經(jīng)綸,2010)。然而,當(dāng)前中國社會(huì)政策已呈現(xiàn)碎片化現(xiàn)象,具體表現(xiàn)為:一是因職業(yè)、行業(yè)的差異而實(shí)行不同的政策體系,如社會(huì)保障領(lǐng)域就存在著城鎮(zhèn)職工、城鎮(zhèn)居民、機(jī)關(guān)事業(yè)單位的養(yǎng)老保險(xiǎn)、醫(yī)療保險(xiǎn),并且社會(huì)保險(xiǎn)的繳費(fèi)主體、繳費(fèi)標(biāo)準(zhǔn)、保險(xiǎn)水平等方面明顯不同;二是因戶籍制度不同而采取城鄉(xiāng)有別、地域有別的社會(huì)政策體系,如城鄉(xiāng)在教育資源、公共衛(wèi)生資源、社會(huì)救助等領(lǐng)域均是一種非均等化的供給體系。此時(shí)如果再發(fā)展以地域身份為要件的社會(huì)政策,則容易造成地區(qū)之間社會(huì)福利水平更加分化。因此,應(yīng)積極探索如何實(shí)現(xiàn)以全國統(tǒng)一的公民身份為基礎(chǔ)的社會(huì)政策。
2. 社會(huì)政策的“政策導(dǎo)向”上升為“法律導(dǎo)向”
社會(huì)政策的“政策導(dǎo)向”一般指國家或政府機(jī)關(guān)為達(dá)到某種目標(biāo),根據(jù)當(dāng)前的經(jīng)濟(jì)社會(huì)發(fā)展?fàn)顩r制定的相關(guān)行動(dòng)方案,其多以條例、規(guī)定、草案、意見、辦法等方式呈現(xiàn)。社會(huì)政策的“法律導(dǎo)向”主要是國家或政府的行動(dòng)方案,由全國最高權(quán)力機(jī)關(guān)制定法律,并在全國范圍內(nèi)強(qiáng)制實(shí)施。不難發(fā)現(xiàn),“政策導(dǎo)向”的社會(huì)政策容易使政府就特殊狀況做出靈活反應(yīng),而且執(zhí)行起來高效、迅速,亦可以擺脫以往政策的約束。然而“政策治國的另一缺陷是由于缺少制度上的糾錯(cuò)機(jī)制,一旦政策不對(duì)路,實(shí)施的效率越高,不良的后果越發(fā)嚴(yán)重”(智賢,1995:74)。美國人類學(xué)家斯科特通過考察前蘇聯(lián)、坦桑尼亞等國的歷史發(fā)現(xiàn),那些試圖改善人類狀況、提高人類福祉的大工程和大項(xiàng)目,在缺乏民主討論的“偉大政策”指引下,大都以失敗而告終,從而更加劇了人們生活的困苦(詹姆斯·C·斯科特,2008)。
西方福利國家的發(fā)展歷程體現(xiàn)的也是以“法律導(dǎo)向”作為根基來保障社會(huì)政策的有效實(shí)施。如1601年英國的《舊濟(jì)貧法》;19世紀(jì)德國制定的《疾病社會(huì)保險(xiǎn)法》《工傷事故保險(xiǎn)法》《老年和殘障社會(huì)保險(xiǎn)法》等社會(huì)保險(xiǎn)法;1935年美國制定了《社會(huì)保障法》《全國勞資關(guān)系法》《緊急救濟(jì)撥款法》等法律;1942年,隨著《社會(huì)保險(xiǎn)和相關(guān)服務(wù)》(又稱《貝弗里奇報(bào)告》)的出臺(tái),英國相繼頒發(fā)了《教育法案》《國民保險(xiǎn)法案》《國民健康服務(wù)法案》《就業(yè)政策白皮書》《家庭津貼法案》等一系列社會(huì)法。實(shí)言之,社會(huì)政策的“法律導(dǎo)向”是依法治國的具體實(shí)踐。“法律導(dǎo)向”的社會(huì)政策,在制度上明確了政府的權(quán)責(zé)以及公民的義務(wù),此有助于遏制政府利用公權(quán)力為權(quán)貴階層或特殊個(gè)人謀取不當(dāng)?shù)美?/p>
3. 社會(huì)政策諸環(huán)節(jié)力求程序公正
程序公正經(jīng)歷了從自然公正觀到正當(dāng)程序觀的演變。自然公正觀通常表示處理紛爭(zhēng)的一般原則和最低限度的公正標(biāo)準(zhǔn),又稱為“訴訟程序中的公正”(龔祥瑞,1993:126),它要求“任何人不能自己審理自己或與自己有利害關(guān)系的案件”,“任何一方的訴詞都要被聽取”(戴維·M ·沃克,1988:628)。正當(dāng)程序觀要求“解決爭(zhēng)端的程序必須公正合理”,而且“個(gè)人的權(quán)利都由正當(dāng)程序保護(hù)”(肖建國,1999)。程序公正觀不僅影響了英美法系國家的司法體系,也深刻地影響著這些國家的政策制定。
程序公正的理念對(duì)公正的社會(huì)政策的實(shí)現(xiàn)至少體現(xiàn)在兩個(gè)方面:
一是社會(huì)政策諸環(huán)節(jié)廣泛的公民參與。為確保一項(xiàng)社會(huì)政策或制度的公正性,廣泛的公民參與必不可少,因?yàn)椤罢呓^不能僅僅理解成官方聲稱的目標(biāo),而且還包括廣闊范圍內(nèi)的所有參與者之間被模式化了的行為方式,這樣人們才能夠了解要發(fā)生的事情”(H.K.科爾巴奇,2005:21)。一般而言,社會(huì)政策的諸環(huán)節(jié)包括議程設(shè)置、制定、實(shí)施、評(píng)估與變動(dòng)等,公民參與這些環(huán)節(jié)也是國家充分運(yùn)用公共理性以獲取公正的社會(huì)政策的需要。以新醫(yī)改為例,2005年7月國務(wù)院發(fā)展研究中心葛延風(fēng)得出了“我國醫(yī)改基本不成功”的論斷,至此拉開了醫(yī)療衛(wèi)生體制新一輪改革的序幕,直到2009年4月《中共中央、國務(wù)院關(guān)于深化醫(yī)藥衛(wèi)生體制改革的意見》的出臺(tái)。這一過程歷經(jīng)了政策議程設(shè)置、備選方案的設(shè)計(jì)和選擇、最終方案的內(nèi)部醞釀、公開征求意見和醫(yī)改意見最終出臺(tái)五個(gè)環(huán)節(jié)。在每個(gè)環(huán)節(jié),政府充分聽取了來自學(xué)術(shù)和政府研究機(jī)構(gòu)、民眾乃至外國政策專家、世界衛(wèi)生組織對(duì)醫(yī)療改革的意見和建議。社會(huì)各界廣泛參與的醫(yī)療改革,不僅有利于確保社會(huì)政策的合法性和公正性,也為涉及公共性社會(huì)政策的制定樹立了典范。
二是與社會(huì)政策相關(guān)的信息要公開透明。為擴(kuò)大公民參與和保障公民參與的有效性,信息的公開透明非常必要,特別是牽涉到與政策相關(guān)的利益群體時(shí),傾聽社會(huì)政策的受益者、受損者的聲音,更是保障公民知情權(quán)、參與權(quán)和監(jiān)督權(quán)的重要方式。而暗箱操作、信息壟斷、“民意被代表”等非正常化的社會(huì)政策運(yùn)行方式可能在政策的制定上具有較高效率,但缺失了民意的充分表達(dá)和不同利益主體間的博弈,政策的合法性將打折扣,最終也不利于社會(huì)政策的有效運(yùn)行。因而,為保障社會(huì)政策的公正性,信息的公開透明尤為重要,當(dāng)然這種信息應(yīng)當(dāng)全面、可靠和真實(shí)。
4. 國家應(yīng)大力向弱者和貧困地區(qū)提供更多的福利資源,并謹(jǐn)防“負(fù)福利”現(xiàn)象
從對(duì)福利供給的對(duì)象看,社會(huì)福利可分為選擇型福利和普惠型福利。其中,選擇型福利主要以家計(jì)調(diào)查作為福利提供的依據(jù),其對(duì)象多為社會(huì)中的弱勢(shì)群體,如下崗失業(yè)人員、貧困人口、殘疾人等;普惠型福利主要以公民身份作為福利提供的依據(jù),受惠對(duì)象一般是全體人民或某一群體的所有社會(huì)成員,如兒童福利、老年人福利。考諸西方福利國家的發(fā)展史,不難發(fā)現(xiàn)它們大都是先采取選擇型的福利,通常優(yōu)先保障社會(huì)中的弱者,其后才是面向全體人民的普惠型福利。本質(zhì)而言,在公共資源一定的情形下,國家應(yīng)當(dāng)遵循“最少受惠者最大利益”的分配原則,此乃一種“公平的正義”。
如果我們認(rèn)同福利應(yīng)首先保障弱勢(shì)群體的話,那么當(dāng)下及未來對(duì)各種福利資源進(jìn)行配置時(shí)就應(yīng)當(dāng)避免“負(fù)福利”現(xiàn)象。秦暉(2010)將福利的再分配反倒增加了不平等、拉大了收入差距這種反向的福利調(diào)節(jié)叫做“負(fù)福利”。回顧中國社會(huì)福利的發(fā)展歷程可以發(fā)現(xiàn),“負(fù)福利”現(xiàn)象確實(shí)存在。研究表明,在計(jì)劃經(jīng)濟(jì)時(shí)期,個(gè)人就職何種性質(zhì)的單位以及在單位中擔(dān)任何種職務(wù),就決定了一個(gè)人的級(jí)別。級(jí)別不僅體現(xiàn)了個(gè)人社會(huì)地位和級(jí)別的高低,也反映出不同級(jí)別的人與各種資源、利益、機(jī)會(huì)之間的關(guān)聯(lián)。比如在單位的住房分配過程中,除了工作年限外,主要考慮的就是個(gè)人的行政級(jí)別(李漢林,2004:55)。
中國業(yè)已提出建立適度普惠型社會(huì)福利制度的構(gòu)想,也就是使社會(huì)福利惠及所有老年人、殘疾人和困境兒童。因此,中國社會(huì)福利的發(fā)展面向是全力避免“負(fù)福利”,摒棄社會(huì)福利政策的“逆向調(diào)節(jié)”現(xiàn)象。走出“負(fù)福利”邁向“正福利”的方式可從如下三個(gè)方面考慮:一是在保障對(duì)象上,在對(duì)所有弱勢(shì)群體(如“三無人員”、低保者、農(nóng)民工、殘障者)普遍保障的基礎(chǔ)上,逐漸向其他群體推進(jìn),直至惠及全體國民;二是在保障地域上,繼續(xù)加大對(duì)農(nóng)村公共物品的供給力度,還應(yīng)提高對(duì)落后地區(qū)的財(cái)政轉(zhuǎn)移力度;三是在保障水平上,由滿足社會(huì)成員的基本生存需要向更高水平的生活需要邁進(jìn)。
公正的社會(huì)政策并不是靠朝夕之力就能形成的。如在全國實(shí)行統(tǒng)一的以公民身份為標(biāo)尺的社會(huì)政策還需要在眾多制度方面進(jìn)行改革:跳出“政策治國”的傳統(tǒng)觀念,踐行“法律治國”的理性思維,尤其是良法善治的理念,需要政府及民間的合力推動(dòng);程序公正既要求政府釋放權(quán)力,也要?jiǎng)?chuàng)設(shè)公眾參與政策制定和利益表達(dá)的機(jī)制;在權(quán)力監(jiān)督機(jī)制不完善的狀況下,“負(fù)福利”現(xiàn)象的根除也非易事。顯然,公正的社會(huì)政策的實(shí)現(xiàn)需要一個(gè)過程,這個(gè)過程可能漫長,但追求公正社會(huì)政策的步伐不能放慢。
參考文獻(xiàn)
[1]孫立平等,《改革以來中國社會(huì)結(jié)構(gòu)的變遷》,《中國社會(huì)科學(xué)》,1994年,第2期。
[2]湯夢(mèng)玲,《中國“三個(gè)差距”(貧富、城鄉(xiāng)和區(qū)域)的現(xiàn)狀及對(duì)策》,《經(jīng)濟(jì)研究參考》,2011年,第71期。
[3]王小魯,《灰色收入拉大居民收入差距》,《中國改革》,2007年,第7期。
[4]曾繁正,《西方國家法律制度社會(huì)政策及立法》,紅旗出版社,1998年,第165頁。
[5]陶繼坤,《西方國家社會(huì)保障制度調(diào)節(jié)收入分配差距的對(duì)比分析》,《當(dāng)代經(jīng)濟(jì)研究》,2010年第9期。
[6]王延中、龍玉其,《社會(huì)保障與收入分配:問題、經(jīng)驗(yàn)與完善機(jī)制》,《學(xué)術(shù)研究》,2013年,第4期。
[7]鄧大松、仙蜜花,《社會(huì)保障轉(zhuǎn)移支付對(duì)收入分配差距的調(diào)節(jié)效應(yīng)》,《社會(huì)保障研究》,2013年,第6期。
[8]鄭秉文,《機(jī)關(guān)事業(yè)單位養(yǎng)老金并軌改革:從“碎片化”到“大一統(tǒng)”》,《中國人口科學(xué)》,2015年,第1期。
[9]關(guān)信平,《朝向更加公平、平等和高效的社會(huì)政策》,《廣東工業(yè)大學(xué)學(xué)報(bào)》(社會(huì)科學(xué)版),2013年,第3期。
[10]姚大志,《呼喚公正》,《天津社會(huì)科學(xué)》,2001年,第4期。
[11]詹奕嘉,《低保“含金量”高了,“關(guān)系保”“人情保”也多了》,《新華每日電訊》,2012年12月31日。
[12]魏文彪,《保障房受益數(shù)據(jù)緣何遭質(zhì)疑》,《證券時(shí)報(bào)》,2012年8月6日。
[13]鄭秉文,《法國社保制度:安全網(wǎng),還是火藥桶?》,《社會(huì)科學(xué)報(bào)》,2008年3月20日。
[14]約翰·羅爾斯,《政治自由主義》(增訂版),萬俊人譯,譯林出版社,2011年,第197頁。
[15]王磊、胡鞍鋼,《中國社會(huì)管理創(chuàng)新的制度背景》,《探索與爭(zhēng)鳴》,2011年,第9期。
[16]王思斌,《社會(huì)政策時(shí)代與政府社會(huì)政策能力建設(shè)》,《中國社會(huì)科學(xué)》,2004年,第6期。
[17]吳忠民,《從平均到公正:中國社會(huì)政策的演進(jìn)》,《社會(huì)學(xué)研究》,2004年,第1期。
[18]馬歇爾,《公民身份與社會(huì)階級(jí)》,載:郭忠華、劉訓(xùn)練,《公民身份與社會(huì)階級(jí)》,江蘇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5頁。
[19]岳經(jīng)綸,《建構(gòu)“社會(huì)中國”:中國社會(huì)政策的發(fā)展與挑戰(zhàn)》,《探索與爭(zhēng)鳴》,2010年,第10期。
[20]智賢,《Governance:現(xiàn)代“治道”新概念》,載:劉軍寧等,《市場(chǎng)邏輯與國家觀念》,三聯(lián)書店,1995年,第74頁。
[21]詹姆斯·C·斯科特,《國家的視角》,王曉毅譯,社會(huì)科學(xué)文獻(xiàn)出版社,2008年。
[22]徐道穩(wěn),《中國社會(huì)政策轉(zhuǎn)型研究》,南開大學(xué)博士論文,2007年,第22頁。
[23]杜飛進(jìn),《我們應(yīng)該建設(shè)一個(gè)什么樣的政府》,《學(xué)習(xí)與探索》,2011年,第1期。
[24]龔祥瑞,《西方國家司法制度》,北京大學(xué)出版,1993年,第126 頁。
[25]戴維·M ·沃克,《牛津法律大辭典》(“自然正義”詞條),光明日?qǐng)?bào)出版社,1988年,第 628 頁。
[26]肖建國,《程序公正的理念及其實(shí)現(xiàn)》,《法學(xué)研究》,1999年,第3期。
[27]H.K.科爾巴奇,《政策》,張毅等譯,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1頁。
[28]秦暉,《謹(jǐn)防“負(fù)福利”再創(chuàng)新高》,《經(jīng)濟(jì)觀察報(bào)》,2010年12月24日。
[29]李漢林,《中國單位社會(huì)》,世紀(jì)出版集團(tuán)、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33頁。
[30]楊繼繩,《再談公務(wù)員福利分房》,《炎黃春秋》,2010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