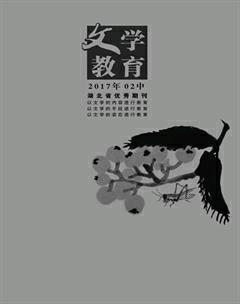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為何及如何
內容摘要:在技術理性的時代,人文學科的存在受到人們的質疑。作為一名中國現當代文學的研究者,文學研究應該為何以及如何?文學表達了人在面對存在時的情感與反應,個體需要拒絕遺忘,保持精神性和先鋒性,以回應復雜的時代精神狀況。
關鍵詞:技術理性 中國現當代文學
在技術的時代,人文學科的存在受到質疑。柏拉圖式的對純粹思辨的興趣,在技術和群體的包圍下,面臨著巨大的危機。人的自我實存、人的高貴性,漸漸被遺忘。工具理性成為社會思潮的主導,人的完整性遭到分割。大學的學科劃分和研究也走向破碎。中國現當代文學,狹義上屬于文學范疇,廣義上屬于人文學科。文學與社會學、心理學、歷史學等人文學科的不同在于它指向人的實存,表達人在面對世界時的情感與反應。它記錄了人在面對存在時的喜悅與興奮,恐懼與顫粟。在技術統治世界時,文學更需要為機器統治下的時代提供溫度。
中國現當代文學,是現代大學學科范疇下的一個分支。在技術理性的時代,各行各業被劃分得細致。個體的存在被固定在一個具體的位置,處于龐大社會機器上的一環。個體的自我實存不斷受到擠壓,或者消失。技術的統治只需要各就其位的螺絲。任何企圖僭越秩序的個體都會受到警告。可是,人文學科的存在,即使人文學科自身受到技術的滲透,依然為個體找回自我實存提供精神資源。人的高貴僅僅表現于存在力圖實現自身的上升運動之中。這也許就是人文學科,中國現當代文學學科的存在意義。我們需要它提供愛、情感、道德等非理性因素,來對抗工具理性的冰冷。中國現當代文學學科研究的個體,時刻不能忘記其肩負的使命。不能在技術統治下物化、群體化,失卻個體實存的獨立聲音。雖然,這很理想化。
人類在20世紀經歷了兩次世界大戰,西方自文藝復興以來的人文價值、理性價值受到質疑。高高在天的那個人的存在也遭到懷疑。人類歷史上從來沒有面對如此普世性的價值與信仰危機。雖然早在19世紀克爾凱郭爾和尼采率先就對天國的那個人的存在發出挑戰。東方也不例外。不過,與西方遭受的信仰危機不同,東方是在遭到技術理性的沖擊后開始反省。日本在1868年后進入“明治維新”時代,清王朝則在一次又一次與西方工具理性的交鋒下在1911年走向滅亡。按照目前學科體制的劃分,以進化論時間觀為指導,中國現代文學是在滿清王朝逐漸滅亡的時候產生的。所以,在中國現代文學產生的源頭,存在強烈的技術理性思維,渴求以技術理性對抗西方武力的侵略。“五四”時期,“德先生”(democracy)與“賽先生”(science)的口號成為當時的時代主潮。反倒是魯迅,在當時清醒地看到更深層面的人的實存,揭示出傳統中國思維中的“劣根性”。只是,“救亡”很快壓倒“啟蒙”。所以,中國現代文學在20世紀30年代后有“席勒化”的傾向。知識分子逐漸依附于群體、政治。1949年,當中國大陸實現社會主義革命后,個體實存被逐漸取消。文學的存在意義在于與政治合作,鞏固意識形態的地位。層級分明的作家協會、報刊、審查等組織的建立,知識分子被納入體制,或者,不合作的個體則遭到放逐。這一僵化的文學制度到后來愈發可怖。當今天我們回過頭去思考現當代文學的發展歷程時,這一災難性的場景依舊令人類深思。我們不由自主地想起東方另一個國家發生的事情。具有反諷意味的是,斯大林式的文學制度對取消個體實存的企圖,在中國大陸起到了更有效的作用。這一現象值得中國知識分子的反思。
當學科也被納入體制,成為強大的國家機器的一環,個體在此時面臨著選擇。一方面,各類協會的建立,有效地將個體存在進行收編和改造。群體不需要異質的聲音。整齊、統一是其特性。國家機器的運轉,個體各就其位形成合力,是群體最希望看到的。另一方面,人是高貴性的生物,在面對集體無意識時,個體渴望突圍實現自我實存。可是,在技術的時代,個體選擇突圍存在巨大風險。人被限制在社會的各行各業。人類必須通過在龐大機器下的勞作才能獲得生活資料。而且,鮮明的層級的存在使得個體渴望在國家機器中到達金字塔尖。雖然幾乎沒有個體能夠最終完成這一夙愿。不過這卻符合國家機器設定者的初衷。所以,個體的反抗意味著將失去生活資料的來源。這是現代個體喪失自我實存的很大原因。除卻層級森嚴的體制秩序,國家機器中的審查、暴力機構的存在,也無時不刻地對個體進行監督。而這些機構營造的恐怖氣氛,讓個體在實現自我實存時蒙上了陰影。在過去發生的災難中,國家機器不僅取消個體的獨立性,還通過暴力取消個體身體的合法性。卡夫卡在《城堡》中營造的現代人在面對冰冷的、無所不在的,卻又不可見的國家機器,讓每一個個體不禁毛骨悚然。更可怕的是,當K面臨審判的時候,卻沒有具體的原因。
那么,在面對無所不在的秩序時,個體要放棄自我實存,與群體合流嗎?“秩序井然的機器嚴格地界定了被原子化的人的功能、義務和權利,所有的人都被視作完全可以互換的東西,這樣它就壓制了創造性,壓制了個人的冒險,因為這些因素威脅了秩序。”①維護秩序成為了國家機器存在的因由。可是,即使在斯大林時期,俄國也有布羅茨基、帕斯捷爾納克等個體保存其存在的尊嚴,在十年浩劫中,遇羅克、張志新、顧準也沒有喪失個體實存,雖然他們的身體的合法性最終被取消。借用魯迅的一句話,“自己背著因襲的重擔,肩住了黑暗的閘門,放他們到寬闊光明的地方去。”②雖然那個肩住黑暗閘門的人可能最終會被黑暗所吞噬,但是一絲光明滲入了鐵屋子,會刺痛更多個體的雙眼。放棄自我實存,個體將被群體收編。而保存個體實存,將為日漸僵化的技術時代帶來活力。時代的進步需要創新與變革,需要有個體對國家機器的秩序提出質疑。這是美好的愿望,也是魯迅在《摩羅詩力說》中一直呼喚的精神界戰士。中國現當代文學具有先鋒性,它的發展將一直處于未完成性中,反映時代的精神狀況及個體在面對復雜時代時的困惑。
作為現當代文學研究領域的原子化個體,必然面臨技術理性和國家機器的限制。在技術時代,工具理性成為時代主潮,個體的價值被機器物化和量化。于是,作為一門更強調“務虛”的學科,它不能直接創造物質價值,自然受到冷落。而龐大的國家機器更無孔不入,為維持其秩序,對持異端聲音的個體進行收編和整合。各類文學團體、組織、評獎機制、期刊審查,共同構成機器的運行秩序。個體要實現實存價值,面臨嚴峻的考驗。所以,面對挑戰,不僅中國現當代文學學科,更是人文領域需要思考的問題。只是,在強大的秩序下,當前的狀況不容樂觀。知識成為部分人手中的膏腴之具,成為走向機器金字塔尖的工具。個體的生存離不開生活資料,如果將其視為目的,以知識作為手段,與國家機器合謀,這是時代面臨的困境。時代呼喚有良知的聲音。我們經歷了太多歷史的災難。在文革結束后,很多個體在面對指責時,沒有反思,將災難指向國家機器。可是,正是那些喪失個體實存的人與國家機器的合謀,才導致一場持續十年之久的浩劫。但最終,沒有個體承擔責任,所有的指責指向一個大寫的群體:國家機器。
拒絕遺忘,保持精神性與先鋒性,是現當代文學學科研究需承擔的責任,也是時代對她的期盼。個體的實存不僅在于要實現其生活資料,更應有更高意義上的追求。面對復雜的時代精神狀況,我們不需要精神的贗品。面對一個具體的作家作品,我們需要有合理的價值判斷。個體的獨立聲音很刺耳,也會給個體自身帶來痛苦。面對日漸秩序井然的國家機器,若沒有吶喊,沒有狂人,鐵屋子將愈加牢固,將壓制更多的個人主體性。而如果學科的研究者們放棄個體實存性,人文精神的未來將走向何方?作為一名剛入門的中國現當代文學專業的研究生,曾滿懷高韜的理想主義,可是在經過一年的學習后,也曾產生過懷疑與虛無。生活中存在一種無形的秩序,它迫使一切事物、一切人都為它服務。它消滅任何它不能容納的東西。人看來就要被它消化掉,成為達到某一目的的純粹手段,成為沒有目的或意義的東西。教育也成為其中的一環。可是,絕望之為虛妄,正與希望相同。時代的美好正在于其復雜性、多樣性與不可預見性。正像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其揭示人的靈魂的深與復雜,呈現個體存在的多樣性。因此,即使荒誕如一些歷史事實,也有地下文學發出異質的聲音。國家機器所希望達到的絕對的秩序井然是不存在的。現當代文學學科需要在這個時代發出獨立的聲音。
注 釋
①[德]卡爾·雅斯貝爾斯:《時代的精神狀況》,上海譯文出版社2013年版,第49-50頁。
②魯迅:《魯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135頁。
參考文獻
[1]魯迅.魯迅全集.[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
[2[德]卡爾·雅斯貝爾斯[M].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13.
(作者介紹:吳泰松,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在讀碩士,研究方向:海外華文文學,中國現當代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