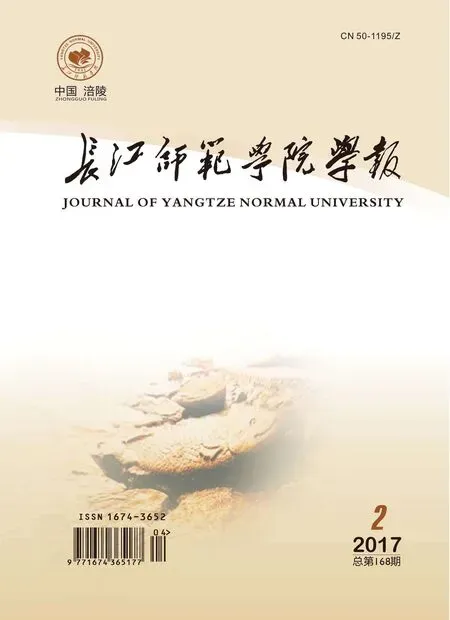《黃金時代》:存在主義的東方式言說
崔金巧
(河南大學 文學院,河南 開封 475001)
《黃金時代》:存在主義的東方式言說
崔金巧
(河南大學 文學院,河南 開封 475001)
《黃金時代》作為王小波的發軔之作,其為20世紀中國文學留下的智性讀解空間與西方存在主義有著特定的意義關聯。文本以其自由敘事肌理網結,無論是對孤獨個體的發現與關注、生存困境背后荒謬存在的意義追尋、還是對人類終極存在的詩性回歸訴求,無不充盈著西方存在主義置于中國現代性語境后的東方式理念闡述。
王小波;《黃金時代》;存在主義;荒謬
置身于20世紀晚期中國文壇的王小波,最為敏感地捕捉到了全球化狀態下中國現代性歷程的困境,《黃金時代》作為我國的先鋒性作品便順利進入到一種關于“存在”的東方體驗與言說。從現有研究成果來看,論者涉及到了文本敘事藝術、作者思想淵源以及性描寫等方面,其理論援引無外乎巴赫金的狂歡化理論、福柯的權利理論等。但是運用存在主義理論觀點解讀該作品的研究視點,僅限于西方文學對中國文學整體影響上的零星介紹,或止于少數顯性話語分析。而《黃金時代》文本敘述的表意空白所顯現出的存在主義特征,諸如人生虛無之境的心靈體驗、他人地域與自由理念的質詢等,無疑是開啟其文學迷宮的一個重要入口。于此,要從根莖上解讀該先鋒作品的源流性存在,存在主義視域下的文本研究有著重要的思辨性價值。
一、孤獨個體的拷問:此在的迷失
作者王小波借助“王二”形象以一場精神上的絕對拷問游戲消解了看似神圣莊嚴的世界。而作為此在的迷失,作品展現了對孤獨個體的強烈關注。王小波作為敘述人于生活與文本構筑的開放性空間之自由出入,更是渲染著一種悖謬與反諷,乃至其寫作行為本身似乎都是一種布滿痛楚與迷惘的實踐。
“存在”的人面對的是“虛無”,當人類個體感知到自我本源性破碎的真實,卻又不得不承擔起已然“在世”的存在,背負起孤獨個體直覺體驗中的無家可歸感,實照應著存在主義的應運而生。《黃金時代》中王二與陳清揚間生成的系列話語解決的無非就是“我是誰”及“我在哪里”的命題。文本敘事是圍繞“考證陳清揚是否是破鞋”的問題展開的。當然,王小波最為質樸的行動表達在于“反面論證”。作品開頭的情節復述便是以序列性否定推動“辨偽”敘事邏輯的。值得玩味的是,王二的“理性推理”表面上合乎情理,但回歸事件本身又充滿怪誕。文本對破鞋的定義在于“偷漢子”。首先,陳清揚認為自己沒有偷漢子,自我認定自己非破鞋,然而他人對其是“破鞋”的指認行為又讓她無意識承認自己是破鞋這個前提,不然,又何須證明呢?“我”的存在要以他者存在之否定為前提,本身就是一種潛在枷鎖。其次,王二從邏輯上證明了陳清揚不是破鞋,但該證明又非嚴謹,因為“偷漢子”行徑存在自身也無從辯證。若陳清揚是“明火執仗”與某個男人有染,是否就在邏輯上擺脫了“偷”的概念?同時指認本身亦存在非議,如果說陳清揚偷了漢卻沒被發現,是否該認定為“無”?若出現有指認效力的偽人證、物證,那么即便不是罪犯,又何以推脫?于此意義上,“眼見為實”不也難逃一種荒謬?作品中對于搞破鞋事件,可謂多方各執一詞,其立場的復雜也促生了作品本身的妙趣橫生。于此,我們不禁反思,難道關于“破鞋”問題僅是一個道德層面上的困境嗎?不然,其深層含義更在于個體生存狀態的思考。當王二和陳清揚真正達到了“偉大友誼”的實現,將破鞋行徑公之于眾時,不僅他者回歸到了詢問的原點,就連陳清揚本人也因此獲得了精神上的解脫,“用不著再去想自己為什么是破鞋”[1]41。自我精神上對否定之否定的前提捕捉到,否定了定義之有也便獲得了定義之無。正如海德格爾從他人對自我異化角度談人的非本真生存方式,人們將異化理解成人生存的普遍形式。他者在自我形成過程中的介入,也使自我永久的被限定在異化的境地[2]51。王小波有意讓“破鞋”的問題成為無從考證的事件,意在闡釋“真相之無”這樣一個存在性理念,即當人的存在被遺忘后,真相不可能獲得檢驗。在缺少終極價值的環境中,“自我”在與社會的疏離中不斷被遮蔽,找不到存在的位置,孤獨個體自我身份拷問的意義也便在這里。
《黃金時代》中的個體孤獨等陰郁心情與文本表層敘事的“狂歡”“戲謔”可以說形成了一種反差極大的閱讀體驗,以存在主義美學視角觀察文本,能夠讓我們更好的捕捉作者冷幽默背后的嚴肅主旨。如果說“破鞋證偽”事件反映的是遺忘自我存在帶來的生存疏離的話,那么“斗破鞋”的罪孽交代則揭露出荒謬世界里個體生命的荒涼與堅韌。王二和陳清揚的關系從無罪到數次交代間罪惡檔案袋的不斷變大,而其罪孽交代的真相無外乎就是評論界所鄙夷的大量“性描寫”。行動造就本質,直至批斗結束時對“愛情罪孽”的承認,可以說陳清揚找到了“我之為我”的一種自在。“誰也不這么寫交待。但她偏要這么寫”[1]46,因為愛情是罪上之罪,誰也無法處理如此大罪,只能放了他們。王二和陳清揚以精神上、性愛上的放浪不羈對抗著文本中頻繁出現的“證明”“交代”等詞,正是通過放棄自我思考和自我選擇的自由,使自己“物化”成“自在的存在”。如果說愛上王二之前,陳清揚接受王二是出于一種受虐心理,那么當陳清揚愛上王二,她與王二的情愛就包含了自我選擇。所以陳清揚說,“以前她承認過分開雙腿,現在又加上,她做這些事是因為她喜歡。做過這事和喜歡這事大不一樣。”[1]46的確,“喜歡”在于“自我”自由精神意志的選擇,在此意義上也便承擔了自己為此所應負的責任:認為自己“并不清白”。她也因此從一個在世界荒誕面前企圖逃避的“怯懦者”變成了敢于承擔的“荒誕英雄”式人物,這是一種“回歸本我”的表現。“實際上我什么都不能證明,除了那些不需證明的東西。”[1]5于社會規范而言,觸犯必要獲得訓罰,不然規范就會崩塌,文本卻以“干破鞋”事件與“愛情”的等同勾畫將其徹底顛覆。陳清揚借大罪否定有罪,敘述回到起點,于此,王二看到陳清揚“她那破裂的處女膜長了起來”[1]45,成為了《黃金時代》畫龍點睛的一筆。但敘述的結束并非意義的完結,個體生命面臨的依舊是赤裸裸的時間侵襲。而對于經歷了這樣一場“文革”浩劫的世界存在依舊是一種實在,不是嗎?
王小波的寫作風格某種意義上說是自我對話式的,是對自我存在的追問。規訓式社會中,當面具下的自我認同陷入日常思維慣性,存在的本真意義又何所是?事實上,“我”抑或“王二”們無論在自我身份上做何種轉換都無法逃脫荒誕的生存處境。唯此,王小波才能于過去、現在和未來間穿梭自如,直述歷史表象遮蔽下的生存真相,拷問存在本身的純粹狀態。《黃金時代》中諸多敘述是借助山上自然世界與山下現實世界兩維空間構筑的,“空間變換,如此高高在上的空間,再次從現實中脫序,這正好是脫序的王二所處境遇的一種象征。”[3]個人存在的追問是赤裸裸的,為“性”添加了很多附加值,以獲得精神上的安慰與困境中的突圍,而把存在的意義從終端遷回到過程,這種行為方式本身確是帶有存在主義烙印的。
二、生存體驗的求證:存在的荒謬
眾所周知,“黑色幽默”作為王小波寫作的標簽性存在,“它的哲學理論主要建立在現代反理性的哲學即弗洛伊德主義、柏格森的直覺主義、存在主義,尤其是薩特的存在哲學之上”[4]33。王小波以一種存在勘測者身份的回望姿態,以及切身的生存體驗勾勒出了那個時代人的精神狀況和生存情境。從文革中的怪誕到人性中的怪誕,文本超越性背后與其說是一種醒世恒言式的憂患,倒不如說在于一種生命存在的哲學思考。存在的荒謬作為一種形而上、無根由的沖突,既是一種可望不可及的痛苦,又何嘗不是一種西西弗斯的幸福?從意義的構成去尋找路徑和出口,《黃金時代》中,作者從“性愛”和“政治”兩個敏感維度展開鋪敘,除了對人類存在境遇可能性方面的反思外,還在于對存在荒謬性的求證立場。
“性愛”可以說貫穿《黃金時代》始終。何謂愛,何謂性?毋庸置疑,性而上的“靈”與愛而下的“肉”是人類愛欲得以實現的兩種基本形式,兩者間的對立與兩難則顯示了人類對把握自我的無能為力,于此構成了個體生命的存在悖論。某種程度上說,性愛作為王小波文本寫作的對象與載體,儼然隱藏著一種重大隱喻。《黃金時代》中陳清揚“破鞋證偽”事件發展以王二與其真正“搞破鞋”得以扭轉,于是兩者之間的復雜關系成了文本一荒謬視點。“破鞋”罪名與性之間的相互扭曲,使得害怕陷入生存困境的陳清揚,經歷了一場由性的試驗、交流到情愛的演變過程。最終在陳清揚的材料“交代”中,她將被遮蔽的“性”化成了發自內心的“愛”擊潰了“破鞋說”,當然事實上,自王二成了她的“野漢子”時該困擾就已自動瓦解了。該細節意義在于,王二和陳清揚以人性上的無拘釋放和性愛上的自由狂放宣告了神圣莊嚴的權力專制的無能為力。在交待材料的述罪場景中,“性”無疑成了世界此在灰暗、無趣底景上的化妝狂歡,甚至成為進入那個時代夢魘般的迷宮索引。性作為隱私性存在,王小波卻將其放置于“存在”的核心曝露人的存在窘境,以探尋人性的幽深,在此意義上,性描寫應歸還至靈魂原屬中去,尋求一種自由的存在狀態。“想吃和相愛都是人性的一部分,如果得不到就會成為障礙。然而,在我的小說里,這些障礙本身又不是主題。真正的主題,還是對人的生存狀態的反思。”[5]34人物在對政治極權的反抗中,正是以性愛作為支撐力量和武器來對抗存在的荒謬的。于此,性愛與政治作為文學的重大資源,可謂隱藏著有待揭示的人之存在的本質,其在弘揚精神自由、洞照存在之思方面具有無可替代的作用。如果說《黃金時代》中的“性”違規之行對公認道德規范的突破屬于生存狂歡的話,那么,王小波的“性愛細節”對公認道德的沖擊實屬敘述之狂歡。陳清揚行其所行,對傳統共識提出挑戰,直陳愛情,不僅顛覆了俗世的生存觀,甚至對神圣提出了全新的定義。正如敘述者說陳清揚像“蘇格拉底對一切都一無所知”[1]42,烏托邦式性狂歡,也只能就此結束。跳出意識形態圈,對性進行去蔽還原,將歷史之上的文化代碼一一解開,王小波完成了其“存在論”視野中的審美建構。
“文革”在文化學上的重要特點之一,在于它極端的荒誕性。王小波在《黃金時代》中以自由不羈的話語方式展現了一種歷史生存本真的鏡像,表現出世界的荒誕性及人生的虛無性,引申契合著西方存在主義文學的話語闡釋。有論者將王小波這種融合歷史記憶于個人經驗中追尋存在的寫作方式命名為“直接存在主義”或者“超級存在主義”[5]388。的確,王二所面臨的生存境遇看上去荒唐怪誕,但恰恰就是那段歷史的真實場景,每個個體都在角色中經歷著自我的消長,某種意義上,我們甚至可以說《黃金時代》延伸了“倫敦天空的發明者”[1]361的展現維度。于荒誕中揭示文革的內在邏輯是王小波該文本的整體底色,其用一種漫不經意的筆調寫滑稽之中蘊含血淚的生活場景,以其表面的偉大壯麗與本質的極端丑鄙兩種完全錯位的東西無縫地親合為一體,其結果只能是無與倫比的荒誕。當然,較之社會生活語言荒誕更深刻的乃是整個社會思維邏輯的荒誕。如陳清揚等人物一開始所恪守的邏輯全然是一種極端荒誕邏輯,甚至有一種充滿鬧劇性的詭譎效果。鑒于文本作者述說的場外性與目的性,“文革”荒誕性的成因更在于文化構成的詭異:除了它自身原始的文化基因,還會借助一些現代性的控制形式。對比西方現代主義文學中的荒誕意象,如《鼠疫》中的鼠疫、《城堡》中的城堡、《審判》中的法庭等,均體現出一種讓人無從認識理解的距離感。也正是文本對此種“巫魅”文化的特殊“場效應”描寫,觸及了“文革”的深層邏輯。“文革”的文化構成使其荒誕加劇了極端自由性,并由此升華成了一種絕對存在,于是違反人類文明基本邏輯的現象組合成了隨處可見的尋常之物,如王小波筆下的“牛屎”等。當然,所有真實的存在都有其不可言的視點所在,有些狂歡性情節,在文革中或許不可能發生,因為我們體驗到的文革酷行,完全無法寫成如此酒神式狂歡敘述,而王小波把文革寫得如此輕松,不是對歷史的扭曲嗎?如此而言,荒謬世界的再現無法離開“想象”“幽默”等手法的運用,而且是以只有那個時代的人們才狂熱信奉的邏輯,《黃金時代》文字恣肆狂放,故事視點無限夸張放大,但這種荒唐更在于一種荒誕小說模式的構筑,即對中國這一特定年代下人性之本的挖掘。在此意義上,它可以無限地膨脹原有荒誕,甚至任意衍生荒誕中的新荒誕,以便完成由“事件性”到“本體性”的升華。加謬說:“一個哪怕可以用極不象樣的理由解釋的世界,也是人們感到熟悉的世界。然而一旦世界失去幻想與光明,人就會覺得自己是陌路人。”[6]6時代總是不斷地制造神圣與新生事物,于是生存體驗鏡相的表達必在于一種殘暴酷虐的極致展現,而這本身又何嘗不是一種荒誕?于此,《黃金時代》里的文革描寫具備了極為深刻的美學意義。
三、詩性回歸的訴求:存在之“思”
本源詩性聯結存在,王小波的《黃金時代》是一場從本源性探尋到生存之思的超越過程。海德格爾說:“必須有思者在先,詩者的話才有人傾聽。”[7]作者從王二的夢走入陳清揚的夢再回歸到自己的夢,可以說其文學形象加諸了對存在方式與意義的深入探索,荒誕和存在于作者筆下都有了本體性意義。無論是對個體存在“虛妄”境況的省視還是對“沉默的大多數”生存困境的體察,存在與虛無在現實困境中的自我救贖無不渲染著敘述語境中的潛在訴求。顯然,從反社會的生命哲學到以和諧為準則的生命詩學,文本的終極魅力更寄意于東方式“詩意的棲居”。
《黃金時代》中那成長起來的處女膜是引人深思的,其話語在于探尋人類所遺忘的存在以及生存狀態中展現出來的多種可能性。尼采的《權利意志》中寫到:“虛無主義是迄今為止對生命價值解釋的結果。”[8]3其實王小波的自由立場中兼存著尼采式的虛無主義思維。在詩意匱乏的年代,各種社會枷鎖某種程度上加速了自然個體對存在本真的偏離,“既然非本真性生存不可或缺,人的沉淪以及連帶著的人類思維用 ‘非道德’來指涉的生存現象就都有了出場的必然性、合理性。”[9]274-275存在與虛無,看似矛盾的概念結合體,卻對客觀境況道出了生存的意義。世界得以永存不正得益于希望與絕望所共有的虛妄特質嗎?王小波曾以一個登山家的故事幽默回應“為什么寫作”的問題,“有人問一位登山家為什么要登山。誰都知道登山這件事既危險、又沒有什么實際的好處,他回答道:‘因為那座山峰在那里’。”[10]135王小波此回答的用意無非在于表達藝術的一種生成性、敞開性探尋。有研究者指出,王小波的創作是“曠野上的漫游”[11],“曠野”應該代指的就是前文所提及的虛無。同時學界對其“反烏托邦寫作”的定位,其實追蹤到根源上仍舊源于虛無主義藝術。由于“王二們”存活的時代特性,王小波將實存世界照“反烏托邦”的面目描寫,依托的不正是那套“革命時期”的邏輯推理嗎?概言之,“反烏托邦寫作”中王小波的用意在于回歸人生虛無之境以尋求自我存在的精神解脫。于此,《黃金時代》文本自身的功能性便體現在對生命存在之謎的勘探,而文本敘說的虛幻奇譎所顯現出的自由敘事質地,無不與“自由”的虛無之境或者“虛無”的自由之思相關。人物顯像成了為解釋存在而存在的實驗性編碼,其敘述在解碼過程中既表現一種戲謔中的嚴肅,又彰顯一種對遺忘存在的可能性敞開。于虛無中尋求價值,只有如此才能于存在與本真的質詢中得以自由思索。
存在主義的人生是痛苦的,但存在方式卻是可以自由選擇的。就像“王二”這個形象,承受了那個年代知青們身體與心理上的雙重壓力,沉默和反抗兩種選擇使他在本能反映下選擇了后者,即尋求生存的異化。同時,文本最具諷刺意味的是陳清揚需要證明自己不是“破鞋”的時候,世俗總是不能包容她,當她真的做了“破鞋”的時候,反而得到群眾的諒解,這也是人生生存方式的異化。“人先是一種非本真的生活狀態,從某種意義上說,非本真使本真有了選擇的可能。”[8]109世界的荒謬性也在于此,不同向的生存境遇產生了一場王二與陳清揚間的“偉大友誼”,但依舊不能否認這是特定條件下的自由選擇。薩特將存在方式分為“自在的存在”與“自為的存在”兩種。前者在于說一種本真自由選擇后的實在;而后者要以前者為基礎性存在,沒有“自在”的“自為”將流于抽象。在此基礎上,可以斷言“自為”的絕對自由性以及人的本質性自由。回歸到的現實存在的話,人作為孤獨個體沒有選擇環境的自由,但擁有做出選擇的自由,當然這種自由的后果便是所謂的生存困境帶來的迷失感。而自由選擇本身的自由仍舊會步入另一種瓶頸,即逃避自由或否認對現存不合理存在的證偽。由此而言,生存困境其實并不僅僅是外在規則的禁錮壓力,根源在于存在者放棄自由選擇的路徑。另外,《黃金時代》以敘述之輕再現生存之重的寫作技法,與米蘭昆德拉的名作《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有某種驚人的相似。托馬斯的生活顛簸,無不在暗示著輕與重相對存在。而陳清揚開始一直覺得搞破鞋是罪,到最后真搞了破鞋,反而失去了負罪感,直至最終回歸到自己和王二之間的愛情原罪。一切皆在于自我意志轉移之后的輕重轉化,不是嗎?一旦離心產生,便會產生生命失去依托的恐懼。所謂向心之重,其實就是作為一種救命稻草性質的心理向度。從某種意義上,選擇是絕對的。這看上去好像只是形式主義,但是在限制隨心所欲上卻非常重要。生命個體在知曉生存的虛無之后,仍然有活下去的希望,也即薩特所說的“存在主義是一種人道主義”[12]24。當然,海德格爾說的“現代”是一個貧乏的時代,也并非說現代缺乏一般的意義與價值,而在于說它缺乏詩性的真理。現實生存的世界皆屬于人為意志等構成的非本真基礎,而所謂詩性的真理乃是本真存在的自由游戲意義。現實真實所謂的“無”其實來自于一個沒有地基支撐的“虛無”處境,孤獨個體無家可歸的絕對命運。此處的“家”乃指本真的家,即本真的世界[13]。在遺忘了 ‘本原性關聯’的世界里,也只有來自本真深處的詩與思的對話保持并傳達著本源性的言說,能夠穿越黑暗遮蔽達到一種存在的澄明。故王小波說:“一個人只擁有此生此世是不夠的,他還應該擁有詩意的世界”[14]246。所謂“詩意的世界”,我們認為應該就是生命個體本真存在生發出來的詩之思,而《黃金時代》文本自身價值也便在于一種由來已久的精神召喚。
綜上所述,《黃金時代》為20世紀中國文學留下的讀解空間,無疑充盈著西方存在主義置于中國現代性語境后的東方式理念闡述。文本無論是對此在迷失的個體價值追問、生存荒謬的反面求證、還是人類生存終極意義的思考與探索無不顯現出其幽默話語背后的存在主義哲思。于此,《黃金時代》作為存在主義視域下的研究文本,可以說對解開覆蓋于非本真表意層上的文化代碼有著可行的現實意義。
[1]王小波.黃金時代[M].南京:譯林出版社,2015:5-361.
[2]蔣承勇,等.20世紀西方文學主題研究[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3:51.
[3]陳曉明.重讀王小波的《我的陰陽兩界》[J].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1(12):55-72.
[4]任小玲.美國黑色幽默小說研究[M].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06:33.
[5]韓袁紅.王小波研究資料[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34-388.
[6][法]加繆.西西弗斯神話[M].杜小真,譯.北京:三聯書店,1987:6.
[7]張文初,牟方磊.《存在與時間》的情感論[J].中國文學研究,2011(1):14-18.
[8]李天英.存在主義美學智慧與文學精神[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5:3-135.
[9][德]馬丁·海德格爾[M].林中路,孫周興,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97:274-275.
[10]王小波.我的精神家園[M].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1997:135.
[11]易暉.曠野上的漫游——讀王小波[J].北京社會科學,1998(4):86-92.
[12][法]讓-保羅·薩特.存在主義是一種人道主義[M].周煦良,湯永寬,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5:24.
[13]余虹.虛無主義——我們的深淵與命運[J].學術月刊,2006(7):14-22.
[14]王小波.青銅時代[M].廣州:花城出版社,1997:246.
[責任編輯:志 洪]
I206.7
A
1674-3652(2017)02-0098-05
2017-01-16
崔金巧,女,河南鶴壁人。主要從事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