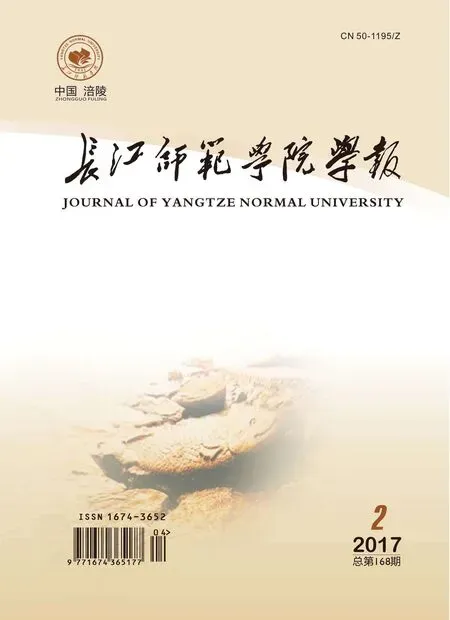加里·斯奈德詩歌中的禪宗意識
邱食存
(1.四川文理學院 外國語學院,四川 達州 635000;2.西南大學 中國新詩研究所,重慶 400715)
加里·斯奈德詩歌中的禪宗意識
邱食存1,2
(1.四川文理學院 外國語學院,四川 達州 635000;2.西南大學 中國新詩研究所,重慶 400715)
美國后現代性思潮受到了禪宗特別是“離兩邊”思維與“空無”理念的重要啟發。興起于1950年代的美國后現代主義詩歌普遍沾染了強烈的禪宗意識。加里·斯奈德是這一派詩人最為重要的代表之一。作為禪宗“平常心是道”的具體體現,斯奈德詩歌大多來源于日常生活,體現出一種身心合一的生活態度。其次,斯奈德詩歌少有自我主體意識,缺少西方傳統詩歌中的內在理性邏輯,結構松散,這種“無我”之空性意識使得萬事萬物在斯奈德詩歌中自然呈現。
加里·斯奈德;禪宗;“平常心是道”;“無我”;后現代性
每到一個社會的重大轉型時期,那些渴望突破傳統而又沒有多少話語權的人們總會把目光投向異域文化,從中汲取可供改造、轉化和吸收的養料與啟發,從而創造出足以對抗傳統的新的理論與實踐。美國的1950年代就是這樣的重大轉型時期。“垮掉派”“黑山詩派”等新一代詩人在美國時下嚴苛的政治、社會和文化現實之下奮起反抗,發動旨在反叛象征型現代主義詩歌的變革運動,拉開美國后現代主義詩歌創作的大幕,這與他們普遍從佛教禪宗中找到各自的精神旨歸有很大關聯。為了對抗美國現代主義中強勢的歐洲傳統,“垮掉派”等新一派詩人們在把目光回溯到龐德-威廉斯“美國本土主義”的同時,更注重吸收海外那些契合美國當下后現代時代精神、可以為其所用的思維和理念。畢竟,“從中國人的觀點看,后現代主義可能被看做是從西方傳入中國的最近的思潮。而從西方的觀點看,中國則常常被看作是后現代主義的來源。”[1]而中國文化中最具有后現代性特質的莫過于禪宗了。在反二元對立思維方面,禪宗中的“離兩邊”與“空無”等思維和理念同后現代性思想頗具“異質同構性”[2]。加里·斯奈德是新詩人中最具有禪宗意識的詩人之一。
一、“離兩邊”思維與“空無”理念
對“垮掉派”詩人影響最大的禪宗經典主要是《金剛經》《壇經》和《心經》。《金剛經》是佛陀通過回答其十大弟子中號稱“解空第一”的須菩提的提問而宣講的佛法,全文不著一“空”,但通篇都是關于“空”的智慧,如“不住于相”“凡所有相皆是虛妄。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不應住色生心”[3]。
《壇經》把觀念分成36對,包括“邪與正對、癡與惹對、愚與智對、亂與定對、慈與毒對”等,這似乎也是一種二元對立式的劃分,但《壇經》接著說:“出入即離兩邊,自性動用。共人言語,外于相離相,內于空離空。”[4]《壇經》又云:“佛法是不二之法。佛性非常非無常,是故不斷,名為不二。佛性非善非不善,是名不二。蘊之輿界,凡夫見二。智者了達,其性無二。無二之性,即是佛性。”[5]這種“離相亦離空”的“不二”與“離兩邊”思維,對待萬事萬物不斷然肯定,也不完全否定,不執著于是非善惡。
《般若波羅蜜多心經》,即《心經》,也注重“離兩邊”與“空無”等思維和理念。經文中提到的“四諦”(“苦、集、滅、道”)、“五蘊”(“色、受、想、行、識”)、“六根”(“眼、耳、鼻、舌、身、意”)及其對應的“六塵”(“色、聲、香、 味、觸、法”)所統攝的大千世界、萬事萬物,無一不具有“空性”,就連“空”的概念本身也是“空”。既然都是空,還有什么值得執著?所以要破除“我執”以求得“無明”境界。這樣,《心經》強調萬事萬物都存有各種可能性,看似對立之物也可以相互轉化,如“正即是反,反即是正”(《心經》中的“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與“不正不反”(《心經》中的“不生不滅”)[6],這種思維打破二元對立思維,即令二元混同。正是在這一點上,解構主義“呼應了禪宗反邏輯的、斷裂式的思維”[7]。德里達對強調超驗所指和自我身份定位的邏各斯(Logos)(指“原初意義”“中心”),“絕對”概念的解構也必然會導致一種“去中心”“無中心”的現實圖景。
二、平常心是道
后現代主義具有強烈的批判精神,這種批判同“實現人的美的生活緊密地結合在一起”,相應的批判活動也就成了“一場生活和藝術的游戲”[8]。從“垮掉派”詩人所普遍看重的禪宗“空無”理念來看,所謂“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所說的并不是一般意義上的那種完全遠離現實世界、摒棄所有意識思維的“空虛”,相反,禪宗注重日常生活中的生命體驗,強調的是“平常心是道”。馬祖道一禪師曾說:“平常心是道。謂平常心無造作、無是非、無取舍、無斷常,無凡無圣。經云:‘非凡夫行,非賢圣行,是菩薩行。’”[9]這里所說的“平常心”可以說是排除“二元對立”思維的自然之心,崇尚天然自在的狀態,反對人為的浮夸矯飾的言行態度。正如史特倫(Frederick J.Streng)所理解的那樣。
“空無”是對日常生活的認知,但又不依附于日常生活。它認識到各具特色的實體、自我、“善”與“惡”以及其它實踐中的方方面面;但這種認識是基于這些事物的空無品性。這種智慧并不是某種神秘性的入迷狀態,而是日常生活中對自由的享受。[10]
說到底,“空無”不僅僅是一種理念,它更是一種生活態度。
加里·斯奈德詩歌大多來源于日常生活,可以說是禪宗“平常心是道”的具體體現。日常生活中的勞作是斯奈德詩歌的重要主題之一。對于詩人而言,專注于日常勞動是“艱辛而又愉悅的任務”[11],與修行無異,體現的是一種身心合一的生活態度。
換地漏、擦水龍頭、參加集會、收拾屋子、洗盤子、查油表——不要認為這些會干擾你從事更重要的追求。我們為“道”而進行修行,但這樣一輪家務活并不是我們基于此而希望能逃離的困擾——日常勞動就是我們的道。[12]
這種身心合一的生活態度在詩歌《籬笆樁》(“Fence Posts”)被發揮到了極致。
我可以加點煤油
70美分一加侖
這是你在酒館附近買油的費用
達到防水效果得用3.50加侖
外加半罐5加侖的,6美元,
來涂刷120個籬笆樁
選用液材的話,我可以節省30美元但你得算上你的時間成本[13]
詩人絮絮叨叨,用平淡無奇的口吻細述如何做籬笆樁這一“小事”,沒有任何象征性暗喻。對于斯奈德,寫詩和做籬笆樁一樣,都是勞動,都要放空自己的各種欲望、不求深刻,專注于萬事萬物的“真如”實性,才能身心合一。
日常生活中,粗俗語也是一種真實,難以回避。在《漿果宴席》(“The Berry Feast”)中,他寫道:
“去他媽的!”郊狼號叫著
跑掉。
……
唱著歌,一個酒鬼突然來個急轉彎
靚妞!快醒來!
要夾緊腿,把邪惡
從胯下擠出來
瞪著紅眼的家伙快來了
軟的勃起了,假裝虔誠的哭泣
滾到太陽下,曬干你僵直的身體![14]
在《作為一名詩人你應該知道些什么》中,他寫道:
親魔鬼的屁股,吃屎;
搞他角狀帶倒鉤的雞巴,
搞女巫,
操所有的天使
和金燦燦芳香的少女——[15]
在當時的時代背景中,在被視為高雅的詩歌中使用粗俗話具有強烈的反叛破壞意味,表達了他們真實的內心感受。
三、“無我”之空性
斯奈德對禪宗觀念的接受首先源于其出生于對基督教持強烈批判態度且在政治上也一直有反叛傾向的家庭。斯奈德認同“局外人”身份,對待美國資本主義和西方形而上學等主流話語往往采取一種邊緣人的心態,其詩作往往顛覆二元對立思維,強調差異之中的和諧一體性。斯奈德對禪宗思想的信仰,打破了“柏拉圖—笛卡爾的主觀/客觀、身/心、人/自然、自然/超自然的二元論”[16],讓詩人可以跳出諸如內在世界/外在世界、理智/非理智與主體/客體等二元對立思維的局限。斯奈德詩歌少有自我主體意識,缺少西方傳統詩歌中的內在理性邏輯,結構松散,有種“濃厚的非我論傾向”[17]。這種“無我”意識使得萬事萬物在斯奈德詩歌中自然呈現:隨意并置,沒有闡釋,缺乏意義,現代主義那種線性時間意識也不見蹤跡。對于詩人,事物就是事物本身,而暗喻、象征、結構等等不過是現代主義強加之物,只會讓詩歌陷入僵化的定式思維,扼殺詩歌的生命活力;詩歌就是事物的自呈現,即“自然而來”[18]。這種開放性的詩歌賦予了讀者更多的想像空間。
有學者認為“無我”意識具有很強的后現代主義色彩:“不少后現代詩人發現,要想寫出最能表達自我真實的詩歌,先得放空武斷的自我,因為夾雜著人的各種復雜角色的各類文明因素早已把自我真實變得模糊了。”[19]斯奈德對“空無”頗有體悟,對“空”的翻譯使用過不同的英語詞匯,如“emptiness”“empty”“nothing”“void”等等。斯奈德曾在日記中寫道:“形式——在恰當的點把事物省掉 /橢圓,空(emptiness)。”[20]在之后的另一篇日記中,他寫道:“空(empty)水杯與空無一物(full of nothiing)的宇宙一樣空 (empty)。”[21]
《心經》篇幅簡短且意蘊無窮,可能是斯奈德最為鐘意的禪宗經典了。斯奈德一直推崇玄奘的一個主要原因是玄奘當年從印度帶回并翻譯了梵文版《般若波羅蜜多心經》,他在詩中寫道:“佛教學者——朝圣者,帶回了著名的《心經》——這一頁濃縮了全部超凡智慧的哲理經典——在他的背囊中。”[22]
斯奈德也曾談及他對《金剛經》的體會:昨夜幾乎悟到“無我”。我們可能認為,“自我來自于某種普遍的、無差別的事物,也會回歸其中。”事實上,我們從未離開過,何來回歸。/我的語言慢慢消退,意象變得模糊。蘊含著萬千變化的事物從未改變;恒久未變,時間也就沒有意義;沒有時間,空間也就消弭。我們隨即歸于空無。/“須菩提,若菩薩有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即非菩薩。”/“你做菩薩,我做出租車司機,送你回家。”[23]
斯奈德體悟到的“無我”體現的正是《金剛經》所反復宣講的“空無”(斯奈德使用的是void)觀。“凡所有相皆是虛妄”,萬事萬物真正的“實相”是“無相”“空無”才是一切法、名、色、相的本性,獨立于時空之外,既然人們“從未離開過”,所以也無需執著于“回歸”。正如斯奈德在一次訪談中指出,“偉大的詩人不僅要表現自己的自我,還要表現出所有人的自我。為此,詩人必須超越自我。恰如道原禪師所言,‘探究自我是為了忘卻自我。忘卻自我,便能與萬物融為一體。’”[24]
斯奈德詩歌大多體現了一種擯棄各種先入之見的“空性”詩學,“無我”意識在斯奈德詩歌中隨處可見。《八月中旬沙斗山瞭望哨》(“Mid-August at Sourdough Mountain Lookout”)是詩集《砌石》中的第一首詩,分為兩節:“山谷中煙云迷霧/五日大雨,三天酷熱/松果上樹脂閃光/在巖石和草地對面/新生的蒼蠅成群。//我已經記不起我讀過的書/曾有幾個朋友,但他們留在城里。/我從鐵皮杯子喝寒冽的雪水/越過高爽寧靜的長天/遙望百里之外。”[25]該詩將“敘述者置于遠離文明的高山之巔。代詞 ‘我’直到第二節才出現,這反映出了敘述者的避世心態。‘我’在同一行中再一次出現后,就沒再出現過,似乎自我已成了負擔。”[26]這樣,主語的省略和延遲體現了詩人有意改變“以主體觀客體”這一慣性思維,使詩歌呈現出“以物觀物”的視角,讓讀者對于詩中展現的自然有種直觀的感受,從而生發出更多的聯想。而且,敘述者強調說他讀過的書現在已經記不起來了,也沒有嘗試著去回憶起來,這莫不是斯奈德對禪宗“空無”觀的參悟在其詩歌中的具體體現。
并置結構的使用往往會加強詩歌閱讀過程中多義聯想的催發。據美國學者墨菲(Patrick D.Murphy)觀察,并置結構增加了多重意義的可能性。無論是名詞還是動詞,許多詞語的意義取決于讀者如何調整該詞與其前后詞語的順序。最有效的解讀方式常常是對并置結構所產生的多重意義做出同步回應[27]。這種并置結構在斯奈德詩歌中處處可見,如上面所引用的詩歌中的山谷、霧、雨、熱、松果、樹脂、巖石、草地、成群的蒼蠅,等等。這種沒有人類“主體”參與的自然景物并置似乎是在展示詩人“為賦予土地自身代理權”而“遠離自我中心的利己主義”[28]的決心。
《道非道》(“The Trail Is Not a Trail”)這樣寫道:
我開車下了高速公路/開出一個出口/順著公路/來到一條小路/沿著小路開/我最后開到了一條土路/到處坑坑洼洼的,停了下來/我走上一條小徑/小徑越來越崎嶇難行/直到消失——/來到荒野之上,/處處可行。[29]
詩人從高速公路一路下來,似乎道路越行越窄,直到無路可行,但“路”這一絕對概念上的“無”恰恰成就了一種“無中心”的“有”,反倒是處處有路可行了。詩人似乎在表明,去除我執、放空自己,方能明心見性、暢“行”無礙。
這種“空無”理念在《表面的漣漪》中也有類似表達:
廣袤的荒野/房子,孤零零。/荒野中的小房子,/房子中的荒野。/二者皆忘卻。/無自然/二者一起,一所大的空房子。[30]
頭兩行中的“廣袤的荒野”與“小房子”體現的是一種典型的二元對立思維;從第三、四兩行開始,詩人借助《心經》中的“色空”思維,看到了兩者之間轉化的可能性。可以說,詩人正是通過這種禪宗思維來解構包括基督教神學在內的西方傳統的理性思維模式的,人造世界與自然萬物具有可以相互轉化的和諧一體性,并不存在與人類文明完全對立的自然。
同樣,詩集《龜島》中的《松樹的樹冠》(“The Pine Top”)也展現了人與自然之間的和諧一體性。
藍色的夜
有霜霧,天空中
明月朗照。
松樹的樹冠
彎成霜一般藍,淡淡地
沒入天空,霜,星光。
靴子的吱嘎聲。
免的足跡,鹿的足跡
我們知道什么。[31]詩歌前六行景物羅列并置、自然呈現。第七行人未見,但聞“靴子的吱嘎聲”,非主體性自我(靴子)乃是融于自然之中的普通一物,所發出的聲音更加襯托周遭之幽寂。“兔的足跡,鹿的足跡/我們知道什么。”進一步體現了主體超脫自我、憑直覺感悟自然的禪境,即消除了主體與客體、本質與現象等二元對立界限的澄明之境。
而長詩《藍色天空》(“The Blue Sky”)[32]更是這種“空性”詩學的絕好詮釋。該詩以佛教中的藥師佛(Old Man Medicine Buddha)①藥師佛,也稱藥師琉璃光如來、大醫王佛、十二愿王等。為眾生解除疾苦,他享有極高威望。但這種威望在主流佛教中卻受到了壓制,似乎被邊緣化了,這也許是藥師佛受到斯奈德關注的主要原因。為切入對象:
從這里向東方
遠在佛家世界之外 十倍于
恒河沙粒
有一塊稱作
琉璃光凈土
里面是痊愈之佛
琉璃光如來
你要花上一萬二千個夏季
沒日沒夜地開車向東
才能抵達琉璃光凈土的邊界
藥師琉璃光的凈土——
“花上一萬二千個夏季/沒日沒夜地開車向東”指的是日常生活中的欲念和痛苦等生命體驗,詩人將這種生命體驗同沒有疾苦、和諧一體的琉璃光凈土聯系起來,強調了終極目標的無止境性和追求過程的重要性。這一過程中,并沒有什么統一的“中心”可供讀者作為其解讀的根據,因為哪怕讀者發現某個能指似乎可以作為解讀依據,另一個不太相關的能指卻又接踵而來,令人難以確定某種單一結論。《藍色天空》就像是萬花筒,充滿了各種故事、曼特羅頌詞和單詞連綴,最終導致詩歌意義上的不確定性。
天上的 穹蓋……卡姆
天堂 赫曼……卡姆
[同志:在同一片天空/篷帳/曲線之下]
卡馬拉,阿維斯陀,腰帶卡姆,一把彎曲的弓
愛神,欲望之神“瑪雅之子”
“花之弓”
以上詩句所涉及的各種“空”(天空、篷帳、曲線、彎曲的弓、花之弓等等)都可以理解為是禪宗“空無”(Sunyata)理念的具體化。及至詩歌的末尾,
藍色天空
藍色天空
藍色天空
是凈土
藥師琉璃光的凈土
那里鷹
飛出了視界
飛。
此處,詩人一再強調“藍色天空”,似乎是在表明所謂的“意義”仍然像藍色天空的“藍色”那樣難以捉摸,因為,藍色天空不再是一種顏色,而是一種“空”,在廣大的空間中,意義是難以確定的。那只飛進這片“藍色”消失不見的鷹似乎暗示了萬物本無確定本質的品性,同時,天空也因為有了這只不懈飛翔的鷹的存在而凸顯了其“空”的品性,這樣,“空無”也可以說是“真如”(tathata)①大乘佛教認為,一切存在之本性為人。法二無我乃超越所有之差別相,故稱真如。例如如來法身之自性即是。真如乃一切現象(法相)之實性,與一切法相非異非一,非言語、思維之所及。。總之,萬物相異而相依,即所謂“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參悟其中奧妙,便能超越日常生活中的各種欲望執著、到達和諧一體的境界。斯奈德借助禪宗的“空無”理念解構了強調二元對立的邏各斯中心主義,即以“空無”之說點明日常生活中各種“中心”理念的虛幻性。
對德里達而言,任何超驗性的所指都不構成中心地位,這無疑“無限制地延伸了意義的邊界和戲謔性”[33]。而斯奈德對自然的理解充滿了德里達式戲謔性的解構傾向。
自然是一大套慣例的集合,完全是源自于瞬時形成的各種隨性的模式和指定;完全可能在
任何時候都會消失;僅僅是作為一種戲謔的形式繼續存在:宇宙的/喜劇性的樂趣。[34]
斯奈德詩歌表現的主要也是這種“宇宙的/喜劇性的樂趣”,大多具有戲謔性,而這種戲謔性跟斯奈德對禪宗公案的參悟緊密相關。對于禪宗公案及其背后思維特性,鐘玲曾有這樣的總結:
公案大抵是禪師為了啟發徒弟,而采用非直接的答話,采用非平常的行為方式,因為徒弟通常會陷入平常的理性思維,或陷入二元分法,鉆牛角尖而不自知。公案思維基本上是顛覆性的,顛覆平常用的思維方式,因此它常是突然的、斷裂的、跳躍式的、不合事實的、不合邏輯的、不合常理的、答非所問的、或藕斷絲連的、密碼式的,而且不能,也不應該用邏輯語言來解釋的。[35]
著名的“趙州無字”公案體現的就是典型的公案思維,常為研究者所征引。該公案是趙州從諗禪師(778-897年)與弟子之間的對話。據《五燈會元》卷四記載:“問:‘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師曰:‘無。’曰:‘上至諸佛,下至螻蟻,皆有佛性,狗子為甚么卻無?’師曰:‘為伊有業識在。”[36]按照任繼愈的理解,從諗禪師在對話中“以通過狗有無佛性的討論,打破禪師僧的 ‘有’‘無’執著和相對認識。”[37]看似不合常理邏輯,實則含有大智慧。
斯奈德對“趙州無字”公案深有參悟,多次直接化用。《神話與文本》(Myths&Texts)中,詩人就曾明確提及對該公案的體悟:
三月里的風
吹來拂曉的光
吹落杏花朵朵。
爐子上的咸火腿冒著煙
(坐思趙州無字我的雙腳睡了)[38]
前夜,詩人苦思“趙州無字”公案,于入神、釋懷之中安然地坐著睡著了,這似乎是“無”,醒來時,春風、春光、春花等自然景致以及火爐、咸火腿等日常生活事物猶在,這好像是“有”。詩人似乎在暗示“有”或者“無”乃自然實在,不可執著。
斯奈德還曾寫道:“野獸/有佛性//所有都是/除了郊狼”[39],這似乎是對“趙州無字”公案的轉化。按照西方邏輯學來理解,野獸有佛性,郊狼屬于野獸,在這大小前提均成立的情況下,必然會推出郊狼有佛性這一結論,而詩人卻說郊狼沒有佛性。這是公案式的反邏輯思維。
斯奈德詩歌的戲謔性還體現在萬事萬物“真如”實性的強調。斯奈德注意到禪宗和基督教的一大區別就在于,基督教太過于強調超驗理性,而禪宗則不然。
在超驗之外是偉大的戲謔和轉化。頓悟到腦洞大開的空之理念之后,時隱時現的百萬小宇宙之空性就在于能單純且充滿愛心地認識到耗子及草籽的無限美好和珍貴品性。[40]
總之,加里·斯奈德是新詩人中最具有禪宗意識的詩人之一。作為禪宗“平常心是道”的具體體現,斯奈德詩歌大多來源于日常生活,體現出一種身心合一的生活態度。其次,斯奈德詩歌少有自我主體意識,缺少西方傳統詩歌中的內在理性邏輯,結構松散,這種“無我”之空性意識使得萬事萬物在斯奈德詩歌中自然呈現。
[1]王治河.后現代主義辭典[M].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3:3.
[2]邱紫華,于濤.禪宗與后現代主義的異質同構性[J].南京大學學報(哲學·人文科學·社會科學版)2014:(3).
[3]張燕嬰,陳秋平,等.論語·金剛經·道德經[M].北京:中華書局,2009:334-335.
[4]李申.六組壇經[M].[中國臺灣]高雄:佛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7:198.
[5]丁福保.佛學大辭典[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293.
[6]釋從信.心經[M].臺北:圓明出版社,1990:46、60.
[7]鐘玲.中國禪與美國文學[M].北京:首都師范大學出版社,2009:42.
[8]高宣揚.后現代:思想與藝術的悖論[M].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104.
[9][北宋]道原,著;顧宏義,譯注.景德傳燈錄譯注(全五冊)[M].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9:2252.
[10]Frederick J.Streng.Emptiness:A Study in Religious Meaning[M].Nashville:Abingdon Press,1967:159.
[11]Gary Snyder.Axe Handles[M].San Francisco:North Point Press,1983:85.
[12]Gary Snyder.The Practice of the Wild[M].San Francisco:North Point Press,1990:153.
[13]Gary Snyder.Axe Handles[M].San Francisco:North Point Press,1983:25.
[14]Gary Snyder.The Back Country[M].New York:New Directions,1971:5.
[15][美]埃利特奧·溫伯格.1950年后的美國詩歌:革新者和局外人(下)[M].馬永波,譯.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511-512.
[16]Rudolph L.Nelson.Riprap on the Slick Rock of Metaphysics:Religious Dimensions in the Poetry of Gary Snyder[J].Soundings,1974(5):210.
[17]Bob Steuding.Gary Snyder[M].Boston:Twayne Publishers,1975:41.
[18]Jon Halper.Gary Snyder.Dimensions of a Life[M].New York:Random House Inc,1991:125.
[19]Dan McLeod.The Chinese Hermit in the American Wilderness[J].Tamkang Review,1983(1):170.
[20]Patrick D.Murphy.Understanding Gary Snyder[M].Columbia: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1992:5.
[21][23][34][40][42]GarySnyder.EarthHouseHold:TechnicalNotesandQueriestoFollowDharmaRevolutionaries[M]. New York:New Direction Publishing Corporation,1969:19、308、21、128、128.
[22]Gary Snyder.Mountains and Rivers without End[M].Washington D.C.:Counterpoint,1996:160-161.
[24]Gary Snyder.The Real Work:Interviews&Talks 1964-1979[M].New York:New Direction Publishing Corporation,1980:65.
[25][美]加里·斯奈德.八月中旬沙斗山瞭望哨[M]//[美]埃茲拉·龐德.美國現代詩選(下).趙毅衡,譯.北京:外國文學出版社,1985:554.
[26]Patrick D.Murphy.Understanding Gary Snyder[M].Columbia: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1992:45.
[27][28]Patrick D.Murphy.A Place for Wayfaring:The Poetry and Prose of Gary Snyder[M].Corvallis:Oregon State University Press,2000:45、46.
[29]Gary Snyder.Left Out in the Rain[M].San Francisco:North Point,1988:127.
[30]Gary Snyder.No Nature[M].New York:Pantheon,1992:381.
[31][美]加里·斯奈德.松樹的樹冠[M]//[美]埃茲拉·龐德.美國現代詩選(下).趙毅衡,譯.北京:外國文學出版社,1985:566-567.
[32]Gary Snyder.Mountains and Rivers Without End Plus One[M].Bolinas:Four Seasons Foundation,1979:38-44.
[33]Jaques Derrida.Structure,Sign and Play in the Discourse of the Human Sciences[M]//Writing and Difference.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78:280.
[35]鐘玲.中國禪與美國文學[M].北京:首都師范大學出版社,2009:246-247.
[36][宋]釋普濟.五燈會元[M].北京:中華書局,1984:204.
[37]任繼愈.佛教大辭典[M].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2:887.
[38]Gary Snyder.Myths and Texts[M].New York:Totem Press,1960:38.
[39]Gary Snyder.A Range of Poems[M].London:Fulcrum Press,1971:73.
[責任編輯:志 洪]
I106.2
A
1674-3652(2017)02-0090-08
2016-12-30
四川省教育廳人文社科項目“中美后現代詩歌發生學比較研究”(16SB0224);重慶市研究生教育教學改革研究項目“碩士生參與性教學模式研究”(yjg143047)。
邱食存,男,湖北黃崗人。博士,主要從事中美詩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