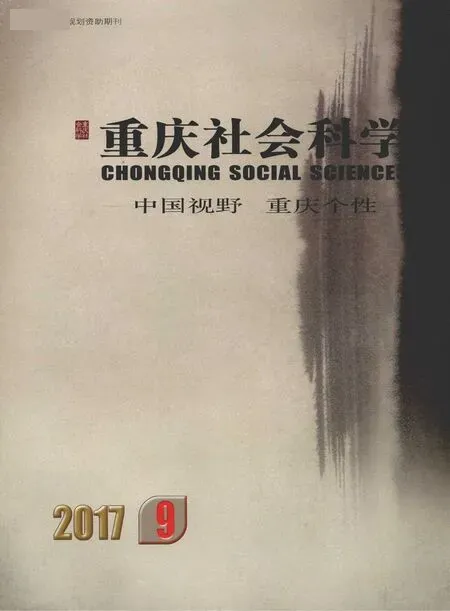法院調解社會化的制度重構*
曾令健
法院調解社會化的制度重構*
曾令健
民眾參與司法調解是中國司法的關鍵問題。至于法院調解社會化的形式,道路選擇仍是根本問題。制度重構的分析重心及切入點應是那些影響或支配制度構造、發展面向的思路與框架。在法院調解回歸解紛機制屬性之后,可將委托調解作為制度重構的主線,并堅持規范化、組織化發展面向。依循漸進式改革觀,可選擇從公權合作型委托調解邁向國家—社會互動型委托調解的制度重構“三階段”說。
法院調解 社會化 制度重構 漸進性 “三階段”說
民眾如何更好地參與司法調解是中國司法的一個關鍵問題。2014年《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要求“保障人民群眾參與司法……在司法調解……等司法活動中保障人民群眾參與”,以“完善調解、仲裁、行政裁決、行政復議、訴訟等有機銜接、相互協調的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加強行業性、專業性人民調解組織建設,完善人民調解、行政調解、司法調解聯動工作體系”。法院調解社會化是民眾參與司法調解的核心路徑。歷部 《民事訴訟法》(1982年、1991年、2012年修正)均規定法院邀請調解,2004年《關于人民法院民事調解工作若干問題的規定》不僅細化邀請調解,還“創設”委托調解,爾后一系列司法解釋均不同程度涉及法院調解社會化之制度安排。2015年中共中央辦公廳與國務院辦公廳 《關于完善矛盾糾紛多元化解機制的意見》、2016年最高人民法院 《關于人民法院進一步深化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改革的意見》與《最高人民法院關于人民法院特邀調解的規定》再度強調整合力量、助推法院調解、促進糾紛解決的糾紛解決觀念與制度建設思想。
2016年司法解釋旨在引導、規范委托調解(即“特邀調解”),但目前尚不能據此斷言委托調解為法院調解社會化惟一形式。一是迄今司法解釋沒有明確表達此種觀點。二是司法解釋也沒否定邀請調解。相反,第17條給邀請調解保留了空間:“特邀調解員為促成當事人達成調解協議,可以邀請對達成調解協議有幫助的人員參與調解。”三是司法解釋不是法律,而民訴法對社會化形式的表述較為粗疏,具有倡導性、促進性立法之意味。
就法院調解社會化形式而言,道路選擇仍是一個根本問題。這里擬從制度重構的立場入手,反思作為原則的法院調解,倡導以委托調解為主線的發展定位及規范化、組織化的發展面向,并基于漸進改革理念提出制度重構 “三階段”設想。
一、制度重構:態度與立場
首先,制度設計尤其對程序事宜作制度安排,大抵“仁智相見”。如調解期限設為10天,抑或20天,還是30天,不同期限設置間并無本質區別,或均可以充足理由證成該種設置之必要及可行。關鍵問題是,相關理論證成與邏輯自洽分析常常無法被證偽。凡不能被證偽的命題皆需小心對待。此意義上,這些具體以至瑣碎的制度安排通常重要卻未必關乎宏旨。
其次,對于具體制度尤其邀請調解與委托調解之不足、缺陷,既有成果已有不同程度的涉及①依照2011年《最高人民法院關于人民調解協議司法確認程序的若干規定》,人民法院立案后委托調解達成的協議的司法確認,依《最高人民法院關于人民法院民事調解工作若干問題的規定》辦理。此處將受理作為訴訟系屬的起算點,立案之前包括審查起訴階段的委托調解則被等同于人民調解。圍繞該種委托調解之協議確認還有一系文章,如王亞新:《訴調對接和對調解協議的司法審查》,《法律適用》2010年第6期;潘劍鋒:《論司法確認》,《中國法學》2011年第3期;范愉:《訴訟與非訴訟程序銜接的若干問題——以〈民事訴訟法〉的修改為切入點》,《法律適用》2011年第9期;向國慧:《調解協議司法確認程序的完善與發展——結合〈民事訴訟法〉修改的思考》,《法律適用》2011年第5期。2016年特邀調解的司法解釋又嘗試“委派”與“委托”的二元劃分來尋求解決辦法。,[1][2][3][4][5]對此不予贅述,盡管這些是制度重構的智識參考。
第三,制度建構在某種程度上是研究的較高層次。一方面,筆者主張堅持“問題出發型研究策略”,強調“問題中心”、關注“中國問題”、注重“理論關懷”,以法律實踐為切入點,從而提煉、驗證、回應、修正法學理論,從繁復、瑣碎、龐雜的法律實踐中抽勒出具有學術生命力與理論張力的問題,遂分析之。這可避免學術研究與立法工作的混淆。學術之核心要義在于實現知識增量、追求理論貢獻,所謂的“一切為了思想”,應盡可能避免出現法學研究之 “環大會堂現象”。[6]學者之使命在于提出有批判力、洞察力的命題,如果可能則建構具有思想深度的理論體系,而非“立法草案”的執筆者。另一方面,從立法論視角研究制度也是非常重要的,并應在理論探討之深度及廣度達至相當程度后方宜進行。這是理論成果的現實轉換。當學術界尚未對法院調解社會化完成有針對性、深入的研究之前,任何期圖提供一整套通盤制度設計的想法,往往是學者的某種學術激情。充分、透徹的理論證成以及“理論—實踐”之反復應照、修正及耦合,是制度設計及其研究的前提性工作。②此方面的經典性、深入人心的例證無疑是200年前圍繞德國民法典編纂展開的那場曠日持久的學術論戰。其中,薩維尼旗幟鮮明地主張,法乃“民族精神”之體現,非立法者可任意創造,也非純粹的理性產物,法典編纂依賴諸多主、客觀條件。其中,法學研究與法典編纂也有重要關聯。詳見:(德)弗里德尼希·卡爾·馮·薩維尼:《論立法與法學的當場使命》,許章潤譯,中國法制出版社,2001年。
最后,研究重心與分析的切入點應當置于那些可能影響或支配制度構造、發展面向的基本思路與主體框架。在理論層面,這類研究可保持論述的學理性,不會陷入一般、瑣碎的制度細節;在實踐層面,這類研究可能影響、決定制度命運,并不同程度地影響具體制度設計。支撐某項制度、引領制度重構的思路與原則,以及依循這些思路、原則而建構的基本框架最能發揮“提綱擎領、牽一發而動全身”之功效。
二、一項原則的反思:作為解紛方式的法院調解
在相當長時期內,法院調解被視為一項民事訴訟基本原則,這也是訴訟法學界主流看法。實踐中更是以司法實務基本原則對待,但制度實踐的后果是“調解審判化”與“審判調解化”之共生。反思調解原則關乎法院調解社會化之正當性及制度重構。由于調解與審判的本質區別,所以二者共存于同一審判結構往往影響司法活動的依法、依程序開展。如果將調解視作基本原則,則可以適用于訴訟任何階段。因為基本原則的含義在于其對民事訴訟之立法及司法的全過程具有指導意義,且貫穿訴訟始終,并對訴訟產生根本影響。眾所周知,我國法院調解制度有其獨特發展歷程,是不同時期相對復雜的歷史背景與社會文化綜合作用的產物。盡管立法視其為基本原則,但顯而易見的是,法院調解更多是一種糾紛解決機制或案件處理方式,不具備指導訴訟的功能。制度緣起及其發展也表明,法院調解與仲裁、私力救濟等一樣,只是糾紛解決機制而已。即使不說法院調解與審判截然不同、“水火不容”,但二者確是兩套解紛機制。
法院調解回歸糾紛解決機制有利于法院調解社會化的制度重構。其一,在邏輯上,重構或修正訴訟原則將涉及整個訴訟機制,工作之巨可想而知。事實上,法院調解不對整個訴訟活動產生指導作用,也不是立法的基本出發點。此意義上,法院調解社會化的制度重構不牽涉基本原則,也不影響整個訴訟架構及程式。這個制度重構僅是“局部戰斗”。其二,視法院調解為一種與審判、仲裁、和解、私力救濟等并列的解紛機制,使得建構一套體現公力救濟與社會型救濟相銜接、互動的解紛機制名正言順。否則,一個訴訟基本原則何以與作為解紛方式的審判銜接、互動。凡說銜接與互動,各者在邏輯上應具有同質性、相似性。狹義的司法權為一種判斷權,這主要針對裁判者的功能而言,與調解者促進合意的功能定位相距甚殊。將兩種在糾紛應對時擁有不同處理思路的解紛方式組合起來,這無疑是“一加一大于二”的系統論在法院調解制度改革中的運用,而法院調解社會化正是此種努力。當然,從世界范圍來看,也不應截然絕裂調解與審判,忌將二者全然對立,畢竟司法權內涵在悄然發生著變化,即使極不明顯。在奉行法治主義傳統的國度,調解(包括和解)也越來越為司法程序、法官所認同、接受,并一定程度上改變著既有司法理念及模式。①美國學者Marc Galanter對美國民事審判所作的法律社會學考察表明,美國的訴訟案件數以及審判結案的案件數在相當長時期呈下降之勢,且調解、和解等糾紛解決方式業已為司法所接受,并重塑著美國司法的格局。 詳見:Marc Galanter, “A Settlement Judge,not a Trail Judge:Judicial Medi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Vol.12 Journal of Law and Society 1~18(1985);Marc Galanter,“The Emergence of the Judge as a Mediator in Civil Cases”,Vol.69 Judicature 257~62(1986);Marc Galanter,“The Vanishing Trial:An Examination of Trials and Related Matters in Federal and State Courts”,Vol.1 Journal of Empirical Legal Studies 459~570(2004)。
三、法院調解社會化的定位:以委托調解為主線
調解具有一副反程序的外觀,而法院調解社會化之實踐更是將其演繹到極致。但法院調解及其社會化的形式外觀不應成為制度實踐中隨意、拖沓、冒進等行為之借口。作為一種解紛方式,法院調解社會化應具有明確、恰當的定位。依“國家—社會”分析框架,可將委托調解分情況界定:首先,在參與的非司法力量不具有足夠充分、顯著的社會屬性時,這種制度安排屬于國家權力的統一行使及其引發的分工、配合;其次,當社會屬性較明顯的調解組織參與司法調解時,國家與社會之二元互動論可能成立,但這種情景下的委托調解亦未能構成一個具有獨立品格與特有屬性的解紛領域。總言之,當下委托調解實踐實為一種斑駁、交雜的糾紛解決多元主義的體現,透露著不盡相同的制度意涵。這是基于當下集中型權力體制展開的分析。無論社會轉型的進程及結果如何,委托調解中透露出的注重社會力量與法院力量的交接、互動、協作,以及適當加大社會力量的調解權重,都是些富有價值的啟發。故而,將法院調解社會化界定為國家力量與社會力量互動、共存的糾紛解決方式,具有廣袤的制度發展空間與旺盛的理論生命力。
對法院調解社會化的結構定位,不僅利于指引制度重構的方向,且有助于扭轉當下司務中的問題。法院調解社會化之所以如火如荼,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相關制度及實踐契合 “司法能動”、“大調解”諸潮流。在這些浪潮中,司法突破被動、消極等傳統特征,于是乎“作為法庭的街道”成為了當下司法的一道景觀:法院常常超越司法被動與消極性原則,針對糾紛、主動出去、盡快入手、及早解決,以達到糾紛解決之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的統一。①該項研究表明,對于勞動爭議類糾紛,如果勞動者通過集會、游行表達訴求,法院、政府等會主動與之接洽并尋求解決之道,而黨政方面也常常會指示政府部門主持勞動者與企業之間的調解;前述情形不僅與現行糾紛解決程序規定大相徑庭(在一起個案中,聚眾上街的勞動者們甚至可以不經過勞動爭議仲裁程序,而由法院工作人員在集會現場為其辦理訴訟案件的受理手續,從而繞開勞動爭議仲裁程序,以便“便捷地”、“高效地”維護其權益;或重復查封、凍結企業之設備、賬戶,通過給“企業施加更多的壓力”,從而使勞動者在調解中處于有利地位),且此類集體維權行動的效果往往較勞動者各自依程序尋求權利救濟要方便、快捷、有效得多。關鍵之問題在于,法院會主動迎合這些糾紛。詳見:Yang Su,Xin He, “Streetas Courtroom:State Accommodation of Labor Protest in South China”,Vol.44 Law and Society Review 157~84(2010).法院調解社會化正好“大展身手”,許多案例可以佐證。當這些做法遭遇 “不鬧不解決”、“小鬧小解決”、“大鬧就徹底解決”的社會心理,從長遠而言,不僅無助于糾紛解決,還將與法秩序發生沖突。筆者認為,即便在“能動司法”、“大調解”的潮流中,法院既不能發揮主導作用,更不宜充當“排頭兵”。②有研究對法院在“大調解”中占據“主導”地位的本土實踐進行過反思,也認為法院在現有的制度環境下很難真正地扮演起“大調解”中的主導角色。詳見:王祿生:《地位與策略:“大調解”中的人民法院》,《法制與社會發展》2011年第6期。同理,法院調解社會化應是一種相對溫和、持久的制度實踐,應定位為常規性解紛機制,而非應急性解紛手段。此外,明確法院調解社會化的結構定位可避免“程序倒流”。該現象一定程度上透露出制度的命運:在集中型權力體制之下,制度極可能被選擇性適用,且常常可能“變臉”,以滿足即時性需要。在此意義上講,對法院調解社會化的結構性定位不是限制其功能發揮,而是對制度良性運作的一種保護。
四、制度發展面向:規范化、組織化
長遠而言,法院調解社會化應當堅持規范化、組織化的道路,但不一定需要遵循專業化的發展方向。規范化幾乎是所有制度建構、改革的一個方向,法院調解社會化的規范化重在強調對法院調解社會化的具體制度予以明確、細化。所謂法院調解社會化之組織化,即通過設置機構、厘定規程,使法院調解社會化更加具體、明確、易操作。從廣義上講,組織化可以劃歸規范化的范疇。組織化視角對于法院調解社會化的制度重構具有重要意義。從既有實踐來看,委托調解的組織化程度最高,仍需加強規范化建設;邀請調解與人民陪審員參與法院調解的組織化程度相對較低,幾乎依附于法官以及常規的司法活動,其社會化屬性相對較弱。這種比較也在某種程度上揭示了規范化、組織化重構法院調解社會化時可能不得不直面的抉擇。
另外,作為國家權力與社會力量共同作用的場域,法院調解社會化的性質就決定著,專業化或者說職業化不是主要發展面向。從理論上講,如果受托組織實施市場化運作,也可能引發專業化、職業化的法院調解社會化形式。這將面臨兩個問題:其一,只有在市場化極度發達的社會,這種理念才有付諸實踐之可能;其二,市場化運行中的“利益追逐”與糾紛解決中的“公正執法”可能會發生沖突。君不見,許多公用企業在市場化運行之后都產生了或多或少的問題,何況是作為社會秩序維系手段的糾紛解決權?當然,有一種限制“恣意”、“不公”的力量來自于當事人對調解的決定權。姑且擱置專業化、職業化不表,法院調解社會化不僅不排斤專業技術人員的參與,且作為重要的糾紛解決資源,專業技術力量應當被規范化、組織化地吸引至法院調解社會化之中。
五、制度重構的漸進性思路
制度重構應當堅持漸進式改革,一步步展開、勿急勿躁,以減少劇烈的制度變革可能誘發的社會“陣痛”。但凡具有成文法傳統的制度體系,往往具有強烈的變革色彩。①一些杰出的比較法成果可以充分地說明此問題。相當意義上講,1804年《法國民法典》是“法國大革命精神的一個產物,這場革命旨在消滅往昔的封建制度,并在其廢墟上培植財產、契約自由、家庭以及家庭財產繼承方面的自然法價。1789年后的年代里所發生的一系列革命事件對于該法典的形成極為重要。”[(德)K·茨威格特 H·克茨:《比較法總論》,潘漢典、米健、高鴻鈞、賀衛方譯,潘漢典校訂,貴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44頁]社會主義國家的法總被視作脫離羅馬日爾曼法系所構成的另外一個法系,“在蘇聯……自1917年革命以來,一種獨具一格的法發展了起來”。法典制訂也具有政權更迭的表征功能。“自從共產黨人取得政權以來完成了大量的法典制訂工作,特別是在波蘭、捷克斯洛伐克及南斯拉夫這樣一些以前不曾在全國范圍內實現法的統一的國家。”[(法)勒內·達維德:《當代主要法律體系》,漆竹生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84年,第28、228~229頁]維阿克曾言:“法典編纂的目的,是通過體系性的和包羅萬象的新秩序對社會進行總括性設計。”[Franz Wieacher,Privatrechtsgeschichte der Neuzeit,1.Aufl.,1952,S.197(2.Aufl.,1967,S.323)。 轉引自(日)大木雅夫:《比較法》,范愉譯,朱景文校,法律出版社,1998年,第 154 頁(注 5)]成文法傳統正是中國法律體系的一個重要特征。即便如此,仍有漸進式改革的空間。事實上,這種漸進式變革的法制變遷對于中國而言并不陌生,甚至可從當下制度變遷中找尋例證。比如我國民訴法規定的社會化形式是邀請調解,但司法解釋對其闡釋時,一種將法院調解案件托付與非司法力量的做法也悄然成形,并在“橫空出世”后“迅速竄紅”,且少了邀請調解在條文中長達數十年的“沉默”、“潛伏”、“蟄伏”。當然,委托調解還是一宗尚未事功的制度改革,但其借助司法實踐土壤得以“生根發芽”并“笜壯成長”。在此意義上可以說,司法實踐是制度變革包括法院調解社會化制度重構的滋生地,②中國司法改革中一個值得關注的問題是,往往改革的思想(或者說思想淵源)來自高層,而具體的制度探索與實踐則源于地方的能動與突破。這方面例證可謂不勝枚舉,如20世紀后期的“一步到庭”之庭審制度改革,如21世紀初期的人民監督員制度,如是等等。這也為制度重構的漸進式改革提供了可能。
在漸進式變革中,成文法傳統本身也能為這種溫和、有序的改革創新提供制度性的“庇護空間”。如自上而下地推進法院調解社會化改革,應有序、克制、溫和、漸進、分步驟地重構,如“通過試點推進重構”。一個不爭的事實是,當代中國法院調解社會化必須正視社會力量的解紛能力有限,“多快好省”的思路極可能釀成“欲速則不達”的苦果。漸進式變革方可避免社會力量之“力有不逮”。最為重要的是,無論如何論證司法權與調解權,在既有司法框架下推行規范化、組織化的法院調解社會化,最終都將觸及將糾紛調解權分割、讓渡給社會調解組織的敏感一刻。對于尚需在權力架構中努力爭取話語權的法院系統而言,這無疑需要頑強的毅力與極大的勇氣。故而,漸進式制度重構之路就益發緊要。
六、制度重筑的“三階段”構想
對制度重構的立場和觀點做一個概括式描述:在漸進式制度重構過程中,貫徹規范化、組織化的制度發展面向,并將法院調解社會化定位為國家權力與社會力量交接、互動的作用場。為實現該企畫,大抵可將制度重構的進程分為三個階段,依次推進。
第一個階段,慎用法院邀請調解并逐步減少其適用比重,同時將委托調解作為法院調解社會化的一種主要形式。雖從公開報道看,邀請調解的適用頻率高、成功率高,但田野調查表明,該制度既缺乏運行動力,也容易偏離司法運行規律,還與規范化、組織化的制度發展方向相悖。相比而言,委托調解應作為制度重構的主要方向,故第一個階段應調適二者的比重,為進一步重構打好基礎。雖然現行立法并未對委托調解予以正名,但不損及制度重構的可行性。一個便利的例證是,法院委托調解在許多國家和地區都是重要、正式的訴訟與非訴訟之銜接制度,或有近似的制度安排。如中國臺灣地區的“法院移付調解”,即法院或法官將進入訴訟系屬的案件委托給鄉鎮市調解委員會。[7]該種制度例可為制度重構提供信心。
第二個階段,除家事糾紛等特定案件之外,①特定案件的范圍依憑兩種方式予以限定:其一,列舉特定案件類型,如家事糾紛、鄰里糾紛、房屋租賃糾紛、勞務糾紛、勞動合同糾紛及其他案情簡單且法律關系明確的案件(如在交通肇事案件中,由于交通事故責任認定書對事實認定和責任劃分有極大幫助,同時又由行政訴訟處理事故責任認定分歧,故便于開展和解工作);其二,將糾紛與普通民眾生活存在相當程度的關聯性作概括標準,在具體處理則由法官裁定。通過列舉與確立標準相結合的方式,對訴訟和解之案件范圍予以必要限定。可將調解從訴訟中予以剝離且以訴訟上之和解替代現行法院調解制度,同時加大法院委托調解的建設及適用力度。如條件成熟,則以訴訟上之和解徹底取代法院調解。至此,法院邀請調解以及人民陪審員參與法院調解這兩種情形從制度層面而言幾乎不存在,而法院委托調解雖然名義上可稱為法院調解,其實后者業已為訴訟上之和解取代之后,故而,此時的法院委托調解實際上已經無形中轉變身份,成為一種典型的法院附設調解,成為堅持法治中心主義的訴訟活動之補充性機制。該階段是改革中最為艱巨的一環,也是具有決定性意義的一環。這樣一種法治中心主義的訴訟活動與委托調解的交相輝映在世界范圍內有其成功范例,縱然個中經由的路徑不同。通常認為,1976年龐德會議(Pound Conference)上有學者提出“多門法院”(Multi-Door Courthouse)觀念,將小案子從法院移至社區法律中心。[8]1980年代末,Marc Galanter指出,美國民事訴訟的惟法治中心主義觀被“捅破”,和解被接納。[9]1998年《ADR法》鼓勵每個地區法院設置ADR項目。不限于美國,調解以及附設性調解已經成為當今世界糾紛解決方式中最具活力與魅力的制度。②調解在一些國家的實踐及發展趨勢,可參閱(澳)娜嘉·亞歷山大主編:《全球調解趨勢》,王福華等譯,中國法制出版社,2011年。
第三個階段,從公權合作型委托調解邁向國家—社會互動型委托調解。當下法院委托調解更多屬于行政力量與司法力量的結合、協作。這于發揮社會力量之解紛潛能并無多少助益。當然,這與當下社會自身能量有限存在莫大關系。畢竟相當長時期內“傳統的社會自生功能幾乎被完全鏟除了。于是,使社會自組織程度驟然下降到一個空間的低點,所以我們對于‘自生社會’的良性機能只能越來越陌生”。[10]故而,在社會轉型期,自上而下的國家力量在培育、吸納、開發糾紛解決的社會資源方面仍大有可為。通過政府力量的推動,完全有可能打造出真正具有民間屬性的社會糾紛解決組織。③應該說,緣于社會轉型出自總體性社會之故,當下諸多所謂的民間性解紛機制都存在屬性不明確尤其民間性成色不足的問題,如仲裁、人民調解等。可參閱汪祖興:《仲裁機構民間化的境遇及改革要略》,《法學研究》2010年第1期;汪祖興:《中國仲裁制度的境遇及改革要略》,法律出版社2010年,第138~143頁;范愉:《〈人民調解法〉:讓人民調解回歸民間》,《中國法律》2010年第6期。不僅培育社會力量對于委托調解意義重大,且社會力量的增強對社會自身應對糾紛解決也有重要意義,惟如此,司法才可能成為終局性解紛機制。筆者認為,高度發達的司法體系并不意味受理案件數或處理案件數多,甚至不一定是司法效率最高的法院,也不大可能是人案“剪刀差”的法院。司法系統之發達甚至不完全在于司法系統本身,而在于社會自身的糾紛解決能力。如果社會型救濟體系足夠發達,則有限的司法負載便可引領社會規范的運作,實現社會正義的生成。
這種社會型救濟與司法救濟之互助、共濟局面在美國有所體現。研究顯示,聯邦法院受理案件數自1980年代中期以來持續下降,降幅達60%;民事結案率下降,1962年11.5%,2002年1.8%;州法院類似。[11]這很大程度上利益于法院附設ADR(包括法院附設調解)的開展。當大量糾紛通過社會型救濟甚至私力救濟予以解決,①關于現代美國社會中的私力救濟,可參閱(美)羅伯特·C.埃里克森:《無需法律的秩序——鄰人如何解決糾紛》,蘇力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3年;(美)唐納德·布萊克:《正義的純粹社會學》,徐昕、田璐譯,浙江人民出版社,2009年;(美)唐納德·布萊克:《社會學視野中的司法》,郭星華等譯,法律出版社,2002年;(美)唐納德·布萊克:《法律的運作行為》,唐越、蘇力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4年。法院可抽出足夠的人、財、物來“作好”判決,從而樹立行為規范、引導社會風氣、維系社會秩序。②除費斯教授之外,還有很多學者糾紛對被體制化、大規模地予以非訟化處理表示擔憂。如Hazel G.Genn,Judging Civil Justic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0);Elizabeth G.Thornburg, “Saving Civil Justice”,Vol.85 Tulane Law Review 247 (2010);Edward J.Bergman,John G.Bickerman,eds.,Court-Annexed Mediation:Critical Perpectives on Selected State and Federal Programs, (Silver Spring:Pike&Fischer,1998)。司法ADR對提升司法體系的形象、助長司法體系的權威可謂功不可沒。因此,培育、吸納、開發糾紛解決的社會資源,實現從公權合作型委托調解邁向國家—社會互動型委托調解,是法院調解社會化制度重構中最重要的環節。
[1]李浩:《法院協助調解機制研究》,《法律科學:西北政法學院學報》2009年第4期,第62~70頁
[2]李浩:《委托調解若干問題研究——對四個基層人民法院委托調解的初步考察》,《法商研究》2008年第1期,第133~140頁
[3]李浩:《調解的比較優勢與法院調解制度的改革》,《南京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2002年第4期,第19~27頁
[4]肖建國:《司法ADR建構中的委托調解制度研究——以中國法院的當代實踐為中心》,《法學評論》2009年第3期,第135~144頁
[5]范愉:《訴前調解與法院的社會責任——從司法社會化到司法能動主義》,《法律適用》2007年第11期,第2~7頁
[6]陳瑞華:《論法學研究方法》,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 年,第 113~116、177~179 頁
[7]范愉:《訴訟與非訴訟程序銜接的若干問題——以〈民事訴訟法〉的修改為切入點》,《法律適用》2011年9期,第30~34頁
[8](美)詹姆斯·E.麥圭爾 陳子豪 吳瑞卿:《和為貴:美國調解與替代訴訟糾紛解決方案》,法律出版社,2011 年,第 11~12 頁
[9]Marc Galanter,“The Emergence of the Judge as a Mediator in Civil Cases”,Vol.69 Judicature 257~62(1986)
[10]王毅:《中國走向公民社會的困難、可能與路徑選擇》,載資中筠:《啟蒙與中國社會轉型》,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年,第194頁
[11]Marc Galanter, “The Vanishing Trial:An Examination of Trials and Related Matters in Federal and State Courts”,Vol.1 Journal of Empirical Legal Studies 459~570(2004)
Institutional Reconstruction towards Socialization of Judicial Mediation
Zeng Lingjian
It’s vital for the masses to participate in judicial mediation,as to chinese judicature,and the path of judicial mediation is also a fundamental issue.Frankly,the essential respects and the breakthrough points of institutional reconstruction should be ideals and frames which are dominating the structure and development of the system.Recognizing judicial mediation as one of dispute settlement mechanisms,we should fouce on court-entrusted mediation,and pay more attention to standardization and organization of it.Following the reformism of progressivity,the hypothesis named Three-Stage Development Strategy can be employed to make the court-entrusted mediation tranfromed from Public Powers’Cooperation to State-Society Interaction.
judicial mediation,socialization,institutional reconstruction,progressivity,Three-Stage development Strategy
西南政法大學中國仲裁學院 重慶 401120
國家社科基金西部項目“合作主義視野中城鎮基層糾紛解決實證研究”(批準號:13XFX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