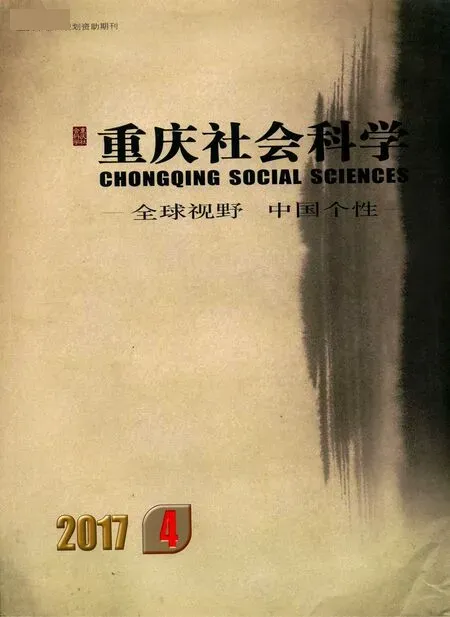新能人治村的操作機理與地域特征*
李 寬
新能人治村的操作機理與地域特征*
李 寬
蘇南地區的村莊治理模式可以用新能人治村來概括。與原來的治理模式相比,當前的能人治村呈現出三個新特點:在產生的方式上,采取鄉鎮政府選拔和村民選舉相結合,更加注重組織的培養;在行為目標上,追求集體利益的最大化,更加注重公共需求;在能力要求上,由經營型向管理型轉變,更加強調守業能力。這些新特征的出現,與當地實行以招商引資為主的發展方式、以村級為核心的集體經濟、土地管理的規范化和松散的社會結構有關,具有鮮明的地域和時代特征。
社會治理創新 社區建設 “三農”問題
對我國農村治理主體的探討經歷了由士紳向地方精英的拓展,形成了基層治理研究的“士紳”模式和“地方精英”模式。士紳模式認為基層的治理主要由依靠科舉制度出身的官員、士大夫及其家族來完成,在家國同構的框架下,由他們保持著信息的溝通,主導著地方秩序。隨著科舉制度的衰落和對日常生活研究的深入,士紳模式逐漸被地方精英模式所取代。地方精英的涉及面更加廣泛,只要是在某方面比較出眾、有一定的號召力就可被認為是精英。在基層治理中,大致可分為依靠體制性資源的政治精英、在市場中取得成功的經濟精英和在村莊生活中具有影響力的民間權威(李猛,1995)。在當前的形勢下,經濟精英在村莊的治理中發揮了更大的作用。
一些人將經濟精英主導的村莊治理稱為“能人治村”。這些村莊主要分布在沿海發達地區,那些在經濟領域獲得成功的個人逐漸步入村莊政治領域,承擔起了治理責任。這批人走向村莊治理的核心與“雙強雙帶”政策有關,也契合了普通群眾發家致富的期盼。[1]
對于能人治村的效果,存在著兩種不同的認識:一種是對能人治村給予積極評價,肯定他們所作出的貢獻。能人在村莊中發揮的作用主要表現為以下方面:一是將個人的經驗、關系和資金等資源奉獻出來,對村莊進行經營,促進集體經濟的發展;二是在村莊中實行民主基礎上的權威政治,實現精英主導與群眾參與的有效結合;三是改善村莊社會面貌,恢復村莊的秩序和活力。這種認識從經濟、政治和社會的角度概括了能人對村莊帶來的有益影響。[2][3][4][5]從表面上看,在能人的帶領下,村莊確實發生了許多可喜的變化,農民的生活水平有了較大提升。另一種是從村莊內部結構的視角指出能人治村的消極影響。在經濟方面,認為這些經濟能人確實將自己的資源用于村莊,讓村莊的經濟獲得了發展,但是自己從中獲取得更多,有侵吞集體資產的嫌疑;在政治參與方面,則利用自己的經濟優勢使普通村民被邊緣化,導致村民參與村莊政治的積極性降低;三是在社會層面,主導了人際交往規則變遷,讓村莊的人情出現異化。[6][7][8][9]10]他們更加喜歡將這些經濟精英稱為 “富人”,而不是“能人”。
上述認識從不同角度闡述了對能人治村的理解,也從側面表達了對村莊治理的期待,希望經濟精英們既有很強的個人能力,又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質。學者們對于這些能人在市場中所獲得的能力并不懷疑,比較擔心的是他們如何處理個人利益與集體利益的沖突。上述研究調查的區域集中在民營經濟比較發達的浙東地區,如果將此問題放在其他地區進行考察,可能會得出不同的結論。同時,相關的分析也只是集中在村莊的層面,而對鄉鎮政府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分析較少。若是拓展對此問題的研究,可能會有新的發現。
一、“新能人治村”的特征
蘇南地區的新能人治村有著比較顯著的特征,主要體現在干部的產生方式、行為目標和能力要求方面,與原來的能人有較大的不同。
(一)村干部由選拔與選舉相結合產生
在蘇南地區,村干部在選拔與選舉相結合的方式下產生,不同于其他地區僅由村民直接選舉產生。選舉是從村莊民主的角度來理解,表達了村民的意愿,考察了干部們的群眾基礎。選拔則體現了鄉鎮政府的意志,顯示上級對村干部的認可程度。鄉鎮政府的選拔在某種程度上也意味著穩健的晉升制度,內含著對村干部不斷進行培養的意味。在成為村里的主要負責人之前,村干部要經過組織長期的考察、培養和多個崗位的歷練,獲得一致的認可之后,才能走上比較重要的工作崗位。比如,許多村的支部書記都是從生產隊長開始做起,歷任民兵連長、會計、村委會副主任、主任,最后才成為真正的“當家人”。當前,村民小組逐漸弱化,村民小組長只是負責具體的聯絡工作。村委會工作人員的選拔主要來自企業、聯防隊和個體戶。有能力和意愿到村委會工作只是前提條件,至于能否到村委會工作還要看相應的考試和考察情況,而不是村民的選舉。即便能夠到到村委會工作,也不是直接被選舉為村委會委員,而是要從一般的辦事員開始做起,在身份上是臨時性聘用人員或社區工作者。只有工作比較出色,積累了相應的工作經驗,達到了相應的要求,才有可能被提名為村委會委員候選人。
從上述村干部產生的過程可以看出,鄉鎮政府在其中發揮了主導性作用,村民的選舉只是作為民意參考。即便某個人具有很強的能力和較好的民意基礎,也不大可能僅通過選舉的方式就當選為村干部,鄉鎮政府或選舉委員會的提名才是所要過的第一道關。這也并不意味著鄉鎮政府通過行政消解了自治,提名的干部一定能夠當選,而是將村干部的產生作為一個培養的過程。村干部的能力不只是依靠自己在市場經濟中獲得,更多的是依靠組織的培養。經過長期的考察和培養之后,才可能成為村干部。如果某人的能力、民意基礎太差,鄉鎮政府也不會讓其擔任重要的職務。
(二)以集體利益最大化為行為目標
蘇南地區村干部以集體利益最大化為行為目標主要表現為以下方面:一是讓集體經濟獲得發展。讓集體經濟獲得發展,主要來自于鄉鎮政府的要求。只有當集體經濟發展之后,鄉鎮的財力才會得到保障,各項工作才容易開展。因此,能否發展集體經濟成為上級對其考核的重要指標,并且這個指標很容易量化。沒有集體經濟的發展,就沒有他們的晉升,在這個評價體系中也就沒有太多的地位。集體經濟的發展與個人的進步緊密相關。
二是維護村莊的合理秩序。秩序對村莊來說是一項重要的“公共品”。形成合理的公共秩序,就要求村干部們行事公允,獲得大多數村民的認可。如果村干部們不能做到這些,就可能讓村民們產生反感,在村莊選舉和日常治理中就會表現出來。盡管在干部的產生中組織的意圖占了較大的比重,但是村民的認可也同樣重要。在選舉過程中,村民即便是不投反對票,也可以棄權的方式表達無聲的抗議。村民對秩序不合理的最為直接的表現形式就是日常治理中的不配合,讓村干部的工作無法開展。在取消農業稅費之后,村干部與村民的互動很大部分落在了惠民政策的落實上。當前,這些政策不只是簡單地發錢、發物,還涉及眾多公共工程的修建。當村民不認可村干部的行為時,就會認為這些工程不是為自己帶來便利,而是損害自己的利益。這樣一來,就使得村莊的整體利益受損,影響了村莊的治理。為了落實各項工作、獲得村民的認可,村干部們必須維護村莊的合理秩序。
三是對村民的生活進行托底保障。課題組在蘇南地區調查時,有兩個比較明顯的感受:一是村莊的上訪戶比較少;二是村莊貧困人口得到了比較多的照顧。在村莊中上訪戶比較少,一方面說明邊緣人群比較少,大部分人還參與著村莊的政治、社會生活,沒有被“甩出去”。另一方面,則說明村莊的照顧比較周到,沒有讓村民產生太多的不滿。如果村干部的行為明顯超越了某些界限,讓村民們產生意見,那么就會冒出上訪戶來,利用各種機會來反對村干部,干擾村干部的正常工作。村莊除了對殘疾人和符合條件的癌癥患者兩類人群進行照顧外,還會評選出若干個低保邊緣戶,即家庭比較困難或患重大疾病,但不能列入低保戶的家庭進行幫扶。盡管幫扶的金額不是很大,但盡量地將符合條件的村民納入進去,至少可以讓村民獲得心理上的安慰。在村莊中沒有邊緣人的出現或者說極少,也是集體優越性的重要表現。這說明,將公共資源用在托底保障,在發揮個人積極性的前提下,尚保留著平均分配的傳統,而不是唯個人能力論。
(三)由經營型向管理型轉變
經營型能人多產生于改革開放的初期,當時面臨的問題是如何經營好集體資源,讓集體經濟獲得更快的發展。在此背景下,產生了大量的“老板書記”。主要有以下三種情況:一是村支書將村莊當成企業來經營,自己扮演著“老板”的角色。將村莊的發展當成事業來做,雖然自己的獲利不多,但是村莊得到了發展,自己收獲了榮譽和成就感。二是讓“老板”來當村支書。當村干部就要有帶領大家致富的能力。也許,有些人的思想非常端正、作風也比較正派,而且還很勤勞,執行上級的政策不折不扣,但缺乏把握市場的能力,這也不適合擔任新時期的領路人。三是做了一段時間的村支書之后,掌握了許多的資源,自己去辦公司、當“老板”。這三類人的特點比較明顯,第一類是自己沒有公司,將村莊當成自己的公司,有能力無私心;第二類是先“老板”后村支書,在有了能力之后,經過組織的培養才成為村支書,為村集體作貢獻;第三類是組織培養過程中,發生了一定的異化,有了能力之后,沒有完全地用在集體上,而是為自己謀取利益。這三種類型的美譽度逐漸降低,村民們對第三類書記的意見較大,其存在會影響鄉村治理的秩序。
當前,農村中更加需要管理型的村干部來“守業”,對創業型村干部的要求在降低。管理型村干部所面臨的主要工作有三個:一是管理集體資產,實現保值、增值。二是協調處理各種村莊中的矛盾,保持社會的穩定。當前,處于社會矛盾的突發期,社會問題逐漸增多,維穩的任務落到了基層社區之中。相應的工作必須由村干部來完成,將矛盾和問題及時地化解。三是完成上級交辦的任務,完成對村民的服務工作。隨著服務型政府建設的步伐不斷加快,政府對村民有許多的補貼和服務,需要村干部進行配合,將其傳達給村民。同時,還有許多的創建活動,如新農村建設、環境綜合整治、房屋拆遷等,需要村干部進行落實。這類工作需要用心去做,不斷將任務進行細化,而不需要冒太大的風險,比較平穩。
上述三個特點所產生的基礎還是能人治村,只是與既有的模式稍有不同而已。盡管鄉鎮政府在其中發揮了較大的作用,但他們還是村莊的一員,尚未進入正式的科層體制,還可以在村民自治的框架下進行討論。
二、“新能人治村”的基礎
蘇南地區的村莊治理以新能人治村的形態呈現,與其他地區有較大的不同。這種形態的出現與以政府為主的招商引資發展模式、以村級為核心的集體所有制、土地管理的規范化和比較松散的社會結構有關。
(一)招商引資為主的發展模式
蘇南地區的集體經濟發展比較早,也擁有著比較深厚的集體主義傳統。改革開放后,雖然引進了大量的外資,發展了招商引資經濟,但并沒有削弱集體的力量,只是改變了發揮作用的形式。在發展經濟的過程中,任務和壓力在政府,但是土地以生產隊或村民小組為基礎。這就意味著若要發展經濟,必須對土地進行強有力的控制,只有掌握了土地資源,才能獲得發展的主導權。我國實行的是“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土地集體所有制,在此關系中,土地屬于集體,但又不明確為哪個具體的層級。三級所有本身就不排除公社或者鄉鎮政府對土地利益的支配和占有。從基層政府的角度來講,有著明確的將土地權力上收的沖動,但又不能完全上收,而讓自己陷入無盡的紛擾之中,成為實際的管理者。因此,本地的集體所有制更多體現在村級層級,但鄉鎮政府會進行有效管理。村民小組層級基本上被虛化了,不再成為一級核算單位。
招商經濟在較大程度上需要下級的配合,如果沒有相互之間的良好配合,就不能將土地資源效用充分發揮。政府只有發展的任務,但沒有發展的資源,因而必須牢牢控制住村干部的任命,如此方能控制資源的分配,比如土地的開發和資金的使用。這就決定了本地更需要以選拔的方式來產生干部,而不是以個人為主的競選。即便是競選,個人也沒有太多的資源,不可能影響村莊政治。因為發展的不是民營經濟,所以,大部分人沒有多少資金,這些企業家也沒有進入村莊政治的欲望。為了讓這些村干部們承擔起發展的職責,政府也就肩負著對干部進行遴選和培養的責任。只有讓這些干部們從基層做起,在不同的崗位上進行歷練,他們才能夠知曉各方面的情況,能夠掌握住大局,將一個村莊發展、經營好,實現集體資產的保值和增值。
(二)以村級為核心的集體所有制
以村級為核心的集體所有制對村干部的行為產生了兩方面的影響:一是不能讓自己的財富增長過快,侵吞集體的財產;二是必須將經營所得的收入全部用在集體方面,對村民進行照顧,保障村莊的公平秩序。以村級為核心的集體所有制要求村干部們將集體利益放在首位,而不能過多地追求個人的私利。村干部們過多地追求自己的私利,不在經營和管理方面用力,就達不到上級的要求,不能實現發展的目標,也會遭到村民的指責。
以村級為核心的集體所有制,使得村集體擁有大量的可支配收入,并在村莊內進行分配。集體收入的存在為照顧村民生活、提供相應的保障奠定了經濟基礎和道義基礎。既然收入屬于集體,那么就應該讓集體成員進行分享,對弱勢群體進行照顧。如果弱化集體的所有權,強化村民的承包權和經營權,那么集體就沒有收入,或者說收入極少,結果是富了個人、窮了集體。如果說集體的核心是村民小組一級,那么村級的收入就較為有限,支配能力會大大下降,在村莊內部的統籌變得不大可能。若將實際的支配權放在村民小組一級,多數情況會演變為本組內部的共有制,而不是公有制,會將集體收益均分掉,而不是用在發展上或對貧弱群體進行適當的照顧。以村級為核心的集體所有制為村干部們追求集體利益最大化提供了基礎保障和制約性條件。
(三)土地管理的規范化
經營型能人產生的重要條件是村莊擁有可以讓其進行經營的土地資源。在管理制度不健全的情況下,村莊享有較大的自主開發權。交通便利、條件優越的村莊,在頭腦靈活的村干部帶領下,將農業用地轉化為非農用地,獲得較多的增值收益。當時的經營主要是利用集體的土地興辦集體企業,或者建設廠房進行出租,發展壯大集體經濟。經營型能人有經濟頭腦、風險意識和品牌意識,通過在市場中搏擊,獲得了市場機會。在市場經濟的初期需要這種干部的存在,對村莊進行良好的經營。
2005年之后,土地管理逐漸規范和嚴格起來,發展的主導權逐漸上收到了政府手中,發展的模式轉變為以工業區、開發區為載體,而不再是村莊中的企業集中區。同時,在鄉鎮企業改革之后,村莊不再直接經營企業。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的規模進行了鎖定,不再可能進行大面積擴展,依靠土地的擴張進行發展的模式終結。現在,則是進行招商引資,提供土地或者廠房的租賃,發展的最大可能性就是實現既有集體資產的保值、增值。這也就使得村干部具有濃厚的職業經理人色彩,主要對以村為主的企業集中區進行管理,為企業提供服務。他們要有一定的管理能力,對集體資產進行有效的管理,對廠房進行適當的翻修,并選擇合理的出租方式,對村干部的經營性能力的要求在降低。能否實現集體資產的保值和增值,是對當前干部最大的考驗。
能人的類型與經濟發展的模式緊密相關。原來的集體經濟多是實體經濟,而現在則是租賃經濟,從地產、房產中獲得更高的收益。對于經營性活動來說,很難進行監督,在某些時刻需要給予他們一定的自由裁量權。可是,管理性活動則不然,可以對其進行有效監控。因此,也就產生了由經營型向管理型能人的轉變,他們都是村莊中的能力出眾者,但側重點有所不同。
(四)較為松散的社會結構
本地的村莊治理中呈現前述特征也與比較松散的村莊社會結構有關。松散的村莊社會結構主要表現為兩個方面:一是血緣關系比較松散,沒有形成緊密的“自己人”認同;二是經濟關系比較松散,沒有形成緊密的利益結合體。由于近代以來的戰亂,蘇南地區移民較多,沒有形成緊密的血緣共同體。在經濟的發展過程中,本地發展的是集體經濟和招商經濟,居民以在工廠中上班者居多,難以與企業經營者結成緊密的關系參與到村莊政治中來。這就使得蘇南地區的派性政治色彩比較弱,沒有辦法形成對立的派系。從這個角度上來講,村莊政治比較平淡,沒有太多的曲折和故事。
村干部不依靠派性政治選舉而產生,也就決定了他們與普通村民之間的距離基本相等,私人邏輯運作的空間比較小。[11]他們成為村干部不是依靠某個人的支持,而是獲得了絕大多數人的認可。那么,他們工作的目標就是要為大多數人謀福利,而不是為某個人負責。為了大局著想,村干部們會堅持比較一致的原則,獲得大家的認可。當堅持了原則之后,干部就有了說服村民的底氣,村民也沒有反駁的理由。這也就在客觀上造成了集體利益最大化的結果。
能人治村新特征的出現是建立在相應的經濟和社會基礎之上的,經濟發展模式、集體所有制的實現形式、土地管理方式和社會結構的變遷對村莊的治理結構有重要的影響。
三、結論與討論
新能人治村需要一定的經濟基礎、社會基礎和外部條件才會產生。最為重要的經濟基礎就是本地集體經濟的發展,土地控制在村級。在集體經濟發展的過程中,自然會產生與鄉鎮政府的緊密關系。鄉鎮政府希望通過各種方式來對村莊進行控制,最為明顯和有效的手段就是影響村干部的產生和工作方式。這種控制不只是表現在選拔上,還體現在對村干部的培養方面。在民營經濟發達的地區,直接選舉出來的是已經在市場經濟中擁有較強能力的人,而在集體經濟發展的條件下則要通過不斷歷練和培養才能成為真正的當家人。當然,村莊的社會結構和土地管理的規范化也會對村干部的行為邏輯產生較大的影響。
新能人治村是蘇南地區村莊治理的突出特征,遠比其他地區表現得明顯,但這并不意味著其他地區沒有能人治村,或者說該地區的能人就不存在問題。在集體經濟發展初期,由于監管不到位,出現了村干部侵吞集體財產的事件,引起了政府的高度重視和村民的反感。這種現象的出現,具有一定的客觀原因。政府為了發展經濟,鼓勵村干部們租賃土地或廠房帶頭致富,并作為一項重要的任務來落實。在土地的租賃效益尚未顯現出來之時,不存在太大的問題。當情況發生變化后,就成為了村莊分化的基礎,村干部成為比較富裕的階層。隨著能人由經營型向管理型的轉變和相關制度的完善,新上任的干部基本上不存在相關的問題,村莊治理也逐漸步入良性循環的軌道。
從全國的范圍來看,鄉村治理逐漸走向規范化,科層制的色彩逐漸增強,只是表現的形式有所不同罷了。在蘇南地區,行政化是通過將村莊的精英吸納進入體制實現的;在浙北地區則是將政府的工作人員派駐到農村去,實現聯村干部的常態化,對村干部進行經常性的督促和指導。隨著土地“三權分置”的實施,集體在其中發揮的作用也越來越強,鄉鎮政府也在利用這個契機,重振農村的集體經濟。當然,相應的管理制度也會更加嚴格,對村干部的能力和素質亦提出了新的要求。
[1]劉炳香 韓宏亮:《能人治村:新農村建設的戰略選擇》,《理論學刊》2007年第8期,第33頁
[2]盧福營:《經濟能人治村:中國鄉村政治的新模式》,《學術月刊》2011年第10期,第23頁
[3]盧福營:《論經濟能人主導的村莊經營性管理》,《天津社會科學》2013年第3期,第78頁
[4]王金紅:《村民自治與廣東農村治理模式的發展》,《華南師范大學學報 (社會科學版)》2003年第4期,第53頁
[5]施從美:《江蘇“富人治村”現象觀察》,《唯實》2013年第6期,第45頁
[6]賀雪峰:《論富人治村》,《社會科學研究》2011年第2期,第111頁
[7]歐陽靜:《富人治村與鄉鎮治理邏輯》,《北京行政學院學報》2011年第3期,第44頁
[8]余彪:《公私不分:富人治村的實踐邏輯》,《南京農業大學學報 (社會科學版)》2014年第4期,第17頁
[9]魏程琳 徐嘉鴻:《富人治村:探索中國基層政治的變遷邏輯》,《南京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4年第3期,第8頁
[10]鄭風田:《富人治村的“美”與“險”》,《人民論壇》2010年第2期,第4頁
[11]趙曉峰:《公私定律:村莊視閾中的國家政權建設》,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年
The Operating Mechanism and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of Governing Villages by the New Generation of Able Men
Li Kuan
The village governance model can be summarized by the new able people government in Sunan aera.Compared with the original governance model,there are three new features:in the way,it takes the township government selection and villagers election combination,and pay more attention to organizational training;in the behavioral goals,they pursuit the maximization collective interests and pay more attention to public demand;in the capacity requirements,it transforms the management to the administration and more emphasis on business ability.The emergence of these new features,with the local implementation of investment-based development approach to the village as the core of the collective economy,land management standardization and loose social structure,with distinct geographical and temporal characteristics.
innovation of social governance,community-building,issues concerning “agriculture,countryside and farmers”
上海行政學院社會學教研部 上海 200233
*該標題為《重慶社會科學》編輯部改定標題,作者原標題為《新能人治村:蘇南地區的村莊治理》。基金項目: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構建全民共建共享的社會治理格局研究——聚焦人口流入型地區”(批準號:15ZDC028)。感謝譚林麗、陳鋒、劉向東、王子愿、盧青青、江亞洲、朱愛和孫自然等在調查過程中給予的指導和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