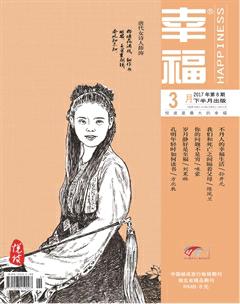紙窗
楊蓉
姥姥活著的時(shí)候,每年年節(jié)下給姥姥糊紙窗是我的頭等大事。
姥爺去世后,姥姥一直獨(dú)居。房子是早些年的舊房子,兩間。一間儲(chǔ)物,一間住人。儲(chǔ)物一間,有門(mén),無(wú)窗。住人一間,則一門(mén),一窗。窗是木框的,上兩扇,下三眼。下三眼,是大框,安的玻璃。上兩扇,全是小格格,需用紙糊。
糊紙窗,是個(gè)極細(xì)致的營(yíng)生。先得步行往鎮(zhèn)上買(mǎi)好白麻紙(后用一種韌性很好的高麗紙),及各色預(yù)配的彩色紙。還要在火爐上熬好稠稀恰當(dāng)、不見(jiàn)疙瘩的面漿糊。再就是把前一年的舊窗紙扯掉,并用小鏟將窗棱上的土渣、殘紙、舊干漿糊跡等細(xì)細(xì)鏟凈。這一應(yīng)做下來(lái),半日光景就過(guò)完了。接下去,才能將新漿糊均勻涂抹于窗棱上(一定要抹均勻,否則粘不平整),取先就裁剪好大小的紙,小心騰挪,疊對(duì)好位置,輕輕粘上(最好一次成功)。最后,再用炕帚子自上而下?lián)醿杀椋秃昧恕:寐榧垖樱φn才算完成一半了。待上窗的紙與漿糊稍干后,還要在麻紙上再貼一層花樣剪紙。先時(shí),姥姥總自己剪。至后,市面上就有賣(mài)現(xiàn)成的了。總之,紅點(diǎn),綠點(diǎn),裝飾的喜氣、好看,即可。糊裱裝飾一新的紙窗,像上轎新人的面龐,一片燦爛。
紙窗多趣。一就趣在漂亮上,趣在如上所說(shuō)的裝飾上。玻璃窗貼窗花,感覺(jué)很單調(diào)。紙窗則不然,有麻紙的白作底,貼上綠葉紅花,或草蟲(chóng)鳥(niǎo)雀,紅白相映,更覺(jué)“暖綠滿(mǎn)檐,山蜂亂飛”,一室冉冉春氣。紙窗又趣在隔而未隔,大有種朦朧意韻。屋外若有人行過(guò),玻璃窗一覽無(wú)余,紙窗則人影綽綽,叫屋內(nèi)的人心生好奇。而日色透過(guò)窗戶(hù)照進(jìn)來(lái),亦不似玻璃窗那般直白直辣,反倒是柔和和暖喧喧的,就連投到炕上的光色,都隱約著窗紙的紋絡(luò)。有月之夜,更是一派旖旎。曾記古人就有回文詩(shī)句云:“香篆裊風(fēng)青縷縷,紙窗明月白團(tuán)團(tuán)。”紙窗還有一趣,便如清人鄭板橋筆下所言,“風(fēng)和日暖,凍蠅觸窗紙,冬冬作小鼓聲”,真是好玩極了。
當(dāng)然,紙窗較玻璃窗,利弊亦是分明的。紙窗容易舊。再好質(zhì)地的紙,也不經(jīng)日曬風(fēng)吹。時(shí)久,紙色便會(huì)泛黃,看著不美不說(shuō),還會(huì)影響屋內(nèi)采光。這樣,就需勤糊勤換。糊好的紙窗,用手指節(jié)輕觸,會(huì)嘭嘭作響。若用指尖一捅,就破了。俗話(huà)說(shuō):“捅破窗戶(hù)紙”;俗話(huà)形容年輕人戀愛(ài):“男追女隔座山,女追男隔層紙”,彼紙此紙,即紙窗紙。此即紙窗衍生出的文化內(nèi)涵。不過(guò),如非情非得以,亦非蓄謀故意,紙窗一般是不會(huì)輕易破洞的。一旦稍有小洞,炎炎夏日倒大可不以為然,若遇到冷冬,有寒流襲來(lái),真?zhèn)€就應(yīng)驗(yàn)了土話(huà)說(shuō)來(lái)的:“指頭頭大的窟窿,椽頭頭粗的風(fēng)”。
姥姥年歲大了,也節(jié)儉慣了,紙窗糊好,一年光景里很少再動(dòng)。若破,就像給衣服打補(bǔ)丁一樣,隨便剪片紙補(bǔ)上。若舊了,也就任由其舊著去。紙窗一舊,姥姥的老屋就愈發(fā)像個(gè)老屋了。
姥姥曾養(yǎng)過(guò)一只貓,黃毛貓,特懶,一吃飽喝足,就四腳舒展的偎著姥姥躺在枕邊。午日正喧時(shí),紙窗投進(jìn)來(lái)的光,昏昏照在它身上,一呼吸,那毛像在舞。
后來(lái),這一情景,常入我夢(mè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