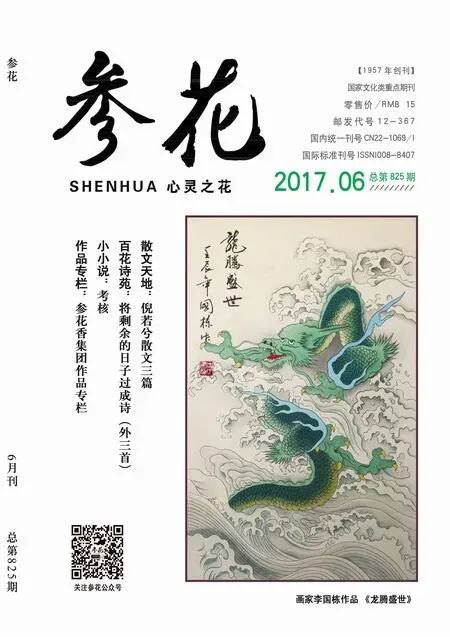周作人的序跋研究
◎趙蕾
周作人的序跋研究
◎趙蕾
本文以周作人為他人所作序跋為研究對象,研究其批評背景,以求管窺周作人文學批評態度和批評風格。文章認為,周作人在序跋中具有知識性、學理性的批評背景,自由、寬容的批評態度,以及感受式、印象式的批評方式。
周作人 序跋 批評背景 批評態度 批評方式
序跋是文學創作與文學批評的一種特殊形式,往往序在文前,跋在文后,起到對正文進行介紹或補充說明、解釋的功能。序“用以說明文獻著述和出版意圖、方法、體例、作者情況、著作出版過程等相關事宜,有的還對作家作品進行簡要的評論”,“跋的寫作體例、內容等,與序沒有嚴格區別,因而一般合稱序跋,如現今圖書中的前言、后記”①。序跋作為一種特殊的批評方式,與正文一同出版,既面對讀者,又和作者有著親密的聯系。序跋有著自由的體例、廣闊的言說空間和指涉范圍,對正文本具有重要的闡釋功能,可稱為副文本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從性質上講,序跋是一種文學批評,是一種與正文本相對的副文本。
現代作家對序跋很重視。魯迅先生曾說:“沒有木刻的插圖還不要緊,而缺乏一篇好好的序文,卻實在覺得有些遺憾。”②他的《〈吶喊〉自序》長久以來作為魯迅研究的重要史料;胡適《〈嘗試集〉自序》“不僅追溯了現代詩歌由起步到發展的歷史,討論了有關新詩創作的問題;而且涉及整個五四文學革命的發生等一些超乎詩歌創作范圍之外的史實”③。同時,郭沫若、茅盾、巴金等也有大量序跋文章存世,并對序跋這一文體有相關的論述,足見文學作家對序跋的重視程度。
據統計,周作人為他人所作序跋有220篇之多,近30萬字。在《燕知草》跋中,周作人曾提出:“作序是批評的工作,他須得切要地抓住了這書和人的特點,在不過分的夸揚里明顯地表現出來,這才算是成功。跋則只是整個讀過之后隨想的寫出一點印象,所以較為容易了。”④因此,研究周作人為他人所作的序跋,可以管窺其文學批評的態度與風格。在文本選擇中,本文以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的《知堂序跋》為主。編輯者鐘叔河是周作人作品的重要編輯,他在序文中寫道:“周氏一生所寫的序跋文,在這一冊中,大約包羅無疑了。”⑤因此,本文的主要文獻來源于《知堂序跋》中“為別人所作的序跋”一輯67篇。
一、知識性、學理性的批評背景
作序是一種批評的工作,天然地要求作序者對文本內容有充分的了解,甚至有涵蓋文本的能力。周作人為之作序跋的書,既有現代新文學的散文、小說,也有外國文學理論的中譯本,有中國的民歌集,也有古代的音韻詩歌鼓詞,還有關于繪畫、醫學等的,涉及多種學科門類。從這些書目可以看出,周作人具有廣泛的閱讀視野,而在具體寫作中,他的序跋不只是對于書中內容的簡單介紹,而是就這個話題進行有效的申發,體現出非常淵博的學識。周作人不僅介紹書的內容,而且從自己的治學經歷出發,介紹了書的特點甚至書籍所涉及的學科特點,引導讀者的了解和興趣。周作人的序跋批評工作,并不僅是“戲臺里面喝彩”地作介紹,而是有著濃厚的學理辨析。他以豐富的知識和科學的分析,講述文學的意義和書中內容的意義,為其進行價值的辨析。
周作人對民歌的系列序言可以體現他的這些批評特點。在早期的為劉半農輯錄的民謠集《江陰船歌》所作序中,周作人旁征博引,談民歌的分類、中外民歌的特征,對民歌之“民間”進行了定義,并對民歌的本質和地位給予了恰當而明確的定位。他認為民歌的特質,并不主要在于精彩的技巧和思想,只要能真是表現民間的心情,便是純粹的民歌。他表示,雖然反對用鑒賞眼光批評民歌的態度,但是贊成作者的輯錄,認為可以作為國人自我省察的資料。在《歌謠與婦女》中,也贊成作者兼顧社會意義和文學趣味,去研究歌謠中的婦女生活,在《〈海外民歌〉譯序》和《〈潮州畬歌集〉序》中,他都表達了類似的積極態度。
但是,周作人對民歌的態度有一個由支持到懷疑的轉變。在《重刊〈霓裳續譜〉序》中,他開始如實地表達自己思想的轉變,表示自己對民歌的質疑。他總結了五六年來民歌搜集出版的情況,并指出,以前他認為民歌是最古的詩,是純粹的民間創作,而現在則認為民歌是“民間的講故事或說書都很是因襲的技藝,這里邊的新奇大抵在于陳舊的事件或陳舊的詩句之重排改造,不是民眾自己的創造”。隨后,作者引介中國古代的例子,引出自己的重要觀點:“我以前覺得中國自大元帥以至于庶人幾乎人生觀全是一致,很以為奇,隨后看出這人生觀全是士大夫階級的,而一樣地通行于農工商,又極以為怪,現在這才明白了,原來就是這么一回事,中國民眾就一直沿用上一階級的思想并保留一點前一時期的遺跡。”鑒于此,他主張用新的態度對待民歌,即首先要把民歌當作文學去研究或鑒賞,不要離開文學史的估計而過分地估價,特別是不要因民眾、民族等觀念而憑一時的感情作出批評。這種前后不同的態度,不只是對民歌的價值褒貶,而是對民間思想的真實性由認可到懷疑的變化,這表明他對一種純粹的真實性的堅持。
這樣的一批序文,可以看出作者對古今中外民歌的知識性了解。周作人序跋豐富的知識背景背后,是科學的學理精神和巨大的邏輯力量,正是這一特點,促使作者在進行批評工作時,有著非常冷靜的批評態度、獨特的詮釋角度和思考方式。在《〈文學論〉譯本序》中,他說:“我平常覺得讀文學書好像喝茶,講文學的原理則是茶的研究。茶味究竟如何只得從茶碗里去求,但是關于茶的種種研究,如植物學地講茶樹,化學地講茶精或其作用,都是不可少的事,很有益于茶的理解的。”⑥周作人的學識和學理,正方便他“物理地”或者“化學地”以多方位的角度,去進行批評的工作。
由此,也就不難理解作者對《沉淪》的批評何以具有強大的說服力,正是在其豐富的學識和科學的學理性背景下,他為郁達夫的寫作做了雄辯式的正名:他認為,郁達夫的《沉淪》屬于非意識的不端方的文學,是出于自然的本能的受戒者的文學,但并不應擔負不道德的惡名。同時,這也幾乎可以驗證孫郁對他獨特性的評價:“當《新青年》諸人沉浸在口號式的說教中時,惟有他以豐富的知識論證了新文學之所以出現的必然,所謂上呼應于非正宗的儒學傳統,旁及歐美的個人主義藝術,下接今人的精神欲求。”⑦
二、自由、寬容的批評態度
自由與寬容是周作人文藝批評的基本態度。周作人在序跋中常常謙虛地表示自己并非在做批評,而只是表達一下感受和見解。在《竹林的故事》序中,周作人認為廢名的小說講述的是平凡人的生活,而非大的悲喜劇,卻正是現實。他提到:“特別的光明和黑暗固然也是現實之一部,但這盡可以不去寫他……將來著者的人生經驗逐漸進展,他的藝術自然也會有變化,我們此刻當然應以著者所愿意、給我們看到的所滿足,不好要求他怎樣的照我們的意思改作,雖然愛不愛看是我們的自由。”⑧在《文藝批評雜話》中,周作人談到,“我以為真的文藝批評,本身便應是一篇文藝,寫出著者對于某一作品的印象與鑒賞,決不是偏于理智的論斷”,文藝批評“里邊所表現的與其說是對象的真相,毋寧說是自己的反應”,正因為如此,在批評文藝作品時,“一方面想要誠實的表白自己的印象,要努力于自己的表現,一方面更要明白自己的意見只是偶然的趣味的集合,決沒有什么能夠壓服人的權威;批評只是自己要說話,不是要裁判別人”⑨。
周作人的文藝批評態度從根本上是由其對文藝本身的態度決定的。他認為文藝的根本是表現自己,而非為政治或者為人生,而每個人的個性都是不同的,因而在面對他人的文學時,便應當采取寬容的態度。他主張文藝的創作是出于自身情感的需要,他在《〈自己的園地〉舊序》提到:“我因寂寞,在文學上尋求慰安,夾雜讀書,胡亂作文。”⑩在《文藝上的寬容》中提到:“文藝以自己表現為主體,以感染他人為作用,是個人的而亦為人類的,所以文藝的條件是自己表現,其余思想與技術上的派別都在其次。各人的個性既然是各各不同,那么表現出來的文藝,當然是不相同。”(11)因此,進行文藝批評和文藝創作時,他反對以自己為唯一正確而不認可他人的做法,而 “主張自己判斷的權利而不承認他人中的自我,為一切不寬容的原因,文學家過于尊信自己的流別,以為是唯一的道,至于蔑視別派為異端,雖然也無足怪,然而與文藝的本性實在很相違背了”。
這種藝術觀并非周作人從一開始便提出和認可的,而是隨著時間發展逐漸發生的變化。在《中國新文學大系·散文一集》的導言中,他評價自己于1919年寫的文章《祖先崇拜》:“無論一個人怎樣愛惜他自己所做的文章,我總不能說上邊的這兩節寫得好,它只是頑強的主張自己的意見,至多能說得理圓,卻沒有什么余情。”(12)可見,文藝觀的逐漸變化,使周作人在逐漸放棄啟蒙的說教,不再追求教育的意義,而逐漸退回自己的園地,追求“余情”和藝術的況味。因而,在進行批評時,也主張寬容的態度。這種強調主觀欣賞、寬容鑒賞的批評方式,與純理性的、科學的批評方式不同。主張誠實與謙和的批評態度,使他的批評文章尊重作者的感情和思想,認可自在的人性,認同人本真的生活經驗,而并不去規定人“應該”描寫怎樣的生活,所要求的只是真誠與坦率。周作人自由寬容而非意圖說教的批評態度,使他的序跋文章具有獨特的價值,本身就可作為一篇文藝作品!
三、感受式、印象式的批評方式
在自由、寬容的批評態度之上,周作人的序跋具有感受式、印象式的批評方式。在評《桃園》時,他認為其中的一些人物,“即使不討人家的喜歡,也總不招人家的反感,無論言行怎么滑稽,他們的身邊總圍繞著悲哀的空氣。廢名君小說中的人物,不論老的少的,村的俏的,都在這一種空氣中行動,好像是在黃昏天氣,這時候朦朧暮色之中一切生物無生物都消失在里面,都覺得互相親近,互相和解。”(13)在這里,周作人以比喻和通感的方式描繪出自己理解的意境,這不同于一些干澀的序跋文章緊扣文本而缺少闡發,而是以一種文學性的話語表達自我感受和印象,以呼喚讀者的進入。
評及《莫須有先生傳》,這種感受性的傾向更加明顯。作者自言是在“用舊式批語評之曰:情生文,文生情”(14),并且舉了兩個例子談自己讀這篇小說的感覺:一是談小說似流水的自然蔓延之感,和給人帶來的清風拂面的柔順感受:“這好像是一道流水,大約總是向東去朝宗于海,他流過的地方,凡有什么汊港灣曲,總得灌溉瀠洄一番,有什么巖石水草,總要被披拂撫弄一下子才再往前去,這都不是他的行程的主腦,但除去了這些也就別無行程了”;二是借莊子的對風的論述,談廢名小說的順其自然和行云流水之感,認為小說寫得看似沒有道理,實則有內在的節奏和感覺,即是文生情情生文。周作人在文中提到,很多人認為《莫須有先生傳》難懂,他自稱也不能給出解答。但是,這樣鑒賞式、印象式的解讀,其實正是他給出的“讀懂”的方法。
印象式、感受式的批評最大的特點是注重情緒,能夠直接與作者和讀者的情感對接。正與作者對批評的看法相合:“我相信批評是主觀的欣賞不是客觀的檢查,是抒情的論文不是盛氣的指摘。”(15)在《雜拌兒之二》序中,作者戲言序跋文章的書寫:“以為文章切題為妙,而能不切題則更妙。”(16)切題意指符合邏輯地正面對文本提出分析,是理性的規范的思考。而不切題,是從自己的閱讀感受說起。看似不切題,實則這種言外之意正是源于自己最初和最真切的閱讀感受。這也正符合了他對文學的認知:文學的創作既然是源于情緒,那么閱讀當然也應該首先注重自己的情緒和感受,這才和作者的創作動機真正地吻合,也是文學的美學意義之一。
當然,類似于《莫須有先生傳》這樣的評價,讀起來其實是有些費力的。如他后期的一些序跋和私人讀書筆記,純粹走向文言而少解釋,確實會容易有理解上的難度,從而影響讀者的接受。但是,作為一種批評方法,這種“中國式”的批評仍然是值得學習的。它注重感性的理解,注重意蘊和情思以及心靈的體會。文學是人學,可以表達自己創作的心跡,也可以豐富人對世界的感受,而這樣的文學批評,正是和這個意義上的文學功能相通的。他的文學史意義正如錢理群所言:“如果五四時期科學的時政批評對中國傳統批評是一種歷史的否定與反叛,那么,主觀的印象、鑒賞式的批評卻又是在更高層次上與中國傳統批評取得了內在的聯系。”(17)
周作人曾為俞平伯的《雜拌兒之二》作序,他認為這些散文是“以科學常識為本,加上明凈的感情與清澈的智理,調和成功的一種人生觀,以此為志,言志固佳,以此為道,載道又復何礙”(18)。這個評價標準其實也可以拿來理解周作人自己,以豐富的雜學作背景,將科學的學理性分析和細致的感受印象內在地契合,使他的文學批評既能清楚地看到作品背后的來源和紋路,卻又有鮮活的感受。當代作家中還難以斷言誰有這樣成熟的風格。如果把這條批評之路追根溯源,則可發現,對中西經驗有著高度契合的批評者,正可從周作人說起。因此,即使從文學批評的角度來說,依然可以借用舒蕪的話:周作人是我們不應該拒絕的遺產!
注釋:
①徐鵬緒等:《中國現代文學文獻學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4年版,第458頁。
②魯迅:《魯迅全集·編年版,第6卷 1929-1932),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4年版,第546頁。
③徐鵬緒等:《中國現代文學文獻學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4年版,第458頁。
④⑤⑥⑧⑩(12)(13)(14)(15)(16)(18)周作人:《知堂序跋》,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292頁,編者序Ⅰ,第310頁,第252頁,第25頁,第371頁,第225頁,第259頁,第25頁,第330頁,第331頁。
⑦周作人:《周作人精選集》,北京燕山出版社,2009年版,第3頁。
⑨張菊香編:《周作人代表作》,鄭州:黃河文藝出版社,1987年版,第79-83頁。
(11)周作人:《自己的園地·雨天的書·澤瀉集》,長沙:岳麓書社,1987年版,第8-9頁。
(17)錢理群:《歷史的毀譽之間——簡論周作人文藝批評理論與實踐》,《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從刊》,1988年第1期。
[1]徐鵬緒.中國現代文學文獻學研究[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4.
[2]魯迅.魯迅全集·編年版·第6卷(1929-1932)[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4.
[3]周作人.知堂序跋[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
[4]張菊香.周作人代表作[M].鄭州:黃河文藝出版社,1987.
[5]周作人.自己的園地·雨天的書·澤瀉集,[M].長沙:岳麓書社,1987.
[6]錢理群.歷史的毀譽之間——簡論周作人的文藝批評理論與實踐[J].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1988(04).
(責任編輯 葛星星)
趙蕾,女,本科,山東省德州市齊河縣文化局,科員,研究方向:現當代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