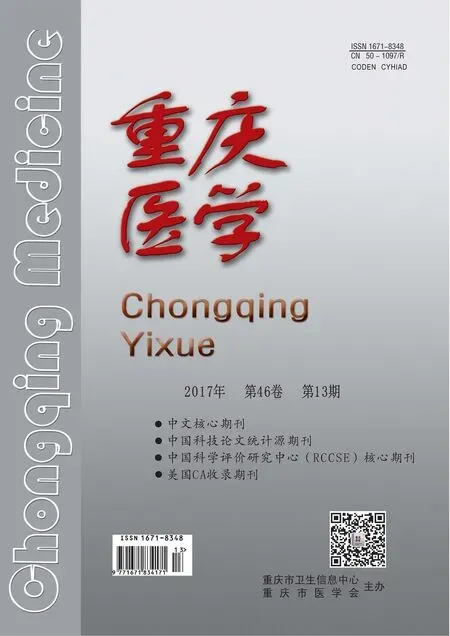新型毒品濫用與男男性行為者艾滋病的傳播*
蔣和宏,陳 于 綜述,歐陽琳 審校
(1.重慶市疾病預防控制中心 400042;2.重慶醫科大學公共衛生與管理學院/醫學與社會發展研究中心/健康領域社會風險預測治理協同創新中心,重慶 400016)
·綜 述·
新型毒品濫用與男男性行為者艾滋病的傳播*
蔣和宏1,2,陳 于2綜述,歐陽琳1△審校
(1.重慶市疾病預防控制中心 400042;2.重慶醫科大學公共衛生與管理學院/醫學與社會發展研究中心/健康領域社會風險預測治理協同創新中心,重慶 400016)
新型毒品;艾滋病;男男性行為者
自2007年以來,性接觸持續成為我國艾滋病的主要傳播途徑,尤其是男男性接觸感染呈快速上升趨勢,在人類免疫缺陷病毒(human immunodeciency viruses ,HIV)的經性傳播途徑中,新型毒品起著很重要的作用,新型毒品濫用者會因吸食新型毒品后更易發生群體性、無保護性的性交及性交頻次增加,從而大大增加HIV的感染概率和傳播風險[1]。男男性行為者(man who have sex with man,MSM)是艾滋病/性傳播疾病(acquired immune deficiency syndrome,AIDS/sexually transmitted diseases,STD)的三大高危人群之一[2],也是使用新型毒品的高危群體之一[3],主要包括男同性戀者(gay)、男雙性戀者(Bi)及與同性有性接觸史的男異性戀者(MH)[2]。近年來,國內外已有大量關于新型毒品濫用與感染和傳播HIV的關系研究,國外還有較多關于新型毒品濫用與MSM人群感染和傳播HIV的關系研究,國內近年來也有一些相關研究報道。本文重點關注新型毒品濫用對MSM感染HIV的影響。
1 新型毒品及其濫用現狀
1.1 新型毒品 新型毒品是相對鴉片、海洛因等傳統毒品而言,主要是指人工化學合成的致幻劑、興奮劑類毒品,是由國際禁毒公約和我國法律法規所規定管制的、直接作用于人的中樞神經系統,使人興奮或抑制,連續使用能使人產生依賴性的一類精神藥品。在美國和很多國家,新型毒品因在酒吧、歌舞廳等娛樂場所流行而被稱為“俱樂部藥物”[1]。根據新型毒品的毒理學性質,新型毒品分為興奮劑、致幻劑、兼具興奮和致幻劑、抑制劑四類,代表物質分別為甲基苯丙胺(MA,俗稱冰毒)、麥角乙二胺(LSD)、二亞甲基雙氧安非他明(MDMA,我國俗稱搖頭丸)和三唑侖等。我國常見的新型毒品有冰毒、搖頭丸、氯胺酮(即K粉)、咖啡因和三唑侖。
目前,合成毒品出現種類和數量增多、成分不確定的問題,越來越多的新型合成毒品改頭換面、掩人耳目,逃避打擊,在形式上甚至以藥品或飲料的外包裝出現。還可以從網上查到一種“新新型毒品”,又叫“新精神活性物質”。這些“新精神活性物質”一般通過修改現有毒品的化學結構,從而變成新的物質。與冰毒、K粉等新型毒品相同,新精神活性物質同樣是合成毒品,但大多具有更為強烈的興奮或致幻作用,而且更易于逃避法律管制。
1.2 新型毒品濫用現狀 盡管新型毒品進入我國的時間不長,但由于新型毒品制造方法相對簡單、價格相對便宜、容易獲得[4],吸食人數迅猛上升,已成為21世紀全球范圍內濫用的主要毒品,引起了嚴重的社會和公共衛生問題。據國家禁毒委發布的《2015年中國毒品形勢報告》顯示:我國新型毒品濫用相當嚴重,已經超過海洛因等傳統毒品,截至2015年底,全國現有吸毒人員234.5萬名(不含戒斷三年未發現復吸人數、死亡人數和離境人數),吸食海洛因等阿片類毒品和濫用合成毒品者分別占41.8%和57.1%;在2015年新發現的53.1萬名吸毒人員中,濫用合成毒品人員占80.5%,其中濫用冰毒等苯丙胺人員占73.2%;2010-2015年全國濫用海洛因等阿片類吸毒人員所占比例從69%逐年減少到41.8%;濫用合成毒品人員所占比例從28%逐年增長到57.1%;濫用人群以男性為主,占85.6%,以35歲及以下年齡為主,占62.4%,無業人員居多,占69.5%。
2 新型毒品與艾滋病
新型毒品為導致中樞神經興奮類精神藥物,吸食后可使人產生持續的興奮,增強性欲,增加性行為頻次,延長性持續時間,易發生無保護性的性行為及群體性濫交,大大增加了HIV傳播和感染風險[3]。高良敏等[5]調查發現,云南省某地區使用冰毒者達到81.27%,“最近一次使用后與他人發生性行為”、“最近3個月使用后,與他人發生過性行為”的HIV感染率高于使用后未與多人發生性行為者。傅繼華等[6]在青島市調查305名新型毒品吸食者發現,最近一年與臨時性伴發生過性行為者占89.8%,發生性行為時從不使用、有時使用安全套的占94.1%;通過錢或提供毒品方式得到過商業性伴提供性服務的占81.6%,發生性行為時從不使用、有時使用安全套的占83.6%。分析余姚市看守所345名男性新型毒品濫用者發現16.2%混合用藥,66.1%的人吸毒后會發生性行為,性伴數多且不固定,65.4%的性伴是臨時性伴或性服務工作者[7]。女性性工作者(female sex workers,FSW)無保護性的多次性交以及多性伴性交等高危性行為,與吸食新型毒品顯著相關[8]。由此可見,新型毒品的使用大大增加了高危性行為的發生頻率,從而增加了HIV的感染和傳播。
使用新型毒品還可使機體的細胞免疫和體液免疫受損,機體免疫力降低,從而增加HIV 的感染機會[3]。新型毒品濫用可影響AIDS患者的血清學檢測結果,還可影響HIV/AIDS患者的臨床表現[9]。濫用新型毒品還對HIV/AIDS的治療有影響[10-11]:可降低患者的抗病毒治療依從性、維持較高的病毒載量、發生機會性感染、導致病毒耐藥性的發展,使抗病毒治療效果下降,從而使HIV感染者病死率增加。
3 新型毒品與MSM
3.1 MSM使用新型毒品的主要原因 MSM人群是新型毒品使用的主要人群之一,使用的原因主要包括三方面:一是情緒的釋放和增加愉悅感。新型毒品提供了一個社交的經歷和情緒的釋放,幫助他們在社交活動的中心場所(如迪廳)開放自己,年輕的MSM使用率較高[12-13];新型毒品還能使人產生欣快感和自信感[14],增加MSM在長時間舞會中的體力和耐力;HIV陽性的MSM以吸食新型毒品來消除恐懼、減少恥辱及HIV傳染給他人的愧疚[15]。二是新型毒品可以使一些人產生性喚起,削弱性抑制力,獲得更多的性動力和持久力,MSM中使用程度很高;在研究男同性戀者的群交行為時發現,新型毒品被廣泛地用于提高性刺激和性能力[1]。三是對新型毒品的錯誤認識。某些MSM社區人員認為新型毒品不易成癮,使用冰毒后可以集中精力做一項工作;還有一些MSM以減肥為目的,受誘惑而嘗試。此外冰毒價格低廉,能產生較長的刺激性,因而在MSM中廣泛使用[4]。
3.2 MSM人群新型毒品使用種類及現狀 MSM人群是濫用新型毒品的重要人群,在西方,毒品使用在MSM中相當流行,國外相關研究顯示,在MSM場所內新型毒品的使用比例非常高[16]。MSM人群中使用非常普遍的新型毒品是冰毒、可卡因、搖頭丸、GHB和K粉,它們通常被單獨使用或混合使用[17]。冰毒在MSM人群中被廣泛使用,不同年齡、不同學歷、不同種族和不同HIV感染狀況的MSM都曾使用過冰毒[4,13]。相關研究顯示MSM在公園等公眾場所更傾向于吸食冰毒、可卡因,而在迪吧、浴室等商業性娛樂場所更傾向于使用poppers、K粉和GHB[18]。還有一種“0號膠囊”,在同志圈內使用也較普遍,使用后也能產生強烈的性沖動,并出現幻聽、幻視等現象,會使安全套使用率在MSM人群中大大降低,在網絡和男同浴池可以購買到,存在監管空白[19]。美國的一項研究顯示亞裔MSM人群中有51%的人使用新型毒品[20]。HIV陽性的MSM與HIV陰性的MSM相比更可能濫用各種新型毒品或多種新型毒品混合使用[21]。國內一項匿名調查發現:2 114名MSM中有180人使用過毒品,占8.5%[2]。向男性提供性服務的男性性工作者(money boys,MB)是MSM中的特殊亞人群,MB中吸食新型毒品的比例較高,劉慧等[22]對我國深圳、上海兩市的122名MB調查發現有28.7%的MB在場所內使用新型毒品。對杭州市10例MB進行個人訪談發現有3例曾經吸過毒,使用過搖頭丸、K粉和冰毒等新型毒品[23]。新型毒品在年輕的MSM中使用程度較高[12]。有研究表明年紀小、文化程度低、在網上和酒吧找伴侶的MSM是濫用新型毒品的主要人群[24]。
3.3 新型毒品對MSM人群傳播和感染HIV及艾滋病治療的影響 相關研究顯示新型毒品濫用與MSM人群的高危行為之間有密切聯系,而MSM人群又是艾滋病感染率較高的人群,這無疑造成該人群艾滋病疫情的進一步蔓延。近年來我國MSM人群中HIV的感染率逐年上升,或許與新型毒品的濫用導致的HIV高危性行為增加有關。若多種新型毒品合用會更進一步增加發生無保護性肛交等高危性行為的可能性,加大艾滋病的傳播概率[25]。
MSM與臨時性伴在性行為之前或過程中使用新型毒品后易發生無保護性的肛交,尤其是HIV陽性的MSM,這加速了HIV的感染和傳播[26-29]。使用新型毒品的MSM在迪吧、賓館等公共場所易發生群交[19]。對MSM群交行為的研究發現,濫用新型毒品使HIV感染率再度呈上升趨勢[1]。于增照等[2]對我國9個城市的2 114名MSM匿名調查發現:gay、Bi毒品組的性伴數高于非毒品組、參與向同性“買”性活動百分率和近1年曾去外地與陌生男子性交百分率均高于非毒品組,gay、Bi毒品濫用者約30%曾參與同性性交易,Bi毒品組近1次與女性發生性行為安全套使用率低于非毒品組,MH毒品組近6個月同性肛交時安全套使用率、近1次與女性發生性行為安全套使用率明顯低于非毒品組。新型毒品濫用導致的多性伴、匿名性伴增加及群交等高風險性活動/性行為加大了使用者感染和傳播HIV的可能性[2,24]。Bi是向女性傳播HIV的主要人群,也是HIV從MSM向一般人群傳播的重要“橋梁”[2]。MB約占我國MSM人群的9%。MB存在商業性行為和多性伴等多種高危性行為,易感染HIV,是HIV傳播的重要核心人群[30]。由此可見,MSM人群濫用新型毒品后更多的性伴數、更可能作為“0”號參與無保護性肛交、使用安全套和正確使用安全套的可能性減少等因素導致了MSM人群中感染和傳播HIV的可能性增加。
研究發現感染HIV的MSM使用MDMA后可能出現血清素綜合征,且MDMA可以對MSM的免疫系統產生抑制作用,抑制B細胞的活化,使CD4+細胞數、NK細胞數下降,損害機體的細胞免疫和體液免疫,增加HIV的感染機會[31]。相關研究表明冰毒濫用與抗病毒治療依從性降低、維持較高的冰毒載量、發生機會性感染和感染HIV的MSM死亡率增加有關[32]。
4 結 論
由于性傳播已成為中國艾滋病傳播的主要途徑,因而針對與性傳播有直接關聯的新型毒品濫用的研究變得日趨重要,MSM人群作為艾滋病高感染率人群和新型毒品使用的主要人群之一,將成為首要重點關注人群。新型毒品濫用已成為一個嚴重的社會問題。新型毒品濫用會增加不安全性行為,降低人的免疫力,增加HIV感染和傳播風險,并對HIV/AIDS的治療產生不利影響。MSM人群是使用新型毒品的主要人群之一,其HIV感染率較高與濫用新型毒品有很重要的關系,因此對此類人群的行為應高度重視。在今后的MSM干預工作中,加強毒品與艾滋病危害的宣傳,減少新型毒品的使用,矯正吸毒者的行為,降低毒品和艾滋病的不利影響迫在眉睫。
[1]夏國美,楊秀石,李駿,等.新型毒品濫用的成因與后果[J].社會科學,2009(3):73-81.
[2]于增照,張北川,李秀芳,等.毒品使用對男同/雙性愛者艾滋病高危行為的影響[J].中國預防醫學雜志,2009,10(6):433-437.
[3]黃鋼橋,袁秀琴,陳曦.新型毒品濫用與艾滋病的傳播[J].實用預防醫學,2014,21(5):638-640.
[4]Fisher DG,Reynolds GL,Napper LE.Use of crystal methamphetamine,viagra,and sexual behavior[J].Curr Opin Infect Dis,2010,23(1):53-56.
[5]高良敏,趙金山,楊江華,等.云南某地區新型毒品使用人群HIV感染率及其影響因素分析[J].中國皮膚性病學雜志,2013,27(11):1130-1133.
[6]傅繼華,姜珍霞,李令國,等.新型毒品吸食者性行為特征分析[J].中國公共衛生,2012,28(2):240.
[7]賀曉,史宏輝,邵迪初,等.新型毒品濫用者感染HIV、梅毒、HCV狀況調查[J].浙江預防醫學,2014,26(3):278-279.
[8]Rawson RA,Gonzales R,Pearce V,et al.Methamphetamine dependence and 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 risk behavior[J].J Subst Abuse Treat,2008,35(3):279-284.
[9]向紹密,農幼豐,周梅,等.新型毒品與HIV/AIDS相關性的研究進展[J].中國臨床新醫學,2013,6(4):384-387.
[10]Rajasingham R,Mimiaga MJ,White JM,et al.A systematic review of behavioral and treatment outcome studies among HIV-infected men who have sex with men who abuse crystal methamphetamine[J].AIDS Patient Care STDS,2012,26(1):36-52.
[11]Kipp AM,Desruisseau AJ,Qian HZ.Non-injection drug use and HIV disease progression in the era of combination antiretroviral therapy[J].J Subst Abuse Treat,2011,40(4):386-396.
[12]Cochran BN,Cauce AM.Characteristics of lesbian,gay,bisexual,and transgender individuals entering substance abuse treatment[J].J Subst Abuse Treat,2006,30(2):135 -146.
[13]Halkitis PN,Green KA.Mourgues P.Longitudinal investigation of methamphetamine use among gay and bisexual men in new york city:findings from project BUMPS[J].J Urban Health,2005,82(1 Suppl 1):i18-i25.
[14]Marques Pontinha CM.Club drugs[J].Acta Med Portuguesa,2012,25(1):60.
[15] Reback CJ,Larkins S,Shoptaw S.Methamphetamine abuse as a barrier to HIV medication adherence among gay and bisexual men[J].AIDS Care,2003,15(6):775 -785.
[16]Fernandez I,Jacobs RJ,Warren JC,et al.Drug use and hispanic men who wave sex with men in south florida:implications for intervention development[J].AIDS Educ and Prev,2009,21(5):45-60.
[17]Morgenstern J,Bux DA,Parsons J,et al.Randomized trial to reduce club drug use and HIV risk behaviors among men who have sex with men[J].J Consult Clin Psychol,2009,77(4):645-656.
[18]Semple SJ,Strathdee SA,Zians J,et al.Factors associated with sex in the context of methamphetamineuse in different sexual venues among HIV-positive men who have sex with men[J].BMC Public Health,2010(10):178-183.
[19]張磊.危險的“0號膠囊”[J].現代養生,2015,8(1):9-10.
[20]Operario D,Choi KH,Chu PL,et al.Prevalence and correlates of substance use among young Asian pacific islander men who have sex with men[J].Prev Sci,2006,7(1):19-29.
[21]David WP,David S,Catherine A.Consistency and cange in club drug use by sexual minority men in New York City,2002 to 2007[J].Am J Public Health,2010(100):1892-1895.
[22]劉慧,薛琿,馮鐵建,等.兩城市場所內男性性工作者新型毒品使用現況[J].中國艾滋病性病,2011,17(6):643-645.
[23]程潔,羅艷,陳樹昶,等.杭州市男男性工作者生存狀況的定性調查[J].江蘇預防醫學,2012,23(5):48-49.
[24]Chen X,Li X,Zheng J,et al.Club drugs and HIV/STD infection:An exploratory analysis among men who have sex with men in changsha,China[J].PLoS One,10(5):e0126320.
[25]Yu G,Wall MM,Chiasson MA,et al.Complex drug use patterns and associated HIV transmission risk behaviors in an internet sample of U.S.men who have sex with men[J].Arch Sex Behav,2015,44(2):421-428.
[26] Purcell DW ,Moss S,Remien RH,et al.Illicit substance use,sexual risk,and HIV-positive gay and bisexual men:diferences by serostatus of casual partners[J].AIDS,2005,19(Suppl 1):S37-S47.
[27]Forrest DW,Metsch LR,Lalota M,et al.Crystal methamphetamine use and sexual risk behaviors among HIV-positive and HIV-negative men who have sex with men in South Florida[J].J Urban Health,2010,87(3):480-485.
[28]Mackesy-Amiti ME,Fendrich M,Johnson TP.Symptoms of substance dependence and risky sexual behavior in a probability sample of HIV-negative men who have sex with men in Chicago[J].Drug Alcohol Depend,2010,110(1/2):38-43.
[29]Golub SA,Starks TJ,Payton G,et al.The critical role of intimacy in the sexual risk behaviors of gay and bisexual men[J].AIDS Behav,2012,16(3):626-632.
[30]Liu H,Liu H,Cai Y,et al.Money boys,HIV risks,and the associations between norms and safer sex:a respondent-driven sampling study in Shenzhen,China[J].AIDS Behav,2009,13(4):652-662.
[31]Romanelli F,Pharm D.Use of club drugs by HIV-seropositive and HIV-seronegat-ive gay and bisexual men[J].Int AIDS society USA Topic HIV Med,2003,11(1):25-32.
[32]Rajasingham R,Mimiaga MJ,White JM,et al.A systematic review of behavioral and treatment outcome studies among HIV-infected men who have sex with men who abuse crystal methamphetamine[J].AIDS Patient Care STDS,2012,26(1):36-52.
10.3969/j.issn.1671-8348.2017.13.041
重慶市衛生和計劃生育委員會醫學科研項目(2015MSXM093)。 作者簡介:蔣和宏(1981-),碩士在讀,主管醫師,主要從事性病、艾滋病預防與控制研究。△
,E-mail:328513118@qq.com。
R512.91
A
1671-8348(2017)13-1848-03
2016-11-18
2017-01-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