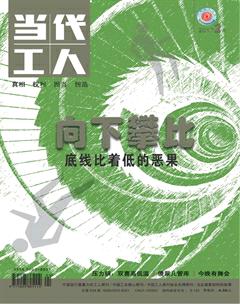誰帶壞了誰
龔平
早年間那一幕
1980年代那10年,20多歲的德平在一個集體小廠做工會干事。那時每逢年節,工會都要給困難職工發補助金。第一次參加困難職工評議會,把德平驚得不行,“車間、科室領導都認為自己的某個員工最困難,證據五花八門,什么家有80多歲癱瘓的老母了;兒女多,花銷太大了;媳婦是農村戶口沒有工作了。互相吵,互相貶,要把補助金搶到手。”德平說。
這不算完,艱難博弈后,補貼名單敲定、公布,其后工會的門檻就會被職工踏平,這個問:憑啥沒有我?那個喊:你們偏向!他們找出各種證據證明自己比誰誰更慘。德平記得,“有一師傅找的證據令人哭笑不得,他說他兒子因盜竊進去了,家里人承受不了,需要工會補助。你說說!”
那個年代如此比慘,以求得到那一二十塊錢補助,皆因國家窮,人更窮,可以理解。現在人們仍舊比慘,原因就復雜多了。“你都弄不清到底是中國人骨子里愿意比慘呢,還是什么制度使人不得不比慘。”德平說,“或許是想不出好辦法了,只能比慘,不比慘就得不出相對公正的結果。”
向下看齊
在這方面,最典型的要數高校發放助學金時、國家評定貧困縣時。
2016年11月,主流媒體和網上共同比較熱乎的一個新聞是:云南高校貧困生上臺演講“比窮”爭助學金。說的是有高校在評定助學金時,讓學生上臺演講比窮,根據投票劃定等級,再匹配相應的助學金。網傳聊天截圖顯示,某班在評定過程中,“班主任執著不休”“非讓把住址還有家庭狀況說清楚”,“我旁邊兩個哭的”“又一個學生說不下去哭了”。
對此,德平不以為意,“這種事多了,以前也有報道,但沒像這次這么熱鬧。天知道這次發的什么神經。”德平這么說,是因為他覺得在媒體泛泛的、不痛不癢的“損害學生自尊”的批評中,社會未見得能感同身受學生受到的傷害,“我一同學的女兒就被這么折磨過,我比你們了解。”
據德平講,他這個同學是真窮!“說上無片瓦遮身,下無立錐之地絕不為過。”同學有佝僂病,媳婦是農村戶口,還有小兒麻痹后遺癥。這二人結合到一起,還生了一個女兒,其困難可想而知。靠著低保金和親朋的資助,加上在社區公益崗掙那點兒錢,兩口子好歹算把女兒供上了大學,女兒的用度花銷也多起來。兩口子不得不以每月800元把50多平方米的房改房租出去,借鐵路邊的圍墻,壘了一間五六平方米的小磚房湊合住。
“我跟他女兒很熟。每次孩子放假回來,我都去看她,拿點吃的花的用的。孩子真懂事,每次見我都笑盈盈的。可孩子老偷偷哭,他爸告訴我的。”德平說。有一次,同學把他叫去,拿女兒的日記給他看,“談不上是日記,就一作業本,上面記了孩子兩三天的感受,回校時落家里了。”
從孩子對這兩三天的記述里,德平了解到,孩子不忍心讓爸媽為她受更多苦,就在學校打零工,但錢還是不夠用,不得不申請助學金。“學校都一個德行,讓孩子上臺講家里怎么窮。要命的是,這所高校不知中了什么邪,申請助學金還有名額限制,最后,這丫頭和一同學條件差不多,老師讓他們再比一把,決出勝負,還是上臺演講,還是比誰家里窮……”
講到這,個頭近一米八的德平滿臉漲紅,眼里含淚,聲音哽咽。
沉靜了一會兒,德平說:“孩子受不了這個呀,可為了爸媽,不受也得受哇!那幾頁日記,好些地方都被淚打濕了,字都看不清了。”德平脫口而出幾句罵人話。這要是讓憤青式網友知道了,難聽的話肯定更多。
德平的不解是,“你說誰愿意向下攀比呀,可學校就這么個做法,你不向下攀比行嗎?就說這孩子,她不往下攀比行嗎?都是被逼的呀!”
我是窮人我怕誰
德平無意中戳中了一個原因,很多人的向下攀比除了個人文化素質和道德水準等原因,也是組織化、制度化的結果。在這方面,很多縣不愿摘掉貧困縣帽子,甚至以進入貧困縣行列為榮,就是一個鮮明的佐證。
早在1992年,為慶祝成為“國家扶貧開發重點縣”,湖南邵陽縣全城放鞭炮,竟致煙花爆竹脫銷。20年后的2012年,與邵陽縣相鄰的新邵縣步其后塵,1月末,幾行大字出現在戶外一大型顯示屏上:熱烈祝賀新邵縣成功納入國家集中連片特困地區,成為新時期國家扶貧攻堅的主戰場。落款是:中共新邵縣委、新邵人民政府宣。盡管新邵縣領導作了辯解,但無論如何,向下攀比的心態,似也成了兩縣官民的共同文化心理。
其后的2013年11月,習近平到湘西考察時首次作出“實事求是、因地制宜、分類指導、精準扶貧”的重要指示。2014年1月,中辦詳細規制了精準扶貧工作模式頂層設計,推動了“精準扶貧”思想落地。
這兩年,“慶祝成為扶貧縣”的現象不見了,這有賴于中央“精準扶貧”戰略的實施。但是,向下攀比的文化心理,在很多人心中沉淀下來。
2016年11月4日,湖北巴東縣廣播電視臺在微信公眾號推送了《陳行甲:精準扶貧中,自強感恩教育要跟上》一文。作者陳行甲寫道,在扶貧中,有些貧困戶不懂感恩,卻無理取鬧,“我是窮人我怕誰”“我是小老百姓我怕誰”“我掐著你玩”。陳行甲要求加強對群眾的自強感恩教育。
陳行甲是巴東縣委書記,2015年5月獲全國優秀縣委書記稱號。拋開“加強感恩教育”這一提法是否妥貼不提,單說陳行甲在文中羅列的那些現象,足以佐證向下攀比已不是個別現象,“我是窮人我怕誰”已經突破底線,再往下,恐怕就是“光腳的不怕窮鞋的”“我是惡人我怕誰”。
發展向上,人性向下,這需要文化反思、制度反思:社會何以如此?人何以如此?在現有文化和制度背景中,人與社會在怎樣互為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