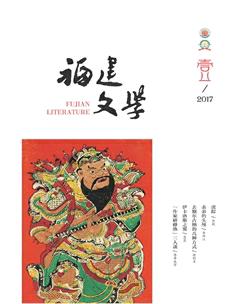地理,皆史也
林志民
多數旅行者——包括我,雖然走過天南地北、歐亞美非,往往是匆匆而來、潦草一看,了無心得,只算到此一游的過客,最大的成果是狂拍照片,發了許多朋友圈,證明自己去過哪兒,讓大家知道人在哪兒。
蕭春雷的旅行不一樣。他關注人與自然的關系;他知道可看什么,該找什么;他能俯瞰大勢,又析研精微;他知道哪座山是萬山之祖,哪座城是城池之母;在張掖,他發現觻得古城遭黃沙追逐,渴死在河邊;在毛烏素,他追問沙漠中的統萬城,是城池招致荒漠,還是沙漠上真可以造城;他探究大山何時隆起,大地為何下陷;登別迭里山口,瞧見千年前玄奘的背影;在帕米爾高原,發現條條最偉大的道路會聚于此。別人只看熱鬧,春雷卻找到秘門密道,帶我們登大堂、入暗室,深入淺出,左右旁通,終于豁然開朗。
“有人問我為什么喜歡旅行,”蕭春雷寫道,“因為我希望了解另外一些人的生活,了解人類應對草原、沙漠、海島、凍土、雨林等自然環境挑戰的智慧。”春雷這幾年做過許多壯游,因此收獲了三本新書,《自然骨魄》《大地棲居》《華夏邊城》,統稱“中國的掌紋”系列。
春雷告訴我們許多歷史和地理知識,揭示地理現象背后的諸多秘密。他的三本書,每篇都讓我驚訝贊嘆:他懂得這么多,他的文章寫得真好啊!我想起維吉爾《牧歌》中贊頌羅馬的詩句:此城高于他城,就像喬木高于灌木。
蕭春雷花那么多時間從事旅行寫作,我曾略有異議。春雷是我敬佩的作家,我覺得他如果更多的從事文學創作,會寫出極好的傳世之作。
在古代,人們只要有膽量走出家鄉,在村里就會引人注目,當他回來繪聲繪色講述陌生世界的故事,就成了旅行作家。遷徙與旅行,曾是早期人類活動的主要方式,也是歷史與文學寫作的重要源泉。在《出埃及記》里我們看到,摩西帶領閃的子孫離開埃及,前往應許之迦南地,那時腓尼基人正在海上探險,而阿拉伯人還在沙漠流浪。荷馬史詩描寫奧德修斯駕船駛入黑色海洋,看見世界像個圓盤,四周有大洋河環繞。希羅多德十年游歷歐亞,幾乎走到當時已知世界的盡頭,在《歷史》中,他把世界想象為一片沒有邊界的平原。一代又一代旅行者在帆船上,在馬背上,記下所見所聞,成為人類正史的重要篇章;他們眼中攝入的世界圖景,數千年來一幅一幅拼湊,終于構成我們今日所見完整的地球畫面。
可如今,世界已變得和當初那個村莊一樣狹小,風景區擠滿游客,自拍神器將愚蠢的大頭貼在風光里,即時從異國他鄉傳來。在這個透明的時代,對于一個嚴肅的作家,旅游地理的文章要怎么寫?除了那些攻略,這類文章誰會認真看呢?
蕭春雷沉甸甸的三本書,證明我錯了。
春雷說:“地理,皆史也。”關于人和自然,陽光下,每座城市、每個村落,天天都有故事發生;燭火中,那些深邃的窗戶里,夜夜有秘密在醞釀。一代又一代,故事接續故事,秘密遮掩秘密,墳塋覆蓋墳塋,朝代淘汰朝代。哪條古道值得行走,哪座高山值得注目,月光和星光之下發生過什么,河流的上游下游、時間的過去現在有什么關系,這一切,永遠引人入勝,永遠訴說不完。
蕭春雷以古先知悲天憫人式的關注和思考,以箴言式的寫作風格,以優美典雅的文字,為我們講地理,講旅行,講歷史,講人和自然的故事,講得精彩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