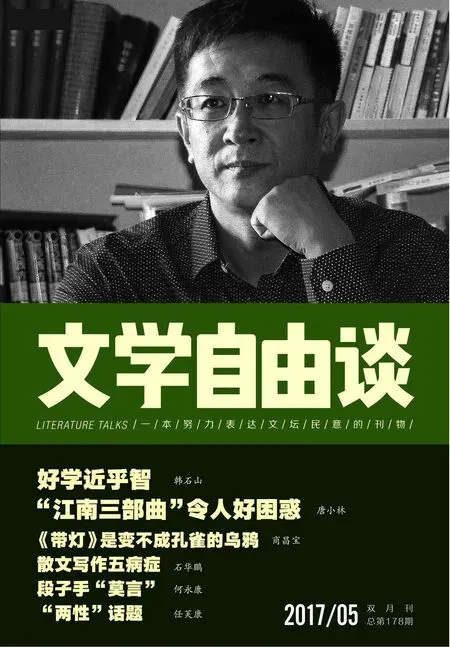《不成樣子的扯淡》自序(外一篇)
李建軍
《不成樣子的扯淡》自序(外一篇)
李建軍
我曾經(jīng)做過(guò)很多夢(mèng),卻從來(lái)沒(méi)有將成為當(dāng)代文學(xué)研究專家當(dāng)作自己的夢(mèng)想。我讀碩士和博士的專業(yè),都是文藝學(xué)。在我看來(lái),文藝學(xué)研究更自由,更有趣;它正像陸機(jī)在《文賦》中所說(shuō)的那樣,“課虛無(wú)以責(zé)有,叩寂寞而求音”,致力于對(duì)文學(xué)規(guī)律性問(wèn)題的把握,可以自由地介入任何一個(gè)文學(xué)研究領(lǐng)域,可以將所有文學(xué)現(xiàn)象當(dāng)作自己的研究對(duì)象。
中國(guó)當(dāng)代文學(xué)研究當(dāng)然很有趣,也很重要,卻是地位最低、最受歧視的學(xué)科。坊間流傳著這樣一個(gè)笑話,說(shuō)學(xué)術(shù)界存在著這樣一條“鄙視鏈”:研究文學(xué)理論的,看不起分段研究文學(xué)史的;研究外國(guó)文學(xué)的,看不起研究中國(guó)文學(xué)的;研究中國(guó)古代文學(xué)的,看不起研究中國(guó)現(xiàn)代文學(xué)的;研究中國(guó)現(xiàn)代文學(xué)的,看不起研究中國(guó)當(dāng)代文學(xué)的。還有人如此刻薄地表達(dá)過(guò)對(duì)中國(guó)當(dāng)代文學(xué)研究的鄙夷和不屑:“感冒無(wú)藥可治,所以世間的感冒藥最多;現(xiàn)當(dāng)代文學(xué)最沒(méi)有研究?jī)r(jià)值,所以研究現(xiàn)當(dāng)代文學(xué)的人最多。”
這樣的學(xué)科歧視,當(dāng)然是沒(méi)有道理的。事實(shí)上,當(dāng)代文學(xué)研究不僅很重要,而且難度也很大。因?yàn)椋?dāng)代文學(xué)研究的對(duì)象,是現(xiàn)在進(jìn)行時(shí)態(tài)的文學(xué)。研究當(dāng)代文學(xué)意味著巨大的閱讀量,意味著你必須關(guān)注古今中外的文學(xué)。就像上游的水不會(huì)受下游的水質(zhì)影響,而下游的水質(zhì)必然會(huì)受上游的水質(zhì)影響一樣,一個(gè)研究古代文學(xué)的人,完全可以不讀當(dāng)代作家的作品,但一個(gè)研究當(dāng)代文學(xué)的人,卻不能不讀古代文學(xué)作品。研究當(dāng)代文學(xué)的學(xué)者,倘不大量閱讀當(dāng)代作品,倘不熟悉古今中外的作家作品現(xiàn)象,那么,他就無(wú)法建構(gòu)起一個(gè)開(kāi)闊的比較視野,他的研究的深度和有效性,也就要大打折扣。
其實(shí),當(dāng)代文學(xué)研究的難度,還不在閱讀量之大,也不在關(guān)注面之廣,而在它要求研究者要有成熟的判斷能力和評(píng)價(jià)能力。對(duì)于那些已經(jīng)處于完成狀態(tài)的文學(xué)現(xiàn)象來(lái)講,一切都已定型,且有大量的信息和資料可作依憑,研究者無(wú)須面對(duì)一部作品,做“第一個(gè)吃螃蟹的人”;但是,處于生成過(guò)程的當(dāng)代文學(xué),卻面孔模糊,性質(zhì)不明,很難把握,研究這樣的新鮮的文學(xué)現(xiàn)象,既考驗(yàn)著研究者的趣味和鑒賞力,也考驗(yàn)著他的人格和德性。你要有過(guò)人的勇氣,要擺脫人情世故的纏繞。會(huì)呼吸的寫(xiě)作者,就站在你的對(duì)面。他們的像筆尖一樣銳利的眼睛,緊緊地盯著你的嘴巴,看你如何評(píng)價(jià)他的作品。一個(gè)時(shí)代的整體性的文化氛圍,消費(fèi)主義時(shí)代的市場(chǎng)邏輯,也微妙地影響著你的態(tài)度和感受,干擾著你對(duì)作品的基本判斷和最終評(píng)價(jià)。
我想要說(shuō)的,就是這樣一個(gè)事實(shí):當(dāng)代文學(xué)研究并不是輕松容易的“靜態(tài)研究”,而是艱難而復(fù)雜的動(dòng)態(tài)批評(píng)。它所面對(duì)的,不僅是作品,還有作者。在一個(gè)沖突性的對(duì)話情景里,求真的批評(píng)甚至就意味著對(duì)抗,意味著傷害,意味著冒天下之大不韙,意味著成為眾矢之的甚至“人民公敵”。
然而,很多時(shí)候,我們的當(dāng)代文學(xué)研究和文學(xué)批評(píng),卻是高度“和諧”的,是皆大歡喜的。研究者與被研究者之間,批評(píng)者與被批評(píng)者之間,處于一種異化性的“認(rèn)同關(guān)系”模式中。沒(méi)有不滿。沒(méi)有質(zhì)疑。沒(méi)有抗辯。沒(méi)有拒絕。在掌聲和鮮花構(gòu)成的喜氣洋洋的歡樂(lè)氛圍中,在文學(xué)“大獎(jiǎng)”的令人目眩的光環(huán)下面,那些備受推賞的當(dāng)代作家感覺(jué)良好,飄飄欲飛。他們只有“朋友”,沒(méi)有“敵人”,于是,他們也只有快樂(lè)和停滯,而沒(méi)有焦慮和進(jìn)步。他們?nèi)狈φ嬲墒於鴩?yán)肅的讀者,缺乏敢于質(zhì)疑和坦陳己見(jiàn)的對(duì)話者。他們成了一群幸福而又不幸的人,因?yàn)樗麄兩钤诒蝗巳捍負(fù)淼墓陋?dú)狀態(tài)里。
是的,由于種種復(fù)雜的原因,中國(guó)當(dāng)代文學(xué)仍然停留在不成熟的發(fā)展?fàn)顟B(tài),停留在對(duì)他者經(jīng)驗(yàn)的簡(jiǎn)單化的模仿階段。我們雖然努力擺脫了“三突出”之類的僵化模式——事實(shí)上,有的作家仍然在用這樣的方法寫(xiě)作,例如《大秦帝國(guó)》就屬于“三突出”模式的小說(shuō),但是,由于徹底否定自己民族的文學(xué)傳統(tǒng),我們時(shí)代的文學(xué)長(zhǎng)期處于“拔根狀態(tài)”。走出解凍狀態(tài),我們將目光轉(zhuǎn)向西方。我們懷著好奇而急切的心情模仿西方的現(xiàn)代主義文學(xué)。某些著名作家簡(jiǎn)直就是用漢語(yǔ)來(lái)寫(xiě)西方小說(shuō)。這樣的文學(xué)顯得既膚淺又虛假。中國(guó)文學(xué)期待自我意識(shí)的覺(jué)醒和自我個(gè)性的成熟。我們需要恢復(fù)漢語(yǔ)文學(xué)的尊嚴(yán),需要建構(gòu)“中國(guó)格調(diào)的大文學(xué)”。
我的文學(xué)批評(píng)理念,就建立在這樣的基本認(rèn)知和判斷上。我希望,我們的當(dāng)代作家能認(rèn)識(shí)到自己的局限和問(wèn)題;我希望,中國(guó)的當(dāng)代文學(xué)能自覺(jué)和成熟起來(lái)。關(guān)于文學(xué)批評(píng)的基本理念,關(guān)于文學(xué)批評(píng)在當(dāng)下的境遇,關(guān)于批評(píng)家的責(zé)任倫理,關(guān)于我與某些作家和批評(píng)家的“沖突”,許多年來(lái),我零零星星寫(xiě)過(guò)不少文章。
本來(lái),將這些文章裒為一集,老老實(shí)實(shí)地題名為《論文學(xué)批評(píng)》,是最為妥實(shí)的選擇。但是,透過(guò)表象來(lái)看,我的這些文章內(nèi)里,分明表達(dá)著對(duì)一種文學(xué)風(fēng)氣的不滿。這是一種在文學(xué)創(chuàng)作和文學(xué)批評(píng)上都并不鮮見(jiàn)的庸俗的文學(xué)風(fēng)氣。它體現(xiàn)著一種可怕的市儈哲學(xué),那就是“成功即一切”。在這樣的風(fēng)氣里,對(duì)利益的追求壓倒了對(duì)真理的熱愛(ài),市場(chǎng)的交換原則取代了真理的絕對(duì)原則。
是的,在當(dāng)下的多種樣態(tài)的文學(xué)性表達(dá)中,我們經(jīng)常會(huì)看到言不及義而又煞有介事的胡扯。這種用時(shí)髦的話語(yǔ)包裝起來(lái)的胡扯,就是美國(guó)學(xué)者法蘭克福所說(shuō)的“扯淡”(bullshit)。正像法蘭克福在《論扯淡》中所指出的那樣,“在我們的文化里,最突出的特征之一就是:有太多的人在‘扯淡’。”“扯淡”的典型特點(diǎn),就是不在意“真實(shí)”,只在意自己的“企圖”和“目的”。扯淡者幾乎都是法利賽人。對(duì)他們來(lái)講,當(dāng)下的現(xiàn)實(shí)利益高于一切,所以,他“不在乎自己說(shuō)的話是否正確地描述了事實(shí),他只挑選或編造符合他目的的話”。有必要指出的是,一切形式的扯淡,都意味著侮辱。它不僅侮辱人們的人格,也侮辱人們的智商;不僅侮辱聽(tīng)者和讀者,而且更加嚴(yán)重地侮辱言說(shuō)者。
為了表達(dá)自己對(duì)文學(xué)上的種種“扯淡”現(xiàn)象的不滿,為了引起大家對(duì)“扯淡”現(xiàn)象的警惕,我接受朋友的建議,索性將這本薄薄的小冊(cè)子題名為《不成樣子的扯淡》。如此命名,雖然略顯唐突,或貽“野哉”之譏,但是,循名責(zé)實(shí),似乎也還不失恰切。
我希望,這本小書(shū),能對(duì)讀者理解我們時(shí)代的文學(xué)批評(píng)和文學(xué)寫(xiě)作狀況,提供一點(diǎn)有價(jià)值的信息和微末的幫助。
(《不成樣子的扯淡》,將由廣東人民出版社出版)
是什么阻遏了陳忠實(shí)的“豹變”?
真正偉大的作家,幾乎無(wú)一例外,都是人類的盜火者。他們是普羅米修斯的精神之子。他們像丹柯一樣,舉著自己的燃燒的心,引導(dǎo)人們走出黑暗的森林,來(lái)到灑滿陽(yáng)光的大草原。
真正意義上的寫(xiě)作,仿佛漫長(zhǎng)而孤獨(dú)的夜行。無(wú)邊的黑暗包圍著你。沒(méi)有可以交談的旅伴。沒(méi)有可以休息的驛站。
你走在無(wú)邊的曠野上,走在沒(méi)有道路的荒原上。目的地到底有多遠(yuǎn)?不知道。何時(shí)可以到達(dá)?不知道。你唯一知道的,就是無(wú)論刮風(fēng)還是下雨,都不能停下來(lái),都得義無(wú)返顧地往前走。
倘若身處一個(gè)不正常的寫(xiě)作環(huán)境,你的文學(xué)之旅會(huì)更加艱辛,所感受到的痛苦還要更多,所要承受的壓力還要更大。除了旅途的孤獨(dú)和疲勞,你還要體驗(yàn)?zāi)擅麪畹目謶指泻徒箲]感的折磨。
恰似一只被幽囚的蟲(chóng)蛹,你被千絲萬(wàn)縷的線織進(jìn)厚厚的繭里。沒(méi)有人能幫助你。你要想獲得新生和自由,就只能靠自己,一點(diǎn)一點(diǎn),從內(nèi)部咬破那層殼,從黑暗里,破繭而出,來(lái)到一個(gè)可以看見(jiàn)陽(yáng)光的世界。
這是自己賦予自己生命的工作,一件艱難而偉大的工作。
只有擺脫這幽囚心靈的殼,你才能創(chuàng)造更好的自己和更好的作品。
在破繭而出的那一刻,你就變成一只美麗的蝴蝶。
人們管這叫“蝶變”。
也有人稱它為“蛻變”。
在《被禁錮的頭腦》中,切斯瓦夫·米沃什講述了一位波蘭詩(shī)人的困惑:“一位波蘭的民族詩(shī)人,描寫(xiě)了他在1824年作為沙俄的政治犯被押往東方的經(jīng)歷。他把俄羅斯精神比作蛹,他憂心忡忡地問(wèn)自己,當(dāng)自由的太陽(yáng)照臨時(shí),是什么昆蟲(chóng)將破繭而出:‘是鮮艷的蝴蝶飛臨大地,還是掉出一只黑夜骯臟的昆蟲(chóng)——飛蛾?’時(shí)至今日,沒(méi)有任何跡象可預(yù)卜這只蛹中會(huì)飛出歡快的蝴蝶。”(切斯瓦夫·米沃什:《被禁錮的頭腦》,廣西師范大學(xué)出版社,2013年版,第26頁(yè))
一個(gè)像俄羅斯這樣的前現(xiàn)代國(guó)家的未來(lái),的確撲朔迷離,很難預(yù)知,然而,一個(gè)不斷突破自我的作家精神上的蝶變,卻是可知的——他的精神的蟲(chóng)蛹,一定會(huì)變成一只美麗的蝴蝶。
子曰:“齊一變,至于魯;魯一變,至于道。”(《論語(yǔ)·雍也》)國(guó)家生活必須有一條上進(jìn)之路,有對(duì)“大道”境界的追求,而且,只有通過(guò)變革,一個(gè)國(guó)家才有可能日新又日新,漸臻文明境界。在司馬遷看來(lái),所謂“道”,即“變”之“道”;人類生活的發(fā)展和國(guó)家生活的變化,有著無(wú)可抗拒的規(guī)律,甚至有著數(shù)學(xué)般精確的時(shí)間節(jié)點(diǎn),就像他在《天官書(shū)》里所說(shuō)的那樣:“夫天運(yùn),三十歲一小變,百年中變,五百載大變;三大變一紀(jì),三紀(jì)而大備:此其大數(shù)也。為國(guó)者必貴三五。上下各千歲,然后天人之際續(xù)備。”(司馬遷:《史記》,中華書(shū)局,2006 年版,第 161 頁(yè))人類必須認(rèn)識(shí)這個(gè)“大道”和“天運(yùn)”,順應(yīng)這些規(guī)律和變化。
國(guó)家生活如此,個(gè)體生活亦然。對(duì)求道君子來(lái)講,個(gè)體人的生命體驗(yàn)和精神變化,似乎也有一個(gè)季節(jié)般井然有序的內(nèi)在規(guī)律。孔子在《論語(yǔ)·為政》里說(shuō):“吾十有五,而志于學(xué)。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仲尼根據(jù)自己的生命體驗(yàn)和人生經(jīng)驗(yàn),揭示了這樣一個(gè)普遍規(guī)律:“志于學(xué)”的人,每隔十年,便有一次明顯的心理變化和人格發(fā)展。
君子上達(dá),小人下達(dá)。真正的作家,都有一種努力使自己的精神生活更加高尚和美好的沖動(dòng)。
每一個(gè)偉大的作家,在自己的一生里,都要經(jīng)歷幾次精神上的蝶變。
蝶變意味著思想的成熟,也意味著寫(xiě)作經(jīng)驗(yàn)的成熟。
詩(shī)人的精神蝶變,具有很大的個(gè)體差異性,幾乎無(wú)規(guī)律可循。但是,小說(shuō)家的精神蝶變是有規(guī)律的,甚至還有一條“黃金律”——他們最大的精神蝶變,大都發(fā)生在孔子所說(shuō)的“不惑”和“知天命”兩個(gè)里程碑式的生命節(jié)點(diǎn)之間。
準(zhǔn)確地說(shuō),許多偉大的小說(shuō)作品,都是在作家44歲甚至50歲之后完成的。
愛(ài)倫堡在評(píng)價(jià)契訶夫的時(shí)候說(shuō):“安東巴甫洛維奇總共活了四十四歲,最后幾年,還是在重病之中,住在雅爾塔與世隔絕。(四十四歲時(shí)托爾斯泰還沒(méi)有開(kāi)始寫(xiě)《安娜·卡列尼娜》、陀思妥耶夫斯基正在寫(xiě)《罪與罰》、岡察洛夫還不是《奧勃洛摩夫》的作者。如果斯丹達(dá)爾四十四歲時(shí)便死去,那么他只會(huì)留下《阿爾芒斯》和幾篇論戰(zhàn)性的文章)。”(愛(ài)倫堡:《捍衛(wèi)人的價(jià)值》,遼寧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12頁(yè))契訶夫是這規(guī)則的例外,因?yàn)樗?4歲之前已經(jīng)寫(xiě)出了足以傳世的短篇小說(shuō)和戲劇作品。
但是,許多第一流的偉大作家,卻用自己的寫(xiě)作,證明著這規(guī)律的存在。
雨果最偉大的小說(shuō)《悲慘世界》完成于1862年,是年,他60歲;《九三年》完成于1872至1873年間,即作者70歲至71歲之間。
司湯達(dá)的《紅與黑》完成于1828—1829年間,也就是完成于作者45歲至46歲之間。
托爾斯泰藝術(shù)上最完美的作品《安娜·卡列尼娜》完成于1873-1877,也就是他45歲到49歲之間。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與罰》完成于1866年,是年,他45歲;《卡拉馬佐夫兄弟》完成于1878至1880年間,也就是他57至59歲之間。
岡察洛夫的《奧勃洛摩夫》完成于1859年,是年,他47歲。
由于19世紀(jì)的俄羅斯作家普遍早熟和短壽,所以,對(duì)他們來(lái)講,45歲的年紀(jì),就應(yīng)該算相當(dāng)成熟的年紀(jì)了。
這就是說(shuō),除了契訶夫等人少見(jiàn)的天才般的作家例外,許多偉大作家的經(jīng)典之作,都是在44歲以后寫(xiě)出來(lái)的,甚至就是50歲之后寫(xiě)出來(lái)的。
陳忠實(shí)的《白鹿原》寫(xiě)于1988至1992年之間,也就是他46至50歲之間,與上列偉大作家完成自己的經(jīng)典之作的年齡段,大體吻合。
最后,似乎可以得出這樣一個(gè)結(jié)論:詩(shī)人可以將“出名趁早”的話,當(dāng)作自己揚(yáng)名立萬(wàn)的勵(lì)志格言,小說(shuō)家則可以反其道而行之,無(wú)妨將“大器晚成”,當(dāng)作自己的座右銘。詩(shī)人需要充沛的青春激情,小說(shuō)家需要充分的人生經(jīng)驗(yàn),所以,優(yōu)秀的老年抒情詩(shī)人與優(yōu)秀的青年小說(shuō)家,就都比較少見(jiàn)。
陳忠實(shí)就經(jīng)歷過(guò)至少兩次精神蛻變和文學(xué)蝶變。第一次蝶變,發(fā)生在20世紀(jì)70年代末期,接近他的不惑之年;經(jīng)此一變,他漸漸認(rèn)識(shí)到了“本本”里的教條主義問(wèn)題,擺脫了“新八股文學(xué)”的窠臼,從而完成了從虛假的“概念化寫(xiě)作”和“公式化寫(xiě)作”,向貼近“生活體驗(yàn)”的轉(zhuǎn)化。從1985年到接近知天命之年的這段時(shí)間里,發(fā)生了第二次脫胎換骨的精神蝶變——他完成了從“生活體驗(yàn)”向“生命體驗(yàn)”的轉(zhuǎn)化,從而塑造了一群會(huì)呼吸的人物,敘述了他們的真實(shí)而苦難的人生,最終創(chuàng)造出一部悲壯而凄涼的民族秘史。
后來(lái),陳忠實(shí)曾經(jīng)用比喻性的語(yǔ)言,描述了自己獲得精神解放和心靈自由的體驗(yàn):“我后來(lái)在多種作品的閱讀中,往往很自然地能感知到所讀作品屬于生活體驗(yàn)或是生命體驗(yàn),發(fā)現(xiàn)前者是大量的,而能進(jìn)入生命體驗(yàn)層面的作品是一個(gè)不成比例的少數(shù)。我為這種差別找到一種喻體,生活體驗(yàn)如同蠶,而生命體驗(yàn)是破繭而出的蛾。蛾已經(jīng)羽化,獲得了飛翔的自由。然而這喻體也容易發(fā)生錯(cuò)覺(jué),蠶一般都會(huì)結(jié)繭成蛹再破繭而出成蛾,而由生活體驗(yàn)?zāi)苓M(jìn)入生命體驗(yàn)的作品卻少之又少。即使寫(xiě)出過(guò)生命體驗(yàn)作品的作家,也未必能保證此后的每一部小說(shuō),都能再進(jìn)入生命體驗(yàn)的層次。”(陳忠實(shí):《陳忠實(shí)文集》,第9卷,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1998年版,第61-62頁(yè))
陳忠實(shí)此處所說(shuō)的“生命體驗(yàn)”,其實(shí)就是人性體驗(yàn)、心靈體驗(yàn)和情感體驗(yàn),就是寫(xiě)出人的內(nèi)在體驗(yàn)的全部復(fù)雜性——他們的理想和欲望,他們的追求和掙扎,他們的絕望和無(wú)奈,他們的幻滅和毀滅。就此而言,所謂“生命體驗(yàn)”其實(shí)就是深刻意義上的“苦難體驗(yàn)”和“悲劇體驗(yàn)”。
《白鹿原》就是這樣一部偉大作品。它凝結(jié)著人物豐富的生命體驗(yàn)和深刻的悲劇體驗(yàn)。它所表現(xiàn)的,已經(jīng)不再是淺層次的生活體驗(yàn),而是深層次的生命體驗(yàn)和人性體驗(yàn)。這部長(zhǎng)篇小說(shuō)是一座名副其實(shí)的文學(xué)高峰。它給陳忠實(shí)帶來(lái)了巨大而不朽的光榮。如果不用更高的理想標(biāo)準(zhǔn)來(lái)要求的話,人們可以說(shuō),陳忠實(shí)已經(jīng)完成了自己的文學(xué)使命。
陳忠實(shí)本來(lái)是有可能寫(xiě)出新的厚重之作的。
他也有繼續(xù)創(chuàng)作長(zhǎng)篇小說(shuō)的抱負(fù)和計(jì)劃。
卵變而成蟲(chóng),蟲(chóng)變而成蛹,蛹化而成蝶。
蝶變之后,是更加艱難的豹變。
對(duì)作家來(lái)講,豹變是比蝶變更艱難的人格發(fā)展和自我超越。
陳忠實(shí)沒(méi)有完成精神上更徹底的“剝離”和文學(xué)上更徹底“豹變”。
不僅如此,他還從《白鹿原》的精神高度上,滑落了下來(lái)。
站在白鹿原下,他舉目四顧,茫茫然不知所向,慭慭然莫敢舒懷以命筆。
文學(xué)之外的攪擾,也讓他心神不寧。
文學(xué)體制內(nèi)部的耗散力,給他帶來(lái)了巨大的傷害。他是文學(xué)體制的受益者,也是受害者。
他的心里霧數(shù)極了。他稱那些讓他霧數(shù)的人和事為 “齷齪”。這是一些極不堪的人和事。陷此困境,他幾乎一籌莫展。他晚年的散文作品,記錄了他內(nèi)心的憤懣和痛苦。他甚至在新世紀(jì)所寫(xiě)的幾個(gè)短篇小說(shuō)里,反復(fù)表達(dá)“一位作家”被“齷齪”所羞辱的煩惱和郁結(jié)。
他的計(jì)劃中的長(zhǎng)篇小說(shuō)寫(xiě)作,就這樣被自己內(nèi)心的羈絆和外部的干擾,給阻滯和擱置了。
這是他自己的損失,也是中國(guó)文學(xué)的損失。
為了完整地理解陳忠實(shí)的寫(xiě)作歷程,理解他的并不舒展的晚年心境,并不理想的寫(xiě)作狀態(tài),我們有必要對(duì)他起步階段的寫(xiě)作和晚年的寫(xiě)作,進(jìn)行梳理和分析,最終回答這樣一些問(wèn)題:陳忠實(shí)的寫(xiě)作是如何起步的?如何完成文學(xué)上的過(guò)渡階段的?他是如何在“寧?kù)o”的狀態(tài)里寫(xiě)出《白鹿原》的?他的晚年寫(xiě)作為何沒(méi)有達(dá)到和超越《白鹿原》的高度?是什么阻遏了他由美麗的“蝶變”而達(dá)猛勇的“豹變”的精神升華?
研究陳忠實(shí)的艱難而非凡的創(chuàng)作經(jīng)驗(yàn),不僅有助于我們認(rèn)識(shí)他自己的創(chuàng)作歷程,而且也有助于我們認(rèn)識(shí)制約作家寫(xiě)作的種種復(fù)雜因素,有助于我們回答那些迫切而沉重的問(wèn)題。
(本文是《陳忠實(shí)的豹變》一書(shū)的引言,標(biāo)題為本刊所加。該書(shū)即將由二十一世紀(jì)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