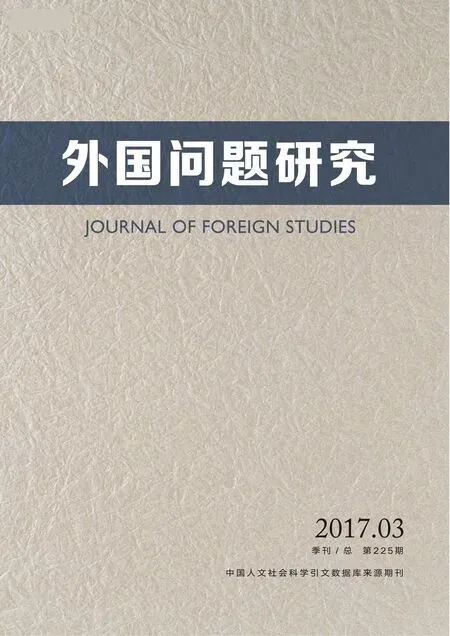“東亞協同體論”再考:“帝國話語”中的“近代”、“超近代”和“社會革命”
汪 力
(東北師范大學 歷史文化學院,吉林 長春130024)
“東亞協同體論”再考:“帝國話語”中的“近代”、“超近代”和“社會革命”
汪 力
(東北師范大學 歷史文化學院,吉林 長春130024)
近代日本在其擴張的過程中,形成了建構帝國統治秩序的話語體系。而中日戰爭中日本使中國迅速屈服企圖的失敗不僅體現了日本軍事上的局限,也表明日本帝國的話語秩序發生了危機。為了應對這一危機,“東亞協同體論”應運而生,三位代表性的“東亞協同體”論者分別從“近代”、“超近代”與“社會革命”的視角,嘗試修復帝國的話語秩序。然而這一努力最終未能克服帝國話語的困境。
東亞協同體論;帝國話語;蠟山政道;三木清;尾崎秀實
從1938年到1940年,隨著中日戰爭的長期化和日本政府的所謂“建設東亞新秩序”口號的提出,“東亞協同體論”的話題席卷了日本的學界與論壇。這種理論主張,以中日戰爭為契機,在東亞建設超越民族國家的、共同體的國際秩序。熱心鼓吹這種理論的,主要是屬于首相近衛文麿智囊團體“昭和研究會”里的所謂“革新”的知識分子。在戰后日本的思想史研究中,“東亞協同體論”起初被認為是企圖利用近衛政權控制軍部的中國侵略“危險的嘗試”,結果墮落為侵略中國的意識形態。*宮川透:《三木清》,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58年,第105—135頁。然而,到了1980年代,“東亞協同體論”卻因為其“理想主義的性格”受到肯定性的評價,被認為與近代日本外交思想中主流的以國家利益為中心的現實主義相比,具有批判性的意義。*高橋久志:《「東亜協同體論」——蝋山政道、尾崎秀実、加田哲二の場合》,三輪公忠編:《日本の一九三 年代——國の內と外から》,東京:創流社,1980年,第50—79頁。伊藤のぞみ:《昭和研究會における東亜協同體論の形成》,岡本幸治編:《近代日本のアジア観》,京都:ミネルヴァ書房,1988年,第227—248頁。接著,隨著后現代主義等各種“現代思想”在日本的流行,“東亞協同體論”又被積極評價為試圖克服帝國主義的國際秩序,同中國的民族主義“連帶”,試圖實現多元的地域秩序“后現代”、“后殖民”思想;*內田弘:《解説》,《三木清 東亜協同體論集》,東京:こぶし書房,2007年,第234—253頁。或者是在總體戰的條件下企圖實現激進的社會變革“革新思想”。*米谷匡史:《戦時期日本の社會思想——現代化と戦時変革》,《思想》 1997年第12期。米谷匡史:《解説》,《尾崎秀実評論集——日中戦爭期の東アジア》,東京:平凡社,2004年,第439—475頁。以及就蠟山政道而言,又反過來被認為是致力于實現東亞的“近代化”與社會經濟發展的,類似于美國戰后“近代化論”的開發不發達國家的思想。*酒井哲哉:《「東亜協同體」から:「近代化論」へ——蝋山政道における地域·開発·ナショナリズムの位相》,日本政治學會編:《日本外交におけるアジア主義》,東京:巖波書店,1999年,第109—128頁。
或許就日本國內的日本思想史研究而言,這種探尋過去思想“可能性”,從而加以繼承的研究姿態,某種意義上無可厚非。然而,雖說思想與現實總是相互乖離,這些見解似乎不能很好的說明,為什么偏偏在日本推進全面侵華戰爭的時候,這些“可能性”被日本的知識分子們熱心提倡。同時,在近年來中國的抗日戰爭史研究中,“東亞協同體論”被批判為企圖瓦解中國人民的抗日斗爭,為日本帝國主義侵略戰爭提供理論依據的侵略思想。*史桂芳:《日本侵華戰爭時期的“東亞協同體論”》,《歷史研究》 2015年第5期。如果“東亞協同體論”真的是所謂重視“他者”的“主體性”的思想,那么恐怕不能簡單地說這種批判僅僅是基于民族主義的“意識形態”批判。然而,本來近代日本的對外思想除了極少數的例外,多數都是主張侵略中國,或者維持在中國的帝國主義權益的思想,*楊棟梁:《近代以來日本的中國觀 第一卷 總論》,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頁。僅僅批判“東亞協同體論”是侵略思想,不能夠很好的說明何以“東亞協同體論”會在這一時期出現。
與其追問“東亞協同體論”是不是真的有所謂“理想主義”成分,不如思考為什么日本的知識人要在中日戰爭長期化的時刻談論這樣的“理想”。與其分析究竟“東亞協同體”能不能稱之為“后現代”或者“后殖民”的思想,不如分析何以日本為了主張建設以日本為中心的“東亞新秩序”,必須批判“近代”,主張所謂“近代的超克”。本文擬從“帝國話語”的視角,*關于“帝國話語”這一視角,劉禾的《帝國的話語政治》,楊立華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9年,從“符號”論的角度揭示了19世紀歐洲帝國主義支配亞洲的“話語秩序”。并聯系東亞國際形勢的變動,探究這一問題。
一、“帝國話語”的結構與危機
入江昭指出,近代日本外交的主流是“現實主義”的,它不是根據抽象的思想原理,而是依據對現實形勢的認識,不斷調整自己的行動。與之相對,在民間,“理想主義”的亞細亞主義外交思想很有影響力。*入江昭:《日本の外交》,東京:中央公論新社,1966年,第27—29頁。同時入江又指出,中日戰爭時期的“東亞新秩序”外交,意味著“明治以來僅僅以軍事、經濟面的具體政策為主軸的日本對外政策,在這里第一次擁有了自己的意識形態。”*入江昭:《日本の外交》,第133頁。
然而,中日戰爭以前的日本外交雖然常常被認為是“現實主義”的,但這并不意味著日本政府沒有將自己的對外政策加以正當化的話語。例如,明治時期日本政府侵略朝鮮的外交行動,一貫打著所謂“實現朝鮮的獨立與永久中立”和“維護東洋的和平”的旗號。如果主張“東亞新秩序”的侵華戰爭時期外交是“意識形態外交”的話,那么高唱“東洋和平”的明治政府侵略朝鮮的外交或許也可以稱之為“意識形態外交”。何況,作為外交行動目標的所謂“真實意圖”與將外交行為正當化的意識形態之間,有時未必有那么清晰的界限。*最近出現了從“東洋的和平”的視角為明治政府的朝鮮侵略外交辯護的研究,例如大澤博明:《朝鮮永世中立化構想と日本外交——日清戦爭前史》,井上壽一編:《日本の外交 第一巻 外交史 戦前編》,東京:巖波書店,2013年,第43—64頁。
從“帝國話語”的視角來看,如井上清所指出,在甲午戰爭、日俄戰爭時期,隨著日本帝國主義的形成,將其正當化的意識形態也形成了。*井上清:《日本帝國主義の形成》,東京:巖波書店,2001年,第149—169頁。然而,將日本的侵略擴張正當化的話語,不應只看作是在事后將外交策略和軍事行動正當化的意識形態,其本身也是日本建立起其對東亞的帝國主義統治的思想要素。這些話語塑造了日本政治家與知識人關于日本統治東亞的秩序思想,并通過教育機關與媒體,控制本國與殖民地的民眾,使得帝國的統治得以安定。在此基礎上,這些話語才能夠時刻為日本的軍事與外交行為提供意識形態的根據。離開這種話語秩序的背景討論個別外交言論究竟是不是所謂“帝國的真意”,意義有限。
隨著明治時代日本的擴張所形成的“帝國話語”,主要包含以下兩個側面:
一是所謂“脫亞論”話語。*如平山洋所指出(平山洋《福沢諭吉の真実》,文藝春秋、2004年),《脫亞論》在其發表時并未產生重大影響,戰后才被重新“發現”。這里使用“脫亞論”一詞并非指福澤諭吉的文章,而是指通過與西洋的同一化為侵略亞洲提供正當性的話語結構。這種話語聲稱日本通過“近代化”,已經成為“文明國”,在主張與西方列強的同一化的同時,用“前近代”、“野蠻”、“專制”等符號歧視其他東亞國家。關于這種歧視性話語的構造,韓東育指出,主要包括“以‘國民國家’取代‘華夷體系’的政治正義性”,“以‘近代文明’征服‘中世野蠻’的文明正當性”,“以‘資本經濟’改造‘自足經濟’的經貿優越性”三個方面。*韓東育:《東亞世界的“落差”與“權力”──從“華夷秩序”到“條約體系”》,《經濟社會史評論》 2016年第2期。其外交策略始終站在“現實主義”立場上,強調日本的“安全保障”的必要性,主張為此“不得不”侵略朝鮮與中國。同時通過參與西方列強所主導的國際法秩序,與列強的亞洲侵略相協調,參與列強分割東亞的競爭。*例如通過“文明與野蠻”話語所進行的正當化甲午戰爭的工作,參見大谷正《近代日本の対外宣伝》,東京:研文出版,2006年,第119—126頁。
二是所謂“亞細亞主義”話語。這是強調日本是“亞洲”國家,將自身與西方列強相區別,主張與亞洲各國“連帶”的話語。這種連帶的根據,第一是“亞洲”這一地域概念;第二是日本與朝鮮、中國等“東亞”國家間地理以及經濟上的“密切的關系”;第三是“同文同種”等有關日本與東亞各國間的歷史、文化的共同性的主張;第四是強調面對即將到來的西方列強“侵略亞洲”的威脅,亞洲各國有共同防御的必要;第五是東亞各國為了成為“文明國”,有必要接受日本的“指導援助”,等等。*關于“亞細亞”這一區域認識的多義性,參見山室信一《思想課題としてのアジア——基軸 連鎖 投企》,第一部:《アジア認識の基軸》,東京:巖波書店,2001年,第31—142頁。其外交策略主要是支援朝鮮、中國等東亞國家內部的“親日派”等勢力,通過干涉內政維持和擴大帝國權益,并向西方各國主張日本在東亞的所謂“特殊地位”。*例如關于甲午戰爭后日本民間的諸種“興亞”活動,參見孔祥吉、村田雄二郎:《罕為人知的中日結盟及其他》,巴蜀書社,2004年;狹間直樹:《日本早期的亞細亞主義》,張雯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7年。
這兩種話語乍看似乎是相互對立的,但事實上并非如此。首先,兩種話語都為正當化日本帝國主義的擴張和維護帝國的權益服務。其次,兩種話語在邏輯上相互補充。也就是說,當日本主張“脫亞論”,參加西方列強侵略中國的競爭的時候,同時會主張日本與東亞的“特殊關系”,強調日本獨自的利益。而當日本提倡“亞細亞主義”,要求與亞洲“連帶”的時候,會同時主張日本是亞洲唯一的“文明國”,主張日本的“指導的地位”。更進一步說,如坂野潤治所指出,在明治大正時期的日本同一論者會根據形勢變化交替主張“脫亞論”和“亞細亞主義”,在這兩種話語間的轉換不被同時代的人看作是所謂“思想轉向”。*坂野潤治:《近代日本とアジア——明治 思想の実像》,東京:筑摩書房,2013年。
這樣的話語秩序在日本的擴張和帝國統治的穩定上發揮了巨大的作用。然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日本蠻橫的“二十一條”外交引起了中國民族主義的昂揚,帝國的話語秩序開始出現破綻。大戰后,隨著國際秩序的變化和東亞地區所謂“華盛頓體系”的建立,帝國日本的話語也進行了調整。如“幣原外交”的理念所體現的,隨著國際聯盟等國際機構高唱“民族自決”與“國際正義”,日本也不得不應對中國民族主義的興起。“幣原外交”在以與歐美各國的“協調”為基本理念的同時,比起日本在華的政治、軍事利益,更重視經濟利益,奉行所謂“古典經濟自由主義”。*入江昭:《日本の外交》,第90—91頁。此外,幣原的所謂“不干涉內政”的理念,企圖通過與中國民族主義的妥協,滿足中國擺脫半殖民地地位的部分要求,來繼續維持帝國權益,特別是所謂“滿蒙權益”。從通過與歐美協調來維持帝國權益這一點來看,也可以看作是“脫亞論”思想的延長。*坂野潤治:《近代日本とアジア——明治 思想の実像》,第173頁。
盡管采取了這樣的轉換,進入昭和期,帝國的話語秩序仍然變得不安定了,到1930年代中期以后終于走向崩潰。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是所謂“協調外交”的崩潰。“幣原外交”中的“不干涉中國內政”話語,只在中國仍處于分裂狀態時有效,當中國的統一逐漸成為現實的時候就會陷入危機。為了鎮壓“滿洲”的中國民族主義運動和準備世界大戰,關東軍發動九·一八事變,建立了傀儡國家偽滿洲國。中國就此向國聯提出控訴,結果日本退出了國際聯盟。由此,日本外交不得不進行重大的方向轉換。此后,盡管日本采取種種手段試圖恢復與英美的協調,*關于所謂“危機中的協調外交”,參見井上壽一:《アジア主義を問いなおす》,第三章:《「東亜モンロー主義」外交とは何だったのか》,東京:筑摩書房,2006年,第87—129頁。不過,針對此點,小林啟治認為,“協調外交”這一概念不能僅僅認為是對英美協調,而是與否定侵略、國際正義等第一次世界大戰后的國際協調理念有關,“滿洲事變”后日本外交即使對個別國家采取“協調”政策,也不應理解為協調外交的繼續。見小林啓治:《二大政黨制の形成と協調外交の條件》,井上壽一編:《日本の外交 第一巻 外交史 戦前編》,第153—154頁。并成功維持了經濟上的貿易往來,但整體仍未能取得成功。關東軍為了正當化所謂“滿洲國”的存在,采用了“王道”等富于“亞細亞主義”色彩的意識形態。*山室信一:《キメラ——満洲國の肖像》,東京:中央公論新社,第108—118頁。這種意識形態轉換又反過來影響到日本國內,帝國話語整體上亞細亞主義的色彩大大增強。本來,近代日本必須不停的向西方表明自己并非“黃禍”而是“文明國”。亞細亞主義話語的主流化使得日本與西洋的同一化變得非常困難。
第二是近代中國統一國家的形成。國民革命后,盡管出現了中國民族主義浪潮的高漲,但政治上仍處于內戰等不安定狀態下。因此,日本仍然能將中國看作“前近代”的“野蠻”與“混亂”。然而,進入1930年代,以南京政府為中心的中國統一的趨勢日益明顯。從1935年起,中國共產黨也轉換了政策。1937年初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后中國的舉國一致態勢,給日本以很大的沖擊。以矢內原忠雄的《支那問題的所在》為首,一時間“支那統一化”成為日本言論界的流行話題。*關于“中國統一化論戰”,參見西村成雄:《日中戦爭前夜の中國分析——「再認識論」と「統一化論爭」》、岸本美緒編《巖波講座 帝國日本の學知 第三巻 東洋學の磁場》,東京:巖波書店,2006年,第294—332頁。有人甚至提出,與中國走向統一相反,日本的國策的統一性由于政府、軍部、政黨等多元行動主體的不統一走向崩潰。*山本実彥:《中國の近狀を報告す》,《改造》,1937年2月號,223頁。雖然如坂野潤治所指出,日本總是在中國的民族主義較為有力的時期主張“脫亞論”,*坂野潤治:《近代日本とアジア——明治 思想の実像》,第155頁。這也必須以事實上中國近代國家尚未形成為前提。不管國民政府實現的統一多么不充分,既然統一的近代國家已經形成,無論日本如何渲染“前近代的野蠻”都只能是自說自話。此外,“亞細亞主義”話語總是強調在中國近代國家形成過程中日本的“指導”的必要性。這一點也隨著在中國統一化的過程中,國家建設的樣板從模仿日本到參考蘇俄、德國等其他國家,走向多樣化而瓦解。*關于1930年代中國思想界流行的作為近代化的模范國的蘇聯形象,參見鄭大華、張英:《論蘇聯“一五計劃”對20世紀30年代初中國知識界的影響》,《世界歷史》 2009年第2期。關于德國的影響,參見柯偉林:《德國與中華民國》,陳謙平等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6年。
第三是馬克思主義在東亞的流行。在1930年代,作為“科學”的馬克思主義的影響力要遠遠超出實際的共產主義運動的范圍。雖然像大上末廣那樣,用馬克思主義的話語強調中國社會的“亞細亞的專制性”,鼓吹日本殖民統治的“進步性”也是可能的,*石堂清倫、野間清、野々村一雄、小林莊一:《十五年戦爭と満鉄調査部》,東京:原書房,1986年,第35—39頁。但是作為一種激進的革命思想,馬克思主義理論中的秩序意識非常的不穩定,“進步”與“反動”的關系不斷的發生變化。在資本主義制度走向終結這一時代認識的前提下,許多年輕的知識分子都認為,曾經“進步”的日本資本主義,如今已經變得“反動”,必將在不久的將來崩潰。此外,這一時期在日本的馬克思主義者間進行的“日本資本主義論戰”中,以山田盛太郎的《日本資本主義分析》為代表的“講座派”占據了優勢。《日本資本主義分析》一書認為,日本資本主義建立在“半封建”的土地制度的基礎上,以為軍備擴張而強行建立的軍事產業為中心,具有結構上的脆弱性,必然走向崩潰。*長岡新吉:《日本資本主義論爭の群像》,京都:ミネルヴァ書房,1984年,第170—172頁。隨著這樣的日本認識的傳播,“半封建”的日本要對中國主張自己“近代”與“資本主義”的優越性變得十分困難。
當話語的統治不安定的時候,作為日本帝國主義的“本能”,暴力的統治范圍就會擴大。偽滿洲國成立以后,日本進一步侵略華北,繼而在1937年發動全面侵華戰爭。如近衛文麿政權的聲明所顯示的,這場戰爭以保護“居留民的生命財產”,“膺懲支那軍的暴戾”為口號。*《盧溝橋事件に関する政府の聲明》(1937年8月15日),歴史學研究會編:《日本史史料5現代》,東京:巖波書店,1997年,第78—79頁。這種圍繞居留民的“人權”的話語,某種意義上也是“脫亞論”的延長。然而,盡管日軍在戰場上連續取得勝利,只要中國拒絕屈服,這種話語對于“收拾事變”就毫無意義。隨著日本政府否認國民政府的合法政府地位,一舉取消宣戰媾和問題,“事變”的“解決”變得更加遙遙無期。在這種尷尬處境之下,為了誘降國民政府,“收拾事變”,近衛政權轉換方針,提出建設“東亞新秩序”的口號,將侵華戰爭的目的重新設定為在東亞建立所謂“新秩序”。*《東亜新秩序政府聲明》(1938年11月3日)、歴史學研究會編:《日本史史料5現代》,東京:巖波書店,1997年,第82—83頁。“東亞協同體論”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之下登場的。
二、蠟山政道:“近代”的再編
盡管“東亞協同體論”并不是蠟山政道提出的,但“東亞協同體論”忽然成為日本學術思想界的中心話題,很大程度是由于蠟山的《東亞協同體的理論》一文的影響。蠟山也不無得意地說,自己“起到了陳勝、吳廣的作用”。*蝋山政道:《國民協同體の形成》,《改造》,1939年5月號,第9頁。通常認為,“東亞協同體論”的共通特征之一是對中國的民族主義有著一定程度的積極評價。*橋川文三:《東亜共同體の中國理念》,《橋川文三著作集》,第七巻,東京:筑摩書房,1986年,第240頁。然而,蠟山卻認為中國的民族主義“犯了雙重的錯誤”,對此進行了嚴厲的批判。他認為,中國民族主義的第一重錯誤是僅僅主張自己的民族主義,缺乏對東洋整體的認識;第二重錯誤是勾結西方帝國主義勢力,與日本對抗。*蝋山政道:《東亜協同體の理論》,《改造》,1938年11月號,第13頁。
那么,蠟山何以對中國的民族主義采取如此嚴厲的批判立場?要理解這一點,不能僅僅只看中日全面戰爭時期蠟山的言論,需要從蠟山長期以來的國際政治思想來考察。
作為日本的國際政治學研究的重要開拓者,蠟山政道終其一生都對國際秩序問題保持著高度的關心。然而,需要注意的是,蠟山的許多論著都討論了中日關系和東亞國際秩序的問題,但其視角大多并非以日本與中國的關系為中心,而是始終注目日本與美國,以及日本與美國所主導的國際機構的關系問題。
早在1928年,蠟山就已經指出,在日本與美國的關系中,比起日美兩國間的問題,圍繞中國的矛盾要深刻得多。*蝋山政道:《國際政治と國際行政》,東京:厳松堂書店,1928年,第181頁。九·一八事變以后,蠟山在擁護日本在中國東北的所謂“特殊權益”,為關東軍的行動辯護的同時,又反對日本退出國際聯盟,認為擁護“滿洲國”與維護日本在國聯的地位可以并行不悖。*蝋山政道:《満洲事変と國際連盟》,《世界の変局と日本の世界政策》,東京:厳松堂,1938年,第21—31頁。與他的主張相反,日本退出國聯,輿論界開始煽動所謂“自主外交”。對此蠟山進行了批判。他指出,盡管中國的民族主義勢力期待國際聯盟、英美和蘇聯的介入,然而這些勢力之間互相對立,不可能統一對抗日本。日本只要與英美保持個別的協調,同時利用中國內部的分裂,就能同時實現帝國統治的安定和與國際秩序的協調。*蝋山政道:《連盟脫退と今後の國際外交》,《世界の変局と日本の世界政策》,東京:厳松堂,1938年,第37—45頁。此外,蠟山還指出,盡管蘇聯的外交非常“自主”,但絕非像日本的“自主外交”論者那樣僅僅主張本國的利益,而是與國聯積極交涉,將本國的利益包裝成人類普遍的利益來主張。蠟山認為這是20世紀新的外交技術,日本應當學習。*蝋山政道:《破綻せる國際機構の再検討》,《世界の変局と日本の世界政策》,東京:厳松堂,1938年,第57—60頁。
1935年蠟山政道的訪美,對于他的“東亞新秩序”構想的形成有著極為重要的意義。后來他在其“東亞新秩序”論集《東亞與世界》的序言中回想,自己的“東亞新秩序”思想是在訪問美國的過程中為了對抗美國人對日本的東亞政策的種種批判而形成的。*蝋山政道:《東亜と世界──新秩序への論策》,東京:改造社,1941年,“序”第1頁。蠟山在訪問的感想中,一方面批判美國人對自己所主張的國際聯盟和華盛頓體制等普遍的秩序的執著,另一方面又認為,美國的根本思想是所謂“實用主義”,美國人所信奉的普遍的理念可以因為實際的需要而修正。為了經濟復興等客觀的需要,美國有與日本妥協的可能。由此蠟山關注羅斯福政權對東亞局勢的所謂“靜觀”政策。*蝋山政道:《危機の視點より観たる日米関係》,《世界の変局と日本の世界政策》,東京:厳松堂,1938年,第108—113頁。
中日全面戰爭爆發以后,蠟山從近代日本在東亞的擴張與英美主導的世界秩序的關系的角度,對戰爭的歷史原因進行了探討。他指出,當近代日本想要超出英美所設定的國際秩序,進行獨自的擴張時,必須要有擴張對象以外的“第三國”的威脅的存在。實際的戰爭對手,在以朝鮮為侵略對象的時候是清朝,而在以中國為侵略對象的時候是俄國。通過這種與第三國的戰爭,日本得以在擴大帝國版圖的同時維持與英美的合作關系。然而,由于辛亥革命和俄國革命,俄國一時間退出了東亞的霸權爭奪,而中國陷入分裂狀態。從而使得日本無法再主張自己獨自的要求,只好追隨英美所設定的國際秩序。此后,蘇聯成功進行了社會主義建設,而中國通過國民革命展開了再統一運動,重新回到國際舞臺,這樣日本獨自的權益開始動搖。同時,由于英美對于國民政府的統一運動采取樂見其成的態度,導致“滿洲事變”的發生,“協調外交”崩潰。也就是說,近代日本的擴張總是需要與中國或者俄國等“第三國”的對抗和與英美主導的國際秩序的協調這“兩重性”的條件。當這種“雙重條件”不能維持的時候,帝國的統治秩序就會出現困難。蠟山認為,為了克服這種困境,日本需要建立由自己主導的“自律的軸心”。*蝋山政道:《支那事変の背景と東亜政局の安定點》,《世界の変局と日本の世界政策》,東京:厳松堂,1938年,第185—192頁。
至于蠟山這個時期具體構想了怎樣的“自律的軸心”,有必要注意他提出了其獨特的“開發”思想。蠟山在論及統治華北的原理的時候,一方面批評三民主義中最重要的理念“民族”不過是19世紀的舊觀念,由于其“感情”的支配,國民政府才“墮落”到共產黨的人民戰線戰略中;另一方面,蠟山又主張,為了防止華北出現“思想真空”導致共產主義乘虛而入,應當將三民主義以“民生”為核心進行重組,成為“民生、民權、民族”的順序,再加以利用。*蝋山政道:《北支政治工作の文化的基礎》,《世界の変局と日本の世界政策》,東京:厳松堂,1938年,第211—214頁。蠟山又認為,圍繞怎樣開發中國,有三條相對立的路線,即英國所支持的國民政府的開發,日本主導的“滿洲國”式開發,中國共產黨所主張的蘇聯式開發。他斷言,國民政府的開發不僅是從屬于英美帝國主義的半殖民地式開發,而且其范圍僅僅局限于一部分的城市,廣大農村仍處于完全未開發的狀態;共產黨所提倡的蘇聯式開發雖然不乏將來的可能性,但是既然中共已經選擇與國民政府合流,就失去了其獨自的意義。至于日本主導的“滿洲國”式開發,蠟山聲稱,這種開發主要出于政治軍事方面的目的,因此與從資本的邏輯出發的帝國主義的開發有著根本不同;然而,至于其具體的政策,蠟山批判說,由于過度依賴政府機關以及財閥等特權資本,日本總是推行自以為是的教條的開發政策,被中國人“誤解”為帝國主義也是無可奈何。他主張有必要動員更多的民間資本和文化團體,給日本式開發增添活力。*蝋山政道:《支那開発の國際相克線》,《世界の変局と日本の世界政策》,東京:厳松堂,1938年,第224—235頁。
眾所周知,1938年,恰好在武漢陷落和近衛政權的“東亞新秩序聲明”之前不久,蠟山發表了著名的《東亞協同體的理論》一文,其中將中日戰爭的意義規定為“東洋的覺醒”,認為國際聯盟和九國公約等歐美主導的東亞秩序發生破綻,體現“東洋的統一”的東亞區域秩序成為現實。蠟山又認為,像岡倉天心的《東洋的理想》那樣的感性的表達東洋意識是完全不夠的,何況東亞其實并不存在統一的文化,比起文化的統一,在日本的指導下推進協同體式的經濟開發更為重要。他主張,與這種開發相結合而建立的新的中國政治體制,應該是地方的自治政府與中央的聯邦政府相統一的雙重體制。*蝋山政道:《東亜協同體の理論》,《改造》,1938年11月號,第6—27頁。
這些主張對于世界秩序的意義,到歐洲大戰爆發之后,蠟山才在《世界新秩序的展望》一文中進行了清晰的表述。這里,蠟山首先再次強調,中日戰爭的根本原因在于日本在東亞的特殊地位與英美所主導的普遍的國際秩序間的矛盾。繼而他指出,這次歐洲大戰的原因與此也有相似之處。本來東歐的民族構成十分復雜,民族主義很不發達。盡管德國和俄國在這個地區有著各自的特殊地位,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德國的敗北和俄國革命的影響,兩國都從東歐暫時撤退。于是,英法等帝國主義國家將并不適用于該區域的民族主義的原理強行灌輸到這一地區,建立起眾多小國,從而無視了德國和俄國客觀的生存需要。所以,蠟山主張,日本的“東亞新秩序”問題并不是日本的特殊問題,而是世界史規模的秩序變革的一環。*蝋山政道:《世界新秩序の展望──東亜協同體を序曲として》,《改造》,1939年11月號,第4—19頁。
然而,必須指出,這一宏偉的世界秩序變革的目的,不外乎尋求與美國所主導的世界秩序的妥協。蠟山主張,盡管日本所提倡的“東亞新秩序”與《九國公約》矛盾,但事實上日本政府并不敵視美國,始終希望美國能夠認清東亞的“現實”,邀請美國商討《九國條約》的修改問題。修改的基準,首先當然是承認日本在東亞的“特殊地位”,其次是共同“援助”中國的近代化。*蝋山政道:《世界新秩序の展望──東亜協同體を序曲として》,《改造》,1939年11月號,第19—24頁。也就是說蠟山的開發論并不是封閉的,相反,可以說是對英美開放的,對其“門戶開放”的要求采取妥協的態度。反過來也可以說,蠟山是為了與美國主導的國際秩序協調,使美國承認日本在東亞的所謂“特殊地位”,才主張這樣的開發論。
對美國,蠟山的“東亞協同體論”與其說是要超越美國主導的世界秩序,建立“亞細亞主義”的東亞秩序,還不如說是為了與美國的世界秩序妥協,才需要制造日本獨有的“世界秩序原理”。同時,在中國終于艱難的實現以軍事動員體制為中心的民族國家這一曾經是日本所提倡的“近代”時,蠟山卻將其批判為過時的十九世紀的殘余,或者是依附于英美帝國主義的似是而非的“近代”,而主張只有日本所主導的東亞的協同體式的開發才是真正應當追求的“近代”。也就是說,從日本帝國主義的話語構造來看,這不過是為了修復由于與西方同一化的困難和中國統一近代國家的形成而帶來的帝國話語秩序破綻。在這個意義上,蠟山政道的“東亞協同體論”可以說是帝國話語中“近代”的再編。
三、三木清:“近代的超克”的形成
在與“東亞協同體論”有關的知識分子中,三木清引起了眾多研究者的注意。他作為當時日本最具代表性的哲學家,積極提倡“東亞協同體論”,并擔任了昭和研究會關于“東亞協同體論”的報告書《新日本的思想原理》的起草工作。他的“東亞協同體論”,最后主張解決“資本主義的問題”,開拓世界史的新階段,可謂開創了太平洋戰爭下的“近代的超克論”的先河。*三木清在“近代的超克”思潮中的位置,參見廣松渉《〈近代の超克〉論》第六章:《三木清の「時務の論理」と隘路》,東京:講談社,1989年,第126—155頁。然而,本來三木清是“西洋”與“近代”的傾向很強的知識分子,對東亞的國際秩序問題并不關心。如果三木作為一位嚴肅的哲學家,并非只是隨著時局任意的轉換立場,那么他何以走向這樣的“東亞協同體論”,就有加以考察的必要。
盡管在20年代三木一度接近馬克思主義,在中日全面戰爭前夜,他已經開始與馬克思主義保持一定的距離,并對蘇聯的現實采取批判的態度。不過,他并沒有因此轉向國家社會主義等右翼的“改造”思想和民族主義,而是堅持進步立場,探索抵抗法西斯主義的統一戰線。*三木清:《自由主義の將來性》,《三木清全集》第十五巻,東京:巖波書店,1967年,第16—18頁。作為哲學家,三木并非討論具體的政治問題,而是通過討論“文化”問題表達自己的政治見解。他批判當時流行的將日本主義思想與法西斯主義相結合的現象,指出這種排外主義的日本主義盡管大聲主張所謂“日本的東西”,實際上卻無法說清究竟什么是“日本”的;雖然激烈排斥西方文化,卻利用德國的全體主義哲學為自己辯護。三木認為,這種法西斯主義之所以能夠主張日本“全體主義”的特質,不過是由于日本社會還遺留有很多“封建殘余”而已。真正的“日本精神”絕非抱殘守缺、故步自封,而是不斷吸收中國、印度、西方的先進文化來發展自己。現在被說成屬于“西方”的很多東西其實并不是西方所特有,而是如近代科學等具有普遍性的近代文化。所以,現代的日本文化也不應該封閉自己,而應當在保持民族的主體性的同時,將西方文化“身體化”,使之真正成為自己的一部分。這樣做的結果,將能夠形成一種新的“人道主義”。*三木清:《日本的性格とファシズム》,《三木清全集》第十三巻,東京:巖波書店,1967年,第241—267頁。這就是三木所構想的抵抗法西斯主義的邏輯。
從這種追尋普遍性的立場出發,三木開始注意到日本帝國主義結構中帝國話語秩序的破綻。之所以如此,是因為三木認為,這種破綻正是他所指出的日本主義的局限性的表現。在1935年中日兩國圍繞華北事變的紛爭中,三木提出了如下見解。日本在推動華北分離時打出了“共同防止赤化”的旗號,然而“赤化”也就是共產主義的問題首先是一個思想問題。在日本,可以用“日本精神”來鎮壓共產主義,但在中國宣傳“日本精神”毫無意義。如果不用思想而企圖用暴力來解決這個問題,那么就會得出日本必須用暴力征服全世界,以根絕“赤化”的荒謬結論。因此,為了“日支親善”,日本不能在中國宣傳“日本的東西”,而必須向西方傳播近代文化那樣,主張具有普遍性的意識形態。*三木清:《日支思想問題》,《三木清全集》第十五巻,東京:巖波書店,1967年,第28—35頁。
1937年,中日全面戰爭爆發。三木將其看作獲得他所主張的普遍的思想的良機。三木認為,日本人雖然以“日支親善”為戰爭目的,卻沒有有效的方法讓中國人理解這一點。中國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激烈抵抗,證明了日本人在“思想戰”中的失敗。這種失敗表明了“日本精神”的局限性。日本有“日本精神”,中國也有“支那精神”,主張“日本精神”是不可能說服中國人的。為了“日支親善”,日本必須主張具有“世界的妥當性”的思想。*三木清:《日本の現実》,《三木清全集》第十三巻,東京:巖波書店,1967年,第438—443頁。
從這種“普遍”的視點出發,三木就必須將中國認識為“他者”。因為如果中國和日本是同質的,那么日本主張“日本精神”也能夠統治中國,沒有尋求“普遍性”的思想的必要。因此,三木對于傳統的“同文同種”等亞細亞主義話語持批判的態度。他指出,實際上日中兩國人種不同,雖然同樣使用漢字,其含義卻完全不同,以“同文同種”為根據主張“日支親善”是沒有說服力的。本來,專門研究“哲學”這一西方學術的三木對于中國思想等“東洋”的學術興趣有限,這一時期卻開始關心思想界流行的一些中國研究,特別是津田左右吉的中國思想論對他啟發很大。津田認為,雖然古代中國向日本傳播了許多文化,但這些基本上只影響了一部分貴族,對于一般民眾幾乎毫無影響。日本的歷史文化是獨立發展的,并未和中國形成一個“東洋”世界。三木在對津田這一區別中國文化與日本文化的邏輯表示贊賞的同時,又認為不應完全否定“東洋一體”。也就是說,“東洋一體”的實現,不是依據“共同的傳統文化”等文化史上的關系,而是只有通過創造新的具有普遍性的文化才有可能。從這一觀點出發,三木指出,津田對佛教的影響力評價過低,佛教之所以能對中國和日本以及整個亞洲發生巨大的影響,就是因為它所具有的普遍性。*三木清:《日本の現実》,《三木清全集》第十三巻,第446—457頁。
從這種視角出發,三木認為,中國歷史倒可以給現在的日本提供不少啟示。在中國漫長的歷史中,最具世界性文化影響力的是唐代。然而這并不是因為唐的國力比明或者清要強,而是因為魏晉南北朝期代多民族文化的融合,以及對印度文化等外來文化的吸收,最終形成了一個具有普遍性的文化。此外,日本能實現其獨自的歷史發展,也是因為文化上不僅不排外,還總是吸收外來先進文化來發展自身的文化。這也是日本的近代化能夠成功的原因。三木主張,今天的日本文化也不應采取自我封閉的態度,而應該努力吸收西方的先進文化,創造具有普遍性的文化來實現“東洋的統一”,從而為世界的統一作出貢獻。*三木清:《文化の力》,《三木清全集》第十四巻,東京:巖波書店,1967年,第318—335頁。
出于這種對“他者”的認識的視角,三木對蠟山政道那種否定中國民族主義的價值的觀點進行了批判。三木指出,中國的民族主義是伴隨著中國向近代國家的轉變所必然出現的事物,具有客觀的進步意義,而且并非與建構“東亞協同體”矛盾,相反正是它的前提。日本應該接受中國近代國家的形成,如果要對中國的民族主義加以限制,也不能從日本民族主義的立場出發,而必須從世界的普遍性的立場出發,這時日本的民族主義也應當受到同樣的限制。*三木清:《東亜思想の根據》,《三木清全集》第十五巻,東京:巖波書店,1967年,第311—312頁。
由于三木把侵略中國的戰爭看作獲得“普遍性”的契機,他就不得不站在肯定戰時“日本的現實”的立場上。這里他提出了“歷史的理性”的思想。三木引用黑格爾的歷史哲學,指出歷史并非通過道德的善或者主觀的普遍的目的前進,相反通過私利私欲等“惡”來實現歷史的普遍性。這就是黑格爾所說的“理性的狡計”。然而,三木并不以黑格爾的邏輯為滿足,因為這種邏輯把人看成了歷史的道具,不符合三木的人道主義思想。為了解決這一矛盾,三木計劃通過“技術”來統一主觀與客觀、歷史與主體、情念(pathos)與理性(logos),這就是他所謂“構想力的邏輯”,最終成為三木晚年宏大的哲學冒險。*三木清:《歴史の理性》,《三木清全集》第十四巻,東京:巖波書店,1967年,第249—260頁。此外,三木號召,日本的知識分子應該更有自信,因為現在日本的問題離開知識分子的作用是無法解決的;同時,知識分子也應該更加積極的關心現實。日本所面對的現實過于重大,不允許任何人置身事外。知識分子不應揣測懷疑日本的戰爭動機,采取消極的不合作態度,而應該從“歷史的理性”的立場重視其歷史意義。三木還聲稱,如果無法發現這樣的歷史意義,就只有自己“賦予”它一個新的意義。*三木清:《知識階級に與ふ》,《三木清全集》第十五巻,東京:巖波書店,1967年,第239—242頁。
從這種肯定現實的立場出發,三木終于進一步對他本來的抵抗對象法西斯主義,也采取了積極包攝的態度。三木認為,近代的自由主義的知性過于抽象,對于身體和歷史等具體性缺乏理解,而另一方面民族的協同體的思想與之相反,在理性和開放的態度上有所欠缺。所以,新的知性應該建立在利益社會(Gesellschaft)和共同體(Gemeinschaft)的辯證統一的基礎上。這樣產生的新的“全體主義”,才有可能成為指導“世界革新”的普遍性。*三木清:《知性の改造》,《三木清全集》第十四巻,東京:巖波書店,1967年,第191—216頁。三木主張,這種“世界史的”理念的目標是“確立超越自由主義、共產主義、全體主義的新的思想原理”,*三木清:《世界の危機と日本の立場》,《三木清全集》第十五巻,東京:巖波書店,1967年,第387頁。從而解決資本主義問題這一二十世紀最大的世界史課題,“東亞協同體”正是實現這一世界史的普遍性的途徑。*三木清:《現代日本に於ける世界史の意義》,《三木清全集》第十四巻,東京:巖波書店,1967年,第149頁。
中日戰爭前夜的三木雖然已經告別馬克思主義,但仍在努力探索抵抗法西斯主義的普遍性。他從而發現了日本帝國主義的話語秩序的破綻,將其視為獲得普遍性的契機。由此他發現了中國這一“他者”,并高度評價中國民族主義的歷史意義。然而,由此三木也給侵略戰爭賦予積極的意義,并呼吁知識分子積極參與侵略戰爭。這在某種意義上也是一種修復帝國的話語秩序的努力。進一步,由于三木參與帝國話語秩序的建構,法西斯主義就從他抵抗的對象變成了“辯證法的揚棄”的對象。最終三木所構想的世界史的普遍性,是一種通過“東洋的統一”來解決資本主義問題的一種“近代的超克”的邏輯。如果“近代的超克”可以看作是日本主義的一個頂點,那么三木就從對抗日本主義的立場出發,通過參與帝國的話語秩序的建構,最終為最為極端的日本主義的出現打開了道路。
四、尾崎秀實:“民族問題”與“社會革命”
與蠟山政道和三木清不同,“東亞協同體論”的另一位參與者尾崎秀實從自己的在中國的體驗出發,一貫關注中國問題,并從馬克思主義的立場,發表了大量獨特的評論。尾崎在他眾多的評論文章中,最關注的始終是現代中國的“民族問題”。這一點也體現在尾崎有關“東亞協同體論”的評論中,他說:“與民族問題相比,‘東亞協同體論’應該認識到自己是怎樣可憐和微不足道。”*尾崎秀実:《東亜協同體の理念とその成立の客観的基礎》,《中央公論》,1939年1日號,第13頁。然而。與此同時,尾崎又對當時推行統一和抗戰的國民政府,始終采取十分批判的態度。
從尾崎同情中國共產黨的立場來說,這種態度某種意義上理所當然。不過,為了從理論上理解尾崎的立場,我們有必要具體的分析尾崎所謂“民族問題”的意義。“民族問題”一詞聽起來十分模糊,可能會被理解為少數民族權益或者一般的民族獨立問題。但就共產主義者尾崎而言,其“民族問題”的概念與馬克思列寧主義或者說共產國際的世界革命思想有關。列寧在20世紀初俄國馬克思主義者圍繞俄國革命中的民族問題的論戰中,形成了其“民族自決”的思想。他堅決擁護俄國與東歐少數民族的民族自決權利,但認為“民族主義”基本是資產階級的歷史課題,無產階級沒有積極加以主張的必要,并反對崩得等團體“民族文化自治”的口號。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后,列寧深入研究帝國主義問題的結果,開始重視殖民地解放的問題,提出了“帝國主義與民族”這一20世紀的根本課題。俄國革命后,隨著歐洲革命的退潮,共產國際形成了重視殖民地半殖民地解放斗爭的世界革命戰略。這一戰略在主張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運動具有歷史進步意義,無產階級應當參與的同時,又認為在資本主義制度走向滅亡的帝國主義時代,民族資產階級不可能徹底解決民族解放問題,總是想與封建勢力和帝國主義妥協。所以能夠徹底完成民族解放任務的只有無產階級及其先鋒隊政黨,無產階級應該在支援資產階級左派的同時奪取民族解放運動的領導權。*參見太田仁樹:《レーニンにおける資本主義と民族問題》,《岡山大學経済學會雑誌》,第19卷3、4號。
從這一理論的前提出發尾崎的邏輯就變得十分清晰。在他看來,既然國民政府是民族資產階級右翼的政權,就必然會向地主階級和帝國主義妥協,不可能根本解決“民族問題”。尾崎在接到西安事變的新聞當天寫下的,預言了蔣介石的存活的《張學良政變的意義》一文,向來得到高度評價,被認為依據深刻的科學的分析對事情的發展作出了正確的預測,成為“尾崎秀實傳說”的一部分,*米谷匡史:《解説》,《尾崎秀実時評集》,第453—454頁。然而事實上這篇文章的內在邏輯并不一貫,在指出國民政府的統一得到廣泛的支持,作為統一的象征的蔣介石不會被殺害的同時,又認為這種統一不過是表面文章,并未根本改變社會結構,這種“統一”越進展中國社會依附于英美帝國主義的半殖民地化越加深,西安事變不過是這種“統一”的矛盾的體現而已。*尾崎秀実:《張學良クーデターの意義——支那社會の內部的矛盾の爆発》,《中央公論》,1937年1月號,第406—414頁。此外在“中國統一化論戰”中,尾崎激烈的批判支持國民政府統一中國的矢內原忠雄,分析了國民政府主導的產業開發如何與英美等“國際資本”相勾結,從而完全沒有資本主義發展的前景,對矢內原的論敵大上末廣表示了支持。*尾崎秀実:《支那の産業開発と國際資本》,《尾崎秀実著作集》第一巻,東京:勁草書房,1977年,第131—135頁。更進一步,在中日全面戰爭走向擴大化之際,尾崎又分析了國民政府的軍閥本質及其與財閥、列強的關系,對國民政府進行了激烈批判。*尾崎秀実:《南京政府論》,《中央公論》,1937年9月號,第23—36頁。
雖然尾崎如此激烈的批判國民政府,但這絕不意味著尾崎對中國的民族主義評價不高。也就是說從尾崎的邏輯來看,中國民族主義的本質是世界史的帝國主義時代的反帝民族主義,其根本的力量源泉不在于國民政府,而在于人民大眾。國民政府并非中國民族主義的真正的代表,不過是部分的利用這種巨大的能量,勉強維持外觀上的“統一”而已。所以尾崎始終關注中國的“民族運動”,并將中國共產黨看作領導革命的民族主義的核心力量。共產黨雖然現在受到國民黨的“圍剿”,勢力受到很大打擊,但由于其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轉換,又獲得了集結民族運動的能量的良機。隨著這一政策轉換成為現實,國民黨的本質的變化也就是再次左翼化也不是絕對不可能的。*尾崎秀実:《南京政府と中國共産黨》,《尾崎秀実著作集》第一巻,東京:勁草書房,1977年,第213—214頁。隨著戰爭的進行,尾崎還認為,國民政府如此激烈抵抗的原因不在于其民族主義的意識形態,而是為了集中在上海、南京一帶的英美帝國主義的利益。國民政府由于其內在的脆弱性,有可能尋求與日本妥協,以便再次鎮壓共產黨。但在這種情況下,日本所期待的“和平”也不可能實現,中國人民必然會拋棄蔣介石,集結在以中國共產黨為核心的抗日勢力的旗幟之下。*尾崎秀実:《蔣介石よどこへ行く》,《尾崎秀実著作集》第二巻,東京:勁草書房,1977年,第302—303頁。尾崎的“‘支那’赤化的趨勢大體上是沒有問題的”*尾崎秀実:《支那は果して赤化するか》,《尾崎秀実著作集》第一巻,東京:勁草書房,1977年,第197頁。這一命運般的斷言,應當從這樣的邏輯來理解。
在尾崎看來,即便日本帝國主義能打倒國民政府,也不可能戰勝這一巨大的革命的民族主義的力量。然而,如果說這是否意味著尾崎認為日本絕對不可能“解決”中國的“民族問題”,從而“收拾”“支那事變”的話,則又并非如此。尾崎參與近衛內閣和昭和研究會,并參與“東亞協同體論”的討論,一方面固然出于黨的情報工作的需要,同時也是因為他從中看到他所期待的中日戰爭“大乘的解決”的可能性。他比任何人都要強調“東亞協同體”中的“民族問題”,與其說是為了討論如何應對中國的抗日運動,不如說是期待著日本的“革新”也就是社會主義的變革。*尾崎秀実:《東亜協同體の理念とその成立の客観的基礎》,《中央公論》,1939年1月號,第17—18頁。如果日本能夠變革資本主義體制,實現社會主義的“革新”,當然中國也能隨之順利掙脫殖民地、半殖民地位,以民族解放為中心的“民族問題”自然就解決了。這一點也可以從尾崎在所謂“和平運動”中為汪精衛偽政權提供的意識形態中也能看到。他主張,汪精衛政權在得到日本朝野和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支持的基礎上,應當謀求“民族問題”的根本的解決。*尾崎秀実:《汪精衛政権の基礎》,《尾崎秀実著作集》第二巻,東京:勁草書房,1977年,第378頁。
由此,在尾崎看來,“東亞協同體論”論的最終指向是包含中日兩國的整個東亞的“革新”。而作為馬克思主義者,他自然十分重視這一“革新”的經濟基礎。就“東洋一體”的理念而言,尾崎向來對明治以來“亞細亞主義”的“同文同種”論述不以為然,認為依靠“鄰邦”和“同文同種”之類的議論來達成中日兩國間的理解,實乃“百年待河清”之舉,這類“‘東洋的’支那論”,本質上都是為“大陸政策的本原的方法”即武力擴張服務的。*尾崎秀実:《支那論の貧困と事変の認識》,《尾崎秀実著作集》第一巻,東京:勁草書房,1977年,第220—221頁。不過,這種嚴厲的批判不代表尾崎不構想某種中日間“連帶”的共同性,這種共同性在他看來正是東亞革新的社會基礎。這一基礎就是土地問題。尾崎根據“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論”的中國認識,指出中國社會變革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度的革命任務,并認為隨著中日戰爭的展開,動員民眾參加抗戰的需要帶來了實現這一變革的契機。然而,土地問題并不僅是中國的問題,也同樣是日本社會變革的核心問題。尾崎援引“講座派”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指出日本農業同樣存在著嚴重的小農土地不足,地租過高等問題。這樣,“東亞一體”的共同性倒不在于“同文同種”,而在于共同的“革命任務”。“實現建設東亞新秩序這一高遠理想的現實條件,首先應該是東洋諸社會的內容即半封建的農業社會的解體,以及由此而來的農民解放。日本必須先自己革新,再為諸民族高度的結合創造條件。”*尾崎秀実:《東亜共栄圏の基底に橫たわる重要問題》,《尾崎秀実著作集》第三巻,勁草書房,1977年,第210—216頁。也就是說尾崎以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恢復了在批判“亞細亞主義”的過程中失去的“東亞共同性”。
作為一種激進的革命思想,馬克思主義理論內部的秩序意識是非常不安定的。然而正如全世界共產主義者的大多數這一時期都接受了共產國際的“保衛社會主義祖國”即保衛蘇聯的邏輯所表明的,如果占據“社會主義”的位置,就能取得相當的優越地位。尾崎秀實的“東亞協同體論”及其“東亞社會主義革命”的構想,在這個意義上也可以說是一種“社會帝國主義”的話語。如果將尾崎為中國共產黨的情報工作作出的卓越貢獻另當別論的話,*戰后尾崎作為共產國際的諜報員為人們所熟知,但其實他也為中國共產黨的情報工作作出了諸多貢獻,參見渡部富哉:《尾崎秀実を軸としたゾルゲ事件と中共諜報団事件——彼らは侵略戦爭に反対し中國革命の勝利のために闘った》,白井久也編:《國際スパイ ゾルゲの世界戦爭と革命》,東京:社會評論社,2003年,第27—51頁。他戰爭時期的言論活動,也可以看作一種企圖利用馬克思主義話語來解決帝國話語秩序的危機的努力。
結語:“東亞協同體論”的歸結
“東亞協同體論”關注的焦點,在于如何應對中國的抗日民族主義。通過對以上三位“東亞協同體”論者的思想邏輯的整理,可以發現以下的力學結構。個別的“東亞協同體”論者越是批判中國的民族主義,他的思想就越重視“對英美協調”,越“近代”;反之越高度評價中國的民族主義,其思想邏輯就越傾向于挑戰英美主導的世界秩序,并主張“近代的超克”。蠟山在探索與美國妥協的途徑的同時,激烈批判中國的民族主義;三木雖然主張吸收西洋文化,但隨著積極評價中國的民族主義,開始主張解決“資本主義的問題”,實現新的“世界統一”。尾崎秀實認為中國的民族主義是革命的民族主義,予以極高的評價,同時積極主張打倒英美帝國主義,并暗中期待世界共產主義革命。蠟山政道明確坦白了這一力學結構,他主張如果與英美的妥協順利進行,那么日本扶持的中國新政治體制應該采取地方高度自治的分權的聯邦制;而如果這種妥協不順利,則不得不采取權力相對集中的集權的聯邦制。*蝋山政道:《東亜協同體の理論》,《改造》,1938年11月號,第27頁。
當然,“東亞協同體論”內部“對英美協調”與積極評價中國民族主義的矛盾,并非意味著這一時期英美主導的世界秩序與中國民族主義之間存在著嚴重對立。事實上恰恰相反,隨著中日全面戰爭的爆發,英國和美國等西方列強為了遏制日本帝國主義的擴張,不得不開始摸索與中國的合作;同時中國也期待著戰爭的所謂“國際的解決”。*參見鹿錫俊:《抗戰前期國民政府對日美關系的反應》,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史研究室等編:《一九三 年代的中國》下卷,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年,第444—460頁。“東亞協同體論”中兩者的對立的奧秘就在于,日本為了繼續侵略中國,必須將中國的民族主義與英美主導的世界秩序相分離。這或許正是“東亞協同體論”背后的“帝國的真意”所在。
此外,此時“東亞協同體論”里的種種區域秩序構想,不可避免的與中國的國家構想與秩序觀相對立。首先與蠟山所定義的日本主導的開發構想和國民黨主導的依靠英美的開發構想這一對立相反,這一時期隨著日本侵略的擴大,本來國民政府重視輕工業、以輸出為重的工業化構想,急速地向以重工業和軍事產業為重心的自我中心化構想轉變。*參見嚴鵬:《國家作用與中國的工業化道路:一個李斯特主義的解讀》,《當代經濟研究》 2015年第12期。至于三木清所主張的以日本的“普遍性”來引領東亞新秩序,如馮友蘭所指出,“在歷史上,在地理上,或在文化上,無論就哪一方面說,中國本來是東亞的主人”,雖然中國在甲午戰爭中敗給日本以后,不得不以日本為模仿國來建設近代國家,但這不過是因為日本在近代化,特別是軍事力量的建設上取得了成功而已,如果中國也實現了近代化,那么“中國天然是東亞的主人”。*馮友蘭:《新事論》,《三松堂全集》第四卷,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316頁。盡管在工業和軍事力量方面一時處于劣勢,但中國并沒有對自己根本的價值觀失去信心。當日本無法用暴力征服中國時,開始主張自己價值觀的普遍性,自然不可能為中國所接受。
最后,尾崎秀實的“社會主義變革”構想并非是他一個人獨自的意見,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是與近衛新體制運動有關的“左派”知識人的共通理念。然而,這一“革新幻想”在面對天皇制的壁壘時,也不得不中途挫折。*伊藤隆:《大政翼賛會への道——近衛新體制》,東京:講談社,2015年,第231—232頁。誠然,“革新左派”可以勉為其難的將天皇制、戰時體制與“社會主義”結合起來,然而這樣的“社會主義”必然是以天皇制為中心的,致力于戰時動員的國家社會主義亦即“日本法西斯主義”。近衛新體制的結局也可以說是“東亞協同體”的“夢想”的一個歸結。
2017-03-02
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東亞諸國當今紛爭的歷史淵源研究”(編號:15CSS028)。
汪力(1988-),男,安徽宣城人,東北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博士研究生。
A
1674-6201(2017)03-0020-12
(責任編輯:馮 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