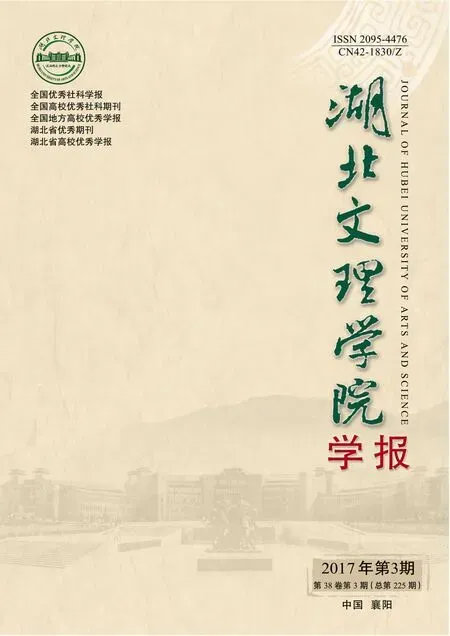王蒙文學作品中的公園、外國文學、音樂及語言
——以《仉仉》為例
趙 露
(中國海洋大學 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山東 青島 266100)
王蒙文學作品中的公園、外國文學、音樂及語言
——以《仉仉》為例
趙 露
(中國海洋大學 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山東 青島 266100)
從《青春萬歲》到《奇葩奇葩處處哀》(內含《仉仉》),再到剛剛發表的《女神》,“文壇常青樹”王蒙一直保持著綿延不息的創造力與創作力。雖然年過八旬,但王蒙仍是那個“青春萬歲”“生活萬歲”“愛情萬歲”的“年輕人”,他的創作不僅承接著過去,更“試驗”著未來。在《仉仉》中,從其公園、外國文學、音樂及語言等審美質素的運用皆可察見王蒙文學作品的承接性與超越性。
王蒙;《仉仉》;審美質素
20世紀80年代,《夜的眼》《春之聲》《風箏飄帶》《海的夢》作為“集束手榴彈”接連發表。30多年后,《奇葩奇葩處處哀》《仉仉》《我愿乘風登上藍色的月亮》作為又一波的“集束手榴彈”更是幾乎同時寫就,同時發表。耄耋之年的王蒙活力依舊、精彩依舊、青春依舊!
從《青春萬歲》到《蝴蝶》再到《奇葩奇葩處處哀》,60多年來,王蒙筆耕不輟、孳孳不倦,一直葆有著綿延不息的創作感覺和創作活力。最新文集《奇葩奇葩處處哀》既承接了過去,更“試驗”著未來。本文以《仉仉》為例,從王蒙文學作品中的公園、外國文學、音樂及語言等審美質素著手,以期探討王蒙文學作品的承接性與超越性。
一、公園:紀實與虛擬
“公園”是王蒙人生中“有意味”的場所,更是其文學作品中的一個重要審美質素,“游園”也是其中的一個重要場景。童慶炳曾言明童年經驗對于作家的重要影響:童年經驗基本上是一種心理效應,它隨著年齡的增長和環境的變化而改變,一個人在青年還是老年回顧自己的童年其感覺和印象可能是很不一樣的,這意味著一個作家可以不斷地吸收童年經驗永不枯竭的資源。[1]《王蒙自傳》中詳細記錄了作者幼時“游園”的經歷:父親和好友傅吾康聯合在北海公園買了一條游艇,我們去北海公園劃船,吃小窩頭、蕓豆卷、豌豆黃,“傅吾康叔叔曾經讓我坐在他的肩膀上去北海公園,我有記憶。”[2]王蒙和已故的妻子崔瑞芳第一次相見是在北海公園,“初戀似乎還意味著北海公園。……我們首次在北海公園見的面,此后也多次來北海公園。我們在北海公園碰過雨、雷和風。”[2]王蒙的青春時代也與頤和園密切相關,“六十二年前,當我動筆《青春萬歲》的時候,十九歲的小王蒙就那么鐘情于頤和園了”。頤和園是楊薔云、鄭波、張世群們青春的徜徉與張揚。公園是張思遠和海云愛情的生發地。湖邊長堤是鹿長思和鄭梅泠尋夢、圓夢與悵惘的追憶。“陽春召我以煙景,大塊假我以文章。”耄耋之年的王蒙再一次徜徉在大風中的頤和園,站在十七孔橋上看“波濤洶涌,石橋山丘,長廊庭院,漫天落葉”,記憶蔓延在眼前,情思涌動在心頭,“我每去一次頤和園,都要欣賞昆明湖的碧波,驚嘆于湖水的美麗與自身的渺小。”[3]再加上老友的一通電話,“我們都老了”(王蒙曾坦言自己很喜歡“我們都老了”,認為這句話特別有感情,特別人性化),《仉仉》便應風景與情思而生了。
開頭便是主人公李文采游園的見聞與隨想,緊接著的不是情節的順延,而是追溯到早晨的夢境:約翰·克利斯朵夫的人頭和形狀與數目不確定的書;然后又追溯到更早的時間:少年時代的紅纓槍與文學、月光與青紗帳、地瓜與大黃米地頭,青年時代的外國文學書與外國語大學、卷舌音與小舌音、老革命身份與黨委工作,還有“崇拜得五迷三道”的《約翰·克利斯朵夫》《復活》《悲慘世界》《紅與黑》《雙城記》《青年近衛軍》和外國文學書籍“特殊的刺活鼻孔的”氣息。由氣息引出了仉仉,因為仉仉深諳外國文學的味道。接著追憶了與仉仉的相處與自己的萬分痛苦和“被幫助”,然后是50多年后的離休、游維也納與老同學聚會,又一次的游大湖公園以及和仉仉的相遇,仉仉的離世與仉仉寄還的筆記本,到最后的“其實挺好”。在這其中,有王蒙自己真實的經歷:共青團的工作經驗、外國文學的閱讀、被打成“右派”的無奈、2012年舊稿《這邊風景》的發現……然而,在你覺得李文采是王蒙的同時,你又有深深的懷疑:王蒙對妻子崔瑞芳是始終如一深愛的,在危難之時妻子也決不會搞揭發,這從其對王蒙小學老師的態度上即可看出。這就是小說家的紀實與虛構了。小說家的天才之一就是讓讀者覺得這是他又不是他。這到底是不是王蒙呢?在你心里產生這個疑問的時候,說不定王蒙這時候會會心一笑。王蒙曾多次談到對小說紀實與虛構的看法,見解十分精到:“結構小說的一個基本手段,是虛構。虛構這個詞我還不十分喜愛它,我非常喜歡的一個詞叫虛擬。小說是虛擬的生活。”[4]“小說之吸引人,首先在于它的真實,其次(或者不是其次而是同時),也因為它是虛構的。如果真實到你一推開窗子就能看到一模一樣的圖景的程度,那么我們只需要推開窗子就可以看到小說了,何必還購買小說來讀呢?如果虛假到令人搖頭,又令人作嘔的程度,又怎能被一篇小說感動呢?”王蒙進而提出,作家一方面要從實際生活出發,發現別人所未發現之物,用生活實際提供的種種因子進行奇妙的排列組合,用其他方面的經驗補充某一方面的有限的經驗;另一方面,他(她)也可以設想生活發展的種種可能性,那些從未發生過但有可能發生,或者為某些人所向往又為另一些人所恐懼的尚不存在的事情,盡情發揮自己的想象來帶動、啟發、推進讀者的想象,使讀者進入一個既是充分現實的又是充分虛構的,既是令人信服的又是莫須有的世界。[5]小說應當求“真”,寫現實,寫生活,還有真實的內在感受與情感,但不一定要太寫實,有虛擬,有虛構,有生發,小說才能更靈活,更生動,更加有情味。另外,《仉仉》中不僅有個人經歷和個人命運的浮沉,還有歷史、時代與社會的風云變幻,也有白日夢與反思,是個人、歷史、命運的萬花筒,政治、愛情與性別的糾結激蕩,是“故國八千里,風云三十年”,是風雨與陽光兼程的一生,這是王蒙一貫的筆法。更有夢境與現實的交織,時間和空間的交錯,情感與思想的火花,不僅有現實感和厚重的哲理色彩,還有夢的浪漫與自然的詩情。“公園”的加入不僅詩意了故事發生的場景,推動了故事情節的發展,而且與主人公的心境交相輝映,情景交融,相得益彰。相比早期創作中景物主要提供情節生發的環境,后期作品中景與情與境與人更加內在地渾然一體,詩意盎然,情致宛然,更加有韻味與余味。這固然是由于彼時中國當代文學的風景“禁忌”,也可見作者文藝創作的精到與圓熟。王蒙確實深諳小說紀實與虛構的奧妙,詩與真在這里更加完美地融合在一起。
二、外國文學與音樂:觸動與靈感
王蒙的老朋友劉紹棠說,王蒙屬于城市,更注重引進、借鑒、吸收外國文學的表現手法。“在我當時所工作的共青團委會的院落外面,是一個新華書店門市部,我常常到那里去吸吮油墨的香味。我徘徊徜徉于書林,流連忘返。”[5]60多年前的青春記憶在寫《仉仉》的時候奔涌而出。王蒙極愛讀書,“前四十年,周末的主要活動是讀書。”[6]有會背誦千家詩的姥姥和愛背唐詩、愛讀文學的二姨相伴,兒童時期的小王蒙熱衷于閱讀《唐詩三百首》《千家詩》《道德經》《莊子》,青春時代更是閱讀了大量的左翼文學、蘇聯文學與歐美文學。“我開始走上創作道路時喜歡讀的是托爾斯泰、屠格涅夫、愛倫堡。”[7]可以說,王蒙的青春時代是與文學尤其是蘇聯文學互為一體的,“蘇聯文學構成了王蒙文藝思想的重要精神資源,也成為王蒙文學創作的一種重要特點,并在相當本質的意義上影響了王蒙文學創作的價值取向和精神風貌。”[8]王蒙接受了蘇聯文學的理想主義、浪漫主義精神,接受了其中的歷史感、宏大、光明甚至是感傷的一面。同時,歐美文學豐富的想象力和文學經驗也拓寬了王蒙的文學視野和精神空間,影響了王蒙的藝術觀念和藝術形式,創作手法更加多樣,使其具有更開放的文學視野,更加寬容、多元與兼收并蓄的文學觀與世界觀,當然這也與王蒙的個性與修養相關。這些都成為作者日后文學創作的滋養與靈感來源。王蒙坦言:“讀書,也可以觸發你寫作的沖動。”[6]在寫《青春萬歲》的時候,作者一遍又一遍地讀《青年近衛軍》,甚至畫出它的結構圖,想要弄清作者是如何將那么多人物妥帖地放在這部鴻篇巨制中;《青春萬歲》中有一段旁白:“我每每尋覓,一種光明的奇妙的生活……”王蒙在自傳中明確指出:“這是王蒙學了法捷耶夫在《青年近衛軍》里的旁白‘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最后是在紛飛的戰火中,用靴子作容器,喝下了戰友用生命代價舀來的帶著戰士的苦味與友情的濃郁的水。”[2]《組織部來了個年輕人》更是與《拖拉機站站長與總農藝師》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二者共有其中一個相近的主題:反官僚主義;故事發生的環境都是在基層組織,人物也有相似的對應關系。但王蒙又超越了《拖》,他沒有放棄自己的獨立思考和文本發生的環境——娜斯嘉式的英雄是否存在于當時復雜的生活中,“我無意把他寫成娜斯嘉式的英雄,像一個剛剛走向生活的知識青年能夠像娜斯嘉那樣。那似乎太理想化了。”[9]還有《風箏飄帶》與杜富門·卡波特(美國)的《災星》、《仉仉》與特奧多爾·施篤姆(德國)的《茵夢湖》,所不同的是,王蒙都給了它們光明的結尾:懂得了自己的幸福并相信什么都會有的佳原和素素,“其實挺好”的李文采。外國文學中的“戀頭癖”或許與約翰·克利斯朵夫的人頭有關:《十日談》《莎樂美》……,中國文學其實也有:《水滸傳》《將軍的頭》……王蒙不僅從外國文學中汲取營養,更注重對中國文學的繼承、發揚與有機融合,比如李商隱、老莊、《紅樓夢》,這是其不斷創新、不斷突破、不斷超越的土壤與來源。王蒙不論走得多遠,腳步始終落在大地上,就像李文采雖然穿著奧地利的西式格子呢大衣,頭上卻戴著“本市賣烤白薯小販常戴的灰藍毛線軟帽子”。
王蒙還非常喜愛音樂,“我喜歡音樂,離不開音樂。音樂是我的生活的一部分,我的生命的一部分,我的作品的一部分。有時候是我的作品的一個非常重要的、頭等重要的部分。”[10]王蒙覺得自己寫短篇小說就像在歌唱,“寫短篇小說的時候我像一名歌手,懷著溫馨和憂傷,懷著憐憫與嘲弄,含著淚或者微笑著大叫著歌唱。”[11]并提出要像唱歌一樣地寫短篇小說:“短篇小說應該是一首首發自心靈的歌。每一個作者在寫每一篇作品的時候,應該確定這一篇作品的調子。它是一首頌歌嗎?哀歌嗎?浪漫曲嗎?詼諧曲嗎?”[5]一個人的青春記憶是不可磨滅的,王蒙的青春與音樂聯系在一起,與歌唱聯系在一起,“一九四九年給我的第一個記憶,就是‘嘩啦’一下子,比錢塘江海潮都厲害——全是歌!”音樂影響了王蒙的生活和文學創作,也定將延續下去。1980年,王蒙在美國衣荷華大學參加活動時聽到歌曲《偶然》(根據徐志摩詩譜寫),觸發了他寫《相見時難》的靈感,而且,在寫作過程中,歌曲也隨行其中,“當我寫《相見時難》的時候,我不停地與藍佩玉和翁式含一起重溫四十年代、五十年代的那些歌兒。我是哼著那些歌寫作的。”[10]1981年,王蒙重聽了青年時代最喜愛的柴可夫斯基的《如歌的行板》后,王蒙對妻子瑞芳說:“我要寫一部中篇小說,八萬字,題目就叫《如歌的行板》。”后來,王蒙又寫了散文《行板如歌》。還有《春之聲》與約翰·施特勞斯的《春之聲圓舞曲》《歌聲好像明媚的陽光》與《喀秋莎》《仉仉》與德語民歌《勿忘我》。“音樂是我的老師,當然,音樂也為我服務,它可以引起我的回憶,觸發我的感受。”[10]“并從中有所發現,有所獲得,有所超越、排解、升華、了悟。進入了聲音的世界,我的身心如魚得水。”[3]音樂給予了王蒙生活的感懷與排遣,更滋養與豐富了其文學創作。
王蒙不僅欣賞,更加思考與突破,“文學與藝術,對我不僅是審美的對象,更不僅僅是娛樂的方式,接受它們的時候,我的投入我的激動我的沉浸,使它們成為我的年輕的生命的價值追求、價值標準、價值情愫。”[2]因而,外國文學與音樂不僅給了王蒙觸動與靈感,作者也更加巧妙地將其與文章結合在一起,實現新的藝術探索。《仉仉》中外國文學與情節和人物性格的發展密切聯系在一起,且更加強化了人物性格,對外國文學的看法亦反映了當時中國的社會語境。而且,《仉仉》雖深得《茵夢湖》的精髓,但卻完全是王蒙式的題材,王蒙式的風格,王蒙式的藝術感覺,《茵夢湖》原文的引用更是畫龍點睛之筆,更好地呈現了人物的心境,審美效果大大加強。而音樂不僅成為了文章的一部分,更營造了唯美浪漫的氛圍,且更加凸顯文章主旨與哲思。總之,《仉仉》將《茵夢湖》與《勿忘我》更為巧妙地融入了文本故事情節的發展、人物性格的建構、場景氛圍的營造與渲染,不僅浪漫、詩意,而且加入了厚重感、開闊感以及智慧與哲思,小說的整體結構更加藝術,布局謀篇更加精致,王蒙的創作手法與風格也更加成熟與精湛。60多年來,王蒙一直走在中國當代文學的創新與變革之路上,一直在突破與超越自己。“雖然,我一個人的能力有限,但是我愿意把路子走得寬一些,我希望我的寫作在藝術手法上呈現出一種多元的景象。”[5]《仉仉》展現了王蒙文學創作的新風貌與新可能。
三、“王蒙體”語言
文學是一種語言的藝術。“王蒙之于語言,恰如魚之于水。”[8]王蒙是一位“感覺型”和“語言型”作家,具有超常敏銳的語感與非凡的語言學習能力和語言創造力。
《仉仉》延續了《悶與狂》的“耄耋抒懷”和“少年狂歌”,語言在舞蹈,修辭在狂歡。“惡霸家里有外國文學書的譯本,沒有人讀,他讀,一接觸就如醉如癡如喝了糊涂湯。”“歐洲文學書,翻譯過來氣味與它的人物一樣強烈,像酒非酒,像‘四合一’香皂,像龍涎香,……”“他信筆由韁,磕磕碰碰,東拉西扯,咕咕噥噥,詩詩文文……”仉仉朗誦《勿忘我》的時候,“訴說得好苦、好甜、好夢幻、好云彩,好大的西北風啊。她的聲音是低語也是吶喊,是喁喁也是忽忽,是大火也是微風。”[12]語詞的重疊,詞組或短語連珠似的排比使語氣淋漓盡致,推動了小說的氣氛與節奏;博喻更是前呼后擁而來,“妙喻如舟”,令人目不暇接,如漢賦般洋洋灑灑,如交響樂般奔放激昂,而且多是“陌生化”、創新化的喻體,給人以新鮮感與刺激。“他將比喻和排比當成文學的舞步,閃轉騰挪、大開大合、疾風驟雨、密不透風,恣意地宣泄自己的情感。”[13]王干說王蒙有語言的擴張欲,喜歡把各種各樣的名詞、動詞、形容詞進行重疊。王蒙自己還說“最喜歡用的是把矛盾式的詞和句子用在一起,比如你這個崇高的卑鄙的人,我是經常用這種方式。”另外,王蒙還提出不僅古詩文、古典白話小說、翻譯作品、“五四”新文學的語言可以作為我們寫作的資源,時尚語言也可以是。《仉仉》中有“最新款的銀器”與“路易·威登箱包的專賣店”,牛氣沖天,每件衣服只做一件的“巴寶莉專賣店”,“高級香料與特級防腐劑”這樣前衛時尚的語詞。更為突出的是,《仉仉》的語言還有一種詩意,有一種浪漫,有一種韻味。不論是自然、夢境的描摹,場景、情境的營造,人物心境的摹寫,都有一種意境、詩境和詩情,藝術性更高,更加流光溢彩,宛若天成。這樣一種“眾生喧嘩”“雜語狂歡”“妙喻如舟”、排比如珠、詩情盎然、新鮮多樣的“王蒙體”語言,這樣一種“新的意識形態話語的探索和試驗”,實是“重建了另一種語言和存在(我們更習慣成為現實)的關系,重塑了語言與存在的一種動態的多向性、無序性和模糊性,在這種語言流中呈現為一種無限性的意義敞開。”[9]
語言既是工具,也是思想。人不僅能控制語言,語言也能控制人。“人一旦選擇了某種語言,那么他的思想和思維方式事實上就由這種語言從極宏觀的限度內無形地決定了。”[14]五四時期的文白之爭、30年代的大眾語文與拉丁化實際上也是思想的爭鋒。語言深深控制著人類的思想和思維方式。王蒙深刻地看到了語言文字推動思想的力量,“語言文字的這種促進思想的作用一方面說明了符號的功能,一方面說明了表達與思想的不可分。”“思想內容的發展變化會帶來語言符號的發展變化,當然,反過來說,哪怕僅僅從形式上制造新的符號或符號的新的排列組合,也能給思想的開拓以啟發。”[11]“王蒙體”實是突破了單一的文學觀、單一的思維定勢和線性思考,消解了一元和對立,消解了“只此一家,別無分號”,認為世界不只存在一種真理,一種可能,而是多元、多樣、包容、理解與兼收并蓄。這從20世紀80年代王蒙對先鋒文學的支持和保護中即可窺見一斑。而這種開放的世界觀和文學觀反過來也滋養了王蒙的文學創作,使其更加多樣,更加“活”,也更具張力和創造力。
總的來說,《仉仉》與王蒙之前的作品不僅有承接,更有突破。革命、青春、愛情的相互激蕩,歷史、政治、個人命運的變幻浮沉,文學、音樂的激發渲染,還有人性與時代的反思,“王蒙體”語言的波詭云譎。但《仉仉》更加浪漫,結構更加精致,更加藝術化,更加有意境,更加有情致,王蒙在其中為我們創造了一個浪漫、美好、感懷卻又韻味悠長的藝術世界,這也證明了老王蒙不僅能作小說,更能作風格不同的小說!
憂患春秋心浩渺,情思未減少年時!只要心兒不曾老,王蒙尚能小說也!
[1] 童慶炳.文學審美特征論[M].武漢: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2000:212.
[2] 王 蒙.王蒙文集第41卷[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4:7-163.
[3] 王 蒙.王蒙文集第17卷[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4:75-192.
[4] 王 蒙.王蒙文集第24卷[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4:47.
[5] 王 蒙.王蒙文集第21卷[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4:67-335.
[6] 王 蒙.詩酒趁年華:王蒙讀書與寫作[M].北京:商務印書館,2016:7-223.
[7] 王 蒙.王蒙文集第28卷[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4:325.
[8] 溫奉橋.王蒙文藝思想論稿[M].濟南:齊魯書社,2012:59-273.
[9] 溫奉橋,編.王蒙·革命·文學——王蒙文藝思想研究[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8:98.
[10] 王 蒙.王蒙文集第40卷[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4:185-188.
[11] 王 蒙.王蒙文集第20卷[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4:45-188.
[12] 王 蒙.奇葩奇葩處處哀[M].成都:四川文藝出版社,2015:103-126.
[13] 嚴家炎,溫奉橋.王蒙研究:第二輯[M].青島:中國海洋大學出版社,2015:188.
[14] 高 玉.魯迅的語言觀與創作及其與中國現代文學發生的關系[J].魯迅研究月刊,2000(4):30-45.
(責任編輯:倪向陽)
I207.425
:A
:2095-4476(2017)03-0046-04
2016-12-15;
2017-01-03
趙 露(1992—),女,山東龍口人,中國海洋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碩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