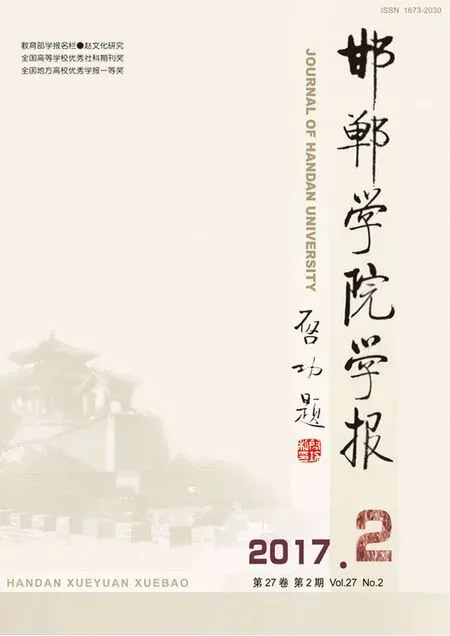《中國文化史講義》緒論
喬福錦
(邯鄲學(xué)院 太行山文書研究中心,河北 邯鄲 056005)
《中國文化史講義》緒論
喬福錦
(邯鄲學(xué)院 太行山文書研究中心,河北 邯鄲 056005)
文化是包括價值信仰、政治制度與社會生活方式在內(nèi)的民族共同體存在方式,也是精神性、規(guī)范性與歷史性存在的生命結(jié)構(gòu)系統(tǒng)。中國古典文化經(jīng)歷了上古、中古、近古即奠基、規(guī)范與化成三個不同歷史時期,也經(jīng)歷了相對完整的文化歷史“全程”。以精神文化為統(tǒng)領(lǐng)且集學(xué)術(shù)文化、制度文化、社會文化三位一體的中國文化史,是具有專門史品格的廣義文化史,是中國文化從奠基、鞏固到成熟的“三世”演化全程史,也是傳承著華夏民族文化“道統(tǒng)”的精神史。
結(jié)構(gòu)系統(tǒng);分期歷程;編著體例
中國是一個具有至少五千年歷史傳承延續(xù)的文明古國。由于史官文化發(fā)達(dá),雖飽經(jīng)內(nèi)憂外患,仍留下浩如煙海的史學(xué)典籍。然而學(xué)科意義上的文化史,遲至近代在西方影響下才開始出現(xiàn)。伴隨著文藝復(fù)興之后人文主義思潮的興起,歐洲人開始關(guān)注自己的文明歷史進(jìn)程。由于地理大發(fā)現(xiàn),了解不同的文明的需求日漸強(qiáng)烈,加之近代科學(xué)的發(fā)達(dá)與自我反思意識的增強(qiáng),文化史作為一個學(xué)科,從 18世紀(jì)開始逐漸形成。晚清民初,隨著國門的打開,中國人了解外來文明的需求日趨迫切,對于自己民族歷史的反省意識日益強(qiáng)烈,專業(yè)意義上的中國文化史研究也隨之產(chǎn)生。
近百年來的中國文化史研究,可大體分為民國創(chuàng)建、文革中斷與新時期學(xué)科重建三個階段。1902年,梁啟超《新史學(xué)》的發(fā)表,是中國近代史學(xué)產(chǎn)生的標(biāo)志,也可以看作是文化史學(xué)在中國萌芽的開端。1914年,林傳甲《中國文化史》一書由上海科學(xué)書局出版,被學(xué)界稱為中國本土出現(xiàn)的第一部文化史著作。1922年梁啟超發(fā)表《關(guān)于文化史研究的幾個重要問題》的講演,則是文化史學(xué)科自覺意識形成的標(biāo)志。五四新文化運(yùn)動之后,以胡適、傅斯年為代表的“科學(xué)史學(xué)”和以錢穆、柳治徵為代表的保守主義史學(xué),均十分重視文化史研究。文化史作為專門之學(xué),此一時期亦在大中學(xué)校課堂出現(xiàn)。1922年,“中國文化史”作為高中“公共必修課目”,開始在中學(xué)開設(shè)。①見李國均、王炳照《中國教育制度通史》第7卷,山東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60頁。1926至1928年,處于新舊制并存時期的清華大學(xué)歷史系,舊制部開設(shè)世界史、通史、《史記》《漢書》、中國哲學(xué)史、中國史、明史等課程,中國文化史是其中重要一門,新制部課程有中國通史、中國外交史、美國史等門類,中國文化史同樣位列其中。②參閱《清華大學(xué)史料選編》,清華大學(xué)出版社1994年版。此外,師范學(xué)院開設(shè)“本國文化史”,已成為常例。大學(xué)文、理、法學(xué)院開設(shè)“中國通史”,亦特別“注重文化之發(fā)展”。 20世紀(jì)50年代之后,從前蘇聯(lián)傳來的教條主義,成為中國大陸學(xué)術(shù)文化與高等教育的精神主導(dǎo)。庸俗社會史論研究取代文化史研究,文化史作為一個學(xué)科,由此被迫取消。文革后期“批林批孔”運(yùn)動中,中國數(shù)千年正統(tǒng)文化幾乎遭到全盤否定。在此背景下,中國文化史被儒法斗爭史所替代。同一時期,偏安一隅的港臺學(xué)術(shù)界,依然延續(xù)著民初以來不絕如縷的學(xué)術(shù)命脈。新時期以來,中國大陸學(xué)界與外部世界聯(lián)系恢復(fù),與民國學(xué)術(shù)的聯(lián)系亦同時接通。1982年12月“中國文化史研究學(xué)者座談會”在上海召開,此之后,《中國文化史叢書》開始編輯出版。1986年1月“首屆國際中國文化學(xué)術(shù)討論會”在上海復(fù)旦大學(xué)舉辦,文化史研究開始受到學(xué)界廣泛關(guān)注。①參閱周積明先生《二十世紀(jì)的中國文化史研究》,《歷史研究》1997年第6期;何曉明先生《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文化史研究》,《史學(xué)月刊》2009年第5期;周兵先生《新文化史與歷史學(xué)的“文化轉(zhuǎn)向”》,《江海學(xué)刊》2007年第4期;楊齊福先生《20世紀(jì)中國文化史研究之回顧與展望》,《淮陰師范學(xué)院學(xué)報(bào)》2000年第2期。在新的歷史與文化背景之下,中國文化史重新成為大學(xué)歷史專業(yè)主干課程,非史學(xué)專業(yè)多將文化史列入必修或選修目錄,各類中國文化史教材陸續(xù)問世。20世紀(jì)末至新世紀(jì)初,隨著國學(xué)研究的復(fù)興,國外新文化史研究的興起,歷史學(xué)“文化轉(zhuǎn)向”趨勢的形成乃至社會文化史研究日益深入,中國文化史研究進(jìn)入新的階段。②參閱周兵先生《新文化史與歷史學(xué)的“文化轉(zhuǎn)向”》,《江海學(xué)刊》2007年第4期。文化通史、文化斷代史及各種專題文化史著作層出不窮,學(xué)科重建亦被提上日程。
20世紀(jì)的中國文化史研究,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近百年的學(xué)術(shù)積累,亦為這一學(xué)科得發(fā)展奠定了深厚基礎(chǔ)。然而,相對于幾乎同時復(fù)興甚至起步更晚的中國思想史、中國社會史等學(xué)科,中國文化史學(xué)科建設(shè)過程并不順利。究竟什么是文化史研究的“文化”亦即學(xué)科對象為何,文化史的研究范圍如何界定,文化史與一般史著的區(qū)別何在,如此一些關(guān)于文化史研究中的基本問題,學(xué)界目前仍存在大的分歧。概念內(nèi)涵與外延爭論不清,導(dǎo)致研究對象不清,學(xué)科定位不準(zhǔn),學(xué)術(shù)體系建構(gòu)殘缺不全,歷史分期,各有標(biāo)準(zhǔn),著作體例極其混亂。面對此種局面,從20世紀(jì)90年代中期起,即不斷有學(xué)者開始作反思性研究。本敘論以先哲時賢的學(xué)術(shù)成就為基礎(chǔ),結(jié)合自己多年的教學(xué)實(shí)踐,試圖針對目前存在的主要問題,作以概略性論述。這樣的論述,為個人數(shù)十年教學(xué)研究實(shí)踐之總結(jié),是《中國文化史講義》體系建構(gòu)的提綱,也可視作學(xué)科建設(shè)意義上的學(xué)術(shù)反思與問題探索之舉措。
一、結(jié)構(gòu)系統(tǒng):學(xué)、政、俗三位一體
“文化”一詞,中國古已有之。《易·系辭下》曰:“物相雜,故曰文。”“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于天,俯則觀法于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yuǎn)取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1]漢人許慎《說文解字》云:“文,錯畫也,象交文。”“文”之本義,系指各色交錯的紋理,在此基礎(chǔ)上,“文”字被不斷引申,逐漸具備符號、文字、文獻(xiàn)、典章、禮儀、制度等義。《尚書·舜典》疏曰:“經(jīng)緯天地曰文。”[2]《論語·雍也》曰:“質(zhì)勝文則野,文勝質(zhì)則史,文質(zhì)彬彬,然后君子。”《禮記·樂記》云:“五色成文而不亂。”[3]《禮記·樂記》:“禮減而進(jìn),以進(jìn)為文”,鄭玄注:“文猶美也,善也”。《尚書·大禹謨》:“文命敷于四海,祗承于帝。”[2]《日知錄》卷7《博學(xué)于文》:“君子博學(xué)于文,自身而至于家國天下,制之為度數(shù),發(fā)之為音容,莫非文也。”[4]與“文”相隨之“化”,也是一個被逐漸引申的漢字。“化”之本義,為變易、生成、造化。后被引申為改造、教化、培育等。如果說“文”之重點(diǎn)在形態(tài),“化”之重點(diǎn)則在過程。所謂化民成俗,以文化俗、化政、化野是也。《莊子·逍遙游》云:“化而為鳥,其名曰鵬。”[5]《易·系辭下》曰:“男女構(gòu)精,萬物化生。”[1]《黃帝內(nèi)經(jīng)·素問》云:“化不可代,時不可違。”[6]《禮記·中庸》曰:“可以贊天地之化育。”[3]《孟子》講:“所過著化,所存者神。”《荀子·不茍》云:“神則能化矣。”[7]注曰:“化,謂遷善也。”“文”與“化”并聯(lián)使用,較早見之于《易·賁卦·象傳》:“(剛?cè)峤诲e),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1]所謂“天文”,指天道自然規(guī)律;所謂“人文”,指人倫社會規(guī)范。漢以后,“文”與“化”逐漸合成一辭而用。《說苑·指武》云:“圣人之治天下也,先文德而后武力。凡武之興,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誅。”[8]《文選·補(bǔ)之詩》云:“文化內(nèi)輯,武功外悠。”[9]“文化”在此又與華夷之辨相關(guān)。“華夏”一詞最早出現(xiàn)在《尚書·武成》:“華夏蠻貊,罔不率俾。”[2]孔安國解釋為“冕服采裝曰華,大國曰夏”,此處之“華”,義與周“文”相近。“文化”也與“文明”相近。《周易·賁卦·彖辭》曰:“文明以止,人文也。”[1]錢穆《中國文化史導(dǎo)論》(弁言)云:“文明編在外”,“文化編在內(nèi)”;“文明可以向外傳播,文化則必須由其群體內(nèi)部精神累積而產(chǎn)生。”[10]
從詞源上講,英文中的文化(culture),來自拉丁文culture。原意指耕種、栽培、養(yǎng)殖之舉乃至原始農(nóng)業(yè)耕種、栽培及養(yǎng)殖等謀生范式。古希臘城市社會形成之后,西方文明開始定型。Culture又被引申為培養(yǎng)、訓(xùn)練、教養(yǎng)、陶冶等。與之不同,華夏農(nóng)耕文明起源時間雖早且最為成熟,文化概念之形成,卻與實(shí)際耕作無關(guān)。圖案、花紋等精神性創(chuàng)作,才是“文”乃至“文化”一詞之本根。“文化”詞源之不同,也表現(xiàn)在人與自然、民族與個體、教養(yǎng)與智慧等關(guān)系認(rèn)識之相異。③關(guān)于中西文化概念之由來及異同,近年來討論文章極多,相關(guān)著作與教材亦有涉及,可比照參閱。西方注重物質(zhì)文化與底層耕作,中國更注重精神文化與上層教化。中文之文化概念,強(qiáng)調(diào)文治教化,上下一體,西方文化概念,重視開拓進(jìn)取,關(guān)注前后。要之,中西文化概念起源不同,各自的側(cè)重點(diǎn)也不同。
文化研究成為一個學(xué)科之后,文化概念的使用開始要求有確切的涵義。有學(xué)者講,“文化的概念既不是多所指的,也不是模棱兩可的,而是以歷史沿襲下來的體現(xiàn)于象征符號中的意義模式,是由象征符號體系表達(dá)的傳承概念體系,人們以此達(dá)到溝通,延有無發(fā)展對生活的知識和態(tài)度”,[11]103然而給其下一個嚴(yán)格和精確的定義,卻非常困難,文化作為一個學(xué)術(shù)概念,其定義極難把握。不同文化背景、不同學(xué)科背景的學(xué)者甚至同一學(xué)者觀察角度不同,關(guān)于文化概念的理解亦大不相同。近代以來,語言學(xué)家、哲學(xué)家、社會學(xué)家、人類學(xué)家、歷史學(xué)家等均試圖從各自學(xué)科的角度來界定文化的概念。但迄今為止仍沒有獲得學(xué)界公認(rèn)的定義。美國人類學(xué)家A.L.克婁伯和C.克魯克洪合著的《文化,關(guān)于概念和定義的檢討》(Culture,A Critical Review of Concepts and Definitions)一書,對自泰勒以來西方的文化定義現(xiàn)象進(jìn)行過統(tǒng)計(jì)研究。在這本書里,羅列了從1871年到1951年80年間關(guān)于文化的定義,至少有160余種。①參閱《文化:關(guān)于概念和定義的檢討》,轉(zhuǎn)見馮天瑜先生《中國文化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12月版。
1871年,英國人類學(xué)家愛德華·泰勒(Edward Tyior)在其所著的《原始文化》一書“關(guān)于文化的科學(xué)”一章中說:“文化或文明,就其廣泛的民族學(xué)意義來講,是一復(fù)合整體,包括知識、信仰、藝術(shù)、道德、法律、習(xí)俗以及作為一個社會成員的人所習(xí)得的其他一切能力和習(xí)慣。”這是廣義文化概念的典型表述,已涉及到文化結(jié)構(gòu)之組成。
作為“復(fù)合整體”且具有結(jié)構(gòu)意義的文化,自然需要分層。從學(xué)術(shù)分層的意義上把握文化概念,也是學(xué)界試圖找到文化定義核心要素的一個切入點(diǎn)。關(guān)于文化分層,西方學(xué)者有物質(zhì)文化與精神文化兩分之說;有精神文化、制度文化、物質(zhì)文化三分之說;有物質(zhì)、制度、風(fēng)俗習(xí)慣、思想與價值四分之說;有物質(zhì)、制度、精神、行為、語言等五分之說。有物質(zhì)、社會關(guān)系、精神、藝術(shù)、語言符合、風(fēng)俗習(xí)慣六大子系之說。1925年梁啟超先生在南開大學(xué)作《中國文化史》演講,其中關(guān)于“社會組織篇”,包括婚姻、姓氏、鄉(xiāng)俗、都市、家族和宗法、階級、階層等方面。所撰《中國文化史目錄》,包括種族、政治、法律、教育、交通、服飾、學(xué)術(shù)等28篇。梁氏視域中的文化,可分為多層。新時期中國大陸第一個文化史專業(yè)博士點(diǎn)創(chuàng)建者、目前最為流行的馮天瑜先生所編之《中國文化史》教材,將文化分為學(xué)術(shù)思想、行為、制度和物質(zhì)文化四個層面。②參閱馮天瑜先生《中國文化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12月版。根據(jù)文化的結(jié)構(gòu)和范疇,學(xué)界又把文化分為廣義和狹義兩種概念。狹義文化指哲學(xué)、宗教、文學(xué)、藝術(shù)、政治、經(jīng)濟(jì)、倫理、道德等等,即小寫的文化(culture with a small c)。廣義文化,則是包括精神文明和物質(zhì)文明所創(chuàng)造的一切東西,即大寫的文化(Culture with a big C)。余英時先生針對《文明論衡》一書所使用概念時曾講:“我在這里所用的‘文明’只有一個意義,這意義是與廣義的‘文化’沒有分別的,但我所用‘文化’一詞則有廣狹兩種含義:廣義的不必再說,狹義的是指‘學(xué)術(shù)思想’等社會的精神面而言的。”[12]252從廣義角度觀,文化結(jié)構(gòu)也可分作多層。
殷海光先生在《中國文化的展望》一書中,將克魯伯(A. L. Kroeber)和克羅孔(Clyde Kluckhohn)所列百余種“文化”概念,歸為六大類。1、列舉描述過程的,2、歷史性的,3、規(guī)范性的,4、心理性的,5、結(jié)構(gòu)性的,6、遺傳性的。③見殷海光先生《中國文化的展望》,上海三聯(lián)書店,2002年12月版第28頁。殷先生試圖從文化概念之切入角度,對文化概念作歸類。實(shí)際上,文化六類概念,也可簡化為三類。列舉描述過程,歸歷史性,“結(jié)構(gòu)”、系統(tǒng)性歸規(guī)范性,心理性、遺傳歸精神性。文化三要素,包括歷史(過程);規(guī)范(制度);精神(思想)。六類概念,也可約化為精神性、規(guī)范性、歷史性三層。學(xué)界、官方與民間社會三個層面,與精神、制度、物質(zhì)三層文化結(jié)構(gòu)相通,亦與文化概念三種類型一致。④參閱龐樸先生《一分為三》中相關(guān)論述,另見《龐公之“三”》,2017 年1月7日《光明日報(bào)》。
考之中國學(xué)術(shù)史,以精神性、規(guī)范性、歷史性三個維度把握“文化”意義的本質(zhì),亦可尋到經(jīng)典依據(jù)。《尚書·泰誓上》曰:“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孔傳云:“天佑助下民,為立君以政之,為立師以教之。”[2]孔傳所講,即涵蓋學(xué)、政、俗三個層面。顧炎武曰:“文之不可絕于天地者,曰明道也,紀(jì)政事也,察民隱也,樂道人之善也。若此者,有益于天下,有益于將來。多一篇,多一篇之益矣。”所謂“明道也,紀(jì)政事也,察民隱也”,亦可理解為道、政、俗三個文化層面之論。王靜安先生論清代學(xué)術(shù)流變時曾云:“道咸以降……學(xué)者尚承乾嘉之風(fēng),然其時政治、風(fēng)俗已漸變于昔,國勢亦稍稍不振。”(《觀堂集林》卷二十三)此種論述,亦可作文化“學(xué)”、“政”、“俗”三個層面劃分之據(jù)。陳寅恪先生論中國思想史時指出:“南北朝時,即有儒釋道三教之目。故自晉至今,言中國之思想,可以儒釋道三教代表之。此雖通俗之談,然稽之舊史之事實(shí),驗(yàn)以今世之人情,則三教之說,要為不易之論。故兩千年來華夏民族所受儒家學(xué)說之影響,最深最巨者,實(shí)在制度法律公私生活之方面,而關(guān)于學(xué)說思想之方面,或轉(zhuǎn)有不如佛道二教者。”[13]陳先生之論述,其實(shí)亦從三個層面展開。
文化各個層面之間的邏輯聯(lián)系,同樣是學(xué)界十分關(guān)注的課題。1922年,梁啟超發(fā)表《關(guān)于文化史研究的幾個重要問題》的演講。梁先生云:“因果是自然科學(xué)的命脈……。史學(xué)向來并沒有被認(rèn)為科學(xué),于是治史學(xué)的人因?yàn)橄肓钭约核鶒鄣膶W(xué)問取得科學(xué)資格,便努力要發(fā)明史中因果,我是這里頭的一個人。我去年著的《中國歷史研究法》內(nèi)中所下歷史定義,便有‘求得其因果關(guān)系’一語。我近來讀立卡兒特著作,加以自己深入反復(fù)研究,已經(jīng)發(fā)覺這句定義全錯了。歷史現(xiàn)象最多只能說是‘互緣’,不能說是因果。”歷史文化各層面之間,既有“互緣”;又有“因果”。①參閱梁啟超《關(guān)于文化史研究的幾個重要問題》,轉(zhuǎn)引自牛潤珍《關(guān)于歷史學(xué)理論的學(xué)術(shù)論辯》,百花洲文藝出版社,2004年版第18頁。注重各學(xué)科、各層次的“互緣”與“因果”,也是文化結(jié)構(gòu)分析的關(guān)鍵。
文化作為民族的生存方式,涉及物質(zhì)、制度乃至思想等層面。各層之間的歷史與邏輯聯(lián)系,必不可少,精神文化的存在自然離不開物質(zhì)與制度條件。胡適先生《中國哲學(xué)史》后改為《中國思想史》,放棄“哲學(xué)史”概念,即與抽象的哲學(xué)無所寄托有關(guān)。西方近現(xiàn)代人類學(xué)研究,強(qiáng)調(diào)“大傳統(tǒng)”與“小傳統(tǒng)”之分,重視上層文化與下層文化、精英文化與大眾文化、高雅文化與通俗文化之別。②參閱余英時先生《從史學(xué)看傳統(tǒng)——<史學(xué)與傳統(tǒng)>序言》,見《余英時文集》,廣西師大出版社2014年6月版,第一卷。在中國傳統(tǒng)中,文化卻是包括價值信仰、政治制度與社會生活方式在內(nèi)的民族共同體存在方式,是精神性、規(guī)范性與歷史性存在的生命結(jié)構(gòu)系統(tǒng)。學(xué)界、官方與民間社會,三個傳統(tǒng),構(gòu)成一個文化整體,并不存在截然分別的“大”與“小”分別與對立的兩個傳統(tǒng)。錢穆先生在《國史大綱·引論》中講:“近世史學(xué)革新派所關(guān)注者,有三事:首則曰政治制度,次則曰學(xué)術(shù)思想,又次則曰社會經(jīng)濟(jì)。此三者,社會經(jīng)濟(jì)為其最下層之基礎(chǔ),政治制度為其最上層之結(jié)頂,而學(xué)術(shù)思想則為其中層之干柱。”[14]錢先生同時指出,學(xué)術(shù)指導(dǎo)政治,政治領(lǐng)導(dǎo)社會,文化三個層面,是一個有機(jī)整體與結(jié)構(gòu)系統(tǒng)。[14]陳寅恪先生將家族作為民族文化生命寄托之處,家族文化之考論,與學(xué)術(shù)傳承、政治興亡相聯(lián)結(jié),同樣十分重視文化結(jié)構(gòu)之整體聯(lián)系。從整體角度觀,學(xué)、政、俗(社)三位一體,正是文化個層面“互緣”的結(jié)果。其中學(xué)術(shù)為主導(dǎo),典制是關(guān)鍵,民間社會則是基礎(chǔ)。文化道統(tǒng)基于社統(tǒng);彰與政;寄于學(xué)統(tǒng)。其中,學(xué)統(tǒng)中有承道使命、人文精神、教化意識;政統(tǒng)中有民本思想、德治觀念、一統(tǒng)要術(shù);俗統(tǒng)中有自然的(民義)、倫理的(宗法)、藝術(shù)的(市類)。“百姓日用而不知”之“道”,即吉爾茨“社會歷史行為的象征因素”。“三統(tǒng)”貫“一統(tǒng)”,形成文化生命“系統(tǒng)”③參閱拙稿《朱熹文化世界的“三統(tǒng)”整合》,《河南教育學(xué)院學(xué)報(bào)》2007年第2期。,貫穿著民族文化之根本精神。此處之精神“道統(tǒng)”,即指世代相承之華夏歷史文化傳統(tǒng),不同與現(xiàn)代新儒家常講之神秘體驗(yàn),卻與錢穆先生之歷史文化精神說接近。要之,文化是包括價值信仰、政治制度與社會生活方式在內(nèi)的民族共同體存在方式,也是精神性、規(guī)范性與歷史性存在的生命系統(tǒng)。鄉(xiāng)土中國與典制中國、學(xué)術(shù)中國一起,構(gòu)筑起文化中國。此一文化意義上的中國,亦即禮樂中國、道統(tǒng)中國。④參閱張新民先生上海會議論文“三個中國”之說及杜維明先生文化中國之說。在此意義上講,中國文化史實(shí)是包括學(xué)術(shù)文化史、制度文化史、社會文化史在內(nèi)的中國文化史生命史。當(dāng)代西方興起的新文化史研究,對于文化概念歷史性因素與社會性因素的強(qiáng)調(diào),亦值得特別重視。⑤參閱周兵先生《新文化史與歷史學(xué)的“文化轉(zhuǎn)向”》,《江海學(xué)刊》2007年第4期。艾爾曼的中國思想史研究的轉(zhuǎn)向,也可視作思想史與社會史、政治史與文化史結(jié)合的表現(xiàn)。⑥參閱艾爾曼《中國文化史研究的新方向——值得探討的問題》,見《學(xué)術(shù)思想評論》第三輯。
王云五先生在《編纂中國文化史之研究》中講:“我國士大夫之著作,要皆偏于廟堂之制度,號為高文大冊,其有關(guān)閭閻之瑣屑,足以表現(xiàn)平民之文化者,皆不屑及焉……”⑦參閱《編纂中國文化史之研究》,商務(wù)印書館1936年版第15—16頁。這如此之推斷,并不準(zhǔn)確。與文化可分為學(xué)術(shù)文化、制度文化、社會文化三個層面相一致,歷史文獻(xiàn)也可分為學(xué)術(shù)著作、制度典章、民間文書三類。如果說《周易》為上古精神之文本,《尚書》《三禮》《春秋》為上古制度之文本,以《豳風(fēng)·七月》為代表的《詩經(jīng)》“十五國風(fēng)”,則是上古社會文化之典型文本。《豳風(fēng)·七月》是農(nóng)耕社會四時歷程的真實(shí)記錄,⑧錢穆先生《中國文化史導(dǎo)論》第6頁有《豳風(fēng)》地理環(huán)境為晉南陜東之說,可參閱。是“天文”與“人文”合一的經(jīng)典反映,某種意義上也是以農(nóng)耕文明為基礎(chǔ)的整體中國文化之集中寫照,是中國文化之系統(tǒng)結(jié)構(gòu)文本。風(fēng)、雅、頌三者之文體及社會分別意義,先輩詩賢或曾關(guān)注。其文化分層意義,則有必要特別強(qiáng)調(diào)。《毛傳》:“《七月》,陳王業(yè)也。周今遭變,故陳后稷先公風(fēng)代之所由,致王業(yè)之艱難也。”[15]《周禮·籥章》云:“掌土鼓、豳籥。中春晝,擊土鼓,吹豳詩,以逆暑。中秋夜迎寒,亦如之。凡國祈年于田祖,吹豳雅,擊土鼓,以樂田畯。國祭蠟,則吹豳頌,擊土鼓,以息老物。”[17]《鄭箋》曰:“《豳詩》,《豳風(fēng)·七月》也。《豳雅》亦《七月》也。《豳頌》亦《七月》也。”姚際恒《詩經(jīng)通論》云:“鳥語、蟲鳴,草榮、木實(shí),似《月令》。婦子入室,茅、綯、升屋,似風(fēng)俗書。流火、寒風(fēng),似《五行志》。養(yǎng)老、慈幼,躋堂稱觥,似癢序禮。田官、染織,狩獵、藏冰,祭、獻(xiàn)、執(zhí)功,似國家典制書。其中又有似《采桑圖》《田家樂圖》《食譜》《谷譜》《酒經(jīng)》。一詩之中無不具備,洵天下之至文也。”[16]《豳風(fēng)·七月》以西周禮樂文化精神為主線,是社會文化史的歷史性存在,古人亦有《七月》一篇,集中風(fēng)、雅、頌三體之論。《豳風(fēng)·七月》,體大文備,“其道情思者為風(fēng),正禮節(jié)者為雅,樂成功者為頌。”此“風(fēng)、雅、頌”三位一體之文本,既是中國文化之學(xué)、政、俗三位一體之文本載體,亦是中國文化史編纂之文本追求。
二、分期歷程:上古、中古、近古“三世”進(jìn)化
文化是民族生命形態(tài),是文化生命傳承延續(xù)的過程。文化概念,自然屬于歷史性范疇。近代“歷史主義”,將世界上所有地區(qū)的歷史視為一個統(tǒng)一的過程,共同遵守同一個時間參照系。然各地區(qū)歷史卻呈現(xiàn)出時間、速度之先后。歷史向前演化發(fā)展,即可視作歷史過程之體現(xiàn)。斯賓格勒在《西方的沒落》一書中說,大多數(shù)文化都經(jīng)歷過一個生命周期,西方已然走過文化創(chuàng)造階段,正通過反省物質(zhì)享受而邁向無可挽回的沒落。他認(rèn)為沒有人類共同的歷史,歷史是各個文化的歷史,但各民族文化均要經(jīng)歷從興起、興盛到衰落的生命過程,則是人類的共同命運(yùn)。歷史學(xué)家不僅要重建過去,更重要的是預(yù)言,用他的話說就是“我們西方歷史尚未完結(jié)的各階段的思想方式、時間長短、節(jié)奏、意義和結(jié)果”。正因?yàn)槿绱耍段鞣降臎]落》被很多人認(rèn)為是一部未來之書,斯賓格勒也被稱為“西方歷史的先知”。中華文化的歷史階段性,在孔子之著述中,亦有明確之體現(xiàn)。在農(nóng)耕文明為主導(dǎo)的中國古典社會,從歷史性意義上講,文化成長與發(fā)展的過程,與自然天年具有同構(gòu)性。孔子所作之《春秋》,是以天文四時架構(gòu)人文歷程的具體展現(xiàn),也是中國文化歷程之經(jīng)典表述。錢穆先生在《中國文化史導(dǎo)論·弁言》中講:“中國文化問題,實(shí)非僅屬一哲學(xué)問題,而是一歷史問題。中國文化表現(xiàn)在中國已往全部歷史過程中,除卻歷史,無從談文化。我們應(yīng)以全部歷史之客觀方面,來指陳中國文化之真相。”[10]
傅斯年先生在《中國歷史分期之研究》中講:“要以分期,為之基本,置分期于不言,則史事雜陳,樊然淆亂,無術(shù)以得其簡約,疏其世代,不得謂為歷史學(xué)也。”[19]41錢穆先生《國史大綱》“引論”云:“若言洞設(shè)譬,中國史如一首“詩”,西洋史如一本“劇”。一本劇之各幕、場有其截然不同之變換,詩則只在和諧節(jié)奏中轉(zhuǎn)移到新階段,令人不可劃分。”[14]然《中國文化史導(dǎo)論》論中國歷史,仍有清晰的分期線索可尋。基督教把西方歷史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伊甸園”階段,是神創(chuàng)造人的階段;第二階段是人的“墮落”階段;第三階段是神來”拯救”人的”墮落”的階段。黑格爾的歷史三期說,以為歷史是一個正、反、合的進(jìn)步歷程,此與基督教之歷史觀一致,與儒家學(xué)者關(guān)于中國歷史的分期,也有相似之處。梁啟超先生曾講:“四千余年之歷史未嘗一中斷者,誰乎?我中華也。”[18]作為未曾中斷的華夏歷史文化,如人生可區(qū)分為童年、青年、壯年、老年不同時期一樣,也有自己的生命周期。春生、夏長、秋收、冬藏的歷程,是自然的歷程,是文化生命演化的歷程。《春秋》“四時”結(jié)構(gòu)與分期,即遵循這一基本原則。以《春秋》今文經(jīng)學(xué)為代表之“三世說”,是儒家歷史觀、史學(xué)觀之集中體現(xiàn),也是中國古典文化史分期的基本依據(jù)與原則。朱子云:“但以儒者之學(xué)不傳,而堯、舜、禹、湯、文、武以來轉(zhuǎn)相傳授之心不明于天下,故漢唐之君雖或不能無暗合之時,而其全體卻只在利欲上。此其所以堯舜三代自堯舜三代,漢祖唐宗自漢祖唐宗,終不能合而為一也。”《朱文公文集》卷三六《答陳同甫》)朱子的“王霸義利之辨”,將“三代”、“漢唐”相區(qū)分,以為宋以后是“后三代”。此種歷史觀,也與《春秋》“三世”說一脈相承。1902年夏曾佑先生《最新中學(xué)中國歷史教科書》出版,其分期概念雖借鑒西方,其分期原則卻源于中國傳統(tǒng)今文經(jīng)學(xué)“三世說”。夏曾祐先生再《中國古代史》中講:“本編亦尊今文學(xué)者,惟其命意與清朝諸經(jīng)師稍異,凡經(jīng)意之變遷,皆以歷史因果之理解之,不專在講經(jīng)也。”[20]537-539“三世者,進(jìn)化之象也。所謂據(jù)亂、升平、太平,與時俱進(jìn)是也。三世之歷史之情狀也。”[21]夏著以今文經(jīng)學(xué)之觀念詮釋文化史,所謂上古世,自草昧傳疑時代至于周末;中古世,從秦漢極盛時代至于唐代;近古世,始于宋至于當(dāng)今。其中古與近古分界的理路,也同近代日本漢學(xué)家內(nèi)藤湖南“唐宋變革論”有某種聯(lián)系。①參閱內(nèi)藤湖南《概括的唐宋時代觀》,載《日本學(xué)者研究中國史論著選譯》,中華書局1992年版。陳寅恪評夏曾佑《中國歷史》教科書云:“作者以公羊今文家的眼光評論歷史,有獨(dú)特見解。”[22]94柳詒征先生的中國文化史三期分法,將邃古至西漢分為第一期,東漢至明季為第二期,自明季迄于今為三期。將秦漢之前為上古時期,唐宋之前為中古時期,元以后為近世。此與梁啟超及夏曾佑先生之分期說,亦有相通之處。錢穆《中國文化史導(dǎo)論》分期,也與夏曾佑大體相近。民國初年北大史學(xué)系所開設(shè)之?dāng)啻罚稚瞎拧⒅泄拧⒔拧⒔浪钠冢鐚⒔捞貏e時期除外,仍未脫離“三世”基本架構(gòu)。教學(xué)說明則云:“中國上古史、中國中古史、中國近世史,史學(xué)系新班用之,分三年講完。蓋史學(xué)以時代相次,乃能明其原因結(jié)果,此乃應(yīng)用科學(xué)方法整理史學(xué)者。”②《國立北京大學(xué)講授國學(xué)之課程并說明書》,收入《北京大學(xué)日刊》第6分冊,民國9年10月19日,第3-4版。受西方觀念的沖擊,近代學(xué)界關(guān)于中國歷史分期,又多以中外關(guān)系變化為主要參照因素。梁啟超先生曾有“中國之中國”、亞洲之中國、世界之中國”三分說。這種分期方式,保留著今文經(jīng)學(xué)“三世說”的痕跡,卻又明顯帶有時代新意。
20世紀(jì)50年代,中國古代史分期問題,曾是歷史研究的“五朵金花”之一。關(guān)于中國歷史分期,出現(xiàn)三分、四分、五分等說法。馮天瑜先生所著《中國文化史》,以“三次轉(zhuǎn)折”為分期之表界。具體分為前文明時期;文明奠基及元典時期;一統(tǒng)帝國文化探索、定格期;胡漢、中印文化融會期;近古文化定型期;中西文化交匯及現(xiàn)代轉(zhuǎn)型期等。此種分期方式,雖已擺脫外來“五階段”理論的影響,考試關(guān)注文化自身變化的階段性特征,但分期標(biāo)準(zhǔn)與標(biāo)準(zhǔn)一致性原則如何遵循,仍有可討論之處。
不同時代、不同角度、不同學(xué)者的歷史分期,各有自己的標(biāo)準(zhǔn)。筆者以為,以文化史發(fā)展歷程為中心線索的歷史分期依據(jù),應(yīng)從時間變動、地域轉(zhuǎn)換與文化自身變革三個維度去尋找。其中時間進(jìn)化的維度,主要以朝代變革節(jié)點(diǎn),地域轉(zhuǎn)換的維度,應(yīng)多考慮文化交流與多元文化因素的加入,自身變革的維度,應(yīng)以文化內(nèi)在轉(zhuǎn)型為基本參照。科學(xué)的歷史包括文化史分期,無疑應(yīng)以文化自身變革主要學(xué)理依據(jù)。③見馮天瑜、楊華先生《中國文化史分期芻議》,《學(xué)術(shù)月刊》1998年第3期。
從時間維度看,轉(zhuǎn)型時期是歷史進(jìn)程的標(biāo)界點(diǎn)。余英時先生特別關(guān)注文化巨變時期,這樣的時期,正是歷史轉(zhuǎn)彎處。所謂“軸心時代”之說,在中國文化史上,即是第一次大轉(zhuǎn)型時代。學(xué)界特別看重的“唐宋之際變革”,是中古與近古的分界點(diǎn)即第二次轉(zhuǎn)型的節(jié)點(diǎn)。唐宋之際,既是朝代更替的標(biāo)界,也是近古歷史的起點(diǎn)。
歷史上的王朝更替,往往也以地域中心轉(zhuǎn)變與文化重心轉(zhuǎn)移為標(biāo)志。希臘與羅馬,東周與西周,是最為典型的。④同上。《春秋》所謂華夷文化之辨,亦與地域內(nèi)外之分密切相關(guān)。錢穆先生《國史大綱》論中國文化之拓展,十分重視地域轉(zhuǎn)換因素。地域、家族與文化,也是陳寅恪先生討論魏晉至隋唐歷史的重要參考指標(biāo)。⑤參閱陳寅恪先生《天師道與海濱地域之關(guān)系》,見三聯(lián)書店2001年4月版《陳寅恪集》之《金明館叢稿初編》;《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中亦有相關(guān)論述。陳寅恪先生在《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中指出,江左“自晉室南遷之后,本神州文化正統(tǒng)之所在”。陳先生認(rèn)為研究唐代歷史,“首先應(yīng)將唐史看作與近歷年史同等重要的課題來研究。蓋中國之內(nèi)政與社會受外力影響之巨,近百年來尤為顯著,……。因唐代與外國、外族之交接最為頻繁,不僅限于武力之征伐與宗教之傳播,唐代內(nèi)政亦受外民族之決定性的影響。故需以現(xiàn)代國改觀念來看唐史,此為空間的觀念。其次是時間上的觀念。近百年來中國的變遷報(bào)速,有劃時代的變動。對唐史亦應(yīng)持此態(tài)度,如天寶以前與天寶以后即大不相同,唐代的變動報(bào)劇,此點(diǎn)務(wù)須牢記。”[23]34此處涉及多元文化交流之義,“空間的觀念”與“時間上的觀念”,均被先生所看重。馮天瑜先生曾以“地中海時期”、“大西洋時代”說,“由西向東、從北徂南”說來作論述,強(qiáng)調(diào)的也是地域因素。國內(nèi)外學(xué)者關(guān)于唐宋社會轉(zhuǎn)型的討論,使分期建立在更為堅(jiān)實(shí)的歷史基礎(chǔ)上,也使得文化轉(zhuǎn)型與地域南北轉(zhuǎn)移連接在一起。
除時間與空間維度外,文化自身變革,不僅是歷史分期的又一依據(jù),且最為重要。春秋戰(zhàn)國時代,從文化層面觀,“道術(shù)將為天下裂”,乃精神層面之變;“禮崩樂壞”乃制度層面之變;世襲宗法系統(tǒng)的崩解則為社會層面之變。“不待始皇之并天下,而文武之道盡矣,”此即文化自身巨變的歷史證明。[25]在中古時期制度文化已然完善的前提下,唐宋之際,民間社會文化建設(shè)大規(guī)模展開,此亦是中國文化史的大變革時期。
從時間變化、地域轉(zhuǎn)移、文化自身變革三個維度考察,中國文化史實(shí)際經(jīng)歷了奠基、發(fā)展、成熟三個時期。中國文化第一次轉(zhuǎn)型,從東周時期開始,最終完成,則在秦代,故以周秦之交為第一、二期分界。第二次巨大變革期,在唐宋之際。此一變革“準(zhǔn)備期”在隋朝科舉制興起之際即已開始,至“唐中葉”庶民社會建立,轉(zhuǎn)型開始,到宋代社會文化重建完成而結(jié)束。從宋至清代中葉,均是近古文化的進(jìn)一步完善,本質(zhì)并未大的改變。文化“三期”說,與今文經(jīng)學(xué)的“三世”史觀,亦有相通之處。
中國文化史的完整過程,經(jīng)歷三個階段,各有自己的階段性特征。“文化史”上限,應(yīng)與一般史(普遍史)上限相區(qū)別。普遍史可前追,文化史應(yīng)自“人文化成”開始講。從考古學(xué)意義上講,上古文化史可上推至“新石器時代”,孔子論中國文化,則自堯舜始。張橫渠曰:“上古無君臣尊卑勞逸之別,故制以禮,重衣裳而天下治,必是前世未得如此,其文章禮樂簡易樸略,至堯則煥手其有文章。”[24]這是對上古民族精神奠基歷史的贊許,也是對中國文化史上限之特別限定。上古文化之開端,自堯舜始。上古文化史之下限,則在東周末年,這也是民族精神奠基時期。周公制禮作樂,是華夏民族最終形成的關(guān)鍵。夫子西周鑒于夏、商兩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之論,即是對三代“文治教化”的肯定。禹夏國家體制奠基,西周華夏民族意識的覺醒與春秋儒家學(xué)統(tǒng)的建立,乃是上古歷史的主題。上古文化的最重要成就,是民族精神載體即“學(xué)統(tǒng)”的確立。以《春秋經(jīng)》為載體的孔門儒學(xué)體系的建立,不僅是三代文治之自覺,是“華夷之辨”的清醒,亦是中華學(xué)統(tǒng)確立的標(biāo)志。春秋時代孔子對上古三代歷史文獻(xiàn)的系統(tǒng)研究整理與廣泛傳播,為中國文化“學(xué)統(tǒng)”的創(chuàng)立,奠定了堅(jiān)實(shí)的學(xué)術(shù)基礎(chǔ)。所謂“軸心時代”,即可作為歷史反思、精神意識覺醒與民族文化意識形成的體現(xiàn)。
中古時期的歷史轉(zhuǎn)變,從春秋戰(zhàn)國之際即已開始,正式開端,自秦統(tǒng)一始,中古史下限則在唐代末年。以《周禮》為藍(lán)本的“三省六部”政治體制的確立,以家族文化民族文化依托的局面形成及儒家道統(tǒng)意識的日益覺醒,是中古時期的歷史主題。但這一時期歷史的最大貢獻(xiàn),是制度建設(shè)的展開。中國文化“政統(tǒng)”的確立,無疑是中古歷史的主要成就。陳寅恪先生在《隋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上篇《統(tǒng)治階級之氏族及其升降》之開篇處云:“唐源統(tǒng)出于夷狄,故閨門失禮之事不為異。”先生又云:“即然此簡略之語句亦含有種族及文化之問題,而此二問題實(shí)李唐一代史實(shí)關(guān)系之所在,治唐史不可忽視者也。”[13]政治制度之建設(shè),同樣與文化自覺分不開。從漢代至隋唐的政治制度建設(shè),均與文化建設(shè)相伴隨。《唐六典》的頒布,即是中古時期制度文化建設(shè)之成就體現(xiàn)。
唐代中葉開始的社會轉(zhuǎn)型,近代以來頗受海內(nèi)外學(xué)界重視。真正意義上的近古社會,則從宋代才正式開始。①海外學(xué)者如謝無耐、內(nèi)藤湖南則主唐宋之際。參閱馮天瑜先生《中國文化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12月版,第145-146頁。儒家道統(tǒng)觀念之最終確立,文官體制之完善與民間社會禮制化之完成,是這一階段歷史的主題。如果說上古文化重在精神奠基,中古文化重在制度建設(shè),近古民間社會之文化重建乃至以上古三代為目標(biāo)的“人文化成”的實(shí)現(xiàn),則是最重要成就。“百姓日用而不知”之“俗統(tǒng)”的最終形成,也是中國文化走向成熟的標(biāo)志。②參閱拙稿《民間社會之文化重建——以朱子之人生志業(yè)為案例》,《中國社會歷史評論》2010年卷。陳寅恪先生講:“蓋自漢代學(xué)校制度廢弛博士傳授之風(fēng)止息以后,學(xué)術(shù)中心移于家族,而家族復(fù)限于地域,故魏晉南北朝之學(xué)術(shù)宗教皆與家族地域二點(diǎn)不可分離。”[13]17此處所講,針對的是中古亂世,對應(yīng)的是門閥世家。華夏禮樂文化的普遍家族化,則自宋開始。宋代以后以鄉(xiāng)賢、鄉(xiāng)約、家族為主導(dǎo)之禮樂書香社會,已成為學(xué)術(shù)文化與制度文化的深厚社會為基礎(chǔ)。從宋至清,近古文化最終定型。清代中葉《紅樓夢》的問世,是中國社會文化重建大業(yè)最終完成的藝術(shù)寫照,也是文化集成“時代”“歷史全程”完成的體現(xiàn)。
中國古典文化經(jīng)歷了上古、中古、近古即奠基、規(guī)范與化成三個不同歷史時期,也經(jīng)歷了相對完整的歷史“全程”。文化史三期演化,從學(xué)統(tǒng)講,以孔子、董仲舒、朱子三位巨人出現(xiàn)為標(biāo)志,經(jīng)典儒學(xué)、制度儒學(xué)、社會儒學(xué)因而形成;從政統(tǒng)方面講,以西周、漢唐、宋明為節(jié)點(diǎn),其中漢唐時代最為關(guān)鍵;從民間俗統(tǒng)講,經(jīng)歷上古文化萌芽、中古發(fā)展與近古化成,其中近古之宋明時代最值得關(guān)注。晚晴西方文化涌入,徹底改變了中國文化自身的發(fā)展軌道與歷程。③參閱拙稿《民間社會之文化重建——以朱子之人生志業(yè)為案例》,近年出現(xiàn)的“三層儒學(xué)”之說,以韓星先生之論最為清晰,可參考。“三世”之后的近代變革,已超出中國文化史自身的發(fā)展邏輯,自當(dāng)另論。所謂“更化”之論,正可概況近百年之歷史文化巨變。然從大的過程看,從“中華一體、內(nèi)外合一、四海一家”的《春秋》“大同”史觀看,近百年的中西文化沖突時代,仍為超出“人文化成天下”之第三期歷程。④錢穆先生有第四期之說,見《中國文化史導(dǎo)論》第253頁,筆者以為,此一時期,仍可置于中國文化第三期之“更化”階段討論。
自此意義上觀,福山“歷史終結(jié)說”,確有其理論價值與借鑒意義。“歷史終結(jié)論”源于法蘭西斯·福山 1988年所作的一次題為“歷史的終點(diǎn)”的講座,之后寫成《歷史的終結(jié)》一文,1989年在美國新保守主義期刊《國家利益》發(fā)表,標(biāo)志“歷史終結(jié)論”作為一個理論體系正式問世。西方意義上的“歷史終結(jié)”說,與中國文化中的“太平世”目標(biāo)說,確有相合之處。包涵著最終目標(biāo)的儒家歷史觀,不僅關(guān)注歷史過程,更關(guān)注“歷史進(jìn)程”與“歷史全程”。《春秋》止于“獲麟”,《毛序》曰:“《麟趾》《關(guān)雎》之應(yīng)也。《關(guān)雎》之化行,則天下無犯非禮,雖衰世之公子,皆信厚如《麟趾》之時也。”司馬炎所擬修史計(jì)劃,“上述陶唐以來,至于麟止”。①見《史記·太史公自序》。司馬炎之史觀,更近《春秋》。蔡邕《琴操》載,夫子見麒麟,乃歌曰:“唐虞世兮麟鳳游,今非其時來何求?麟兮麟兮我心憂……”朱子《詩集傳》曰:“若《麟之趾》,則又王者之瑞。有非人力所致而自至者,故復(fù)以是終焉。”“簫韶九奏,麟游鳳儀”,乃“太平世”之象,故有麒麒出,祥瑞現(xiàn)。諸文“備”矣,天下“平”矣,故歷史“終”焉。《春秋》備于“獲麟”,標(biāo)志著文化與歷史使命的完成。太平世文化理想實(shí)現(xiàn)、歷史“全程”才可“終結(jié)”。②參閱拙稿《文化史視野中的<春秋經(jīng)>》,原載《遼東學(xué)院學(xué)報(bào)》2010年第5期,轉(zhuǎn)見2011年第3期人大復(fù)印資料《歷史學(xué)》第3期。
要之,文化“三世”與文化史“三期”之“全程”歷史,是孔子所著《春秋經(jīng)》之歷史總體框架,也是中國文化之命運(yùn)歸宿。以今文經(jīng)學(xué)的“三世”分期為基本參照,以時間變化、地域轉(zhuǎn)移和歷史文化的階段性特征為衡量標(biāo)準(zhǔn),中國古典文化經(jīng)歷了上古、中古、近古即奠基、規(guī)范與化成三個不同歷史時期。③見《余英時文集》,廣西師大出版社2014年6月版,第十二卷第49頁。重回中國傳統(tǒng)之“三世”分期,以上古、中古、近古劃分全部古典文化史,即是本講義分期之選擇。
三、編著體例:“一統(tǒng)”貫于“三統(tǒng)”
晉杜預(yù)《春秋經(jīng)傳集解序》云:“其發(fā)凡以言例。皆經(jīng)國之常制,周公之垂法。史書之舊章。仲尼從而修之,以成一經(jīng)之通體。”章學(xué)誠云:“吾于史學(xué),蓋有天授,自信發(fā)凡起例,多為后世開山,而人乃擬吾于劉知幾。不知劉言史法,吾言史意,劉議館局纂修,吾議一家著述,截然兩途,不相入也。”[25]錢穆先生在《國史大綱·書成自記》中言:“欲求簡要明當(dāng),則于重之國學(xué),先必有所取舍。又必先有一系統(tǒng)之觀點(diǎn),以為其取舍之標(biāo)準(zhǔn)。必先主一‘體’,乃能有所取裁。凡所裁之寬狹長短,一視與其‘體’之相副相稱以為度。”[14]余英時先生講:“陳先生治佛教及文學(xué)史,最重視著作的體例。”[12]238著作體例,為歷代著學(xué)人所看重,《中國文化史講義》之編著,體例確定同樣十分重要。目前看,可供選擇者,主要有如下數(shù)種。
其一,具有普遍史意義的史著。可分三種情形,首先是編年體“通史”。孔子所著之《春秋》,為儒門之經(jīng)典,亦是歷代史學(xué)著作包括編年史之典范。梁啟超先生認(rèn)為:“舊史皆詳于政事而略于文化。”[26]290《春秋》雖以政治事件為主,但內(nèi)容遠(yuǎn)超此范圍。從某種意義講,作為編年體史著的《春秋經(jīng)》,亦可視作文化史經(jīng)典。④參閱拙稿《文化史視野中的<春秋經(jīng)>》。所謂“知我”、“罪我”,即可為證。這部具有“廣義文化史”意義的史書,涉及禮樂、歷數(shù)、天文、地理等各個方面。以史體統(tǒng)史料,以史料見史心,即是《春秋》之史法。作為《春秋》之后另一部影響巨大的編年體史著,“《通鑒》,不特紀(jì)治亂之跡而已,至于禮樂、歷數(shù)、天文、地理,尤致其詳。”[13]488從廣義文化史角度觀,亦無不可。《春秋》及《通鑒》雖側(cè)重于政治,文化精神則貫穿其中。此種著作方式,對于現(xiàn)代學(xué)人之影響亦十分明顯。民初納入北大文科的國史編纂處,其首要工作是編纂通史與民國史長編。長編纂輯又分為政治史、文明史兩種。政治史以年表、大事記、志三類為主(民國史加列傳),文明史分為經(jīng)濟(jì)、風(fēng)俗、宗教、科學(xué)、哲學(xué)、文學(xué)、美術(shù)等類,⑤《國史編纂略例》,《北京大學(xué)日刊》民國7年3月5日。轉(zhuǎn)見高平叔先生編《蔡元培史學(xué)論集》,湖南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142頁。恰與廣義文化史相通。然而從體例觀,以年月為主線的編年體史著,并不適合于中國文化史編著。
其次是紀(jì)傳體“正史。”傳統(tǒng)中國的“正史”即廿四史,具有全面性,綜合性意義,是古典史學(xué)著作中最為標(biāo)準(zhǔn)的普遍史,同樣涉及禮樂制度等文化史內(nèi)容。司馬遷《史記》“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之理想,也是中國文化史編著的指導(dǎo)思想。梁啟超先生曾指出,傳統(tǒng)史學(xué)有“四弊”:“一曰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國家。吾黨常言,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譜。二曰知有個人而不知有群體……”正如梁啟超先生所言,“正史”以帝王將相即精英層面為主體,并不能反映歷史全體之貌,文化精神并非其關(guān)注之重點(diǎn)。作為傳統(tǒng)普遍史的典范,正史之體例同樣不適于中國文化史編著。
再次是現(xiàn)代意義上的普遍史或全史,其實(shí)這種體例之史著,乃是西方史學(xué)觀念引進(jìn)之后的產(chǎn)物。1901年9月30日,梁啟超在《清之義報(bào)》發(fā)表《中國史緒論》。其中云:“前世史家,不過記載事實(shí);近世史家,比說明所記事實(shí)之關(guān)系,其原因結(jié)果。前世史家,不過記述一二有權(quán)力者興旺隆替之事,雖名為史,實(shí)不過一人一家之譜牒;近世史家,必探索人間全體之運(yùn)動進(jìn)步,即國民全部之經(jīng)歷及其相互關(guān)系。”1902年2月8日,梁先生在《新民叢報(bào)》發(fā)表《新史學(xué)》。其中云:“于今日泰西通行諸學(xué)科中,為中國所固有者,惟史學(xué)。史學(xué)者,學(xué)問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國民之明鏡也,愛國心之源泉也。”“善為史者,必研究人群變化之現(xiàn)象,而求其公理公例之所在。”[21]梁啟超先生所提倡之新史著,即要求具有觀察“人群變化”之普遍意義。梁啟超先生曾講,“普遍史即一般之文化史”。梁氏《中國文化史》撰寫設(shè)想,即與此觀念相關(guān)。陳寅恪先生亦曾有著“通史”(為《通鑒》)之愿,陳先生所設(shè)想中的通史或普遍史,一如所撰之政治史著作,文化精神必然貫穿其中,惜未能完成。當(dāng)下之大學(xué)通史或普遍史教材,經(jīng)濟(jì)、政治、軍事、外交等無所不包,卻無貫穿其中的民族精神在,自然也不是中國文化史撰寫的體例選擇。
其二,專科文化史,亦即學(xué)科意義上的專門史。在現(xiàn)代學(xué)科體系中,文化史與哲學(xué)史、思想史等并列,乃是標(biāo)準(zhǔn)的專門史。近代西方有思想文化史(intellectual history)學(xué)科,在目前通行的史學(xué)學(xué)科目錄中,“二級學(xué)科”中即有包括思想文化史在內(nèi)的專門史一科。然在中國舊式學(xué)者眼中,專門的思想文化史,并非專門學(xué)問。陳垣先生曾云:“思想史、文化史等頗空泛而弘廓,不成一專門學(xué)問。……欲成一專門學(xué)者,似尚需縮短戰(zhàn)線,專精一二類或一二朝代,方足動國際而重出遠(yuǎn)。不然,雖日書萬言,可以得名,可以啖飯,終成為講義的教科書的,三五年間即歸消滅,無當(dāng)于名山之業(yè)也。”[27]354-355陳垣先生關(guān)于思想文化史的評論,建立在以考證史學(xué)為標(biāo)準(zhǔn)的基礎(chǔ)上。他所理解的專門史,仍是狹義的文化史。這樣的思想文化史,局限于狹義層面,并不能反映中國文化史全貌。文化無所附托,似無根之‘游魂’,顯然亦難做體例選擇對象區(qū)別于嚴(yán)格意義專門史,還有一種合學(xué)科專門史于一體的史著。在《<國學(xué)季刊>發(fā)刊宣言》中,胡適先生對于國學(xué)與中國文化史有如下表述:“我們理想中的國學(xué)研究,至少有這樣一個系統(tǒng):中國文化史:1、民族史2、語言文字史3、經(jīng)濟(jì)史4、政治史5、國際交通史6、思想學(xué)術(shù)史7、宗教史8、文藝史9、風(fēng)俗史10、制度史。”胡先生并在文中講:“國學(xué)的方法是要用歷史的眼光來整理一切過去文化的歷史。國學(xué)的目的是要做成中國文化史。國學(xué)的系統(tǒng)的研究要以次為歸宿。”[28]708胡適先生心目中的國學(xué)著述,無所不包。胡先生以為,如此即可構(gòu)成以專史為學(xué)術(shù)取經(jīng)的中國文化史系統(tǒng)。胡適之先生還曾講:“我們所提倡的‘整理國故’,重在‘整理’兩個字,……是用無成見的態(tài)度,精密的科學(xué)方法,去尋求那以往的文化變遷沿革的條理線索,去組成局部的或全部的中國文化史。”[28]胡適之先生所倡導(dǎo)的“系統(tǒng)”中國文化史,是現(xiàn)代科學(xué)史觀視域中的中國文化史,其實(shí)也是缺少精神貫通的拼盤性質(zhì)的廣義文化史。
近年出現(xiàn)的另一種特殊專門史,是廣義背景下的狹義文化史。目前被作為高校教材使用的馮天瑜先生所著之《中國文化史》,重點(diǎn)敘述學(xué)術(shù)思想文化演變的歷程,對精神世界與具象世界的“雙向”互動,也給予關(guān)注。其研究的主要對象,是“在廣義文化背景下研究狹義文化(精神文化)”。①見馮天瑜先生《中國文化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12月版,第19頁。此種體例之史,實(shí)是廣義文化史背景之下的俠義文化史。從廣義文化與俠義文化結(jié)合的角度看,已有改進(jìn)之處。但依然是狹義上的專門文化史,并不足以反映中國文化史之全體之貌,同樣有明顯的體例缺陷。
其三,以狹義為精神統(tǒng)領(lǐng)的廣義文化史。相對于一般史著,文化史最應(yīng)重視者是歷史之“義”。“義”是文化主場,文化理想,也是文化精神。歷史之“義”不僅可顯材料之精神,亦是組織零碎材料的理論框架與觀念體式。史中之“義”,也最為孔子所看重。孟子論《春秋》云:“其文則史,其意則丘竊之矣。”孟子所理解的《春秋》,可從文、事、義三個層面觀。文是敘事方式;事為歷史事實(shí);義乃文化精神。繼承這一傳統(tǒng),后世史家多以孔孟所倡導(dǎo)之“義”為主,歐陽修《新五代史》與鄭思肖“所南心史”均為典型。對于史著之“義”論述最詳者,是清代中期的章學(xué)誠。章學(xué)誠《文史通義·內(nèi)篇答客問上·言公》上篇曰:“夫子因魯史而作《春秋》。孟子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自謂竊取其義焉耳。’載筆之士,有志《春秋》之業(yè),固有久之求,其事與文,所以藉為存義之資也.。[25]卷五云:“夫事即后世考據(jù)家之所尚也,文即后世之問章家之所重也。然夫子所取不在彼而在此,則史家著述之道,豈可不求義意所歸。”[25]。又云:“史所貴者義也,而所具者事也,所憑者文也……非識無以斷其義……能具識者必知史德。德者何?謂著書者之心術(shù)也。”以“心術(shù)”所統(tǒng)領(lǐng)之史,亦即鄭思肖所謂之“心史”。余英時先生在《章實(shí)齋與柯林伍德的歷史思想》文中講,柯氏“把人類的行為分為兩類,一為‘自然過程’,如飲食男女之類,此非歷史學(xué)家所欲過問之事;另一則為‘歷史過程’,蓋即人類自覺地創(chuàng)造的種種習(xí)慣與制度之類——易言之,即文化耳——這才是歷史研究的主題”。柯氏將文化作為“歷史主題”的思路,與章學(xué)誠重視歷史之“義”的精神,亦有相通之處。[12]193龔自珍《尊史》云:“出乎史,入乎道,欲知道者,必先為史。”[29]所謂史之“道”,亦可謂史之“義”。
重視歷史之“義”的傳統(tǒng),在中國近現(xiàn)代學(xué)術(shù)史上,仍在延續(xù)。章太炎先生論文化與民族精神云:“仆以為民族主義如稼穡然,要以史籍所載人物、制度、地理、民俗之類為之灌溉,則蔚然以興矣。”[30]371梁啟超先生云:“夫所貴重史者,貴其能敘一群人相交涉相競爭相團(tuán)結(jié)之道,能述一群人所以休息生息同體進(jìn)化之狀,使后之讀者愛其群,善其群之心,油然生焉。三曰知有陳跡而不知有今務(wù)。四曰知有事實(shí)而不知有理想。……史之精神為何:曰理想是已。”[21]陳寅恪先生曰:“以往研究文化史有二失:舊派失之滯。舊派所作中國文化史,……不過抄抄而已。其缺點(diǎn)是只有死材料而沒有解釋。讀后不能使人了解人民精神生活與社會制度的關(guān)系。新派失之誣。新派是留學(xué)生,所謂‘以科學(xué)方法整理國故’者。新派書有解釋,看上去似很有條理,然甚危險(xiǎn)。”[22]陳先生《王觀堂先生挽詞序》云:“吾中國文化之定義,具于《白虎通》。三綱六紀(jì)之說,其意義為抽象理想最高之境,猶希臘柏拉圖所謂Idea者”[13]陳寅恪先生所講之?dāng)啻罚瑯又匾暁v史之“義”。在陳先生看來,政治制度史撰寫,根本上是一種文化史書寫。《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唐代政治史述論稿》,均是以斷代政治史形式出現(xiàn)的史學(xué)經(jīng)典,視其為斷代文化史經(jīng)典,也無不可。在《唐代政治史述論稿》“自序”中先生講:“夫吾國舊史多屬于政治史類,而《資治通鑒》一書,犬為空前杰作。今草茲稿,可謂不自量之至!然區(qū)區(qū)之意,僅欲令初學(xué)之讀《通鑒》者得此參考,或可有所啟發(fā)。……”《通鑒》所超出一般政治史者,正在于其中存歷史之“義”。《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上篇卷首曰:“唐源流出于夷狄,故閨門失禮之事不以為異。朱子之語頗為簡略,其意未能詳知。然即此簡略之語句亦含有種族及文化二問題,而此二問題實(shí)李唐一代史事關(guān)鍵之所在,治唐史者不可忽視者也。”[13]余英時先生講:“他的重點(diǎn)始終是放在廣義的文化史方面。”①見《余英時文集》第五卷,廣西師范大學(xué)出版社,2006年版第212頁。談及“晉至唐文化史”時講陳先生講:“本課程講論晉至唐這一歷史時期的精神生活與物質(zhì)生活的關(guān)系,精神生活包括思想、哲學(xué)、宗教、藝術(shù)、文學(xué)等;物質(zhì)環(huán)境包括政治、經(jīng)濟(jì)、社會組織等。”②見《陳寅恪先生編年事輯》第80頁;另,“通史”與“專史”,見《各國學(xué)術(shù)之現(xiàn)狀及清華之職責(zé)》,載(《叢稿二編》第361頁。這樣的史著,即是貫穿著歷史之“義”的文化史。作為通史存在的錢穆先生的《國史大綱》之所以受到世人稱道,亦以其“義”之存也。錢穆先生《國史大綱》“引論”認(rèn)為,“科學(xué)”史學(xué),“往往割裂史實(shí),為局部詳細(xì)之追究。以活的人事,為死的材料。治史譬如治巖況,治電力,既無以見前人整段之活動,亦無先民文化精神,漠然無所用之情。”[14]為錢穆先生所看重的歷史文化精神,也同樣貫徹到他的全部史著撰寫實(shí)踐中。重“義”之傳統(tǒng),在中國文化史之現(xiàn)代書寫中,亦有實(shí)際體現(xiàn)。鑒于舊時代史書為“皇帝家譜”之弊端,柳詒徵先生所撰之《中國文化史》,以“民族社會變遷進(jìn)步”為主線,“舉凡教學(xué)、文藝、社會、風(fēng)俗以致經(jīng)濟(jì)、生活、物產(chǎn)、建筑、圖畫、雕刻”等,均納入取材范圍,這樣的文化史,體例雖近廣義文化史,然其取材,仍以“民族全體之精神所表現(xiàn)者”為選擇對象。③參閱柳詒徵先生《中國文化史》“緒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10月版。
如果說廣義文化史近于一般意義上的普遍史,狹義文化史是以精神文化為統(tǒng)領(lǐng)的專門史,以狹義為精神統(tǒng)領(lǐng)的廣義文化史,既近于普遍史的文化史相區(qū)別,也與時下流行的狹義文化史不同。此一學(xué)術(shù)視域中的中國文化史,不僅有“文”之結(jié)構(gòu),有“事”之陳述,更有“義”——華夏歷史文化傳統(tǒng)之精神表達(dá)。韓愈在《原道》中說:“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所謂道也,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以是傳之孔子,孔子以是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31]其實(shí),中國文化“道統(tǒng)”,并非僅存于圣賢一心之傳,而是貫穿于學(xué)術(shù)、制度與社會生活之中,“道統(tǒng)”即是民族精神。以精神文化為統(tǒng)領(lǐng)且集學(xué)術(shù)文化、制度文化、社會文化三位一體的中國文化史,是專門史角度即具有專門史品格的普遍史,是中國文化從奠基、鞏固到成熟的“三世”演化全程史,也是承載著華夏民族文化“道統(tǒng)”的精神史。換言之,在此總體設(shè)想之下的中國文化史,是本于《春秋》大義即以中華文化精神——文化“道統(tǒng)”為統(tǒng)領(lǐng)的文化史,是陳寅恪先生所看重的承載著華夏精神的“所南心史”,也是站在“人文更化”之時代立場所撰寫的觀照“風(fēng)、雅、頌”文化“三層”與“據(jù)亂、升平、太平”歷史“三世”之“全程”的“一以貫之”的民族“精神史”。④參閱拙稿《文化史視野中的<春秋經(jīng)>》。
百余年前,在強(qiáng)大的外來文明沖擊之下,數(shù)千年傳承不斷的中華文明迅速解體。處此“天翻地覆”之時代,保存故國歷史,恢復(fù)民族文化記憶,已成為華夏仁人志士的共同心愿。《史記·太史公自序》云:“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jì),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bǔ)敞起廢,王道之大者也。”[32]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有了新的內(nèi)涵,“存亡繼絕”的文化傳承意義,更為重要。文明復(fù)興的精神主導(dǎo)是文化,文化重建是中華文明復(fù)興的基礎(chǔ)工程。文化史撰寫,是華夏傳統(tǒng)人文學(xué)術(shù)重建的重要措施,是華夏文化重建的重要途徑,也是華夏民族文化“道統(tǒng)”傳承延續(xù)的文本依托。編著一部本于中國傳統(tǒng)且體現(xiàn)時代特色的《中國文化史》,是為“為往圣繼絕學(xué)”之使命所托,是無愧于先人、對得起后代的人生志業(yè)。一部具有“普遍史”容量、“全程史”長度與“精神史”縱深的《中國文化史》,也是本講義之編著體例追求。
[1]周易[M]. 北京: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1999.
[2]尚書正義[M]. 北京: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1999.
[3]禮記正義[M]. 北京: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1999.
[4]日知錄集釋[M]. 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3.
[5]莊子集釋[M].北京:中華書局,1961.
[6]姚春鵬. 黃帝內(nèi)經(jīng)[M]. 北京:中華書局,2010.
[7]荀子集解[M]. 北京:中華書局,2007.
[8]劉向. 說苑[M]. 合肥:黃山書社,1993.
[9]蕭統(tǒng). 文選[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10]錢穆. 中國文化史導(dǎo)論[M]. 北京:商務(wù)印書館,2003.
[11]文化的解釋[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12]余英時文集[M]. 桂林:廣西師大出版社,2014.
[13]陳寅恪. 唐代政治史述論稿[M]. 北京:三聯(lián)書店出版社,2001.
[14]錢穆. 國史大綱[M]. 北京:商務(wù)印書館,1996.
[15]毛詩正義[M]. 北京: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1999.
[16]姚際恒. 詩經(jīng)通論[M].北京:中華書局,1958.
[17]周禮注疏[M]. 北京: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1999.
[18]梁啟超. 中國現(xiàn)代學(xué)術(shù)經(jīng)典:梁啟超卷[M]. 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
[19]傅斯年.傅斯年史學(xué)論著[M]. 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14.01.
[20]朱維錚. 周予同經(jīng)學(xué)史論著選集[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
[21]梁啟超. 中國現(xiàn)代學(xué)術(shù)經(jīng)典:梁啟超卷[M]. 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
[22]蔣天樞. 陳寅恪先生編年事輯[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23]北大中國中古史研究中心. 紀(jì)念陳寅恪先生誕辰百年學(xué)術(shù)論文集[M]. 北京: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1989.
[24]張載集[M]. 北京:中華書局,1978.
[25]章學(xué)誠. 文史通義[M]. 北京:中華書局,1994.
[26]梁啟超. 中國近三百年學(xué)術(shù)史[M]. 北京: 中國書店,1985.
[27]陳智超. 陳垣來往書信集[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28]胡適. 中國現(xiàn)代學(xué)術(shù)經(jīng)典:胡適卷[M]. 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
[29]龔定庵 全集類編[M]. 北京:中國書店, 1991.
[30]章太炎. 章太炎全集(三)[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
[31]韓愈. 原道[M]//韓昌黎全集:卷11. 北京:中國書店,1991.
[32]司馬遷. 史記[M]. 北京:中華書局,1959.
(責(zé)任編輯:蘇紅霞 校對:周冰毅)
K203
A
1673-2030(2017)02-0067-11
2016-11-05
喬福錦(1956—),男,河北邢臺人,邯鄲學(xué)院地方文化研究院太行山文書研究中心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