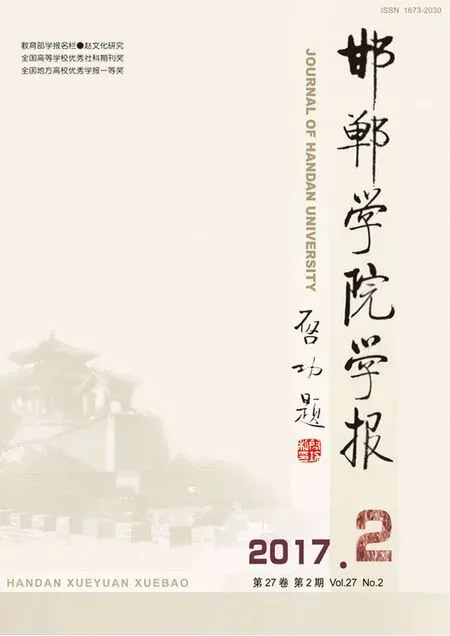論《繁花》與中國古代文論的關聯
楊杰蛟
(湖南師范大學 文學院,湖南 長沙 410081)
論《繁花》與中國古代文論的關聯
楊杰蛟
(湖南師范大學 文學院,湖南 長沙 410081)
從中國古代文論的視角來解讀金宇澄的《繁花》可以發現,其繼承了儒家“詩教”為核心的文學觀,以紀傳體的手法塑造人物、結構小說,大量借鑒話本、擬話本的敘事形式,在推動傳統文論現代發展的同時實現了對于上海故事的全新講述。
金宇澄;《繁花》;“詩教”;紀傳體;話本擬話本
作為一位常年從事編輯工作的作家,金宇澄清楚地意識到,近百年以來西方文藝理論與文學經典深刻影響到了中國小說的面貌,如何重建中國傳統小說的敘事模式顯然成為值得思考的問題。正如他自己在接受訪談時所言,“很多年來,我們也已經習慣讀西方式樣的文本敘事,《繁花》是傳統話本模樣……是向傳統敘事致敬。”[1]7基于這樣自覺的創作追求,中國古典文學與文化思維在觀念與筆法上令《繁花》具有了典型的傳統民族特征,這成為《繁花》在當下市場環境中贏得讀者的關鍵因素,也為如何更好地講述“中國故事”提供了有益的藝術參照與啟示。
一、“溫柔敦厚”的“詩教”傳統
中國文化自古以來便受到經世致用思想的根本性制約,知識分子普遍表現出一種針砭時弊、心憂天下的情懷,道德教化由此也就成為各大藝術門類共同遵循的審美標準和價值尺度。以《詩經》開創現實主義文學傳統為起點,韓愈、柳宗元、周敦頤、龔自珍、梁啟超等人均從不同層面對這一藝術主張加以推崇與發揚。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受到儒家所倡導的“中庸”哲學思想影響,“中和之美”成為中國古代藝術所堅持的審美準則,這便使得“詩教”傳統自然而然地具有了“溫柔敦厚”的特點。正因為此,屈原才在《離騷》中將對黑暗政治現實環境的抨擊轉換為“上下求索”的動力,曹雪芹的《紅樓夢》則在揭露封建文化行將就木的必然結局時滲透出對筆下人物的深切憐憫之意,可以說,這種堅持“溫柔敦厚”的“詩教”觀念在金宇澄的《繁花》中又一次得到了承續。
《繁花》所要表現的是上海這座現代化都市在1960年代至1990年代末近40年期間的世事變幻,正如有論者指出的那樣,“小說的主體故事分成兩個時代,六、七十年代多半是悲劇,八、九十年代以鬧劇為多”,[2]150如果說前一時期的“悲劇”還可歸咎于外部社會環境,那么后一時期的“鬧劇”則完全由人類自身的欲望所造成,金宇澄恰是在這樣兩個看似并不相同的時代中審視著蕓蕓眾生的人生遭際與精神狀態。
在小說的單數章中,作者集中筆墨完成的是又一部“文革”敘事,普通上海市民的日常生活景象成為故事的核心,緊張的外部政治環境將正常的人性徹底扭曲。阿寶的父親曾經毅然決然地投入民族解放斗爭的洪流之中,但由于有過被捕入獄的經歷,自然成為不被信任的對象,最終被發配至上海市郊的曹楊新村,長期的批斗與刁難使得他徹底喪失原有的反抗精神。當哥哥嫂子從香港回大陸探親之時,他所選擇的是將親人趕出家門以求自保,一句“不響”反射出的正是其內心的矛盾與恐懼。與滬生青梅竹馬的姝華從吉林返城之后已經精神錯亂,盡管她在上山下鄉時的遭遇早已不得而知,但卻不難想象這個曾經喜好閱讀老書、外國書的年輕人究竟經歷了怎樣不堪回首的劫難。
而在小說的雙數章中,物欲化的市場經濟時代開始成為批判的鋒芒所指,雖然小說表面上只不過是不厭其煩地描述著一場又一場大同小異的飯局,但人物對于物欲和情欲的執著才是每一次飯局上真正的主菜。梅瑞原本是滬生的女朋友,但當結識身為公司老板的阿寶之后她的興趣便隨之發生了轉移,更具荒誕意味的是,她最終陷入的竟是自己姆媽與小開之間的情感糾葛,漫長的牢獄生活成為她此后人生的全部內容。至于陶陶的女友小琴更是如此,當她意外身亡之后,陶陶在翻閱警方轉交的遺物時終于意識到所謂的愛情原本并不存在,“保持笑容”不過只是小琴欺騙自己的一道把戲而已。
事實上,類似的情節安排在當代作家的創作中并不罕見,例如余華的《兄弟》便同樣是以“文革”和改革開放作為故事背景來記錄中國人的某種生存狀態,小說前半部的殘酷與后半部的荒誕恰恰代表著余華對這兩個時代最深刻的認知,因此,他依然遵循著過往的寫作經驗將這樣的生存景象盡可能地變形、夸張處理,以期最大限度地實現作品的精神意圖與批判功能。但是,金宇澄并未采取同樣的敘事策略,“《繁花》主要的興趣,是取自被一般意義忽視的邊角材料——生活世相的瑣碎記錄,整體上的‘無意義’內容,是否存在有意義,興趣在這一塊,看城市的一種存在,不美化,也不補救人物的形象,提升‘有意義’的內涵,保持我認為的‘真實感’”,[3]4因此,蓓蒂為尋找鋼琴最終化為金魚的童話想象成為對“文革”歷史的最強烈抗議,李李在復仇之后卻選擇剃度出家也讓浮華時代中的食客們重新陷入思索,節制而不乏力度的描述既避免讓讀者沉湎于簡單的感官刺激,又有效地實現了諷喻與規勸的效果。正是這種人道主義的悲憫情懷使得《繁花》在對人物悲劇性命運的表現過程中完成了對外部環境與人性本身之惡的批判,同時又以節制與含蓄的敘事之美復現了“溫柔敦厚”的詩教原則。
二、綱舉目張的“列傳”筆法
司馬遷的《史記》作為中國第一部紀傳體通史,打破了此前史書大多以記事為核心的編年體形式,首次嘗試以人物為中心來再現歷史,使得紀傳體這一敘述方式在中國傳統文學中得以占有一席之地,進而深刻影響到后世作家的創作。現代作家沈從文便指出:“過去我受《史記》影響深……《史記》列傳中寫人,著筆不多,二千年來還如一幅幅肖像畫,個性鮮明,神情逼真。”[4]318而在金宇澄這部近40萬字的《繁花》中,他同樣明顯借鑒了《史記》塑造人物的列傳手法,先后描寫了滬生、阿寶、小毛、陶陶、蓓蒂、姝華、梅瑞等十余個主要人物的情感歷程,為上海爺叔作傳成為作者的寫作目的之一,可以說,正是這些個體生命的喜怒哀樂才讓上海這座大都市在紙面上逐漸生動起來。
《史記》的人物傳記之所以能得到后世的諸多褒揚,首先來源于其擺脫了過往多為帝王將相立傳的寫法,而是將以閭巷之人為代表的下層人物納入自己的視野。在金宇澄的筆下,中國社會面貌的變遷并不一定需要借助于典型的宏大敘事才能加以表現,小人物命運的偶然性中原就包含著對時代大潮的順應與抗拒,這顯然同司馬遷敘事寫人的觀念暗然相合。滬生、阿寶、小毛三人的成長故事是小說的情節發展主線,毫無疑問的是,他們并不直接決定著中國歷史的走向,然而,小說最后三人的命運卻表現出極大的相似性,墮入虛無成為共同的結局。“人命不可強求。現在我做門衛,小股票炒炒,滿足了。”小毛在生命最后階段的感慨隱然暗示著個體在面對紛繁多變的歷史風云時的無奈和落寞。
“常規化的深刻,不要也罷,我借古畫,對人物的認識,寥寥幾筆,畫一個人,散點透視”。[3]4金宇澄的表述點出了《繁花》對《史記》的又一繼承之處,即重視以簡潔質樸的細節描寫直接凸顯人物性格,避免敘述上的重復性,這在人物之間的對話中便可見一二。“滬生說,小毛認得姝華后,抄了不少相思詞牌名,倦尋芳,戀繡衾,琴調相思引,雙雙燕。姝華面孔一紅,起身說,我回去了。滬生說,好好好,我不講了。”實際上,滬生在年少時便對姝華有過愛慕之情,但他始終不曾明白袒露過心事,反而只是通過轉述小毛的暗戀來隱晦地述說情意,符合人物年齡的語言在此處便鮮明地體現出兩人相互之間的性格與心理狀態。
再者,《繁花》中人物的生平經歷被均勻分布到三十余章的篇幅之中,讀者可以從不同的視角來觀察、認識同一人物性格的多個側面,故事人物形象的豐富性和多面性被充分地展示出來,這正符合司馬遷所擅長使用的“互見法”。例如,滬生和陶陶的對話是小說開篇“引子”部分的主要內容,而兩人的對話中又先后涉及到梅瑞、阿寶、汪小姐、李李、小毛等故事的主要人物,并且這些人物的性格在該部分也得到了適當的暗示,這正是《繁花》中人物性格的展示方式之一種。又如,“引子”部分陶陶樂此不疲所講述的無外乎就是上海弄堂中男女的偷情故事,他本人實際上也是這些大同小異的故事中的一員,然而,小說結尾處陶陶卻對小琴產生了真摯的愛情,這種看似矛盾的表現顯然使人物的性格特質更加清晰、鮮活起來,旁見側出手法的大量運用自然成為《繁花》取得成功的關鍵原因。
三、說書藝人的敘事立場
自唐代以來,敘事性文體在中國文學的版圖上便已呈現出愈加活躍的趨勢,隨著宋、元兩代商業經濟的高速發展,勾欄瓦肆中的城市居民有了更強烈的文化消費需求,這直接推動了話本、說唱乃至戲劇等敘事性文學的興盛,其題材多為傳奇、公案、愛情等,藝術特征也表現出口語化、市井化等傾向,它們的成熟意味著中國古代敘事文學已步入自己的黃金時代。翻開《繁花》首頁,極具典型性的上海景象描述過后出現的是“古羅馬詩人有言,不褻則不能使人歡笑”這句錢鐘書的論斷,似乎已在透露出彼時金宇澄所持的敘事立場。“文學在我眼里,不是廟堂,取悅讀者,也不是低下的品質,我喜歡取悅我的讀者,很簡單,你寫的東西,是給讀者看的……我想做一個位置很低的說書人,‘寧繁毋略,寧下毋高’。”[3]4這樣的表述則更是清晰準確地道出了作者心中最為理想的寫作狀態,也證明《繁花》確實充分吸納與借鑒了話本、擬話本的敘事藝術。
正如前文所述,《繁花》在正式展開故事的敘述之前特意加入了一個“引子”部分,這首先就在形式結構上完成了對傳統話本體制的摹仿。入話、正話、結尾是傳統話本的基本構成部分,其中作為話本開端的入話部分有時以一首或多首詩詞點明故事題旨,有時則以與正話內容相關的小故事開頭,這既是為了在現場表演時吸引聽眾所作的有意安排,更是包含有引領聽眾把握“話意”的目的。滬生與陶陶在菜場偶然相遇后的談話俗則俗矣,但是卻令陶陶感到難得的興致盎然,尤其是當“滬生預備陶陶拖堂,聽慢《西廂》”時便已頗具舊時說書之意。還需指出的是,該部分內容中對于往事有限的回溯部分實則是以預敘的方式令讀者對故事全貌先有初步印象,這同話本、擬話本慣用的預敘方式也是類同的,之后故事的發展在前期的交代與鋪墊之后也就是順理成章的了。
《繁花》除卻在形式結構的層面上汲取了話本、擬話本的營養之外,同時還在具體的敘事模式上完成了向中國傳統文學的致敬,這用金宇澄自己的話來說便是“愛以閑談而消永晝”。《繁花》的敘事盡管是圍繞著上海市井社會中的眾生百態來展開,實際上卻由無數個相互聯系但各自獨立的小故事連綴而成,所有的故事人物都具有“講述”的功能,至于小說中無所不在的關于城市細節的鋪陳則更是承接了宋元話本直至《金瓶梅》《海上花列傳》的精神血脈。
與此同時,在對《繁花》與傳統話本、擬話本之間關聯性進行考察的同時,我們也不應忽視這樣一個現象,即《繁花》本身特殊的寫作樣態,其最早實際上是以網絡寫作的模式出現在讀者眼前,講述上海故事的“弄堂網”成為它的首發之地,網友與作者的互動交流部分地改變了小說的人物、情節等關鍵要素。“2011年5月至11月那大半年,我最初化名在網絡論壇上每寫出一小節,讀者就追著看、跟帖、寫評論,我整個人沉浸在里面,跟他們互動,30多萬字《繁花》收工,我有種特別奢侈的幸福感。”[5]3假使說金宇澄談及的“說書人”意識是其主體觀念的自覺產物,那么當代獨有的網絡平臺在文學生產機制上就起到了同古代書場類似的功用,小說不再是作者一人的獨創,接受者的期待視野直接干預到作品最終面貌的呈現,專業作家在一定程度上所充當的正好是古代說書藝人的身份。
綜上所述,金宇澄的《繁花》在思想觀念上承繼了儒家“溫柔敦厚”的詩教傳統,對人物形象的表現深得《史記》紀傳筆法之助,敘事策略的方面則與古代話本、擬話本之間頗有相似之處。艾略特曾就個人創作與文化傳統的關系談到:“假如我們研究一個詩人,撇開了他的偏見,我們卻常常會看出:他的作品中,不僅最好的部分,就是最個人的部分也是他前輩詩人最有力地表明他們的不朽的地方。”[6]2這樣的評價放在金宇澄身上想必是恰當的,正是他對古代文學觀念的自如把握方才賦予《繁花》以足夠的文化分量與思想高度。
[1]高慧斌. 金宇澄:我為什么要用方言寫《繁花》[N]. 遼寧日報,2015-9-7.
[2]項靜. 方言、生命與韻致——讀金宇澄《繁花》[J]. 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4(8).
[3]金宇澄,朱小如. 我想做一個位置很低的說書人[N]. 文學報,2012-11-8.
[4]沈從文. 沈從文全集:第19卷[M]. 太原:北岳文藝出版社,2002.
[5]許旸. 金宇澄:有種奢侈的幸福感[N]. 文匯報,2015-8-17.
[6]艾略特. 艾略特詩學文集[M]. 北京:國際文化出版公司,1989.
(責任編輯:李俊丹 校對:蘇紅霞)
I207.4
A
1673-2030(2017)02-0056-03
2017-03-05
楊杰蛟(1988—),男,湖南岳陽人,湖南師范大學文學院中國現當代文學專業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