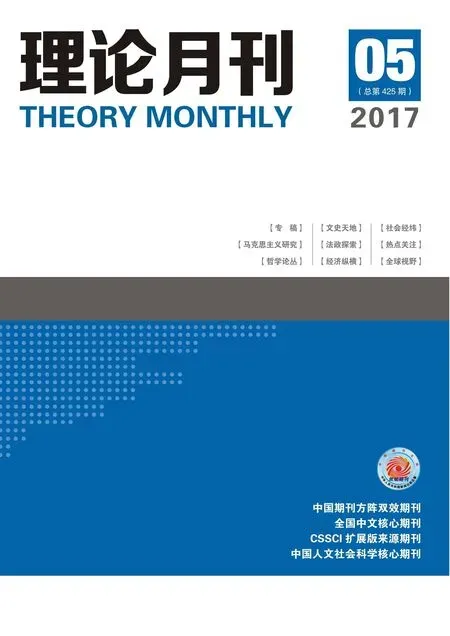文化創意產業園區的生態種群關系和管理策略
□徐海龍
(首都師范大學文學院,北京 100089)
文化創意產業園區的生態種群關系和管理策略
□徐海龍
(首都師范大學文學院,北京 100089)
“生態”是個龐大的生物環境系統,在同一生態環境中,不同物種之間出現了以食物、資源和空間關系為主的“種間關系”,基于生態學中的種間關系理論來解釋文化產業中藝術家、企業以及周邊產業之間所存在的生態關系,重點分析了一些文化產業園區從藝術烏托邦到商業旅游景點演化的原因,提出了保持園區創意活力、防止生態衰退的管理策略建議。
生態環境系統;種間關系;文化創意產業園區
“生態”這個詞在生物學中代表了一個龐大的生物環境系統,這個系統是由非生物和生物兩部分構成,分布著各類物種。同一生活環境之中,不同物種之間出現了以食物、資源和空間關系為主的“種間關系”[1]。把生態學理念引入文化創意產業園區是一個新的研究視角。可以說,一個特定的文化產業園區里面生存著藝術家(工作室)、文化生產企業和傳播企業、周邊廠家和店鋪等多個不同種群,也隨之產生了種間關系,這些關系能夠對相關的種群產生正相互作用和負相互作用。
藝術和商業能否兼容一直是困擾文化創意產業園區發展的頭號問題。這些區域最初由于廉價地租和街區特色吸引了大量藝術家自發聚集,誕生了很多藝術作品及展覽,例如北京798藝術區、上海的田子坊文化街區等。隨著地域知名度提升,原本一個尊崇差異、先鋒和反叛的烏托邦演變為一個商業旅游景點,最終失去活力而萎縮。這種發展軌跡在我國當前很多文化產業園區屢屢出現。一個自然生態環境的繁榮需要種間關系的多樣平衡和能量循環,反之則使生態圈的生命能量逐漸衰減,某些生物群落退化消亡。類似地,我們可以用種間關系來分析文化產業園區的退化原因。
1 寄生和捕食:藝術家與文化企業的關系
1.1 寄生
生態學中的“寄生”是指一方生物給另一方生物提供營養物質和居住場所,前者生物(宿主)受害,后者生物(寄生物)受益。文化產業園區內核心生態位就是藝術家,我們可以把這些人(階層)看作是文化產業生態群里最基本生產者,可稱之為“創意者”“創意階層”。他們是一個園區里面的“原住民”,大量的個體、工作室或是團隊依賴才華靈感、生活體驗和信息資料進行創作。這些人才和作品(IP)成為了文化企業、經紀人和盜版者的食餌。
盜版和仿制無疑是“寄生蟲”的行為。盜版方完全靠創意者的“養分”生存;創意者幾乎沒有從盜版方獲得實際回報,他們避開盜版者會生存得更好。因此盜版方與創意者形成了寄生關系。從整體行業來講,盜版、剽竊和仿制發揮的是一個長期慢性的負作用。例如一些畫家村或民俗村里的著名雕塑景觀被重復濫用;仿制跟風的手工藝品充斥柜臺、價格虛高。而原創藝術家由于沒有獲得相應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受到極大損害。
除了盜版方,如果文化企業(經紀人)與藝術家簽訂了一定較長時期的合約,但不允許藝術家進行創新(例如一些畫廊限定畫家的作品類型),不給予藝術家更多的市場推廣和指導。長期來看,雖然藝術家獲得了一些經濟回報,但是企業方只想榨取(抽傭)藝術家的市場價值,沒有協助促進藝術家的藝術生命成長和價值提升。這樣,文化企業與藝術家也形成了類似的寄生關系。作為宿主的創意階層慢慢被作為寄生物的資本方消耗掉了靈感和才氣。
1.2 捕食
“捕食”通常指一種生物以另一種生物為食的現象。捕食與寄生有類似地方,它們都是一方獲取另一方提供的營養,并對另一方造成傷害。捕食與寄生存在幾個區別:首先,寄生物通常不立即殺死宿主,捕食行為通常必置獵物于死地。第二,寄生物通常比宿主弱小,而捕食者與獵物相比,體形更大或是更強壯。第三,如果寄生關系雙方分開,寄生物難以單獨生存,而宿主可健康成長,兩者之間無必需的數量關系。但是捕食者與獵物卻是相互制約對方的數量,一般表現為“獵物先增先減,捕食者后增后減”的不同步變化。它們相互之間具有調節和抑制作用,以維持兩個種群數目的相對穩定①例如羊群(被捕食者)與狼群(捕食者)之間的關系:被捕食者增多,引來捕食者增多;捕食者數量增多,必然引起被捕食者隨之減少;被捕食者減少,隨后必然引起捕食者的數量減少;之后,被捕食者因天敵減少而增加,接著又使捕食者增加。。
文化創意產業園區內雖然不會出現肉體毀滅的現象,但是從“創意生命”“藝術生命”來看,一些大規模迅速的盜版行徑可以非常快地毀滅原創,讓其血本無歸,這也形成了捕食行為(捕食性寄生)。除此之外,更具有文化產業討論意義的捕食關系是在資本方、企業方與藝術家之間發生的。一些資本方和企業方利用文化產業園區的投資、稅收、地租等各方面優惠政策進駐,但并沒有詳細評估和長期孵化創意的規劃,也沒有與特定藝術家進行長期合作經營的打算。他們的目標是在短期內購買和囤積園區內各種“IP”和項目,之后也很少與原創者討論后續開發。一方面,藝術家在資方面前,雖然獲得了一定的知識產權酬勞(很多項目都是以很低廉價格被收購),但是對于自己作品今后命運的話語權,無論是自身經濟實力、市場掌控力還是媒體輿論,都處于明顯的弱勢地位;另一方面,大量熱錢一股腦涌入園區搜尋投資目標,急功近利、短期收購、無視差別創新、圍捕熱點再一哄而散。大量IP被買斷后,經過初步加工包裝就進行轉包或是上市銷售,產業鏈延伸不足。并且一些原作品被誤導、歪曲和濫用,失去了原初珍貴的藝術水準和價值導向。從這個角度看,資方和企業方并不是在開發創意,而是在扼殺創意——“出一個、搶一個;用一個、死一個”,這就是典型的捕食關系特征。
當然,這不意味著要清除捕食關系,徹底驅逐文化創意園區的資本方和企業方。事實上,捕食關系對于生態平衡也有積極的一面。例如狼群捕食羊群但并沒有造成羊的滅絕,反而也會在一定程度上刺激獵物的進化。一個藝術街區引入文化企業和藝術經紀人,一方面會使藝術家及作品經受市場和受眾的摘擇選粹,擴大傳播也獲得資金;也會滌蕩園區的閉門造車、曲高和寡和陳詞濫調之風,從而引發創新競爭。另一方面,文化產業園區內的文化企業長期以商業準則去捕食創意者,隨著時間進展,一些創意者(包括企業)必定會感到創作瓶頸和類型重復,為了躲避潮流模式的僵化危害,必定會導致創意分化和進化。這是我國政府積極建設文化產業園區、發揮集聚效應的意義之一。
盡管如此,由于藝術家的創作生產具有偶發性、不穩定性和長期性,創意容易引發盲目跟風和濫用。如果資方和企業方都把自己視為捕食者、速食者,把藝術家視為手中獵物,那么就極易形成盲目和過度的“圍獵”,以及對創意群體的蔑視之風。少數幾個藝術家被熱炒,創意被囫圇吞棗或過度消費,更多差異化的藝術家和作品被忽略,版權費兩極分化,最終導致園區內的創意階層(種群)減少甚至滅絕。因此,捕食關系具有文化產業園區建設初期的野蠻生長的特征,作為單純捕食者的文化投資方和企業,他們對創意種群的間接促進效應,是一個市場倒逼的結果,需經歷一個代價慘重的長期過程。
2 從偏害共生到競爭:文化創意產業與周邊產業的關系
在一些開放式的文化創意產業園區,如果把園區內的藝術家和文化企業作為一個文化(創意)產業群落來看待,它面對的一個重要關系就是與非授權的周邊產業(企業)的關系。藝術家本人、作品展覽和藝術節會吸引大量觀眾和游客,拉動此地的餐飲、娛樂、住宿和工藝紀念品的消費;飯店、酒吧、書店也可以利用園區的建筑特色和文化符號作為自身招牌(例如“某某主題場所”)。比起寄生和捕食關系,文化產業與周邊產業屬于一種間接的共生關系。共生可以分成幾種現象:偏利、偏害、互利。“偏利”指種間相互作用對一方沒有影響,而對另一方有利(促進作用);若對一方沒有影響,對另一方有害(抑制作用)則稱偏害共生;互利共生意味著兩個種群之間互惠互利。
非授權的周邊企業并沒有直接索取藝術家、創意者的價值,但是間接地利用了園區的文化氛圍和人氣進行經營。在園區發展的初期和中期,少量周邊企業的進駐以及消費者對文化產業從業者的生產生活并沒有產生太多影響。因此二者之間形成了偏利共生,即對一方無害,對一方有利。隨著園區的藝術特色和文化號召力越發顯著,更多非文化創意產業入駐,增長的商業氣息、山寨產品以及喧鬧人群開始干擾和異化藝術工作者的創作環境和心境,文化產業與周邊產業的關系就逐漸演化為偏害共生。
從偏利到偏害,文化產業與周邊產業兩個群落還可以共生,但是當大批的餐飲和旅店希望入駐園區,那么與文化產業群落就形成了生態學意義上的競爭關系。“競爭”是生活在同一區域的兩種或兩種以上生物爭奪資源和空間,從而相互妨礙、排斥的現象(例如大象與獅子搶奪水源)。處于競爭關系的雙方會表現為優劣勢之分,隨著優勢種群數量擴大,將驅逐劣勢種群。所以在一個區域內,競爭關系的雙方雖然不會直接傷害彼此,但也間接形成了你死我活的生存狀態。
文化產業園區有限的寫字樓、街道、水電等硬件設施是各個種群賴以生存的基本資源,而資本相對雄厚、現金流更快的周邊企業處于競爭優勢,占據園區空間,也提升了園區的平均租金,那些從事原創的藝術家工作室和小型藝術機構,由于承受不了年年上漲的房租而陸續遷出。曾有學者調查數據顯示,從2003年到2006年,北京798藝術區內藝術家工作室的數量呈增長趨勢,但是自2007之后,園區日租金漲到了6元/平方米,而過去一些黃金地段寫字樓日租金均價也不過7元/平方米,到2008年藝術工作室只剩下27家,2013年798藝術區的入駐機構總數是576家,但是藝術家工作室只占4%,約23家個體工作室,而商鋪和餐飲卻占比32%,大約184家,嚴重擠占了藝術家生存的空間[2]。到2015、2016年,藝術家基本搬離了北京798藝術區[3]。在上世紀末、本世紀初形成的上海田子坊藝術街區,到2015年的店鋪租金最高達到每月8萬元,超過了上海新天地。學者實地調研發現,田子坊目前20%以上的店鋪經營時間不足一年,商家流轉迅速,越來越少老店能夠抵抗住高昂的租金。近40%的店鋪只能達到收支平衡的狀態,20.83%的店鋪虧損,盈利的店鋪僅占27.08%。并且,業態同質化與低端化的趨勢非常顯著,服裝店占到了22.92%,其次是手工藝品和餐飲業,均占14.58%,在田子坊中文化場所占比最低,僅有2.08%[4]。
3 走向互利共生的種群關系
從上面分析可以看出,寄生、捕食、偏害和競爭都不是良性的、成熟的園區種群關系,其根本原因就在于藝術家很少能從這些資方、企業方獲得創作生產方面的培育營養。而資方和企業不管是拋棄某個藝術家還是退出這個園區,都可以繼續尋找和吸收養分。竭澤而漁的結果是園區藝術創意生命的退化,很多藝術家和手工藝人開始大批量制造類型化、重復的文化商品。玩家走了,只剩商家。“藝術烏托邦”變成“商業旅游區”[5]。這是我國各地一些文化產業園、民俗文化村以及歷史街區衰落的重要原因之一。
紐約蘇荷區,中國的798、田子坊這樣的開放型街區都是經歷了舊城居住區、工業區、藝術區到商業區幾個階段,文化創意產業園區憑借藝術家的創作活力煥發生機,之后逐漸發生群落演替,藝術家遷到更偏遠的地方重建新的“藝術圣地”,再開始新的循環。文化創意產業園區與傳統產業集聚區的一個重大區別是,前者的選址需要一個文化歷史資源積淀豐厚、思想觀念活躍、工作與日常高度融合、生活便利的地方。也就是說,它的萌生依賴于一個繁榮富足的文化生態大環境。所以,如果任其自然更替,那么適合于建園的地域環境會越來越少(被商家占據),藝術家以及先鋒反叛的生存領地距離文化經濟中心越來越遠,更重要的是一個城市的創新風氣和多元文化風貌將被商業文化所擠壓和驅散。很明顯,這種自然演化將導致未來沒有適宜地域建設文化創意產業園區。
除了寄生、捕食、偏利共生、偏害共生和競爭關系之外,自然生態中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種間關系就是“互利共生”,即兩個種群之間互惠互利,相互依賴。如果彼此分開,則雙方或者一方不能獨立生存。兩種生物的數量變化趨勢不像捕食關系那樣“此消彼長,此長彼消”,而是呈現同時增加,同時減少的同步性變化。那么作為園區管理者,如何讓園區的種間關系更多地呈現出互利共生呢?
3.1 發展長期孵化工程和文化經紀行業,讓藝術家與文化企業(資方)從捕食關系走向互利共生
文化創意產業園區要從藝術烏托邦開始進行產業升級和進一步發展,就需要文化企業(資方)進駐。為了遏制更多的急功近利的捕食關系產生,園區管理者首先要提高入園壁壘,評估和篩選更加專業的文化企業入園[6]。并且,在各種扶持政策上激勵企業與藝術家簽訂長期創意孵化合同,讓雙方長期交流合作,在價值觀、文化生產和生活情趣三個層面逐漸形成互相借鑒、和諧共鳴的關系。稅收部門和產業基金可以對項目長期孵化周期所帶來的市場損失和風險進行一定的補償。
前面提到園區的少數藝術家和IP被集中圍獵和“捕殺”,其他大量創意群體被忽視,解決這個問題的有效方法是大力引進和發展專業化的文化藝術經紀人和經紀公司。因為經紀人的存在意義和收入來源就在于挖掘和推介各種創意,疏通市場信息。因此它們就像是自然環境中的分解者(微生物),促進大量藝術作品產生的營養價值分解輸送到整個園區的企業群。如果經紀人這一種群數量發展起來,“分解和輸送創意”的市場行為必定會從少數幾個熱門IP身上轉移開去,在園內廣泛開展。
園區需要建立和保障嚴格的知識產權制度,懲罰盜版和免費使用者,促使文化企業給予創意者相應回報。這樣,藝術家的身份和價值獲得尊崇,創意階層就會持續存在和擴大,企業又會陸續被吸引進園區內尋找不同的合作方。
從長期來看,這幾種措施有利于藝術家與文化企業(資方)從寄生和捕食關系走向互利共生,產生廣泛的生態位分化①生態位(ecological niche)是指一個種群在生態系統中,在時間空間上所占據的位置及其與相關種群之間的功能關系與作用。所謂生態位的分化,是指在同一地區內,生物的種類越豐富,物種間為了共同食物(營養)、生活空間或其他資源而出現的競爭是越激烈的,這樣,對某一特定物種占有的實際生態位就可能越來越小。其結果是在進化過程中,兩個生態上很接近的物種向著棲息地分化、食性上的分化、活動時間分化或其他生態習性上分化,以降低競爭的緊張度,從而使兩種之間可能形成平衡而共存。,出現多個形態各異的共生群落,園區整體趨向長期合作、休戚相關、同步增減的穩定狀態,減弱了捕食關系導致的市場調節滯后性的危害。
3.2 限定周邊企業的進駐數量、開辟特定營業區域,防止滑向偏害和競爭
前文提到,園區早期的少量周邊產業與文化產業形成了偏利關系(對文化產業無影響,對周邊企業有利)。隨著周邊產業進一步發展,工藝品商鋪、文化主題餐館會傳播園區的創意符號,營造一些文化潮流和傳奇故事。很多創意者與買家的商務洽談是在咖啡館和酒吧進行的。從某種意義上說,一個園區內的咖啡館的數量反映了該園區創意活動的活躍程度,這可以稱之為“咖啡館效應”[7]。所以,文化產業群落與周邊行業群落共同提高了園區的人氣和影響力,二者可以形成互利共生的關系(尤其是在開放式街區)。
但是,為了防止這種互利共生滑向偏害和競爭關系,不讓脆弱的藝術家種群面臨巨大的生存壓力,管理部門就要限制園區內非文創企業的數量,保留少許尊崇創意、充滿藝術風格的周邊企業,禁止大量唯利是圖、與文化產業無關的商家進駐。國內一些全封閉或半封閉園區就是采用這種方式,例如北京“新華1949”和“尚8”文化創意產業園。開放式園區可以專門開辟一個園區外圍附近的場地來集中非文創企業,如產權交易中心、食街、工藝品街等。同時,管理部門對于園區中心場地租金進行減免補貼,這樣就可以把更多地皮供給藝術家工作室、策劃公司、美術館、劇場等產業組織,讓藝術生產在一個相對安靜和純粹的環境氛圍中進行,同時又沒有割裂與支撐產業、世俗生活的關系。
4 結語
建設文化創意產業園區不能只看重其對房地產和其他產業的商業價值提升作用,而忽視園區藝術氣息的維護和文化建設,以及它們對城市文脈和人文精神的滋養。這種目光短淺、殺雞取卵的逐利行為絕不是一個國家發展文化產業的價值取向。無論對于文化產業生態學的研究,還是對于實際的園區生態建設,闡述和明確產業種群關系只是第一步。更緊迫、更重要的工作是對多個園區內的文化產業與周邊產業的發展關系進行長期數據監測和評估,歷史性地統計和分析創意群落、文化企業群落以及周邊產業群落在園區內的出生率、死亡率、遷入率、遷出率,從而基本明確各種群生存的最適宜與最危險的數量范圍,以及區域密度閾值,這樣才能更加科學有效地進行管理政策的制定和實施。
[1]李振基.生態學[M].北京:科學出版社,2014:45-49.
[2]遲海鵬.藝術區現狀研究:以“798”藝術區為例[D].北京:中央美術學院,2014:31-35.
[3]宋宇晟.從“烏托邦”到旅游景點:798藝術區褪去光環?[EB/OL].(2016-08-18).中國新聞網.http://www. chinanews.com/.
[4]張琰.他們為什么離開田子坊[N].瞭望東方周刊,2016-08-25;于海,鐘曉華,陳向明.舊城更新中基于社區脈絡的集體創業:以上海田子坊商街為例[J].南京社會科學,2013(8):60-65.
[5]譚娜.生態學視域下的文化創意產業鏈重構研究[J].東岳論叢,2014(7):134-142.
[6]王重遠.基于生態理論的都市創意產業集群研究[J].貴州社會科學,2009(9):26-30.
[7]劉壽吉,戴偉輝,周纓.創意產業的生態群落模式及專業性公共服務平臺研究[J].科學進步與對策,2009(9):49-53.
責任編輯文嶸
10.14180/j.cnki.1004-0544.2017.05.008
G124
A
1004-0544(2017)05-0047-05
首都師范大學課題項目:京津冀城市群文化建設與傳統文化資源可持續、協同發展研究。
徐海龍(1978-),男,河北唐山人,文學博士,首都師范大學文學院文化產業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