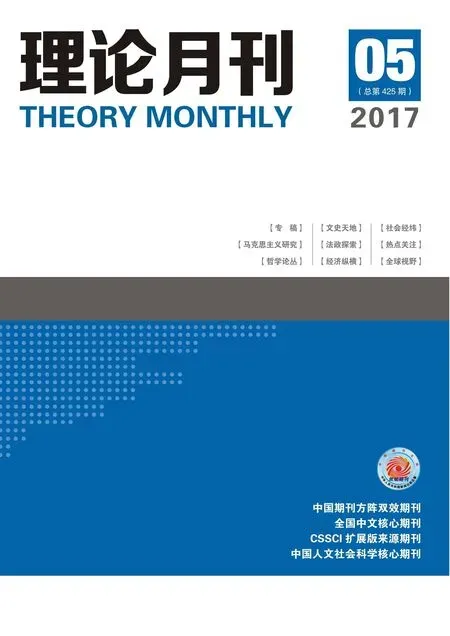景頗族民間宗教信仰中的自然觀與神鬼觀
□徐俊六
(云南師范大學文學院,云南昆明 650500)
景頗族民間宗教信仰中的自然觀與神鬼觀
□徐俊六
(云南師范大學文學院,云南昆明 650500)
景頗族特殊的歷史地理環(huán)境、自然生態(tài)環(huán)境與人文政治環(huán)境造就了景頗族“靈魂不死”與“萬物有靈”原始樸素的宗教觀念,以及渾沌的時空觀與幻化的物象觀。在此基礎上,景頗族先民通過“以己度物”的方式運用渾沌思維與幻化思維臆造出各種神鬼,從而構建景頗族民間宗教信仰體系。在景頗民間宗教信仰中,神與鬼均是景頗人虔誠信奉、敬畏與祭祀的對象,在很多語境與場合中,神與鬼沒有嚴格的界限,經(jīng)常出現(xiàn)神鬼相混、神鬼一體的現(xiàn)象,這是景頗族民間宗教信仰中比較特殊的地方,值得深入研究與探討。
景頗族;民間宗教;萬物有靈;目瑙齋瓦;自然觀;神鬼觀
從民族分布來看,景頗族生活的地域比較特殊,主要居住在今天中國云南德宏傣族景頗族自治州的隴川、盈江、瑞麗、芒市、梁河五縣市,緬甸北部的克欽邦、印度的阿薩姆地區(qū)與泰國的清萊府,總人口約200萬,在中國境內(nèi)的景頗族約15萬。景頗(Jinghpo),在其他國家和地區(qū)叫Theinbaw(森博),Singpho(新頗),Singfo(新福),Chingpaw(貞頗),Jinghpaw(景頗)。中國的景頗既是族稱,也是支系的稱謂,包含景頗、載瓦、勒期、浪速與波羅五個支系。景頗族區(qū)域廣大,從中國西部到中南半島北部均有分布,各地的地理條件與氣候特征大致相似。追溯歷史的起源,景頗族是一個歷史復雜、由北向南逐漸遷徙的民族,一個經(jīng)歷了中原、高原與山地多自然生態(tài)的民族,一個相對封閉、又兼具文化交融的跨境民族。
景頗先民面對廣闊的生存空間、惡劣的自然環(huán)境與多種不可知的自然現(xiàn)象,與其他民族的先民一樣用一種“以己度物”的方式來思考與解釋外界事物,于是出現(xiàn)了“靈魂不死”與“萬物有靈”的觀念,以及能夠創(chuàng)造各種形象的渾沌思維與幻化思維,這就是景頗族原始樸素的自然觀,這種原始樸素的自然觀是景頗族民間宗教形成的基礎,也是推演臆造各種鬼神存在的心理機制,同時也是一種古典生態(tài)智慧。
1 景頗族民間宗教信仰中的自然觀
1.1 “靈魂不死”與“萬物有靈”
“靈魂不死”觀念認為,人有兩部分組成,即肉身與“弄拉”(景頗語Ngongla)即靈魂。當肉體與靈魂和合為一時,人就健康;當肉體與靈魂分離時,人就會犯病或進入夢境。所以,景頗族認為人入睡后,靈魂就脫離肉體,進入另一個世界,靈魂在夢境中游蕩時不能被打斷,一旦被打斷,人的靈魂就回不來,人就要生病甚至死亡,這就是景頗族的“靈魂不死”觀念。“靈魂不死”的思維模式推而廣之,延伸到整個自然界,凡是自然界中的事物均與人相似同樣具有靈魂,這就是大多數(shù)早期先民們共同信奉的“萬物有靈”觀念。
“萬物有靈”又稱“泛靈論”或“萬物有生論”,是原始先民們的思維方式或思維特征,它相信自然界的萬事萬物均與人相似,同樣具有生命與靈魂,而且生命與靈魂是可以分離的,生命停止而靈或魂可以不滅的一種思想。“萬物有靈”是宗教與哲學產(chǎn)生的思想基礎,是遠古人的思想智慧,它闡釋的是人與自然、人與萬物的關系,探討的實質(zhì)是人與自然的共生關系。遠古時期,景頗族的先民們在與自然相處的過程中,對自然界的各種奇異現(xiàn)象無法進行合理的解釋,于是根據(jù)自然現(xiàn)象出現(xiàn)的特征及其規(guī)律結合當時人們的思維進行了人、鬼(神)、靈魂等的劃分,并付諸于日常的生產(chǎn)生活中且世代相傳至今。這是在生產(chǎn)力極度低下的狀況下,早期先民對自然作出的最樸素的解釋,這種樸素的無任何功利性的認知觀也為景頗族與自然和諧共處找到了思想基礎。就像恩格斯(Friedrich Von Engels)所說,“在遠古時代,人們完全不知道自己身體的構造,并且受夢中景象的影響,于是就產(chǎn)生一種觀念:他們的思維和感覺不是他們身體的活動,而是一種獨特的,寓于這個身體之中而在死亡后就離開身體的靈魂的活動。從這個時候起,人們不得不思考這種靈魂對外部世界的關系。”[1]在云南德宏盈江縣卡場村的田野調(diào)查中,“靈魂不死”或“萬物有靈”的原始觀念還有一定的遺存,如,一旦有人生病,信奉民間宗教的群眾首先還是請景頗族的祭師即董薩來念鬼,他們認為人生病是鬼魂在作祟,只有把鬼魂祭祀好或驅(qū)離人的身軀人才會好起來。
“萬物有靈”的學術概念最先來自被稱為人類學之父的英國人類學家愛德華·泰勒(Edward Burnett Tylor)。泰勒在他的著作《原始文化》中,用了大量的篇幅來闡釋“萬物有靈”,他在文中論述到“我們看來沒有生命的物象,例如,河流、石頭、樹木、武器等等,蒙昧人卻認為是活生生的有理智的生物,他們跟它們談話,崇拜它們,甚至由于它們所作的惡而懲罰它們。”[2]這里的“蒙昧人”就是我們所說的原始社會時期的先民。泰勒在他的論著中說到“每一塊土地、每一座山岳、每一面峭壁、每一條河流、每一條小溪、每一眼泉水、每一棵樹木以及世上的一切,其中都容有特殊的精靈。”[3]在這里,泰勒進一步補充說明了“看來沒有生命的物象”,其實都是有某種“精靈”附著的,這種“精靈”就是“萬物有靈”的“靈”。泰勒在考察原始宗教后,繼續(xù)解釋“萬物有靈”,他說,“在原始宗教里,物品被看作是賦有像人一樣的生命。”[4]在這里,更進一步說明了“萬物有靈”的廣泛性,“物品”也是和人一樣具有生命存在的物體,同時也說明了“萬物有靈”與原始宗教之間有某種淵源關系。意大利17-18世紀著名的哲學家、美學家維科(Giovanni Battista Vico)也提出了相關的論述,他說,“原始人類還沒有自己的觀念,使自己感到驚奇的事物都是有一種實體的存在,正像兒童們把無生命的東西拿在手里跟它們游戲言說,仿佛它們就是些活人。”[5]在這里,維科把原始先民們的思維與兒童的心理作了對比,想要表達的是人類早期思維特征類似兒童心理。法國哲學家、民族學家列維-布留爾(Lucien Lévy-Bruhl)在描述原始人的思維時說“我們不能在原始人的集體表象中發(fā)現(xiàn)任何東西是死的、靜止的、無生命的。有足夠的證據(jù)證明,所有的存在物和所有的客體,甚至非生物、無機物以及人的手制作的東西,都被原始人想象成能完成最多種多樣的行動并能受到這些行動的影響。”[6]列維-布留爾接著說“到處存在著生命和力量的本原。”[7]列維-布留爾在考察北美印第安人、澳大利亞土著與“巴菲歐蒂人”等后,提出了原始人的思維模式,認為原始人的思維方式是一種“集體表象”,這種“集體表象”與所有的存在物包括有機物、無機物以及人工物品均具有生命力,并影響著原始先民們的意識活動。除了以上論述外,還有孔德(Auguste Comte)、斯賓塞(Herbert Spencer)、恩斯特·卡西爾(Ernst Cassirer)等人也有相關的闡釋,他們認為原始思維與兒童心理存在天生的類比性,具有抽象性特征。“萬物有靈”的觀點,中國學者也有相關的闡釋,如,吳中勝撰文,“萬物有靈,宇宙萬物都是活潑潑的生命體。這在現(xiàn)代人眼中,簡直是荒唐可笑之事。但在詩性思維中,這是宇宙萬物的本質(zhì),是不容爭辯的事實。”[8]張強在其文章中說到,“靈魂信仰是萬物有靈的核心,也是其學說構成的基礎。萬物有靈是人類史前時期的必然階段,同時也是人類對自然的初步讀解。萬物有靈給予人類以向外體察自然萬物的窗口,在這個窗口上,人類所獲得的能力,就是神化自然,通過神話來讀解自然。”[9]其他學者對“萬物有靈”也進行了相關論述,不再一一列舉。共同的一致的觀點是,“萬物有靈”是原始蒙昧時期先民們相通的思維特征,這種思維方式是“以己度物”,以自身出發(fā)想象未知自然,從而構筑一個人格化的世界。
1.2 時空渾沌與物象幻化
景頗族先民們用一種以己度物、以己感物的方式建構了“靈魂不死”與“萬物有靈”的原始觀念,認為自然宇宙中的萬事萬物與人一樣具有靈魂。這是自然人格化也是人造自然物的第一步,有了內(nèi)核還得有其外在的形態(tài),使之具體化與形象化,這就是景頗族民間宗教信仰中的時空觀與物象觀。時空的狀態(tài)與物象的具體化是靠人們的渾沌思維與幻化思維來構建的意象體系。景頗族民間宗教信仰中所謂的神鬼世界與神鬼物象均是通過渾沌思維與幻化思維的方式臆造而來,具有神話思維的特征。
中國社會科學院蕭家成研究員在研究神話時說,“神話思維可分析為渾沌思維、幻化思維等,而渾沌與幻化(變幻與超力)是神話思維的主要特征。它是一種處于尚未分化的、原始狀態(tài)的、不發(fā)達的思維形態(tài)。”[10]渾沌與幻化是原始蒙昧時期人們想象世界與自然最普遍的思維方式,是一種前邏輯思維,原始先民們在觀察世界萬物時以自身為參照物,運用不發(fā)達的思維方式臆想存在與非存在的事物,總體特征是感性與直觀。蕭家成接著講“渾沌思維是指將自然、社會、人類、動物、植物、神鬼等,都視為與人類自身同類的事物。從現(xiàn)代人的角度看,這可以說是一種擬人化或神靈化的文學手法;但從原始人類的角度看,在他們的思維中,這些事物本來就被看作是同一的。”[11]渾沌一詞,出自《淮南子·診言訓》:“洞同天地,渾沌為樸,未造而成物,謂之太一。”[12]“太一”就是渾沌元氣,是宇宙的原始。漢代王充《論衡·談天》:“說易者曰:‘元氣未分,渾沌為一’”。[13]這里的“渾沌”是指宇宙天地未形成前的初始狀態(tài),這種狀態(tài)是尚未分離的原初的模糊不清的。又如神話故事中經(jīng)常提到,“天地混沌如雞子,盤古生其中”。“混沌”亦渾沌,記載了中國漢民族的創(chuàng)世主神盤古誕生的環(huán)境,也是天地渾沌一片而盤古孕育其中。渾沌思維是早期先民們思考宇宙時間與空間的基本方式,認為天體與大地原本是連在一塊,相互聯(lián)系。景頗族史詩“目瑙齋瓦”開篇這樣講述:
遠古,
天還沒有形成,
地還沒有產(chǎn)生。
在朦朧和混沌里,
有個皮能帕拉(拉:指男性、陽性),
有個迷能瑪木占(木占:指女性、陰性)。
有個木托拉,
有個頂山木占;
有個木章拉,
有個普蘭木占;
有個鳥詩拉,
有個鳥卡木占;
有個濤智拉,
有個濤浪木占。
在朦朧和混沌里,
上有能萬拉(能萬拉:傳說中創(chuàng)造萬物的男神),
下有能斑木占能斑(木占:傳說中與能萬拉共同創(chuàng)造萬物的女神)。
能萬拉向下漂移,
落到能斑木占的身上,
能萬拉在上搖擺,
能斑木占在下抖動,
創(chuàng)造天地的神已有了。
男神有了,
女神有了。
就要造天了,
就要打地了。
萬事該出現(xiàn)了,
萬物該產(chǎn)生了。”[14]
這段文字是神話史詩“目瑙齋瓦”的序歌,介紹了天體自然未形成之前宇宙的狀態(tài),是“朦朧和混沌”的,這是景頗族先民們對自然宇宙最早的認知,是在沒有一定時間觀與空間觀之前對世界的模糊認知。這種認知與世界上大多數(shù)民族的起源神話大致相似,均是先民們對未知世界一種樸素的感悟,在原始蒙昧時期有其合理性。
“幻化思維認為只要兩類事物有局部的形態(tài)或?qū)傩陨系念愃疲涂蛇M行聯(lián)想對比,并將它們納入一個模糊的整體關系之中;于是它只取其某一點上的相似,從而把本來毫無關聯(lián)的事物聯(lián)結到一起。”[15]幻化思維是神話思維的另外一種形式,它將渾沌的整體變成一個個具體而鮮活的形象,幻化思維主要表現(xiàn)在將幻化的對象具象化,使它變成可感知可親近可探索的某種存在物。景頗族史詩“目瑙齋瓦”里這樣講述著故事:
遠古,
瓦襄能退拉的創(chuàng)造,
能星能銳木占的繁衍,
生下了一個凹眼睛、窄臉膛的。
它是什么呀?
潘瓦能桑遮瓦能章,
給它取了名字:
“它就是石巖的伙伴,
大地的朋友,
會叫會跳的黃猴。”
遠古,
瓦襄能退拉的創(chuàng)造,
能星能銳木占的繁衍,
生下了一個高眉骨、短臉膛的。
它是什么呀?潘瓦能桑遮瓦能章說:
“它就是石巖的伙伴,
大地的朋友,
整天蹲在石頭上的灰猴。
等將來有了森林,
等將來有了草坪,
它將在森林里玩耍,
它將在草坪上奔跑。”
遠古,
瓦襄能退拉的創(chuàng)造,
能星能銳木占的繁衍,
生下了一個圓眼睛、短臉膛的,
它一半像猴,一半像人。
它是什么呀?
潘瓦能桑遮瓦能章說:
“它就是石巖的伙伴,
大地的朋友,
居住在石巖上的黑猴。”
從此,
居住在石巖上的有了,
生活在大地上的也有了,
石巖不再感到冷清,
大地不再覺得寂寞。
遠古,
瓦襄能退拉的創(chuàng)造,
能星能銳木占的繁衍,
生下了高低不平的一片,
上面長滿了綠瑩瑩的東西,
這是什么地方呀?潘瓦能桑遮瓦能章說:
“這是長滿了花草的農(nóng)齋地方(農(nóng)齋地方:泛指野外,蜂類生活的地方),
將來的蜂類,將生活在這里。”[16]
以上四則小故事,介紹了黃猴、灰猴、黑猴與蜂地的生成,前三種動物的生成是幻化思維的形似,“凹眼睛、窄臉膛”的是黃猴,“高眉骨、短臉膛”的是灰猴,“圓眼睛、短臉膛”的是黑猴;后一種事物的生成是幻化思維的、“高低不平、綠瑩瑩”的是蜂地。幻化思維是以點繪面,以局部窺視全局的思維方式來探知事物的全貌,因此幻化思維其實也可以說是類比思維的一種運用。
渾沌思維與幻化思維是神話思維的兩種基本形式,也是神話產(chǎn)生的兩種心理機制。渾沌思維除了能夠解釋原初世界的時空觀外,還有“萬物有靈”觀念中生命的交感狀態(tài),即人類與其它動植物甚至神鬼都是某一系原始祖的后代,都具有感性特征,這是人與自然處于未分離的原始狀態(tài)的一種反映,是一種膠著的整一的原生態(tài)生命體狀。幻化思維除了能夠解釋各種物象的生成外,還可以解釋自然的奧秘,如聲音的來源、嗅覺的來源、四季的起源與變化等等;也可以解釋各系造物主擁有無限的神力;同樣可以解釋天、地、人、神、鬼之間的關系等等。
1.3 原始樸素的自然觀是一種古典生態(tài)智慧
“所謂生態(tài)智慧,是指理解復雜多變的生態(tài)關系并在其中健康地生存和發(fā)展下去的主體素質(zhì),它既包括文化理念,也表現(xiàn)于倫理和制度,并最終指向于一種生活方式。在兩千年的文明進程中,中國傳統(tǒng)文化逐漸形成了以儒釋道三家為核心內(nèi)容的文明體系,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17]曾繁仁也說,“中國古代先民在科技不發(fā)達的情況下,基本上是靠天吃飯,自然生態(tài)就顯得特別重要。所以,生態(tài)智慧在古代典籍中特別豐富,盡管見解有所差異,但卻‘都表達了農(nóng)民的渴望和靈感。’”[18]在中國古代傳統(tǒng)文化中,包括少數(shù)民族在內(nèi)的各民族創(chuàng)造了極具智慧的生態(tài)理念,景頗族就是其中的一支。景頗族由北向南逐漸遷徙的特殊歷程,造就了景頗族特殊的歷史地理環(huán)境、自然生態(tài)環(huán)境與人文政治環(huán)境,在這種特殊的生境中,在認知與改造自然的過程中,景頗族先民們開發(fā)了他們的頭腦,積累了智慧型的生態(tài)倫理思想。這些生態(tài)倫理思想亦即前文所述的“靈魂不死”與“萬物有靈”“渾沌”與“幻化”等原始樸素的自然觀念。
景頗族“靈魂不死”或“萬物有靈”觀念的產(chǎn)生有其深刻的歷史背景與深層的民族心理意識。景頗族史詩“目瑙齋瓦”記載了很多“靈魂不死”的現(xiàn)象,“歷經(jīng)五次創(chuàng)世后,彭干吉嫩(創(chuàng)世主)與木占純威(造物母)終于停止呼吸,他們的氣息變成了財富,皮膚變成了植物,心臟變成了金子,腦漿變成了銀子,骨骼變成了鋼鐵銅,頭顱變成了寶石與寶物,牙齒變成了白瓷,肚子變成了農(nóng)作物,腸子變成了項鏈,身體變成了肥料。”[19]這些帶有神話思維特征的最原初的想象是景頗族“靈魂不死”或“萬物有靈”觀念的主要表現(xiàn)。“生態(tài)倫理意識是指基于人與自然互利共生、同榮共存的生態(tài)關系,主張把人類倫理觀念擴展到人與自然的關系中去,承認有生命和無生命的各種自然物生息或存在的權力和價值,反對人類征服自然、主宰自然的霸道行為,主張建立起人與自然協(xié)調(diào)發(fā)展的伙伴關系。”[20]景頗族史詩“目瑙齋瓦”的故事說明景頗族先民們認為自然萬物有生命與靈魂,自然萬物與人類在生命的起源上同質(zhì)同構,因此,人類與自然是親緣關系,均是創(chuàng)世神的孕育物、都是大地的子民,應平等地相處、相親、相融與相合。大地為人類提供生成、生活、生存與生長的養(yǎng)料,人類應該反饋自然大地,維護自然的有機生命,使其繁榮生長,促進人類與自然的共生、人類與自然的可持續(xù)狀態(tài),這些原生性的思想來源于景頗族最原始最樸素的自然觀。
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儒家的“天人合一”即“天人之際,合而為一”,主張?zhí)欤ㄗ匀唬┡c人的相融相合的和諧狀態(tài),是中國古代存在論生態(tài)智慧。張載的《西銘》“無一物非我”“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即“民胞物與”的意思,是人與萬物同受天地之氣而生發(fā),人與萬物平等思想的典型表述。莊子《齊物論》“天地與我并生,而萬物與我為一”[21]同樣也表達了自然萬物與人類平等的思想。《老子·第二十五章》“大曰逝,逝曰遠,遠曰反。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22]老子闡述了“道為天下母”的理念,《老子·第四十二章》“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23]這些思想與景頗族“靈魂不死”與“萬物有靈”“渾沌”與“幻化”的原始樸素的自然觀高度契合,都是中國古典生態(tài)智慧。筆者在訪談景頗族著名的文史專家李向前的時候,他也認為景頗先民存在不一般的智慧。以下是訪談資料:
……
筆者:這確實很遺憾。“目瑙齋瓦”的內(nèi)容上,您看,有沒有特別想提示我的地方。
李向前:內(nèi)容上我的書都寫了,不過版本的問題或是校對的問題,書中有很多錯誤的地方還沒有更改過來,這以后有機會再做吧。有一點我想說的是景頗族先民們的原始性思維意識其實是真正的正宗的“唯物主義”。而不是像其他人講的那樣是一種唯心主義的。為什么這樣說呢,在“目瑙齋瓦”的第一部分,講的是天體宇宙世界的誕生,這些事情在先民們用當時的能力無法解釋時,用la/majan,男女或是雄雌來表達事物的產(chǎn)生,如,“上有能萬拉(能萬拉:傳說中創(chuàng)造萬物的男神),下有能斑木占能斑(木占:傳說中與能萬拉共同創(chuàng)造萬物的女神)。能萬拉向下漂移,落到能斑木占的身上,能萬拉在上搖擺,能斑木占在下抖動,創(chuàng)造天地的神已有了。”這個“能萬拉”與“能斑木占”在創(chuàng)世紀里表達的是神,天神。其實這些東西是什么呢,就是今天科學證明的電子、光子與離子等物,只是那時人們無法解釋,就這樣想象了,就是“物質(zhì)不滅”定律。你說是不是唯物的,很佩服先人們的智慧。
筆者:這個觀點很新穎,對我有很大的啟發(fā),以前只是認為景頗族有“靈魂不死”與“萬物有靈”的觀念,看來“物質(zhì)不滅”才是硬道理……①筆者于2015年2月4日在德宏芒市德宏州文聯(lián)辦公室訪談了李向前。
景頗族民間宗教信仰中的自然觀在闡釋世界與自然萬物方面,雖與儒家和道家樸素的哲學世界觀存在差異,思維方式有所不同,但其信仰對象的生成機制、生成形態(tài)與演化過程是景頗先民實踐經(jīng)驗不斷總結的結果,意味著景頗先民同樣有智慧的頭腦,且充滿遠古的自然性與生態(tài)性。
2 景頗族民間宗教信仰中的神鬼觀
在“靈魂不死”與“萬物有靈”的基礎上,景頗先民以自身為參照物,對宇宙與自然界進行了類比聯(lián)想與對比聯(lián)想,運用渾沌思維與幻化思維的方式創(chuàng)造了大量的神與鬼,并定期祭祀,這些神鬼就是后來景頗族民間宗教中區(qū)別于其他民族特別是漢族的神鬼。
神鬼在現(xiàn)實世界中并不存在,但它是早期人類在認識世界與改造自然的過程中的一種感知,也是對自然社會的一種解釋,這種神鬼觀念自它誕生的那刻起就與景頗族人們緊密相連,至今影響依在。景頗族民間宗教信仰中的人神鬼是一個相互依存的概念,早期先民在一定的時空環(huán)境中根據(jù)人自身的特點運用原始樸素的觀念如具象思維、形象思維、抽象思維、類比思維等創(chuàng)造出一系列具有超自然力的對象,即神與鬼,景頗人們創(chuàng)造出神鬼,神鬼又對人們付諸于各種影響。
神,會意字,從示從申。“示”指“先人序列”。“申”本義為“交媾”“生殖”。“示”與“申”組合表示“繁育眾人的先人”,是人類的祖先,引申為繁育萬物的天靈,即天地萬物的創(chuàng)造者或主宰者,如《說文解字》曰:“神,天神引出萬物者也。”[24]神也指各種神靈,如,《周易·說卦》“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者也。”[25]《禮記·祭法》“山陵川谷丘陵能出云為風雨,皆曰神。”[26]神也指各種精神存在,如,《莊子·養(yǎng)生主》“方今之時,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而神欲行。”[27]“神是人們把客觀自然物及自然現(xiàn)象加以形象化而產(chǎn)生的一種虛假形象,大都屬于自然崇拜范疇。因外界自然物與自然力的變化莫測,在原始人的頭腦中引起一系列的畏懼和猜測,故敬畏之情油然而生,認為世間萬物皆有某種主宰,從而對之加以祟拜產(chǎn)生神。”[28]神的概念在歷史的發(fā)展中,演變成了各種各樣的超自然物,有將自然物人格化的自然神,如雷神、太陽神、月亮神、火神等;有將社會現(xiàn)象人格化的社會神,如財神、智慧神、愛情神等;有將祖先加于神圣化的,如家族神、民族神等;還有其它如擬人神、抽象神等。
鬼,本義是有宗教信仰或迷信的人認為人死后有“靈魂”,這種靈魂即為“鬼”。如,《說文解字》“人所歸為鬼,從兒,田象鬼頭,從厶,鬼陰氣賊害,故從厶。”[29]可見,鬼的出現(xiàn)與人類的活動緊密相關,是伴隨人類生產(chǎn)生活出現(xiàn)的一種特殊心理意識反映。鬼字歷史悠久,文字出現(xiàn)時就有了鬼字。從甲骨文看,鬼,象形也,下面是個“人”字,上面是一個可怕的腦袋,與人十分相似,從“鬼”的字大多與迷信、神怪有關。如,《禮記·祭義》“眾生必死,死必歸土,此之謂鬼。”[30]《楚辭·屈原·國殤》“身既死兮神以靈,子魂魄兮為鬼雄。”[31]《淮南子·本訓》“蒼頡作書,而天雨粟,鬼夜哭”。[32]《論衡·訂鬼》“鬼者,老物之精也。”[33]除此之外,還有很多的文獻也有對鬼的相關記載,如,戰(zhàn)國的《穆天子傳》《山海經(jīng)》;兩漢的《括地志》《列仙傳》;六朝的《列異傳》《靈鬼志》《拾遺記》《搜神記》;唐代的《傳奇》《獨異志》《古鏡記》;宋代的《稽神錄》《括異志》;金元的《誠齋雜記》《子不語》;明代的《剪燈新語》《西游記傳》《西游補》;清代的《聊齋志異》《平妖記》《三異筆談》《挑燈新錄》等。在各歷史時期,人們根據(jù)歷史文獻記載以及結合當時的社會環(huán)境豐富了“鬼”的含義,創(chuàng)造了符合時代特點與地方特色的各種“鬼”,賦予了鬼各種闡釋與解讀。所以,鬼的含義也是在歷史的發(fā)展中、在人們的邏輯思維發(fā)展中不斷地發(fā)生變化,從最初的“鬼,歸也”發(fā)展成為后來的邪靈、魔鬼、妖怪、吸血鬼、活死人等含義,有著鮮明的歷史特點、時代特點與地域特色。
從景頗族史詩“目瑙齋瓦”的記載以及現(xiàn)存的文化事象中,我們能夠了解到景頗族有神鬼概念、神鬼崇拜、神鬼祭祀與神鬼文化。在訪談景頗族著名學者趙學先、金學良、李向前時,他們也表達了同樣的觀點,以下是訪談內(nèi)容:
……
筆者:趙老師,我很想弄清楚景頗族到底有沒有神的概念。我看一些資料都在講景頗神鬼或鬼神,而一些學者認為景頗族是沒有神的,您怎么看這個問題?
趙學先:由于特殊的歷史社會原因形成了特殊的自然原始宗教。一般來講,景頗社會只是尊鬼敬鬼,在祭祀中一般不提神,只說哪種鬼哪種鬼。要說神,景頗族沒有具體的詞匯來描述。如果是神,可以說他是眾神之神、眾生之主。
筆者:那還是有神的觀念的,只不過景頗族鬼的外延比較大,已經(jīng)包括了某些神的概念,能否這樣講,善鬼即是神,惡鬼即是鬼呢?
趙學先:應該可以。
筆者:有些學者認為景頗族沒有像漢族這樣至上神的概念,是因為景頗族的歷史發(fā)展緩慢、經(jīng)濟落后等原因,是這樣的嗎?
趙學先:這樣的理解是符合馬克思唯物論的,當然這也是一種理解嘛。我們從歷史上看,其實在江心坡一帶奴隸制已經(jīng)發(fā)展得比較完善,你說這是社會發(fā)展緩慢的原因嗎,不見得吧。這有可能是景頗族的自然原始宗教觀念造成的,景頗族有天鬼、地鬼與人鬼,這就是原始自然崇拜與祖先崇拜的產(chǎn)物,當然是包括了神的概念,應該有神的位置,只是習慣了鬼的稱呼、鬼的祭祀①筆者于2015年1月14日在云南民族大學荷葉山住宅區(qū)1幢1單元301訪談了趙學先。。
……
筆者:謝謝金老師。金老師,我在整理資料的過程中,看到和聽到了很多關于景頗族鬼神觀念的解讀,有的說景頗族只有鬼,沒有神;而有的說景頗族具有鬼也有神的概念,您怎么看這個問題?
金學良:我認為景頗族是有鬼有神的。只是說在景頗地區(qū),在景頗人的觀念中,鬼的觀念很深入人心,鬼的觀念形成了一種傳統(tǒng)一種習慣,大多數(shù)景頗人一般只說鬼而不說神,但在實際的祭祀過程中,是能夠看出有神的觀念,有神的影子的。比如說,景頗的鬼分為好鬼善鬼,壞鬼惡鬼,這樣的區(qū)分很鮮明地說明景頗原始宗教里是有神的,神即是好鬼善鬼,只不過是沒有表達出來,實際是存在的。
筆者:為什么會存在有神無神的理解呢?
金學良:這恐怕是不同的研究者的不同理解吧。很多年前,有些學者在研究景頗族原始宗教時提出過景頗族神鬼的關系,他們認為,景頗族的宗教觀念中只有鬼,而沒有神,至少是沒有像漢族所崇拜的至上神的出現(xiàn)。他們認為,景頗族由于特殊的歷史原因及緩慢的社會發(fā)展水平,在景頗社會中一直沒有形成神的概念,伴隨的都是鬼的概念。這是從社會發(fā)展與宗教演變的角度來看待這個事的,僅從這點上看,看似有些道理。因為像漢族的神,它是人們經(jīng)過長期的加工整理,匯集了人們思維的高度抽象化與高度凝結化而成的,并在不同的歷史時期賦予其不同的內(nèi)涵與外化的形象,像道教中的各種神仙一樣。而景頗族沒有這樣的歷史條件與社會環(huán)境。
筆者:除了歷史社會原因外,還有其他原因嗎?
金學良:應該還有。比如說語言傳統(tǒng)語言習慣、各地的風俗也是不同的。我想有人認為景頗族沒有神,只有鬼,恐怕只是從語言上的認知。景頗語中確實很少提到神,神的詞匯非常少。但這不能說沒有神的觀念或概念吧。就像一個東西一個事物在不同的地區(qū)或語言中有不同的表達一樣,如“人”,漢語說“ren”,英語說“person”,景頗地區(qū)也是這樣的。如,我們一般說天空晴朗的時候說,“天是藍色的”,而緬甸的景頗地區(qū)的人們說“天是灰色的”,是因為緬甸高地地理位置的原因,天空經(jīng)常是灰蒙蒙的,即是是晴天天空也是覆蓋著一層灰似的。所以,我認為,景頗族的鬼的觀念應該包括神的概念,只是表達方式的不同而已。景頗的鬼應該包含“神”與“鬼”,不同的場合鬼的表達含義是不一樣的,有時候是指鬼,有時候是指神。
筆者:謝謝金老師,這個問題我基本清楚了①筆者于2014年12月18日在云南民族大學呈貢校區(qū)博雅院訪談了金學良。。
……
筆者:李老師,還有一個問題,景頗族的觀念里到底有沒有“神”的概念?
李向前:要說有,那就是天上的,就是天神。景頗族的神鬼概念與漢族的還不太一樣。神,就是天上的,如太陽神、雷神、風神等。鬼又分天鬼、地鬼與野鬼,鬼又分好鬼壞鬼善鬼惡鬼。在很多景頗地區(qū),祭祀奉養(yǎng)在家的就不叫鬼,那是景頗族的祖先崇拜,像漢族的家堂上供奉的祖先一樣,那些在家外邊的野鬼、餓死鬼、嫉妒鬼、難產(chǎn)鬼等才是鬼。景頗族的鬼分為天鬼就是天神、祖先崇拜,還有好鬼壞鬼善鬼惡鬼。
筆者:有的學者認為,景頗族沒有像漢族那樣的至上神是因為景頗經(jīng)濟社會發(fā)展緩慢的原因,是這樣的嗎?
李向前:應該說,這是一個原因。景頗族的歷史社會的確比較特殊,導致整體發(fā)展不如漢族。還有一個比較重要的原因是景頗族封閉的社會體系與結構,與其他民族接觸不多,特別是與先進的漢民族融合不多。更為重要的是,漢族的神,大多是在道教、佛教的基礎上形成的,而景頗族沒有這樣的宗教原因。景頗語的詞匯中沒有一個能與神相匹配的詞匯,如果要找,那就是“sagya”(釋迦),類似佛教的“釋迦摩尼”,當然,這是吸收了佛教的教義,受佛教的影響②筆者于2015年2月4日在德宏芒市德宏州文聯(lián)辦公室訪談了李向前。。
景頗族民間宗教信仰中的神鬼是一種特殊的文化現(xiàn)象,它區(qū)別于其它地區(qū)其它民族的神鬼概念,是景頗民族性與地域性相結合的特殊觀念反映。景頗族由于長期的遷徙與動亂,較長時間內(nèi)沒有形成一個完整統(tǒng)一的社會結構,從而造就了景頗族長期封閉、固步、發(fā)展緩慢、文化體系不發(fā)達的狀況,沒有像漢族那樣發(fā)達的文化結構與體系,所以長期以來,景頗族原始宗教里一直沒有神的概念,至少沒有像漢族所崇拜的至上神的概念。但這并不意味著景頗族從來沒有神的觀念,研究景頗族史詩“目瑙齋瓦”文本,可以找到景頗族最初只有24種鬼,后來演化成100多種鬼,對景頗族宇宙天地萬物形成之前及100多種鬼的研究后發(fā)現(xiàn),景頗族的鬼與神在很多場合是同一的,即景頗鬼亦是景頗神,在景頗族的觀念中,鬼神一體、神鬼一家,特別是宇宙世界自然形成之前的各種創(chuàng)世主,其實就是各種神靈。“在民族文明發(fā)展的低級階段,神與鬼由于形態(tài)相似,職能相同,故常常混淆或合一,并沒有高低貴賤之分,這種情況反映在神話中,就是神鬼并存,相互融合,相互斗爭,并且互為補充。”[34]魯迅也說“天神地抵人鬼,古者雖有辨,而人鬼亦得為神抵,人神淆雜,則原始信仰無由蛻盡。”[35]景頗族民間信仰中的鬼是個大范疇,有兼具鬼神的意思,不同場合鬼的表達含義也不一樣,有時候是指鬼,有時候是指神。鬼有善鬼與惡鬼之分、鬼能福人佑人也能禍人害人,祭鬼就是祭神。景頗族史詩“目瑙齋瓦”中詳細記述了神鬼同祖同宗、同形同構、同性同質(zhì),在長期的歷史發(fā)展與融合中形成了獨特的神鬼共生的景頗民間宗教文化,這是景頗族宗教文化最具特色的地方,也是景頗族傳統(tǒng)文化與其他民族傳統(tǒng)文化的主要區(qū)別。
3 結語
景頗族是一個十分特殊的民族,民族起源紛繁復雜、民族支系來源眾多、民族語言形式多樣、遷徙歷史迂回曲折,這樣的生境造就了景頗族歷史上政治制度的多樣性、文化習俗的獨特性與宗教信仰的復雜性。
景頗族民間宗教信仰中的自然觀與神鬼觀是景頗先民在長期的生產(chǎn)生活中的經(jīng)驗總結,是對自然界原始樸素的解釋,充滿遠古性、朦朧性、生態(tài)性與智慧性。景頗先民在生產(chǎn)力極度低下的環(huán)境下對自然世界進行感知、體悟與解釋,在沒有任何參照的情境下,運用人類早期的思維方式對各種未知的自然世界、自然現(xiàn)象給予情感的觀照,于是出現(xiàn)“靈魂不死”與“萬物有靈”的自然觀。在自然觀的聯(lián)動下,景頗先民憑借“以己度物”的方式通過幻想臆造出各種神鬼,并認為神鬼主宰整個自然界。因此,為了族群生產(chǎn)生活的延續(xù),各種神鬼成了景頗族祭祀、供奉與敬畏的對象。又因為景頗族特殊的歷史地理環(huán)境、人文政治環(huán)境與生產(chǎn)力低下的影響,景頗先民臆想出的神鬼不像其他民族特別是漢族的神鬼觀念,景頗族的鬼在很多場合與語境中其實就是神,神鬼之間并沒有清晰的界定,經(jīng)常出現(xiàn)神鬼相混、神鬼一體的現(xiàn)象,這是景頗族民間宗教信仰中十分特殊的地方,也是學者們可以繼續(xù)深入探究的問題。景頗族民間宗教信仰中的自然觀與神鬼觀在景頗族傳統(tǒng)文化特別是民間文化中扮演著十分重要的角色,原始樸素的自然觀與神鬼觀在今天的景頗族聚居區(qū)仍然發(fā)揮著作用。
[1]恩格斯.路德維希·費東巴哈與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4.
[2][3][4]愛德華·泰勒.原始文化[M].連樹聲,譯.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5:390,519,553.
[5]維科.新科學[M].朱光潛,譯.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7:162.
[6][7]列維-布留爾.原始思維[M].丁由,譯.商務印書館,1981:94,95.
[8]吳中勝.萬物有靈觀念與中國文論的人化現(xiàn)象[J].中國文化研究,2011(2):174-179.
[9]張強.萬物有靈:人對自然的初步讀解[J].南京政治學院學報,2002,18(3):38-42.
[10][11][15][19]蕭家成.勒包齋娃研究:景頗族創(chuàng)世史詩的綜合性文化形態(tài)[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47,48,54,13.
[12][32]劉安撰,高誘注.淮南子[M].北京:中華書局,2010:235,116.
[13][33]黃暉.論衡校釋[M].中華書局,2006:472,934.
[14][16]李向前.目瑙齋瓦[M].芒市:德宏民族出版社,1991:1-2,17-18.
[17]張家成.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的生態(tài)智慧[C]//中國武義·國際養(yǎng)生旅游高峰論壇暨鄉(xiāng)村生態(tài)休閑養(yǎng)生文化研討會論文集,2011.
[18]曾繁仁.生態(tài)文明時代的美學探索與對話[M].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2013:42.
[20]張樹禮.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的生態(tài)智慧[J].中國林業(yè)產(chǎn)業(yè),2014(11):42-44.
[21][22][23][27]老子·莊子[M].呼和浩特:遠方出版社,2004:57,11,14,69.
[24][29]許慎撰,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3,434.
[25]王弼注,孔穎達正義.十三經(jīng)注疏·周易正義[M].北京:中華書局,2011:197.
[26][30]禮記[M].呼和浩特:遠方出版社,2004:102,105.
[28][34]周明.神、鬼、人:三位一體的神話結構[J].社會科學研究,1989(2):89-94.
[31]楚辭[M].呼和浩特:遠方出版社,2004:43.
[35]魯迅.中國小說史略[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5:22.
責任編輯劉宏蘭
10.14180/j.cnki.1004-0544.2017.05.006
B989.1
A
1004-0544(2017)05-0034-08
2016年云南師范大學博士科研啟動項目(16SQ016)。
徐俊六(1982-),男,云南昆明人,法學博士,云南師范大學文學院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