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爸的生活課
佚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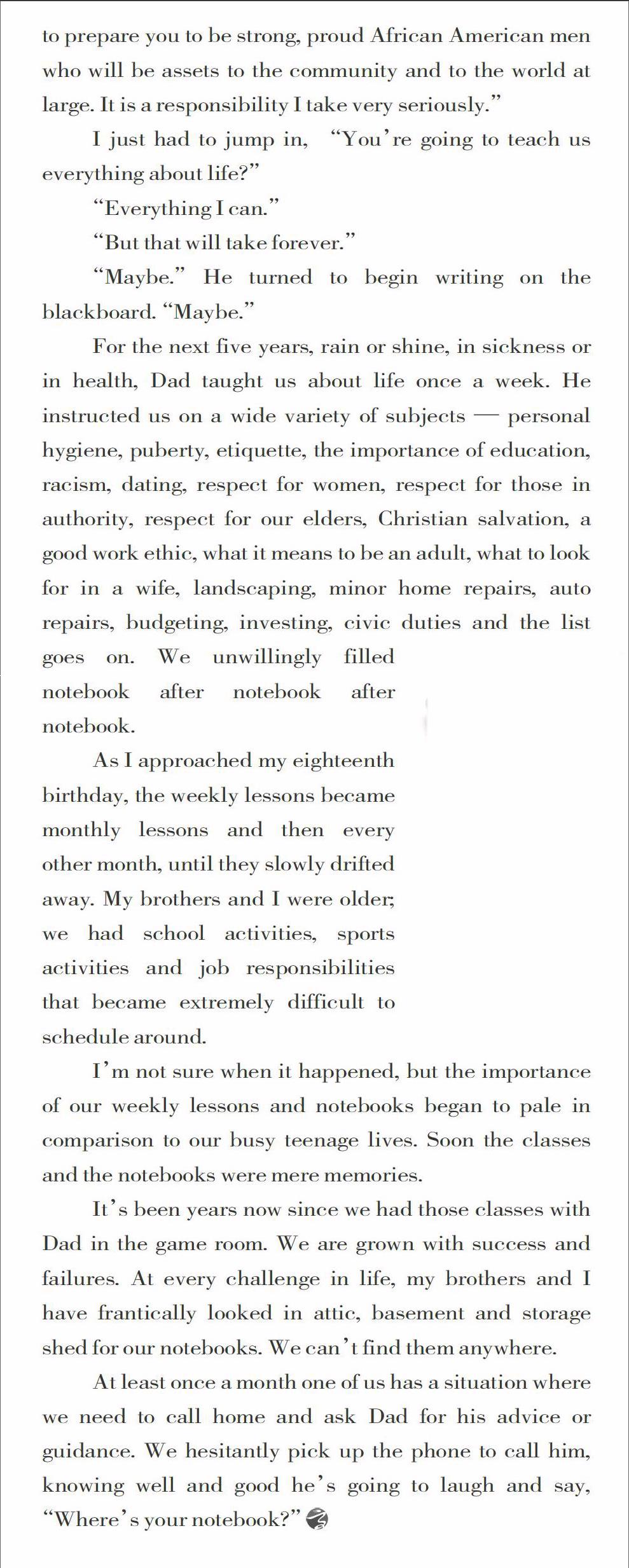
我13歲的時候,爸爸把我和兩個弟弟叫進家里的游戲室。我當時特別興奮!我以為我們幾個會一起玩臺球,或者彈球,甚至還想著可能會一起看電影。
爸爸在我們到達游戲室前,大聲喊道:“帶筆記本和筆過來。”
我和弟弟們立馬停下了腳步,驚恐地相互看著。他的要求很奇怪,我們興奮的感覺瞬間變成了恐懼。這讓我們感覺更加嚴肅和無趣,就好像家庭作業、家務,甚至是更糟糕的家庭會議。
我們拿上各自的筆記本和筆,心里仍然想著爸爸召集我們的原因。我們排除了家庭會議的可能,因為媽媽現在還在外面逛街。
走進游戲室,我們看到三把金屬折疊椅面向一塊大黑板。爸爸讓我們坐在椅子上,而不是坐在離我們不遠的軟墊沙發上。
他嚴肅地說道:“我想要你們集中注意力,所以才讓你們坐在椅子上。”
我們立刻就撅起嘴巴,面露不悅,然后就開始哼哼唧唧地不停抱怨。
最小的弟弟問:“媽媽在哪兒?我們不是要等媽媽嗎?”我坐在那把十分不舒服的金屬椅上,一聲不吭地扭動著。
另一個弟弟也嘆息地問:“需要很久嗎?”
爸爸平靜地說道:“你們的媽媽要幾小時后才會回來,如果你們一定要知道的話,她回不回來和我們沒有一點關系。這得多長時間完全取決于你們,你們越是專注,學到的東西就越多,進展就越快,這事兒就會結束得越早,明白了嗎?”
“是!先生。”我們毫無熱情地回答。
然后,爸爸就開始上課了:“現在,我們要做的是,開一個只屬于我們男人的家庭周會。會議時間定在每周六早上,但是如果你們學校有課,或者有體育活動,會議時間就改在星期天去教堂做完禮拜后。我將會教你們我從生活中學到的東西,將你們培養成對社區乃至整個世界有用的堅強而自豪的非裔美國人,這是我的責任。我要慎重對待。”
聽到這,我忍不住插一句:“您要教我們生活中的所有事情嗎?”
“盡我所能。”
“那會花很長時間哦。”
“也許。”他轉過身在黑板上寫下:“也許。”
在后來的五年里,無論是天晴,還是下雨,無論健康,還是生病,爸爸每個星期都會給我們上一次關于生活的課。他教授的內容非常廣泛——個人衛生,青春期,禮儀,教育的重要性,種族,約會,尊重女性,尊重權威,尊敬老人,基督教的救贖,良好的職業道德,成年人該承擔哪些事情,該找一個怎樣的妻子,綠化,家里的小修理,汽車維修,預算,投資,公民義務,等等。我們極不情愿,但還是寫了一個又一個筆記本。
當我快到18歲時,每周一次的課程變成了每個月一次,然后兩個月一次,直到最后慢慢消失。我和弟弟們都長大了,我們要參加學校的活動和體育運動,還要承擔工作上的責任,要安排好這所有的事情變得極其困難。
我不知道從什么時候開始,和我們忙碌的青少年生活比起來,我們每周一次的課程和用來記錄的筆記本,已經不那么重要了。很快地,這些課程和筆記本只存在于我們的記憶里。
爸爸在游戲室里給我們上課的時期已經過去很多年了。在成長的過程中,我們經歷了成功與失敗。在接受生活中的每一次挑戰時,我和弟弟們都會瘋狂地跑去閣樓、地下室和儲物間,尋找我們的筆記本。可是,我們翻遍了每一個地方都找不到它們。
每個月至少有一次,我和弟弟們中的一個會遇到一些難題,需要給爸爸打電話,請他給建議或指導。我們拿起電話,卻遲遲不敢給他打,因為我們知道,他一定會笑著說:“你們的筆記本去哪兒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