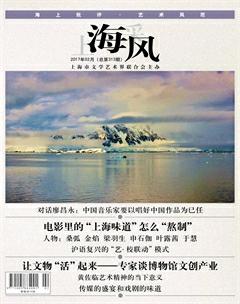出外景
陸壽鈞
老電影人都知道,過去攝制組到外地去尋找和拍攝符合劇情的場景,叫“出外景”。一部影片,全在攝影棚和本地拍攝的情況很少,所以“出外景”是電影人的常態,往往一“出”就是幾個月,電影人和他們的家人對此都已習以為常了,你能“出外景”,證明你正有活在干,大家都還需要你。最怕常在家和廠里閑窩著,沒活干,那是要讓人看不起的。所以,電影人和家人一說起“出外景”了,常會帶有一種自豪感。我熟悉的一位漆工師傅得了白血病,領導為了照顧他的身體,不再讓他“出外景”了,他反懷疑起是否領導對他有什么看法,那時的電影人啊,就這樣!
老電影人都知道,“出外景”是個既辛苦且還帶有一定危險的活,那么多人在人生地不熟的異地拍戲,難免照顧不周,無論食宿都不如家中方便,至少不如在家中安全。攝制組又常處于搶拍狀態,為了掌控好拍攝周期,每天都是沒日沒夜地干,把人累得昏頭昏腦,偶爾也會因此喪命的。1974年,重拍《渡江偵察記》,演員徐俊杰感冒發燒,為了不影響拍攝,攝制組送他去當地的衛生所打了一針青霉素,想不到竟過敏而亡。他1962年畢業于上海電影專科學校,高我一屆,大家彼此都很熟悉,真想不到在電影廠中只工作了十二年就“走”了,為拍電影而獻身,“走”在外景地。如今,我一寫起這段往事,眼前就浮起他那熟悉的笑容……有位大家都叫他“阿彪師傅”的照明技師,身體特別壯實,卻在外景地誤食了毒蘑菇而身亡。另一位照明技師收工時去江邊洗手,不慎跌入江中淹死了。還有一位與我同姓的年輕攝影師,在北京“出外景”時因工傷而沒能救治過來……這樣的例子,比我還老的電影人還能舉出不少。誰都沒有統計過電影人“出外景”后沒能回家的有多少,但誰都不會由此而懼怕“出外景”,只是一說起這些,大家都會有一種悲壯感!
“文革”后,我一直在文學部搞劇本工作,一個劇本搞成后就移交攝制組去拍攝,再轉到另一個劇本的工作上去了,基本上沒有跟隨攝制組“出外景”的機會。唯一的一次是在1983年的春節前,我責編的《漂泊奇遇》是廠里的重點劇目,移交攝制組后,導演于本正邀請我與兩位編劇跟隨攝制組的主創人員按原著艾蕪先生《南行記》的路線一起走一遍,他們看外景,我們爭取把劇本改得更好些,在這過程中,讓我體驗了一下“出外景”的自豪感和悲壯感。自豪感就不多說了,我們接到這個邀請,證明攝制組還需要我們,并相信我們還能把劇本改得更好,當然自豪!悲壯感則是身處在這荒無人煙、野獸出沒的深山老林中的人都會油然而生的。偶爾路遇一兩個少數民族的壯漢,還都身佩長刀防身呢,我們一行,卻都赤手空拳,如遇不測,怎么去應對?開弓哪有回頭箭,我們幾個人就這樣一路走完了當初艾蕪先生的南行行程。幸好,途中有驚無險,只遇到過一個小偷,被山東漢子軍人出身的攝影師彭恩禮一把抓住,送交了當地的派出所。我一路在想:以后攝制組要在這險惡的環境中生活、工作幾個月,將遇的艱險,誰都難以預料,讓我更感受到了他們的悲壯感。彭恩禮16歲就參軍,20多歲就在上影當上了攝影師,先后拍攝了《碧玉簪》《尤三姐》《藍光閃過之后》《石榴花》《喜盈門》《漂泊奇遇》《咱們的退伍兵》《滴血鉆石》等20余部影片,卻離休沒幾年就病故了。電影人一年四季常在外奔波操勞,在自豪感和悲壯感中自愿透支,一到老,就會呈現其后果。彭恩禮重病在身時,卻還在小區的老年活動室里有說有笑,走時卻又悄然無聲,更讓我感受到了老電影人的自豪感和悲壯感……
上世紀九十年代中后期,隨著電影廠的改革,文學部被撤銷,我這個黨支部書記兼副主任也與大家一樣,成了下崗人員,讓我感受到了另一種悲壯感,并自愿去深化這種悲壯感。我未接受特殊照顧,被重新安排工作,也不要每月三百元的生活補貼,自行在廠里組建了一個二級制片公司,自行籌資,自己寫劇本,想拍一些自己想拍的影視劇。同時,也可為廠分憂,解決一部分人的上崗。在這些年中,我們公司拍了不少影視劇,是我這一生中值得回憶的歲月。其中有部名為《熒屏后面》的長篇電視連續劇在創作和攝制過程中所遇到的一些事則感動了我后半輩子。這部電視劇是寫“電影人在改革中也可拍電視劇了”中所發生的那些事,我想要及時反映老電影人在改革中的生存狀態,這也是我的責任,其中當然也有我的影子,更有上影人的風采。劇中有個副導演的角色,是我依據高我一屆的學長鄭家聲塑造的,他和徐俊杰是同班同學,從上海電影專科學校畢業后一起分配到上影演員劇團工作,因他的形象不適合演工農兵,一直未有發揮的機會,后轉行到導演部門工作,當過好幾部戲的副導演,勤懇工作了一輩子,快到退休時,卻連副高(二級)都未評到,而此時他又得了絕癥,我曾為他仗義在一次評定職稱的會議上疾呼過,終于在他臨走時,評到了副高……他的妻子倪以臨,是宋慶齡母親倪家的后代,畢業于上海戲劇學院表演系,也是上影演員劇團的演員,很有才華卻一直低調,而當她得知我要拍這樣一部電視劇時,卻懇求我一定要讓她來演劇中那個副導演的妻子,她說她有這個生活經歷,肯定能演好的。我怕太刺激了她,有些于心不忍,可她還是堅持要演。雖然這個角色只是劇中的一個配角,戲份不多,可她演得極其認真,真得讓誰都會感覺到就是這么回事!她在外景地演完了最后一場戲時,卻再也忍不住地嚎啕大哭了一場,攝制組的人誰都默然無聲,難以上前去說上一句安慰的話,只能任她傾吐完心中的苦水……這種悲壯感誰會忘卻?!在此劇中飾演導演的是老演員馮笑老師,他比我年長10歲,但在我小時候就在看他出演的影片了,他把戰爭年代的小戰士演得栩栩如生。其中,《鐵道游擊隊》里的那位彈土琵琶的小游擊隊員,更讓人難以忘懷。“彈起我心愛的土琵琶,唱起那動人的歌謠……”,那充滿勝利信心的歌聲一直縈繞在我耳邊。我們這代人中,很多人是哼著這首歌長大的。他還拍過很多影片,后來也執導過一些電視劇,應該說,他是輝煌過一段時間的。他離休后安于平淡,我常見他在傍晚時分與他所養的一條小狗一起散步,見了誰都笑瞇瞇的,對一切都顯得非常滿足。我常想,曾經輝煌過的人在退下來后能有這種心態應該是很不容易的。我們在籌拍《熒屏后面》時,其中的“導演”一角,大家不約而同地都想到了他。他看過劇本后,一點也不計較酬金的多少,也沒提出任何要求,就答應了我們的邀請。他說:“當了一輩子的影視演員,最后再演演自己,也該!”于是,他息影六年后再次出山了。攝制組的人員大多比他小一輩或半輩,他卻從未拿過一點架子,兢兢業業地把這個角色演好。當演到劇中他的副手——一位默默無聞卻又勤懇了一輩子的老副導演倒在自己的工作崗位上的這場戲時,他的雙眼閃亮著發自內心的淚花,卻又平靜地敘說著自己的經歷和內疚,這場戲,讓在場的每一個人都深受感動。在做后期時,他希望能自己配音,而當他發現自己工作的節奏已跟不上整體的節奏時,又主動放棄了配音,一切都服從整體的需要。其實,他已大病在身。醫院查出他的不治之癥后,家屬為了減少他的痛苦,希望他多活些日子,一直對他隱瞞著。我唯一能為他做的事是,讓攝制組突擊出一個像帶來,無論如何讓他看到自己演的最后一部電視劇。那天,我把這盤像帶送往他家時,他在家過完了節日正準備去醫院。他靠在一張舊床上,人一下消瘦得不像樣子,然而,他依然是滿臉笑容。他似乎還不知道自己真實的病情,但我卻又感到,他可能又一切都知曉,只是為了不讓親朋們痛苦而強忍著自己的痛苦罷了。后來,聽他的家屬說,他在我們離開后,堅持著看了其中的幾集才去了醫院,不久,就傳來了噩耗……一位從戰爭年代走來的紅小鬼,在為新中國的影視事業辛勤勞作了一輩子后,默默無聲地離開我們了。他的級別還不夠在報上發訃告,送行的人也不多。一切都顯得默然無聲。末了,又去了。但他那土琵琶的歌謠還留在人間,他在《熒屏后面》的“絕唱”,又讓我在心中流淚。據說,他臨終時,讓家人不必悲傷,權當他又去“出外景”就是了……我聽后心中五味俱全,我創作《熒屏后面》,想體現老電影人的自豪感和悲壯感,然而,在這部片子攝制過程中所發生的一切,讓我一直懷疑到現在:這種自豪感和悲壯感我能體現得了嗎?!
我自2002年4月退休至今已近15年,在我所居住的上影公寓內每年都有老電影人相繼離去,住在上影公寓外離去的人更多。他們離別時大多關照家人:不必悲傷,也不要去驚動年老多病的老同事們,就算我去“出外景”了……老影人們大多已沒有正常的“外景”可出,而“出外景”已成了他們的“歸宿”,人人都能坦然面對——
老廠長徐桑楚最后一次住院前,還坐著輪椅讓人推著來到上影公寓的老年活動室來與大家一一握手告別……
老導演徐昌霖在直感將不久于人世前,讓家人搬了把藤椅在上影公寓大門口坐了整整兩天,笑對著進出的上影人,與大家告別……
執導過我編劇的《通天長老》《燭光里的微笑》的老導演姚壽康和吳天忍,在得了絕癥后,前者仍然在上影公寓的老年活動室中盤腿而坐,與大家談笑風生。后者則仍然還與大家一起打牌說笑。他們都向大家聲明過:死后不開追悼會,當我們去出外景就是了……
在我突發心肌梗塞后,女導演史蜀君給我打來了電話,熱情地向我推薦了一張藥方。而當我從外地休養回來后,卻聞她已因“心衰”而病故,后來才知道,她早已得了絕癥,只是不愿對人言說而已……她的病先于我,重于我,卻還在關心我,真不知讓我說些什么好。
在我剛寫完此文時,又傳來一直與史蜀君搭檔拍過多部好電影的攝影師趙俊宏病故的噩耗,他臨行前也關照家人不開追悼會,權當他又去“出外景”了……
我們文學部的老同事也已先后“走”了好幾位:金大漠、李偉良、謝友純、孟森輝、斯民三、沈寂、邊震遐……對于這些搞文學工作的編劇、編輯來說,經常外出組稿和“下生活”等于“出外景”,與往常一樣,一個個都走得悄然。集老軍人、老記者、老作家、老編輯、老編劇一身的邊震遐在行前寫下了這么一段深情的話:“我此生最大的財富是友情,友情也是我畢生不堪承受之重,即使我鞠躬盡瘁,也不能表達我的感動于萬一、感恩于萬一和感奮于萬一。”是的,上影老影人們臨行前帶走的和留下的都是這份令人不堪承受之重的友情,這就讓“出外景”的自豪感和悲壯感更含深意、更為動人!他們都為上影曾有過的輝煌作出過貢獻,為上影新的輝煌奠定了基礎,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改革開放的新時期為此而作出過種種自我犧牲并大大透支過體力和精力,然后,他們又從未后悔過,逐一臨行時,都能坦然面對。如今,一個個開著小轎車進出上影的后人們,該如何去面對以往的這些老上影人呢?倘若漠視了他們,倘若利用了上影這個平臺賺足了名利后又一個個“華麗”轉身而去的話,那就多少顯得有點厚顏無恥了!當你們也到“臨行”時,還存幾多坦然?
上影真要取得新的輝煌,上上下下能否傳承和弘揚上影的光榮傳統是關鍵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