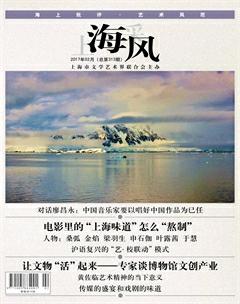黃佐臨藝術精神的當下意義
黃佐臨是中國話劇史上響當當的、至今依然不斷被提起的名字。作為上海人民藝術劇院的創始人之一,黃佐臨為上海乃至全國的話劇事業發展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他倡導的“以赤子之心,不求名不求利,做終生獻身于話劇事業的真誠藝術家”的精神激勵著一代代話劇工作者。2016年是著名戲劇、電影藝術家、導演黃佐臨先生誕辰110周年。近日,由中國劇協、市文廣局、市文聯指導,SMG(上海廣播電視臺、上海文化廣播影視集團)主辦,上海劇協、文廣演藝集團、上海話劇藝術中心承辦,上海戲劇雜志社、上海采風雜志社協辦的“上海市戲劇家協會成立60周年重要研討系列——黃佐臨藝術創新精神繼承與發展”主題研討會在上海文藝會堂隆重舉行。國內眾多戲劇界專家、藝術家、藝術工作者出席此次研討會。會上,部分嘉賓和黃佐臨先生家屬黃海芹作了主題發言,回憶佐臨先生的生活點滴、為人處事,探討如何深入理解他的戲劇觀,如何更好地繼承、弘揚佐臨先生的藝術創新精神。
黃佐臨——舞臺上一個站著的人
黃海芹(黃佐臨女兒):我很幸運生活在這個家庭里頭,我父親和母親對我們的培養是非常民主、非常自由的,沒有任何限制,讓我們根據自己的個性去發展,我覺得這是他們對我們最大的信任和包容。我們一共是五個兄弟姐妹,四個女兒一個兒子,父親對我們五個人的教育是完全不一樣的。我父親和我媽媽都是很真實的人,所以在當時的社會里能夠受到大家很真心的愛戴,這是很不容易的。我爸爸在文化大革命當中還出了三件“怪事”:第一,他沒有在群眾運動中挨過一次打,大家很敬愛他;第二,在文化大革命當中他只能得15元的生活費,人家都不夠花,可是他卻省出了一百元,人家問他你要干什么,他說我擔心我那些孩子們。當時不能夠通信息,作為他孩子的一員,我心里一直是非常感動的;第三,他好不容易從“牛棚”里出來,聽說上海人藝排了《第二個春天》,他自己買了票去看,看了還寫了好幾條意見交上去,于是他在家里受到了我們幾個兒女的“批斗”:你現在不是權威了,還提什么意見?但他不管,他就是這么執著。記得在他年紀很大時還排了《家》,從劇院走到我們家其實蠻近的,但他有的時候都走不回來,要到邊上歇一歇,是路人把他送回來的。當時我們跟他說,你不是小青年了,干嘛這樣拼。他常常不理我們,然后輕輕地嘀咕一句說:不工作,活著干什么?我們家里頭有好幾個是搞戲的,大家很好奇我們在家里面怎么談戲的,其實我們就是很隨便地談,想到什么談什么。父親對我們的教育是潛移默化的,教我們怎么做人。我姐夫是搞舞美設計的,他為父親的墓碑設計了好幾種方案,其中有一種是:在舞臺上一個站著的人,當時他分別拿給了我姐姐和我們幾個子女看,結果我們不約而同地點著“舞臺上站著的人”說,這個最好,因為他給我們的榜樣就是:永遠站著的一個人。
童雙春(滑稽表演藝術家):我跟黃先生接觸雖然不是很多,但是黃先生的一舉一動、一言一行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我永遠不會忘記4月14號這個日子,這是我們滑稽劇團合并到上海人藝的日子。合并了以后,我們滑稽戲選擇的素材、表現的方方面面都比較寬廣了,內容也比較深厚了,演出節目的質量、表演水平也有所提高。此外,我覺得黃先生是個伯樂。那時候我們排《梁上君子》,黃先生還特命吳媚媚當助理導演。我們知道吳媚媚老師的表演是非常好的,但是她文化知識比較淺,是小學文化程度,所以我們做夢也沒有想到,黃先生會讓吳媚媚做助導的位子,吳媚媚當時是既激動又高興。黃先生對于我的滑稽戲創作也有很大的幫助。比如,我有一個戲《囧人黃小毛》,黃先生看過后說這個是好戲,可以再放大一點,超過一個多小時就可以成為一個大戲了。我們被并入人藝后,劇院讓我們到青浦農村去勞動,到工廠去跟工人朋友拜弟兄,通過跟農民和工人接觸以后,在農村、工廠里經過鍛煉后,我們思想上也有了一些變化,各方面都有所提高。那時我們到工廠、農村演了不少作品,得到了社會各界的好評。所以我覺得黃先生是一個伯樂,他善于發現好的本子、好的表現手法。黃先生的中國民族的概念非常強,他把我們吸收進來,心里想的是中國式的喜劇。像黃先生這樣的大師真的不多見,我想,只有把我本身的工作做好,才是我們對黃先生最好的報答。
熊源偉(上海戲劇學院教授):我跟佐臨老師有兩次比較親密的接觸。1962年時,佐臨老師到上海戲劇學院給我們上了兩天的課,就講布萊希特,一下子洞開了我的視野。改革開放后,我到了北京,成為最早研究現代派戲劇的人之一。我覺得這跟佐臨老師很有關系,他讓我知道應該用多元的視角去看世界。另外一次接觸是1988年,排《耶穌·孔子·披頭士列儂》,那是沙葉新寫的本子,請我來排。一開始沙葉新想請佐臨老師給我當藝術指導,我高興得不得了,那時佐臨老師就和我們在人藝的食堂吃飯聊,后來我還到他家去聊,聊完以后他跟沙葉新說,熊源偉可以導,我就不要當藝術指導了。剛開始我以為佐臨老師看不上我,不肯當藝術指導,沙葉新說不是的,佐臨老師相信你。后來我們演出以后,佐臨老師還到臺上來看我們,表揚了我們。這次接觸讓我更感受到了一個長者的風范,素養、修為、人格的魅力。我覺得佐臨老師這種大度的、很紳士的、又學貫中西的腔調,是我們上海的腔調。我做學生時,正好是滑稽劇團跟方言劇團并入上海人藝時,因此我們看了很多滑稽戲。當時佐臨老師把嚴順開找來排《一千零一天》,自行車在臺上騎來騎去,我看得入迷。我覺得喜劇真的是佐臨老師的一個理想,他希望在上海能夠有喜劇院,在大師的眼里,滑稽戲一點都不低檔,是很高檔的。中國現在太缺乏喜劇,人們需要喜劇,不要讓那些爛小品把中國喜劇搞爛了。所以我認為佐臨老師這個愿望,有關部門應該考慮。此外,我總覺得佐臨老師的貢獻與他目前這個地位還不夠對等,上海應該把佐臨老師當作上海的人文標志之一。
任廣智(國家一級演員):我很榮幸和佐臨先生合作過兩次。他最后一個戲是《鬧鐘》,當時佐臨先生派人把劇本送到我那里,我看了后,第二天到佐臨先生家去,我說了一句,黃老您敢導,我就敢演。可以想見這個劇本當時是處在一個什么樣的狀況下,這也反映了佐臨先生的膽量。談到佐臨先生的創新精神,沒有膽子是沒有辦法創的。他確確實實貫通中外,他研究了蕭伯納、易卜生、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等,又對滑稽戲、話劇、京劇、芭蕾舞、電影等各種藝術門類進行了研究,從中國的戲曲中吸取很多養料,這種集大成,在全國是很少有的。在排練過程當中黃老給我的感受是,不但有擔當,有探索,有信任,還有創造,他始終探索的是一條中國話劇表演的道路,他沒有局限在易卜生、蕭伯納、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布萊希特或梅蘭芳上,他始終探索的是如何用更加真善美的方法來體現內容,讓話劇更深入地發展。我們要研究佐臨先生的創造精神究竟是什么,哪些內容構成的,怎么發展起來的。話劇是門實踐的藝術,但是理論上的建設確實也是需要的。我們有責任沿著佐臨先生開創的中國的話劇表演道路走下去,進一步努力,而且不光是演出、頒獎的事情,理論建設也應該有所作為。
黃佐臨的戲劇觀與戲劇理想
榮廣潤(上海戲劇學院教授、戲劇評論家):佐臨先生無疑是大家一致公認的上海話劇乃至中國話劇一個旗幟性的人物。1962年的廣州會議上,他發言時提出了寫意戲劇觀。我覺得當時產生的震動以及我們今天來看它的意義,都是非常重大的。第一點,佐臨先生的寫意戲劇觀可以說是他一生追求的目標,佐臨先生求藝時候產生的戲劇理想,他用一生來實踐、來追求,這種精神非常了不得。第二點,他從布萊希特著手,要求大家打破戲劇觀的單一跟狹隘,但是他并不是簡單地去追隨或者模仿布萊希特。他更希望吸收布萊希特的東西,來形成戲劇能夠揭示生活的本質,能夠表達生活的詩意這樣一個目標,這是超越生活表象、超越藝術模仿生活的一個美學理念、一種追求,我覺得對今天來講非常有啟發。因為我們今天停留在生活表象的作品非常多,電視劇更是這樣,非常世俗化,我們的戲劇作品中,沒有對生活的本質、生活背后的詩意進行深入探索的作品比比皆是,而佐臨先生一生不滿足于那些東西。第三點,佐臨先生的寫意戲劇觀非常開闊。上世紀二三十年代,佐臨先生在英國生活,對當時西方的戲劇流派非常了解。他是一個戲劇視野特別寬闊的人,了解西方戲劇思潮,學術非常淵博,但是他的取向很清楚,就是要把西方的寫實的、理性的戲劇理念和中國的注重情感、寫意的戲曲緊密結合起來,他要創造的是中華民族特有的一個演劇體系和戲劇體系,佐臨先生的志向真的是非常遠大。
俞洛生(國家一級導演、演員):我覺得黃院長的《漫談“戲劇觀”》是他的宣言,這個宣言不僅對上海,對全國的話劇界起的作用也是不可估量的,而且隨著時間的推移,越來越能體現他對全國話劇事業發展的推動。我覺得他介紹布萊希特也好,提出向民族戲曲學習也好,醉翁之意不在酒,不光是介紹這些不同的戲劇觀,他的目的是要拓展我們的視野,開闊我們的眼界,使我們對不同的戲劇觀有所了解,而且可以在我們的創作當中去應用它。《中國夢》可以說是黃院長在世時比較滿意的一個體現寫意戲劇觀的作品,但是它既不是布萊希特的,也不是完全民族藝術化的,在《中國夢》當中有許多非常有創造性的表導演的手法,這是黃院長融會貫通以后的獨特的創造。我覺得這個戲非常值得再完整的復排一下,從這里面我們可以去研究黃佐臨的創新精神,他的戲劇觀,他所追求的一些東西,這是蠻有價值的。我們來繼承黃佐臨的創新精神,要研究他的劇目,要把文字的東西變成形象的東西。黃佐臨在上海人藝幾十年,帶領了一群很杰出的藝術家,出了很多優秀的作品,上海人藝也形成了自己獨特的品格,上海人藝的創作思維的開放性、藝術風格的質樸、創作的貼近生活,以及具有南方地域文化風格的一種包容的精神,這種風格確實跟北京人藝是不同的。
王曉鷹(中國劇協副主席,國家一級導演):佐臨先生提出的寫意戲劇觀對中國戲劇的影響,既體現在理論概念上,更體現在創作實踐上,無窮無盡的邊界的創新探索由此開啟。最讓人吃驚的是,黃老在那樣的環境當中能夠用那樣的眼光看待中國戲劇,一個高瞻遠矚的戲劇家的影響會在時代中漸漸地顯現出來。最初我看到寫意戲劇觀如同發現了新大陸。至今佐臨先生的導演思維框架還對我現在的導演創作有著顯而易見的影響。中國戲劇發展到今天,黃佐臨先生的寫意戲劇觀已經體現得非常廣泛了,廣泛到大家進行創作時,特別是年輕一代的戲劇人在進行創作時,已經很少會想到寫意戲劇觀這個概念。寫意戲劇這個創作概念早已成為大家創作思維中非常自然有機的一部分。黃老當時提倡喜劇,他說喜劇里有很多內容是幽默的、智慧的,同時是批判的、諷刺的,這樣的喜劇跟我們現在的那種娛樂的、淺薄的喜劇有本質上的不同。所以我覺得我們要有意識地去踐行黃老先生的寫意戲劇觀,主動地踐行他渴望建立的有中國特點的演劇學派,這不是出一兩個作品的問題,而是戲劇界有相當一部分人或者年富力強的劇團能夠有意識地追尋黃老先生的戲劇理想的最本質的部分,讓他在我們今天的戲劇創作當中體現他的價值。這是上海話劇藝術中心,也是我們這一代導演能夠去紀念黃老先生的最好的方式。
孫惠柱(上海戲劇學院教授):黃佐臨先生上世紀二三十年代在英國留學,使得他了解了全世界劇壇的全局,然后再回過頭來看我們的中國戲曲。他和北京人藝的焦菊隱一樣,兩位都是學貫中西的人。但是黃佐臨比焦菊隱更厲害的一點是:把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布萊希特、梅蘭芳這三個名字放在一起,至于叫體系或方法或風格都無所謂,能夠把這三個名字放在一起是最大的學術的眼界。現在講的更多的是黃佐臨在推廣、介紹布萊希特方面做的貢獻。事實上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方法最早在中國的推廣,黃佐臨和他的夫人丹尼也做了不少工作。斯坦尼的第一本書,不是俄文出的,而是英文出版的,那時佐臨夫婦正好在英國留學。后來1938年他們在重慶教課的時候,已經用上了斯坦尼的方法了。所以蘇聯專家來到中國十多年前,就是佐臨夫婦在傳播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但是黃佐臨先生眼界廣,絕不局限于某一個體系或者某一種方法,那時我們需要寫實的表演方法,他就集中精力教現實主義的表現方法,斯坦尼體系的。然后他發現這方面一家獨大了,他又介紹布萊希特,又不斷地推我們的戲曲。在他的眼中,實際上布萊希特、斯坦尼、梅蘭芳雖然有各自的特色,但是是可以打通的。
佐臨精神的當下意義
喻榮軍(上海文廣演藝中心副總裁、國家一級編劇):在2001年,我第一次讀到佐臨先生的《振興話劇戰略發展十四條》,當時的體會是相見恨晚、震驚不已。第二天,我在給劇院市場部開會的時候,我就說我們已經做的、現在正在做的、未來準備要做的,其實早在1988年,我們的佐臨院長就已經告訴我們該怎么做了。我們縱觀佐臨先生所說的關于話劇發展戰略的十四條意見,應該作為一個整體來看,它們是相輔相成、缺一不可的,佐臨先生從話劇發展的各方面都提出那么細致的統一的想法,這對我們來說有著無窮的力量。
今天,我們開這個紀念佐臨先生誕辰110周年的研討會,其意義在哪里?佐臨先生對我們的未來意味著什么?我覺得對我們話劇中心來說,佐臨先生意味著靈魂,對于我們的創作者來說,他意味著藝術家的良心,對我們話劇藝術來說,他意味著一種堅持和創新的精神。如今,話劇中心的定位是創意、品質、多元,這三個詞不是我們自己憑空想出來的,它是從佐臨先生的精神里來的,其實佐臨先生的精神就是我們海派話劇的風格,這跟我們這座城市的風格也是相融的。佐臨先生導演布萊希特的作品《伽俐略傳》的一句臺詞,就是:思考是人類最大的快樂。我覺得佐臨先生對于我們的未來來說,就是意味著我們要不斷地去思考,意味著我們作為一家劇院,作為一個藝術工作者,在中國的現實環境下,我們要懂得如何去處理戲劇和權力的關系,如何處理戲劇和市場的關系,如何處理戲劇和資本的關系,因為權力的蠻橫、資本的誘惑和市場的擠壓,它時刻讓我們思考:如何保持一個戲劇工作者的良心,要承擔一家劇院的責任,要為話劇藝術的發展而努力。
陳雨人(SMG藝術總監):佐臨先生在中國的戲劇家當中是具有非常特殊地位的一位專家。他提出寫意戲劇觀具有很大的創意和創新,他這種創新是站在我們民族戲劇的立場上,能體現我們民族戲劇的一些特點。而且他在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和布萊斯特、梅蘭芳的演劇風格當中找出了一些差異和共同點。上世紀八十年代末,我看過他導的《中國夢》,體現出來的一些詩情,中國舞臺藝術的一些形式,寫意的感覺,讓我們這些學戲劇的人很有感觸,知道了很多新的東西。佐臨先生在長期的實踐當中,無論是排戲還是拍電影,都很自覺地以人民大眾為中心,他曾經說過,文藝工作者必須要有高度的社會責任感,運用自己的敏銳感覺反映大眾生活,以啟示人生和社會的正確關系。樸素的、自然的、明確的、健康的、有血有肉的,帶泥土氣息的才是真正的文藝工作者。當前我們的戲劇也碰到了前所未有的機遇,我們今天紀念佐臨先生,就是要學習佐臨先生為舞臺藝術孜孜不倦的追求以及他的創新精神,真正繼承佐臨先生這一輩藝術家不求名不求利,真正獻身于話劇的精神,以弘揚社會主義價值觀為主題,創造出無愧于我們這個時代、無愧于我們這個城市的作品。
吳孝明(上海市文廣局藝術總監):今天這個會是為了更好地緬懷黃佐臨先生對文化的追求,他的創新精神。特別是當下的文化人,思考怎么來繼承和發揚佐臨先生的精神,在繼承傳統的同時去更好地創新。尤其是在上海當下,在整個文化發展的過程中間,對佐臨老師的這種懷念和思念,更加的強烈。他在藝術上的精益求精、孜孜不倦,在生活中平易近人,關愛所有的員工。他當時設想在上海要成立喜劇院,在斯坦尼和布萊斯特的表現形式上面更好地拓展喜劇的運用,當時在全國的人民藝術劇院中這是一次完全的創新。對當時來講,這么一個舉動也推動了舞臺喜劇的發展,包括影視的發展。佐臨老師不但是一個藝術家,他更是一個藝術的改革家,他的這種文化工匠精神在當下尤為重要。我們現在往往講到繼承,創新就很難發展。佐臨在繼承的同時又有創新,在創新的同時很好地繼承了藝術的發展。佐臨老師的精神對當下文化發展有很大的現實意義。特別是文化創新,對我們來講,往往是講得多做得少。但是佐臨老師恰恰是做得多講得少。所以佐臨老師的思想引領著上海戲劇。我們今天在這里既是懷念佐臨先生,又是更好地用佐臨先生的精神推動我們當下的文化發展。
楊紹林(上海市戲劇家協會主席):上海戲劇、中國戲劇是和黃佐臨先生的名字分不開的。今天,面對一個需要文藝精品而且一定能夠產生文藝精品的時代,一個需要文藝大師而且一定能夠產生文藝大師的時代,紀念黃佐臨先生誕辰110周年具有特別的意義。一、紀念黃佐臨先生,我們要紀念和學習他始終與祖國共命運,與時代同呼吸,與人民共患難的崇高品格和精神境界。二、紀念黃佐臨先生,我們要紀念和學習他強烈的創新變革意識。藝術貴在創新,貴在創造新形式、新手段。黃佐臨先生是一位具有強烈創新意識的大師,是中國戲劇界最善于變革舞臺樣式的一位高手。他曾指出,創新首先應該看導演對于劇中詩意的表現是否情投意合。幾十年來,他一直在舞臺上鍥而不舍地反復實驗,追求一種非寫實的詩化的藝術境界。三、紀念黃佐臨先生,我們要紀念和學習他淡泊名利,對藝術精益求精,以戲劇為生命的赤子之心。在藝術的世界馳騁60余年的黃佐臨先生,熱愛戲劇,視藝術如生命,共導演了100多臺戲劇和多部電影,他還廣泛涉足戲曲、芭蕾、滑稽戲等各個領域,并為之做出了杰出貢獻。四、紀念黃佐臨先生,我們要紀念和學習他關心培養藝術人才成長的寬廣胸懷和大師風范。黃佐臨先生選拔培養人才不拘一格,不論資排輩,不搞幫派,而是以藝術準則為主。他總是不遺余力地耐心引導一批又一批演員走向成熟,走向成功之路。
如果說今天我們上海的話劇人做了一些有利于話劇發展的事情,這個智慧其實也源于佐臨先生坦然面對極端環境的智慧對我們的影響。我們應該感謝佐臨先生讓我們認識戲劇世界之深、之廣的魅力。研討會總有結束的時候,但是我相信他的精神不是結束,而是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