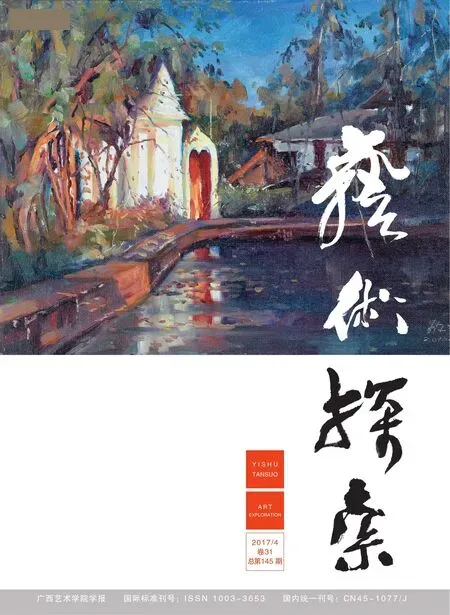冀中笙管樂與西安鼓樂比較研究
孫茂利(中國藝術研究院研究生院,北京100029)
冀中笙管樂與西安鼓樂比較研究
孫茂利
(中國藝術研究院研究生院,北京100029)
冀中笙管樂與西安鼓樂都是以笙管為主導的樂器組合類型。這種樂器組合類型屬于鼓吹樂的一種,在歷史上與國家制度有密切的聯系。鼓吹樂由于制度規定性在音樂本體(律調譜器曲)諸層面具有一致性。在“鼓吹樂系”俗化過程中,由于“樂”之性能加強,出現了區域間豐富的差異。冀中笙管樂、西安鼓樂所承載的樂器組合、樂器形制與宮調系統具有一致性、相通性的內涵,具體體現在十七苗笙、九孔管與七調為一體的存在,彰顯中國音樂文化大傳統在當下的積淀。二者在音樂本體又存在差異性內涵,這是對傳統接衍與承載過程中,在相對穩定的前提下都產生了一定程度的變異所致。
冀中笙管樂;西安鼓樂;音樂本體;比較研究
冀中笙管樂與西安鼓樂都形成了以笙管為主導的樂器組合類型,這并非不約而同的選擇,而是由于制度上的規定、規范所致。明代制度規定,小祀樂用鼓吹樂類型①參見項陽《小祀樂用教坊——明代吉禮用樂新類型》,《音樂與表演》(南京藝術學院學報)2010年第3、4期。,但沒有指出具體的樂器組合。根據《清朝文獻通考》中所載:“凡常祀:三皇廟、顯佑宮、東岳廟、城隍廟、關帝廟、火神廟、黑龍潭樂奏慶神歡,器用簫二、笛二、管二、笙一、云鑼一、鼓一,俱和聲署承應。”②《清朝文獻通考》,四庫全書本。清代“通祀”樂器組合基本以笙管為主,至少說明這種樂器組合類型作為定制在國家層面上是存在的。那么笙管樂器組合與鼓吹樂的關系如何認定?歷史上這種樂器組合形式以怎樣的方式存在?具體的樂器形制如何?對當下有何影響?對于以上問題的解答,需要對二者的樂器組合與樂器形制作進一步的探究,也需要從禮樂、俗樂宏觀的文化格局,用樂的觀念,審美因素等層面加以綜合的考量。
一、笙管樂器組合與鼓吹樂之關系
鼓吹樂是傳統音樂中“一類以打擊樂器與吹奏樂器為主的演奏形式和樂種”③中國藝術研究院音樂研究所編《中國音樂辭典》,北京:人民音樂出版社,2007年,第125頁。。鼓吹從軍中走來,作為一種重要的功能性用樂的形式,自漢魏以降,在國家意義上進入禮樂體制之后又不斷擴展其使用功能,隨著“樂”之功能的側重,漸成“體系化特征”。④項陽《重器功能,合禮演化——從金石樂懸到本品鼓吹》,《中國音樂》2011年第3期,第9頁。管子與嗩吶則是鼓吹樂中最具代表性的兩件樂器,在不同歷史時期,引領著鼓吹樂的發展。
管子簡稱管,源于龜茲國。隋唐時期,多種形制的篳篥已經在隋唐燕樂的諸部伎樂中廣泛使用,宋代教坊十三部,其中就包括“篳篥”部。⑤《中國音樂辭典》,第25頁。陳旸《樂書》有《篳篥》條注曰:
今教坊所用,上七空后、二空,以五、凡、工、尺、上、一、四、六、勾、合,十字譜其聲。⑥(宋)陳旸《樂書》卷一百三十,四庫全書本。
這條文獻給出九孔管孔位與譜字的對應關系,以“合”字為筒音,“勾”字對應背二孔。這種九孔管的形制見于此后歷代官方文獻的記載,并一直延續到當下。
嗩吶在金代由波斯、阿拉伯國家傳入中原地區,晚于篳篥幾百年,但是發展的速度很快。嗩吶在明代正德年間(1 5 0 6~1 5 2 1年)已經普遍使用①《中國音樂辭典》,第3 8 0頁。,至明末已是遍及全國。顧炎武感嘆“鼓吹,軍中之樂也,非統軍之官不用。今則文官用之,士庶人用之,僧道用之。金革之氣,遍于國中,而兵由此起矣”②(明)顧炎武《日知錄》卷五“木鐸”,黃汝成集釋,長沙:岳麓書社,1994年,第168-169頁。。嗩吶的樂器形制、聲學原理與管子顯然是不同的:前者為木質的錐形管,前七背一;后者則為圓筒形直管,前七背二。但既然嗩吶融入了鼓吹樂系統,并作為主奏樂器,主要由在籍官屬樂人群體③關于鼓吹樂與樂戶的關系,包括樂籍制度的研究,參見項陽《山西樂戶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年。所承載,那么其樂律、樂調等本體中心特征必然要融入這個體系。嗩吶、管子在調名、定調標準等多個層面具有一致性與相通性,均可以說明在歷史演進過程中二者相互影響,以至趨于同一的關系。“前七背一”八孔管的出現,可能是受到嗩吶形制的影響。八孔管出現在清代文獻中④清代文獻《律呂正義后編》(1746年)、《皇朝文獻通考》(1787年),包括民國時《清史稿》,都記載有九孔管與八孔管兩種形制的管子。,并逐漸取代九孔管成為主流。當下雖有九孔管留存的區域或樂社,但背二孔基本廢置不用,造成這一現象的原因還有笙簧失律,及音階形式變化顯示的用樂觀念的變化等因素,但管子由九孔向八孔的轉化,與隸屬同一鼓吹樂系統的嗩吶不無關系。孔位轉化的問題還需要進一步深入的研究。但無論如何,管子與嗩吶,在鼓吹樂的發展中都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作為制度下重要的功能性用樂的形式,鼓吹樂歷來由在籍官屬樂人承載,并通過宮廷至地方官府形成的網絡化與體系化的樂機構,擴大了這種用樂形式影響的范圍。明清以來,鼓吹樂是真正具有上下相通性的樂器組合形式,從宮廷到各級地方官府到軍中,顯示出鼓吹系統旺盛的生命力。隨著樂籍制度解體,鼓吹樂系俗化⑤《重器功能,合禮演化——從金石樂懸到本品鼓吹》,第9頁。過程中,“樂”之功能逐漸加強,出現了帶有區域特征諸多“樂種”的稱謂,如“笙管樂”“鼓樂”“吹打樂”“吹歌”等。總之,笙管樂器組合是鼓吹樂下的一種樂器組合類型,是鼓吹樂系豐富內涵的重要體現。
二、音樂會社樂器形制共時與歷時相結合的比較
冀中笙管樂與西安鼓樂所用的樂器,包括各種形制,在歷史文獻中可以找到相應的記載,是傳統音樂文化大傳統在當下的積淀。本部分主要以“器”為主,同時兼有“調”的探討。
(一)十七苗笙、九孔管與七調⑥相關研究可參見:逯鳳華《泰山岱廟藏譜〈玉音仙范〉譜本研究》,中國藝術研究院2008年碩士學位論文;徐倩《膠東道樂“勾凡調”及相關研究》,中國藝術研究院2009年碩士學位論文。
1.共時性存在
冀中地區部分音樂會還留有十七簧滿字笙。如保定地區雄縣韓莊村音樂會、里合莊音樂會都存有十七簧滿字的木斗笙。里合莊音樂會已經解散,但原在會里點笙的劉信臣,家里仍存有十七簧木斗笙,且各苗音位他都能倒背如流。他點笙時,“是以笛子的筒音為標準,然后以五度、尖字—塌字(八度)依次校對”⑦喬建中、薛藝兵、(英)鐘思第、張振濤《冀中、京、津地區民間“音樂會”普查實錄》(以下注釋簡稱《普查》),載《中國音樂年鑒》,1994年,第293頁。。這種以“五、八度”調律協配點笙的方法,與傳統笙的“母律居中八五度調律法”⑧景蔚崗《中國傳統笙管樂申論》,長沙:湖南文藝出版社,2005年,第182-186頁。是一致的。雄縣張崗鄉、雄縣西安各莊音樂會抄本扉頁還有十七簧笙音位的“笙苗歌”及“橫笛竅音、管竅音”與笙簧音位的對應⑨《普查》第290頁。,另外,保定雄縣孤莊頭村音樂會、滄州東姜村音樂會、天津靜海小黃莊音樂會等,亦曾經使用十七簧笙。在十七苗笙定制的基礎下,冀中各音樂會所用笙還有十五簧、十四簧等缺簧笙的存在,在具體笙管音位的設置上各會社也是略有不同。
西安鼓樂社所用十七苗笙,裝有十簧,七管無簧。但根據岳華恩、劉析羽在《笙在西安鼓樂中的演變》提到的信息,作者在為西安及周圍各縣鼓樂社修理笙的過程中,發現一些從清代流傳下來,年代久遠的笙,有些笙雖然裝有十簧,但是一些無簧的孔管則留有曾裝有簧片的痕跡,作者推測,“西安鼓樂原來所用之笙絕不僅有十簧,而至少應有十四簧”①岳華恩、劉析羽《笙在西安鼓樂中的演變》,程天建、李寶杰編《長安鼓樂研究論文選集》,西安:西安地圖出版社,2000年,第309頁。。相同的情況也出現在河北音樂會中,當下許多音樂會所用笙多有缺簧少字的情況。比如勝芳南音樂會現用十七苗十五簧笙,首尾兩管缺簧,但會中樂師息全德還能說出以前這兩簧對應的音位②《普查》第338頁。,可見,勝芳南樂會曾經使用滿簧笙。
會社所用笙制的基礎都為十七苗,雖然仍有部分會社使用全簧滿字笙,或是能夠說出十七苗笙對應的音位,但大部分會社笙簧經歷了一個逐漸失律的過程,重復音增多,這也是笙制在歷史上整體發展的趨勢。在這一過程中,由于笙作為重要應律樂器的地位,缺簧少字對音樂本體中心特征的幾個方面均產生了聯動性的影響,如用調的變化、樂器形制的改變等等。
冀中音樂會多有九孔管的分布,而且與上述十七簧滿字笙留存的樂社在相當程度上是吻合的。在上述存有十七簧笙的音樂會之外,仍有九孔管分布的區域還包括:廊坊地區永清縣北五道口村音樂會,保定地區雄縣的葛各莊音樂會、北沙口村音樂會、北大陽村音樂會、開口村音樂會,北京大興縣北辛莊音樂會,等等。雖然有些會社的成員還能說出九孔管對應的音位,但一般不用于實際演奏,或通過木頭、蠟等方式堵住背下孔,僅擱置手指頭用。西安鼓樂現用管子為八孔,但其傳承的工尺譜中有“勾”字,根據管子譜字與指孔一字對一音的關系,“勾”字對應的就是九孔管的背下孔。因此,毫無疑問,西安鼓樂也曾經使用過九孔管。
會社中,與九孔管、十七苗笙樂器形制相對應的是七調的使用。但是當下會社中,一般使用八孔管,十七苗笙或有缺簧,因此這種對應關系在共時層面可分兩種。其一,傳承的工尺譜中有七調,因笙簧失律,管子通過更換大小哨的方式維持七調完整的演奏。如勝芳音樂會通過管子更換大小哨的方式演奏七調,分別是大哨四個調:正大調(六字調)、大凡調、啞一調之一(塌尺起頭)、啞一調之二(六字起頭);小哨三個調:正小調(正調)、五字調、小工調③《普查》第333頁。。其二,當地沒有七調文本,但有七調調名完整的表述。如雄縣南街村音樂會,會中有九孔大管;北樂會有七個調門:七個眼的正調,六個眼的正調、越調、小工調、悶工調、乙字調,六個眼的反調;南樂用兩個調門:正調、小工調。④《普查》第296頁。當地南樂會的調門,包含在北樂會調門范圍之內。
會社曾使用九孔管與十七苗笙,其宮調使用基本在七調范圍之內,但當下會社所用樂器又發生了改變,七調實現方式也產生了差異。會社中即便有九孔管的留存,一般也不用于實際演奏;笙制的基礎都為十七苗,但相當部分會社都出現缺簧少律的現象;七調在不同會社的實現方式差異,僅從調名的豐富性存在足以證明。
2.九孔管與十七苗笙是維持七調完整性的必要條件
九孔管、十七苗笙與七調是唐宋以來的傳統,唐宋燕樂二十八調的“七宮”與明清工尺七調存在基本的承繼關系。即是說,九孔管、十七苗笙與七調自唐宋以降,整體的發展脈絡沒有中斷,并一直延續到當下。之所以是九孔管、十七苗笙,是因為這種樂器形制具備維持七調完整性的核心與必要條件。
楊蔭瀏先生在燕樂調理論研究時,提出“一宮需有七個音,四宮需有十個音。六宮需有十二個音,在用到六宮的時候,就用全了十二個半音”⑤楊蔭瀏《中國古代音樂史稿》,北京:人民音樂出版社,2009年,第263頁。。笙管樂隊中,對轉調起到制約作用的是笙,因此理論上一攢十七苗笙需十二律齊備,才能對應七調所需要的音位。根據傳統笙的八五度調律法,十七苗笙按此生律法是可以生全十二律的,再加兩簧就可以十二律旋宮。⑥《中國傳統笙管樂申論》,第211頁、第259-260頁。楊先生認為,十九簧笙或十七簧笙加兩義管,都是為了“達到翻全十二調的目的”①《楊蔭瀏全集》卷六,第2 0 0頁。。因此從理論的角度,在笙管樂中,九孔管、十七苗笙與七調是相輔相成的。對笙簧音位與宮調結構的問題,學界還有一種觀點,陳克秀、張振濤認為十七苗笙備有十一律,其宮均的極限為五均②詳見:陳克秀《雁北笙管樂的調查與研究》,《中國音樂學》1994年第3期,第45頁;張振濤《笙管音位的樂律學研究》,濟南:山東文藝出版社,2002年,第44-45頁。。兩種觀點的差異就在于笙簧音位取音的范圍。對于這一問題,應該置于笙管樂隊組合中的整體語境中加以把握,考慮到“律、調、譜、器”各個層面的制約關系,另外也要注意活態中樂人對宮調的理解,以及實踐時創造性的運用,具體問題具體分析。
3.九孔管、十七苗笙的歷時性存在
九孔管與十七苗笙在唐宋以來,特別是在官方文獻中均有明確的記載。管子在北魏時可能已經扎根于華夏大地③詳見《中國音樂辭典》,第128頁。,隋唐時盛行,根據陳旸《樂書》所引當時尚存的唐代典籍《唐樂圖》,唐代已經存在十七苗笙。陳旸《樂書》中除了九孔管,還有十七苗笙的記載:“圣朝太樂諸工,以竽、巢、和并為一器,率取胡部十七管笙為之。”④陳旸《樂書》卷一百三十,四庫全書本。宋代笙有多種形制,十九簧的巢笙、十三簧的和笙列為“雅部”樂器,而九孔管、十七苗笙則列“胡部”,屬“胡漢雜陳”,非“華夏正聲”。所謂“胡漢雜陳”,是從樂隊組合的整體相對于“華夏正聲”而言,其中也包括了漢族傳統樂器,如笙。笙只因管數差異而分“雅”“胡”,代表了文人階層正統的“雅樂”觀念。元代文獻對笙、管記載不甚明確。《元史》卷七十一記有:“頭管制以竹為管,卷蘆葉為首,竅七。笙制以匏為底,列管于上,管十三簧如之。”《續文獻通考》認為,《元史》中所載“頭管”與“篳篥”實為一物,其形制應該未有改變。⑤《續文獻通考》記載:“蓋其制雖有不一,而其器未嘗不同。遼金但稱觱篥,而不稱頭管。元志乃并稱之,其實一物而已。”(清)張廷玉《續文獻通考》卷一百十,四庫全書本。明代對這兩件樂器使用的記載則“信而有證”,《明會典·大樂制度》卷一百四十八:“笙十二攢。用紫竹十七管。下施銅簧、參差攢于黑漆木匏中。有觜項。亦黑漆。上垂彩線(巾分)錔。頭管十二管。以烏木為之。長六寸八分。九孔,前七、后二。兩末、以牙管束。以蘆為梢。”明代的唐順之在《稗編》中,還以九孔管的譜字對應十二律呂:“管色字譜:五、凡、工、尺、上、四、六、一、勾、合。管九孔,六、勾二字并后出,合字在管體中……九孔內四、一、工、凡皆有高、下二聲;五字有高、下、緊三聲;惟上、勾、尺無高下。蓋仲、蕤、林三律不分清濁自然應律也。”⑥(明)唐順之《稗編》,四庫全書本。清代官方文獻中,亦有九孔管的記載。秦蕙田《五禮通考》記載“今時用頭管共有九孔,樂工相傳取音為合、四、乙、上、勾、尺、工、凡、六、五、高乙、高上,其通長為合”⑦(清)秦蕙田《五禮通考》,四庫全書本。,《御制律呂正義后編》則謂“頭管之制,則自唐以來傳之不失”⑧《御制律呂正義后編》卷六十八,四庫全書本。,所言甚是。清代的十七簧笙,“以聲字考之,與《稗編》所載相合,則猶是前明之舊也”。由此,以九孔管、十七苗笙作為定制,在歷史發展過程中,這條脈絡一直延續到當下,沒有中斷。
清代,十七苗笙已有缺簧情況的出現。《御制律呂正義后編》記載:“今小笙十三簧,實亦十七管獨四管無簧耳。大笙十七簧而四管不用,實亦十三簧耳。注:第六管、第十六管為啞工不設簧,第十七管凡字太高,第九管勾字不成聲,雖設而簧亦不用。故十七簧笙,十五簧笙,皆止十三簧”。⑨《御制律呂正義后編》卷六十五,四庫全書本。清代笙已有十五簧、十三簧等不同笙簧數的差異,但其十七苗的定制沒有改變。《御制律呂正義后編》所記載的笙缺四簧,這在當下會社的笙中也有所體現,比如多數會社第九管都為“上”,代替了“勾”字;用十五簧笙的會社,一般是首尾兩管缺簧,且第十七苗或為“清凡”,當比“凡”字高;第十六管“啞工”,冀中音樂會笙師所述譜字也與之對應⑩《笙管音位的樂律學研究》,第99頁。。笙簧獨缺這幾個譜字,是因為這幾個譜字所對應律位處于笙傳統調律法生律次序的末端。文獻與活態的互證,可以說明歷史上在同一體系內傳承的技術性知識在細節上一致性、相通性的存在。
(二)九孔管、八孔管——大管、小管
會社現在用于演奏的管子,一般為八孔管,相對于九孔管,背二孔棄置不用,“勾”字音位缺失,說明八孔管可以承載九孔的職能。但“以上代勾”等方式的運用,與笙簧失律、音階性質及用樂觀念的變化不無關系。在此首先對清代文獻中八孔管記載進行一些梳理。
清代官方文獻中有九孔“大管”、八孔“小管”兩種形制。《五禮通考》記載:
今之頭管實有大小兩種,大者禮部太常并親樂所用,小者乃吳中所制,隨歌曲與笙笛相合為用也……大管之孔九,取音為十二(乃合、四、乙、上、勾、尺、工、凡、六、五、高乙、高上之十二字),小管之孔八,取音為九(乃合、四、乙、上、尺、工、凡、六、五之九字)。因大管有“勾”字孔無“凡”字孔,取凡字為工字、六字兩孔,仍取高乙、高上兩字于最上一孔;而小管無勾字孔,有凡字孔,即取凡字于本孔,其最上一孔又不兼取兩字,故小管聲字之減于大管。①(清)秦蕙田《五禮通考》,四庫全書本。
清代九孔“大管”與八孔“小管”有以下幾點不同:1.使用的場合、用樂的性質不同。大管為禮部太常所用,屬“雅樂”,小管為“吳中所制,隨歌曲與笙笛相合為用”,可能就有俗樂兩種對應的問題,如果用于禮制儀式,就屬于禮樂類下,與“雅樂”對應的“俗樂”,如不對應禮制儀式,則是與禮樂對應的俗樂。②此處俗樂的雙重定位問題,參見項陽《俗樂的雙重定位:與禮樂對應/與雅樂對應》,《音樂研究》2013年第4期。2.大管九孔有“勾”字,小管八孔不用“勾”字;“勾”字對應蕤賓,聲應在工尺譜字“上”“尺”之間。3.筒音都對應“合”字,但音高不同,大管“合”字為笛之“低上”字,小管“合”字乃變宮“尺”字,小管筒音及各孔音高應都高于大管一個大二度。4.大管取音范圍廣,小管相對于大管,缺少勾、高乙、高上三音。清代的“大管”“小管”與陳旸《樂書》中提到的“然其大者九竅,以觱篥名之;小者六竅,以風管名之”,管之“大、小”者又顯然是不同的形制。
當下鄉間樂社中所用八孔管,也有大管、小管之說,但與清代文獻中的“大管”“小管”不同。河北地區北樂會與南樂會使用調高相差四度的小管子、大管子,并作為判別兩種樂社類型重要的標準之一,但這種標準只是一般的區分,并不絕對。據筆者在河北徐水高莊村音樂會的考察,他們就使用了D調、G調兩種形制的管子。西安鼓樂中的管子有高管與低管(俗稱“嗡管”)之分,李石根先生介紹這兩種管子分兩個聲部,齊用時“將嗡管作五度倒眼,與平調笛、笙相和,以增加音響的厚度”③《西安鼓樂全書》卷一,第37頁。。高管、低管作“五度倒眼”,說明西安鼓樂社也有相差四度小管、大管存在。聯系筆者在南集賢村樂社的采訪,擔任管子演奏的張俊介紹,他們用的管子分高管(G調)和低管(D調),但高管市面上沒有賣的,都是自制。
(三)管子大哨、小哨與“掣音”演奏技巧的運用
冀中音樂會還有同管更換大、小哨用于轉調的情況。通過換哨的方式,可以在不改變指法的情況下,使筒音及各孔音高都可以相應升高或降低二度,從而達到轉調的目的。比如管子用“大哨”,筒音為“合”,換小哨后,筒音為“四”。音樂會成員對此有明確的概念,換哨后相對于大哨,他們認為小哨“尖一把字”,或稱“上一把字”。使用大、小哨的音樂會,如保定雄縣西安各莊音樂會、北沙口村音樂會,廊坊永清縣北五道口村音樂會、文安縣蔡頭村音樂會,天津靜海元蒙口南村音樂會等。在這些音樂會中,大、小哨又有許多相近的表述,如“大、小引子”“大、小玩意兒”等。
大、小哨還對應宮調的使用。多個音樂會的抄本上,在曲名中就顯示出這種對應關系。智化寺音樂使用大、小哨,其“正、背、皆、月”四調均指大哨而言,“小哨正調”合于大哨正調(F調),但因為小哨質地較軟,吹起來省勁,因此智化寺的“正調”是以“小哨‘正調’為準”④《笙管音位的樂律學研究》,第190頁。。勝芳音樂會通過更換大、小哨轉七調,其中大哨吹“上字調、啞一調、大凡調、六字調”,小哨吹“尺字調、五字調、工字調”,這種對應關系是固定的。勝芳音樂會大、小哨均為自制,長度、質地、寬度等沒有嚴格的標準。
管子演奏中,還可以通過唇口的控制,氣息的“頂”“掣”,半音指法的運用,在同一指孔調節音高,一孔兩音甚至三音。這種技巧還是衡量一位管子演奏者技藝水平的重要標準。
管子通過換哨并配合“掣音”技巧轉調的記載見于清代文獻。《清朝文獻通考》中說道:“轉調則必易哨。蓋哨薄則軟,軟則聲低;哨厚則硬,硬則聲高;哨長而聲亦低,哨短而聲亦高。”①(清)張廷玉《清朝文獻通考》卷一百六十七,北京:商務印書館,第6310-6311頁。《清朝文獻通考》還介紹了相差一律、同為八孔管的頭管、中管用哨的情況:“頭管比中管低一律,皆前七孔,后一孔。頭管為中音部樂器。中管為中高二部樂器。上端有蘆哨,可升降字音二度,名曰‘掣音’。”②(清)劉錦藻《清朝續文獻通考》卷一百九十五《樂八》,萬有文庫本(第2冊),北京:商務印書館,1955年,第9422頁。哨之軟硬、長短對音高都有一定的影響,哨的形制有細微的差別,因此易哨后還需要配合“掣音”之法,以達到調定音高的目的。所謂“掣音之理,至為精妙,然掣音之數多少不同,則未著有定法也”③《清朝文獻通考》,第6311頁。。這是一種基于演奏實踐而出現的方式,“易哨”與“掣音”之法拓展了管子這件樂器宮均實踐的范圍,應該出自專業樂人、樂工之手。作為歷史上鼓吹樂最主要的承載群體,官屬樂人無疑發揮了重要的作用,是他們智慧的集中體現。
(四)雙云鑼
云鑼是會社樂器組合中另一個重要的應律樂器。會社使用的云鑼一般為銅制,十面鑼共一架上,用雙槌敲擊。在冀中音樂會與西安鼓樂社中,坐樂演奏時,還有會社使用雙云鑼。雙云鑼在西安鼓樂中有著普遍的應用,定調與笙相同,因為其坐樂“大曲”都是以某調的“雙云鑼八拍坐樂全套”命名,因此雙云鑼的使用在西安鼓樂社中較為凸顯。西安鼓樂社用的雙云鑼為二十面基本相同的小鑼,音位、音高相同。但雙云鑼的使用又絕非西安鼓樂所獨有,冀中音樂會坐樂演奏時也多使用雙云鑼。
云鑼的記載首見于元代。《元史·禮樂志》記載:“云璈,制以銅,為小鑼十三,同一木架,下有長柄,左手持,而右手以小槌擊之。”④(明)宋濂等著《元史》卷七十一,北京:中華書局,1976年,第1176頁。十三鑼的“云璈”就是后世所用之云鑼,據《律呂正義后編》記載:“云鑼即云璈也,十面同一木架。案云鑼之制不知其所自起,元史始見于宴樂。我朝乃用于丹陛樂,凡十面應四正律、六半律。其器小,其聲高也。”⑤《律呂正義后編》卷六十八,四庫全書本。《律呂正義后編》給出了云鑼音位的排列及律分,對于《元史》中出現的十三鑼及音位排列,書中提出“制十三鑼為一架,今不可考,如其有之,則必從下增合四乙三字,猶宋燕樂以最下一聲為合字之義云爾”⑥《律呂正義后編》卷六十八,四庫全書本。。
雙云鑼的使用,《揚州畫舫錄》中也有一些有價值的信息:
是樂前明已有之,本朝以韋蘭谷、熊大璋二家為最。蘭谷得崇禎間內苑樂工蒲鈸法,傳之張九思,謂之“韋派”。大璋工二十四云鑼擊法,傳之王紫稼。同時沈西觀竊其法,得二十面。會紫稼遇禍,其四面遂失傳。西觀后傳于其徒顧美掄,得十四面,美復傳于大璋之孫知一,謂之“熊派”。蘭谷、九思,蘇州人。大璋、知一,福建人。西觀,蘇州人。美掄,杭州人。至今揚州蒲鈸出九思之門,而十四面云鑼福建尚有能之者。⑦(清)李斗《揚州畫舫錄》卷十一《虹橋錄》下,北京:中華書局,1960年,第256頁。
明代文獻目前尚未有云鑼的記載,但明代有云鑼并用于演奏是毫無疑問的。所引文獻中所記載的二十四鑼、二十鑼,有可能就是冀中音樂會與西安鼓樂社中用于坐樂演奏的雙云鑼。其形制可能為單架十二鑼、十鑼的并置。民間所用雙云鑼形制及演奏技法,極有可能是來自在籍樂人的傳承。
根據《律呂正義后編》中所繪云鑼圖像及音位排列,加以共時層面的比較,冀中許多音樂會都有與之一致的音位排列。如筆者田野考察中,對勝芳音樂會、徐水高莊音樂會、文安里東莊音樂會的云鑼音位的記錄,都與其記載是一致的。智化寺音樂有七調的云鑼音位圖,但現在使用的只有“背調”,這一調的音位排列與文獻及上述會社是一致的。云鑼可能也經歷了逐漸失律的過程,導致減少了宮調的使用,在這一點上與笙相同。
結語
冀中笙管樂與西安鼓樂作為音樂會社類型的團體組織,其所用樂器組合類型、樂器形制、宮調體系具有一致性、相通性內涵。本文認為,會社樂器組合及樂曲從傳統國家意義而來,其樂器形制、宮調系統既存在相通一致性,亦在鼓吹樂民間存在的發展過程中產生一定的變異。笙管樂隊組合的用樂機制應為十七苗笙、九孔管與七調為一體的存在,這種同一性在兩地樂社樂譜系統中有明確顯現。對這一問題的梳理研究,有助于我們進一步探究中國傳統音樂“律調譜器”之間的綜合作用及制約關系。總之,冀中笙管樂與西安鼓樂,其當下所承載的音樂本體,既有相通一致性又有變異性,彰顯中國音樂文化大傳統在當下的積淀。
(責任編輯、校對:徐珊珊)
AComparativeStudyonWind-PipeMusic inMiddleHebeiProvinceand Drum
Music in Xi'an
SunMaoli
Both w ind-p ipemusic inm idd le Hebeip rovince and d rum music in Xi'an fallinto the category of themusicalinstruments combination formatw ithw ind and pipe instruments at the core.As a type ofw ind and d rum music,itbore historically on country system.The ontologicalaspects ofw ind and d rum music,namelymelody,tone,score,instrumentand the musicalpiece,show consistency and harmony ow ing to the institutionalp rescrip tions.In the p rocess ofpopularization,the musicalentertainmentofthew ind and d rum music was loom ing large,resulting in thew ide variety between d ifferentregions. The shape and structure as well as combination formats ofmusical instruments in w ind-pipe music in m idd le Hebei p rovince and d rum music in Xi'anwere connotatively consistentwith the officialmode ofancientChinesemusic,which finds testimony in themusicalinstruments combination ofw ind-p ipemusic inm idd le HebeiProvince as culturaltradition carried down ac ross ages.The d iscrepancy inmusicalontology of the two exists alongside their common features,which accrued in the p rocess ofevolution.
Wind-Pipe Music in Midd le HebeiProvince,Drum Music in Xi'an,MusicalOntology,Comparative Study
J63%%
A
1003-3653(2017)04-0103-07
10.13574/j.cnki.artsexp.2017.04.013
2017-04-28
孫茂利(1986~),男,山東平陰人,中國藝術研究院研究生院2016級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傳統音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