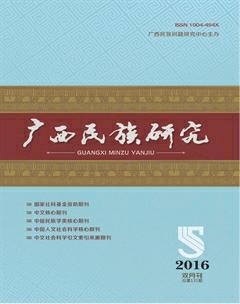走出邊緣:陽江苗族代耕農(nóng)的文化適應(yīng)與社群重構(gòu)
溫士賢
【摘 要】移民群體從原本的社會結(jié)構(gòu)中脫嵌出來,在短期內(nèi)難以融入移居社會,進而成為社會夾縫中的邊緣群體。面對邊緣化的生存情境,不同的移民群體會采取不同的應(yīng)對策略。20世紀90年代,云南山區(qū)的苗族群眾進入廣東陽江代耕。在邊緣化的生存情境中,他們并沒有走上同化的道路,而是建立相對獨立的代耕社區(qū),并利用自身的文化資源和親屬網(wǎng)絡(luò)建構(gòu)自身的主體性。
【關(guān)鍵詞】苗族;代耕農(nóng);邊緣化;文化適應(yīng);社群重構(gòu)
【中圖分類號】 C912.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 - 454X(2016)05 - 0111 - 006
一、問題的提出
遷移是人類社會的一種普遍現(xiàn)象,也是人類群體謀求生存的一條重要途徑。當移民群體進入異文化的社會環(huán)境時,不僅面臨著生存問題,而且也將面臨異質(zhì)文化的沖擊。移民群體在短期內(nèi)難以融入移居社會,他們往往處于兩種文化和兩種社會的邊緣地帶,成為美國社會學家帕克(Robert E. Park)所說的“邊緣人”(marginal man)。帕克將“邊緣人”界定為兩種文化對抗中產(chǎn)生的一種新的人格類型:他和兩種文化生活與歷史傳統(tǒng)截然不同的人群密切地居住、生活在一起。但他絕不愿意快速地與自己的傳統(tǒng)割裂,即便他被允許這么做。由于種族偏見的緣故,他也無法在短期內(nèi)被他正在其中尋找社會位置的新社會所接受。他成為兩種文化和兩種社會邊緣的人,而這兩種文化和兩個社會絕不可能完全地滲透和融合在一起。[1 ] 892移民群體不可避免地經(jīng)歷著兩種文化的碰撞,進而使他們產(chǎn)生一種焦慮、緊張、失落和缺乏歸屬感的人格類型。帕克借用心理學的概念來分析移民問題,為移民問題研究提供了一個新視角和新方法。但總體來說,帕克是在同化論的理論框架下對移民問題進行分析。在他看來,不同族群間的往來互動,會逐漸消弭族群間的文化差異,移民群體最終會融入主流社會。[2 ]
實際上,移民群體所遭遇的情境是多樣的,他們對邊緣情境做出的反應(yīng)也不盡一致。帕克的后繼者斯通奎斯特(Everett V. Stonequist)對邊緣人理論做了補充完善,他將移民群體對邊緣情境的反應(yīng)歸納為六種可能的類型:1. 逐漸接近主流文化群體,通過融入主流文化群體以擺脫其邊緣地位;2. 放棄融入主流文化群體的念頭,成為劣勢群體的領(lǐng)導人;3. 自我孤立化,不和其他人交往,甚至移居到不致發(fā)生心理緊張的地方居住;4. 當邊緣人大量出現(xiàn)的時候,這些邊緣人可能自己組成一個邊緣群體,使這些邊緣人有所歸屬;5. 利用邊緣人的特殊境遇,在科學及藝術(shù)方面發(fā)揮更大潛力;6. 最后的可能性是人格趨向解體,例如犯罪、自殺及精神病等。[3 ]邊緣情境是移民群體在文化適應(yīng)過程中所經(jīng)歷的一個特殊階段,斯通奎斯特提醒研究者要動態(tài)地、差別化地看待邊緣人和邊緣情境。大量的移民研究表明,移民群體在社會適應(yīng)過程中,并沒有完全融入主流社會。相反,在異文化的社會環(huán)境中,移民群體仍在竭力保持自身的主體性,并以此來應(yīng)對主流社會的排斥與擠壓。
近年來,中國社會產(chǎn)生了諸多類型的移民群體,如工程移民、生態(tài)移民、自發(fā)移民、鐘擺式移民[4 ]304-324等等。不管何種類型的移民群體,普遍面臨著生存適應(yīng)與文化適應(yīng)問題。國內(nèi)一些學者將移民群體的貧困、不適、尷尬的生存境遇歸因于他們所處的邊緣情境。[5 ]誠然,邊緣情境可能將移民群體置于劣勢地位,但同時也可能為移民群體提供更多的生存機遇。在流動性日漸增強的現(xiàn)代社會,所謂的邊緣人只是一個相對的概念。某一社會中的邊緣人,跨越到另一社會中則可能成為主流群體。對處于邊緣情境中的移民群體來說,他們也并非必須經(jīng)歷一種人格分裂狀態(tài)的調(diào)適階段。相反,一些移民群體會采取自我邊緣化的生存策略,通過利用傳統(tǒng)文化資源和社會網(wǎng)絡(luò)來建構(gòu)自身的主體性。
2013年8月至2015年12月,筆者對由云南文山壯族苗族自治州(以下簡稱“文山州”)廣南縣遷移到廣東陽江代耕的苗族移民進行了追蹤調(diào)查,累計調(diào)查時間達200余天。據(jù)統(tǒng)計,陽江的苗族代耕農(nóng)有300余戶,共計2000余人,① 他們建立了大大小小的十余個代耕社區(qū)。盡管他們在異鄉(xiāng)定居20余年,但與當?shù)厣鐣冀K處于一種融而未合的閾限狀態(tài)。本文以這一群體為個案,探討移民群體如何應(yīng)對邊緣情境,以及他們?nèi)绾巫叱鲞吘壔纳胬Ь巢⒅匦陆?gòu)自身的主體性。
二、多重邊緣中的苗族代耕農(nóng)
在20世紀八九十年代,珠三角地區(qū)的工業(yè)化進程開始迅速推進。在工業(yè)經(jīng)濟的刺激下,城市周邊的農(nóng)民開始棄農(nóng)務(wù)工,收益較低的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活動逐漸被冷落。在這一時期,中國農(nóng)村雖已推行家庭聯(lián)產(chǎn)承包責任制,但農(nóng)民仍要承擔國家下達的公購糧任務(wù)。在當時的農(nóng)業(yè)政策下,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不僅是農(nóng)民的個體行為,同時也是國家規(guī)定的一項政治任務(wù)。為完成國家規(guī)定的生產(chǎn)任務(wù),田地富余而又缺少勞動力的村落,不惜將土地“轉(zhuǎn)讓”給外來群體代耕。相關(guān)研究表明,在20世紀八九十年代,有數(shù)十萬山區(qū)農(nóng)民進入珠三角農(nóng)村地區(qū)代耕。[6 ]可以說,改革開放后期出現(xiàn)的代耕現(xiàn)象,是中國社會工業(yè)化進程所帶來的連鎖反應(yīng)之一。
陽江地處珠三角的外緣地帶,經(jīng)濟社會發(fā)展相對滯后。借助毗鄰珠三角的地緣優(yōu)勢,當?shù)剞r(nóng)民紛紛外出務(wù)工,致使田地出現(xiàn)大面積拋荒,當?shù)卮甯刹拷?jīng)常因無法完成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任務(wù)遭到上級批評。在此情況下,當?shù)卮迕窈突鶎诱畬⒁M代耕農(nóng)作為完成公購糧任務(wù)的權(quán)宜之計。一個偶然的機會,陽江田地大量拋荒且需找人代耕的消息傳播到文山州的廣南縣,居住在大山深處的苗族人開始為之心動。
廣南縣地處滇桂黔三省區(qū)交界處,是一個典型的山區(qū)貧困縣。山區(qū)、半山區(qū)占全縣總面積的94.7%,壩區(qū)面積僅占5.3%。[7 ]1與此同時,受人類活動的影響,當?shù)氐耐恋厥F(xiàn)象非常嚴重。在其貧瘠的土地上,生活著壯、漢、苗、瑤、彝、回等11個民族群體。受歷史因素的影響,苗族群眾主要居住在高海拔的山區(qū)地帶,當?shù)亓鱾髦皾h族住街頭、壯族住水頭,苗族住山頭、瑤族住菁頭”的說法。生活在大山中的苗族人,如同費孝通先生所描述的“患土地饑餓癥者”,[8 ]294他們希望獲得異鄉(xiāng)的土地資源來擺脫生存危機。相關(guān)研究表明,苗族的自發(fā)遷移現(xiàn)象在云南山區(qū)非常普遍,他們在一些地區(qū)發(fā)展出相對穩(wěn)定的移民村落。[9 ]可以說,遷移不僅是苗族人尋求生存的重要手段,同時已成為一種文化慣習植根于他們的思想觀念之中。
1991年底,在親友的介紹下,廣南縣馬堡村的楊發(fā)明、李正林等人進入陽江尋地代耕。經(jīng)人介紹,他們找到雙捷鎮(zhèn)樂安管理區(qū)的村干部。當?shù)氐拇甯刹繉λ麄兊牡絹矸浅g迎,并承諾轉(zhuǎn)讓100畝田地給他們永久耕種。楊發(fā)明、李正林二人返回家鄉(xiāng),組織了24戶苗族家庭遷移此地代耕,他們在雙捷鎮(zhèn)樂安管理區(qū)建立了第一個苗族代耕社區(qū)——云南隊。
在第一批苗族移民落腳定居之后,缺少田地的苗族群眾相繼進入到陽江農(nóng)村代耕,他們在代耕田地的邊緣建立起自己的代耕社區(qū),如麥洞村、大更村、高橋村、燈芯塘等。其中,雙捷鎮(zhèn)的樂安村是苗族代耕農(nóng)分布最為集中的區(qū)域,在其轄區(qū)范圍內(nèi)分布著五個代耕社區(qū)。在當時的社會背景下,代耕是實現(xiàn)土地和勞動力優(yōu)化配置的一種有效的制度安排。然而,這種民間自發(fā)的遷移行動,并沒有得到政府的支持和認可,由此導致了代耕農(nóng)群體長期處于邊緣化的生存狀態(tài)。
對當?shù)貪h族村民來說,苗族代耕農(nóng)是一群熟悉的陌生人。雖然兩個群體比鄰而居,但彼此之間卻缺少認知和了解。苗族代耕農(nóng)的語言、服飾和宗教儀式等文化特征,被當?shù)卮迕褚暈椤肮之悺焙汀奥浜蟆钡臇|西。為避免招致外部群體的歧視,他們并未選擇在當?shù)卮迓渲卸ň樱且劳刑锏亟⑵鹣鄬Ω綦x的代耕社區(qū)。對苗族代耕農(nóng)來說,空間上的自我隔離是應(yīng)對社會排斥以及化解自身文化劣勢的一種有效策略。相關(guān)研究表明,當社群隔離自愿發(fā)生時,有著相同文化背景的群體聚集在一起可以給他們的生活帶來更大的便利,而且還會產(chǎn)生一種歸屬感和安全感。[10 ]
與政策性移民不同,苗族代耕農(nóng)的自發(fā)遷移行動非但沒有得到制度保障,反而是受到各種制度的排斥與擠壓。土地制度和戶籍制度,是與苗族代耕農(nóng)生存發(fā)展密切相關(guān)的兩項制度。然而,近20年來,這兩項制度的變革卻使苗族代耕農(nóng)淪為制度的犧牲品。盡管苗族代耕農(nóng)獲得了土地的“永久”使用權(quán),甚至是所謂的“所有權(quán)”,但當前的土地制度和相關(guān)的法律政策并不支持民間的土地“轉(zhuǎn)讓”行為。隨著土地價值的凸顯,當?shù)卮迕裨噲D剝奪代耕農(nóng)手中的田地,并由此引發(fā)了諸多的矛盾糾紛。相關(guān)政府部門在處理苗族代耕農(nóng)的土地糾紛時,要么相互推諉,要么堅持“依法辦事”的原則,將其推給司法部門解決。地方司法系統(tǒng)在審理代耕農(nóng)群體的土地糾紛案件時,往往依照現(xiàn)行的法律政策進行審判,代耕農(nóng)群體也因此失去了占有代耕土地的“合法”依據(jù)。
傳統(tǒng)村落社會的地籍與戶籍之間具有較高的一致性,只有具備相應(yīng)的戶籍,才享有開發(fā)村落土地資源的權(quán)利。在當前的行政管理體制下,戶籍是政府對個人成員權(quán)利認可重要依據(jù)。盡管苗族代耕農(nóng)在異鄉(xiāng)村落定居20余年,但由于不具備當?shù)貞艏麄兪冀K不能享有對代耕土地的完全權(quán)利,同時也無法享受地方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務(wù)和社會福利。有學者指出,“戶籍身份的一個重要功能,就是不僅把個人與家庭或組織單位連在一起,而且還總是把個人與一定的地域連在一起,并界定一個人在何處能享受權(quán)利,而在何處不享有權(quán)利。”[11 ]437從社會管理的角度來看,苗族代耕農(nóng)處于兩種社會的夾縫之中,他們脫離原籍地的管理,同時也未能被移居地的地方政府所接納。
戶籍制度給他們的生活帶來諸多不便,特別是在辦理相關(guān)證件時,他們只能回到原籍地去辦理。苗族代耕農(nóng)迫切希望解決戶口遷移問題,然而,國家的制度設(shè)計卻忽略了這一群體。盡管當前的戶籍制度日益開放,但這種開放性僅是限定在由農(nóng)村向城鎮(zhèn)的單向流動,而未能關(guān)照到在不同農(nóng)村地區(qū)之間遷移流動的農(nóng)業(yè)移民問題。由于苗族代耕農(nóng)處于制度的邊緣,其面臨的各種問題也難以得到有效解決。
三、黏合性的文化適應(yīng)策略
在文化決定論者看來,文化結(jié)構(gòu)支配著個體的社會行動,同時也主導著社會群體的行為規(guī)范和價值理念。然而,個體成員不僅是文化原則的執(zhí)行者,同時也是文化原則的修改者和建構(gòu)者。在適應(yīng)新環(huán)境的過程中,苗族代耕農(nóng)對自身的文化生活做出積極的調(diào)適,與此同時,他們也在堅守著自己的文化內(nèi)核與民族特性。金和霍斯將移民群體的這種文化適應(yīng)模式稱為“黏合性適應(yīng)”[12 ]156-183。對苗族代耕農(nóng)來說,黏合性的文化適應(yīng)不僅避免了與主流文化的沖突,同時也是他們進行文化建構(gòu)的一種有效策略。
進入異鄉(xiāng)的漢族社會,苗族代耕農(nóng)不可避免地受到異質(zhì)文化的沖擊。文化沖擊首先來自語言方面。這些來自云南大山中的苗族移民,大部分只能講苗語,只有少數(shù)人能夠講普通話。而在當時,陽江當?shù)卮迕衲軌蛑v普通話的也是少數(shù)。當這兩個群體相遇時,幾乎無法進行語言溝通。語言上的障礙給苗族代耕農(nóng)的生活造成諸多不便,甚至連購買日常用品都非常困難。在回憶最初的語言障礙時,定居樂安麥洞的苗族代耕農(nóng)陶劍榮講道:“我們把鹽叫鹽巴,陽江人把鹽叫‘象昧;我們把煤油叫油水,陽江人把煤油叫火水。說半天都不知道我們要買什么,跟他們講話就像傻瓜一樣。”苗族代耕農(nóng)意識到,必須入鄉(xiāng)隨俗,否則就很難在移居地生存下去。在與當?shù)卮迕竦慕煌^程中,他們有意識地學習當?shù)卣Z言。經(jīng)過幾年時間的交往,大部分苗族代耕農(nóng)都能夠熟練地使用普通話和陽江方言。但在群體內(nèi)部,人們?nèi)砸悦缯Z進行交流,并將民族語言視作民族認同的重要標志。
服飾是苗族文化中最為引人注目的部分,也是其民族身份的重要標識。美國人類學家路易莎·謝恩(Louisa Schein)曾指出,“民族服裝對苗族的身份,在所有地方都是最重要的。”[13 ]62當苗族婦女進入漢族地區(qū)之后,遭遇到文化上的尷尬。苗族人習以為常的民族服飾,往往會招致漢族村民異樣的眼光。為此,當她們走出代耕社區(qū)時,會自覺地換上普通的服裝,盡量弱化民族的外顯標志,以避免招致周邊群體異樣的目光。但在代耕社區(qū)中,苗族婦女仍習慣穿著傳統(tǒng)的苗族服飾。特別是在年節(jié)慶典和婚喪儀式等重要場合,苗族婦女都穿著民族服裝參加。在陽江定居之初,婦女們無法購得苗族服飾,她們要托人從云南老家?guī)н^來。在最近幾年間,一些人做起了販賣苗族服飾的生意,從而滿足了女性對苗族服飾的需求。
代耕社區(qū)不僅為苗族代耕農(nóng)提供了一個相對隔離的生存空間,而且也為他們的文化適應(yīng)提供了較大的回旋余地。對苗族代耕農(nóng)來說,遷移只是改變了生活場所,其生活方式并沒有太大的改變。在群體內(nèi)部的生存實踐中,他們?nèi)糟∈刂鴤鹘y(tǒng)的生活方式與文化法則。澳大利亞人類學家格迪斯認為苗族人堅定的文化認同堪與猶太人比肩:“他們被分割成若干個小群體,并且散布在廣闊的地理范圍內(nèi)。他們被其他群體所包圍,但仍保留著自身的文化認同。這一點堪與猶太人比肩且更加令人震動,因為他們?nèi)狈ξ淖趾驼y(tǒng)宗教的整合性力量,也因為他們保存的文化特征數(shù)量極大。”[14 ]52信仰和儀式是文化的內(nèi)核,也是民族價值觀的深層次體現(xiàn)。即便遷居異地,苗族移民仍然保持著原有的信仰與儀式活動。
走進苗族代耕農(nóng)的家屋,便可發(fā)現(xiàn)在其堂屋正壁上供奉的祖先牌位以及用于驅(qū)鬼治病的各種符咒。苗族人具有較強的祖先觀念,在他們看來,即便是遷離故土,祖先的靈魂仍在守護著他們。在春節(jié)、元宵、中元等節(jié)日,以及在婚喪嫁娶、生兒育女、遷居新房等重要儀式場合,苗族代耕農(nóng)都要祭拜祖先,告慰祖先家中發(fā)生的重大事情。在祭祖儀式中,一般會追溯同輩、父輩和祖父輩三代以內(nèi)的先人。① 苗族人的家族觀念在其祭祖儀式中得到充分體現(xiàn),人們所祭拜的三代祖先,不僅包括一個家庭中的直系長輩,同時也包括三代以內(nèi)的本家族的所有去世的家族成員。可以說,祭祖活動不僅是對祖先的追思,同時也在不斷強化家族成員之間的血緣聯(lián)系。
在苗族人的觀念中,祖先是家族的守護神,土地神是村寨保護神,不管走到什么地方,都要拜祖先、拜土地神。在云南原籍地時,每個村寨都有自己的土地廟。定居陽江之初,苗族代耕農(nóng)便在附近的林地中修建了簡易的土地廟,在每年的農(nóng)歷二月初二進行祭拜。在祭拜儀式結(jié)束后,人們即在土地廟前聚餐。“村長”組織大家對有關(guān)集體的重大事項進行商議,并通過看雞卦來預(yù)測接下來一年村落的運勢。土地神信仰無形中將移民群體凝聚起來,苗族代耕農(nóng)認為“拜了一個土地,大家就像一家人,大家要有福同享,有難同當。”
雖然置身異己的社會環(huán)境中,但苗族代耕農(nóng)群體的儀式活動并沒有因此而減少,如出生儀式、結(jié)婚儀式、改名儀式、葬禮儀式和各種巫術(shù)儀式在日常生活中頻繁上演。盡管操辦這些儀式活動要花費一筆不菲的開支,但在文化慣性的驅(qū)動下,人們?nèi)匀蛔裱@些文化法則。這些看似可有可無的儀式活動,對苗族代耕農(nóng)來說卻是不可或缺的文化元素。儀式活動是聯(lián)結(jié)社群成員的重要媒介,同時也是共同體形成的重要場域。儀式活動的開展,不僅滿足了移民群體的精神需求,同時也將散居各地的苗族代耕農(nóng)充分調(diào)動起來,使之認識到自己并不是孤立的社會個體。
四、傳統(tǒng)網(wǎng)絡(luò)與社群重構(gòu)
移民群體從原本的社會結(jié)構(gòu)中脫嵌出來,在短時期內(nèi)會處于一種脫嵌與無序狀態(tài)。但只要移民群體擁有某種共同聯(lián)系,其群體內(nèi)部便會被重新整合起來,進而形成一個有序的、聯(lián)系緊密的移民群體。看似孤立、零散的移民群體,其背后往往有一整套的社會網(wǎng)絡(luò)和文化體系作為支撐。盡管苗族代耕農(nóng)處于邊緣化的生存困境之中,但他們并不是一盤散沙式的生存狀態(tài)。借助傳統(tǒng)的血緣親屬網(wǎng)絡(luò),分散各地的苗族代耕農(nóng)被整合為一個聯(lián)系緊密的移民社群。這在很大程度上增強了苗族代耕農(nóng)的生存能力,同時也使自身的主體性不斷被激發(fā)出來。
苗族人具有遷移傳統(tǒng),然而不管身居何處,他們都保留著強烈的家族觀念。相關(guān)研究表明,即便是流散海外的苗族人,也依然保留著自己的家族觀念和民族認同。[15 ]42苗族代耕社區(qū)雖是一個有機的整體,但其內(nèi)部則是由不同的家族所構(gòu)成。如云南隊的33戶代耕農(nóng),是由李、楊、陶、熊、侯五個家族構(gòu)成;麥洞村的11戶代耕農(nóng),則是由陶、王、楊、侯四個家族構(gòu)成。共同的祖先記憶和血緣關(guān)系成為凝聚家族成員的天然紐帶。在日常生活中,家族成員保持著緊密的社會往來,并且具有較高的家族認同感。每個家族都有一個精明強干、辦事公正的男子充當家族的頭人,其職責主要是組織協(xié)調(diào)家族內(nèi)部的重大活動,并負責處理與其他家族和外部社會的關(guān)系。特別是在處理重大事務(wù)的過程中,家族構(gòu)成社會行動的基本單位。家族觀念的存在,不僅為苗族人提供了可資利用的社會網(wǎng)絡(luò),同時也為他們的生存提供了基本的保障。
苗族人的家族觀念具有較強的伸縮性,它可以將不具有血緣關(guān)系的社會成員納入到家族組織中去。苗族學者張曉指出,苗族人的家族關(guān)系,就像一個平面圓圈,“它以家庭為核心,以血緣為半徑,血緣越近的,關(guān)系就越親。但是貫穿其中的軸心,就是擁有共同的祖先,區(qū)別僅在于各自所處的位置離這位祖先有多遠,彼此的距離又有多遠。”[15 ]42苗族人家族觀念的無限延展,可以擴大至同姓集團。在苗族人的觀念中,同姓即是同一遠古祖先的后裔,彼此即是兄弟姊妹。這種具有伸縮性的家族觀念,可以靈活地將移民群體整合起來。
在苗族社會中,同姓之間借助家族觀念進行社群重構(gòu),異姓之間則是通過親屬網(wǎng)絡(luò)進行社群重構(gòu)。在苗族代耕社區(qū)內(nèi)部的各家族之間,存在著盤根錯節(jié)的親屬網(wǎng)絡(luò)。對苗族移民來說,親屬網(wǎng)絡(luò)越龐大,其可資利用的社會資源也就越多。構(gòu)建親屬網(wǎng)絡(luò),最為直接和有效的方式便是締結(jié)姻親關(guān)系。一旦兩個家庭間建立起姻親關(guān)系,兩個家族,乃至兩個社區(qū)便處于親屬網(wǎng)絡(luò)之中。
相對于親屬的生物屬性,人類學更為關(guān)注它的社會屬性。在傳統(tǒng)苗族社會,主要社會關(guān)系和社會行動均是借助親屬關(guān)系網(wǎng)絡(luò)展開。在異鄉(xiāng)的生存實踐中,苗族代耕農(nóng)有意識地建構(gòu)自己的親屬網(wǎng)絡(luò)。實際上,許多苗族代耕農(nóng)在遷徙陽江之前彼此并不熟識,其社會網(wǎng)絡(luò)是在遷徙陽江之后才逐漸建立起來。在群體內(nèi)部進行交往時,苗族代耕農(nóng)從家族觀念和親屬關(guān)系兩方面來編織自身的社會網(wǎng)絡(luò)。
例如,曾在陽江平崗鎮(zhèn)寨山村代耕的王應(yīng)榮,于2011年在其姻親的介紹下來到樂安買房定居。在寨山代耕時,他與定居樂安的苗族同鄉(xiāng)并不熟識。來到樂安定居之后,他便主動到附近的幾個代耕社區(qū)中認親戚。在苗族代耕農(nóng)群體中,王姓較少,王應(yīng)榮便從妻子侯氏的關(guān)系入手來編織自身的親屬網(wǎng)絡(luò)。王應(yīng)榮得知云南隊有侯氏家族,便主動前去認親。用他的話說,“雖然大家沒有親戚關(guān)系,以前也不認識。但在陽江這個地方我們?nèi)松伲龅酵盏木驼J作兄弟,不是同姓的就認作親戚。現(xiàn)在,云南隊的姓侯的和我們是親戚,他們都叫我姑爹,有事情大家都會相互幫忙。”這種擬制的親屬關(guān)系,既是苗族人家族親屬觀念的擴展,同時也是苗族人建構(gòu)出的一種結(jié)群策略。
有學者指出,苗族社會的最大特點便是其相互依賴性。[16 ]30在社群整合過程中,苗族代耕農(nóng)利用傳統(tǒng)的家族觀念和親屬網(wǎng)絡(luò)來構(gòu)建自身的社會網(wǎng)絡(luò)。對他們來說,社會網(wǎng)絡(luò)成為他們在異鄉(xiāng)生存的重要資本。個體成員唯有將自身融入本群體的社會網(wǎng)絡(luò)之中,才能實現(xiàn)自身的生存和發(fā)展。在家族觀念和親屬網(wǎng)絡(luò)的整合下,分散的苗族代耕農(nóng)被有機地整合在一起,從而使他們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邊緣情境中極易出現(xiàn)的人格分裂的精神特質(zhì)。
實際上,所謂的“外人”不僅是一種社會事實,同時也是人為建構(gòu)的符號,其地位和處境最終還是由他的力量所決定的。[17 ]124當外來群體的力量足夠強大時,他們可以構(gòu)建出自身的社會網(wǎng)絡(luò),進而與當?shù)卮迕裾归_競爭。隨著分散的苗族代耕農(nóng)不斷走向整合,他們與當?shù)卮迕裨诹α繉Ρ壬习l(fā)生了逆轉(zhuǎn)。現(xiàn)在,僅分布在樂安村委會轄區(qū)內(nèi)的苗族移民就有800余人,這個數(shù)字已接近當?shù)貞艏丝诘娜种弧钒残姓骞灿腥丝?15戶,3168人,① 但這些人口零散分布在21個村民小組之中,平均下來每個村民小組僅有30戶,150多人。加之當?shù)卮迓渲械摹熬ⅰ贝蠖噢D(zhuǎn)移到城鎮(zhèn)之中,留在村中的多是老人和能力較弱的村民。在碎片化的村落結(jié)構(gòu)中,苗族代耕農(nóng)具備了一定的生存優(yōu)勢,這使得當?shù)卮迕癫坏貌徽曔@些外來移民。苗族代耕農(nóng)的社群整合,不僅使其在移居地的社會根基得以進一步鞏固,同時也使他們逐漸擺脫了邊緣化的生存地位。
五、結(jié) 語
在主流觀念看來,移民群體的社會適應(yīng)就是一個不斷融入主流群體,逐步被主流群體同化的過程。實際上,不同的移民群體會根據(jù)自身特點發(fā)展出不同的適應(yīng)策略。一些移民群體通過積極學習主流社會的文化標準來克服自身的文化劣勢,而某些群體則會采取拒絕主流文化的態(tài)度來應(yīng)對自身的文化劣勢。對處于邊緣地位的移民群體來說,放棄自身的文化資源與社會網(wǎng)絡(luò)并不意味著能夠在主流社會中獲得生存優(yōu)勢。相反,在適應(yīng)新環(huán)境的過程中,傳統(tǒng)文化與民族特性仍在發(fā)揮積極作用。
通過苗族代耕農(nóng)的生存策略可以看出,他們并沒有選擇融入主流群體,而是在主流群體之外建構(gòu)自身的移民社群。相關(guān)研究表明,珠三角地區(qū)代耕農(nóng)采取個體化的生存策略,在面對生存困境和當?shù)卮迕竦臄D壓時,他們往往處于孤立無援、內(nèi)部分化的狀態(tài)。[18 ]而分布在陽江的苗族代耕農(nóng)借助家族組織和親屬網(wǎng)絡(luò)實現(xiàn)了社群整合,從而在很大程度上增強了自身的生存能力和群體力量。可以說,正是通過群體內(nèi)部的團結(jié)互助,苗族代耕農(nóng)才得以走出邊緣,在異質(zhì)文化的社會空間中生存下來。
參考文獻:
[1] Park R E. Human Migration and the Marginal Man[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1928,33(6):881-893.
[2] Park R E, Burgess E W. Introduction to the science of sociology[M].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70.
[3] Stonequist E V. The Problem of the Marginal Man[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1935,41(1):1-12.
[4] 周大鳴. 永恒的鐘擺——中國農(nóng)村勞動力的流動[G]//柯蘭君,李漢林.都市里的村民:中國大城市的流動人口.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1: 304-324.
[5] 陸海發(fā),白利友. 邊疆少數(shù)民族自發(fā)移民的邊緣化處境及其成因分析——基于對云南K縣的調(diào)查[J]. 北方民族大學學報,2012(3): 39-46.
[6] 申群喜,胡波,葉立新,等. 珠三角代耕農(nóng)的生存境況及相關(guān)問題研究[J]. 云南財貿(mào)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06,21(1): 67-70.
[7] 云南省廣南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廣南縣志[M].北京:中華書局,2001.
[8] 費孝通. 費孝通全集:第二卷[G].呼和浩特:內(nèi)蒙古人民出版社,2010.
[9] 陸海發(fā). 云南K縣苗族自發(fā)移民問題治理研究[D].昆明:云南大學博士論文,2012.
[10] 郭星華. 社群隔離及其測量[J]. 廣西民族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0(6).
[11] 陸益龍. 戶籍制度——控制與社會差別[M].北京:商務(wù)印書館,2004.
[12] Hurh W M, Kim K C. Adhesive Sociocultural Adaptation of Korean in the U.S.: An Alternative Strategy of Minority Adaptation[J].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1984,18(2):188-216.
[13] 路易莎.少數(shù)的法則[M].校真,譯.貴陽:貴州大學出版社,2009.
[14] Geddes W R. Migrants of the mountains : the cultural ecology of the Blue Miao (Hmong Njua) of Thailand [M].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76.
[15] 張曉. 美國社會中的苗族家族組織[J].民族研究,2007(6).
[16] 左振廷. 關(guān)于Hmong人家族組織的文化生態(tài)整體性研究[J].廣西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5(1).
[17] 陳柏峰. 村落糾紛中的“外人”[J].社會,2006(4).
[18] 黃曉星,徐盈艷. 雙重邊緣性與個體化策略——關(guān)于代耕農(nóng)的生存故事[J]. 開放時代,20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