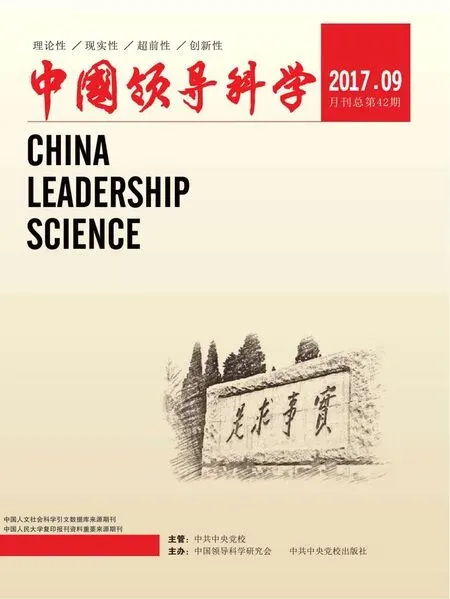西方自由主義的“普遍性”批判
◎張 竑
西方自由主義的“普遍性”批判
◎張 竑
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不斷對我國意識形態領域進行侵擾和干涉,企圖動搖我國人民的信念。本文通過分析西方自由主義的“普遍性”的非歷史來源、西方自由主義的“普遍性”自身的邏輯錯誤和西方自由主義自身的不合理性三個角度,對西方自由主義的“普遍性”觀點進行批判。
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理性批判
當代西方資本主義國家通過各種手段、利用各種媒介渠道,不斷對我國意識形態領域進行侵擾和干涉,企圖用思想武器動搖我國人民的信念,阻撓我國的發展。他們的這些做法,體現了文化霸權主義和話語霸權主義,根源于冷戰思維的殘余和西方中心主義的固執。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批判和駁斥西方自由主義的“普遍性”觀點,是我國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的重要責任和神圣使命。本文嘗試從三個方面對西方自由主義的“普遍性”觀點進行批判。
一、西方自由主義的“普遍性”的非歷史來源
西方自由主義號稱個人自由的“普遍性”來自何處?西方學者的答案通常是給出一種先驗的回答或者邏輯的假定。比如“天賦人權說”、“神意說”、“人性說”、“理性說”、“先驗說”、“經驗傳統說”等等,以“天賦人權說”為例來進行理論反駁,其他假說的性質可與此類似。今天距離“天賦人權說”提出已有200多年,當我們冷靜地審視這套理論的時候,就會發現它不僅實踐效果有明顯的局限性,而且理論本身也有明顯的脆弱性。
從實踐的角度看,“天賦人權說”僅在法國和美國取得了效果:孟德斯鳩和盧梭的理想設計是通過法國大革命結束了封建制并建立了共和國;美國的杰弗遜把“天賦人權”寫進《獨立宣言》。在英國,霍布斯和洛克的相關理論不是事前的啟蒙,恰恰相反,是事后的總結。當19世紀的戴雪以及20世紀的哈耶克在分析英格蘭法治的時候,二人都認為英國的法治是源于英國人的民族本性,而并非源于啟蒙學者的思想。在德國,幾乎從未真正信仰過“天賦人權說”。在廣大的第三世界國家的幾百年奮斗歷程中,“天賦人權”僅僅是政治理想的口號。
從理論的角度看,“天賦人權說”自19世紀開始就一直飽受抨擊。因為這種假說根本就是憑空而造出的,沒有歷史和哲學的根源。被黑格爾視為“政治生活和宗教生活的積極狂熱”,被邊沁稱之為“修辭上的胡鬧”,被梅因稱之為“純粹理論的信條”,終被馬克思用唯物史觀進行了批判和取代。馬克思認為,權利并非每個人生而有之,是特定的社會生活條件決定了權利的內容和范圍。肯尼迪的法律政治學揭示了“天賦人權說”的內在矛盾性,即人們永遠都在利己與利他、個人與社群之間無所適從,而“天賦人權說”并沒有給人們肯定和明確的價值判斷。歐洲的后現代主義學者認為,人類永遠是在權力和訓誡下掙扎,“天賦人權說”只不過是以文明的壓迫代替了野蠻的壓迫。
可見,“天賦人權說”具有非歷史性,人權不是天賦的。正如馬克思所說,一定的社會存在決定一定的社會意識,是由于隨著生產力的不斷發展,舊的生產關系必須讓位于新的生產關系時,這種新的生產關系的發展使人們頭腦中產生了對于人權這個概念新的意識、新的理解和新的規定,人們沒有意識到這種新的意識根源于生產力的發展,于是借口是“天”賦予了這種人權的規定性,憑借這一學說妄圖沖破舊勢力對生產力發展的阻撓。同樣,“神意說”、“人性說”、“理性說”也是如此,都是憑空捏造一個非歷史性的學說來試圖解釋歷史、沖破障礙。這種新的生產方式(資產階級生產方式)在人的頭腦中重新定義了人們對人權的理解,由于這種理解不是在一個人或一代人之中完成的,而是具有歷史繼承性動態地發生著改變,所以人們以為這種意識是在頭腦中先驗存在著的,于是康德提出了“先驗論”,其實恰恰相反,先驗的錯覺來源于人們經驗的不斷改變。哈耶克的“經驗傳統”說認為“個人自由”不是人為設計的,而是由傳統演化、逐漸形成的。但他所說的傳統,只是指近百年的現代社會發展傳統,并不是指從人類一開始就存在至今的傳統。
西方學者的眾多答案有一個共同的問題,就是缺乏歷史性,僅僅依靠主觀的臆斷或抽象的想象,企圖賦予自由主義“普遍性”一個合法的來源,說到底仍然是一種唯心史觀的表現。西方所謂的自由主義僅是西方物質生產活動、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的暫時性產物,對于不同時期、不同地域、不同條件的社會或國家來說,并不具有普遍性。如果非要說是普遍性的話那也僅是有限度的普遍性,而不是所有社會或國家都普遍適用或者同時適用的。西方自由主義“普遍性”的來源,如馬克思批判資產階級觀念所說的那樣:“你們的觀念本身是資產階級的生產關系和所有制關系的產物,正像你們的法不過是被奉為法律的你們這個階級的意志一樣,而這種意志的內容是由你們這個階級的物質生活條件來決定的。”[1]這才是問題的本質。
二、西方自由主義“普遍性”的邏輯錯誤
西方的自由主義突出強調個人具有選擇的權利,屬于個人的私人事務。比如,有關信仰、情感、性愛、婚姻、嗜好、興趣、思想、學說等等方面,“不強加于人”是基本原則,無論是以國家、政府、社會、團體、輿論、宗教的名義都不可以強加于人。[2]這正是西方所謂“自由”的要義所在。按照這種邏輯,西方自由主義應該允許反對自由主義的其他主義、信仰、思想和學說的發表和發展的權利,這才能體現出自由主義的“自由”要義,而政治家、政府、法律一般不能干預這種自由。那為什么西方國家熱衷于對我國人民的自由選擇指手畫腳呢?這不正說明他們所謂的自由主義根本就不自由嗎?
西方自由主義者以我國人民的選擇是在“不自由的狀態下”為借口,質疑中國共產黨存在的合法性。他們認為我國人民是被中國共產黨強迫做出自己選擇的,以救世主的心態來對待中國人民,并以此借口來干涉我國內政,甚至顛覆我國的政權。這種強盜邏輯不是現在就有的,早在西方殖民擴張時期就已存在了。西方以臆想和偏見為基礎,丑化中國共產黨的形象,捏造我國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的偽現狀,以所謂的“普世價值”為懸設,賦予西方以“神圣使命”來解救中國人民,打造所謂的西方式的民主政治體系。這是明顯的強盜邏輯。他們不以事實為根據,不以中國人民的真實想法為根據,僅以西方中心主義的狹隘觀念,不擇手段地丑化中國共產黨、丑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建設成就,其心何其毒也。
西方的做法有兩方面的深層原因。一方面是帶有冷戰思維的殘余,心底里仇視社會主義中國、敵視社會主義陣營,以不消滅社會主義就會被社會主義所消滅這種僵化固執的思維方式看待世界,沒有辯證地看到時代的發展和形勢的變化。現今時代是和平與發展的時代,每個國家、各國人民都有選擇自己發展道路的權力,人民選擇適合自己的發展方式和政治制度是天經地義的,不容他國干涉和阻撓。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是國家間交往的底線原則。
另一方面是西方國家忌憚中國的高速發展,忌憚中國所具有的巨大潛力和強大凝聚力。西方國家不希望看到中國的發展和強大,以為中國強大起來就會像西方國家尤其是像美國那樣,搞極權主義和霸權主義,他們不了解中國人民的處世原則與中國所特有的發展理念。與西方傳統游獵民族的處世原則和生存理念截然不同,發源于農耕文明的中華民族自古以來就是愛好和平的民族,西方以征服、掠奪為原則,中華民族以和睦、安居為原則,從這一點上來說,中國人更能理解為什么西方人骨子里會對中國有如此強盜邏輯。
三、西方自由主義自身的不合理性導致其不具有“普遍性”
西方學者在用自由主義的“普遍性”指責我國的時候,卻沒有意識到他們所謂的自由主義自身具有不合理性。在北美和西歐,自由主義的充分發展實際上正在走向它的反面。
西方自由主義在政治領域,突出表現為西方的民主政治體制。西方自由主義民主政治的原則是,每個人可以自由地選擇積極地或者消極地參與政治選舉活動,這是每個人的權利,但實際情況卻是大多數人“事不關己,高高掛起”,對于政治活動非常消極甚至干脆不參與。普通民眾對政治很冷淡,多以娛樂節目的心態看待政治選舉活動,所以總統、議員的得票率常常極低。普通民眾對政治的冷淡態度導致民主選舉活動被各種別有用心的利益集團所操控,帶來的結果是對大多數人的不利。2016年美國總統大選就是典型事例,選舉結果出來后,美國的中產階級(現今美國人數最多的階級)椎心泣血,整個精英階層大跌眼鏡,這就是典型被操控的結果,說明在資本主義社會,資本的力量必然導致資本與政治的結合,只有這樣,資本才能獲得更大的力量,獲取更多的收益;但對于普通民眾來說并不是好事,資本的力量越強大,民眾的力量越弱小。以致于出現西方“倡導個人自由的自由主義似乎反而使大多數人可能在政治上處于無能為力的不自由狀態。”[3]
西方自由主義在文化精神領域,突出表現為社會變成了個人原子化的社會,即人與人之間日益孤立分離,人際冷漠、人情淡薄、精神空虛、心理躁動。在衣食無憂的情況下,發現自己的人生沒有目的、身處的世界沒有意義、生活沒有價值,于是吸毒、暴力和性放縱泛濫成災;西方的“新聞自由”提倡多元和多樣,但實際上變成了在媒體的控制下的不自由,多元和多樣變成了一元化和同質化;西方自由主義提倡啟蒙精神,事實上變成了愚民精神;西方自由主義倡導理性至上,現如今理性變成了反理性的有效工具,個體的自由自主被異化、被商品化,變成了對個人從心靈到生活全方位的枷鎖和奴役。
正是因為西方自由主義本身所具有的弱點和缺陷,導致如今各種宗教的復興,西方學者和民眾開始反思和質疑這種自由主義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一個自身不合理的理論卻要把它“普遍化”,就意味著故意把有眾多弱點和缺陷的自由主義硬說成是普遍的真理。他們硬要把不合理的“真理”強塞給中國,非要中國嘗嘗這種歪理的苦果,背后的居心,不正是唯恐中國不亂的陰謀嗎?
面對西方國家以自由主義“普遍性”為代表的偽真理輸出活動,廣大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應高度警醒,積極運用理論武器和現實依據批判這種偽真理、偽命題,自覺維護我國意識形態的自主性,促進人民群眾對于西方意識形態滲透的辨別力的提高,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貢獻理論工作者的智慧和力量。
[1]《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17頁。
[2][3]李澤厚:《哲學綱要》,中華書局2015年版,第31頁;第32頁。
責任編輯:王鵬凱
D091
A
2095―7270(2017)09―0039―03
(本文作者:中央黨校哲學教研部博士研究生,中共黑龍江省委黨校機關黨委宣傳科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