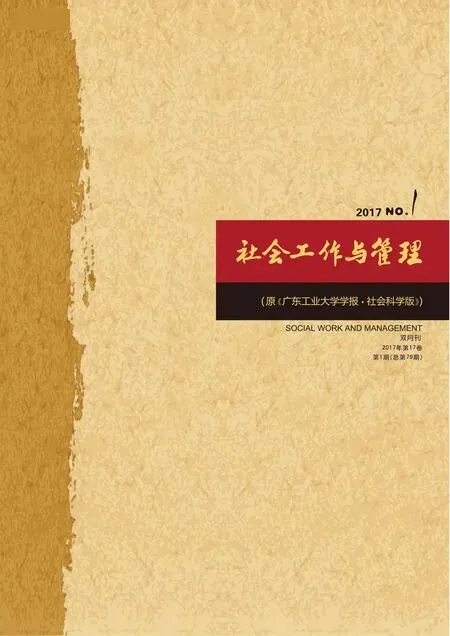少數民族流動人口社會工作服務路徑探析
——以云南A機構布依族社工介入為例
玉萬叫,喬東平
(1. 中共西雙版納州委黨校,云南 景洪,666101;2. 北京師范大學社會發展與公共政策學院,北京,100875)
少數民族流動人口社會工作服務路徑探析
——以云南A機構布依族社工介入為例
玉萬叫1,喬東平2
(1. 中共西雙版納州委黨校,云南 景洪,666101;2. 北京師范大學社會發展與公共政策學院,北京,100875)
我國少數民族流動人口日益增多,他們在城市面臨很多問題和困難,急需社會工作服務的介入。A社工機構通過近十年為流動布依族服務的經驗,探索出通過成立布依族婦女互助小組搭建為布依族流動人口增權的互動機制。布依族婦女互助小組成員實際充當“一線社工”來為整個族群服務,依托該互動機制,刺激布依族婦女的能力建設,培育布依族流動人口的民族主體性,使社工服務效果符合布依族的需求。因自助組織有自身的缺陷,A機構應協助布依族婦女互助小組鏈接更多的資源;讓社區其他人群參與布依族的活動,避免布依族群體內卷化的發生;適當考慮婦女互助小組成員的社工倫理等。
少數民族流動人口;婦女增權;自助組織;社區工作
一、研究背景與問題的提出
隨著我國改革開放的深入推進,我國少數民族流動人口日益增多,每年有少數民族流動人口約1 000萬人。[1]少數民族流動人口進入城市后,不僅和漢族流動人口一樣受到城市社會的制度性排斥,且自身所攜帶的本民族文化和鄉村文化必然會與漢族文化和城市文化發生一系列的接觸和互動,[2]在城市社會中處于“雙重弱勢”的地位,[3]面臨如語言、習俗、就業、教育等方面的諸多困難。近幾年,我國社會工作得到了一定發展,正在起步中的民族社會工作主要關注邊疆少數民族地區的社會工作,對于少數民族流動人口關注的較少。城市作為不同民族和各種文化的主要交匯點,是民族問題的主要引發區。[4]少數民族流動人口關系到城市社會的穩定和我國民族關系的全局。[5]做好少數民族流動人口社會工作對社會穩定、民族團結都具有重要的作用。云南A機構已經做了近十年的布依族流動人口社會工作服務,并積累了寶貴經驗,分析其經驗,對流動少數民族社工服務具有借鑒意義。
我國民族社會工作研究處于正在被建構的階段,目前無專著,且已發表的相關文章數量少。早期研究民族社會工作的學者將民族社會工作界定為在少數民族地區開展的針對少數民族人口的助人工作。[6]隨著民族社會工作的發展,學者們不斷擴展其服務對象和針對區域。目前,我國民族社會工作的范圍以民族地區為主,同時兼顧城市中的少數民族流動人口。[7]在理論構建方面,有學者基于增權理論,從增權理論的個人、人際、社會三個層面出發,提出社工應該從不同的層面來給少數民族流動人口增權。[8]李林鳳基于福利文化理論,認為少數民族流動人口可分為具有宗教特點和宗法性特征的兩類福利文化資源,應根據不同的福利文化來開展社工服務。[9]然而此方面的研究缺少微觀的單個流動少數民族的分析研究。在服務模式分析方面,上海的自上而下、購買社工機構服務、招募少數民族社工服務社區少數民族以及實現社工、社區和社團的互助等成功的經驗受到學者的認可。[10]也有學者認為,對少數民族社會工作人才培養的研究及實踐,是推動民族社會工作發展最為直接也是最為長遠的路徑。[11]已涌現出的對少數民族流動人口社會工作服務的研究多基于機構的主體角度來分析,機構如何從流動少數民族出發,挖掘少數民族主體性的相關研究較少,本文將在此方面進行探討。
二、研究對象與研究方法
A機構秉承扎根社區,與流動人口為伴,促進社區互助合作,實現有尊嚴、有價值、有保障的勞動和生活的理念,已在昆明市流動人口較多的社區服務了十多年。調研所在社區隸屬于昆明市五華區普吉路街道辦事處,該社區聚集大量流動人口。據機構估計,該社區的流動人口為原住民人口的5—8倍,本文所介紹的布依族就居住在此社區。該社區的布依族流動人口主要來自貴州省安順地區。他們聚集而住,在社區中形成一個個布依族院子,他們操著布依族語言,過著布依族節日,過著拾荒為生的生活。因拾荒工作的特殊性,布依族流動人口人際交往范圍較小,大部分僅限于同族、同鄉、同業人之間,與城里甚至城中村社區里的居民來往甚少。布依族院子和社區的其他部分形成了“二元社區”。布依族有多子多福、重男輕女的現象,一般的布依族流動人口家庭通常有3~5個孩子。在布依族流動人口中,布依族婦女的地位較低。布依族神話傳說賦予了男性高尚而女性附屬的地位,重男輕女的生育觀念加劇了布依族男尊女卑的觀念。背井離鄉到昆明,布依族流動人口不能享受戶口附帶的一系列權利和資源;且由于拾荒收入較低,家庭孩子數量較多等原因,布依族孩子輟學現象較嚴重。
為了與布依族流動人口、機構工作人員建立良好的關系,以深入了解A機構布依族流動人口社會工作服務情況,筆者采用質性研究法,于2014年7—9月和2015年3月分別在A機構及其所在社區實習與調研。
首先,采用參與觀察法。本人參與到A機構的日常工作中,觀察社工開展的服務,同時也參與到布依族流動人口的日常生活中。
盡量不要用正式的訪談方式去問布依族,而是去他們家做客,拉拉家常,與他們從事活動。(機構負責人AL)
流動少數民族社會工作板塊負責人XM是此次研究的重要對象之一。
觀察她的行為,她怎么與老鄉們相處,與她服務時就具體的問題來詢問,這本身就是一個帶有感情的介入方法。(工作人員YX)
在調研中,筆者主要采用了在觀察中詢問問題的方式。為了深入了解布依族家庭,在調研期間,筆者每天拜訪兩個布依族家庭,觀察其家庭情況、家人之間的互動、婦女在家里的地位等,并就有關問題進行訪談。其中一個家庭的信息如下。
Y家庭有5口人,Y(丈夫),W(妻子),3個孩子,YA(大女兒)、YB(二女兒)、YC(兒子)。夫妻倆主要從事拾荒工作,在空余時間,丈夫Y大哥會幫建工老板拉土,妻子W大姐周一到周五到A機構公益小飯桌做飯,W大姐是布依族婦女互助小組的骨干人員。該家庭收入每年為46 000~48 400元,消費支出為31 680元/年,其中房租和水電費4 800元/年,孩子教育費4 480元/年(孩子都在讀小學),生活費21 600元/年,服裝費800元/年(僅過年買)。
其次,采用半結構訪談法。筆者訪談了8位機構負責人和社工(見表1)以及5位布依族大姐(見表2),以深入了解A機構的整體狀況和布依族流動人口社會工作開展的歷史進程和運行情況,以及社區和婦女互助小組的情況、服務內容、服務方法和成效等。

表 1 被訪談機構負責人和社工的基本情況

表 2 被訪談5位布依族大姐的基本情況
機構工作人員和布依族婦女都了解本研究的目的,且在征得被訪者同意的情況下,筆者才開展訪談。筆者與某些工作人員和布依族婦女參與活動過程時,根據原先的訪談框架,就一些問題進行提問;服務結束后,再將所得材料記錄下來,查缺補漏,反復對其進行提問,以得到真實的答案。
三、布依族流動人口社會工作服務路徑
A機構與流動人口為伴,扎根于布依族流動人口所在的城中村之中,做了近十年的布依族流動人口社會工作,經歷了“互相認識”“澄清探索”“衰落擱淺”“思路轉換”等階段。
(一)以兒童為點撬動整個族群
2007—2012年,A機構遵循如圖1所示的社工服務路徑對布依族流動人口進行介入。由兒童為點撬動整個流動布依族族群,在跟進的過程中發現布依族的問題和需求,并開展相應的服務。
當時我們在社區里提供兩種服務,一種是課業輔導,另一種是康樂活動。小孩子就過來玩,其中有一群小朋友,他們不跟漢族人說話,但是他們也很渴望來玩,然后我們跟他們聊天。慢慢地,我們通過游戲與這些孩子建立起了信任關系。我一個人背著一個包,就是我們最早的外展樣子,我就背著玩具、書、餅干、小禮物等,(布依族巷子里的)小朋友們看到這么多好東西就來接近我。如果我找到他們中的一個小孩子,就可以把他們整個院里的小朋友都認識,因為他們是以院落的方式居住的。通過這樣的方法,我們發現了問題,(并)開展活動。(機構副主任ZR)

圖 1 2007—2012年A機構對布依族流動人口的介入路徑
A機構通過兒童活動中心和外展活動接觸到布依族流動兒童,發現兒童的需求和問題,展開相應的諸如兒童安全教育小組等服務。社工與兒童建立了信任關系后,進一步接觸到布依族家長。社工借用布依族的“酒文化”,與兒童父母建立起聯系。
與這些孩子混熟了以后,我就去他們家,跟家人聊天,差不多到了吃飯的時間就買點酒跟他們喝。布依族的酒文化很濃,喝了酒就交了朋友,也認識了。但是喝完酒想到錢賺得少,生活郁悶啦,我們就發現他們夫妻家庭暴力很嚴重,然后我們就開展反家暴活動。(機構主任AL)
介入家庭后,機構發現布依族家庭存在家庭暴力現象,便針對此開展反家庭暴力活動。一般情況下,布依族婦女是家庭暴力的受害者。社工積極動員婦女群體開展婦女健康、生計等小組,進而展開對婦女的介入思路,挖掘婦女的刺繡優勢,利用布依族婦女所擁有繡花的優勢和機構所囤積的大量廢舊物來進行舊物改造,成立舊物改造中心“綠工坊”。
開展家暴個案的同時,我們也組建一些婦女小組,(如)舞蹈小組、刺繡小組等,激發婦女去做一些事。看到老婆在舞臺上跳舞,他們就會想,原來老婆還有這樣的能力。漸漸地,丈夫就會用欣賞的眼光去看待他身邊的這個人。(機構主任AL)
機構通過開展布依族文藝演出、布依族傳統“六月六”等民族活動來介入整個族群。
機構以布依族兒童為介入點,因為兒童具有強烈的好奇心與求知欲,便于社工接觸到大量的布依族兒童。一般社區工作建立關系由拜訪社區的重要人物或社區機構入手[12],易于短時間獲得族群的信任。布依族兒童在整個布依族中無權威性,不利于社工在短時間內得到布依族流動人口的信任,以及根據服務對象的困難與需求靈活及時地開展針對性的社工服務。該時期的A機構對布依族流動人口的社工介入帶有明顯的社會救助式特征,表現為A機構為主動服務者,而布依族流動人口為服務的被動接受者,這樣不利于布依族流動人口自我成長。此外,該服務模式需要引入大量的社工對布依族流動人口進行服務,布依族流動人口的主動性被抑制的同時,作為主動方的機構介入思路也容易枯竭,這也是A機構布依族社工服務處于“衰落擱淺”的原因。
(二)服務開展主體為“布依族婦女互助小組”
2012年,A機構緊扣云南少數民族特色,突出少數民族的自主性,成立了流動少數民族社會工作板塊,由社工XM提供專門服務。
A機構所服務的布依族流動人口聚居在3個大院里,且很少與社區的其他人來往。由于拾荒工作的原因,布依族流動人口與社區中其他居民有一定的隔閡,甚至受到社區其他成員的歧視和排斥。族群中部分人的惡習也在布依族流動人口和社區里其他人交往中增添了一道障礙。在XM服務之前,受團結互助的布依族傳統文化影響,各個院內的布依族團結互助,但院與院之間彼此很少往來。
我不跟他們(布依族流動人口)玩,跟你說我覺得他們有一股垃圾的味道,難聞,太臟了。(社區其他成員)
也不能全怪社區里的人,他們(拾荒布依族)也有順手牽羊的時候,看到別人家值錢的會在撿垃圾中帶走。(機構副主任ZY)
你居住在社區里,不得不與其他人來往,不僅是本族人,還有其他人,所以針對他們的問題,必須從社區著手。成立互助小組,先讓他們之間形成一個整體,再慢慢擴展到外圍。(機構副主任ZY)
思路轉換后,機構在社區中培育布依族婦女互助小組,旨在構建布依族流動人口間的互相支持網絡,激發布依族婦女自我發展的能力,以提高布依族婦女的地位,轉變原來帶有明顯社會救助式的服務方式,培育流動布依族群體的主體性,激發其發現自身議題的能力。
接手之前他們間隔閡很大,互相之間往來很少。若僅僅是按照救助式的方式去幫助這些布依族老鄉,那么這些布依族老鄉會越來越依賴我們。擺脫這種救助式的方式就是賦權,開展婦女互助小組。在開展的過程中擴展人脈,形成自助組織,培養婦女“大姐”,將一些事情交給“大姐”帶領這布依族老鄉去做。(社工XM)
布依族婦女互助小組屬于社區自助組織。自助組織是指為了滿足共同需要,克服共同面對的困難和問題,尋求個人和社會改變的一群人自發形成的組織。[13]布依族婦女互助小組通過外力機構的推動漸漸成立,旨在群體間的自助和互助。少數民族社會工作板塊成立后,XM每天對布依族流動人口進行家訪或拾荒勞作;將機構資源帶入群體,與婦女們開會討論,以民主的方式選出活動方式,以培育婦女的參與能力。漸漸地,XM與婦女們建立了良好的信任關系。在機構的介入下,布依族婦女互助小組建成,共有30多位婦女成員參與,選出3名婦女骨干,分別負責統籌、財務、文藝等事項;且在3個布依族大院分別成立了下一級布依族婦女互助小組。
我們的任務就是要教會他們管理和組織的知識、方法、技巧。而這些的目的就是讓他們自己關注自己的問題,讓他們學會解決自身的問題。(社工XM)
將弱勢群體從受助者的角色轉化為幫助者是自助組織運行模式的顯著特征之一。[13]3年來,A機構教授了婦女小組成員管理、組織、策劃等方面的技巧,培育其鏈接和整合資源以及發現本族議題的能力。布依族婦女互助小組作為中介,積極發揮著機構和布依族流動人口服務中介的作用,以布依族貧困生助學項目和工藝小飯桌為例。
1.布依族貧困生助學項目
布依族流動兒童輟學現象較嚴重,在XM的努力與爭取下,2013—2014年,XM從機構中爭取到了一部分資金,用于資助布依族貧困生。
那這些錢你爭取到了以后,是機構決定要資助他們的嗎?(訪談者)
沒有,是要婦女小組決定。要資助誰啊,這些都是他們來決定的,每個人都說自己貧困,我們機構怎么去資助,但是他們內部是知道哪些家庭好一些,哪些窮一點的。他們內部對大家的情況了如指掌,標準也交給婦女們去定。我和機構就是協助他們,給他們開開會,標準是他們定的。(XM)
熟悉彼此是布依族流動人口的一大優勢。機構積極利用這些優勢,將一些機構辦不到的事情交給婦女小組去商量和討論。項目的資助方案、資助條件等均由布依族婦女提出和通過,機構只是起到協助的作用。婦女小組根據布依族家庭人口、就讀學校性質、家庭收入狀況等來制定資助方案。
2.公益小飯桌
由于父母工作性質的原因,2013年底,布依族婦女互助小組就孩子們的午餐問題向機構提出了本族的公共議題。但限于機構人力、資金、場地等原因,此事便一直耽擱。2014年,XM爭取到機構的部分善款后便分配到該群體上,婦女成員決定將資金用于小飯桌項目,并在機構的協助下制定出項目的方案以及人員的分配等事宜。社工XM和布依族W大姐分別是公益小飯桌的項目負責人和食堂負責人。孩子們的參與及進出條件、管理人員補助標準、飯菜搭配等均有婦女互助小組自己決定。
孩子們要吃什么菜是我們(布依族婦女互助小組)一起定出來的,每天的菜錢為60元(每天60元為菜的總價),也是我們一起定出來的。(W大姐)
我們的孩子要進去吃飯得跟婦女小組說一聲。(L大姐)
從上文兩項目可知,A機構布依族流動人口社會工作服務路徑如圖2所示。

圖 2 2012年至今A機構對布依族流動人口的社工介入路徑
社區組織是達到社區工作的基本目標——調動社會資源、解決社區問題、促進社區進步等的基本手段和方法之一,[12]是集體增權的重要方法。婦女互助小組是布依族流動人口社會工作服務的核心,起到了服務開展主體的作用。A機構將資源通過社工XM帶入布依族流動人口中,婦女小組在此充當資源整合者,通過民主商量討論的方式制定出活動方案,進一步將資源傳入城市流動布依族族群內,如布依族貧困生項目所呈現的。婦女小組在整合資源中可增加自身的權能,培育這些布依族婦女的能力,且制定出來的方案更符合布依族群體的需求。
他們比我們知道自己需要什么,制定出來的貧困生項目方案更符合他們的需求。(機構負責人AL)
你們(社工)來做的飯孩子們不喜歡吃,他們還是喜歡吃我做的。(W大姐)
若布依族流動人口自身發現族群內部的問題或者需求,議題便進入婦女小組,婦女小組通過民主商量討論的方式制定出資源申請方案,再由XM將布依族的需求反饋到機構中,機構根據自身的資源來進一步做反饋,如公益小飯桌所呈現的。此方式能增強布依族婦女小組從主體性出發探討本族議題的能力。
從能力建設的發展性思路出發,布依族婦女互助小組不僅激發了婦女成員的能力建設,更利于激發布依族族群從主體性出發自我發現問題、自我解決問題的能力。布依族婦女通過整合資源、自我發現本族議題、申請資源,實質上是使整個族群“活”了起來,即使機構從該社區撤出,族群內部也掌握了一定的方法來面對社會的變遷。該服務路徑變受助者為幫助者,機構社工是機構和布依族流動人口間的橋梁,機構是資源的提供者,是活動的協作者,以此減輕機構成本的同時,在活動中促進被服務者能力的提高。
當火把節、“六月六”等布依族傳統活動來臨時,社工XM與布依族婦女互助小組成員們制定活動方案。在婦女互助小組的推動下,通過活動的不斷開展,各個院落的布依族打破了原來割裂的狀態,不斷朝互助支持的方向發展。
四、布依族流動人口社會工作服務經驗反思
(一)少數民族流動人口增權的互動機制
“助人自助”是社會工作的核心,“助人”是橋梁,目標在于服務群體的“自助”。一些社會工作者和研究者在工作過程中經過反思后認為,服務對象面臨的根本問題在于他們缺乏足夠的能量和信心,[14]社會工作者的工作便是給服務對象增權。
根據拉帕波特的觀點,增權是一個過程或者機制,依賴這種機制,人群、組織和社區得以控制他們的生活,且增權發生在個人、人際及社會3個層面,社會層面上的增權強調社會行動和社會改變的目標,其過程包括接近、使用政府和其他社區資源的合作行為,[15]自助組織是為群體增權的一個方法。A機構在對布依族流動人口進行介入時,培育出了布依族婦女互助組織,機構資源通過該小組整合,再進入群體;群體公共議題進入該小組,整合后再向機構申請資源。婦女互助小組作為社區中布依族自助組織,讓整個群體“活”起來。該組織與機構、整個布依族流動人口形成了一個增權的機制。通過目前的社工服務路徑,流動布依族族群掌握了申請資源、鏈接資源、整合資源的技能。實質上流動布依族族群掌握了表達自己利益訴求和參與社會資源分配的途徑,達到了社會層面增權的目的。
(二)培育少數民族流動人口自主性的服務機制
在社會工作服務中,少數民族流動人口自主性應是指少數民族流動人口根據本族的價值觀、風俗文化、生活習慣來設定本族的需要和問題,以本族的視角、方式去回應或解決本族的需要或問題。那么社會工作服務就應以少數民族群體所需要的、可接受的服務方式、結果符合其生活習慣來界定“自主性”的問題。社會工作是一個以價值觀為本的專業,價值觀被看作是它唯一或不可缺少的基礎之一。[16]在服務中,社工要對各個民族文化差異及不同民族之間社會文化邊界的變動保持足夠敏感。[17]因此少數民族的價值觀和社會工作者個人的素質是民族社會工作在實務中的具體考慮。[16]通過建立布依族婦女互助小組來培育布依族流動人口的自主性表現在兩方面:第一,從布依族流動人口自身的角度來發現自身的公共議題,即是從本組視角去界定問題及需求;第二,項目或活動均由布依族婦女互助小組討論并得以通過,互助小組成員充當“一線社工”進行服務。這樣的服務方式和服務結果是布依族流動人口所需要和認可的,即符合其生活習慣和價值觀的,由此培育著民族的自主性。
(三)少數民族流動人口社工服務的專業化反思
自助組織內部同質性較強,內部資源有限,與其他相關機構建立聯系就成為重要的獲取資源、發展自身的途徑。[10]然而,A機構僅靠機構的資源和能力對布依族流動人口開展服務,而少了社區和其他社會組織的身影。機構向流動布依族群體提供資源,流動布依族群體向機構申請資源,這在一定程度上會增加流動布依族群體對機構的依賴,結果可能事與愿違。布依族流動人口是社區的組成人員,應以社區為本,社區居委會有一定的職責來對布依族流動人口開展服務。此外,布依族流動人口具有多重身份,昆明城市管理部門、民政部門和民族宗教部門都有一定的責任來服務該族群。機構應協助流動布依族族群向更多的組織鏈接資源。
布依族婦女互助小組成員都是布依族婦女,其服務對象限于布依族流動人口群體,其服務范圍、人員組成具有封閉性的特點。人數較多的少數民族流動人口內部同質的群體成員之間交往較多,容易獲得同群間的鼓勵和幫助,民族內部進一步內卷。[18]布依族婦女互助小組的建立促進了布依族族群內部的團結與支持;但走進社區可看出,布依族流動人口與包括漢族在內的族群間交往并不多,因此機構社工與布依族婦女骨干在制定活動方案時,要多引入社區其他人員,避免布依族內部內卷化的發生。婦女互助小組成員實際充當著“一線社工”,來為整個群體服務。然而婦女小組成員的社工專業性、社工倫理等都受到一定的考驗,在開展具體某項服務時機構需要加以考慮。
城市中的布依族流動人口面臨經濟收入偏低等問題,機構在推進布依族社會工作時,應以文化和發展為視角,構建民族社會工作的任務結構框架,[19]逐漸往發展性社區社會工作推進,與社區、政府等組織共同去改善社區的經濟、社會、文化等環境,[20]去回應社區中經濟建設和發展的需要,改變社區貧困群體落后的狀況[21];而成立布依族拾荒合作社、布依族婦女刺繡合作社便是其中的選擇。
[1]中國少數民族流動人口大多進城務工經商[EB/OL]. (2010-09-16).[2014-12-03]. http://www.ln.xinhuanet.com/jizhe/2010-09/16/content_20918884.htm.
[2]張文禮. 論少數民族流動人口的城市文化適應問題[J]. 西北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3(3):75-79.
[3]朱志燕. 民族形象建構與雙重弱勢:城市中的維吾爾族流動人口——對“切糕事件”的社會學分析[J]. 中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4(34):57-62.
[4]蔣順成. 少數民族流動人口權益保障研究[D]. 北京:中央民族大學,2009:1.
[5]劉燕. 少數民族流動人口的生計方式與城市適應研究——以昆明市H村苗族的社會服務為例[D]. 云南: 云南大學, 2012: 42.
[6]張麗劍,王艷萍. 從民族的角度審視社會工作[J]. 中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5(6):50-52.
[7]任國英,焦開山. 論民族社會工作的基本意涵、價值理念和實務體系[J]. 民族研究,2012(4):8-16.
[8]李立. 社會工作介入城市少數民族流動人口的城市融合的探析——基于“增權”視角[J]. 今日中國論壇,2013(21):41-43.
[9]李林鳳.民族社會工作初探——基于民族文化的視角[D].蘭州大學,2013:Ⅰ.
[10]何乃柱. 社會工作介入城市散雜居社區民族工作的新探索——上海樣本的啟示[J].廣西民族研究,2013(4):38-44.
[11]徐世棟. 關于少數民族社會工作人才培養的幾點思考[J]. 社會工作與管理,2015,15(3):17—22.
[12]周沛. 社區社會工作[M]. 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206.
[13]何欣,王曉慧. 關于自助組織的研究發展及主要視角[J]. 社會學評論,2013(5):61-69.
[14]文軍. 西方社會工作理論[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281.
[15]RAPPAPORT J. Studies in empowerment: introduction to the issue[J]. Prevention in human services,1984(3):1-7.
[16]張麗劍. 少數民族的價值觀和風俗習慣在民族社會工作中的地位[J]. 社會工作,2007(8):37-38.
[17]王旭輝,柴玲,包智明. 中國民族社會工作發展路徑:“邊界跨越”與“文化敏感”[J]. 民族研究,2012(4):17-25.
[18]高向東,余運江,黃祖宏. 少數民族流動人口城市適應研究——基于民族因素與制度因素比較[J].中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2(32):44-49.
[19]王思斌. 民族社會工作:發展與文化的視角[J]. 民族研究,2012 (4):1-7.
[20]陳濤. 社區發展:歷史、理論和模式[J].社會學研究,1997(2):22-27.
[21]吳俊. 發展性社區社會工作實務模式探析[J]. 社會工作與管理,2006,16(1):12-18.
(文字編輯:王香麗 責任校對:徐朝科)
A Study of the Service Path of Social Work for Migrant Ethnic Minorities: A Case Study of Social Work Intervention for Buyi Minority by A Agency in Yunnan
YU Wanjiao1, QIAO Dongping2
(1. The Party School, CPC Xishuangbanna Committee, Jinghong,Yunnan, 666101,China; 2. School of Social Development and Public Policy,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China)
More and more ethnic minorities are moving from traditional rural areas into cities in China nowadays. Facing various problems and difficulties, they badly need social work services. Based on nearly ten years social work service experience for Buyi migrant ethnic minorities, A social work organization has set up an empowerment mechanism for Buyi migrant minority by establishing a Buyi women supportive group. Numbers of Buyi women supportive groups act as “social workers” at the production line to serve all group numbers. The interactive mechanism can stimulate Buyi women ability construction, cultivate Buyi national subjectivity, and let the outcome of social work service conform to the value of Buyi ethnic. For disadvantage of self-help organization, the A agency should assist the Buyi women supportive group to link more resource, include other people to join activities to avoid isolation and consider the social work ethics of the members of the support group.
the migrant ethnic minorities; women empowerment; self-help organization; community social work
C916
A
1671-623X(2017)01-0038-07
2016-04-21
玉萬叫(1990— ),女,傣族,助理講師,碩士;主要研究方向:社會工作,民族文化。
玉萬叫,喬東平. 少數民族流動人口社會工作服務路徑探析——以云南A機構布依族社工介入為例[J].社會工作與管理,2017,17(1):38-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