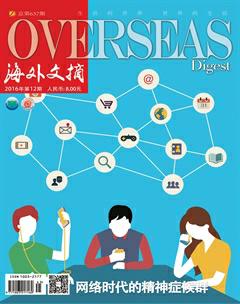當手機成為我們共同的敵人
烏韋·布斯++菲奧娜·俄勒斯
智能手機本應使我們的生活變得更加便捷、高效,但是很多人,尤其是孩子,容易對手機產生強烈的依賴心理。如何健康地使用手機,已經成為教育孩子過程中的一大難題。

在德國,幾乎所有家庭,不管是重組家庭,還是傳統家庭,不管他們是住在公寓中,還是板樓里,都經常這樣爭論。
一方是父母,另一方是孩子,他們中間橫亙著憤怒之源——手機:細長、優雅,偉大的救星,狡猾的引誘。原本是使日常生活變得便捷的工具,如今卻成為持續不斷的誘惑、高效的時間毀滅機器、大受歡迎的消遣方式,有時也是將主人變成奴仆的成癮性藥物。
孩子們應該從幾歲起擁有一部手機,什么時候可以使用,什么時候不能使用,有必要設定禁用手機的時間段嗎?在家里、課堂上和辦公室中,正確使用手機的策略以及它對我們日常生活的影響,都是熱烈討論的焦點。尤其是在孩子全天都待在家里的寒暑假,這些問題更是迫在眉睫。
手機占據了我們的日常生活和注意力,通過不斷發出鈴聲和震動,將一天分割成越來越小的碎片。而家庭正是和這種新的交流工具做斗爭的前沿陣地。家庭中可能有哪些手機問題和風險,父母們是否找到了解決方案,《明鏡周刊》想知道這些問題的答案,以及專家們的建議和警告。
42歲的阿勒克斯珊德拉·柏羅赫在漢莎航空工作,和丈夫以及兩個孩子一起生活。柏羅赫9歲的女兒和11歲的兒子各有一部蘋果手機和一個平板,兒子還有一個筆記本電腦。以下是她的自述:
自從幾周前我的女兒有了手機之后,家里就開始吵得雞犬不寧。她才9歲,還在上小學,但她堅持將自己的手機聯網。她的說法是:如果不聯網,她就沒法和住在城里的朋友萊尼聊天。我的丈夫說:絕對不能答應她。他討厭這些電子設備,他的手機在下班后的大部分時間都處于關機狀態。在車里,他用一部沒有鍵盤的諾基亞打電話。
我們因為一部愚蠢的手機爭論不休。最后我的女兒哭了,我心軟了。現在她每個月有500M流量,和閨蜜們建起一個聊天群,名為“我們是bff”,意思是“最好的朋友”。大多數時候,她們只是發幾個簡單的詞:“你好”、“你好嗎?”或是“我想你”。她們不斷承諾不會忘記彼此,每天都要說30次左右。
我和孩子們達成了協議:他們可以得到一部蘋果手機,而我可以閱讀他們所有的聊天信息。我兒子的班上成立了一個聊天群,班里有29個學生在里面,只有一個男孩沒有加入,因為他沒有手機。沒有WhatsApp的孩子會在很大程度上被孤立起來,足球協會成員、伙伴們都會在聊天中約見或組織活動。
但是作為父母,我們必須控制聊天內容。最近,我兒子的一個朋友給他發送了一張圖片,是個光著上身的女人。我偶然看到了它,并在兒子看到之前將它刪除了。我覺得這張照片很露骨。我的兒子才11歲,喜歡玩打擊樂和滑板,對女孩還不感興趣。
我不知道,我還能控制他的信息多久。他15歲時,肯定不會再愿意讓母親看自己的信息。而正是那時候,控制可能才是最重要的。
對現在的孩子而言,YouTube視頻網站和電視起著相同的作用。我的兒子會連續看幾個小時視頻,《我的世界》是他目前最喜歡的網絡游戲。在游戲中,他用形似樂高積木的磚塊建立起自己的世界,走來走去,殲滅敵人。我覺得這沒什么不好,但不定何時,他也會想玩包含暴力和死亡因素的游戲。我討厭暴力。
有時候他的朋友會過來找他,兩人一起坐在客廳角落的沙發上,分別看著自己的手機。我會說:“你們別在這兒待著。”對我來說,他們去做什么根本不重要,但是手機得留在這兒。
我小時候不聽話時,父母會禁止我看電視來懲罰我,而今天這根本不起作用了。有一次,我的兒子本應做數學作業,需要10分鐘做完。但他仍然繼續玩平板電腦,半小時后才坐到了桌子邊。我當時就發飆了,沒收了他的平板,將智能手機、平板和筆記本等所有電子產品都鎖進了我汽車的后備箱里。
我知道自己并不總是個好榜樣。這些電子設備如同海洛因,能讓人很快上癮。我們規定:吃飯時和上床后都不能玩手機和平板。但有時候我自己也會破例,在吃早飯時查看平板上的信息。我的丈夫就會說:“把平板丟開。”我會對他說:“你也會在餐桌邊讀每日新聞,不也差不多嗎?”
在很多家庭,每天都上演著這樣的較量:艱難,毫無目標,也無法想象該達成怎樣的一致。人們已經無法想象沒有手機和平板的世界,和這些儀器共存的生活才是理所當然。解決問題的第一步可能是看看那些理智的數據和不依托于感覺世界的研究發現。
2006年以來,德國的手機數量已經超過了人口數量。去年,8000萬德國居民簽訂了1.1億份移動通信合同。阿勒克斯珊德·馬克維茨領導的關于手機的調查可能是史上最全面的。他曾任波恩大學初級講師,如今為公司和自由職業者提供手機使用咨詢服務。馬克維茨和同事一起開發了一款名為“menthal”的應用軟件,在獲得手機用戶許可后,記錄他們的行為。目前有6萬人參與其中。對他們的分析顯示:一個手機用戶平均每天會打開他們的手機屏幕88次,35次只是看時間,或是檢查有無新信息,53次是為了寫封郵件、使用軟件或瀏覽網頁。奇怪的是,menthal軟件的用戶每天在手機上花費兩個半小時的時間,但只有7分鐘的通話時間,大部分時間都花在臉書、WhatsApp和游戲上。
這個數字明顯高于手機用戶自己估計的數值。在手機的使用上,學者并不會比貧困的失業救濟領取者更加克制,青少年也不會比成年人沉迷得太多——分別為每天3小時和2.5小時。
在現在的社會中,人們不知休息為何物,所做之事不斷被電子產品帶來的干擾打斷,以至于很難集中注意力地工作和實現真正的放松。它不僅影響了成年人,也波及到孩子和青少年。曼海姆大學的一項代表性研究得出結論:約有一半學生覺得在做家庭作業時被手機干擾或分心;8%的青少年依賴手機的程度,可以說已經是上癮了。
不得不時刻保持在線使得我們的生活節奏越來越快。英國心理學家理查德·威絲曼發現,在10年內,世界大都市行人的步行速度已經增快了10%,尤其突出的是新加坡和中國廣州。這兩個城市在90年代初還位于后列,10年后的第2次觀察中就已經分別位列第1和第4。在新加坡,行人走60步,約18米,需要10.55秒;廣州的行人則需要10.94秒。柏林位列第7,為11.16秒;紐約第8,為12秒。在阿曼、約旦以及巴林的麥納麥,行人的步行速度則緩慢得多。在這些地方,行人走完18米,要用16秒,甚至17秒。
2006年,威絲曼就得出了一個推論:一個社會的技術化、數字化和個性化程度越高,日常生活節奏就越快。但是不僅日常生活節奏加快了,人們的耐心也變少了。1999年,當一個網頁的加載時間長于8秒鐘時,會失去三分之一的訪客,而到了2006年,僅僅4秒之后,訪客的耐心就已經耗盡,如今甚至只需短短2秒。
無所事事、徹底放松的狀態曾是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但如今顯然已經成為奢求。美國科學家開展的一系列研究表明,坐在那里什么都不做,讓很多人感到難受。研究人員請受試者獨自坐在一把椅子上6分鐘和15分鐘,然后描述他們的感覺,超過一半的人表示討厭這樣的經歷。在后來的一次實驗中,受試者可以選擇用遭受電擊的方式打破這種痛苦的無所事事狀態,結果四分之一的女人和三分之二的男人都做出了電擊自己的決定。
這就是我們時代最大的矛盾:先進的數字化本應帶給我們更多的休息時間和更高的效率,結果卻使我們變得更匆忙,更容易精疲力盡。這怎么可能?那些本應減慢生活節奏的儀器,為何技術卻讓很多人感到巨大的壓力?我們怎樣才能在日常生活中保持平靜?必須和波羅赫一家一樣每天斗爭嗎?還有其他可能性嗎?
42歲的法國人卡羅爾·克羅姆有3個兒子分別是7歲、12歲和14歲,還有一個10歲的女兒。只有長子有自己的手機,家里唯一的電視機擺在父母的臥室。10多年來,克羅姆一家一直生活在國外,近一年來開始生活在漢堡。 以下是卡羅爾的自述:
我的哥哥在新加坡一家電腦游戲公司工作,很熟悉IT業。最近他告訴我,在硅谷經理的孩子們上的小學,對手機和電腦的使用有極其嚴格的規定。他們的父母在蘋果、谷歌、臉書、微軟、雅虎等公司越成功,就越反對電子產品對孩子的愚化作用。我覺得這個事實很值得回味。
我的丈夫是個工程師,10多年來,在全世界的很多城市生活過。在上海,我們了解到中國人對電子產品的狂熱。他們從早到晚都在玩電子產品,甚至老年人也不例外。現在,他們已經在網上做一切事情了:聊天、學習、支付、打車、叫外賣,甚至還在手機上做愛,或者至少通過手機約定約會日期。
目前,在伊斯坦布爾也已經人手一部手機了。我還記得我們到那里的第一天,一個技師為我的丈夫組裝電腦。他剛剛為一個土耳其家庭裝了一個超快的路由器。他搖著頭敘述著,3個孩子怎樣無視他們母親的批評,在手機上用想象中的武器噼噼啪啪射擊。他們全都矮胖、慵懶,說不出一個完整的句子。我的上帝啊,多么可怕!
在我心中,德國也不是個好榜樣。我覺得德國父母太漫不經心,不是很擅長定規矩。由于法國的傳統習慣和我自己的童年經歷,在手機的問題上,我成為了嚴格的掌權者。我的長子維克多在漢堡上德法學校,他的一些同學可以玩手機直到深夜。在學校,他們全都睡眼惺忪,注意力渙散,而老師和家長似乎對此根本無能為力。
我學會了3樣東西。第一:父母必須盡早干預,沒有什么比把一個小孩放在電視和平板前,只為讓他保持安靜更糟糕的事情了。第二:父母必須制定嚴格的規則,不要破例留情,這會是致命的。第三:父母必須成為孩子的好榜樣。比如我覺得臉書很重要,因為這樣我可以和在法國的家人保持聯系,但我不會在孩子們面前聊天,周末不會檢查郵件,吃飯時也絕對不會拿出手機,甚至放在餐桌上。
我們請了一個家庭顧問,以舉手表決的方式確定下克羅姆家的規則。每個孩子都必須年滿14歲,才能擁有一部手機。維克多每天可以使用電腦一小時,周五晚上可以更久一點。如果他因此抱怨,我就會沒收他的手機。我們家很少開電視,可能是因為電視放在我們的臥室。有時候我們會一起看《泰坦尼克號》之類的影片。我們的孩子很清楚家里的規則,不會對此發牢騷。我知道這些規定聽起來很嚴厲,但我是為了孩子們好才這樣做的,而且我相信,有一天他們會感激我今天的嚴厲。
應對手機帶來的挑戰,一種不錯的方式就是確立嚴格的規則,而不是事后審判。社會學家、心理學家雪莉·特克勒對克羅姆一家的做法表示贊同,多年來她一直在警告我們手機和數字化將對社會生活產生影響。
特克勒發現,在表面波瀾不驚的生活下,藏著一股巨大的暗涌,它將人們之間的距離拉遠了,哪怕表面上恰恰相反。對于青少年們一邊編寫短信息,一邊和談話對象保持眼神交流的新技能,特克勒持批判態度,因為這是在偽裝專注和關心。她擔心年輕一代會喪失同情心,因為孩子們見面更少,發短信更頻繁,不知道如何理解他人,詮釋他人的反應和表情,并作出恰當反應。特克勒表示,面對面的對話是人類最富有人性的溝通途徑。在談話中,我們展現自己,認識其他人,學會如何被理解,學習接受和拒絕。而總是盯著大大小小的屏幕,對獲得這樣的經驗毫無益處。
在線聊天提供了一種不成熟的一維聯系方式。特克勒表示:短信息服務如此流行,也是因為它為溝通構建了一種新的可能,讓人與人之間可以不用真正親近的交流——不管是地理上的還是情感上的。人們之間的距離總是足夠遠,可以避免受傷;也足夠近,可以有保持聯系的感覺。這種形式的交流多有誘惑力,可以從一組來自美國的數據上看出來:在街道交通中遇難的手機使用者數量,已經超過了酒駕致死的人數。
明確的規定能引向明確的結果,克羅姆一家就是好例子。而模棱兩可的規定和自由狀態容易引發沖突,42歲的單親母親、護士安·里克和她12歲兒子保羅的例子證明了這一點。
里克家的規定是這樣的:上床睡覺前,有客人來訪時,以及吃飯時,保羅必須交出手機。但是這一規定具體何時才會生效?比如什么時候算開始吃飯?是已經坐在餐桌旁,還是在去往餐桌的路上?不久前這個問題引發了矛盾——保羅想在去往廚房的過程中快速寫條信息。“那之后,家里的氣氛就變得不那么美好了。”保羅說。
“真正讓我煩心的是,”安·里克說,“手機是唯一真正對他意義重大的東西。”保羅還在上7年級,母親坐在位于基爾的一套兩居室的廚房里,洗衣機運轉著,冰箱上方掛著公交車時刻表,墻上貼著小孩的照片,那是來自YouTube和WhatsApp出現在他們的生活中之前的時代的圖像。
“如果我現在用不許出門來懲罰保羅,根本毫無意義,因為他可喜歡抱著手機宅在家里了,如果我說:‘你今天不準吃晚飯。他會說:‘好,那我去自己房間了。”室外陽光燦爛,她的兒子卻浪費了大好時光,寧愿一個人窩在家里看電影,這讓她感到悲傷。保羅的手機一直連著網,沒有一分鐘例外:就連在刷牙時,他都在看YouTube上的視頻;在公交車站,他也常常和同學并肩站立,各自沉浸在手機的世界里。
門鈴響起,保羅和他的朋友卡爾洛斯放學回到了家,背著背包,手上拿著手機,很快關上自己的房門,打開了電腦。
保羅,你一天要寫多少條WhatsApp信息?“200條。”他說,“聽起來很多,實際上并不多。女孩們寫得還要多得多。”這個黑發男孩脖子上掛著一副巨大的耳機。
你們都聊些什么?“家庭作業啊,或是約好見面時間。”
此外你們還在手機上干嘛?“看YouTube,刷Snapchat(圖片分享軟件)。我把臉書卸載了,我不需要它。”
還有什么?
“游戲。”
得到第一部手機時,保羅才11歲。他遠遠不是班里第一個擁有手機的人,對此安·里克根本沒有想太多。已經很少有不聯網的手機了,最初她和很多其他母親一樣,覺得能時刻聯系到自己的兒子很好。但是有了手機后不久,保羅就把自己的玩具全部扔在一邊了,就連他一度非常喜歡的樂高機械系列玩具也不例外。“在最短的時間內,我們的兒童房變成了多媒體房。”里克說。里克不了解游戲世界。她的兒子不久就有了個網名,和同學以及陌生人在手機和電腦在線游戲中會面。他每天都收發無數條WhatsApp信息。對于他這個年齡段的男孩來說,這并無特別之處,但是如果他因此發生了改變呢?“我擔心他會變得毫無思想,遲鈍麻木。”里克說,“無法擁有其他能力,再也學不會需要動手做的事情了。”
保羅,你覺得被你母親沒收手機有多糟糕?“我不愿意交出手機,但我能理解她的做法。我看手機的次數其實并不多,有些人放學后會在手機上看5個小時的YouTube視頻,我最多只看一個半小時。”
和幾百萬孩子一樣,他最喜歡在YouTube上看游戲玩家打游戲。這是為什么?“不知道,就是這樣。”
保羅說,他有些同學有手機癮,比如瘋狂迷戀《我的世界》游戲、Snapchat或WhatsApp。但他并沒有上癮。在這一點上,他和母親的看法不一致。里克說:“我感覺,他已經很難忍受沒有網絡的狀態了。”
有一次,安·里克在爭吵中帶著無線路由器去上班了。還有一次,她在一次家庭聚會上沒收了保羅的手機,因為她希望孩子們可以一起做些有趣的事情,而不是泡在網上。但她的舉動引發了激烈的爭吵,因為其他孩子都能夠保留自己的手機。“最后我們之間的關系變得非常糟糕。”里克說。
“現在是夏天,我想多出門,玩長板之類的。”保羅說。他表示這天他也想和卡爾洛斯一起去室外活動。“馬上。再玩一會兒手機,我們就出門。”他們說。然而兩個小時后,他們還坐在房間里。
電子產品的誘惑可能很快就會占據優勢,但這并不意味著青少年們感覺不到自己失去了控制權,或是被推送信息和不耐煩的朋友們所煩擾。一個16歲的漢堡姑娘這樣描述這種感覺:“真正讓我煩心的,是必須馬上回復信息的壓力。其他人可以看到你在線,如果你沒有立即回復,幾分鐘后就會有人問你:‘你生我的氣了嗎?怎么不回復我?”
研究智能手機用戶在應用軟件上行為方式的德國信息專家亞歷山大·馬克維茨稱之為“數字時代的集體崩潰”。馬克維茨相信,持續被外界信息打斷思路有損我們的大腦,影響我們的思考能力和專注力。很多手機應用軟件利用神經活動的規律,促進幸福激素多巴胺的釋放,讓我們一再拿起手機。馬克維茨說,大多數人已經適應了這種有損健康的生活方式,強烈依賴手機,甚至出現了行為障礙。
而來自烏爾姆的腦研究學者、成功的作家曼弗雷德·施皮策爾對此發表了最尖銳的觀點。他認為電腦和手機讓人愚蠢,現代人正走在“數字化癡呆癥”的道路上。
交流心理學教授馬爾庫斯·阿佩爾的研究卻得出了相反結論:電子產品減少社會交際?沒有確切證據;減少社會參與度?支持相反結論的論據更多;網絡導致孤獨?研究證明兩者無關,網絡對健康的影響微乎其微,與抑郁癥也無直接關聯;削弱書面表達能力?就文章數量和質量而言,在電腦上寫作充滿優勢。
阿佩爾甚至將施皮策爾和馬克維茨出的書歸為一個專門的門類——“科學消遣文學”,認為其并不符合科學論文的要求和規則,并表示這些作品沒有仔細權衡考慮,而是歇斯底里,在最糟糕的情況下甚至充滿謬誤。
而馬克維茨對這樣的批評予以了反擊,他說:“小木屋著火了。”如今的情況是如此迫在眉睫,人類根本無法在知道所有問題的確切答案前等待數年。
專家們一致認同的是:我們不能屈服。在手機的問題上不予管教并不是解決之道,然而德國有15%的父母正是采取放任自流的態度的。
圣保利一棟高樓的9層,建筑面積57平米,三居室,4部蘋果手機,兩個蘋果平板,一個筆記本,兩個成年人,兩個孩子。
父親賽爾坎,34歲,手機銷售員;母親德爾雅,32歲,全職主婦;大女兒德林,9歲,上三年級;小女兒塞林,2歲,上幼兒園。
客廳里的筆記本上正在放一家土耳其私人頻道的直播,電視上放著一部肥皂劇。2歲的塞林手上拿著一個粉紅色的蘋果平板,Pepee是她能夠準確發出的少數幾個詞語之一,她一直大喊著“Pepee”,直到德爾雅彎下身子,在YouTube中輸入“Pepee”。
《Pepee》是為3-6歲孩子制作的一部土耳其動畫片,塞林隨意在視頻上點擊著,點中了“5集連放”,一共51:02分鐘。她還不識字,但成功地點中了“播放”。
賽爾坎坐在廚房,他面前的蘋果平板上顯示出一家網店的頁面。“這是我最喜歡的服裝店。”他說,“我幾乎從不在午夜之前回家,我在網上買所有東西:鞋子、褲子、內衣。它們總是很合身。我不知道自己已經多久沒有進過實體服裝店試衣服了。”
9歲的德林躺在她父母的床上。她的手機昨天壞了,如果所有人都在家,她很難有機會拿到平板,她很煩躁,她不喜歡所有人都在家。今天她借了奶奶的手機,“也是蘋果,但是型號太老了,速度很慢。”德林說。她打開了YouTube,準備看她目前最喜歡的視頻《dm Haul》——幾個YouTube女用戶展示自己在連鎖藥店dm購置化妝品的過程。
德林說:“我也想擁有那些電子設備,但是媽媽說太貴了。”整個下午,她都在YouTube上看視頻,一個接著一個,每個的時長都在10-15分鐘之間。
“我會從下午4點放學,一直看到上床睡覺。”她說。德林不理解學校為何要禁止學生使用手機。她說:“我覺得課堂很無聊。老師們教得太慢了。如果我帶手機去上課,就會被他們沒收。媽媽就得來學校找老師取回我的手機。”
母親德爾雅說,德林在YouTube上也能學到很多。例如上一年級時,她的英語成績是班上最好的。3歲時,德林就會說英語句子了,而她的父母都不會。
德林說:“假期時,我的英語越來越好。我會在YouTube上看更多視頻,重復練習我聽到的所有句子。這有點讓老師討厭,因為跟YouTube上那些人相比,他們的英語說不了那么好。而且老師們說英語的語速太慢了。反正很無聊。”
我問德林她已經有手機多久了,她聳了聳肩說:“我想,一直就有。放學回家后,我會吃點東西,同時手上總是拿著平板,那之后我會玩《色彩轉換》游戲或是上WhatsApp,但我不喜歡寫信息,太慢了,我總是要找字母的位置,我更喜歡語音,我的朋友們也是。但是我最喜歡的還是YouTube。”
賽爾坎說:“對我們而言,沒有什么可笑的手機使用規則,比如無手機時間、禁網懲罰、吃飯時不準玩手機之類的。我們家所有人都在玩手機或平板,這也沒什么不好。”
賽爾坎說,有些父母讓他覺得很煩。他們會問他,他允許孩子們上網的頻率和時長為多少,為何德林已經擁有手機了。他們想就班上同學統一使用手機的時間達成一致。“他們瘋了。”賽爾坎說。
“在我們家,一切都是被允許的。”賽爾坎說,“無法接受這一點的人,就別讓孩子來我們家。”
德林家常常有朋友來訪,他們會一起在YouTube上看《dm Haul》。德林說,他們本應晚上8點睡覺,但是有時他們還會在被子里看視頻到凌晨1點。
賽爾坎說:“時代變了,人們卻沒注意到。是的,我們以前可能9點就睡覺了,但那時候電視里在插播廣告,人們在廣告時去睡覺。今天還是這樣嗎?不會了。所以說時代變了,人們不需要看插播廣告了。手機就是我的面包。我也可以不賣手機,而像上一代的土耳其人那樣賣蔬菜,但是我決定擁抱未來。”
對于如何對待電子產品,86歲的瓦爾特·米歇爾給出了一個答案。米歇爾童年隨父母從奧地利逃往美國。他是著名心理學家,尤其因“棉花糖測試”實驗而聞名世界。這項40多年前首次開展的實驗,后來被重復做了多次,有無數不同版本。實驗大體過程總是:一個學齡前兒童坐在棉花糖等甜品前,一個成人告訴他:“你可以馬上吃掉棉花糖,也可以等我再次來到房間時再吃,這樣我會再給你一個。”結果是:約三分之一的孩子馬上吃掉了棉花糖,三分之一先是克制自己,但最終沒忍住,還有三分之一則做到了耐心等待。
在接下來一些年,米歇爾一直在觀察這些孩子中的一部分。他確信,那些能夠克制自己的人,總體而言在學校成績更好,身材更加苗條,過著更好的生活。
控制沖動是人生成功的基本條件,能讓胖者變瘦,在多年后仍然維持婚姻的完整,教育、事業都更加成功。沖動控制是完整人格的重要組成部分,必須如同走路、說話一樣習得。而教會孩子自我控制、遵守紀律、堅持等品質,是父母的首要任務。
所以,我們應該怎么做?我們應該減少使用電子設備的頻率,增加與其他人相處和交流的時間。知道如何掌控自我的人,才能贏回遺失的自由和獨立。具體來說呢?很簡單,先把你的電子產品放到一邊吧。
[譯自德國《明鏡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