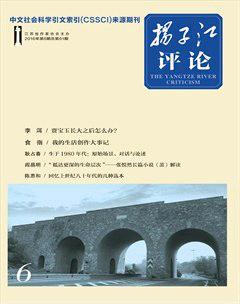直覺、塔布與文學寫作
黃德海
如果我們把夢看成一個作品
不知是不是因為直覺和本能愈晚近愈被推重,夢越來越成為文學幾近公開的隱秘來源,甚至有人奢望,夢可以直接就是一個作品——“如果能有一種夢,夢中的我寫好一首詩、一篇文字或者一篇小說,那么有多好,我只要醒來時一字一字抄下來就行了”a。聲稱能夠把夢平移到紙上的寫作者,也幾乎立即會被認定為某種特別的天才。不必知道莎士比亞說過,“我們是用與我們的夢相同的材料做成的”b,寫作者在某些時刻可能都會暗暗期盼,不用經過艱難的思考、時常的中斷和反復的修改,作品便已自動完成——使用的仍然是我們自身的材料,跟來于現實的沒什么不同不是?
不管夢是對日常精神壓抑的釋放,還是對清醒時思想冗余的消化,我們大體上都容易相信,“夢是人對自己的松手,一種徹底的松手,大概正因為這樣,我們往往相信,夢暴現出某個,或某些‘更真實的我,賦予它一個深向的意義,一個諸如認識我自己的睿智意義”c。隨著弗洛伊德的流行,如下的判斷幾乎被確認為常識:生活在現實世界的“我”被可惡的理性強行管制,只好在夢里流露出自己更本質更率真的一面,從而接近了某種更原始、更具活力、更不受拘束甚至更有時間來歷的東西。現時代文學中經常出現的變形的怪獸,殘缺的人體,黑暗的人心,無序的生長,失控的欲望,放縱的狂歡……差不多都跟夢的釋放有關,“這也許才是夢最富意義的地方,我指的是,一種幾近不可能的自由,一種取消白天世界種種界線的自由”d。
不管取消了多少界線,問題仍然沒有解決,莎士比亞說的相同材料,到底包括哪些呢?是不是夢和現實都來于心靈的圖景,如柏拉圖筆下的蘇格拉底所說?人的心靈塑像,是多頭怪獸、獅子和人三種形體長在一起,人們外在能看到的,只是這一聯合體“人形的外殼,看不到里面的任何東西,似乎這純粹是一個人的像”e。諸多寫作者缺乏洞察,是因只看到人形的人心,看不到塑像里面的幽微,等于抽去了其中本有的怪獸和獅子,人難免平面刻板,缺了特殊的精氣神兒。說到這里,有人或許要迫不及待地斷言,只有把多頭怪獸和獅子釋放到紙上,藝術和文學才可能擁有旺盛的生命力——那些能把在夢中釋放出獅子和怪獸、并落于紙上的人們,將被指認為時代英雄。
原始的、野性的、未經調理的人性姿態,有益于讓文學作品保持活力,把過于柔膩的優美變換為某種莊重的崇高,滌除現代人身上趨于病態的孱弱。不過,這種未經約束的人性原始狀態,仍然有其風險,一不小心,原始的獸性將露出可怕的獠牙。一味放縱和加強多頭怪獸和獅子的力量,會“讓人忍饑受渴,直到人變得十分虛弱,以致那兩個可以對人為所欲為而無須顧忌”,或者“任其相互吞并殘殺而同歸于盡”f。是心靈塑像中的人與兩個精怪,一起構成了生命的活力,而照現代過度思路經營的作品,釋放出來的,往往是多頭怪獸和獅子,那個看不太清晰的人形,只是現實里的行尸走肉,夢境里的淺淡陰影。我們從不少現代作品中感受到的氣息奄奄,或者陽亢的反抗掙扎,差不多都可以看成對兩個精怪的屈從或放縱。
未經馴服的多頭怪獸和獅子,最終在人身上表現出來的,是橫沖直撞的魯莽,不管不顧的欲望。只是因為現時代對原始活力的過度贊許,才將這不加節制的欲望認定為人的內在本質。在蘇格拉底看來,一個人身上會有兩個趨向不同的自我,“一個是天生的對諸快樂的欲望,另一個是習得的、趨向最好的東西的意見。這兩種型相在我們身上有時一心一意,有時又反目內訌;有時這個掌權,有時那個掌權。當趨向最好的東西的意見憑靠理性引領和掌權時,這種權力的名稱就叫節制。可是,若欲望毫無理性地拖曳我們追求種種快樂,并在我們身上施行統治,這種統治就被叫做肆心”g。肆心會讓人忘記屬人的艱辛和榮耀,不是誘導人變得沉溺,就是刺激人變得殘暴。
在蘇格拉底看來,正確對待精神中三種力量的方式,是“讓我們內部的人性能夠完全主宰整個的人,管好那個多頭的怪獸,像一個農夫栽培澆灌馴化的禾苗而鏟除野草一樣。他還要把獅性變成自己的盟友,一視同仁地照顧好大家的利益,使各個成分之間和睦相處,從而促進它們生長”h。“所謂美好的和可敬的事物乃是那些能使我們天性中獸性部分受制于人性部分(或可更確切地說受制于神性部分的事物),而丑惡和卑下的事物乃是那些使我們天性中的溫馴部分受役于野性部分的事物”i。
或許有個問題需要提示,所謂“內部的人性”,顯然區分于心靈塑像中的那個人形,是“人性中之人”,英文翻為“the man in man”,或“the human being within this human being”j。那個人性中的人,是一個不斷認識自己、不斷反省中的人,從而贏得了對心靈塑像的培養權,自反而縮,幾乎接通神性(感受到神性的限制,不正是對神性的接通?)。只有經由自省和教化而生的人性中之人,才有可能讓心靈中的三種力量摶而歸一,裁斷狂簡,歸于彬彬,百煉鋼化為繞指柔——如《莊子·人間世》說的那樣,“雕琢復樸,塊然獨以其形立”。
這奇妙的隱喻另有個以顯現的方式深藏的部分,即不管人、多頭怪獸和獅子多么醒目多么耀眼,最終必然投射在人形的心靈塑像上。通過夢,人們釋放了被文明抑制的活力,變化成各種動人或嚇人的花樣,如振奮時的攘臂或憂郁時的嘯歌。那些活躍在人形塑像上的一切,跟夢一樣,不會有“多出來的東西”,“最多,只是某些我們以為已遺忘的東西,乃至于某個更原初、更幼稚、更未經改善處理、更接近生物性的我”k。再怪誕的夢,也沒有為那個本來完備的自己添減些什么,夢的意義,原不在內容的增加,“而是一個對白天森嚴界線的糾正和解放,通過相同材料的組合,以一種示范的模樣、一種啟示的模樣,告訴我們,我們自己,以及整個世界,可以不必然只此一途”l。
只是,夢經常組合狀況不佳,不保證完整也不承諾完美,它更像是小孩子玩的“what if”游戲——What if 老鼠會說話,What if 狗狗能駕駛飛機,What if 小鴨可以自由飛翔……“我們有絕對的理由相信,夢更多時候因此只能是‘失敗的作品(那些只相信直覺、由筆拖著走的作品亦然),證之我們每個人的實際做夢經驗應該也如此沒錯;還有,橫向的隨機組合,不會有真正觸及稍深一層東西的機會,有時仿佛有但其實不會有,那只是混亂的偽裝……所以,夢不僅總是失敗的作品,還是個初級的作品”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