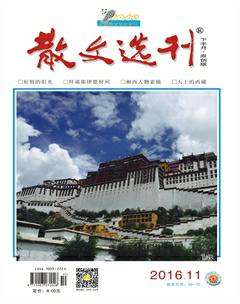湘西人物素描
范誠
凌宇先生
去年國慶期間,在母校舉行的我們畢業30周年同學聚會上,我又見到了凌宇先生。
凌宇先生是母校湖南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全國著名的沈從文研究專家。我們在湖南師范大學讀書時,教我們現代文學課程。
說起來老師與我們有緣。1981年,經過苦讀寒窗,我們考進了湖南師范大學中文系,而凌宇老師也剛好從北京大學研究生畢業,正好分配給我們帶課。
老師中等個子,結實身板,一張國字臉,長得很端正,留著大背頭,頭發有點自然卷曲,額頭顯得很寬闊。說話聲如洪鐘,底氣很足,顯得鏗鏘有力。尤其是他那爽朗的笑聲,常常回蕩在我們的教室、走廊。后來我到了湘西才知道,那是湘西人特有的一種笑聲。
經過一段時間接觸,才知道,凌老師是湘西龍山縣里耶人,畢業于華東師范大學,分配到湖南第一師范學校任教。高考恢復以后,他考上北京大學著名教授王瑤先生的研究生,從事現代文學研究。因為喜歡沈從文先生的作品,加之是湘西同鄉,于是頂住各方面壓力,致力于沈從文創作的研究,發表了多篇學術論文,在全國很有影響。
當時全國通過撥亂反正,思想界、文藝界政策有所松動,沈從文像“出土文物”一樣,被從故紙堆中翻出來,立即受到文學愛好者的追捧。
凌老師給我們講課很認真,備了一本厚厚的講義,基本上按照講義講授,還經常給我們講那些現代文學史上的人文掌故或奇聞軼事,我們像聽“天書”一樣,很喜歡聽。
老師講課也非常直率,對一些問題毫不隱諱。講到他選擇研究沈從文時,導師王瑤先生開始不太贊同。因為當時思想尚很封閉,沈從文被郭沫若定性為資產階級作家,早已被邊沿化。遠沒有“魯(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等容易出成果。當時因為研究沈從文,還受到個別作家的無端指責,說王瑤怎么帶那樣的學生,可見壓力是很大的。但凌宇老師屬于典型的湘西人性格,不信邪,認準的事,幾頭牛也拉不回來。見他很執著,王瑤先生轉而積極支持。
凌老師給我們講授最精彩的課是講沈從文和他的文學創作。當時我們中文系一個年級有200名學生,老師分工帶我們三、四班,結果一、二班的同學也跑來了,還有一些文學愛好者,本來還算寬大的教室里座無虛席,大家專心致志聽凌老師的授課。凌老師也亮起高大的嗓門,盡情地講授著。因為太過于使勁,不時取出手帕擦額頭上的汗珠。他的課成了我在大學四年中最喜歡聽的課之一,我畢業后選擇去了湘西,很大程度上是受他的一些影響。
1985年,我大學畢業,面臨多種選擇,最后去了湘西,到了一家地方報社。在此之前,我還從沒到過湘西,對湘西一點也不了解,但想到是沈從文先生的故鄉,是凌老師的家鄉,心想一定是不錯的。
第一次出差里耶,我在街頭徜徉著,那古老的石板街,飛檐的吊腳樓,給人的感覺特別的好。我找到里耶的朋友,打聽凌老師的舊居,想上門去看看。朋友經多方打聽后告訴我,其實,凌老師還不是里耶鎮上的,是附近一個鄉鎮的。因當時交通不便,后來沒有去了。
大約是到湘西兩年以后,我那時剛談女朋友,即現在的妻子。有一天,我們騎著自行車從文藝路經過,突然看見凌老師在一幫人簇擁下從旁邊走過去,我趕緊停下車來,同老師打招呼。老師先是一驚,聽我自報家門,才認出我來,拉著我的手,簡單問了幾句。見我身邊的女友,問這是你妹妹吧,弄得我一臉通紅。旁邊的都是熟人,就放肆調侃。老師說,你們真像兄妹啊,有夫妻相。老師的嗓音仍是那么洪亮,而我卻越覺得害羞。因老師他們還有事,我們就此別過。
以后多年沒見到老師,但經常在各種報刊、文學雜志上看到老師的文章,并收藏起來,時刻關注著老師的研究動態。老師這段時間,一邊教書育人,一邊潛心研究,成果迭出,不僅發表了許多有影響的論文,還出版專著《從邊城走向世界》《沈從文傳》等,成為國內外著名的學者。我們同學見面時常常談到老師,為有這樣的老師而感到驕傲。
后來,我調到湖南廣播電視臺駐湘西記者站,經常出差或開會到長沙,很想找機會去看看老師,可是想到老師的名氣越來越大,還認不認得我這個無名的小輩呢?心里猶豫著,就沒有去。其實,我們許多同學都一樣,對老師都存敬畏之心,敬的是敬佩老師的成就和為人,畏是自己沒有什么成就,默默無聞,怕被老師瞧不起。事實上,這種想法是多余的,師生之間,是一種緣分,更是一種情分,哪有那么復雜?
大約十年前,在湘西吉首,我又見到老師。這次老師是回故鄉龍山路過吉首,在州政府秘書長和一些人的陪同下,在邊城賓館共進晚餐。有人知道我是凌老師的學生,便給我打電話。我匆匆趕去,打過招呼,就留下來一起陪老師就餐。
歲月讓老師原有的一頭濃發脫落了許多,變得花白,人消瘦了些,顯得個子也小了,但仍然精氣神十足。老師說,他很快就要退休了,退休后回湘西的時間更多了。我說老師要保重身體,以后回湘西由我來作陪,讓老師看看最神秘的湘西,老師客氣地答應著。
一去又是十年。
今年是我們畢業30周年,同學們都很期待,希望搞一次大規模的聚會。留在學校的幾位同學很熱心,操心費力,把我們組織起來。在聚會上,凌老師被推為教師代表,給我們講話。
老師仍是那么風度翩翩,嗓音仍是那么洪亮。老師70歲了,面對的學生也年過半百了。回首往事,不勝感嘆。老師為我們講“人生三不朽”,即“立德,立功,立言”, 該典出自《左傳·襄公二十四年》。老師引用一位先賢的話說,立功,要靠平臺靠機遇。現在所謂的立功,就是指當官,當官是要靠運氣的,每一個當官的人,并不是最優秀的人才,而優秀的人才,往往是當不上官的,所以也不要勉為其難。立言,要靠天賦要有才情,并不是每一個讀書人都能立言的,所以也不要去過分追求。只有立德,主要靠自己修為,這是人人都能做得到的,我希望我們在座的同學,都能在立德上下功夫,保證自己不為塵世污染,堅守道德底線,做一個道德品質高尚的人,這就是我對你們的期望!老師語重心長的一席話,贏得了我們熱烈的掌聲。
有人曾經總結過,人的一生,有“四遇”,就是要遇到四種人。出生后遇到好的父母;讀書時遇到好的老師;婚戀時遇到好的愛人;工作時遇到好的領導。如此,這個人一生就很幸運了,也定能有一番作為。我覺得,這人生的“四遇”,最重要的是要遇到好的老師,因為我們走出家庭,走進學校,正是我們學習知識、樹立人生觀的時候,遇到良師,猶如遇到一盞指路明燈,在老師的指引下,人生就步入坦途。可以說,我們就是在無數良師的教育引導下成長起來的。
古人說過,人生“五十而知天命”。其實,在老師面前,我們雖然到了知天命之年,但永遠是學生。老師的諄諄教誨,是值得我們永遠記取的。
看大門的老吳
老吳原是機關大院看守大門的工友,姓吳,人們都習慣叫他老吳。我至今不知道他的大名,只聽別人都那么叫他,便也跟著叫喊,他也樂于答應。久而久之,我相信沒有幾個人能叫出他的真名來。
老吳中等偏矮個子,有點駝背,右手有點殘疾,實在是其貌不揚。據說老吳原來是湘西某個煤礦的一名工人,后來因為工傷傷了右手,便不能再在井下干活,組織照顧他在廠里當了門衛。因為認真負責,成了礦里守門把關的“一把手”,遠近聞名。當時州委和州政府合署辦公,大院里正要找一個工作負責的門衛,有人推薦他,經考察還真行,便把他調到政府,負責看守大門。
以前不像現在,可以請保安,站在門口,穿著制服,雄赳赳氣昂昂的。以前偌大一個院子,就老吳一個門衛,白天值班,晚上有時也要起床開門。老吳從礦井調進城市,很感謝組織的關心,因而工作更加盡心,在政府看守大門多年,大院里居然沒有被盜過,除了以前社會秩序好之外,與老吳的嚴關把守也有很大關系。
因為工作細致,老吳甚至鬧過一個很大的笑話。
當時的州長叫吳運昌,是一個土生土長的苗族干部,個子不高,衣著十分簡樸,根本不像個領導干部,倒像個農民。那時的領導也不像現在車來車往,下班后都步行。老吳看守他的大門,本來就不認識州長,或者說州長太樸實,根本就沒有引起他的注意。有一次,州長一個人步行從大門口進來,被老吳攔住,問你找誰,有證件沒?州長一時沒回過神來,不知所措。在口袋里摸索了好一會,才說,我是吳運昌,州人民政府的。老吳還是不信,因為憑他的直覺,怎么看都不像。就說,你找人就找人,還敢冒充我們州長?州長一時語塞。這時,旁邊有政府工作人員路過,看到情況前來解釋,老吳才把州長放進去。
因為工作認真,門衛工作做得好,后來州委從政府搬遷出來到了沙子坳,領導點名把他也調過來,到新州委看守大門。
那時候小車也不多,去州委機關辦事很多都是騎單車去的,進大門前先要上一個坡,然后才是平地。有一次,我騎車進州委,因為才爬一陣坡,到了平地,見門口沒人,便騎著進去。騎了約50米,聽見后面有人喊。回頭一看,有人追趕上來,連忙下車。只見老吳氣喘吁吁地跑到我面前,用左手很別扭地敬了一個軍禮,說:“同志,進門要登記!”來得太突然,我一下子不好意思起來,趕忙推車同他返回去登記。心想,這老吳也太認真了。不過從此以后,他就認識我了,每次見面,都笑瞇瞇的,主動和我打招呼。后來,我也搬進了大院,和機關的人說起,他們許多人都有類似經歷。有人故意不下車,他就一直追下去,直到你下車登記為止,特別是他那個軍禮,既禮貌又顯滑稽,往往讓你無話可說,乖乖去登記。
老吳就是這樣一個人,因為把關得好,在州委又看守大門十多年,也沒有發生過盜竊事件。后來他退休了,機關請了五六個保安接替他的工作,有時仍免不了有小偷進門。
老吳退休后,無事可做,有點閑不住,開始在大院里撿垃圾,打掃衛生。后來打掃衛生也發包出去了,他又養花草,栽樹木。大院里養盆景的多,他也學著栽了一些盆景。因為不會修剪,往往長得很零亂,也曾向人家學習修剪,可到自己動手,總是修剪不好。他就每天澆水、施肥,所以,他的盆景長得特別蔥翠。大院里養盆景的經常要出差,夏天沒人澆水,找到老吳,請他澆水什么的,他可最樂意了。每天必先把別人的花木澆好水,才去澆自己的,所以,大家都樂意找老吳幫忙,老吳也從不說二話,爽快答應。
大院背靠青山,里面樹木花草一多,常常引來一些野蜜蜂。老吳看到后,留了心。一次,他找來一個舊圓木桶,在桶子的大口子上,鋸了個小口子,把它搬到樓頂,翻轉過來,下面做了個木架,墊上木板,另在桶子的頂部,蓋上塑料瓦。那鋸的口子剛好讓蜜蜂出入。原來,這是湘西人養野蜜蜂的一種辦法。老吳弄來一些蜂蜜,放在蜂桶里,一下子就引來了好些蜜蜂。那些蜜蜂本是野生的,見有了蜂巢,就在里面安營扎寨,繁殖后代。老吳每年定時取糖,倒也能收獲好幾斤。現在,已經發展到三五個桶了。
那野生蜜蜂采的蜜,原汁原味,特別的好,大院里的人知道了,有時也去買一點。后來要的人多了,往往一搖出蜜,大家便你一點他一點買走了。看到自己的勞動成果有人分享,那是老吳最開心的時候。
老吳已經老了,怕有七十多歲了。但一天到晚在院子里忙乎,身影尚很矯健。我常常看到老吳在陽光下擺弄蜂桶服侍蜜蜂的情景,有時還哼著歌,那感覺,比喝了蜂蜜還要甜蜜。
牌樓的大姐
屋前一灣碧水,屋后疊疊青山。楊清芝的家就坐落在上牌樓組的山腰上,依著山勢搭起了一排吊腳樓,漂亮而實用。
楊大姐今年65歲,身板高大結實,說話快言快語,干活動作麻利,是鄉村特別能干的那種婦女。
因為拍攝紀錄片《酉水人家》,我們選定跟蹤她一家進行拍攝。她沒有猶豫,很爽快地答應了。
她是那種很豪爽的農村婦女,以前曾當過生產隊的婦女主任。她是打藍坳那邊人,自從嫁到這邊,正遇上下游鳳灘電站修建,羅依溪毛坪一帶良田被淹成一片汪洋,他們家向山中后靠移民,于是就搬到上牌樓的山上來了。毛坪村以前有個下牌樓和上牌樓,據說舊時是有牌樓的,不知道何時被拆毀了。到了后來,不見了牌樓,只剩下了地名。再后來,下牌樓被水淹沒了,就只剩下上牌樓了。
楊大姐家只有7分地的茶葉,就在她家吊腳樓的旁邊。那茶葉一篷一篷的,修剪得整整齊齊。到了春天,茶葉發芽了,嫩綠嫩綠。到茶葉長到一芽一葉,就開始采茶了。
古丈是有名的茶鄉,棲鳳湖因為地勢較低,茶葉出來得早。清明前的茶葉是最好的,價格也最高。以前都要自己加工,每斤春茶可以賣兩三百元。現在有人專門收購鮮茶葉,40~60元一斤。四斤鮮茶葉才炒一斤干茶,賣鮮茶葉還合算一些。
楊大姐是采茶能手,每天能采上十斤鮮葉。到了下午,收茶葉的人一來,過秤,就有幾百元收獲。不過,這采茶要天氣好,雨天是不行的。春天多雨,每逢雨天,她就在家做家務,帶孫女。
楊大姐的老公姓羅,是一個老實巴交的農民。平時沉默寡言,很少開口說話。他們有三個兒子,老大老二分別在古丈和吉首工作,只有老三在家搞農業,已經結婚成家,有了三個孩子。
這一帶農村的主要收入是靠養魚和茶葉。一般男人在水上干活,在湖里養魚和網魚。女人操持家務,干點土上的活。季節來了,就上山采茶葉,分工很明確。
別看羅大哥平時不太說話,一到了湖里,網起魚來,就像年輕人一樣,生龍活虎,每晚都有好的收獲。
水上生活的人都喝點酒,主要是為了祛風濕,祛寒。楊大姐有時勞動累了,也跟著喝一口。前些年,鄉里的書記到他們村蹲點,村里安排吃住在他們家。那書記姓何,是個大學畢業才幾年的小伙子。一次書記召集村骨干在她家商量工作,開完會,事情安排妥當,按湘西習慣,就喝酒。書記見她辛苦,叫她也喝一口。沒想到,楊大姐量大,倒把年輕書記灌醉了。書記后來到州里當了局長,有次開車在吉首街上看見大姐,遠遠地停下車,非把大姐請到家中喝酒不可。大姐有事,便借故推辭了。
我問大姐,長期在水邊生活,會游泳嗎?大姐說,會一點,只是游不遠。以前夏天一群婦女常在湖邊洗澡洗衣服,慢慢地就會游了。她說,他老公是游泳好手。還是大集體時,那時他們結婚不久,有一次她蹲在船頭洗衣服,那船就靠在岸邊。老公說,你跩(zuai,蹲的意思)穩,我從坎上跳下來。話音未落,人便從兩三米高的地方跳到船尾。那船小,就像撬板一樣,尾部一個人落下來,就把船頭的她彈進了湖里。那時她還不會游泳,在水里掙扎著。老公看見,并不救他,只是笑。附近的人就起哄。楊大姐游了好一會,喝了幾口水,終于游到岸邊。哭哭啼啼的,罵丈夫沒良心,為什么不去救她?丈夫說,我看著的,絕對不會淹著你。要不你怎么學會游泳呢?說也奇怪,自那以后,她就會游泳了。
丈夫每晚都去湖里網魚。每網了魚,卻要女人去賣。因為男人賣過幾次魚,不太會講話,等了很久都沒有把魚賣掉。而楊大姐一去,一陣吆喝,一會兒就將魚賣掉了。
有一天,正遇到羅依溪的趕場日,楊大姐帶著小孫女早早就趕場來了。她是來賣魚的。老公每天晚上在棲鳳湖中網魚,多少都有幾斤收獲。每網到魚,他們不是每天去賣,而是裝進一個小漁網中,掛在船邊,沉入水中,養起來。到了趕場天早上,楊大姐就下到湖邊,將網兜提起,把魚放進一個大塑料桶中,灌進一些新鮮湖水。然后將船劃到碼頭上,停靠好,背著魚到街上去賣。
羅依溪市場有一條小街,專門賣魚的。棲鳳湖的打魚人,一般都集中在這里賣魚。他們都備有盆子,寄放在居民家中。到了街上,把魚放下來,很快到居民家中取出盆子,將桶子里的魚和水一起倒進盆子中,再添加一點新鮮自來水,那魚又活蹦亂跳起來,看上去很是愛人。
楊大姐賣了多年的魚,趕場的人都熟悉了。加上她口齒伶俐,招呼得好,一般情況下,她的魚賣得很快,上午十點左右,就賣完了。
說起賣魚,她那小孫女,最喜歡跟她去賣魚。小孫女才一歲多,正是活潑好動的時候。每當魚放進盆里,她就要給盆子里灌水。有時撿一根草,伸進盆子中去惹魚,看魚吃不吃。有時那大魚在盆子中跳躍,將她身上濺一身水,她便要用棍子去打魚,被奶奶一手拉住。“魚不懂事,你也不懂事嗎?怪搞。”于是取出身上的手帕,將她臉上身上的水擦干凈,交代她,“你給我站好,要不下次不帶你來了。”這一說,孩子老實了許多。“我給盆子里添水去。”于是孩子又給盆子里添進新鮮水來。
這一天,楊大姐家的魚早賣完了,兒子的一條大草魚還無人問津。那魚太大,有十幾斤重,一般家庭吃不了那么大的,除非是辦喜事什么的。
按慣例,賣完魚,楊清芝帶著孫女去趕場,給孩子買點玩具什么的,那是孫女最高興的事了。
趕場回來,兒子的魚還是沒有賣掉。楊清芝說,我來給你賣魚,你帶孩子去鎮上,給我交20元話費。說著,取出20元,交到兒子手中。
這時,有幾個陌生人走過來,好像是買魚的。楊清芝給魚盆里加了一點水,就招呼起來。
近年來,羅依溪一帶正在修建吉永高速和幾條鄉道,很多外地的工程隊進來了,經常趕場買東西。工程隊人多,食堂常常買大魚。這棲鳳湖網的魚是野生的,味道好,價錢也不貴,所以,他們樂意買。
買主走到近前,那草魚像懂事似的,尾巴一飆,頓時盆子里濺起水來。楊大姐說,“這魚昨晚才網的,野生魚,好新鮮。”來人看了又看,“這么大呀?多少錢一斤?”
“便宜,就賣8元。”
“再便宜一點吧。”
“要的話,稱了重再給你優惠。”
接著就稱重。先把魚捉住,放進大桶子中,一稱,有15斤多。再把魚取出,稱塑料桶,有9兩。扣去皮,合14斤5兩。大姐是個爽快人,“就算你7元一斤,一七得七,五七三五,一百零五元。你送一百整算了。”
來人不再說話,掏出一張大團結,交給楊大姐,提著魚高興地走了。
一百元,對于現在這個時代來說,不算多。但對于楊大姐來說,還是挺高興的,因為終于把魚賣出去了。她還要趕回去采茶葉,一天下來,還可以賣一兩百元。
鄉下人就是靠這季節來掙錢的。
馴猴人傳奇
牛路河位于猛洞河漂流的終點站,這里山高谷深,一條清亮的溪流從山谷中靜靜流過。站在五十多米高的大橋上,俯瞰下去,那碧水像一條玉帶,飄灑在谷底深處。兩岸古樹倒懸,一群猴子在古老的樹枝上歡快地跳躍著,看得出特別的高興。一位老人站在橋邊,凝視著猴群,眉頭舒展著,不經意地笑了。
這位老人便是猛洞河畔有名的馴猴人聶祖清。他像一位將軍,站立著,很有點“威武”。這幫猴子就像他的“士兵”,同他一起,演繹著人與動物與自然和諧相處的傳奇。
有人說,聶祖清生就一副“猴相”,是天生的“猴王”,所以能指揮這么多的猴子。仔細看去,確實有點像。也許是與猴子打交道多了,他的一舉一動有點猴子的影子。到底是猴子像他還是他像猴子,很難說清楚。
他老家是龍山縣紅巖溪塔泥人,1941年出生,今年75歲。他老家一帶,群峰高聳,森林茂密,生態良好,非常適宜猴子生長。也常年有一群猴子生活在那一帶。舊時代,地廣人稀,猴子繁殖相當快。猴子多了,便與當地老百姓爭食物,所以,每年要捕獲一些,以維持生態平衡。久而久之,當地人就傳下來一些捕捉猴子的技藝。解放前,許多人便靠捕捉猴子變賣來養家糊口。解放后,隨著大煉鋼鐵,森林的砍伐,生態的破壞,猴子漸漸少了。但貴州和四川的大山中多猴群。猴子多了,糟蹋莊稼,弄得附近百姓寢食不安,紛紛傳出消息,請人去捕捉猴子。當時捕猴子是政府允許的,并且供銷社收購,每只十七八元。這樣,聶祖清和一些鄉親農忙時在家鄉勞作,農閑時到這些地方捕捉猴子。為了鼓勵他們捕猴子,當地政府還為他們提供伙食。猴子捕捉得多,除了變賣可以收入外,當地政府還給予適當獎勵。這樣,他們在外捕猴子數年。
這捕捉猴子是需要技術的,首先必須身手靈活,在大山中行走如飛,才能跟得上猴子。其次,要掌握猴子的習性,知道它們喜歡去哪些地方,從哪些地方過路,這樣才能放套。再次,要注意一些禁忌,捕捉猴子的人是不能吃猴子肉的,那些小猴子也是不能捕捉的,絕不能斬盡殺絕。
猴子全身都是寶,猴腦可以食用,以前富貴人家吃猴腦,手段特別殘忍,現在已經沒人那么吃了。猴子皮毛可以做衣服,是防止風濕的最好衣物。猴子身上的部件可以入藥……總之,當時是國家定點收購的,據說還用于外貿出口。
1985年,湘西猛洞河平湖游興旺起來了,線路是從王村坐船上行,到小龍洞、猴兒跳一帶,然后返回。沿途峽谷高深,水平如鏡,兩岸古樹倒垂,風光十分秀美。那兩岸還有一群野生獼猴,不時出沒,最能引起游客的興趣。可惜沒有被馴養,不能準時出來,和游客互動。當時旅游公司的領導想,要是有人能馴養猴子,那該多好。于是,公司張貼了招賢榜,專門聘請高人來馴養猴子。在這種情況下,聶祖清來揭榜了,當時他已經44歲。
此前雖然了解猴子的一些生活習性,但真正馴養猴子,他還沒有做過。于是,他決定與猴子交朋友。每天到一定時間,他唱起猴歌——“喲嗬喂哩……喲嗬喂哩……”——一種喊猴子的歌謠,然后給猴子撒下一些包谷籽。開始猴子并不接受他,見他在旁邊,猴子只遠遠地看著,不敢靠近。等他離開了,猴子便跳將過來,一下子把包谷籽吃掉。他知道猴子見他生分,也不管,每天按時喊,去撒包谷籽。如此一段時間,那猴子便不再怕他,可以當著他的面吃東西了。再后來,猴子每天就按時等候他,聽到他熟悉的猴歌,便知道有吃的了,漫山遍野的獼猴都會相互打著“喔喔…喔喔…”的聲響,紛紛朝他飛奔而來。就這樣日復一日,漸漸地,他與這群野性十足的獼猴成了朋友,更成了“兄弟”。
開始猴子怕游船,聽到柴油機的“嗒嗒”聲音,一下子作鳥獸散。再后來,每到游船過來,他就開始叫喚,猴子看到他站在岸邊,便不再害怕,說明對他已經充分信任。于是,游船一來,一些游客向它們拋擲食物,猴子也開始接受。再后來,看到游船過來,那些猴子都跑過來,開始歡迎了。這就實現了游客和猴子的和諧互動,增加了旅游的情趣,很受游客的喜愛。
他還訓練猴子高空跳水,涉水過河。在小龍洞附近,有一片比較寬闊的水面,一邊是垂直的懸崖峭壁,峭壁上生長著一棵大一點的樹,伸向水面。另一邊的絕壁下,有一塊比較平坦的草地。他訓練猴子從峭壁的樹上挑水下來,再泅水過河,到對面的草地上來。每當猴子跳水過河來,他就用食物作為獎賞,那些猴子受到嘉獎,興奮極了,發出“嗬嗬……嗬嗬……”的聲音。
于是,每當游船到來,那猴子高興了,接二連三從高高的樹上跳下來,“撲通……撲通……”墜入河中,然后奮力游到對岸,領取“獎賞”去了。那些游客大多第一次見到猴子跳水游泳,更加開心,紛紛拿出食物,送給猴子們……
一時間,猛洞河平湖游聲名鵲起,被許多游客津津樂道。湖南衛視、中央電視臺都來拍過專題片,更擴大了影響。許多游客帶著孩子是慕名來看猴子的。猛洞河旅游也風生水起,繁榮一時。
在他的喂養和馴服下,猛洞河畔的猴子繁殖很快,由最初的40多只發展為200多只。部分猴子在新猴王的帶領下,重返森林,成為野猴子了。大部分還是跟著他,在猛洞河邊生活,逗樂。
后來,隨著猛洞河漂流的興起,人們喜歡玩更加刺激的,平湖游便衰落下來。這時候,聶祖清也到了退休的年齡,辦完手續休息了。
他退休后,公司另安排一個人喂猴子,那些猴子每天按時來進食,吃完又走了,并沒有建立情感。
漂流興旺以后,公司想把猴群從平湖河邊趕到牛路河漂流點,以增加旅游的樂趣。無奈那些猴子已經習慣了平湖附近的環境,好不容易趕過來,一段時間后,又自行跑回去了。如此數次。公司又想到了聶祖清,把他請出山來。說也奇怪,聶祖清一來,那些猴子十分聽話,跟著他過來了。現在到了牛路河的橋邊,就在附近玩耍。公司也為老聶在橋邊租下兩間小房子,和猴子們一起生活。
這些年來,湘西山中實行退耕還林,樹木越長越大了。許多人打工進城了,因而山中的生態更好了。生態一好,各種野生動物也多起來。老聶住在簡陋的房子中,曾發現兩條毒蛇,被他趕走了。一次去看猴子,猴子“咯咯……咯咯……”給他發出警告。他仔細一看,原來是一條三四斤重的五步蛇盤踞在路中間,抬起頭,向他怒視著。老聶馴養猴子,一般是不殺生的,就趕五步蛇走。那五步蛇昂著頭,不肯走。直到老聶拿來棍子,那蛇才慢慢溜走。
山中生活是艱辛的,但老聶堅守著。他有一個想法,就是想在牛路河上架一根鐵絲或者繩子,他訓練猴子走鐵絲,高空飛渡,讓漂流下來的游客觀看。如果訓練成功,這將是全國首創。還想訓練猴子與游客互相打水仗,一定會為游客增添許多樂趣。但這些需要公司的大力支持。
我們見到老聶時,正是年早春的雨季,三月里的小雨淅淅瀝瀝,下個不停。猴子們躲在樹上,不肯出來。老聶說,到了五六月份來,那猴子應該就會表演了,你們再來看吧。言語中充滿自信。
住戶老向
1990年,我被單位抽調到湘西州委社教工作隊,駐點永順縣王村鎮的百勝村搞社教與扶貧工作,住在向家灣一個叫向代雙的老百姓家中。
向代雙當時四十出頭,是農村那種很勤勞的農民。妻子比他小一點,也是那種善良賢惠的婦女。他們家有4個孩子,大女兒十八九歲,初中畢業后在農村勞動。三個兒子十二歲到十五六歲不等,都在學校讀書。家中還有一個老奶奶,七十多歲,身體尚很硬朗。
他們家住在向家灣最里面的一個角落里。一棟木房子,四排三間,中間是堂屋,兩邊是住房。右邊的主房,分為里外兩間,外間住著他們夫婦,里面是他們女兒的閨房。我到他家時,他們把女兒的閨房騰出來,讓我居住。而把女兒,趕去同老奶奶居住另一棟舊木屋里。我是他們家第一次接待的國家干部,可見他們家對客人的尊重。我后來知道了這情況,要求換出來,和他們兒子住一塊。他們卻怕孩子們頑皮,吵鬧了我,總是沒有換。
那時候湘西農村只吃兩餐,我們在城市吃三餐習慣了,開始很不適應。我當時身強力壯,又每天參加勞動,干體力活。上午十點多吃早餐時,我已經饑腸轆轆了。吃了早餐,到了下午三四點鐘時,又開始餓了。住戶知道了我的情況,他們是燒柴火煮飯的,所以每天早上煮飯時,多放一點水,飯一開,便舀出一碗米湯,留給我喝。而每天在燒柴火中,順便燒幾個紅薯,讓我餓了充饑。雖然這不是什么大事,但令我十分感動。這么一個月下來,我的體重不僅沒有減少,反而增加了好幾斤。
我只在他們家住了一個多月,后來社教分團抽我寫材料,搞接待,便離開了他們家,住到鎮政府去了。雖然在他們家住的時間很短,但結下的情誼卻是一輩子的。
在王村搞了一年,后來又回到單位,再后來調動工作,但幾乎每隔一兩年,都要抽時間去他家看望一下。他們家也在平穩發展中。女兒出嫁,大兒子結婚,二兒子當兵,三兒子又考上了學校。
送小兒子上學時,他們轉道吉首,到我家住了一晚。我給他兒子送一點學費,表示祝賀。開始他們不肯要,我做了好久工作才接受下來。
有一次,我們工作隊的朋友相邀去探望住戶。我出差在外,沒有趕去。聽他們回來講,我那住戶家里發生了一點事,不過已經處理好了。大致情況是這樣的。好像是住戶的大兒子參與打牌,被抓住罰款,而且罰款較重。住戶去鎮派出所找干警,干警不理他。住戶等了半天,不耐煩了,就在樓下吵嚷,憤怒中罵了一句娘。這下干警出來了,對住戶一頓拳打腳踢,把住戶打傷了。那時住戶已經五十多歲,二兒子已經轉業到縣里某鄉鎮,當了武裝部長。小兒子學校畢業后,也去了邊防武警部隊,當了軍官。二兒子于是找到派出所和干警,要求賠禮道歉,承擔醫藥費用。對方以被罵娘為由一口拒絕。湘西有一個不好的習慣,只要是被對方罵娘了,便可以動手打人,似乎理直氣壯。這事拖了很久沒有處理,他們家把情況又反映到老三所在部隊,部隊來函要求盡快處理,地方也沒有處理下來。
不久,老三回家探親,安慰父親。回來后,聽到一些情況,十分氣憤。走到派出所,把那打人的干警喊下樓,問他愿不愿意賠禮道歉。干警仍固執地拒絕。這時,老三動手了,一頓拳腳,把干警打倒在地,說這就是你毆打老人的教訓,說完揚長而去。這事就這么處理了。有時候,民間一些問題,用民間的辦法處理起來,反而容易了結。
大約是2007年春節臨近,我接到他家老二的電話。說他們家的房子被大火燒了。我聽了后,感到震驚。春節前的一天,剛好我女兒大學放假了,我便帶著妻子和女兒前往他們家看望。他們一家住在旁邊老奶奶留下的房子里,原來的木房子已化為灰燼。原來是他們家小孫子玩火,不小心房子著火了。本來是木房子,屋前屋后又沒有水池,所以也沒辦法撲滅,眼睜睜地看著整個家產燒光了,好在人沒有傷著。我感到很惋惜,給他們家送了一點錢,又給永順的一個領導朋友打電話,后來領導指示地方政府給他們家安排了兩千元過年補助,很快送到他們家中。
就在那一次,他們父子帶我到他們家后山去走了一趟。原來,他們村老百姓把后面的山都搞了開發,種上多種樹木和經濟作物,無奈山中沒有一條公路,東西靠背簍背下來很不方便,希望上面安排點資金,修建一條簡易公路。
我覺得這是個好事,要他們立即打了報告,回去后便找到州扶貧開發辦的領導。領導問我這是什么關系,我說是18年前扶貧點的住戶。領導感到很驚訝,說你們還在往來呀?我說,扶貧工作也不是一年兩年的事,是長期的任務呀!領導笑了,為我的這種情分所感動,當即批示安排點錢,督促下面辦理。
第二年,錢就撥下來了,請了挖土機,很快就把路修好了。通路時,住戶打來幾個電話,請我過去參加儀式。我一方面沒有時間,另一方面,聽出老百姓要感謝我的意思,我便沒有去,說只要路修通了,就達到目的了,我去是多余的。
能為老百姓想方設法辦成一點事,我覺得很有意義,需要什么感謝呢?這些樸實的農民呀!
棲鳳湖人家
又到周末,久雨初晴,陽光明媚,難得的好天氣。我和朋友相約,又驅車到棲鳳湖釣魚來了。
棲鳳湖位于湘西古丈縣,原是一片山清水秀的農田村舍。上世紀七十年代,下游修建了一個叫鳳灘的電站,壩高近百米,蓄水深達幾十米,這一片地勢低洼,便形成了一個人工湖泊。后來移民部門又投資在湖的出口處筑了一個調節壩,使棲鳳湖成了一個水產養殖場。湖光山色,令人神往。這里還是電視劇《血色湘西》等外景拍攝基地,至今電視劇中的一些布景,仍保留著,成為人們春游攝影留念的好地方。
一路上,山中的櫻桃花次第開放,雪白的,點綴在枯草叢生的山中,給寂靜的山頭平添了一絲生氣。公路兩旁稻田里的油菜花也開放了,粉黃色的花映亮了田園,令人賞心悅目,給連綿陰雨壓抑的心情帶來輕松和釋放。
我們要去釣魚的地方位于棲鳳湖里面的一個叫洞山的湖汊里,一個姓張的漁民圍了半灣湖,用網箱攔斷,里面養了不少魚。
張姓漁民大名張思明,外號叫“大翅膀”。不知道這別名是怎么來的,反正人家都這么叫,他也樂意答應。他中等個子,瘦長身材,人很精干,也很熱心,待人誠懇,所以去他那兒釣魚的較多。雖然行程較遠,但人們還是樂于去。
他出生于淹沒區的農民家庭,因為電站修建,遷移到非淹沒區的坡上,長大后被招工進了古丈縣冶化廠當了工人。上班十幾年,廠子垮了,下了崗,又回鄉當起農民。因為在廠里學了些知識,又見了些世面,隨后就率先攔湖養起魚來,成了我們所稱的“魚老板”。
雖然是漁民了,其實還住在岸上,在陡坡的山灣里修了座房子,又分得一兩畝茶園,娶了老婆,有兩個孩子,一家人打拼著,生存下來。
春天來了,萬物復蘇,滿山的野花開了,將山野裝扮得十分鮮艷而生動。幾天太陽下來,茶葉也發芽了,開葉了。古丈是有名的茶鄉,人人都會采茶,制茶,加工出來的茶葉嫩綠嫩綠的,泡起來清香可口。因為是清明前的頭一批茶,所以當地人稱“明前茶”。茶葉細嫩,有點像麻雀的舌頭,又叫“雀舌”,是難得的好茶。
春天到“大翅膀”的湖里釣魚,就可以品嘗新鮮的茶,還可以吃到鄉里臘肉,鄉里土雞,再加上才釣上來的活水魚,簡直是種享受,所以,我的朋友們都肯去。
他們家還養了很多只雞,開始是關進雞籠里的,母雞每天回來下蛋,孵小雞。后來漸漸野了,晚上也不回屋進籠了,就在屋后的樹林中歇息,雞蛋也下到野窩里,人無法找到,等到一兩個月,母雞又帶一窩仔雞出來覓食,才知道又多了一窩雞。如此,他家每年都產幾十窩土雞,長到一兩斤一只,公雞才開叫時,宰殺了讓釣魚的客人吃,客人無不稱贊好吃。
他家媳婦能干勤快,是采茶好手,手腳麻利。飯菜也弄得不錯,始終是一副笑臉,給人以賓至如歸的感覺。
他們家還養了幾頭豬。名義上是家養,實則是放養。白天讓它們自己到山上曬太陽、拱土、覓食,夜晚又回到豬欄,喂食物。他家兩個女兒,老大十幾歲,每天放學回來,拿一本書,就去放豬。天黑時把豬趕回,順手扯一些豬草。因為是放養的,又是本地土豬,所以瘦肉多,肉特別香。每年冬天,宰殺幾頭,熏成臘肉,掛到火灶上,一排過去,有幾百斤重,看到都讓人流口水。
“大翅膀”每天就伺候他的寶貝魚。據他說,幾年下來,他網箱里已有三五萬斤魚,每天都要喂一些飼料。加上釣魚的人來人往,每次都要用船接送,他就開著他的小機船,柴油發動機的,“突突突”地來回穿梭著,在水面劃上一道深深的波紋,泛著粼粼的波光,煞是好看。
那魚兒好像通人性似的,每天上午,饑餓時,成千上萬條小魚,在網箱里同一個方向旋轉,沒有一刻停止。待老板撒下飼料,吃飽以后,就沉下去了,不見了蹤影。
大魚是在大湖中的,有鯉魚、草魚、鳊魚,還有叉尾魚等等,天氣熱時,偶爾一兩條躍出湖面,激起水花四濺,很是耀眼。
湖水是那樣的清,因為水深有幾十米,遠遠看去,幽藍幽藍的。近處看則水面透明,偶爾可以看到五六米深處的大魚。炎炎夏日里,只想跳進去洗個澡。
灣盡頭有一條瀑布,高山中的水從那里流下來,沿著石壁傾瀉而下,形成七八米高的瀑布。瀑布下的水更是清亮,夏天在那釣魚也是特涼快的。
“大翅膀”有點愛酒,平日里都要喝幾口。水上生活的人,都要喝點酒,可以抗風濕,強身健體。遇到朋友知己,則多喝幾口。他這人怪,不喝酒很少說話,喝多了便話多,好像要將平時憋著的話說完似的。什么都說,老婆在旁為他急。
他說,這幾年政府鼓勵他們養叉尾,那是美國引進的魚種,加工后魚肉直銷美國的。現在美國經濟不好了,進口少,價格低,還有兩萬多斤魚沒賣出去。叉尾魚是最肯吃釣的,真正的釣魚人都不喜歡,稱它是“哈寶(傻瓜)魚”,見鉤就咬。
他說他湖里有三條野生的“雕子魚”,每條有二三十斤重,游在水里,像箭一樣快捷。那家伙是吃魚的,每條每天差不多要吃一條兩三斤重的魚,每年都要損失他幾千塊錢。他曾放信請釣魚高手去釣,釣到一條可以免費到他湖里釣一個月,三條全釣到可以免費釣一年。許多高手每次一來,用雞腸子做魚餌。那魚刁鉆狡猾,力氣又大,將雞腸子吃掉,繃斷線又跑掉了。后來,他又買來魚槍去打,守了幾晚,放了幾槍,打中了,卻打不死。魚大了,槍彈只能打進表皮,不能穿透內臟,結果表皮一爛,槍彈脫落,過一段,魚又痊愈了。不過,經他一嚇,有一條魚不見了,可能是穿透大網逃進大湖里去了,可是他不知道大網缺口在何處,跑了多少魚也不知道……
這幾年,他在湖里投了十多萬塊錢,可以說是傾家蕩產了。建了一百多米長,幾十米深的大網,光材料費就用了幾萬,買了幾萬塊錢的各種魚,在湖岸修了便道,釣魚臺。以前人家嫌他吃飯的環境差,又在湖邊修了一幢吊腳樓。這不,又花了一萬兩千元錢做了一條小鋼板船,七匹柴油機馬力的,比以前的木船耐用,平穩而快捷……
他還說,老婆給他生了兩個女兒。以前一心要個兒子的,可以傳宗接代,這半灣湖,夠吃幾輩子的了。可惜天不遂人愿。不過現在想通了,只要教育好,女兒還孝順一些。這不,小女兒才四歲,就送到湖對面的幼兒園去了,每天早送晚接,風雨無阻……
夕陽西下,將湖面灑下一層金光,遠山影影綽綽,層層疊疊。“大翅膀”駕駛著他的新漁船,送我們上岸,柴油機“突突”地鳴響著,小船載著我們,向金色波光中駛去……
峒河的苗家少女
入春過后,連下了幾場大雨,滿山變得翠綠起來。湘西峒河沿岸的山林野草被雨水染得綠油油的,像是擰得出綠色的汁來。天氣漸漸變熱,夏天說來就來了。
常言道,春江水暖鴨先知。油菜花剛謝不久,小鴨子就開始下河了。此刻,一群小鴨子才從水中游弋完,走到岸邊歇息著,悠閑地梳理著白絨絨的細毛。趁著這間歇,苗家少女臘香和她的同伴們下河摸魚來了。
這一天是星期六,鄉中學放假,臘香同伴們閑著沒事,就相邀下河來摸魚。
這河好像是專為臘香她們生的,一年四季,她們姐妹就在小河邊玩耍,嬉戲,摸魚,撈蝦,不知不覺中,慢慢長大了。
峒河只是湘西大山中眾多河流中的一條,它發源于鳳凰的臘爾山高地,一路歡笑著,奔跑著,到了大龍洞這地方,水從兩百多米高的山洞中飛流直下,形成一個巨大的瀑布,落入下面的深潭中。接著,便在山谷中蜿蜒流淌。到了巖板寨這個地方,沖擊出一片平地。苗民們依山筑房,臨水而居,守護著這片田園。
那小河更像是一條失落在這深深峽谷中的綠色飄帶,飄舞著、纏繞著一座座大山,澆灌著兩岸的農田。于是,這兩岸成了村民們賴以生存的地方,更成了孩子們的天堂。
少女臘香就住在靠山的小木屋里,因出生于臘月,爺爺給她取名叫臘香。她上有父母,下有一個弟弟,爺爺奶奶是分家而居的。既然是家中的長女,窮人的孩子早當家,許多家務事就落在她身上。而這些家務,大多是在河邊的,與水親密接觸。
那河里有各種各樣的魚,有紅條魚、白條魚、鲇魚等,還有娃娃魚,不過現在很少了。最多的一種是叫“巴巖魚”的小魚,平常就黏在小石頭縫中,你一動它,它便四處跑,會摸魚的伸手順勢趕它,它便乖乖地進入魚簍中。
臘香她們撈魚用的是兩只簍,都叫魚簍,不過,苗語中是有區別的。魚簍是臘香的爸爸用竹子編成的,大簍上寬下窄,尾部鎖死,利于將魚趕進去。小簍是用來裝魚的,呈壺形狀,上口較寬,中間鎖緊,下部分寬敞,但魚兒跳不出來。這小簍常用來捆在腰上。女孩子將魚簍一捆上腰,就顯得特別干練,完全沒有那種少女的扭捏和羞澀。
臘香她們一路嘻嘻哈哈,來到水邊,赤腳踏進水里,頓時一股清涼涌到身上,好暢快呀。趁著幾個姐妹在低頭扎著褲腳,臘香雙手并攏掬起水,用力向她們潑過去。幾個女孩子沒注意,一下子從頭到腳涼到心頭。等反應過來,也用力向臘香潑水,臘香則已做好準備,跳著躲開到一定距離。一時間,潑水聲、尖叫聲、歡笑聲響徹了河谷……
接下來,便開始捕魚。只見她們橫在河中心,站成一排,面朝上游,伏下身子去摸魚。她們將大魚簍口子朝上,屁股朝下,夾在兩腿中間,人彎下腰去,就像騎在一個小馬扎上。一雙手伸長,在魚簍前摸索著,將黏在石頭上的魚兒趕進簍中。一會兒,差不多了,提起竹簍,水嘩嘩地往下流。往魚簍里一看,里面有幾條小魚,活蹦亂跳。于是滿懷喜悅,伸手將魚兒抓住,放進腰上的小簍中。就這樣,一會兒彎下腰去摸,一會兒站起來將魚兒放進小簍,太陽在空中慢慢地移動著,一兩個時辰就過去了。
大龍洞的河岸有許多水車,因為河谷低,兩岸的稻田高,需要水車將水揚起來,灌進稻田里。那水車是圓形的,遠看像蜘蛛網一樣,密密麻麻的。走近看則是用木棍或竹竿扎成的,靠在河邊急流處,隨水流的沖擊而旋轉,將水引上一條木槽,然后嘩嘩地流進水田里。禾苗有了活水,便有了生命,就像汲取大地的乳汁一樣,茁壯成長起來。
那水車因為轉動、摩擦,時常發出“吱呀”的聲音,有時像音樂般動聽。偶爾聽到這聲音,臘香她們不由自主地哼起歌來,唱起卻是流行的音樂。臘香最愛唱容祖兒的《揮著翅膀的女孩》,唱著唱著,自己好像真的長上了翅膀,遨游在山谷上面的藍天中。臘香13歲了,到了多夢的年齡。
正這么想著,天空真的飛了幾只鷺鷥來。這些鷺鷥是到河里撲食的,吃飽了,便飛起來,它們總是成雙成對的,扇動著雙翼,像是在天空中跳舞一樣。
幾歲的男孩女孩就光著屁股,在河里面玩。說是游泳,其實是在玩水,山里孩子學游泳是不要老師教的,在不斷的玩水中嗆幾口水,便學會了游泳。大一點的小女孩則在河灘洗衣服,那是父母勞動弄臟的衣服。還有就是帶著弟弟妹妹來玩,讓他們在水車邊看水車旋轉,在淺水邊翻螃蟹,一玩耍就忘記了時間,肚子餓了才嚷著要回去。
河邊的一個小男孩,在摸螃蟹時手被螃蟹夾住了,“臘香姐!臘香姐!”地叫喚起來。臘香提起簍便跑過去,用雙手扳開螃蟹的鉗子,將小弟弟的手指取出來,那鮮嫩的小手指上,留下了深深的紅印,小弟弟痛出了眼淚。臘香將那小手指放到嘴邊吹幾口氣,又呵幾下,然后用自己的手將小弟弟的小指頭摩挲一會,說不痛了。小弟弟便停止了叫喚,咧開嘴笑了,露出了缺牙的小嘴來。村里的男孩也把牛趕到河里來,讓它們吃河灘上的青草,天熱時讓牛下河游水。而他們自己,早跳進水里游泳戲水去了。
玩耍是孩子們的天性,女孩子也不例外。臘香她們摸魚一陣,便來到水車邊,坐下曬一陣太陽,或者鉆進水車中去玩。那水車中間有一根梁,可以站一個人,人鉆進去,可以跟著水車旋轉的速度,不停地移動著腳步,有點像走城市的跑步機一樣,不過,這水車比跑步機要生動有趣得多。
太陽爬上了山頭,河谷里很靜,靜得只能聽到水車的“吱呀”聲。
摸了半天的魚,臘香她們每人約摸到一斤小魚,早夠一家子吃一餐的了。不過,這魚他們很少吃新鮮的。拿回家,放鍋子里用油炸干,然后炒上干辣椒,用罐頭瓶裝著,帶到學校去,可以吃上好幾天的了。臘香現在已是鎮中學的學生,住校,每周五才回家,星期天下午返學校。學校的伙食貴而且不上口,干魚是最好的下飯菜。
天空中不時又飛來幾只白鷺,在綠色的背景下顯得特別耀眼。臘香常常望著白鷺出神,有時也像白鷺一樣心思飛到很遠很遠的地方。
責任編輯:黃艷秋
美術插圖:知 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