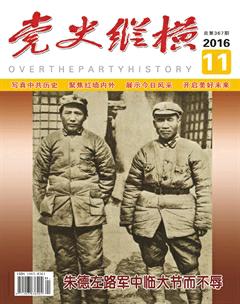郭沫若與魯迅失之交臂的“冰釋”
潘奕含

郭沫若在紀念魯迅逝世十周年的文章中,為自己未能與魯迅謀面而追悔莫及。他說:“自己實在有點后悔,不該增上傲慢,和這樣一位值得請教的大師,在生前竟失掉了見面的機會。”“我與魯迅的見面,真的可以說是失之交臂。”他們究竟為什么失之交臂,個中緣由耐人尋味。
郭沫若對魯迅的最初印象
1920年10月,郭沫若在《學燈》增刊上第一次讀到魯迅的小說,那是《頭發的故事》。他認為魯迅的觀察很深刻,筆調很簡練,但又“覺得他的感觸太枯燥,色調暗淡,總有點和自己的趣味相反駁”。郭沫若還坦言,這種感覺“直到他的《吶喊》為止”。
正因如此,當郁達夫勸他讀《故鄉》和《阿Q正傳》時,他沒有再去讀。他說:“但我終是怠慢了,失掉了讀的機會。以后的著作便差不多連書名都不清楚了。”不過,他在評價魯迅小說和周作人譯作時,明顯地尊重魯迅的小說,認為小說為“處女”,譯文為“媒婆”,“處女應當尊重,媒婆應當稍加遏抑。”顯然,他是有意推崇魯迅。
魯迅卻不領這個情。他說,郭沫若的主張“我是見過的,但意見不能相同,總以為處女并不妨去做媒婆。”“我終于并不藐視翻譯”。魯迅由此談到了郭沫若的翻譯風格,委婉地批評道:“我對于郭沫若先生的翻譯,不大放心,他太聰明,又膽大。”
1921年,郭沫若、成仿吾、郁達夫等成立創造社。成仿吾年輕氣盛,受蘇俄文學的熏陶,思想偏激,撰文批評魯迅的《吶喊》。魯迅對此極不高興,說:“他的‘庸俗的罪名,幾斧砍殺了《吶喊》,只推《不周山》為佳作——自然也仍有不好的地方。”成仿吾不是贊許《不周山》嘛,那么《吶喊》二版時,魯迅就偏偏刪去《不周山》,以“向這位‘魂靈回敬了當頭一棒”。
“我的去不去似乎沒有多大關系”
1924年,魯迅在《論照相之類》中談到,“近來則雖是奮戰忿斗,做了這許多作品的如創造社諸君子,也不過印過很小的一張三人的合照”。所謂“三人”便是郭沫若、成仿吾、郁達夫。他還動氣地批評說,創造社同人在“還未‘革命的時候,就已經將‘語絲派中的幾個人看作眼中釘”。這“幾個人”中便有魯迅。
1926年10月27日,在廣州女子師范學校執教的許廣平致信魯迅,盼他速到廣州中山大學任教。魯迅回信說,“今天看見中大考試委員會名單,文科中人多得很”,“郭沫若、郁達夫也在,那么,我的去不去也似乎沒有多大關系,可以不必急急趕到了”。從魯迅的調侃中可以看出,他是不愿與郭沫若等為伍的。
但此時魯迅正與許廣平熱戀,為她的熾熱感情所動,只得去信解釋:“其實我也還有一點野心,也想到廣州后,對于紳士們仍然加以打擊……第二是與創造社聯合起來,造一條戰線,更向舊社會進攻,我再勉力寫些文字。”
可魯迅終究沒有成行。他告訴許廣平,與郭沫若及創造社間的關系,是因為有好事者從中挑撥所致,如狂飆社的高長虹,“捏造許多會話(如說我罵郭沫若之類)”。他還在一篇雜文中嘲諷高長虹的無事生非:“在廈門的魯迅,/說在湖北的郭沫若驕傲,/還說了好幾回,在北京。”
一直到1927年1月中旬,魯迅才離開廈門來到廣州,而此時郭沫若早已離開廣州。
內山完造的分析
1927年10月,魯迅偕許廣平從廣州到了上海,經過一段時間的思考,已有意與創造社和好。他在致李霽野的信中說:“創造社和我們,現在感情似乎很好。他們在南方頗受壓迫了,可嘆。看現在文藝方面用力的,似只有創造,未名,沉鐘三社,別的沒有,這三社若沉默,中國全國真成了沙漠了。”
他們終于想到一起,都主張恢復《創造周報》,以“作為共同園地”。可是,成仿吾去了一趟日本,聯合的計劃便突然產生變化。日本的左傾文學,使成仿吾更加理直氣壯。他和李初犁、馮乃超等人,反對聯合魯迅,認為魯迅的文學思想與革命文學大相徑庭。
《創造周報》的恢復不得不中止,代之以《文化批判》。馮乃超發表《藝術與社會生活》,第一次用“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概念,向魯迅挑戰。郭沫若是創造社的主心骨,自然要參加對魯迅撻伐的混戰。1927年10月至1928年2月間,他們雖同在上海,都是日本書店老板內山完造的朋友,內山書店經常可見他們的身影,可他們竟然一次也未謀面,此中緣由確實令人費解。
內山完造曾將他們進行過比較,說:“魯迅和郭沫若的性格稍有不同。”郭沫若“從事政治,具有政治家的氣質”,“魯迅先生是純粹的地道的文學家,一旦表明自己的意見,就永不動搖,至今不渝”。一個具有政治家的原則性,一個具有文化人的倔犟個性,當然都不會主動屈就對方,以彌合感情的縫隙,唯一的辦法只能是回避、躲閃,以避免哪怕是邂逅時的尷尬和不安。
郁達夫對魯迅的聲援
創造社責難魯迅的文章一篇接著一篇,甚至以魯迅的籍貫、家族等作為奚落的資料。他們強加于魯迅的是,“代表著有閑的資產階級,或者睡在鼓里的小資產階級”;甚至使用漫罵的語言:“惹出了我們文壇的老騎士魯迅出來獻一場亂舞。現在就讓我們來看他這老態龍鐘的亂舞罷。”
郭沫若以杜荃的筆名在《創造月刊》發表《文藝戰線上的封建余孽》,語氣更加刻薄,氣勢更加唬人。他說,魯迅“像這樣尊重籍貫,尊重家族,尊重年紀,甚至于尊重自己的身體發膚,這完全是封建時代的信念!”
魯迅和陳源、高長虹爭論時,郭沫若還多少理解一點魯迅,可此時的郭沫若反說他們都是非正義的,甚至意氣地將魯迅和陳源、高長虹的論戰,喻之為“帝國主義者間因利害沖突而戰”,是“猩猩和猩猩戰,人可以從旁批判它們的曲直,誰個會去幫助哪一個猩猩?”為逞一時之快,他甚至對魯迅作出這樣的結論:“資本主義以前的一個余孽”,“一位不得志的FASCIST(法西斯諦)”。
郁達夫看了都氣憤不過,認為創造社和郭沫若等情緒化的行為,太不知天高地厚,便仿杜甫《戲為六絕句》,詩贈魯迅,以示聲援:“醉眼朦朧上酒樓,吶喊彷徨兩悠悠。蚍蜉撼樹不自量,不廢江河萬古流。”
魯迅心中雖然也不免凄涼,但還是采取了冷靜的態度,所進行的反擊也僅僅是只言片語,而不是長篇累牘,終不失為仁者胸懷、長者風度。
至今,他們之間還有一段難以理清的懸案。上世紀20年代初,法國作家羅曼·羅蘭致魯迅信,因寄到創造社而沒了著落。1933年12月19日,魯迅在致姚克的信中談及此事:“羅蘭的評語,我想將永遠找不到。據譯者敬隱漁說,那是一封信,他便寄給創造社——他久在法國,不知道這就是很討厭我的——請他們發表,而從此就永無下落。”后來,他還向增田涉談及此事。增田涉在《臺灣文藝》發表《魯迅傳》,披露此事。郭沫若讀后極為惱怒,立刻在《臺灣文藝》發表《魯迅傳中的誤謬》,自作辯正。魯迅在未讀到此文前,即料到郭沫若的態度,他寫信告訴增田涉:“《臺灣文藝》我覺得乏味。郭君要說些什么罷?這位先生是盡力保衛自己光榮的舊旗的豪杰。”
“決不日夜記著個人的恩怨”
1936年,魯迅的肺病日漸加重,體質每況愈下。正在這時,發生了“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和“國防文學”的口號之爭。“國防文學”的口號是周揚、夏衍等人最早提出,并作為上海文藝界的統一政策。
最初,郭沫若對“國防文學”的口號也有不甚了了之處,認為“國是蔣介石統治著”,所以“用‘國防二字來概括文藝創作,恐怕不妥”。但他最終還是接受了“國防文學”口號,而不同意“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的口號,認為魯迅等人“標新立異”所提出的口號,“是錯誤了的理論和舉動”。
魯迅等在提出“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口號時,本想和郭沫若商量,但正如魯迅所說,由于“郭沫若先生遠在日本,被偵探監視著,連去信商問也不方便。”
這年8月上旬,魯迅寫出《答徐懋庸并關于抗日統一戰線問題》,對兩個口號之爭發表了系統的意見,其中一段話說:“我和郭沫若、茅盾兩位,或相識,或未嘗一面,或未沖突,或曾用筆墨相譏,但大戰斗卻都為著同一的目標,決不日夜記著個人的恩怨。然而小報卻偏喜歡記些魯比茅如何,郭對魯又怎樣,好像我們只在爭座位,斗法寶。”
郭沫若讀后深感愧疚,對魯迅“態度很鮮明,見解也很正確”的觀點,表示“徹底佩服”。8月30日,郭沫若不畏酷暑,打著赤膊,在大汗淋漓中寫成《搜苗的檢閱》,有意向魯迅表示歉意。他說:“我自己究竟要比魯迅先生年輕些,加以素不相識,而又相隔很遠,對于先生便每每妄生揣測,就如這次的糾紛吧,我在未讀到那篇萬言書之前,實在沒有摩觸到先生的真意。讀了之后才明白先生實在是一位寬懷大量的人,是‘決不日夜記著個人的恩怨的。因此我便感覺著問題解決的曙光。”
他們的誤解本可以煙消云散,可死神卻一步步地逼近魯迅。10月19日凌晨5時25分,魯迅在上海的寓所病逝。郭沫若和魯迅終未謀面,他們之間的隔閡也沒能冰釋,這成為郭沫若一生的憾事。